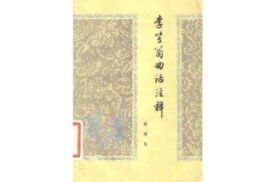李笠翁曲話註釋
李笠翁曲話註釋
《李笠翁曲話註釋》是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徐壽凱。
目錄
李漁《閑情偶寄》中的“詞曲部”和“演習部”,通常被後人稱為《李笠翁曲話》,它是我國古代戲曲理論中最系統、最全面論述戲曲創作和表演藝術的一部理論著作(見《中國歷代曲論釋評》第370頁)。讀完《笠翁曲話》以後,真有一種將其全部手抄一遍的想法,因為,從戲曲理論體系的創立和創新以及對實踐指導的角度而言,《笠翁曲話》真可謂字字珠璣。下面我想以札記的形式,逐句、逐段、逐篇地表述閱讀後的感想,而不是以自己的思路對其進行所謂的系統歸納,因為《曲話》本身的論述順序已經很系統了。感想多的篇章,則多寫一些,感想少的,就少寫一些;再根據笠翁的戲曲理論聯繫一點如今的戲曲現狀,這樣,這篇閑文就有實際的意義了。
《詞曲部》
“結構第一”
笠翁十分重視戲曲創作的文學價值,並且細緻、系統地總結戲曲創作的規律,這是在他以前的戲曲理論家們所沒有做過、或沒有做系統的工作。但理論界存在對李漁曲論評價過高而對《十種曲》評價過低的情況,譚帆先生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說法,“是因為把李漁的曲論和曲作置於不同的參照系之中,即:以湯顯祖到‘南洪北孔’這一系列來觀照李漁的戲曲創作,而從古代曲論缺乏體系性、完整性這一背景來評價李漁的戲曲理論。這兩種評價實際都不完全準確,如果從綜合角度研究李漁,其實李漁的創作(甚至包括小說)與其理論是處於同一層面的,即李漁的戲曲是一種追求輕鬆、圓通、規整的通俗劇,而其曲論則是實現這種創作追求的實踐技法理論。”(見《文藝研究》2000年第1期)。這樣的評價,應該說是不失公允的。
在這一部分中,笠翁指出“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能看出笠翁為學甚為客觀,具有民主科學的精神,他認為“填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把戲曲創作提到與詩文同等的地位,也正因為他重視“填詞”,才會把這個當時旁人認為是“末技小道”的東西進行認真的思考、梳理、研究。《笠翁曲話》對指導戲曲創作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普遍性,就是置於一般文體的寫作,也同樣能夠適用。
對於結構第一的重要性,笠翁以生理(造物之賦形)與建築(工師之建宅)的比喻來說明,而詞采和音律都是“似屬可緩”的。
“戒諷刺”
這一小節中,笠翁提出,戲曲劇本中,不同人物生、旦、凈、丑的行當設置,體現了作者的好惡:“心之所善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凈丑之形。”
還提出對戲曲作者思想境界的要求:“傳非文字之傳,一念正氣使傳也”,戲曲作者應該將“名不與身俱滅”作為自己的追求。笠翁認為,填詞作曲作為一種娛樂方式,將其僅僅作為宣傳工具是不合適的,其內容有託名諷刺、用筆殺人的本意就更是離開了制曲的創作精神,因此,他會在傳奇之前加一段“誓詞”,力戒諷刺。當然,把戲曲的娛樂與諷刺兩種功能截然割裂也完全沒有必要,應該說這取決於觀眾的市場需要,取決於社會歷史發展的形勢,現在有的宣傳部門片面強調寫實,恐怕其實更多關注的也僅僅只是戲曲工具性的教育功能。
“立主腦”
笠翁解釋他自己提出的“主腦”,“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可以說是首先闡述了現在通稱“主題”的主腦的科學涵義,而“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就是說作者立言之本意是為一人一事而設,現在的“主題”至多再提煉一層,即這一人一事表現什麼意思。沒有主腦,“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則可,謂之全本,則為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至今的戲曲創作,仍有這種多中心的現象,雖然創作者認識不同,但如果也經常造成“觀者寂然無聲”的結果的話,就不能不說是創作的缺陷,會使得“有識梨園望之卻走也”。
“脫窠臼”
“脫窠臼”既是對創作必須求新求變的要求,也是成功的訣竅。“取眾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種傳奇,但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其實現在有很多所謂的新戲,都是如此,其“新”只是說明其出現的時間靠後而已。
“密針線”
這一節中,笠翁強調,戲曲的情節前後要有照應鋪墊,“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於埋伏”,能夠經得起推敲。王國維曾經指出元雜劇的情節前後有很多漏洞和不近情理之處,其文學價值只在於“有意境而已”,而笠翁所處的時代,對於當時的戲曲樣式——傳奇的戲劇性的要求,已經提高了一大步,所以他認為“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於元人,獨於埋伏照映外,勝彼一籌”;由此談到傳奇與元曲在藝術上的借鑒問題,“既為詞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於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這其實也是論述了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問題上,不能食古不化,照抄照搬,而是吸收當中的合理之處,“守其詞中繩墨而已”。笠翁認為,“元人所長者,”只不過是曲,而作為曲、白、關目具備的綜合藝術——傳奇,就必須要綜合這三種所長。
“減頭緒”
“減頭緒”和“立主腦”是相關的概念,立主腦必然減頭緒,頭緒減則必然主腦立,“始終無二事,貫串只一人”。其實中國戲曲中意象化了的人物登場,以四小卒代千軍萬馬,點到為止,明白意思即可。老舍先生的話劇《茶館》中雖然人物眾多,但主要人物由壯到老,貫穿全劇,次要人物父子一人扮演,無關人物揮之即去,招之即來,目的只有一個:突出主線,便於觀眾理解,用笠翁的話也可以說是便於“傳”。
“戒荒唐”
正如笠翁在前面論述到的,創作的目的在於傳世,那麼應當在平淡中見功夫,力戒荒唐。要達到這種境界,則必須深入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是來之不易的。這一節中,笠翁還指出了放之文學藝術領域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王道本乎人情。“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由此讓我想到了建國以前,曾在南方紅極一時的以封神戲、濟公戲為代表的大機關布景戲至今所以不傳,笠翁其實於數百年前已經明確指出了原因:沒有本乎人情。對於目下的戲曲創作,是否本乎人情,恐怕仍應該作為指導思想。“使人但賞極新極艷之詞,而忘其為極腐極陳之事”是笠翁認為“最上一乘”的境界。
“審虛實”
對於如何處理虛與實的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笠翁在題中以“審”字明之。“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之謂也。”這是對“虛實”的概念界定。“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這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笠翁提倡“虛則虛到底”,“實則實到底”,“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當前對於一些以“戲說”為主要方式的歷史題材劇的批評,焦點也就多在於此。
“詞采第二”
“貴顯淺”
這個命題的提出,仍是從觀眾角度出發,即作傳奇之前,必須明確受眾群體,為之量體裁衣。“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后得其意思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新時期以來,創作了許多很具哲理性的戲曲劇本,含義確實深刻了,可是票房效果並不見好,恐怕也都存在不夠“顯淺”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笠翁認為元曲是學習寫作劇本的最佳範本。
“重機趣”
笠翁認為,凡事在於意象精神,一靈不滅,自然生機勃發,填詞要有貫穿如細筍藕絲般的靈氣。“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強調了曲作者的悟性和稟賦,其實這符合中國傳統美學精神中“直觀”、“妙悟”的特點,“機趣”是從靈性中來的。
“戒浮泛”
“戒浮泛”與“貴顯淺”是一對必須很好把握的矛盾,關鍵在於“宜從腳色起見”,“常談俗語,有當用於此者,有當用於彼者”,語言需要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而情是曲中貫穿的主線,既是靈魂,又是能夠作為與其他事物的細緻區別,也是笠翁認為容易把握的,要達到“說何人肖何人,議某事切某事”,“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舍景言情”,是“舍難就易”的。
“忌填塞”
笠翁再三強調傳奇“貴淺不貴深”,十分重視戲曲演出的劇場效果,填塞典故、脂粉、直書,就極其影響觀看效果。“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這部分論述,其實已經初涉觀眾學的一些內容了。這一節中,笠翁同意金聖嘆的觀點,即肯定《西廂》、《水滸》的文學價值,也是亮明了自己的藝術取向,這在如今看來,這些古典文學作品的地位不言而明,但在明末清初,對它們的重視則不得不算是一種獨具的慧眼。
“音律第三”
笠翁認為填詞與分股、限字、調聲葉律的文體相比較而言,填詞在操作上的難度是極大的,能“布置得宜,安頓極妥”,便“千幸萬幸”了,要顧得詞品和人情就更難了,所以“總諸體百家而論之,覺文字之難,未有過於填詞者。”關於在創作上的誤區,笠翁以《南西廂》對《北西廂》的改編為例,指出《南西廂》在對西廂故事的搬演推廣上作了貢獻,但在“詞曲情文”上則沒能體現出原著的才情,是抑雅就俗的,所以“有如狗尾續貂”,喪失了原著的精神,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改編標準,也是詞家所重的標準:宮調盡合、字格盡符、聲音盡葉。
對於名著的改編,笠翁持十分謹慎的態度,這對創作而言,是值得推崇的,他認為“誰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時流下?彼文足以傳世,業有明徵;我力足以降人,尚無實據。以無據敵有徵,其敗可立見也。”但是現在大概是因為對劇本的需求太過迫切,所以動輒搬演、翻演名著,成果是豐富了,實質能否保證就不得而知了。而對於不同審美層次的作品,要有區別對待的態度,審美層次的高低並不一定等同於存在價值的有無,有一定的審美層次,就有一定的存在價值,這一點在戲劇批評上是需要明確的,但要實事求是地對劇作的審美層次和存在價值作出判斷。
“恪守詞韻”
這一節中,笠翁認為“合譜合韻方可言才”,說明他還是強調戲曲在詞韻上的規範性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作為古代詩歌的一種形態,戲曲也不能完全脫離這種形式規範,壓韻既能體現動聽的音樂性,又能便於表演者記憶,有著主客觀的審美意義。
“凜遵曲譜”
“束縛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譜是也。私厚詞人,而使有才得以獨展者,亦曲譜是也”,這看似矛盾,實則辯證。傳統也好,規範也好,毫無疑問,是一種陷阱,但所謂創新者,必須經歷落入陷阱——跳出陷阱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可逾越,幾可視為藝術規律,曲譜也正是這樣一種有妙用的“陷阱”。
在本節的結尾,笠翁寫到對於制曲的出新“善惡在實,不在名也”,由此句想到如今一些新劇目標榜自我“創新”、“突破”,宣傳口徑各顯神通,其實比之建國前的一些宣傳語“環球第一”、“青衣鬚生泰斗”等等還有不及之處,是否“創新”,是否“突破”,甚至是“善”是“惡”,在實不在名。
這幾部分講的是填詞制曲的一些具體操作,“當”、“宜”、“難”、“易”、“慎”、“少”等都是相對的用詞,應該理解為針對初學者而發,並非是絕對的金科玉律。用韻的合適優劣與否,直接影響到能否寫出好句,關鍵在於能否悅耳,是否上口。
“賓白第四”
“聲務鏗鏘”
笠翁強調,“賓白之學,首務鏗鏘”,能“人人樂聽”,始終是從表演角度出發要求的。這一節中,他還十分幽默地解決了連用平仄而聲欠鏗鏘的問題,即“用一上聲之字介乎其間,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兩句三句皆去聲、入聲,而間一上聲之字,則其字明明是仄,而卻似平,令人聽之不知其連用數仄者。”理論的價值在於能夠便利地解決實際問題,笠翁指出這一便利的方法后,自信地認為:“一傳之後,則遍地金聲,求一瓦缶之鳴而不可得矣。”
“語求肖似”
這一節中,笠翁道出了自己以制曲為人生至樂的追求,可以在其中享受到自由自在、為所欲為的歡樂。同時提出“肖似”的概念,目的是“勿使雷同”,以生活的真實統一藝術的真實,而情感的真實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又強調“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
“詞別繁簡”
這裡指出“作者只顧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優人,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是不利於戲曲創作的,而自己則是“手則握筆,口卻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完全是以登場演出為主要目的的。有人批評笠翁“填詞既為填詞,即當以詞為主。賓白既名賓白,明言白乃其賓,奈何反客為主”,並不承認賓白的地位,其實仍是以文學視角和標準來衡量戲曲,這是當時無可避免、不必指責的局限,因為即使直到現在,人們評價戲曲劇本仍有這種傾向。
這一節中,笠翁還從賓白創作談到了一般文學創作都需要提倡的個性化規律:“文字短長,視其個人之筆性。”笠翁對於賓白寫作的重視,使得戲曲創作者開始從單一的文學作者向全方位、全能的戲曲編導發展,從而提高了對戲曲作者全能素質的要求。
“字分南北”
這節內容上強調的是“白隨曲轉”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方言與南北曲協調的問題。京劇的字音曾經方言駁雜,在上個世紀之交逐步定型,譚鑫培即在規範京劇字音上作出了京劇創始者的貢獻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也是實踐了笠翁“字分南北”的理論。
“文貴潔凈”
笠翁說:“凡作傳奇,當於開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矣。”我認為這是藝術出精品的規律,藝術作品創作完畢以後,沒有時間的考驗,不可能自命為“精品”。至於什麼是潔凈,並不是以文字少多來定評的。
“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時防漏孔”
“意取尖新”與前面論述過的“重機趣”其實是一個道理,目的就是“移人”,考慮的還是觀眾的接受,“少用方言”也是如此,但笠翁指的是當時通行全國的傳奇,如果現在各地方劇種也這樣效法,就有些形而上學了,沒有方言,地方劇種的特色豈不是喪失無幾,只剩聲腔大源流而已。
“科諢第五”
笠翁把科諢定位在“養精益神”,作用是“驅睡魔”。
“戒淫褻”
在論述科諢問題上,笠翁第一步就強調了尺寸和技巧,遵循的實際上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中和標準,也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本人“風流道學”的特點。
“忌俗惡”
笠翁曲話中對於“科諢之妙,在於近俗,而所忌者又在於太俗”這樣辯證的提法很多,且一般都舉出實例來證明。
“重關係”
“於嬉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愈顯。”這幾句提到忠孝節義,不能簡單地責之宣揚封建道德,而當意會為一種內在需要表達的思想,不過是借忠孝節義舉例而已。笠翁提到的簡雍、東方朔插科打諢的典故,都是“笑中有思索”的優秀範例,這也是科諢不易達到的較高境界。
“貴自然”
科諢也以自然為貴,而非矯揉造作的,“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這源自中華傳統審美習慣,戲曲創作也不能完全脫離這種民族文化審美心理,否則會失去觀眾的承認。
“格局第六”
此處論及的是作劇的一般格式。其中“近日傳奇,一味趨新,無論可變者變,即斷斷當仍者,亦加改竄以示新奇。余謂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很有現實意義,用到對現在很多的“創新劇目”的評價上,也十分貼切,藝術是否創新,不是貼一個“創新”的標籤就行了,重形不重意,藝術生命是不會長久的。
這一系列的程序是傳奇創作的基本格式,正如笠翁所言,“傳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聽人自為政者”,“遇情事變更,勢難仍舊,不得不通融兌換而用之”,不是必須墨守成規的。笠翁曲話雖名為“閑情偶寄”,其實也處處在為同道的後學者十分熱情地提供經驗。
“填詞餘論”
最後一段話中,“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為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神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尚可謂之意乎哉?”,從這裡可以得到的啟示是,過分推敲詞句與作家本意其實容易入歧,最終成為一種臆度。的確賞文有時在於意會,而無一字可言,尤其是中國傳統審美習慣受禪宗的影響很大,對文學藝術的體會經常是“妙悟”而得。
《演習部》
“選劇第一”
在“詞曲部”中,笠翁論述的主要是文學劇本創作方面的問題,因為戲曲是綜合性的藝術,除了文本價值以外,其更多的藝術性體現在舞台表演上,所以,笠翁在“演習部”的第一節的第一句話就是:“填詞之設,專為登場”,開門見山地提齣戲曲創作的目的性。為了實現能夠“登場”的目的,需要按照藝術的規律、科學的方法,訓練出合格的演員,才能真正在舞台上表現出創作者的意圖來。因此,在“演習部”中,用今天的眼光看來,笠翁有很多論述涉及到戲曲教育的若干問題,至今依然能使戲曲教育工作者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
在“選劇第一”的緒論部分,笠翁專門強調了“顧曲周郎”的作用。他認為,“最有識見之客,亦作矮人觀場,人言此本最佳,而輒隨聲附和,見單即點,不問情理之有無,以致牛鬼蛇神,塞滿氍毹之上。極長詞賦之人,偏與文章為難,明知此劇最好,但恐偶違時好,呼名即避,不顧才士之屈伸,遂使錦篇綉帙,沉埋瓿瓮之間。”這樣的情況是“尤可怪者”。笠翁並不把當時有的戲曲演出藝術性低到“瓦缶雷鳴,金石絕響”的原因簡單歸到“歌者投胎之誤”和“優師指路之迷”上,而是認為這都是“顧曲周郎之過也”。用今天的話講,“顧曲周郎”就是內行的、懂得欣賞戲曲藝術的精英人士,他們欣賞戲曲的趣味和態度,有時會對普通觀眾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是導向性的作用,因此,笠翁態度堅決地認為,對於藝術性不高的戲曲作品,應該“使要津之上,得一二風雅之人,凡見此等無情之劇,或棄而不點,或演不終篇,而斥之使罷”,這樣,才會“上有憎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因為“觀者求精,則演者不敢浪習”。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到,笠翁很重視觀眾對觀劇后的反饋,而且是有正確鑒別力的反饋,觀眾的需要就是戲曲演出的市場需要,但要注意,必須是健康的市場需要才是戲曲演出應當順應的。今天有不少有識之士驚呼“戲劇理論批評的缺席”和原創劇目的實際不受歡迎時,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笠翁當年對此類現象的看法,應該是能有所啟發的,作為當代“顧曲周郎”主體的戲劇理論批評工作者們,又是體現健康需要的觀眾主體,要明確自己的任務和職責,要有“主持風雅”的責任感,客觀地評價當代的、特別是原創作品的藝術質量,在輿論上給予廣大觀眾正確的審美情趣的引導,惟其如此,“黃絹色絲之曲,外孫齏臼之詞”的藝術精品才會“不求而至”,而不是恐“違時好”的“隨聲附和”,那就有如“矮人觀場”。
“別古今”
為了能夠很好的“登場”,選好的劇本付排和教學是笠翁擺在第一位考慮的。對於“古本”和“今本”的作用,笠翁認為要準確的對待,既不厚今薄古,也不厚古薄今,而在教授歌童的時候,需要遵循“開手學戲,必宗古本”、“舊曲既熟,必須間以新詞”的先後步驟。在這一小節中,笠翁再次提出了“欲使梨園風氣丕變維新,必得一二縉紳長者,主持公道,俾詞之佳者必傳,劇之陋者必黜”,這裡的縉紳長者,和前面提到的顧曲周郎的責任實際是一樣的,都起到一種引導藝術風氣的作用。
“劑冷熱”
這一小節中“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一語道出了抒情性是戲曲藝術的一大特點,因而戲曲才能成其為“劇詩”。
“變調第二”
有關傳奇的“變”的,笠翁提出了兩點思想,第一是必須變,“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第二是如何變,“貴在彷彿大都”,有“天然生動之趣”,這兩點內容會使人很容易想起梅蘭芳先生有關戲曲改革“移步不換形”的思想,儘管“移步不換形”是梅先生多年從事戲曲創新實踐的體會,但在笠翁戲曲理論中還是能夠發現驚人相似的論述,真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對於“舊劇”的態度,笠翁“喜”的是其形式的美觀完善,“懼”的是內容太過熟悉,其實觀劇是一種見仁見智的主觀審美行為,完全可以只挑想看的看。
“縮長為短”
對於戲曲演出的時間,笠翁認為,完全可以根據觀眾的生活和審美習慣靈活掌握的,並在本節中提出了“縮長為短”的具體操作方法,即用對白和獨白的形式交代原本冗長拖沓的劇情,或是以演摺子戲的方法,“不用全本”,或是根據古本,編一些“稍稍擴充之”的“新劇”,介乎“全本”和“零出”之間,我們似乎可以在這當中窺得今天舞台上仍然活躍的“本戲”、“連台本戲”和“摺子戲”的演出雛形。
“變舊成新”
把一個陳舊的劇本,通過一番拆洗,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笠翁的原則是:“易以新詞,透入世情三味”,而實際的操作是以改科諢、賓白為切入口,對老劇本拾遺補缺,這對我們當前整理和改造傳統劇目,有著很好的啟示,“女媧氏鍊石補天,天尚可補,況其他乎”,只是在於有沒有“五色石”,由此可見,笠翁是很贊成對戲曲乃至於文學創作的革新的,革新是否成功,關鍵在於這種革新是錦上添花還是畫蛇添足。
“授曲第三”
“解明曲意”
笠翁在這一節中指出的“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師講明曲義,師或不解,不妨轉詢文人,得其義而唱”,其實可以理解為是對演員文化素質的要求,不解曲意,“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曲所言何事”,最後導致只能唱“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無曲”的“無情之曲”,這是不可能達到高水平的藝術標準的,“變死音為活曲,化歌者為文人,只在能解二字”,演員的演唱惟有“能解”,方能內外合一,這也可以說是初步涉及到了體驗和表現的統一問題。
“調熟字音”、“字忌模糊”、“曲分言和”、“鑼鼓忌雜”、“吹合宜低”
這幾節中,笠翁還是在授曲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幾點要求,其中根據反切的理論基礎,提出了字頭、字尾、字腹的概念;舉例說明鑼鼓安排的正確位置;以及明確了伴奏音樂與聲樂的主次關係,這些問題既是初學者需要掌握的要領,又是舞台演出時應該遵循的藝術規範。
“教白第四”
笠翁在“詞曲部”中就特別重視賓白在加強戲劇性方面的關鍵作用,這裡又特別指出了賓白教學的難度,他認為,梨園之中,工說白者“百中僅可一二”,與“十之必有二三”的善唱曲者相比,是少的可憐的,這樣的人,“若非本人自通文理,則其所傳之師,乃一讀書明理之人也”,所以笠翁也就特彆強調教授賓白之人,必須有很高的藝術水準。
“高低抑揚”、“緩急頓挫”
對於單一的句子誦讀,正字為主,襯字為客,主高而揚,客低而抑,是笠翁提出的念白原則,其實也就是現代語法語法重音與邏輯重音的概念。而長篇大幅敘事之文,則需要“高低相錯,緩急得宜”,字、詞、句之間要有恰當的對比關係,而不是“水平調”,也就是現在戲曲中的俗語“一道湯”。關於念白注意高低抑揚和緩急頓挫的問題,在教學上,笠翁也提供了標註腳本的具體方法,真是又有理論,又有操作,即便是現在應用,也十分方便。
“脫套第五”
去除陋習,即是脫離俗套,就是一種革新,文學史上的歷次復古運動其實都具有這樣的特點,對戲曲而言,則不論是西子捧心,還是東施之顰,都是不能雷同搬用的。
“衣冠惡習”
齊如山先生曾提出,國劇需要遵循四條藝術原則,其中之一就是“無動不舞”,舞蹈動作在中國戲曲中的淵源由來已久,李笠翁處於明清之際,那時的戲曲主要形態——傳奇,歌舞也是其中的主要藝術表現形式,因而,傳奇的舞台服裝也需要適合舞台上舞蹈表演的實際需要,所以笠翁才會認為,在“歌台舞榭之上”的“婦人之服,貴在輕柔,而今日舞衣,其堅硬如盔甲,雲肩大而且厚,面夾兩層之外……”這樣的情況是“不可解者”,應該是“易以輕軟之衣”,並且明確表示,“予非能創新,但能復古”。歷史往往是驚人的相似的,如今的戲曲舞台上,這種服裝上的“不可解者”仍然再度復活,有的新編劇目,借用西方的經典傳說,女主人公的服裝不但“堅硬如盔甲”,不但“雲肩大而且厚,面夾兩層之外”,連水袖都寬碩無比,自不必說整套服裝的重量了,穿著這樣的演出服,還要要求演員載歌載舞的進行表演,簡直是在考驗演員的武工基礎,恐怕觀眾看了都會和演員一起捏把汗,這樣的“復古”,就不是創新了,而是在笠翁早就批判過的歧途上重蹈覆轍,成為一種新的“衣冠惡習”。
“聲音惡習”、“語言惡習”、“科諢惡習”
以上幾節所反映的,都是在笠翁生活的年代,戲曲舞台上的各種不良的演出陋習,這些陋習往往都是由於因循守舊、故步自封、以訛傳訛,最終約定俗成的原因造成的,笠翁所批判的這些惡習,都仍應該作為我們今天在舞台演出時的警示。
小結:以札記的形式,逐字逐句地梳理閱讀《笠翁曲話》的感受,盡量發表自己個人的看法,而對於一些顯而易見,且大家公認的問題沒有一一贅述,有些聯繫現狀的想法也並不一定與相關的篇章有直接的聯繫,可以算是借題發揮的。當然,逐字逐句,細則細矣,卻難免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憾,好在自己可以用吉光片羽這樣的語詞來藻飾每段札記中的所謂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