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學
上海的作家派別
海派的概念是與京派對立的,最初這兩個名詞是沈從文在上世紀30年代挑起的一場文學爭論中提出的,上世紀30年代寫實小說和抒情小說流派基本上分別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應該是指活躍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廣義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躍在上海的作家派別,包括左翼文學、新感覺派文學、鴛鴦蝴蝶派;狹義的話,就只指新感覺派。
30年代中國沿海商業文化、消費文化的產物。上海在當時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風氣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與中國封建餘毒交雜,社會矛盾尖銳,階級對立嚴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說、“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說、上海灘的腐朽社會風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對海派小說的形成都有影響。魯迅曾說,海派文學為“商”“幫忙”,從中不難看出它的格調。這是一種商業味很濃的文學。海派沒有成立過正式的組織,也未發表過宣言,之所以人們將其視作一派,是由於海派作家在思想傾向、藝術趣味和創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點。對都市文明既有幻滅,又有欣賞的挖掘。
海派作家應該是指活躍在上海周圍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張資平、葉靈鳳、穆時英、曾虛白等。他們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種種愛情糾葛。有人統計1928年前張資平70多萬字的小說中,寫戀愛的就有55萬字。體現都市文化和商業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現代派”詩歌,“新感覺派”小說,以及無法歸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張愛玲、蘇青、林徽因。
廣義上指所有活躍在上海的作家派別,包括左翼文學、新感覺派文學、鴛鴦蝴蝶派;狹義的話,就只指鴛鴦蝴蝶派海派小說主要是以描寫都市生活為題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葉靈鳳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覺派的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和茅盾的《子夜》、張愛玲《金鎖記》《傾城之戀》。
海派文學大體一致的特點:
1.是新文學的世俗化、商業化。小說注重可讀性,迎合大眾口味,是一種“輕文學”;
2.過渡性地描寫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態:夜總會、賭場、酒吧、投機家、交際花等,著重病態生活的描寫;
3.首次提出“都市男女”這一海派常寫的新的主題,造成一種“新式的肉慾小說”;
4.重視小說形式的創新。
5.對都市文明既有幻滅,又有欣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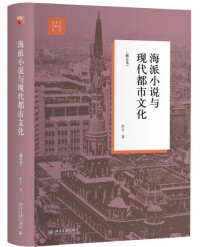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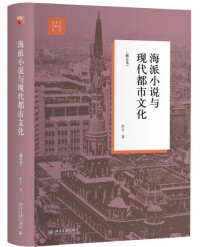
海派文學類書籍
上世紀30年代達到極盛。上海成為文化中心是多層次的。它既是進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創刊、左聯在上海成立,魯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創作……與此同時,上海的一般文化也相應地活躍起來;而反動文化也相當猖獗。還有像《嫖界指南》這樣的妓院文學、色情文化也泛濫成災。五花八門的小報,是上海的又一道“風景”。可以說,當年的上海文化是多方面、多層次、綜合性的複雜的共同體。這也許就是海派文化的一個鮮明的特徵吧。
海派文化肇始於中國畫,亦起源於京劇,作為藝術流派濫觴后,很快漫開至電影、小說、美術教育等領域,乃至社會生活諸多方面,便形成了海派文化這個概念,可見這是客觀歷史的必然產物。
海派文學就是在這個演進的過程中誕生的,可以看到,在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納了吳越文化的和其它地域文化,受到了世界文化主要西方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海派文學。
海派發展三階段:
1.民國初年鴛鴦蝴蝶派
特色:上承《紅樓夢》、《花月痕》的傳統,外受《茶花女》的哀怨與世紀末的感傷的影響,展現出一種落魄者的孤獨感。
2.三十年代現代主義流派
代表人物:張資平、章衣萍;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上海現代派)。
特色:直接取法外國現代主義思潮,如日本新感覺派、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說等,剖析洋場社會人的行為方式和深層意識結構。
描寫“大都會的破體”,呈現出夢魘似的壓迫感。
3.四十年代承言情傳統和現代主義探索的新海派
代表人物:徐訏、無名氏、蘇青、張愛玲
海派兩個主要發展面向:
1.男女兩性間曲折離奇的浪漫故事,與言情小說有密切聯繫。
2.師法外國現代主義新穎活躍而又光怪陸離的表現手段。如新感覺主義。新感覺主義的聽、聞、視、觸、味各種感覺器官,似乎都有某種特異功能,可以直接輸導到被感覺的物體上,賦予它們‘生命感’,從而使來去匆匆的印象組成了感覺流。劉、穆等人把都市風景分解得七零八落、五光十色,在探戈樂的交錯節奏中搖落出濃艷的煙酒味和脂粉氣;他們對都市的感覺帶有光色錯綜感、倏忽感和魔幻感。

海派文學類書籍
繁華與靡爛
“海派”文學的最大特色——繁華與靡爛的同體文化模式:強勢文化以充滿陽剛的侵犯性侵入柔軟靡爛的弱勢文化,在毀滅中迸發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燦爛與罪惡交織成不解的孽緣。當海派文學的淵源時,似乎很難擺脫這樣兩種文化的同體現象,也可以說是“惡之花”的現象。但上海與波德萊爾筆下的巴黎不一樣,巴黎從來就是世界文明的發射地,它的罪惡與燦爛之花產生在自己體腔內部,具有資本主義文化與生俱來的強勢特性,它既主動又單一,構成對他者侵犯的發射性行為,而在上海這塊東方的土地上,它的“惡之花”是發酵於本土與外來異質文化摻雜在一起的文化場上,接受與迎合、屈辱與歡悅、燦爛與靡爛同時發生在同體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衝破傳統的壓抑爆發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慾望,外來文化也同樣在異質環境的強刺激下爆發了放縱自我的慾望,所謂的海派都市文學就是在這樣兩種慾望的結合下創造了獨特的文化個性。
雅俗善惡二元混雜
海派的雅俗善惡二元混雜,來源於上海這個商業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現代都市;另一方面,因為有舊文化的多層包圍,因為現代性質的文化消費並不能排除消極面,現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現出善惡兼備的形態。又由於讀書市場的商業趨利作為重要動因,海派如想無限地求新求奇,就要發展自己的先鋒性;如從眾、從俗、從下,就會追求趣味,反對崇高,擴大自己的通俗特徵。海派的雅俗,還同上海這個都市的讀者分流有關。雅是為了呼應這個城市的雅讀者群,包括洋行、海關、銀行、公司的寫字間讀者,也包括鐵路、郵政僱員的一部分及大中學校師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讀者,有的則構成激進的左翼讀者群)。俗是為了迎合通俗讀物的讀者群體,如低級職員階層、廣大的店員階層和其他居住在石庫門房子里的市民階層。這樣,海派在上海的先鋒文學市場和通俗文學市場兩邊都佔據了位置:表現都市新的觀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學,由先鋒而高雅;俗的支流則表現艷情、恐怖、騙局,收集城市奇聞,製造軟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
海派文學主要有以下三個的意識:
一、都市文化意識
1.書寫與都市對話中的焦慮的情緒體驗、憂鬱感。
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相對於傳統生活方式來說,是座精神孤島;同時都市機械文明使人有被生活拋入急駛的軌道,隨時要倒下來的感覺。
2.漂泊感
切斷了舊有聯繫的新型都市人物,沒有找到新的可供插足的根基,於是成了無根的不安寧的遊魂,漂蕩在十里洋場。‘海派小品里傳達的漂泊情緒反應出他們與革命主潮、傳統文明脫節,找不到自己生存位置,在夾縫中艱難求生的境況’。
二、市民文化意識
1.題材主旨的反崇高性和非重大性。
2.價值取向:享樂式個人主義價值觀與市民意識相契合。
3.思維方式上強調實用理性。
三、文人文化意識
1.兩個主要特點為非純粹性、差異性大。
2.差異性可分為三種:閑適型、批判型、哲理型。
結語:海派文人在大時代的變革中發現自己是小人物並且認同這一身份,同時又不能找到人生的理想支點,重獲文化英雄身份,所以他們在商業社會面前呈現話語失落。
五四新文學發動以來,海派小說的傳統一度受到打擊,新文學發起者對上海作家竭盡嘲諷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創造社發跡於上海,劉半農教授就嘲笑他為“上海灘的詩人”;到了魯迅來概括上海文人時就乾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錘而定音。其實在北京的文人中,劉半農和魯迅都是來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
就在陣陣討伐聲中,一種新的海派小說出現了,那就是創作社的主將郁達夫的小說。郁在日本留學時期開始創作,他的憂鬱、孤獨、自戕都染上世紀末的國際症侯,與本土文化沒有直接的影響。郁達夫對上海沒有好感,對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態度,但這種批判精神使他寫出一篇與上海有密切關係的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這部作品依然未脫舊傳統才子佳人模式,但身份又有了變化,男的成為一個流浪型的現代知識分子,女的則是一個上海香煙廠的女工,也許是從農村來城市打工的外來妹。
郁達夫筆下的流浪知識分子還不具備自覺的革命意識,他與女工對社會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樸素的正義與反抗的立場上。但是隨著20年代大革命風起雲湧,革命意識越來越成為市民們所關心的主題,不但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被卷進去,而且還成為民眾意識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樣一座有著龐大工人隊伍的城市裡,革命風雲不可避免地從此而起。在新文學發展到“革命文學”階段里,上海的作家們沿著郁達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創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學,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在這個城市裡浪漫成性,不斷吸引著摩登熱情的都市女郎,不倦地演出一幕幕“革命加愛情”的活報劇。依然是糾纏不清的多角戀愛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現代版的情慾尖叫,丁玲、蔣光慈、巴金、潘漢年、葉靈鳳等時髦的作家無不以上海為題材,創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學。
30年代的文學史是兩種海派文學傳統同時得到充分發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等“新感覺派”作家的作品;後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但需要強調的是,兩者雖然代表了海派文學的不同傾向,但在許多方面都不是截然分開的。比如關於現代性的刻畫也是《子夜》的藝術特色之一,現代性使小說充滿動感,封建殭屍似的吳老太爺剛到上海就被“現代性”刺激而死,本身就是極具象徵性的細節。同樣,在新感覺派作品里,階級意識有時與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惡之花”結合為一體,如穆時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總會裡的五個人》等許多小說里關於貧富對照的細節描寫就是明顯的例子。
海派文學:
矛盾的《子夜》
《子夜》描寫的上海的民族資本家與外國財團利益的鬥爭細節及其場所(如喪事與跳舞、交際花的間諜戰、太太客廳的隱私、交易所里的戰爭、賓館的豪華包房、麗娃河上的狂歡以及種種情色描寫)體現的是典型的繁華與靡爛同體模式結構。茅盾以留學德國的資本家來代替流浪知識分子,以周旋於闊人之間的交際花代替舊式妓女,其間展開的情色故事從心理到場面都要遠遠高於一般的海派小說。只是作家為了突出左翼的批判立場,才不顧自己對工人生活的不熟悉,特意安排了工人罷工鬥爭和共產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章節,但這方面他寫得並不成功。所以,從本質上說《子夜》只是一部站在左翼立場上揭示現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小說。
劉吶鷗創作《都市風景線》的生活觀照態度歸結為單純和全然,又將這種單純和全然的風格與現代都市的人為造作文化聯繫起來,構成半殖民地上海的獨特的風景線,可以說是對劉吶鷗為代表的海派文學最傳神的寫照。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
30年代是新感覺派與左翼文化把海派文學的兩個傳統推向頂峰的年代,那麼,40年代的海派小說在忍辱負重中達到了成熟與完美。
由於上海是一個中西文化不斷衝撞的開放型的城市,也由於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基本上是一個歐化的傳統,所以海派小說的主人公主要是與“西方”密切相關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消費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說里只是作為消極的市儈形象而出現。在40年代大紫大紅的張愛玲,是一個深受五四新文學教育長大的女作家,但她一開始創作就有意識地擺脫新文學的西化腔,自覺在傳統民間文學里尋找自己的發展可能。
上海這樣一種移民城市,它的許多文化現象都是隨著移民文化逐漸形成的,它本身沒有現成的文化傳統,只能是綜合了各種破碎的本土的民間文化。與農村民間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態出現的,只是深藏於各類都市居民的記憶當中,形成一種虛擬性的文化記憶,因而都市民間必然是個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張愛玲頭一個撿拾起這種破碎的個人家族記憶,寫出了《金鎖記》、《傾城之戀》這樣的海派風格的作品。由於張愛玲對現代性的來臨一直懷著隱隱約約的恐懼感,及時行樂的世紀末情緒與古老家族衰敗的隱喻貫穿了她的全部的個人記憶,一方面是對物質慾望瘋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對享樂的稍縱即逝的恐懼,正是淪陷區都市居民沉醉於“好花不常開”的肺腑之痛,被張愛玲上升到精神層面上給以深刻的表現。張愛玲對都市現代性的靡爛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並消解了兩種海派的傳統,獨創了以都市民間文化為主體的海派小說的美學。
在當代海派文學中,王安憶無疑是最具代表的一個人。在王安憶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已隱約托出她對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的知青,原來是無數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兒女。這座老舊陰濕的城市,包含——也包容——太多各等各色的故事。九十年代的王安憶,則越來越意識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雜擁擠的街市時,才更意識到自己的孤獨與卑微;是輾轉於上海無限的虛榮與騷動間,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協現實的艱難。
由於歷史變動使然,王安憶有關上海的小說,初讀並不“像”當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紀已過,不論是張愛玲加蘇青式的世故譏誚、鴛鴦蝴蝶派式的羅愁綺恨,或新感覺派式的艷異摩登,早已煙消瓦滅,落入尋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這尋常百姓家中,王安憶重啟了大家對海派的記憶。在如此新舊夾纏、混亂迫仄的世界里,上海的小市民以他們自己的風格戀愛吵架、起居行走。他們所思所做的一切,看來再平庸瑣屑不過,但合攏一塊,就是顯得與其他城市有所不同。這裡或許有“奇異的智慧”。套句張愛玲的名言:“到底是上海人!”
王安憶這一海派的、市民的寄託,可以附會到她的修辭風格上。大抵而言,王安憶並不是出色的文體家。她的句法冗長雜沓,不夠精謹;她的意象視野流於浮露平板;她的人物造型也太容易顯出感傷的傾向。這些問題,在中短篇小說里,尤易顯現。但越看王安憶的作品,越令人想到她的“風格”,也許正是她被所居住的城市所賦予的風格:誇張枝蔓、躁動不安,卻也充滿了固執的生命力。王安憶的敘事方式綿密飽滿,兼容並蓄,其極致處,可以形成重重疊疊的文字障——但也可以形成不可錯過文字的奇觀。長篇小說以其龐大的空間架構及歷史流程,豐富的人物活動訴求,真是最適合王安憶的口味。張愛玲也擅寫庸俗的、市民的上海,但她其實是抱著反諷的心情來精雕細琢。王安憶失去了張愛玲那種有貴族氣息的反諷筆鋒,卻有意無意地借小說實踐了一種更實在的海派生活“形式”。
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