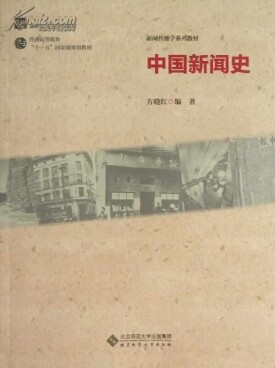新聞史
新聞史
新聞史是指新聞發展的歷史,是評述和研究有史以來人類新聞活動的歷史,重點是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歷史。他提供理論科學的歷史材料,可為當前的新聞工作者作借鑒。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了。這被公認為是我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標誌著我國新聞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階段走上了系統化研究的道路,成為在很長時間裡無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稍後,由他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出版,標誌著中國新聞史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峰。兩座學術高峰的聳立,熔鑄著幾代學人特別是戈公振和方漢奇兩位巨擘的智慧和艱辛。
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幾乎是與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誕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應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1838年寫的《京報分析》。較早對中國新聞事業進行專門研究的文章有: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中土》、1873年《申報》上的《論中國京報異於外國新報》等。這些文章中只有相關的一些文字論及中國新聞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統。較為系統地論述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國各報館始末》,1901年梁啟超的《中國各報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閑話》一書中姚公鶴所寫《上海報刊小史》一節。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國古代報刊與近代報刊的本質差別,啟發人們去思考中國古代新聞事業的起源與變遷,關注尚很年輕的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由此而產生了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不過,作為起步階段的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很粗糙,線索模糊,史料單薄。就是具有中國最早的新聞史專著之稱的《上海報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難找到報刊的確切創刊日期、發行數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語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啟超的文章則更為簡約,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線索。總的來講,1927年前中國新聞史研究尚處於零碎的非系統狀態。
新聞學教育的興起
1920年以後,中國的高等教育中開始設置新聞學專業,最初叫做“報學系”。伴隨教學活動的開展,作為新聞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這期間,雖然沒有專著和代表性的文章問世,但新聞史的教學活動在客觀上卻明顯地促進了新聞史研究的系統化發展,使之邁出了新聞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積累資料、總結規律的新台階。
第一部新聞史專著的出版
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可以說就是這一階段的歷史積累所結出的碩果。在《戈公振年譜》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25年)上海國民大學開設報學系,戈公振任教《中國報學史》……根據多年的教學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資料,戈公振開始撰寫《中國報學史》,將我國新聞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艱辛的勞動。為了證實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寫信虛心向別人求教。為了覓得第一手報刊資料,除了在《時報》刊登‘訪求舊報’廣告外,還不辭辛苦地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等處消磨了大量的時光。10餘年來,他一直不停地廣泛搜集史料,致使擺設在他那書房兼卧室的4張高大的書架上,全部堆滿有關新聞書籍和各種稀有報刊與剪報。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學精神,使同事和朋友們都大為驚嘆。”〔1〕
完成於1926年底的《中國報學史》於1927年11月出版了。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新聞史專著,“系統全面地介紹和論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生髮展的歷史”。〔2〕《中國報學史》彙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國新聞事業產生髮展的大致脈絡,確定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它的出版標誌著中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這在我國新聞史學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此後,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現出全面鋪開之勢,通史、地域史、斷代史、人物史、專題史等方面的專著紛紛問世。據統計,解放前,我國出版的新聞史專著不下50種,絕大多數是1927年後的作品。“這一時期的新聞史研究,在新聞史的各個領域都有所開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基礎。”〔3〕
解放前的徘徊時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國的新聞史研究是有進展的,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大突破。在這50多部作品中,“率爾操觚,展轉抄襲,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調查研究,乾脆閉門造車,連基本的史學求真的精神都沒有。如蔡寄鷗的《武漢新聞史》,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講述武漢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專著。作者記述了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雖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東西,沒有對武漢新聞事業發展的實證考察和總體把握,語言模糊,結構鬆散,全無史書應有的嚴謹態度。這些專著在解放后連再版的價值都不存在了。方漢奇先生曾評價道:“多數新聞史著作的水平還不高,分量也稍顯單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最見功力,影響最大……是舊中國的新聞著作當中唯一有外文譯本的一本書……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唯一再版過的舊中國的新聞史學專著。”〔4〕由此可見,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不僅是中國系統新聞史研究的開山之著,還是解放前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編寫的《中華新聞史》,林語堂用英語寫的《中國報業及輿論史》,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白瑞華所著《中國報業》等書,都是根據《中國報學史》提供的材料寫成的〔5〕”。
解放后的徘徊時期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聞史的研究繼續在海峽兩岸同時進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陸研究的重點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共領導的革命報刊和進步報刊的歷史。這部分歷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響比較深,對古近代報刊史和現代同期其他類型的新聞事業的研究不足。還談不上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全面開展。台灣在此期間累計出版的新聞史方面的專著有30多種,但同樣缺乏深度與力度。台灣在新聞學的教學中長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台灣新聞史專家朱傳譽在1966年曾無奈地說過:“儘管戈著缺點很多,不合時宜,但他以後,國內始終沒有出現過第二本系統性新聞史著作。”該年出版的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應該是台灣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閱此書不難發現,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舊說,沒有進行應有的補正,在現當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體例上,它分主題進行闡述,“無異專史”,違背了通史按時間順序進行全面闡述的基本做法。由於台灣偏居一隅“現存大陸出版的報刊不多”這一先天不足,加上對大陸明顯的敵對情緒,無形中限制了台灣新聞史研究的整體水平。總的來講,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規範、紮實,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整體、客觀的考察。中國新聞史研究處於徘徊狀態。
陷於徘徊的原因
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史料豐富而不確切,后被考訂出有200多處錯誤;闡述系統而不深入,“敘述不免偏頗,如上海報業介紹較詳,其他地區則顯簡略”;並且,“戈著體系欠完整,任何學術專史著作,應以時為經,以其發展為緯。戈氏強分中國新聞事業為官報獨佔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以後、報界之現狀等立章,實屬武斷,與發展史實多所不合”。〔6〕不難看出《中國報學史》本身尚屬不成熟之著,有待發展與完善。
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
經過30多年的積累,1978年夏,方漢奇開始了《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寫作。1981年《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了。在這部50餘萬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國早期的報紙”為題,對我國自唐代以來的新聞事業進行了必要而簡略的闡述,隨後將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間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狀況進行整體描述。此書一出“在海峽兩岸新聞學界曾經引起一定影響,也受到了國外新聞學界的注意”,〔7〕被公認為是,自戈著之後“50年來第一部有影響的新聞史專著”。〔8〕
從《中國近代報刊史》所覆蓋的內容跨度來看,它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基本一致。但比較兩著,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質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擁有上,戈著之所以能歷經半個世紀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它的材料的豐富性,在當時的新聞史專著中確屬少見。1928年5月“天津《大公報》文學周刊刊載署名‘素痴’的《評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文章‘……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來著作之罕見者……’”。〔9〕不過,作為開山之著,它又有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考證。相應地,因事實錯誤而得出的結論也不能成立。方著則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來的新聞史研究的成果,對近代報刊進行了全面的考證,糾正了以往新聞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錯誤,可以說,該書是在全面糾正以往錯誤的基礎上寫就的,不僅對戈公振書中的200多處錯誤一一予以糾正,還糾正了50年來新聞史研究中的各種錯謬之處。此外,書中大量補充了新的史料。考訂之精良,單從註釋中就能看出:作者在敘述1902年到1911年這十年間我國新聞攝影發展的情況時,說:“清朝政府原來對新聞攝影活動多方限制。”在這句話的註釋中,方先生舉了直隸總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緒靈車時,因沿途攝影而被彈劾“大不敬”、被革職一事作解釋,說明當時布衣在攝影方面更是動輒得咎的情形。其次,從戈公振以來,人們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總是粗線條的,材料準備不足,總體把握不夠。而方著則對這兩方面都實現了突破。方漢奇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細膩而全面。不僅有對重大事件與人物來龍去脈的詳細闡述,還有對新聞業務點點滴滴的發展狀況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總趨勢,同時又使人對各個階段發展的特點與重要的細節有深入的把握。基於對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國新聞事業在各個時期發展的總體內容以及特點的不同進行了規範而又科學的分析,使人們對此階段新聞事業發展的了解清晰明了。從而在體例上確立了新聞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時間為經,按新聞事業自身發展中所顯示的主題不同,分別划列出各個時期,按嚴格的歷史分期依次進行陳述。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聞史專著中所不曾確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實,不輕易褒貶人、事。真正做到了論必有據,“論從史出”,無一字空談。方著中對新聞史的分析與論證一般都是拿事實來說話的,持論公允、客觀,有說服力,能使人了解到歷史的本來面目。基於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說這是一部經得起考驗的信史。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材料的充分佔有、體例的完備這些學術規範上來看,還是從指導思想的明晰與科學、持論的公允與客觀這些新聞史研究的科學化程度來看,方著都是一部新聞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僅為社會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統的近代報刊史,他還樹立起了新聞史治史的科學精神;充分地佔有真實的材料,以辯證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去探討新聞史發展的特殊規律。
從此,中國新聞史研究走上了《中國近代報刊史》開拓的科學道路,開始結出累累的碩果。以《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為代表的斷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國現代廣播簡史》、《新華日報史》為代表的專題史、以《鄧拓傳》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為代表的編年史等等新聞史著述在以後的十餘年間相繼問世,填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一個個空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中國新聞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開展的新里程。改革開放20年來的新聞史研究,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聞史專著的總和,而且在質上與此前的新聞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徵:治史嚴謹,注重考證;論述系統、周密;反映歷史客觀、忠實。總體上展現出成熟、科學治史的新風貌。
戈公振以其考證較為翔實、論述較為系統的《中國報學史》開闢了我國新聞史整體性研究道路。此後,在經歷了五十餘年的摸索之後,終於有了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方著以其考證之精良、體例之完備、總結之全面、持證之客觀,樹立起了新聞史研究應當遵循的科學的方法與思路,是我國新聞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學的標誌。戈公振與方漢奇分別開啟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不同階段,是我國新聞史研究歷程上的兩個里程碑。
從中國開始啟動系統化新聞史研究到新聞史研究的成熟發展,期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比較兩個里程碑之間的變革,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啟示:新聞史研究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展開的,其開展的程度與總體水平,無形中要受到環境因素的制約。
其一:新聞事業本身的充分發展是新聞史研究得以開展和深入的前提。
1920年之前,我國沒有出現系統的新聞史研究,根本原因在於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育不足。當時我國近代新聞事業雖然有了百年的歷史,但新聞傳播真正對中國社會產生全面衝擊則是始於戊戌變法期間。到辛亥革命時期,我國報紙與刊物的分離明顯,新聞事業的業務特徵與各種社會功能充分顯示出來。新聞事業開始走向了成熟。從而才萌發了為新聞事業系統做史的必要與意識,開始了系統新聞史的醞釀。而當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空前繁榮,為新時期的新聞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課題內容,從而促進了新聞史研究的領域拓展和步伐加快。
其二:社會環境的相對穩定是新聞史研究得以順利開展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外部條件。
在戈公振之後到建國之前的歷史中,中國新聞事業本身是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電子媒體的產生與發展為新聞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鮮的課題。但這期間之所以沒有產生突破性專著,根本原因在於社會動亂頻仍。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戰事接連不斷。在戰火中收集資料是極其困難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離開了必要的史料,新聞史研究是無法進行的。新聞史研究既受制於這些外部條件,更受一些內在因素的影響。首先,“新聞史是歷史的科學”。〔10〕開展新聞史研究以佔有豐富、翔實的資料為前提。離開了必要的史料積累,不可能有突破之著。台灣近幾十年來,在中國新聞事業史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對中國近現代新聞事業史的研究始終不夠深入,主要是無法充分地佔有這方面的材料所致。其次,研究新聞史的指導思想也決定了新聞史研究的深度與力度。1949年到1978年大陸與台灣新聞史研究中受限制較大即是指導思想的約束。大陸長期受“左”傾思想的影響,致使新聞史研究不能全面開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味強調新聞事業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抹殺了新聞事業的其他特性,限制了研究者對新聞事業本身規律的探索。台灣則受地域限制及對大陸敵對態度的影響,折射到新聞史研究上就是不能客觀實際地對待歷史。台灣新聞史專著中對大陸稱“匪”,一味地污衊,不能解釋歷史與現實。總之,沒有了科學治史的態度,也不可能有科學的成果。而方著之所以成功,首先在於思想的解放。這一點在方著中有明顯的體現。《中國近代報刊史》的風格前後稍異,後半部展開得充分而精彩。方先生在該著《後序》中提到“斷斷續續寫了兩年,當時乍暖還寒,‘左’的思想和‘兩個凡是’思想的束縛還沒有完全解除,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後不一……前緊后松,很多地方沒有充分展開。”可見,指導思想對新聞史研究的影響。
自《中國近代報刊史》之後,我國新聞史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環境寬鬆,社會穩定,正是“盛世修史”的好時機。在充滿希望的21世紀,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肯定會創造前所未有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