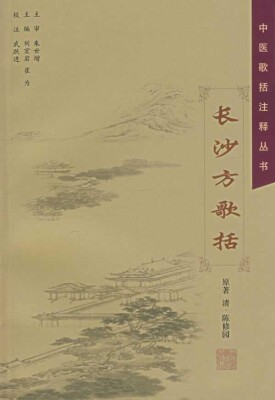勸讀十則
勸讀十則
“勸讀十則”載於《長沙方歌括》卷首,是陳修園對張仲景《傷寒論》的辨證精神,及其方劑應用價值與臨床經驗的深入體會,寫成十條“勸讀”原則,告誡後人應熟讀與應用,繼承與發揚《傷寒論》。陳修園的“勸讀十則”起源於清朝,流傳至今,所涵內容豐富,見解實用,古今皆宜。尤其對醫學界人士啟迪深思,所述醫術醫德給後人留下深刻的教誨。
陳修園(1753~1823),中國清代醫學家。父陳廷啟,號二如,早逝。祖父陳居廊,博學通醫。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就讀於福州鰲峰書院。苦攻經史之餘,還鑽研醫學,專心研究古代醫學經典,頗有心得。見原書文辭深奧,遂加以淺注,或編成歌訣,著《傷寒論淺注》、《長沙方歌括》傳世。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舉。後會試不第,寄寓京師。適光祿寺卿伊朝棟患中風症,手足癱瘓,湯水不入,群醫束手。念祖投以大劑而愈,聲名大噪。后回長樂,任吳航書院山長。
嘉慶三年(1798年),主講泉州清源書院。嘉慶六年(1801年),再入京會試,不第,參加大挑,成績甲等,以知縣分發直隸保陽(今河北省保定)候補。時值盛夏,瘟疫流行,念祖用淺顯韻語編成《時方歌括》,教醫生按法施治,救活甚眾。直隸總督熊謙得痹症,手指麻木,延及臂腕。念祖教以常服“黃芪五物湯”,並開方補腎養肝,病遂愈。其間還治癒當地婦女陰挺症。嘉慶十三年(1808年),吏部郎謝在田頭項強痛,心下滿,小便不利,服表葯無汗,反而煩躁,六脈洪散。經念祖處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再投以梔子豉湯,病不再發。
嘉慶十七年(1812年),署磁州,改任棗強,升同知,擢代理正定知府。公務繁劇,仍撰寫醫書,為人治病。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以年老請休,在福州石井巷井上草堂講學,培養醫學人才;並曾治癒琉球國王之風症。
在醫學理論上陳修園特別推崇張仲景,是維護傷寒派的中堅人物之一,也是繼張志聰、張錫駒之後最有影響的尊經崇古派。在傷寒研究的爭論中,他極力反對方有執、喻嘉言的“錯簡”說,認為王叔和重新編注的《傷寒論》已經把張仲景的學說完整地流傳下來,不能隨便改動和取捨。他在研究《傷寒論》、《金匱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傷寒論淺注》、《金匱要略淺注》和《傷寒醫訣串解》,前兩書曾三易其稿,史書稱其“多有發明,世稱善本”。他還將《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中的方劑和治法編成《長沙方歌括》、《傷寒真方歌括》與《金匱方歌括》,易於記憶、習誦,對後學理解《傷寒論》、《金匱要略》很有幫助。雖然有人說陳修園註疏古籍有獨到之處,但他上述著作的廣泛流傳主要是因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淺出的特點,為後學者、特別是初學者研究張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門的階梯。
陳氏“勸讀十則”,根源於清,流承至今,所論內容豐富,見解明確實用,古今皆宜。此乃啟迪深思,備受人用,醫術醫德醫患,收益久遠矣。
勸讀仲師之《傷寒論》原文,深入理解其精神,強調臨床應用作者對《傷寒論》十分推崇,倍加讚揚。如說:“明藥性始於《神農本經》,論病情始於《靈樞》、《素問》,以葯治病始於伊尹湯液,迨漢仲師出,集伊聖及上古相傅之經方,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經》二書。”《傷寒論》總結了秦漢以前的中醫藥理論,始創臨床醫學辨證著作,開闢了理法方葯的辨證論治體系,奠定了醫學發展基礎,故奉勸後世“讀仲師書為第—勸”。
勸後世醫家遵循《傷寒雜病論》的理論,違背者要“知過必改”陳氏進一步強調仲景書的實用價值,批駁後世醫家由於學習不夠,應用不強,而存在許多弊端,要知過必改。如說“仲景書文義古奧難讀,即劉張朱李四家,雖尊仲聖之說,鮮有發揮,更有庸妄者,顛倒是非”,又誤認為張仲景只“專攻傷寒,其桂枝、麻黃,只行於西北,宜於冬月”,只是“以芎、蘇、羌、獨、荊、防等為感冒切用之品;以補中、歸脾、八珍、六味等方為雜病平穩之方”,而且“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熱為陰虛,多寒為陽虛,自誇為挈領提綱之道,究竟偽術相師,能愈一大病否?”這些無知之談,是很缺乏修養的,而且有錯誤之處,故“以知過必改,為第二勸”。
要知經方之療效神速,若用之得當其效如桴鼓《內經》有記載:“一劑知,二劑已”,即言服—劑全料就有效,服兩劑則病癒。《傷寒論》也說“一服愈,不必盡服”,如桂枝湯服法,一服即服藥的1/3,如果服1/3葯就痊癒則不必將全劑都服完。“可知古人用藥,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劑、1、2劑之間”,即可治癒,說明經方用之得當,其效神速。陳氏指出後世有不同之見,如“薛立齋醫按云:服30餘劑及百劑效。”又如“李士材雲備參五斤,期於三月奏效。”這是服藥的效果,還是病氣已衰而自愈呢?所以應當奉勸用藥不當之人,應精益求精,深入辨證,用方用藥切當,為第三勸。
強調《傷寒論》治療原則是“存津液”三個字,勸告後世醫家治療傷寒,不要耗竭津液如說:“《傷寒論》113方,是以存津液三字為主。”“試看桂枝湯和平解肌,無一非養液之品。即麻黃湯輕清走表,不加姜之辛熱,棗之甘壅,從外治外,不傷營氣,亦是養液之意。”對後世醫家治傷寒,應用“芎、蘇、羌、獨、荊、防、蒼、芷,苦燥辛烈,大傷陰氣。”最簡略的是有些醫生的習氣,認為“二陳湯為發汗平穩之劑”,但是“方中陳皮之耗氣,半夏之耗液,茯苓滲利太早,皆所以涸其汁源,留邪生熱,以致變成煩躁大渴,譫語神昏等證,所謂庸醫誤人者此也。”至於《金匱》之方劑,其主要的宗旨,是“調以甘葯”四字。如後世的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及四物湯、八珍、十全、歸脾、逍遙等劑,都頗得“甘調之意”。勸導後世醫家治病以扶正氣、存津液為主,明經方之有利無害,這是第四勸。
勸告後人不要輕易懷疑仲景之方,可大膽應用“仲師為醫中之聖人,非至愚孰敢侮聖”、“所疑者其方也”,方中無見證治證之品。並且“銖兩升斗畏其大劑”,因而不敢輕易試用。關於用藥劑量的大小不同,是從“宋元諸家”開始,“而極於明之李時珍”。但能讀《本經》而通曉藥性者,也只是知道方中的三四味葯的神妙。況且古今的度量衡有不同,從上古到漢代,從漢到今(清)的劑量也不同,漢代的劑量僅是今日的十分之三,每劑葯分三服,因此,一服也不過是七八錢而已,這較之時方其劑量還為輕。因此,應用經方要通曉藥性,而且以今日的度量衡折算,是不可不知的,這是第五勸。
勸導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思想應用經方治病應靈活掌握,辨證應用。“先入為主,人之通患也。”如“桂枝湯、小柴胡湯,無論傷寒雜病,陽經陰經,凡營衛不和者,得桂枝湯而如神;邪氣不能從樞而外轉者,得柴胡而如神”,而又有人迷惑於“春夏忌桂之說”、“邪在太陽,誤用柴胡反致引入少陽說”,以及“李時珍虛人不可多用”,“張景岳制五柴飲列於散陣(解表劑)”中,都是對桂枝柴胡應用較偏,而先入為主,以致應用不敢用,而不知《神農本經》將柴胡、桂枝列為上品,“久服可以卻病延年”現在有些人不相信《神農本經》而相信今世醫家之言,是很奇怪的。作者又從本身經驗論述,“余用桂枝湯,萬無一失”。而用量“自三錢,亦用至八、九錢,而效者”。至於用柴胡一般不超過四錢,而且浙江江蘇醫生,每用時必以鱉血拌蒸,最多也不過二錢,這都是先入為主的思想所致,而《傷寒論》用柴胡到八兩,“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緩必須重用。”其它還有“細辛、五味,用不過一錢,大棗不過二枚,生薑不過二片,種種陋習,皆違經旨”,所以作者曰:“吾願同事者,先進去市中徇人惡習,而以愈達愈上。”為第六勸。
經方運用得當可“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醫之道也”,這是醫生的天職,若庸醫無術,則病家待弊,究其原因,多為“雜法所誤”,而沒有按仲景法治療,如按仲師法:“四逆、白通以回陽;承氣、白虎以存津,助其樞轉,運其針機,臟腑調和,統歸胃氣,危急拯救”,不單靠人蔘,亦可救其十中二三。作者體會到行醫30餘年,深知經方的效果,可造化生機,祛病延年而起死回生,即要“知經方之權奪造化”,這是第七勸。
勸導學經方要“溫故知新”陳氏說“經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一一於經方查對,必別有神悟。”可見晝日臨證,夜晚讀書,是良好的方法,只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溫故”承經方之旨,神悟受納方能“知新”。這是第八勸。
樹立仲景學術思想為臨床醫學之本仲景是“醫門之仲師,即儒宗之宣聖”因此,可作為衡量後世醫術的標準和分水嶺,“凡有闡揚聖訓者則遵之,其悖者則貶之。”如後世金元四大家之作,有成就也有不足,如劉河間雖然有偏重於苦寒攻下之弊端,“尚有見道之言”;朱丹溪雖然沒有深入研究致病之根源,但“卻無支離之處”;張子和之作,“瑕瑜參半”;最後是李東垣,其“論以脾胃為主,立方以補中為先,徇其名而亡其實,燥烈劫陰,毫無法度。”後世醫著中還有一些人,只是“載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術,邪說流傳,至今不熄”,這正和仲景治傷寒“養津液及調以甘葯之法相反”並對後世醫家也有不同評論及批評。應以仲景學說為正宗,不能有“朱紫之亂”,故奉勸後世讀書當“專一不雜”為第九勸。
說明撰寫“勸讀十則”的想法和目的寫以上意見是作者直言不諱,對於醫學各家門戶之見,藉仲景先聖之功,溯委窮源,對於那些“陷溺未久及穎慧過人者,自必悔而就學”,以經典著作為基礎原則,則不至於走的過遠,所以,作者的目的,“凡我同人,務宜推誠相與,誠能動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則以有言無隱,和氣可親”為第十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