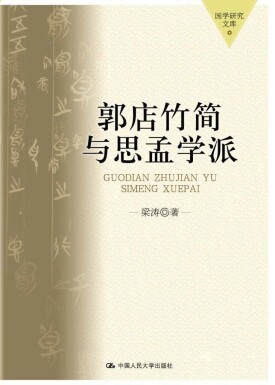思孟學派
思孟學派
嚴格說來,思孟學派應該是子思學派和孟子學派的通稱,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聯繫在一起,稱為思孟學派;但在歷史上二者則可能是分別獨立的,當“孟氏之儒”出現時,“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於只是在墨守師說,缺乏創造,所以真正發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後起的孟子學派。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學派這樣既有著顯赫的地位,又產生不斷的爭議。說它地位顯赫,是因為至少從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傳,居儒學大宗;說它爭議不斷,乃是因為對於“思孟學派”具體何指,其特色為何,甚或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個存有爭議的問題。歷史學家說,我們所知道的只能是流傳下來的歷史。
我們說思孟學派在歷史上爭議不斷,決不僅僅是因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後已經失傳,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後代學者在爭論中往往摻雜了自己的意志、觀念,他們真正關注的也許並不是思孟學派的真實面貌,而是思孟到底從夫子那裡傳下了什麼樣的“道”。在這種情況下,典籍的遺失、缺乏固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理解、判斷,但又何嘗不會為後人的借題發揮、“六經注我”提供了便利;而這種借題發揮、“六經注我”雖然不無其自身價值,但它終歸已不是思孟學派的原貌。首先要從春秋戰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學派的演變、發展;同時更要將其原有的內容與後人的發揮區別開來,終歸我們探討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孟學派,而不是作為“道統”化身的思孟學派。
那麼,思孟學派是如何提出來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讓我們首先對這些問題作一番探討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確把思、孟作為學派看待的應該是戰國後期的韓非子,他在《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這裡雖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們看作“儒分為八”中的兩派,對於二者關係如何,則根本沒有提到。不過韓非子“儒分為八”的說法也有一些讓人費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說的八派並不處於同一時期,最早的子張、漆雕氏(漆雕開)等屬於孔門的七十二子,約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孫氏(荀子)則已到了戰國後期,前後相差約二百餘年,所以韓非所說的“儒分為八”顯然不能僅僅作為並列的學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顏氏之儒”,孔門弟子中除顏回外,還有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仆、顏何、顏濁鄒等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世家》),但多數學者還是傾向認為是指顏回一派。如果是這樣,那麼顏氏之儒就應該是由顏回弟子創立,但又尊奉顏回;因顏回先於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樂正氏之儒”,先秦儒家為樂正氏者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和孟子弟子樂正克,前人考訂樂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麼,“儒分為八”中有曾子弟子創立的樂正氏之儒,卻沒有曾子;如果是後者,則孟子與其弟子分別創立了兩個學派。此外,韓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並不能概括孔門後學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賤儒”共有“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韓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張氏”一家;還有,《孟子·離婁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提到的“從弟子百人,設取予去就”的澹臺滅明等,顯然也都是開宗立派的大師,但均沒有被韓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費解,搞不清韓非分派的根據是什麼。與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則思、孟前後相續,認為二者具有內在的聯繫。
略法先王而不知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說法,子思、孟軻不僅前唱后和,主張一種五行說,而且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擁護。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學的代表人物,他的說法自然有一定根據,所以後世所謂的思孟學派實際也就是由這條材料而來。那麼,如何看待韓非與荀子不同的說法呢?我們認為這可能同二者的著眼點不同有關,韓非所說的可能是歷史上產生的具體學派,而荀子強調的則是學派間的歸屬和聯繫。
我們知道,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主要是通過收徒設教的形式,據劉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歲,始教於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設教,后不斷通過這種形式,孔子在其門下匯聚了龐大的弟子徒眾,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學派。從《論語》、《禮記》等典籍來看,孔子與其弟子的關係往往是寬鬆、自由的,弟子由於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來到孔子門下;也可能由於某種原因離孔子而去,儒家內部似乎始終沒有形成嚴格的組織系統,更沒有對學派的傳授作出明確規定,體現了儒家不同於一般宗教的特點。所以孔子以後,儒家內部雖然出現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過收徒設教的形式。當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門下聚集了一定數量的弟子,在社會上產生一定的影響,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便形成所謂的“派”。這種“派”的數量自然會是很多,遠遠不止於八家,韓非的“儒分為八”只是後人一種籠統、模糊的印象,並不能以此為據。同時,由於韓非乃法家人物,對儒家情況不可能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從旁觀者的立場將其分為兩派,至於二者關係如何,自然不是他所關心的了。荀子的情況則不同,他主要是從儒家內部的派別劃分來看待思、孟的關係,認為二者在儒家內部處於同一思想路線。在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稱讚其為“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是“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認為自己即是出於仲尼、子弓之後。因此,子思、孟軻與仲尼、子弓實際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內部的兩條不同路線,他將思、孟聯繫在一起,並給予批判,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就荀子而言,他也並沒有肯定思、孟就是一個學派。
荀子在批判思、孟時,特別說到“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認為出於仲尼、子游之後。對於這個子游,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子弓之誤,理由是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雲‘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王先謙《荀子集解》引)。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別處之所以屢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師承;本處之所以獨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統。這是絲毫也不足怪的。”所以按照荀子的記載,子游應該是對思、孟產生過影響的重要人物。子思與孔子年齡相差較大,不可能接受孔子的教誨,子思的父親孔鯉也早卒,說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響,完全符合情理。不過從思、孟的言論來看,他們似乎較少談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談到孔子的另一個弟子曾子。如在《禮記》中,子思常與曾子討論孝親執喪;孟子也常將曾子、子思並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離婁下》)這裡的“同道”是說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並不是說在傳授“道統”,但也說明在孟子眼裡,二人確實具有某種聯繫。此外,《孟子》一書提到曾子九次,對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筆下,曾子常常被描繪成剛強、弘毅,具有獨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謂子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捨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公孫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孫丑下》)
這裡的曾子顯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響,“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與曾子以“忠恕”釋“一以貫之”相同。正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往往認為思、孟實際是出於曾子一派。不過仔細分析,以上兩種觀點其實也並不矛盾。前面說過,子思雖為孔子之後,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經幼年喪父的變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這樣一來,與其發生聯繫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數,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較為重要者,子思與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荀子說思、孟一系曾經推崇子游,應該是有根據的。至於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則較為複雜,除了對思、孟產生影響外,可能與荀子也具有某種聯繫。據筆者統計,《荀子》一書多引曾子的言論,對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視(詳見第三章);而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吳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學於曾子門下,這樣看來,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從曾子的思想來看,孟子雖然稱其“守約”,突出了其重視內在精神的一面,但史書也不乏曾子有關論禮的記載,說明他對於外在禮儀同樣十分關注,這樣以後的孟、荀實際都有可能與他發生聯繫,產生共鳴。而可能正是這個原因,當荀子在對儒家各派進行批判總結時,便從自身的立場出發,只將子游劃歸思、孟一系而不談及曾子,但就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對思、孟產生過共鳴。
孔子死後,儒家分裂為八派。據韓非說,他們是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為首的八派。①其中孟氏即孟子,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樂正氏即孟子的弟子樂正子。如此說來,子思、孟氏與樂正氏三派儒者當是一派,即思孟學派。這一學派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與孟子合在一起來評論,已經把子思與孟子作為一個學派來對待。荀子離孟子的時代那麼近,他的話當是可以相信的。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也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②與荀子之說是一致的。當然在歷史上,孟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子思。
子思(約公元前492-前431年)姓孔名伋,他是孔子的孫子,一般認為他是曾子的弟子,也有人說子思出於子游氏之儒。《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
子思提出的"誠"和與此緊密相連的五行說,是思孟學派思想的重要內容。"誠"是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也是道德準則。子思說,"誠者天之道",③即"誠"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還認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說,"誠"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還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說,"誠"是產生萬物的本源。如果沒有"誠",也就沒有萬物。也就是說,主觀上"誠"是第一性的,而客觀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誠"這種主觀精神來說明世界的產生和發展的學說,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
子思的思想具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神秘性。《中庸》二十四章說:"至誠如神"。達到"誠"便具有無比神奇的威力。甚至還認為,只要"至誠",就可以預卜凶吉。國家將要興旺,就一定有禎祥的預兆。而國家將滅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現。可見"誠"與天、鬼神是一脈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認為,達到"誠"的途徑,是要"盡其性",進而"盡人之性",再進到"盡物之性",這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矣"。①這一過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這種思想對漢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較大的影響。
子思提出的"誠",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殷代滅亡之後,為了說明周為什麼能夠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來修補天命思想;春秋後期,天命思想搖搖欲墜,孔子提出"仁"這種道德規範,企圖用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仁"本身雖然沒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誠"的提出,則是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並把上帝泛神化。這種思想是將孔子倫理思想擴大化,從而成為更廣泛、更唯心主義化,以至趨向宗教性的思想。這是思孟學派對儒家
①《左傳》襄公十年。
②《左傳》襄公三十年。
③《中庸》二十七章。
①《左傳》哀公十七年。
思想的重大發展,從而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學的基礎。
子思的"誠"與五行說有密切的關係。鄭玄注《中庸》一章"天命之謂性"時,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即是說,"天命之謂性",包含了五行的內容。章太炎的《章氏叢書·子思孟軻五行說》,認為這是子思的思想。這兒需要說明的是,《中庸》里的"誠"就是"信"。子思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①由此可見,"誠"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則信"的土居中央。可見"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誠"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誠"來代替"信"更說明問題,更易使人理解。子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樣,但其中五行說的內容確是存在的。
《孟子》中的五行說,從表面上看難以發現,但事實上是存在的。
據龐朴研究,《孟子·盡心下》所說的"仁"、"義"、"禮"、"智"、"聖"就是五行。因為從1973年12月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書中,提到"聰"、"聖"、"義"、"明"、"智"、"仁"、"禮"、"樂"等幾種道德規範,並用"五行"和"四行"加以概括:稱"仁"、"義"、"禮"、"智"為"四行",以"仁"、"義"、"禮"、"智"、"聖"為五行。上述八種道德規範,正是《莊子·在宥》所反對的。賈誼《新書·六術》說:"人亦有仁、義、禮、智、聖之行。"這正好是五行,再加上樂即是六行。根據以上材料,則《孟子·盡心下》所說,"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人"字衍)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段話就容易理解了。這裡所說的"仁"、"義"、"禮"、"智"、"聖",與前面《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書和《新書·六術》所說的"五行"是一樣的。可見,《孟子》中的"仁"、"義"、"禮"、"智"、"聖",正是孟子五行說的內容。②"聖"是什麼呢?應該就是"誠"。孟子說,"聖人("人"字衍)
之於天道也",與孟子在另一個地方所說"誠者天之道也,"①聯繫起來看,"誠"就是"天道",因"誠"與"聖"處於相同的地位。《中庸》說"從容中道,聖人也。"與《孟子·離婁上》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也",意思是相同的。可見,"聖"就是"誠",就是中道。它在五行中所處的地位,相當於"土神則信"的中央。事實上,"誠"就是"信"。
從這裡可以看到思孟學派五行說的發展變化:子思首先提出"誠"
的哲學概念,它是居於五行之中央位置的。孟子繼承子思的思想,把"誠"發展為"聖",並使思孟學派的五行說定型為"仁"、"義"、"禮"、"智"、"聖",以至於為西漢以後的人所沿用。
思孟學派的五行為"仁"、"義"、"禮"、"智"、"聖",這些概念本是儒家經常使用的。那麼荀子為什麼要批評它"甚僻違無類。
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呢?關鍵在於思孟把這五個概念不顧其"類"的不同,加以排列為"仁、義、禮、智、聖"的五行順序,而成為閉約的體系,並將其納入人心(即"仁、義、禮、智根於心"),歸入人性
①《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①《左傳》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人性的四端),委諸於命(形成"盡心"--"知性"--"知天"
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這就賦予了五行說以幽隱的內容,從而成了他們的"按往舊造說"。
思孟學派還認為,在"仁、義、禮、智、聖"這五行之中,"仁、義"是一組,而其中"仁"又是根本的。"智、聖"是一組,而其中"聖"更高明。這兩組中,前者又是根本,後者是對前者的理解和力行。"禮"處於兩者之間,正合於《禮記·仲尼燕居》所說的"禮所以制中"的原則,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仁、義、禮、智"四行,以人為對象,而"聖"獨以天道為對象。這些確實是"幽隱"、"閉約"的。荀子有如此批評,就不奇怪了。①總之,思孟學派的五行說,把構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賦予了倫理道德的內容,於是就把過去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五行說唯心主義化了。而這種思想對陰陽家鄒衍有很大的影響。
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在2005年8月青島“易學與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布:“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其專著又引證清儒孫詒讓的話說:“從現存儒家作品看,《禮記·表記》、《坊記》、《緇衣》均引孔子語,證以《易》文,這幾篇出於《子思子》,說明子思也常於易學。”子思如此,孟子亦然。清儒杭辛齋獨具慧眼,他認為:懂得易學並不在於口道乾坤坎離,關鍵在於心法天道德義:“孟子繼孔子之後,七篇之首,即揭明仁義大旨,而歸體於性善及經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及繼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見孟子之不知《易》哉!”
有了上述考據,我們便不難理解思孟學派“性與天道”學說、“性善論”學說、“民貴君輕”學說和“五行學說”的真諦和來源。
孔子“老而好易”,在會通人道與天道、地道之後開始大談“性與天道”,以至於他的高足弟子都想不明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認為自己“學問不高,老師給我們講性與天道的那些話我們聽不懂,聽不著”。《中庸》中的性與天道論就是對孔子有關論述的繼承和發展。孟子的“性善論”來自於《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論斷;其高舉的“義”旗,就是依據孔子提出的仁、義,禮、智對舉思想,對其仁學的節度,對墨家“兼愛”思想的反制;孟子民貴君輕思想是對孔子“革命理論的發展(《易傳·彖·革》講:“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思孟學派對易學也有貢獻,就是解決了大易醫人的問題。我們知道,易經號稱帝王之學,“群經之首”。其醫國問題由《易傳》基本解決;醫病問題由《黃帝內經》基本解決,醫人的問題,則由思孟學派提出的德性論《五行》學說給出了答案。思孟學派比照數術論五行(金木水火土),提出了仁、義、禮、智、聖五行。所謂“聖”不是指“誠”,而是指會同天道、人道的本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認為:“思孟學派這種將數術引入儒門的努力,高揚‘人道’主義旗幟的表現,是企圖把儒家的道德條目加以自然哲學和生命哲學化的明證。其理論勇氣是巨大的,對國人思維方式影響也是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其對我國古代社會發展進程影響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學真正走上了醫國、醫人、醫病的光輝歷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隱含著終始交替的意蘊。由此看來,應是思孟學派開‘五德始終說’之先河。”
思孟學派講善道和德道。就個體而言,就是講仁義禮智善道;就社會講,就是弘揚由易經而來的德道: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民主、法治。此正可謂今日我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