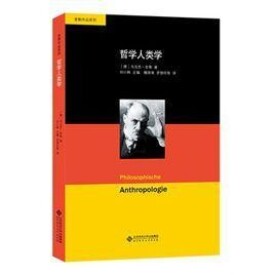哲學人類學
哲學人類學
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論,廣義而言是指哲學上一切關於人的理論、觀點、學說,即相當於傳統的人本主義思潮。狹義的而言,特製二十世紀初由德國人馬科斯·舍勒創立並由同時期的文化人類學家米契爾·蘭德曼等人發展壯大成為包括宗教哲學人類學、生物哲學人類學、心理哲學人類學、文化哲學人類學以及功能主義的哲學人類學等學科分支的龐大哲學體系。
由德國文化人類學家米契爾。蘭德曼在1955年出版,書中全面地闡述了哲學人類學作為一門哲學的來龍去脈,它的主要內容、基本原則及其重要性,而且也得力於蘭德曼廣泛的綜合能力,深入淺出的剖析,行文的明晰曉暢。本書談到了一些著名的人類學家,並且闡明了作為一門哲學學科的人類學,與滲透在倫理學和社會科學中的所有人類學觀點之間的聯繫。它也涉及德國哲學人類學與美國文化人類學之間的關係,論述到了哲學人類學與所有宗教和藝術中內含的“人的形象”之間的差異。
本書追溯了人類學的源流、哲學人類學的緣起,探討了哲學人類學的方法、意義,分別介紹了哲學人類學的主要流派,較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作者的文化哲學人類學(亦簡稱為文化人類學)的觀點。
本書被譽為哲學人類學領域中“標準的權威性著作”。
要了解哲學人類學,本書既可當做入門著作來讀,亦可作為專門性著作來研究。
16世紀末期人類學一詞開始在德國各大學的哲學系中使用。18世紀出現了把人類學分為自然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傾向;前者把人當做一個自然種類,後者把人當做一個被歷史和地理因素個別化了的社會存在。這是為了適應科學分工的需要,這一需要近來日益增長。
結果,人類學的領域已分為越來越多的專門學科,來分別研究人的各個方面。哲學人類學就是為了挽救這種對人的研究的分解狀況,企圖把那些專門學科重新組合於一個共同目標之內,設法給人的研究以條理感。因為沒有條理感,研究人的科學就會忽視人的本質,忽視人性。
雖開始於1920年代,但人卻是西方哲學經常研究的對象。西元前5世紀中葉智者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就制訂了人類學的基本準則︰「人是萬物的尺度」。不久,蘇格拉底也把德爾斐(Delphi)的神諭「知道你自己」作為自己的教條。人、世界和神自有史以來就是西方思想的重大課題,但這三者的重要意義則歷代各有不同。
在古代,著重宇宙或宇宙秩序的概念,宇宙學比神學和人類學佔有優先地位。天體的宏觀世界以其規律主宰人類的微觀世界。中世紀文化仍保留著古希臘的世界結構,不過也有一種變化;在希臘人看來,宇宙秩序的權威凌駕於神之上;但在基督教看來,一個萬能的神是世界的創造者和人的創造者。人不是為著自己而生存,他處於神的一種創造物的地位。儘管嚴格地說來中世紀沒有人類學這門學科,但在神學中卻有一部分談到人的墮落性質及其得救的可能性。在文藝復興時代,人雖未停止在宇宙框架內觀察自己,未否認神的存在,但他卻充分地擺脫了這些束縛而把自己看做注意的中心,而思想的引力中心也從天上降到地下;人可為他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往往以人的尊嚴和優點作為論述的主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還不是哲學人類學,它仍為人是神的寫照這一主題所蠱惑。
(Michel de Montaigne)是對人類學思考作初步嘗試的代表。他這種思考擺脫一切教條的羈絆,而用以經驗為根據的考察精神來探討人的各個不同方面。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經驗主義先驅培根(Francis Bacon)在這方面樹立了一個榜樣,但17世紀的古典哲學卻脫離蒙田所開闢的道路,認為「搖擺不定的人」似乎不足以作為永恆真理的有力支柱。法國哲學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認為人既非天使,也非野獸,而試圖把人理解為墮落的神或高級動物也是徒勞。笛卡兒(Rene Descartes)把個人意識只是看做預測必然性的最敏捷的手段。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和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則認為個人的自我既不實在又無價值。在未拋棄偉大理性主義給現實所規定的體制之前,哲學人類學無立足之地。17世紀末期,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人類理解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給歐洲思想帶來了一種新風格,主張採用經驗的探討方法,要求人們要意識到人類知識所受到的限制。洛克闡明人應當承認自己是這世界的理性主人,但人並不是個絕對主體,而是一個具有形體的意識,帶著人性實體的各種缺點和限制。洛克、休姆(David Hume)以及法國孔狄亞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的哲學可算做哲學人類學。達朗伯(Jean Le Rond d'Alembert)和狄德羅(Denis Diderot)的百科全書也有人類學的傾向。
哲學人類學有了明顯的特點。它是與人文科學密切相關的一個哲學分支。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重新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動物;他們把傳統的自然哲學補充以「歷史哲學」。孟德斯鳩、伏爾泰、康德和黑格爾都相繼發展了一種歷史的或法律的和政治的人類學。在19世紀社會科學高度專門化的情況下,科學專家的視野越來越狹窄,他們過分地誇張他們自己的科學,結果成為他們專門化的俘虜,而不能觀察人的全部及其實質。宗教科學專家看到的只是宗教儀式行為,而經濟學專家則認為個人的或社會的生活都只是全神貫注於個人的物質利益。哲學人類學為了補救這種認識論上的無政府狀態,主張在對人的理解中人生的價值處於首要地位。在人文科學出現之前,古代哲學叫做形而上學;哲學的這一新支可以認為是「人而上學」,以期在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高潮中,再求得人的平衡。
西方思想界長期不接受人是一種自然的存在這一概念;人們把達爾文的進化論看做是羞辱和墮落。另一方面,17世紀理性主義哲學也不把人的身體當作人看待,認為人的本質和他的肉體器官毫無共同之點。哲學人類學則和這種二元論完全相反,認為人的這兩個方面是統一的。經驗證明沒有無身體的思想。人類學的一元論不是本體論的一元論,而是認識論的一元論。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被人認為是自然人類學之父,他的《論人的天生變異》(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1775)是一本繼續蒲豐(Georges-Louis Leclerc,Count de Buffon)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general et particuliere)而寫的著作,他認為只有人才真正有手,使他能製造工具;只有人才會說話、會哭、會笑。通過布魯門巴赫的著作,自然人類學現在可能對人作出更多的理論探討。人的直立姿勢解放了前肢,發展成為手,而手則是技術創造的泉源。同時,直立的姿勢使人擴大了視野,增加了活動領域。雖然人是軟弱的,赤裸的,缺乏自然的防衛手段,但他的身體構造是他身體自由的基礎,他的智慧是保證他生存的最有效的武器。
人是進化的產物,但這一觀念起初不易被人們接受。19世紀上半紀,法國考古學家布歇·德彼爾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在法國北部發現了一些加過工的燧石和其他石器,認為這是遠古文化的遺跡。一直到20年後,即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源始》(Origin of Species)出版時,人們才承認了這一說法。
它的對象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我思故我在」的我,而是對人生存處境的探討。自然人類學不能和文化人類學分開,人的變異不但須從自然方面認識,也要從文化方面認識。人是文化的產物,像蒲豐所想像的純粹野蠻人是沒有的。瑞士生物學家波爾特曼(Adolf Portmann)說︰「人的遺傳所特有的方式不是生物的,而是社會的。」同時,人也是文化的創造者。在18世紀末期,德國浪漫主義先驅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說道︰「我們生活在一個我們自己所創造的世界里。」哲學的見解認為,文化才能是人的存在的組成部分,人的社會實體化和他的身體實體化一樣,是他生存在世界上的先決條件。
1920年代,以現象學、存在主義、人格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哲學思想把個人生活狀況作為中心。哲學人類學是一種體化哲學,把每個存在著的個體都被認為是無法擺脫雙重的具體實在︰它不能沒有身體;同時,在他們作為一個必要的分子的社會團體中(如家庭、國家和政黨),又和其他個人聯繫在一起。這種自我統一不是當下可見的,而是在與各種因素的不斷接觸中探索自己。照哲學人類學家看來,世界上既沒有普遍的真理公式,也沒有對真理的固定準則。真理的真諦就是這樣探索自己,在達到結論前什麼也不能肯定。個人被認為是基本價值的主體,他強使自己承擔起一切主要責任。和理性主義的本體論相比,哲學的人類學更注重個體,它希望成為一種具體人的生活經驗的哲學,而不管什麼本體論的本質。
哲學人類學關注每個個人生活的不可索解的奧秘,心理學的任何模型和圖式對它只能提供有限的理解。哲學人類學不能形成一個學派,而只能代表現代各種不同思想所共有的一種趨向。
對大多數哲學人類學家來說,必須把人和神的關係計算在內,才能確定人在事物全體中的地位。如果說古代思想的主要任務是證明神的存在,現代思想的首要任務則是證明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