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覺派小說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組成部分
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現的“新感覺派”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新感覺派”小說的根本特點是特彆強調作家的主觀感覺而不太注重對客觀生活的真切描寫。劉吶鷗是“新感覺派”小說的最初嘗試者,他創辦於1928年9月的《無軌列車》半月刊,標誌著中國“新感覺派”小說實踐的開始。他的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線》是現代中國第一部“新感覺派”小說集。穆時英和施蟄存把“新感覺派”小說推向成熟和引身運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等手法,凸現對現實生活的感覺和印象。《上海狐步舞》、《梅雨之夕》等是他們的代表作。
這個流派主張以純粹的個人官能感覺作為基點,依靠直覺來把握事物的特徵。他們往往藉助於聽覺、視覺,乃至幻覺的外化描寫,創造出帶有主觀色彩的藝術世界。如《梅雨之夕》的“我”在迷濛的雨霧裡,撐著傘同一位妙齡女郎並肩而行時,彷彿覺得這位女郎是他當年“初戀的那個少女”;倏而又似乎發現他的妻在一家街店旁用“憂鬱的眼光”盯視著他;繼而又好像看到了日本畫伯鈴木春的《夜雨宮詣美人圖》;後來又彷彿覺得他身邊的少女變成了“一個不相干的女人”。作者所描寫的這些錯覺、幻覺是一種深層意識的極其複雜的變異反應,也是交織著情感的與理性的、悲的與喜的兩極對立的心態掃描。而這種變異反應,對立心態正是基於“我”的內心深處的“愛”和“不得所愛”的複雜情緒的。小說主人公心理結構中的這種“愛”的和“不得所愛”的情感因素引發了心理幻覺、錯覺,激發了聯想、想象,從而創造出一種具有深刻性和縝密性的心理世界。再如《熱情之骨》里寫比也爾在理想的愛情破滅后,心情沮喪之時,“覺得天上的月亮也在笑他”;當嘈雜的汽笛聲傳來時,連門窗的“玻璃也在響應”。這種視覺與聽覺交迭複合的通感現象,把比也爾當時的那種自憐、憤怒、失望、抑鬱的混亂心緒客體化、對象化,使藝術描寫增強了可感性,收到立體地表現生活的藝術效果。
借鑒西方意識流手法也是新感覺派的藝術追求。他們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情節連續性和時序性,而以人物思想感情的發展或作者創作思想的需求為線索,來對情節和事件進行新的排列組合,構成了一種節奏起伏多變,情節跌宕多姿的小說世界。如《上海狐步舞》將上海這個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各種圖象,通過作者本人的意識流動來切割和連綴。一忽兒街頭兇殺,一忽兒母子亂倫;一忽兒夜總會燈紅酒綠,一忽兒被迫出賣肉體……。這些時空交錯、空間跳躍的場景片斷,給人撲朔迷離、朦朧恍惚之感。這裡,作者依據直覺來把握事物的現象,並把自己的主觀感覺注入到客觀描寫中去,使客體描寫的每組畫面都洋溢著作者主觀上的危機感與狂亂感,從而構成了現代部市畸形文明和病態社會的瘋狂節奏與旋律。復如施蟄存的《在巴黎大戲院》運用意識流動手法描繪了一個有婦之夫在女友面前的種種猥瑣、庸俗的意識流程,對展示主人公的心理糾葛、刻畫變態人物都有一定的意義。新感覺派小說創作總體傾向的一致性,構成了這個流派產生和存在的基礎;但是,他們創作傾向上的一些嚴重弱點也導致了這個流派的解體。譬如,他們忽視內容的重要性,一味地追新求奇,使其小說的審美理想與生活理想,同群眾的民族心理、欣賞趣味產生了相當的距離;同時,技巧的新、奇、怪並不能掩蓋生活內容的空虛,反而使一些“新興”的技巧失去了富有創造性的魅力。這種難以克服的矛盾,使他們陷入了嚴重的創作危機,於是這個流派在困境中只好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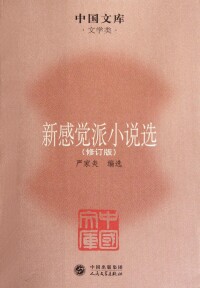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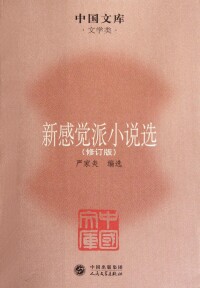
新感覺派小說
新感覺派是崛起於20世紀20年代日本文壇的一種現代主義流派。當時,以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為首的幾個 青年作家,接受歐洲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張起了現代主義的旗幟。他們聲稱不願再單純地描寫外部現實,而要力圖把主觀的感覺印象投注到客體中去,以新奇的感覺來創造由智力構成的“新現實”。鑒此,日本文藝評論家千葉龜雄稱他們為“新感覺派”。在我國又把這種流派稱作“心理分析小說派”,或現代派。新感覺派小說是中國現代小說傾向的一種,其小說內容多表現半殖民地社會都市生活的種種病態和畸形現象。

新感覺派小說
新感覺派小說在中國產生背景
中國的新感覺派小說是在日本新感覺派的影響下,在30年代步其後塵發展起來的。它的產生,既是世界性的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新文學衝擊的一種反饋,又是30年代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空前激化的結果。是時,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夾在越來越劇烈的階級鬥爭的夾板里,感到自己沒有前途,他們像火燒房子里的老鼠,昏頭昏腦,盲目亂竄;他們是嚇壞了,可又仍然頑強地要把‘我’的尊嚴始終保持著”。他們既不滿於舊的社會秩序,又尋求不到施展才華的歸宿,陷入了苦悶、彷徨的困頓之中。為了填補自己精神的空虛,他們追求新的刺激,因而欣賞現代派小說的“新、奇、怪”的表現手法,這就為他們接受日本的新感覺派提供了前提條件。不過,他們並不像西歐的現代派那樣,以一種與現實主義相對抗的形式出現於文壇,而是力圖兼容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等各種新興的創作方法,納入了現實主義的軌道”,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感覺派”小說。
新感覺派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和積極實踐者是劉吶鷗。他原名劉燦波,筆名洛生,台灣省台南縣人。早年在日本東京青山學院攻讀文學時,深受將西方現代派文學與東方精神結合於一體的川端康成的影響。在日本應慶大學畢業后回國,曾先後創辦“第一線書店”和“水沫書店”,出版了許多進步書刊。他自己也譯介過進步的社會科學書籍和日本新感覺派小說集。1928年9月,他創辦《無軌列車》雜誌,團結了一些刻意追求藝術形式創新的文學青年,初步顯露了新感覺派的創作傾向。同年底,《無軌列車》被國民黨查封后,他繼續嘗試新感覺派小說的創作,先後寫出八篇小說,於1930年4月結集為《都市風景線》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本較多的採用現代派手法寫的短篇小說集。
1929年9月,施蟄存與劉吶鷗、戴望舒、徐霞村等集結在一起,創辦《新文藝》月刊,繼續張揚新感覺派的大旗、宣告了這個流派的誕生。施蟄存是這個流派成績最為顯著、影響最大的作家。他是杭州人,早年在中學教書時,著有現實主義小說《江干集》、《娟子姑娘》、《上元燈》等。1929年9月,在他創辦的《新文藝》上,發表了《鳩摩羅什》,才正式涉筆於新感覺派小說創作。《新文藝》僅出版一年,就被國民黨政府查封,又使新感覺派小說創作陷於困頓之中。1932年5月,施蟄存應上海現代書局之聘,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他又以此為園地,或發表國內文學青年的作品,或介紹國外的詹姆斯·喬伊斯、福克納、橫光利一等現代派作家的作品,從而使新感覺派的小說進入一個全盛時期。

新感覺派小說
在《現代》雜誌造就的作家中,穆時英的小說創作對新感覺派的發展具有突進性意義。穆時英是浙江慈溪人,筆名伐揚,1929年開始寫作。他最初發表的小說並沒有新感覺派的味道。大約在1932年以後。他的作品突而轉向新感覺派。他先後出版了《公墓》(1933)、《白金的女體塑像》(1934)等小說集,運用感覺主義、印象主義等現代派手法,來表現大都市光怪陸離的生活,不僅開了“洋場文學”的先河,還使他獲得了“中國感覺派聖手”的稱號。
新感覺派的全盛時期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在劉吶鷗和穆時英棄“文”從政之後,施蟄存又於1935年2月離開《現代》雜誌。到此,這個來去匆匆的文學流派則像彗星一樣悄然而逝了。
新感覺派作家由於受到弗洛依德學說的影響,還十分熱衷於刻畫“雙重人格”的心靈衝突和變態心理。根據弗洛依德學說,人的“本我”(本能)在受到“自我”(理智)和“超我”(道德)的制約的時候就會形成矛盾,構成二重或多重人格。如施蟄存的小說《將軍的頭》描寫了花驚定將軍奉命征討吐蕃的故事。在出征途中,為嚴肅軍紀,他處決了一個企圖調戲民女的兵士。可是他自己卻為這一民女的美色所傾倒。後來在激戰中,他忘記自己正置身於生死搏鬥的戰場,想到與那民女合歡的美事。此念一生,就被飛來的一刀砍掉了腦袋。可是這個沒有腦袋的將軍依然策馬來到那個民女的身邊。小說表現的是愛欲的“本我”與“超我”的軍紀的衝突。這種由兩種相背馳的力所構成的衝突,正是“雙重人格”的典型表現。此外像劉吶鷗的小說《殘留》寫女主人公霞玲在丈夫剛剛亡故之後,一方面確實悲慟欲絕,思念異常,另一方面又在料理完喪事當晚,就挑逗一個男朋友來代替她的丈夫。還有施蟄存的《鴆摩羅什》里的那個內心裡充滿著宗教與性慾衝突的高僧;《石秀》里充滿著友情與性慾衝突的石秀,都是“雙重人格”在性愛方面的代表。在他們筆下的這種“雙重人格”的描寫,一般都是從作者的主觀意念出發,缺乏生活的依據,但在一定程度上較為奇譎地揭示了病態人物的變態心理,為新感覺派小說“開闢一條創作的新蹊徑”。

新感覺派小說
新感覺派的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創作都起始於現實主義,後來才接受了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卻不完全一樣。劉吶鷗、穆時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覺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現代派的技巧的同時,也接受了現代派的文藝觀,成了徹頭徹尾的現代派。施蟄存則從日本新感覺派後期的新心理主義那裡擷取了更多的精華。他是立足於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並吸收現代派的技巧來豐富自己。因此,在他脫手《現代》之後,就以一種新的姿態回歸到現實主義。儘管他們在創作道路和創作的價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為一個流派。也構成了一些共同的創作特色。
首先,新感覺派的創作題材多取材於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態生活,並通過描寫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現象和世相世態,暴露出剝削階級男女的墮落與荒淫、寂寞與空虛,為開拓中國現代的“都市文學”建樹了篳路藍縷之功。劉吶鷗的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不僅是我國最早出版的新感覺派小說集,也是最早出現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說集。作者以他對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繪了都市的賽馬場、夜總會、影院、茶館、富家別墅、海濱浴場等色彩斑斕的場景,也刻畫了舞女、少爺、小姐、交際花、姘頭、資本家、小職員等各式各樣的人物,並以急驟的節奏,跳蕩的結構,活靈活現地顯現出剝削階級糜爛生活的剪影。他的《禮儀和衛生》依據弗洛依德的學說描寫了一夥在“唯樂原則”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蕩縱慾的生活。穆時英的《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領域更為廣泛,也更進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質。其他代表作還有施蟄存的《鷗》和《薄暮的舞女》。
其次,新感覺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們提倡作家要“純客觀”地挖掘與表現人物的潛意識、隱意識活動,以及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由某種客觀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變態心理。相比之下,施蟄存的小說創作則高於劉吶鷗和穆時英。施蟄存的病態小說,題材更為廣闊,內容也更為豐富。他不僅以上海為主要場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態生活,而且還對上海市郊小城鎮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掃描。最初的新感覺派小說把追求新奇的感覺當作創作的關鍵。到30年代初期,他們又接受新心理主義的影響,創作了一批以表現心理分析為主要內容的小說。如劉吶鷗的《殘留》採用主人公霞玲獨白的形式來進行人物的心理剖析,在當時是別開生面的。穆時英的《南北極》、《白金的女體塑像》等小說都是將心理分析作為構成作品藝術形象體系的重要環節,豐富了刻畫心理小說的表現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個新的高度的還是施蟄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陽》、《葯羹》等小說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說的最高水平。
再次,新感覺派十分注重小說技巧的創新。新感覺派作家的創作都是起步於現實主義手法的。但是他們基於“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的想法,刻意移植和實驗現代派的“新興”技巧,有意識地把各種非現實主義的技巧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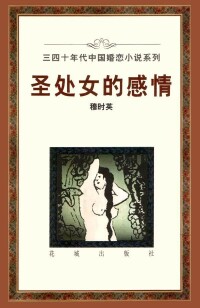
新感覺派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