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武氏墓群石刻
山東嘉祥縣紙紡鎮出土的文物
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位於嘉祥縣紙紡鎮武宅山村北,為漢代祠堂和墓地,始建於東漢桓、靈時期,全石結構,石刻畫像,內容豐富,雕制精巧,是我國保存完整的漢代石刻藝術珍品。現存石闕、石獅各一對,石碑兩塊,祠堂石刻構件四組40餘石。武氏墓地最早見於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南宋洪适將題字與圖像,集於《隸釋》、《隸續》中。1964年將處於深坑中的石闕、石獅,按原位置提升到現在的地坪以上,並建立了寬敞的保護室。1961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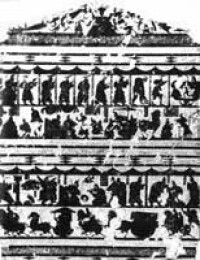
嘉祥武氏墓群石刻
武氏墓相當於東漢桓、靈帝時期(147~189)。除石闕外,諸石祠於宋代以後傾圮。其中的“武梁祠”畫像,最早見於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南宋洪适又錄其部分榜文、圖像於《隸釋》和《隸續》,始以“武梁祠畫像”名之。清乾隆年間,黃易等人掘出祠石,當時認為有 4座祠堂,即武梁祠和根據武梁祠位置定名的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經籌劃保護,就地建屋,將畫像石砌於壁間,外繞石垣,圍雙闕於內,題門額曰“武氏祠堂”。

嘉祥武氏墓群石刻
。

嘉祥武氏墓群石刻
宋代以來金石家累有著錄。武梁碑、武開明碑早佚,現存武斑碑、武榮碑。武斑碑作圭形,額有圓穿,高2.10米。
武梁祠原為單開間懸山頂石構建築。現存 6石,即“武梁祠畫像”3石、“祥瑞圖”2石、“武家林”斷石柱 1石。祠內牆壁和屋頂上都刻滿畫像。三壁上部羅列歷史故事,和祥瑞畫像最豐富,有從伏羲至夏商古代帝王,有藺相如、專諸、荊軻等忠臣義士,有閔子騫、老萊子、丁蘭、梁高行等孝子賢婦;三壁下部為祠主的車馬出行、家居庖廚等畫像。東西壁山尖刻東王公、西王母等靈仙故事,內頂刻布神鼎、黃龍、比翼鳥、比肩獸等各種祥瑞圖像,其旁皆有隸書榜題。
前石室原為雙開間懸山頂石構建築,後壁正中有龕。現存16石,即原“前石室畫像”12石,“后石室畫像”4-5二石,“孔子見老子”1石,供案1石。祠內滿刻畫像,亦有西王母、東王公等神話故事,壁西刻孔子見老子、孔門弟子和祠主經歷和生活的車騎出行、宴樂、庖廚、仙靈神話,以及文王十子、趙宣子、荊軻、邢渠等良卿古賢;西壁下部刻大幅水陸攻戰圖。小龕後壁刻祠主樓閣家居圖,室頂為仙人出行、雷公電母、北斗星君、伏羲女媧等靈仙神話,前石室車騎畫像有大量榜題,與武榮碑所記經歷多相吻合,一般推定祠主為武榮。
左石室原形制與前石室相同,現存17石,即原“左石室畫像”2-9八石,后石室畫像1-3與6-9七石,殘脊石1,花紋條石1,內容布局亦類前室。其中如周公輔成王、二桃殺三士、管仲射小白,以及頂部的海靈山行、升仙圖等均為前室所不見。無榜題,祠主待考。
武氏墓群畫像石雕刻技法主要採用壓地隱起,既保持了平齊的壁面,又使畫像躍然而出。物像外石面留有整齊細密的豎線鑿紋。構圖分層分格組合,層次井然。
這批石刻藝術以其鮮有的“畫像古樸,八分精妙”引起世人的注目,名家學者爭相拓墨,中外書刊廣為著錄。
武氏墓群石刻中的漢石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為加強這批珍貴文物的保護和管理,在此設立文物保管所。1961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4年,將位於坑中的雙闕原位提升現地面,其上建了高大寬敞的保護室;1972年,又將祠石從舊屋中拆出,移置闕室內四周石台上。1981年蔣英矩在進行全面考察後進行了配置復原,提出了“后石室”並不存在的確證。
坐落于山東省嘉祥縣城南的武氏石刻,集文史記載,雕刻繪畫於一身。上溯先秦,融會兩漢;雕古畫今,凝思石上。正是漢代大統一思想文化的產物於反映,它以儒為主,儒道互補,仙道五行思想雜糅,富有兼采眾長的特色,與史記,漢賦,淮南等名篇巨制先後在不同的領域各領風騷,共同構成泱泱大漢的時代精神與風貌。我們完全可以稱武氏漢畫石刻為“漢騷石賦”:漢化楚風,賦於石上,即騷賦精神的凝化形態。
它採用平面淺浮雕即“離地凸起”的雕刻技法,烘托突出渾圓雄壯的造型,纖細遒勁的線條穿繪著逼真的細描,工整流暢圓潤端莊,頗富體積感,運動感和力度感。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中讚歎武氏石刻:“其高古樸茂,琦瑋譎詭之趣,誠非想象所及,雖其形象之表現,沒有不合理處,然能運其沉雄之筆線,以表達各事物之神情狀況,而成一代特殊之風格,非晉唐人所能企及”。它以永恆不朽的價值與魅力,展示這中華民族輝煌的過去,也昭示著民族復興的未來。
我想,兩千多年的藝匠石工們,又豈料這手下頑石也有騰達飛天之日;如若有知,他們還會敞開那雅拙而又浪漫的情懷嗎?
其實藝術這玩藝兒,大都是漫不經心的結果。“藝術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只要是先知這一筆將成為典範,那一刀將載入史冊,也就無法“游於藝”並“行之遠”了,何況那又是為他人營墓造穴,為自家混幾文飯錢,犯得著孜孜訖訖,嘔心瀝血嗎?悠著點,悠著點不妨想想鄉鄰的耕織之苦,朱門的宴遊之樂,天上的青龍朱雀,底下的鳥獸禾木......待想走了神,想出點味,手下的石頭也就有了體溫,有了靈性,從而石破天驚,有了兩千年後的不朽!
其實該朽的已灰飛煙滅朽去了,這才見出不朽的道道來。瞧那“朱雀橋邊”,“烏衣巷口”的崇樓深堂,華車麗輦不是早已隨它們的貴主一同朽去了嗎?荒冢一堆草沒了嗎?留下點影子來,既是石頭的寬容,也是歷史的苛刻——幸運也罷,尷尬也罷,好歹算個見證。兩千多年,實在是條很幽冥的隧道,實在是堵厚重的牆;一下子鑽進去且跳過去,豈不是件很開心的事?古希臘的哲學家曾幻想在時間隧道里也能像在空間里遨遊,其實在漢畫石刻前就可以這樣做到。既知有漢,遑論盛唐,只有這時,我們才會確確實實而不是含含糊糊地自認是“漢家子孫”。面對那粗粗拉拉的石頭,你說這感覺奇妙不奇妙?
並不是所有得人都能找到這種感覺。古與不古,也在一念之間。面壁一時便“上窮碧落之高遠,下極大海之奇觀”“心游萬仞,精騖八極”的不是沒有;但數典忘祖,浮躁的人們慕名來轉一圈,走時連呼上當的卻真不少。其實上當的倒是那石頭。三尺黃土下,千載風雨中,本是躺的坦然,睡的黑甜,又曾招著惹著誰了?何必非要站出來讓不孝子孫們幽思或遺憾?
“花如解語應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石為濃縮的天體,石為可收藏的大自然。丘園石雕,長於院落笙歌。那厚厚道道得說不出話來,睿智得不說出話來,我待要替他說上幾句,想了想詞兒,卻也無言。
石立萬仞,無欲則剛,無言獨化----這恰是與天同契的“漢石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