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畫史
玉台畫史
《玉台畫史》編者湯漱玉,字德媛,錢塘人。出生名門,幼耽翰墨。浙江杭州藏書家振綺堂主人汪小米夫人。是編仿厲鶚《玉台書史》之例,輯歷代能畫之婦女為一編,體例略有變更。分宮掖、名媛、姬侍、名妓四門。凡宮掖二十八人、名媛一百二十五人,姬侍十六人,名妓四十人。后附《別錄》十五,則不入諸門。清人程庭鷺曰:“吾友錢塘汪小米中翰其配湯漱玉,曾輯《玉台畫史》,歷朝閨彥之善畫者,咸詳備焉”。有《說庫》本【無《別錄》】、《述古叢抄》本、《藏修堂叢書》本、《翠琅玕館叢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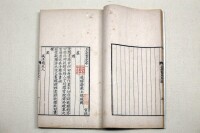
玉台畫史

《玉台畫史》
女性畫家只是受到如名媛、名妓等標示出身名詞的修飾的問題,在明清時期畫史中無遮攔的得到暴露。無疑對畫史產生了致命的影響是階級社會頑固的男性化傾向,可以說,畫史冷落了女性,甚或成了一種男性話語。性別差異鬆動的今天,我們應在比較公允的立場上,以 傳統中國畫盛衰轉折的明代為背景,從性別角度來觀照繪畫女性。

李因芙蓉鴛鴦圖
明中葉歷史上最為強大的妓女群形成,加之政府罰良為娼,大批“犯官”眷屬淪落青樓,其中不乏才華橫溢者。一些風塵女子為迎合社會,除姿色外,亦以文藝修養點綴自己。可以說,中國封建女性的歷史一部分需要在這些藝伎的修養身世中去探討。雅好藝文聲樂的文士往往混跡於青樓優伶之間,他們的詩畫創作也多描繪姿態閑逸體態柔弱情緒淡漠意多嫻婉的藝伎形象。因為藝伎的自由性,文士直接傳授她們的機會要多些,所以造詣一般也不淺,如 李因“畫花鳥,葉大年授以筆法,蒼秀入格,點染生動,大幅亦佳,此閨閣中而得士氣者。”至於 馬湘蘭,“其畫不惟為風雅者所珍,且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相傳繪畫始創於 嫘,直至唐之前繪畫女性很少,能被史載的就更少了。即使到了宋朝,皇帝雅好丹青,沒跡象表明皇帝鼓勵女性繪畫的意思。至元社會對女性繪畫似乎也一樣冷淡。受到元帝褒獎的管夫人實屬寥寥。而至明,僅姜紹書《無聲詩史》就載31人,並辟女史專卷。這裡他繼承《 明畫錄》各門裡以名媛、妓女兩類來區分女性畫家。給予了繪畫女性積極的關注和讚賞。對女性畫家記載更多劃分更細的莫過於湯漱玉的《玉台畫史》,女畫家被分為宮掖、名媛(56人)、姬侍(9人)、名妓(32人)四類,共載宋以前15人,宋34人,元9人(至此期妓女尚少習畫),明97人。初據史籍統計,明以前女性畫家約67人;明一代則有125人之多,且多為嘉靖后的。明以前繪畫女性能力多有限,只以四君子題材偶寄閑情。全才的管夫人是個例外。明代女性畫家多兼擅數科,琴弈書畫詩文皆能。妓女畫家在此時也開始大量出現。那麼究竟是何影響明代女性繪畫人數大增及其畫作水平大幅提高?

文淑
明代地域傳統文化的繁榮,商賈業儒文人經商,文藝開始世俗化。古玩書畫收藏盛行。這些都吸引了大量身份各異的從事書畫的人員的出現。女性從事繪畫成為上流社會、文士家庭和青樓女子中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不再如馬閑卿(陳魯南妻)所疑“此豈婦人女子事乎”,畫完以後多將畫撕毀,她們所繪也不再是“聊復自娛”、“使人不可多見”的活動,而是出現了不但自己從事繪畫甚至還有自己的傳人的女性畫家,如 文淑。
女性處於男性社會中必先經過男性社會意識形態的整合。反映在書畫上,女性要麼通過隱晦曲折的方法表現自己的書畫個性,要麼融入男性繪畫語系。後者在明中後期的女性繪畫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應指出,女性畫家無論受過多麼嚴密的男性繪畫語系的訓練,只要她身處女性境地,作品中總或多或少的流露出自身的意識情趣。在創作態度、表現方法上,可貴的是她們能超出特定的框架表現出非凡的才能和力度,這裡她們不再是男性的影子,而是代表了自己的性別,將自己的真情實感貫徹於作品中,她們有著鮮明女性特徵的畫作拓展了一般男性畫家很少涉及的女性情感的天地。她們見卉木秀芪,花草敷榮,桃穠李素,荼艷桂香,即興點染,施之圖繪,把自己的情思感想都傾注於尋常事物中。她們的作品多筆墨清純,色彩明麗,風格秀美,活脫自然,既無逸筆草草的縱橫習氣又無濃艷柔媚之態,並因春榮秋殘日沐風欺時態種種生出百端情緒。她們自覺發揮了繪畫的特殊作用,豐富了表現題材。女性畫家的作品吻合了社會對她們本身的性別期待,強調興會神到追求得意忘形以清淡閑遠的風致神韻為繪畫的最高境界。
字道珠,錢塘人,詩人沈用濟方舟室。方舟客紅蘭主人所,久而不歸,道珠遙寄《故鄉山水圖》,主人作詩,有“應憐夫婿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之句,當時傳為佳話。方舟妾曰顧春山,道珠嘗約春山河渚觀梅,得句云:“樓外有梅三百樹,美人不到不開花。”其風致可想見矣。
長紆先生之妹,幼時隨父任滇南,長紆補學博回浙,士珊畫《野畦圖》送之,卷中花果,多不能名,蓋滇中物也。后歸王氏,吳穀人祭酒,《題剔銀燈詞》,載有《正味齋集》中。
姚夫人,顧隅東(升)室也。隅東工書畫,自顏所居樓曰“寫山”。夫人亦擅繪事。朱西畯(昆田)《題寫山樓主人墨梅二絕》云:“墨梅舊數楊補之,今看尺幅橫一枝。盡刪海粟百絕句,寫山樓有無聲詩。冷蕊疏花色斬新,鮑夫人合管夫人,問君嫵媚何能爾,莫是羅浮夢後身?”
字佛圖。伊爾根覺羅氏都統,謚勤敏莽鵠立女。勤敏工寫真,其法本於西洋,不用墨骨,純以渲染皴擦而成,神情酷肖,佛圖親授指法,亦工人物,守貞不字,長齋綉佛以終。
《清平樂·題吳中女子呂文安畫雲》:“深閨暇日,偶仿王郎筆。小字親題無氣力,殺粉調鉛第一。圓珠斛得誰家?香車遠隔天涯。陌上依然柳色,門前何處桃花?”阮亭《題馮女郎畫蘭》云:“丐得騷人筆下妍,玉池清照影便娟。一時弱質辭空谷,冶葉倡條盡可憐。”呂馮畫跡,今不可見,姓氏附見兩家集中,亦云幸矣。
字瑟兮,石門吳南泉女,桐鄉程同文春廬繼室。姓特高潔,工詩善畫,初寫折枝花,繼作山水蘭竹,皆出心悟,追蹤於古婦人無此筆也。嘗畫《溪山歸興圖》,春廬題句云:“人間何處覓菟裘,送老溪山一葉舟。慚愧賢妻招隱意,年年看畫過清秋。”

朱筠 幽萼麗台
字飛卿,一字香輪,金壇人,吳縣顧侶松大令(鶴)室也。以孝行稱,畫師南田,風枝露葉,雅秀天然。兼精岐黃之術,侶松令米脂,從征喀什噶爾,飛卿留居吳門。夫家母家,皆恃丹青以給。近時女士工畫者,嘉興沈採石(谷)山水,吳顧芳(蕙)花卉,南海黃畊畹(之淑)蘭竹,並出冠時,何閨閣之多才也!
字閬真,號鉏月,錢塘半江司馬淞女,歸安費錫田室。能詩,兼六法。夫亡,誓以身殉,卒年二十有九。其自題山水畫冊云:“路轉千峰一徑斜,煙霞深鎖野人家。春來更有幽棲處,開遍東風枳谷花。”“家住江南楊柳灣,一蓑煙雨打魚還。數聲蘆荻秋風暮,飽看青溪兩岸山。”“蒹葭深護水雲鄉,門掩青山對夕陽。吟罷小樓閑眺望,晚風吹起白蘋香。”“峰含晚日樹含煙,野水微茫接遠天。如此溪山誰領取,風光輸興釣魚船。”極清婉可誦。
山舟學士嘗《題女史朱雨花畫海棠便面跋》云:“予猶女適德清許氏,一日歸寧,手一扇上畫折枝海棠,生秀圓潤,署款朱新,字雨花,蓋女史所貽也。予叩何人,曰:‘此即五世一堂竹溪戴翁(德清人)之曾孫婦也。’向予慕其家風孝友,嘗買榷訪之,見其祖孫四世,而五世孫徵符方在衽褓,即女史朱所誕育也。夫蠶織針管,是宜所習,不意畫手渲染之妙,其朴而能文可知矣。予生平所見閨秀畫不一,最上如黃石齋先生之蔡夫人,錢尚書母南樓老人,綽有徐黃遺法,妍麗中氣骨古厚,非如吳下文淑惲冰,徒以姿媚一派見長而已。女史年未滿三十而技若此,倘得前人名跡,瀏覽而靜摹之,所造當更有進於是者。予故因猶女之請,跋其便面以報所贈。嘉慶八年歲在癸亥二月之末。”此跋《頻羅集》中未刊,故亟錄之。
宋秋田藏閨秀扇面甚夥,有陳字陳李山水合筆,字無名老蓮子,見《 畫征錄》。李相傳是老蓮女,未知所據。殆亦如青蚓妻女,偶爾渲染,流傳不多,傳畫家者,未之及耳。周南卿亦有閨秀扇面數十頁,鑒別極精。南卿沒后,不知歸於誰氏矣。薩克達氏,雲貴總督謚庄恪阿思哈公第四女,英煦齋協揆(和)配也。善寫生,尤喜以指頭畫鷹,得其神俊。顏所居曰“觀生閣”。每作畫,協揆為之署款,嘗於胡書農學士齋中,見所作《花草胡蝶》卷子,協揆題其後云:“今夏內子得甌香館山水冊子,遂摹之,始悟花卉難,草蟲難,畫蝶尤難。蓋山水可以添染,花蟲則一筆落紙,不可收拾。此內子之獨得,不知有合否?請俟高明指謬。”余雖不解畫,然於畫蝶,每賞之,亦愛則忘丑耶!閨房之雅,洵足媲美鷗波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