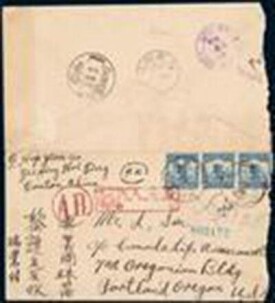興寄
興寄
興寄,是我國古代詩歌的重要特點之一。它原是詩歌創作的要求,但“興寄”的深淺有無,古人不僅常用於詩歌評論,且注重“興寄”的詩,作者往往有意讓它的意味“使人思而得之”,或“以俟人之自得”,而不正言直述。因此,了解這種特點,對閱讀或欣賞中國古典詩歌也是很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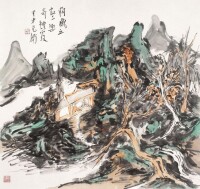
興寄
“興寄”一詞首創於陳子昂,出自其《修竹篇序》:“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 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彭慶生在此注“興寄”為“謂以比興寄託深刻內涵也”,並引用《文心雕龍·比興》中“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 寄諷”加以旁證,可知子昂此處“興寄”是對傳統儒家詩教“興”這一的手法的重提,強調了其內容上言此意彼的寄寓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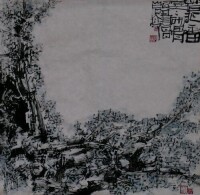
興寄
《詩經》民歌富有現實主義的精神,這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加以漢人尊為五經之一,成為儒家的一部經典,更增強了它在古代文學中的權威性,漢魏以後,每當文學創作出現浮華艷麗的嚴重傾向時,評論家們就會強調《詩經》的優良傳統以反對過分地追求形式。興詩的托物起情,便逐漸受到詩人和評論家的重視,並越來越突出其“起情”的意義。劉勰論比興,就批評漢代文人“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他第一次明確區分比、興的小大輕重,認為詩歌創作拋棄了更重要的興,就遠不如周代詩人的《詩經》了。鍾嶸評張華“興托下奇”,就因他的詩“其體華艷”,“務為妍冶”。到陳子昂提出:“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修竹篇序》)也是為反對“彩麗競繁”,希望恢復“風雅”的傳統而強調“興寄”的。其後,如李白一方面聲稱“將復古道,非我而誰”,一方面強調“興寄深微”
(《本事詩他》);直到明人許學夷所論“漢魏五言、深於興寄,蓋風人之亞也”(《詩源辨體》)等,無不是從發揚《詩經》優良傳統的要求來講“興寄”的。
“興寄”的這種發展過程中,雖然始終沒有離開“興”的本義,卻逐步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它不僅僅是一種“託事於物”的寫詩方法了,而更側重於用這種表現方法所寄託或興起的情。“興寄”逐漸形成和“彩麗競繁”、“其體華艷”的相對概念,用以指對詩歌應具有充實而有意義的思想內容的要求。這和整個“比興”概念的發展變化過程是一致的。如白居易《與元九書》所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過矣;索其鳳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憧關吏》、《塞蘆子》、《留花門》 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從白居易在同文中稱自己有關“美刺興比”的詩為“新樂府”,元稹在《進詩狀》中稱自己的樂府詩“稍存寄興”,可知“比興”和“興寄”的要求是相近的。這種“比興”或:“興寄”,就是要求詩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了。用這樣的要求來衡量齊梁時期的詩作,自然是“興寄都絕”。
唐宋以後,詩詞的“興寄”受到詩人們更大的重視。除上舉明人胡應麟、許學夷等多次用“興寄”的深淺來評論詩歌的優劣外,到了清代,甚至認為“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馮班《鈍吟雜錄》);“伊古詞章,不外比興”(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自序》)。沒有比興就不成其為詩,以至一切文學作品,無不是用比興寫成的,這就把比興的地位提得更高了。比和興的共同特點都是托物寓情。唐宋以後“比興”連用,就往往指托物寓情的共同要求。清代詩人不僅認識到托物寓情的普遍意義,且不滿足於一般的寄託,如陳延焯所論:“托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足以言興。”(《白雨齋詞話》卷六)不僅要有深厚的寄託,還要有廣泛的意義而不專指某一具體內容,情與物之間要有內在的聯繫而不是勉強的比附,才算得“興”。這樣的“興”,就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藝術創作了。古代對“興寄”的要求,這又是一大發展。
“興寄”之所以能成為一種古代寫詩或評詩的重要要求,並得以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這是它本身的特點決定的。首先,“興”不是人為的規定,而是從《詩經》的實際創作經驗中總結出來,又為歷代詩人的創作實踐不斷豐富起來的。這樣,它就符合詩歌藝術的基本規律。所謂。“詩以言志”,詩歌必然是為了表達詩人的某種思想感情而寫,沒有任何思想感情的詩是不存在的。但不藉助於一定事物、不通過具體的形象而直陳其情,也不成其為詩,至少不是好詩。托物寓情正是“興寄”的基本特點,它能受到歷代詩人的普遍重視,並不斷有所豐富,就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