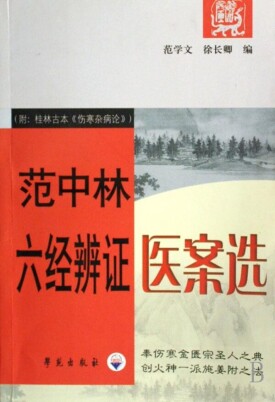范中林
蜀中現代名醫
范中林(1895—1989)四川郫縣太和鎮人,享年94歲,蜀中現代名醫,多年來潛心於《傷寒論》的研究,善用經方,尤以舌診見長,深受火神鄭欽安思想影響。在掌握六經辯證規律治療若干外感和內傷雜病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特別是對於許多虛寒證,疑難病的療效尤為顯著。70年代末由范中林醫案整理小組編寫了《范中林六經辯證醫案選》,范氏用藥悉本《傷寒論》,組方嚴謹,以味精量重為特點。從學者甚眾,早期弟子唐步祺,是其突出的一位。

(圖)范中林
范老治病的特色是認為世上萬病皆可以用六經來分型,萬病皆不出六經範疇。本文總結了范老臨床上最具代表性的三經病病案經驗,仍然感覺意猶未盡。范老的病案看似舉重若輕,實際上需要多少紮實基礎的沉澱,也鞭策我們這些後學者要時時努力進步,心細如髮才能夠膽大不慌。

(圖)附子
[診治]腹脹如鼓,胸脅滿悶,皮色蒼黃;全身肌膚脹硬。大便常秘結,所下如羊糞,已四日未行;下陰不斷滲出臭黃水。舌質深紅,苔黃燥,脈沉實有力。此為陽明腑證兼水熱互結。法宜峻下熱結,兼逐積水,以大承氣並大陷胸湯加味主之。
處方:大黃18克 厚朴30克枳實30克芒硝30克甘遂15克(沖服) 芫花15克(沖服) 桑皮60克先服一劑,瀉下燥屎十餘枚,並臭穢黃水甚多,腹部硬脹消失大半。續服一劑,胸腹腫脹皆消,全身肌膚變軟,下陰外滲之黃水亦止。因自覺病勢頓減,加以客居成都,經濟困難,遂自行停葯回家。不久患者鄰友來告,已康復如常。1979年7月追訪,病癒結婚,並生一子。十年來身體一直很好。
[辨證]患者雖病程頗長,因正值青春,素體陽旺。胸腹脹滿,皮色蒼黃,大便秘結,舌紅苔燥,脈沉實有力,顯然屬陽、屬熱、屬里、屬實。正所謂“大實有贏狀”。再觀之大便硬結如羊屎,幾日未行,應為陽明腑實,痞滿燥實俱備無疑。然此證又現全身肌膚腫脹,從心下連及少腹,脹滿尤甚,同時下陰流黃水而惡臭,皆為熱結水積之象,即燥熱結胸之證。由此形成陽明腑實為主,太陽結胸相兼,邪實病深,錯綜複雜之局面。熱結須峻下,積水宜攻逐,病重不可葯輕。因此,大承氣與大陷胸匯成一方,大劑猛攻之,取其斬關奪隘之力。
四逆湯案例
黃××,男,11歲。原四川成都市學生。1948年秋髮病,神志昏迷,高熱至40℃以上,腹瀉。當時正值腸傷寒流行季節,原四川省立醫院確診為“正傷寒”,某專家認為,病已發展至極期,全身性中毒過重,已屬不治之症。
[初診] 患兒連日來昏迷踡卧,面色灰白烏暗,形體枯瘦。脈伏微細欲絕,唯以細燈草試雙鼻孔,尚有絲微氣息。四肢厥逆,手冷過肘,足冷過膝,甚至通體肢膚厥冷。范老先生辨證此為病邪已由陽入陰,發展為少陰陰寒極盛,陽氣傾刻欲脫之險惡階段。急用驅陰回陽,和中固脫之法,以大劑通脈四逆湯一劑灌服急救。
處方:
川附片120克(久煎) 乾薑120克 炙甘草60克
[二診] 上方,連夜頻頻灌服,至翌日凌晨,患兒家長慌忙趕來連聲說:“壞了壞了,服藥后鼻中出血了!”范老立即回答:“好了好了,小兒有救了!”遂再診。患兒外形、病狀雖與昨日相似,但呼吸已稍見接續、均勻,初露回生之兆。宜繼守原法,以通脈四逆倍加用量再服。
處方:
川附片500克 乾薑500克 炙甘草250克
先以肥母雞一隻熬湯,另以雞湯煎附片一個半小時,再入姜、草。服藥后約兩小時,患兒忽從鼻中流出紫黑色凝血兩條,約三寸長,口中亦吐出若干血塊。這時緩緩睜開雙眼,神志開始清醒,並開口說:“我要吃白糕!”全家頓時破涕為笑,皆大歡喜。遂遵原方,再進四劑。
[三診] 患兒神志已完全清醒,語言自如,每日可進少量雞湯等流質。面色青暗。舌質淡白,烏暗,無苔。上肢可活動,開始端碗進食,下肢僵硬,不能屈伸,四肢仍厥冷。病已開始好轉,陽氣漸復;但陰寒凝聚已深,尤以下肢為甚。原方稍加大麴酒為引,再服。
上方又服一劑后,次日下肢即可慢慢屈伸。再服兩劑,能下床緩步而行。服至十三劑,逐漸康復。
患者於1978年12月26日來函說:“三十年前,范老治好我的病以後,我於1953年參軍,在部隊還立了兩次三等功,現在機械配件廠當鉗工,身體一直很好。”
四逆湯再加乾薑一倍,即本例所用之通脈四逆湯。乾薑佐附子,更能除六腑之沉寒,回三陰之厥逆,救腎中元陽,脈氣欲絕者。倍乾薑,尤能增辛熱以逐寒邪,取辛溫而散之義,加強蕩滌陰邪,迎陽歸舍之效。灌服后,患兒忽然鼻孔出血,家長驚慌失措,以為誤用姜附必死無疑!殊不知此病後期一派陰氣瀰漫,復進苦寒退熱之品,猶如冰上加霜,周身氣血趨於凝聚。此時轉投大劑通脈四逆湯,回陽返本,峻逐陰寒,冰伏凝聚之血脈為之溫通;陽葯運行,陰邪漸化,血從上竅而出,實為通脈四逆推牆倒壁之功,初見起死回生之兆,何驚駭之有?此時此刻,又抓住轉機,當機立斷,在原方大劑量基礎上再加倍翻番,姜、附均增至500克,凝結之血條血塊,均被溫通而逐出。正邪相搏出現新的突破,患兒終於轉危為安。
或問:本例患兒在半月之內,每劑附子用量250-500克,累計6500克,經過三十年之檢驗,預后良好。附子的有效量和中毒量問題,是否值得重新探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認為,上述問題如何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努力運用現代科學手段深入研究,對發掘祖國醫藥學的偉大寶庫,是一項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