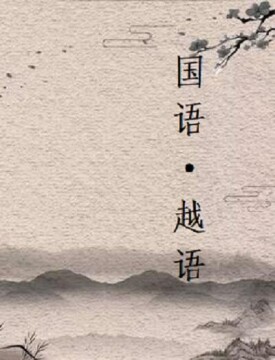國語·越語
國語·越語
《國語·越語》是中國最早的國別史《國語》中的一篇,分上下兩卷,主要記載戰國時期勾踐滅吳之事,有濃厚的黃老道家色彩。
關於《國語》的作者,自古存在爭議,迄今未有定論。最早提出《國語》作者為左丘明的是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後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們的說法,左丘明為孔子《春秋》作傳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盡……稽其逸文,纂其別說……”根據左傳所剩下的材料,又編輯了一本書,即《國語》。班固、李昂等還把國語稱為《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但是在晉朝以後,許多學者都懷疑這類說法。晉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對意見,他在《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中言:“《國語》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宋人劉世安、呂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錫瑞等也都對左丘明著《國語》存有疑問。到了現代,學界仍然爭論不休,一般都否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但是缺少確鑿的證據。普遍看法是,國語是戰國初期一些熟悉各國歷史的人,根據當時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史料,經過整理加工彙編而成。他們認為:《國語》並非出自一人、一時、一地。它主要來源於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後來經過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加工潤色,大約在戰國初年或稍後編纂成書。
國語·卷二十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后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系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
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御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
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以守之。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哺之也,無不歠也,必聞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儘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國語·卷二十一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
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忌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吾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龠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
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眾殷。無曠其眾,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后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引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可:“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
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聞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徵,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
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后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
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后則用陰,先用則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后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御,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
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與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敦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蛙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入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過。子聽吾言,與子分國。
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命工以良金範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國語》以“國”分類,以“語”為主,其寫作意圖是通過記述知名人物的言論、對話或互相駁難,來分析評價人物的高下和事迹的得失,有濃厚的黃老道家色彩。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指出:“《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本篇記述的就是越王句踐面臨敗亡、退保會稽、向吳求和以後,銳意改革,實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謀略,厲精圖治,艱苦奮鬥,終於雪恥滅吳的故事。這是我國歷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向來為人稱道,成為詩詞、小說、戲曲經常引用的素材,今人曹禺在六十年代創作話劇《膽劍篇》,白樺在八十年代創作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上演后都曾引起“轟動效應”。
本文在卷上第一、七、十、十二四個段落中,相對集中地記載了越王句踐在謀划雪恥過程中,幾個關鍵時刻的若干精彩話語和幾個重要場合里的一些巧妙辭令。圍繞著句踐的這些語辭,作者不僅質樸簡練、主次分明地?述了越國自兵敗於吳到興兵滅吳的全過程,線索十分清楚,結構頗為謹嚴;而且,作者還注意把越王語辭的語境一一交代清楚,避免了單薄、枯燥,而顯得豐厚、精彩。讀者從全篇勾勒的背景、所渲染的氣氛、所映襯的對象、所描述的行動中,來聆聽、品味越王句踐的“說”、“誓”、“辭”、“對”的具體內容,他那忍辱負重的頑強性格和體察民情的深入作風,給我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本篇在寫作上,其成功之處,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所記之言與所言之事,主次清楚,融為有機的整體;二、所記之言範圍廣泛,層次豐富,作者史識相當卓越;三、所記之言生動形象,個性鮮明,如身臨其境;四、所記之言法語巧妙,委婉得體,辭令優美、貼切。下面,僅就越王句踐的語辭描寫略加分析。
越王句踐是本篇的中心人物,他的語辭是文中載錄的重點。他在雪恥滅吳這一過程中的光輝形象主要是藉此得以顯現、突出。句踐在文中的五段語辭,每段各有側重,各有特點。一開頭的“說”,是古代的一種文體。它同“述經?理”的“論”、判斷是非真偽的“辨”,有所區別,一般只要求把問題說清楚即可,無需論證。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指出:“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員;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吳納在《文章辨體‧說》類序中強調:“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句踐的這段“說”辭,合乎規範,較為得體,力度極強。
他在敗亡之際,火與血的教訓促使他誠懇地作“自我批評”,主動向國人告罪。但意並不限此,主要目的在於“請更”(懇請變更、改革),即認真找出勵精圖治,果斷地採取厲精圖治的措施。這可以從越王在言說以後所落實的一系列葬死、問傷、養生以及卑事夫差等等行動中得到印證。“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這一說辭,生動形象,可見句踐此時心情沉痛,語調哀婉,很容易打動國人的心弦,引起共鳴。
第七段和第十段中各有兩段“誓”詞。據徐師曾《文體明辨‧誓》 類序:“誓者,誓眾之詞也。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有誓師之詞,…… 又有誓告草臣之詞……又約信亦稱誓…… ”,我們可以看出第二段中句踐“致其父母昆弟而誓”,顯然是“誓告草臣之詞”,兼具“約信”性質。這段誓詞,既生動形象(“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 ,又頗具個性色彩,“將帥……以蕃”這句話中的“帥”字兼有“統帥”、“表率”兩層涵義,文中交代句踐是如言履行、忠實踐約的,這正是他的可貴、可敬之處。第十段中的“誓”辭,是國人一再請戰、句踐許戰以後、越國將士秣馬厲兵、整裝待發之前的“誓師之詞”。在這段“誓”里,既有敵我雙方形勢的冷靜分析,又有吳越兩國知行的優劣比較,更有志行知恥的強調和“常賞”、“常刑”的號令,還有“助天滅之”的鼓動,寫得理正詞嚴,情盛語壯,顯示了凌雲的豪氣和必勝的聲勢。
如果說,前面評析的“說”和“誓”都是越王句踐主動發出,經過精心準備之後才予以頒布而公之於眾,那麼,第十段中對國之父兄請戰的“辭”謝和第的段中對吳王夫差求和地“對”答,則是他臨場發揮,即興說出,從中更可以見出句踐的思想和為人。他內心燃燒著復仇的火焰(從其它史籍中記載的“卧薪嘗膽”等等情節中可見一斑),忍辱負重、力圖興兵、蓄意滅吳,但在這兩個重要場合中,“辭”、“答”的話語卻都表現得那麼謙卑從容、婉轉動聽,不失一國君主和一代霸主的氣度和心胸。這種言在此而意在彼得巧妙措辭,相反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有力地刻畫出句踐深謀遠慮、外柔內剛等性格特徵,我們越仔細咀嚼,越覺得饒有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