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蘇生
陳蘇生
陳蘇生,上海市中醫文獻館館員,上海中醫藥大學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員。先生經常向祝師質疑問難,探求醫學之真諦,后將所錄筆記仿《內經》問難的體裁,輯成《傷寒質難》一書,首創“五段八綱”學說。
先生16歲時,經介紹至上海名幼科沈仲芳之門,從師3年,后又拜鍾符卿先生為師。1943年拜識了祝味菊先生,經幾度長談,心悅誠服地列於祝氏門下。1955年被調往中國中醫研究院進行籌建工作。1961年下放新疆自治區中醫院。先生返滬后,被聘為盧灣區中心醫院、市第一結核病院中醫顧問。1991年經人事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認為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1995年被評為“上海市名中醫”。
理法方葯的整體性是保持中醫藥體系之完整性的需要
中醫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體系,這個體系主要由理、法、方、葯4個方面有機組合而成。理是基本理論;法是治療法則;方是方劑組成;葯是藥物應用。四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理中有法,法中有理,理法的本身,又原本就是運用方葯治療疾病之臨床實踐的反映,然而它又倒過來指導方與葯的實踐。因此,要研究中醫,使中醫事業進一步發展,就必須統觀全局。如果只重方葯,不問理法,硬把理法與方葯割裂開來,是不全面的,也勢必使整個醫學體系瀕臨解體。
當然,不能否認中醫也有一方一葯的研究,有時“單方一味,氣死名醫”,但這畢竟是經驗的反應,不能顯示中醫治病的規律和對疾病認識的全貌。先生與其師祝味菊先生在《傷寒質難》中,把它稱之為“效在於葯”。實際上,中醫治病除了方葯,還有理論依據和治療法則。如黃連止瀉,這是一千年以前的經驗方,但瀉有寒熱虛實之分及兼症之不同,如果都用黃連,效果就不好。早在宋代,寇宗就指出:“今人多用黃連治痢,蓋執以苦燥之義,亦有但見腸虛滲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又不顧寒熱多少,惟欲盡劑,由是多致危困。若氣實初病,熱多血痢,服之便止,不必盡劑,若虛而冷者,慎勿輕用。”因此,必須在理論指導下,制定恰當治療法則,結合有特殊療效的方葯,才能取得更好的療效,這就是“效在於法”。如果把中醫研究單純地局限於方葯,就好比說“宰牛者是刀,而不是屠夫”了。誠然,從殺死牛的角度說,只要有刀,有力氣,任何人只要肯干,肯定辦得到,然而不掌握部位、深淺,必將事倍而功半。而若以方葯治病,不在理法的指導下根據症情的輕重、病位的淺深、體質的強弱、病邪的性質以及時令的變化去靈活運用,而只是憑著黃連止痢、大黃通便的功能而去用藥,那就不僅僅是否能保持中醫藥體系的完整性問題或是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的問題了。
中醫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逐步形成和不斷發展的。例如中風,唐代以前醫家多以“虛中外風”立論,所以其治則和方葯,都有驅風和扶正相兼的特點。宋元開始提出“內因說”。劉河間認為是“心火暴甚”,李東垣認為是“本氣自虛”,朱丹溪則提出“濕土生痰”,增加了滋陰清熱、益氣化痰等方法。清代王清任從氣血理論著手,認為是氣虛造成血瘀,故用益氣活血法,發明了“補陽還五湯”,重用黃芪,益氣行血。清後期張伯龍、張壽頤等人,則根據《內經》“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的論述,結合西醫知識,提出“氣血交並於上,衝激腦氣筋”之說,其治則強調“平肝潛陽,豁痰開竅”。隨著後世理論發展,其治則和方葯也漸漸與唐代以前大相徑庭,療效得到明顯的提高。由此可見,徒有經驗而不能提高理論水平者雖美而不彰。
先生認為,中醫的優勢與特點有許多方面,但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理法方葯的整體性。因為,中醫理法方葯的整體性使臨床的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結合,能夠充分發揮醫生的主觀能動作用。同樣一個感冒病人,地處乾燥的北方的地卑多濕的南方、年輕體壯與年邁體弱、有其他兼病和沒有兼病,所處方葯必須有所不同。但是,都符合中醫理法方葯的要求,都能把病治好,這就是靈活性。但是不管哪一種情況,有一個原則是必須共同遵守的,這就是都要“解表”,“解表”就體現了規律性。這種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結合,就體現了中醫理法方葯整體性的特點和優越性。
陳蘇生老中醫根據哮喘反覆發作,遷延難愈,不易根除的特點,認為“在病為實”、“在體為虛”,“發時當治其實,平時兼治其虛”。發作時治療強調三點:①調整肺氣。哮喘以外邪誘發為多,故多用宣肺疏表之品。但哮喘又有宿根,久病表衛不固者多。若宣散太過,則肺氣受損,當與固表斂肺之品同用,“一開一合”,共調肺氣。②排除痰濁。哮喘病根,在於痰濁。因此,排除痰濁,清除氣道障礙,保持呼吸通暢,也是治療哮喘的重要環節。③脫敏止咳。哮喘發病前多有鼻、眼瞼作癢,噴嚏流涕或咳嗽等粘膜過敏先兆,或有持續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癥狀。遇此,則當脫敏止咳。陳蘇生據此三點,自定二麻四仁湯:炙麻黃、麻黃根、生甘草各4.5g苦杏仁、桃仁、郁李仁、白果仁(打)、百部、款冬花、辛荑、蒼耳子各9g車前草24g。方中麻黃辛散,開腠理,宣肺氣,解痙平喘。但能收縮血管,故高血壓患者不宜用,又因發散力較強,故體虛多汗者亦忌。而麻黃根與麻黃作用相反,能固表止汗,兩者合用,開合相濟,調整肺氣。杏仁降肺氣之上逆,桃仁化血絡之凝淤,二者合用,一氣一血,既能順氣降逆,又能流通肺部鬱血;郁李仁滑腸下氣,滑可去著,白果仁斂肺而不斂痰,二者合用,一滑一澀,有上(痰)下(便)分消之功;百部、款冬花合用乃《濟生方》之百花膏,用於喘嗽不已,亦可治痰中帶血;車前草、生甘草,排痰止咳,調和諸葯;辛荑、蒼耳子散風脫敏。諸葯合用,共奏調氣除痰,脫敏平喘之功。
治療慢性腎病,關鍵在於“葆真泄濁”,這是先生的一貫主張。他說:“腎之功能,葆真泄濁四字盡之矣。其治療的對策,亦不外此四字而已。至於不同的兼夾癥狀,不同的稟賦體質,則隨所見而予以不同之加減。”所謂“葆真泄濁”,包含了“培本”與“祛邪”二方面的內容。葆真就是培補、保養腎臟,使受到病邪侵害之腎臟增強御邪之能力,發揮其填髓生精強筋壯骨之生理功能,使不該流失的腎之真元(如蛋白質、紅血球等)得以封固而不致外泄。泄濁就是將人體罹病以後累積瀦留於體內的、代謝過程所產生的廢殘物質以及多餘的水份等,通過二便或皮膚(汗腺)排出體外。所以,一方面著重“強腎以葆真”,一方面亦重視“泄濁以排毒”,二者不可偏廢。先生認為:“慢性腎病,大多為退行性病變,既有正虛的一面,又有邪實的一面,故純虛純實、純寒純熱者較少見。大多數患者病程長,病因病機複雜,不少病例伴有腎臟實質病變。由此而引起之腎功能障礙,往往寒熱夾雜,虛實相尋。如果膠守一法,純補純瀉,或純寒純溫,皆非所宜。特別是許多患者由於長期應用抗生素及激素,往往伴有葯源性因素,使病理機制格外複雜,在治療上每有顧此失彼之窘。”腎功能不全,並出現氮質血證的腎病患者,既不能葆真,使大量不該泄漏的有益成分(如糖、蛋白等)丟失,又不能泄濁,把體內應該排泄出去的廢料(如尿酸、尿素之類)排泄出體外。因此引起連鎖反應,出現一系列虛實夾雜癥狀。而且病程長則病變的影響面亦大,故慢性腎病不是腎臟一處有病,而是整體性之病理反應。治療對策,亦須衡量機體反應之緩急輕重,各隨其所宜,而處以針對性方案。
至於“葆真泄濁”兩方面,究竟以那方面為主呢?先生認為,腎功能不全者,雖本質是虛,但致虛之原因,總是腎臟遭受邪毒損害所致,此是“因病致虛”,病在先,虛在後,病去則虛自復。遇到如此病例,先生主張四分迥護正氣,以強腎為本,六分清熱解毒來抑制損害之源,因寒熱虛實之不同而隨機加減,務使不偏不倚,保持相對平衡。如果能持之以恆,多能取得較好的效果,此乃治療慢性腎病的“穩中取勝”之法。先生嘗謂:“治療慢性腎炎,須從整體著想,首先要為‘病腎’創造有利之內環境。不宜追求赫赫之功,但冀潛移默化,為自療機制創造良好之條件,即此便是標本兼顧之道。”為此,特創設“強腎泄濁煎”以作為治療慢性腎病之基本方。
牡蠣,歷代又有牡蛤、蠣蛤徠、古賁等稱謂。《神農本草經》載其主治“傷寒寒熱、溫熱洒洒、驚恚怒氣、除拘攣鼠瘺、女子帶下赤白;久服強筋骨……延年。”先生查閱、摘錄歷代諸家本草所載的功效計有:“除熱在骨節營衛,虛熱去來不定、煩滿心痛氣結,止汗止渴,除老血,療泄精,利大小腸,止大小便,治喉痹、咳嗽、心肋下痞熱”(《本草別錄》)。“去脅下堅滿,清熱除濕、止心脾氣痛、痢下赤白、症瘕積塊,癭疾結核(《本草綱目》)。從現代的藥理分析得知,本品含有大量碳酸鈣,故可制胃酸過多並治小兒缺鈣所致之佝僂病。另有實驗證實本品的酸性提取物在活體中,對脊髓灰質炎病毒有抑制作用,使感染鼠的死亡率降低;水提取物能使脾臟的抗體產生細胞數目明顯增多,亦即有增強免疫功能之作用。先生根據前人的經驗及現代藥理實驗的結果,結合其本人臨床實踐,總結出若干葯對。其中常用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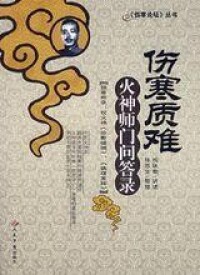
陳蘇生著作
(2)牡蠣配石膏:牡蠣咸寒,功能補腎、清熱、除驚恚怒氣;石膏甘寒,功能清熱瀉火除煩。兩葯合用,治產後多衄。蓋產後腎元本虧,倘懷煩懣驚恚怒氣,則情志過極,火動於內,迫血妄行,故易致衄。此兩者相伍,使熱清火泄神安,則若釜底抽薪,衄自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