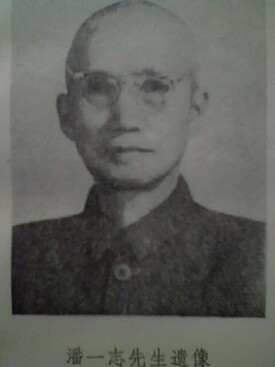潘一志
潘一志
水族史學奠基人——潘一志(1899—1977)原名益智,字若愚,水族,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三洞鄉梅山人。
潘一志出生於水族書香門第。其祖父、父親兩代開辦家庭私塾。受家風影響,潘一志三歲便啟蒙學漢話習漢字,祖父潘文秀是其啟蒙教師。十年苦讀,潘一志家學飽滿,通曉經、史、詩、文。
潘一志比鄧恩銘長兩歲,也有上北京深造的機會,臨行卻慘遭匪劫,僥倖活命。解放前,潘一志三度從軍,數度從政,多次從教,由於性情耿直,為人正派,寧可潔身自好,不願隨波逐流,數次逃官辭官;他嫉惡如仇,為民秉筆直書,告倒兩任貪贓縣長,後來遁世隱居躬耕,心中抱負難以舒展。他對自己前半身的概括與反省是:“誤入塵凡廿九秋,莫再隨波墮濁流”。荔波解放后,他真正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光明和希望。當荔波縣人民政府縣長杜介厘邀請他出山為新政權服務時,他欣然應允,並由衷吟道:“攘臂下車君莫笑,我今卻已得新生”,並將名字“益智”改為“一志”,以表白自己一心一意立志為人民服務的情懷。
解放前棄官歸農張揚中國文人精神,解放后欣喜出山為人民政權出力的知識分子,水族著名文化學者、詩人、方誌學家、水家學研究的奠基人,愛國民主人士,三都水族自治縣首任第一副縣長、政協黔南州前駐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其主要著作《水族社會歷資料稿》是現在研究水族社會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梅山學館驕子 水族山鄉情結
1899年12月25日,也就是清光緒二十五年冬月二十三日,潘一志降生於貴州省荔波縣三洞里(今三都水族自治縣三洞鄉)梅山村的一個亦教亦農的私塾教師家庭。其祖父、父親兩代開辦家庭私塾。祖父潘文秀(1837—1904)字松亭、水族名堂、別號月中居士,晚清秀才,是荔波縣邊陲小村寨的第一個習漢學懂漢文的讀書人…….。
潘一志是獨子,深受祖父祖母的寵愛,三歲便啟蒙學漢話習漢字,祖父潘文秀是其啟蒙教師。潘一志剛接受啟蒙一年,祖父即病歿,課業便由父親潘樹勛承接傳授。由於自幼深受家學的熏陶,加上潘一志記性好,又養成自覺讀書習字的習慣,因此進步很快。潘一志6歲時,其父潘樹勛認為兒子可以與其師兄們同窗了,於是他便成了青年學館里的特殊學生。同窗學長們都稱潘一志是“小人智大”。十年苦讀,潘一志家學飽滿,通曉經、史、詩、文。
1922年中學畢業,追隨辭去校長公職的張玉麟到其家鄉爐山縣(今凱里市)拔茅堡(今麻江縣龍山鄉)的“止園學校”深造。這所學校是張衷白創辦的成人青年私塾。潘一志來到“止園學校”,猶如回到自家梅山學館一樣而倍感親切。
1922年4月“止園學校”遭匪洗劫。學校被迫解散,上京大計告吹。潘一志還被土匪抓去作人質“關羊”,在匪窩輾轉月余,苦苦尋求脫身之計。一日,潘一志趁土匪慶賀打劫大捷酩酊時,深夜逃出那名叫“第五墩”的匪窩。既失上京深造良機,又慘遭匪劫“人質”虛驚,但僥倖保全了性命,卻又是潘一志的萬幸。
二、三度從軍情更迫數度辭官心欲裂
1922年10月,投筆從軍,在駐榕江縣的黔軍第二混成旅任連部書記,做繕寫工作。從軍兩個月後,潘一志發現連長陳俊超專橫跋扈,便借故請假回家不再返回部隊。1923年,他出任荔波縣城區小學教員。
1927年秋後,其父潘樹勛病逝,潘一志返家治喪。潘樹勛的學生遍布鄰近幾縣邊區,又多為水族子弟,學生和家族按水族習俗舉行“開控”。追悼“開控”之時,那些受業於“梅山學館”的遠近新老數百人湧向梅山。頓時悲聲四起,哭聲動天憾地。加上鄉鄰親友,前來奔喪弔唁者近萬。使追悼開控的現場人山人海,耍龍舞獅吹笙,鐵炮鞭炮此起彼伏,熱鬧非凡。治喪的幾天期間,梅山村外竟成了集市。出殯時,送葬隊伍延綿數里,首尾不相見。
1929年4月經省府金庫主任解仲清(潘一志的老師)介紹,潘一志與鄰村好友板南村的潘佩芝一塊離鄉赴興義覓職。途中旅居興仁縣時,潘一志回想招撫受挫事,寫下了《興仁旅次雜感》三首詩。其一云:“誤入塵凡廿九秋,局天蹐地自搔頭;來生祝我成頑石,莫再隨波墮濁流。”這首詩後來輯入《浪遊集》中。
潘一志在興義期間,時逢滇43軍軍長李小炎率部攻黔。潘一志、潘佩芝在戰亂中逃生,路遇一失散家人的老嫗,二人將身上僅有的錢物資助老婦人,便流落興仁、興義等地兩個余月。李小炎任貴州省主席后,潘一志在43軍軍部副官處任書記員。10月,黔25軍反攻,李小炎退走雲南,潘一志辭職。在返回貴陽的途中,路過剛剛停止戰事而硝煙未散的戰地,他寫下了一組詩,抒發對軍閥混戰的厭惡和痛恨之情。
11月,潘一志回到家鄉。離家才一年,梅山村卻在潘采臣、潘府珍的剿匪戰火中全部化為灰燼。
1933年8月,他組織學生排演話劇宣傳抗日,卻遭到荔波駐軍連長王遺起帶兵干涉,產生了衝突。為此,潘一志被迫外出。同年10月,在駐紮遵義的25軍教導師任營部編修,並隨隊赴正安縣剿匪。營長蔣寶藩暴戾殘忍,濫殺無辜。潘一志看到家鄉因剿匪民不聊生的慘狀又在黔北重演,他痛心而憤然辭職回家。這,便是潘一志一生中三次從軍而又處處碰壁、事事違心的經歷。
1935年3月,潘一志任荔波縣二區區員。任職間,縣長韓知重貪污成性,盤剝人民。潘一志收集材料,發動在獨山、貴陽讀書的荔波學生聯合倒韓。韓探悉內情后,欲加迫害。潘一志於8月被迫離職,親赴獨山專署告狀。10月,韓知重被撤職。
1942年,荔波縣長段叔瑜調查省視察員鞏思文在境內被殺一案,非法刑訊殺人,數十百姓沉冤入獄,一時弄得全縣人心惶惶,而真兇卻逍遙法外。潘一志忍無可忍凜然上告,段叔瑜倒台,萬民感激。潘一志卻拒絕赴省受訓令,悄然去職,又皈依教育,出任城區小學校長和荔波中學教導主任。
1943年劉仰方離職,新縣長陳企崇到任。留任的科長趨之若鶩,競相宴請陳企崇。陳蠻橫傲慢,潘一志橫豎看不慣,便不與縣長私交往來。他提筆寫下一副諷刺聯:“七尺台不算高,爬上去就目中無人,真怪!真怪;五斗米何足道,抓到手便得意忘形,實悲!實悲!”此聯傳到陳企崇耳里,陳怒目切齒要尋機報復。
《荔波縣誌稿》在陳企崇的敵視下艱難完稿,潘一志用盡平生對方誌學的研究和對荔波史料的把握,修完九卷集的《荔波縣誌稿》。當時審稿的諸位先生認為此部縣誌是歷來荔波縣誌中史料最詳實,編排最合理,價值也是最高的一部志書。審稿結束,正待送省印刷出書之際,日軍大舉進犯貴州,印刷事擱淺,成為潘一志的終生心病。
1944年11月27日,日軍由廣西攻佔了黔桂邊境的黎明關,進入荔波縣境。縣長陳企崇帶著保警隊聞風棄城逃往榕江縣。一時全縣行政中斷,潘一志視之不忍,便偕同有識之士李伯純等人組織市民疏散。12月3日縣城淪陷,這一天,潘一志無暇顧及剛產後不幾天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兒子,組織人撓亂日軍的追擊路線。至夜,方擺脫日軍的尾追。脫險后,潘一志聯絡各階層人士,於12月7日擬議成立荔波縣自衛委員會保土衛家。后因當日縣城遭美機轟炸,接著日軍於12月18日退回廣西,自衛委員會未正式成立。但其言行在民眾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45年3月,日軍退出荔波縣境三個月後,縣長陳企崇為推卸棄城之責,上報荔波縣遍地皆匪。新任縣長劉琦不知情,也報請大軍圍剿。一時間,第9軍一個營,第19軍一個團、另三個營,第20軍一個營組成剿匪大軍雲集荔波,開赴三洞、九阡一帶水族聚居區,焚村掠寨、破洞攻卡,百姓遭殃。真正的慣匪石子輝等人卻逃往深山,躲過應有的懲罰。獨山專員周希濂邀潘一志進山招撫。為避免戰火殃及百姓,潘一志受命於危難之間,以其大智大勇,隻身深入虎穴,苦口婆心曉以大義,幾經周折,招撫成功,匪患平息,大軍撤離。10日,潘一志方返回縣城。14日,赴榕江縣任縣府秘書。7月離開榕江任獨山專署第一科科長。
1947年元月,潘一志毅然棄職。2月,他兩袖清風,“千里歸囊清似水”地回到家鄉。由於當時政治黑暗,官場腐敗,他三度從軍不順心,數次參政不得志,因此他決心隱居於荔波縣城北15華里的擦耳岩深山之中,創辦農林場,開荒躬耕。
1947至1951的五年間,潘一志在自己的農林場內推行改造社會的農林實體計劃。此時的潘一志心情舒暢,幹勁十足,他曾兩次拒絕荔波縣長周紹伊和獨山專員陸蔭楫的歸政誘逼。“名利逼來急,避之恐不及······世人避役我避官,世人笑我是寒酸”。這是他以詩作來形容自己當時逃避官職如逃瘟疫般的實況。潘一志發誓“不與人間爭名利,偏向荒山刮地皮”,並用“此生已作林家婦,恨不相逢未嫁時”詩句當面回絕舊政邀請。隱居的5年,既是潘一志心境最為舒坦的5年,也是他詩歌創作最豐碩的5年。後來的《歸農集》共有73首詩作,全面反映他自己“開幾畝荒山與天爭利,養兩間正氣隨地皆春”的憤世並不厭世,悲怨並不悲觀,退隱並不退縮的隱居生涯。
三、“益智”更名為“一志”今生有幸慶新生
1949年12月,潘一志過去的學生覃傑和荔波進步人士潘文興等青年,組織游擊隊攻佔荔波,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接管。潘一志對此壯舉投以了極大的關注和熱情。1950年2月,荔波縣人民政府杜介厘縣長信函邀請潘一志出山。他因農林場正值發展的關鍵時刻而謝絕邀請,潛心躬耕。3月,國民黨廣西宜山專員陳與參(荔波人士)組建黔桂邊區“反共救國”軍,佔領了荔波縣城。陳與參部有不少潘一志的學生,陳派周文德恭請他出山任職,遭拒絕。此時戰事又起,潘一志利用農林場有限的積累,盡量的收留因戰亂逃至擦耳岩的城中難民。
1951年1月,荔波第二次解放。同年3月,潘一志接受人民政府的第二次邀請,出山參與新政權的建設工作,任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駐會副主席。
出山後的潘一志通過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系統學習,感悟到自己的局限,便將農林場交給了人民政府。出山之際他以興奮的心情,賦詩唱新生。《新生集》的開卷詩篇寫道:“五年避世樂躬耕,伴鶴盟鷗斷俗情,攘臂下車君莫笑,我今卻也慶新生。”同時他還廢棄了原名“益智”,取用“一志”為新名,以此表達自己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志向。
1952年,潘一志的二女兒潘懋祉被保送到北京醫學院攻讀醫學,潘一志心緒極佳,利用工作之餘以新的觀點修訂《荔波縣誌稿》,后更名為《荔波縣誌資料》(七卷本),1954年2月,縣誌資料脫稿。
自1956年之後,他決心深入研究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於是便開始收集整理水族各方面的資料,利用業餘時間著手編著《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同年赴都勻專署參加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組建籌備工作。8月,當選為第一屆黔南州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人民委員。年底,參加成立三都水族自治縣的籌備工作。
1957年1月,三都水族自治縣成立。原屬荔波縣的周覃區、九阡區併入自治縣。潘一志當選為第一副縣長。同年2月至5月,他參加貴州少數民族參觀團到華北、東北、華中等地區參觀考察。3月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4月,他被選為政協黔南州第一屆副主席。
1960年,其妻兒才遷到自治州首府都勻,相對穩定的家庭生活才回到潘一志身邊。此時雖是國家困難時期,但由於夫人在身邊,潘一志便利用這相對安定的時間,用當時只能找到的馬糞紙和毛邊紙自己動手刻寫、油印30萬字的《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以及《水族潘姓源流考》、《水族源流考》和集《浪遊集》、《歸農集》、《新生集》三集合一的《新舊人生觀詩稿》等書。
1963年7月,《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油印成冊,潘一志將詩書稿分送國家、省圖書館和有關單位及個人。
1964年12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65年應各方面的要求用打字紙重新刻寫油印《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1966年第二次油印工作剛結束,由於文化大革命開始裝訂工作被迫終止,隨之書稿被造反派沒收。同年9月1日,潘一志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掛黑牌遊街批鬥。家中物品被查抄,藏書、文獻和手稿資料被焚毀。在長達5年的審查中,被逼迫寫下20餘次約10多萬字的檢查。
1968年拖著病體被驅趕至由監獄改造而成的州革委“甘塘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1年,潘一志向州革命委員會申請索回第二次油印的《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來裝訂,未獲允許。9月,子女返家探親,潘一志得知兒子潘茂金收藏有他念念不忘的書稿時,欣喜若狂,擠出不多的生活費,買茅台酒慶祝心血成果僥倖存世。並叮囑其子收好書稿千萬不可再輕易示人。
1976年,“四人幫”倒台,中國政治剛開始呈現開朗之勢,就不斷有學者造訪潘一志了解水族情況。1977年夏天,潘一志突然失語、癱瘓,經診斷為腦血栓。11月,他的病情好轉,可言語,也可行走,便寫信叫在貴定縣工作的兒子將書稿帶到貴陽。當潘茂金將志書、詩集稿一應擺在潘一志面前時,他雙手顫抖,老淚縱橫,感慨萬千。他撫摸書稿,言及很想再回到隱居地的荔波擦耳岩去,一副對往昔懷念不已的特殊神態,令身邊的家人一時不知所措。
1977年12月4月,因病情突然惡化,經搶救無效,潘一志懷抱著浸透自己畢生心血的詩書稿離開人世,終年78歲。
潘一志為水族人民留下了寶貴的人格精神財富和珍貴的文化歷史資料。1980年,三都縣民族文史研究組成立后,分別於1981年、1984年將其遺稿《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潘一志詩詞稿》等鉛印問世,聊慰先生九泉之下的英靈。
這是王鴻儒先生對潘一志的紀念性的文章,幾乎概括評價了潘一志的一生:四十年前,當我還在黔南荔波縣中學任教時,就常常聽人說起潘一志。那裡是潘先生的故鄉,流傳著不少關於他的傳說。這些傳說為我描繪了一個喜作古體詩詞的水族文人,一個關心民瘼、善良而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一個拒絕官場、避世躬耕的隱者,一個充滿了傳奇人生的奇人……那時候我的同事里就有潘一志在民國年間從教時的學生,縣城有他住過多年的故居,遞送過辭呈的縣府衙門,他散步時曾經走過的回龍廓,與友人們聚會時互相唱和的月波亭。沿城郊那條碧綠的樟江往西南行去,十裡外的朝陽小學,他曾在那裡當過校長,而在城北的大山裡,有他隱居、耕種了整整五年的擦耳岩小鹿寨……
那時候潘一志先生健在,但已調至州政協工作,任副主席,因此我無緣拜會這位長者。他是作為一個民間口述史中的人物而存在的。我知道一個人的生命要在民間延續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往今來,見諸官修史志中的人物真不知幾千幾萬,但能活在民間口碑中的又有幾人,引“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臧克家紀念魯迅的詩《有的人》中所採取的,其實正是這種民間的立場。不過民間口述史也有它的局限,一是隨著歲月的推移,許多事會漸漸在傳說中變形;一些寶貴的史實,也會隨著知情者的辭世而淹滅。所以那時候我就想,哪一天能看到一本潘一志的傳就好了;1977年,潘一志先生不幸病故后,我的這種希望變得更迫切。後來我聽說黔南州圖書館的馮舉高先生正在做這件事,並且默默地為此耕耘了將近10年。那時候我真的很高興。現在,這本《彎路直走:水族學者潘一志的真實人生》終於送到我手裡,懷著好奇心我開始讀這本書稿,沒想到一拿到手裡就放不下了。我想用我真切的閱讀經驗告訴讀者,這本書真的值得一讀。作者在這本書里,用他流暢而細膩的文筆,為我們寫出了一個真實的潘一志,一個曾經生活在我們身邊,看得見,摸得著,與常人一樣生活著、卻又特立獨行的潘一志!
潘一志生平的感人之處,在我看來,正在這“特立獨行”四字。這是儒家思想的精粹。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君子“精神。君子與小人,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春秋時代,既是道德劃分的尺度,也是一個人社會地位及身份的確認,所以才有“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說。(《左傳·寢公八年》)到得孔子手裡,他才第一次賦予“君子”以全新的道德內涵,《論語》中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那就是說,人作為本體存在具有一種神聖性,道德上的完滿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追求。因此判定一個人是否是“君子”,首先在於人的內在仁道精神,而不是已定的社會身份地位。如孟子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王陽明所說“滿街是聖人”。說的都是道德可以憑一己之力去完善。完善道德的途徑就是“仁”,如孔子所說:“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潘一志在舊社會所經歷的種種,當兵不染行伍之鄙俗、暴虐;為團總則置生死於度外,招撫土匪,以求一方平安;做教師則受學生愛戴;當校長即備受教師擁護。當日本兵入侵荔波,政府官員聞風而逃,他則聯絡鄉紳及地方名士,組織百姓疏散;為獨山專員做押運宮,當得知所運軍糧原系專員違法倒賣,即憤然棄職而去。“他當宮又愛告官,是一個吃官飯又砸官碗的人。”他最後看透了官場的腐敗同險惡,即隱居深山墾荒自食。荔波解放,感於縣長杜介厘親自人山勸說,遂出山參加革命。投身土改,一時難以發動群眾,他竟主動要了一個“地主”成份,搞得朋友抱怨,家人受盡委屈。因對極左政策不滿,他曾提出辭職;辭職不得,見左風愈演愈劇,百姓日子難過,又忍不住再上諍言。潘一志所言所行,無不是應了君子“仁者愛人”的價值標準,因為不隨流俗,所以特立獨行。不幸他生當濁世,知己者少,同道者更少。在別人看來,他的許多行為方式,都不可思議,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兒女都不理解。最後在文革中受盡凌辱,積怨成疾,抱恨而亡。“彎路直走”,舉高將這本傳記文學如此命名,我想正是他要寫出潘一志特立獨行的立意之所在。
潘一志這種特立獨行的仁者之風,發端於水族傳統的道德觀念。水家人質樸、務實,非常善良,但也十分執著。作為歷史上一個較小的族群,能與周邊的漢族,布依族長期和睦相處,這同水族寬容、善於忍讓的性格有關。他們不想惹事,但如果事來了,也決不會輕言退讓。清末咸、同年間,潘新簡領導的水族農民起義即為一證。我的不少水族同事與學生即有此種看似相悖、實則統一的性格。不用說這種民族精神自幼即養成了潘一志強烈的民族自尊與自強意識。另一方面,他從小便接受了漢文化影響。他三歲發矇,讀了十六年私塾后,考入都勻十縣合立中學。他的老師里既有受過儒家“四書五經”浸染至深的秀才、碩儒,也有留學日本歸來、受“五四”新文化影響的新派教師。他的性格的形成既是水族文化與漢文化交融的結果,也是傳統與現代合力熔鑄的結晶。在他看來,民族要發展,就應具有正視本民族文化優劣的博大胸懷,不僅要勇於揚棄落後的方面,更要勇於吸收外族先進的文化。這就是費孝通先生生前主張的“文化自覺”,而潘一志很早就具有這種自覺性。他的…生特別是在中年以後耗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完成的《荔波縣誌稿》與《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在傳承、發展地方及民族文化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勞。他一生創作了350餘首詩詞,不僅記錄了他的苦樂人生,表達了他對理想人格的追求與遭際,不少詩詞還是20世紀水族地區社會生活的實錄。這一切正是潘一志文化自覺性的充分體現。潘一志之在水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除了他高尚的人格精神,也同他為發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業做了大量工作有關。這本書開篇即寫潘一志骨灰回歸故里的安葬儀式,那種盛大、隆重的氛圍中所透露出來的深刻的悲涼,正是水家人對本民族這一傑出文化人不幸早逝的無限惋惜與懷念。
特立獨行的潘一志,不見容於舊社會這容易理解;可是為什麼在新社會他仍然命途坎坷?這就要說到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間產生的衝突了。當代著名的美國學者愛德華·w·薩義德認為知識分子至少具有下列涵義:“知識分子為民喉舌,作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及見解;知識分子的言行舉止也代表/再現自己的人格、學識及見地。”(《知識分子論》),這與中國古代的“土”的涵義庶幾近之,孔子說:“士志於道。”又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遠乎!”可見中國知識分子素有維護道統的責任感,這個“道”,即儒家的人格理想“仁”。通俗言之,可以視為我們今天說的大眾的利益,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也包括個人人格的尊嚴。因此從古至今,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守住自己的信仰與追求,彰顯人格精神,常常抗禮王侯,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潘一志特立獨行的性格正是為著守護他自青年時代起即立下的報國理想、使本民族自強的願望,也是為了守護他的人格精神。新的社會一度讓他看到了實現理想和抱負的可能性,這是他離開擦耳岩的主要原因。但是他畢竟是一介文人,不懂得社會制度的改變不可能讓二千年內長期孕育,形成的封建政治文化一下子消失,文化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這種封建政治文化傳統要求整齊、劃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不容許有超越甚至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任何思想存在,特別是到了以一人之思想為所有人之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特立獨行者必然成為眾矢之的。這樣,潘一志先生在都勻成為第一個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就毫不奇怪了。曾經有過一種理論,道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知識分子一定要附在某個階級某個黨這張“皮”上。皮毛理論的要害就是要打掉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以製造順民和奴才,讓知識分子放棄對人類知識與自由的增進,以及對社會重大問題的思考,對精神、意義、價值取向的追尋。這就是潘一志這樣的人在解放后何以仍然會處處碰壁、為守住知識分子道義與責任而不得不付出慘重代價的根本原因。
應該感謝《彎路直走》的作者,他站在民間立場,以廣泛的採訪,詳實的資料,深入的研究以及生動的敘寫為潘一志這一碰壁經歷作子再清楚不過的再現。可悲的是潘一志在看清了一些事情之後,他連解放前那樣急流勇退、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隱者都不可得。他終於積怨成疾,病中還在想著擦耳岩,甚至在得知擦耳岩已荒蕪不堪的消息后,他流出痛苦憂傷的淚,再也沒有醒來。如果他更早一些,比如第一次遞交辭職報告的50年代,他就回到擦耳岩,他是不是會生活得更輕鬆一點或者他至少是不會在“四人幫”剛被打倒的時候就故去的——可是歷史並沒有“如果”;就算他當時真能辭職,在私有財產公有化的年代,擦耳岩還是他的嗎?他還能回去嗎?……
潘一志辭世后是被水家人迎回生養他的故土去了,但是潘一志並不只是屬於水家人的,他一身的特立獨行所彰顯的知識分子品格,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一份寶貴的遺產,所以我們才說,潘一志是永遠的。儘管我們在他的故鄉,暫時還看不到潘一志紀念館,也看不到他的一尊塑像,但是這館這塑像是屹立在水族人民心上的,永遠,我相信。潘一志奮鬥不息的一生,正如臧克家詩中所寫,他“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是一個“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野火燒”的人。正因為這樣,我想在結束這篇“序”的時候,借用臧克家這首詩中的最後兩句,敬獻給這位精神永在的水族學者: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
群眾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水族文化的研究
1925年,和三都接壤、有水族分佈的都勻,由竇全曾修、陳矩等纂的《都勻縣誌稿》在卷五“地理志·風俗·夷文”部分載:“夷族無文字,惟水族諏吉占卜有專書,至今傳習其中,謂之水書,大氐古篆之遺,第相沿日久漸多訛失耳”,並錄了97個水族文字,以略證“夷漢交通之跡”,提出了“水書”的概念,而且認為水族文字“大氐古篆之遺”的觀點。
1940年,許用權編、胡羽高纂的《三合縣誌稿》一的卷四十一“民族”一節中說:“今日貴州全省除大定有夷文外,土著中惟水家有文字,……而水家文字中除天干地支及象形文字外,居然有文武、輔弼、廉貪等字,假使當日無文化思想、政治組織,焉有此等深切會意、形意之文字”,並收錄了165個水族文字及“水文六十甲子”表。在表后又說:“右列文字,傈三合東鄉水族所用,為醫巫之秘籍,俗謂之反書,又謂之水家文。在三合與荔波接壤之十六水多用之。……其文似古籀、小篆。”在此提出水族文字有象形文字,似古籀、小篆,叫做水家文,除有文武、輔弼、廉貪等漢字外,也有會意、形意之字,有醫、巫兩種秘籍等觀點。
1942年,漢族學者張為綱先生到荔波水族地區進行社會調查,后在當時的《社會調查》第三十六期上發表《水家來源試探》一文,從水家的姓氏、文字、迷信、“歌書”四方面證明“今之水家。蓋即殷之遺民”。關於水族文字,他在文中說:“水家文字,俗稱‘反書”’,“所以謂之‘反書’以其字體多倒書”,“細考其形,竟有與武丁時期之甲骨文字極為近似者”,首次提出了水族文字與武丁時期甲骨文極為相似的觀點。
1943年,漢族學者岑家梧教授到荔波水族地區進行社會調查,搜集到水書抄本45種,後來在《西南民族文化論叢》上發表《水書與水家起源》J一文,從水書的種類、用途、內容舉例、文字結構、來源傳說等去觀察水族之來源,還附有“漢水書對照表”。他認為“水書字跡與刀刻的甲骨文及金文,頗多類似”,
“至少水書與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間,當有若干姻緣關係,亦可斷言也”。岑家梧先生比較系統地研究、介紹了水族文字。
這一時期有關水族文字的研究工作不能不提到潘一志先生所做出的貢獻。潘一志先生是研究水族古文字第一個有成就的水族學者,也是解放前後水族古文字研究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人物。
潘一志先生對水族古文字的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3年下半年,潘一志先生被任命為荔波縣誌整理委員會副主任,主持縣誌的編纂工作。他很快擬出了工作計劃,寫出了十七條工作規則,舉薦了有識之士,把工作開展起來了。他決定對荔波的山脈、河流進行一次認真踏勘,還調查了周覃、三洞、九阡等地歷史上幾次農民起義的傳說、遺物、遺址。由於潘一志先生負責大事志、民族志、人物誌及文化教育部分的纂寫和全志的文字統籌工作,任務是很繁重的。特別是纂寫“氏族志”困難更多。當寫到“民族文字”一節時,他為了能對水族文字和水書作全局、準確的介紹,還特地去水堯在家傳授“水書”的歐海金家作了調查和探討,一住就是兩個多月。歐海金分析了水族文字的象形、會意、假借及反書等造字規律,潘一志也講了漢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歷史情況。二人還就“水書”在手抄、口傳過程中留下的錯訛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潘一志先生編纂荔波縣誌期間,恰逢岑家梧先生來荔波考察,由潘一志先生接待。這從岑家梧先生於“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給潘一志先生的來信可以得到證實。信的全文如下:
潘副主任:
目前赴貴處調查,諸承厚注,銘感實深!返校后,以課務兼忙,未及函謝,罪甚罪甚。近維起居清嘉,著書有得為頌!關於水家來源問題,胡羽高、羅香林、萬大章諸氏只追溯至唐宋二代,弟現於反書中發現若干字體及文法結構與殷代甲骨文相合,足證水家文化淵源甚遠,似可追溯到商代也。刻正探究水家文化與殷人文化之關係,一俟成稿,當即呈正。尊作志稿想已殺青,前承允抄荔波各族人口數目及地理分佈見示,敬乞早日寄下,以便參考。前隨函奉贈《我們的國族》一冊,至祈鑒收為荷!
余不一一,此請著安。
岑家梧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這封信是岑家梧先生離荔波后一個月後寫給潘一志先生的,從信中看出:一是感謝潘一志的熱情款待,大力支持,故有“諸承厚注,銘感實深”,“未及函謝,罪甚罪甚”之言;二是岑家梧此次來荔調查雖已有水族文字“若干字體及文法結構與殷代甲骨文相合”的看法,但文章尚未發表,故說“一俟成稿,當即呈正”;三是岑家梧知道潘一志時任荔波縣誌整理委員會副主任,正在抓緊編纂縣誌,所以稱潘一志為“潘副主任”並說“尊作志稿想已殺青”,還說“前承允抄荔屬各族人口數目及地理分佈見示,敬乞早日寄下,以便參考”,還“隨函奉贈《我們的國族》一冊”供潘一志參考。由此可見岑家梧先生和潘一志先生相互支持又各自獨立地進行著水族古文字的研究。岑家梧先生的成果即後來發表的《水書和水族來源》。
水書為什麼稱之為“反書”?潘一志先生寫道:“據說它與漢人所用的通書是相的,所以漢人叫它做反書”。這種對“反書”的詮釋至今僅見於此,存此一說。1958年後,潘一志先生任黔南州政協駐會副主席期間,在都勻利用工作之餘彙集了正史、方誌、碑碣、檔案文書、民間傳說和私人著作中有關水族的資料,開始編纂《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於1959年底完成初稿,共30多萬字。在該書的第六章水族地區歷史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文化藝術中的“水族文字”一節,潘先生這樣寫道:(水族)“相傳有一種鬼師作擇日佔卜等迷信之用的一百多個古老文字,用這種文字寫的迷信書,叫做‘水書’(譯意)。書中所用的天干、地支、五行生剋、八卦六爻、二十八宿等等,與漢族的通書大致略同,而其字體則甚古。他們以前不用毛筆寫,是用竹片或小木椏燒炭來刻劃在較硬的夾紙上,所以其字跡與用刀刻的甲骨文及金文類似。水書中的文字、倒置斜置是很多的。又有些字象秦的小篆體……在解放前,曾看見清光緒年間的水書抄本,其字較古。
目前所看到的都是清光緒時代以後的,多用毛筆寫,有些字增加,形式也有些逼近今體漢字,但結構仍保持原狀。……追溯往古,也是從說明水族文化與漢族的淵源是很古的。”還附有“漢字對照表”,共錄有200個水族文字,其中有45個字有異體字。
在這裡潘一志先生一方面肯定地指出水族文字淵源很古,有的似甲骨文、金文,有的似秦時的小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清光緒以後,水族文字還在變化之中,字數在增加,形式逼近今體漢字,說明了水族文字是一直在民間運用的“活”的文字。此外,他還指出,以前水族文字的書寫是用竹片、小木椏燒炭在較硬的夾紙上刻劃而成的,所以字跡與用刀刻的甲骨文、金文相似。水族文字的這種刻寫方法現在已不多見了。更難得的是他記錄了許多水族文字的異體字。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水族文字的基礎和寶貴的資料。
編纂了《荔波縣誌稿》、《荔波縣誌資料》
潘一志先生的成果則集中體現在1944年10月編纂完成的《荔波縣誌稿》中。
在《荔波縣誌稿》卷二“氏族志”中潘一志寫道:“荔波所有文字,除漢字外,水家另有一種文字,俗謂之反書。其筆畫多與古象形文類似”,“或為秦以前之另一體文字”,又說“本縣水家文字,與古象形文類似者頗多,亦可作研究民族源流之一助”。書中還附有20個水族文字與象形文、篆文、“古文”的比較表。此外,還列有“漢文水文對照表”,共收入130多字,其中包括不少水族文字的異體字。
在第二編民族資料第二章分述中,專列了第二節水族。其中包括:一是戶口及姓氏分佈情況;二是風俗習慣(含節日、婚嫁、喪葬、迷信等);三是年曆;四是反書;五是文字共五部分。在“反書”一段中,潘一志先生指出:“反書是水族婚喪、起造、擇吉日以及看病用鬼、割蛋判凶吉所用的一種迷信書……,但本族人稱之為‘ㄌㄜ’(勒去聲,是書的意思),‘ㄙㄨㄟ’(水陽平,是水族名稱),即水書的意思”。講述了水書在水族民間的廣泛用途,解釋了水語讀音和本意,即後來常說的“泐雖”。在“文字”一段中,潘一志先生說:“水族文字即反書中所用之字,其筆畫多與古象形文類似”,附有《漢水文字對照表》,共收入145個字,其中包括41個水族文字的異體字。
1953年,潘一志先生利用工作之餘,著手修訂《荔波縣誌稿》,將原稿中的內容改編為地理資料、民族資料、社會資料、歷史資料“四編”,繼續對水族文字進行研究,於1954年2月完成《荔波縣誌資料》初稿。潘一志先生編纂的《荔波縣誌稿》、《荔波縣誌資料》等著作,已經成為研究荔波地區及水族社會、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的重要的寶貴資料,是相關研究人員手中必備的工具書。而其中所包涵的潘一志先生研究水族古文字的成果和大量調查資料,也是現在研究水族古文字必讀的文獻資料。在已知的研究水族古文字的近150年的歷史過程中,潘一志先生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其成果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水族文人潘一志就是一生受孔子思想影響的代表人物。潘一志一生歷經磨難,但孔子積極有為的思想始終佔主導地位,孔子重視道德價值和歷史經驗的思想在他身上充分體現,儒家思想構成了潘一志一生的精神支柱。
潘一志既是水族史學奠基人,又是優秀的水族兒女,他是水族人民群眾中少數的走出水族大山裡村寨的一個有文化和有思想的學者,潘一志一生經歷坎坷,矢志學習洗腦知識新東西,思想進步的很快,又是一位很有品德而不得意的水族學者,潘一志是民國時期的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佼佼者之一。
梅山學館是潘一志的啟蒙之地,也是他走向外面更廣的世界的跳板。當潘一志選擇從梅山學館走出去看世界的時候,已經註定了他必定投身於紛繁複雜的新社會政治與新2006年,貴州民院·貴州水書文化研究中心升格為貴州水書文化研究院,並獲得省編委的編製批文之後,將出版《水族學者·潘一志文集》列為首選課題,並得到潘一志先生傳人原黔南州政協主席潘茂金的大力支持。2008年中秋節前夕,潘茂金先生將出版委託書專程送抵貴州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黨委副書記、貴州水書文化研究院院長唐建榮教授,對潘茂金先生慷慨支持表示衷心感謝!唐建榮教授、馮舉高先生分別為本書作序。
貴州民族學院是全國唯一設置水族語言文學本科專業,並獲得教育部批准招收民族語言文學·水族語言文學碩士研究生的大學。該書出版對於水族語言文學的教學科研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水族學者·潘一志文集》由《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潘一志詩詞》彙集而成。這是潘一志先生為社會、為水族人民留下寶貴豐厚而永恆的精神財富。中國55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悠久而可圈可點的歷史,而且不乏學富五車的賢達。但是,當我們環顧四周,能像潘一志先生那樣數十年孜孜不倦耗盡心力為本民族撰寫出一部30餘萬字歷史資料稿者,卻鳳毛麟角。尤其對於弱小的水族,既沒有通行文字記載自己的歷史,而只有漢文獻語焉不詳或觀點偏頗的史料,更彰顯《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的分量與作者的人格魅力。
潘茂金先生卸任黔南州文聯主席之後,摒棄其他工作,數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先父遺稿整理的工作中,為書稿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對照先父數種版本手稿,校正內部鉛印本千餘處的遺誤;用手寫板在電腦上逐字逐句錄入全書;重新繪製書中各種插圖;為書稿增加了不少註釋;搜集珍貴的歷史照片;糾正因歷史原因,作者違心屈從階級鬥爭為綱理論的一些論述或提法等。可以毫不隱諱地說,如果潘茂金先生沒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傾力奉獻精神,如果潘茂金先生缺乏家學淵源與學術功底,社會也難看到理想校勘版本的《水族學者·潘一志文稿》。這是梅山學館的遺韻,這是潘一志先生精神的延續,這是水族的幸運,這是水家學研究的幸運!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重視歷史傳統在水族知識分子身上的閃光。知識的大潮流之中,也因此造就了一個水族人的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