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於民
藏富於民
藏富於民是指中國古代主張國家減輕賦役徵發,通過藏富於民的方式來發展生產、穩定國家財政收入的經濟思想。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說: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國語·齊語》)主張國家徭役的徵發與賦稅的課徵要適時適量,以此來富民富國。
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裡,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國家財稅收入速度遞增,遠高於GDP增幅,遠高於民眾收入增幅,這顯然是不正常的。長久下去,財富越來越集中在政府手中,經濟增長的好處越來越由政府享受,國愈富,民眾收入在不能保證同等增長的情況下,不公平感就會愈強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應是每一個公民能夠過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國富”之根本目的還在於“民富”。“國富而民窮”從來不是一個社會得以和諧健康發展的根本之道。
金融危機影響所至,國際市場急劇萎縮,出口貿易嚴重受阻,多年來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猛然間倒下了一匹老馬。拉動經濟增長,由“三套車”變成二馬並馳,復甦寄希望於投資與消費。投資方面,中央開出4萬億救市大單,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同時,千方百計刺激居民消費,如“家電下鄉”,各地派發的消費券等等。
中國古代思想家有關封建國家與人民之間物質財富分配關係中主張藏富於民的一種經濟思想。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質財富視為實現治國安民的基本原則。自先秦以來2000多年間,富民思想在中國思想界不斷出現,它所反映的階級內容與時代意義,亦隨時代的變遷而有不同。
中國富民思想的淵源極早,《尚書》中有“裕民”、“惠民”的觀點,《周易·益》有“損上益下,民說無疆”,都把重視人民的利益視為統治者的德政。至春秋戰國時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階級關係的變化,出現了儒、墨、道、法各學派思想家,他們從各自的政治需要出發,從不同角度闡發了富民思想。

儒家富民學說
墨家從小生產者求生存、求發展的願望出發,反對虧人自利,要求在互愛互利中求富。墨家認為求富的途徑在於自己的努力勞動:“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墨子·非命下》)。他們反對統治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辭過》)。要求厲行節約,減輕人民負擔。但墨家在富民與富國關係上,不同於儒家,他們主張“官府實而財不散”(《尚賢中》),要求充實官府而不是藏富於民。認為國家“倉有備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謂“官府實則萬民富”。墨家把小生產者的幸福,寄託於王公大人的雨露陽光,幻想統治者能節用去侈,“愛利萬民”(《尚賢中》),“加於民利”(《節用》),給人民以安居樂業的條件。
道家倡無為,一切因順自然,反對統治者干涉人民的經濟活動,主張“我無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讓人民自由牟取財富。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對人們追求財富的,認為“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因而要求人們“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老子》第十九章),使人民“無知無欲”(《老子》第三章),過儉樸的生活。道家認為,雖然客觀上財富不多,但只要主觀上自我滿足,就算是富足,所謂“知足者富也”(《老子》第三十三章)。道家的富民以寡慾知足為前提,實質上是在生產很不發達狀態下相對於普遍貧困而言的。
法家以富國立論,但早期法家亦多重視富民。如管仲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是富國與富民兼重。《管子》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治國》)。至商鞅,雖有“令貧者富”(《商君書·去強》)之說,但富民並非其目的。及至韓非,提出“足民何可以為治”(《韓非子·六反》),從理論上否定富民的必要。從根本上說法家並不認為富民是可取的,"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管子·國蓄》),“甚富不可使”(《侈靡》),認為民太富,不利於統治。因此主張“民富則不如貧”(《山權數》),“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法家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把富民看作只是從屬於富國所需的一種手段。
西漢時賈誼綜合富民與富國思想,提出國家與人民都需積貯的理論。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繼承先秦儒家不與民爭利的思想,要求取消鹽鐵官營。他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張,反對官僚地主兼并農民,倡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漢書·董仲舒傳》)的均富思想。司馬遷亦反對統治者與民爭利,主張因順人民自由求富的願望,發展農工商虞,達到“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史記·貨殖列傳》)。桑弘羊繼承管仲、商鞅關於民富不可使的觀點,認為民饒則偕侈,富則驕奢,因而反對富民。東漢時王符提出農工商皆有本業,均可富民的論點。荀悅則認為朝廷以輕稅富民,實際是惠利豪民而非農民,說明當時的富民階級主要是豪強地主。自魏晉隋唐至明清,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由鼎盛而衰敗,階級關係也有新的變化,富民的階級內容,更突出了中小地主及富裕工商業者與大地主階級的矛盾,因此,富民思想也更具體反映了這一矛盾及不同富民階層的要求。
輕租稅的要求十分突出。如晉代傅玄要求減輕地租,以發展生產,促進民富。唐初魏徵(580~643)力主“薄賦斂,輕租稅”(《貞觀政要·君道》),楊炎倡兩稅法,以資產多少為課稅標準,意亦在減輕貧者負擔。李翱(772~841)著《平賦書》論述輕斂有利於生產,使“地有餘利,人日益富”。杜佑指出重斂使民流亡,從而國家稅源枯竭,唯薄斂能富民安國。他們都以反對厚斂重租作為富民的首要問題,反映了當時租稅困民之嚴重。在貧富關係上,唐代也出現了為富者辯護的思想。如柳宗元(773~819)說,“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柳河東集·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李覯以《周禮》為據,認為實行一夫百畝制,就能使人儘力,地盡利,從而國實民富,王安石力主打擊大地主、富工、豪賈的兼并,維護中小地主及工商富裕階層的利益。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指責王安石行新法是“奪民”(《宋史·本傳》),“破富民以惠貧民”(《欒城集》)。他們所稱的富民,主要是大地主及工商豪富。葉適抨擊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認為富人實有益於貧者,他頌揚富民“為天子養小民”,是“上下之所賴也”(《水心別集·民事下》)。
為富民辯護的思想更為突出。如丘濬說:“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大學衍義補·蕃民之生》)。王夫之把損富濟貧看作“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宋論》),他認為“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黃書》),“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讀通鑒論》)。明代許多士大夫公然全力為大賈富民辯護,正反映了大賈富民在當時的重要地位。至清代,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激烈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反映在富民思想上,地主階級思想家,不論開明或保守者,都十分強調保護富民,只是對於富民的階級內容,前者主張包括工商富民,而後者則限於地主。在國富與民富的關係上,則主要承襲傳統的“王者富民”論,如唐甄、魏源、包世臣等都強調“富在編戶,不在府庫”(《潛書·存言》)的觀點,在理論上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16、17世紀時荷蘭的國債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時荷蘭國債摺合人均1.6公斤銀子而西班牙國債僅摺合人均0.6公斤銀子,但前者的國債利息在3%至5%之間,西班牙在16世紀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蘭沒有因這種國債而衰敗,而西班牙則從17世紀中葉開始衰落。
18世紀中葉,英國的國債承受力也遠比法國高,前者的人均國債高於法國,但那種高負債不僅沒拖垮英國,反而是英國的國債利息只有法國的一半左右,讓英國不斷強盛。之所以英國(以及當年的荷蘭)的國債融資成本比法國的低一半,其證券市場也比法國更發達,根本原因與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所鞏固的憲政制衡有關,那次革命之後英國王權受到議會的進一步制約,使國王不能隨意徵稅、不能侵犯私人財產,財產稅等只能由議會立法。由於議會更能代表社會的利益,並且其立法與決策過程也非常透明,這使證券投資者對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願意買英國的國債,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資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國的王權不受制約,國王的決策過程又不透明,多次對其國債賴賬、拖欠利息,這些都無法讓投資者對集權政府有信心,其結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見,一個國家是否能長久靠赤字加國債發展,跟其制度架構分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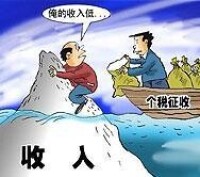
藏富於民
曾經的亞洲飛速發展的四小龍之一,民間投資的發展在政府的支持下突飛猛進,數十年時間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國民迅速地富裕起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各行各業如日中天。天有不測風雲,危機來臨,當亞洲金融危機降臨頭上時,大義的韓國國民紛紛響應政府號召,捐出外匯存款及金銀細軟以渡國家迅速從危機夢魘中擺脫出來。

主張代表學者:郎咸平
當前的左右之爭本質就是“藏富於民”與“藏富於國”的爭議,或者更進一步說就是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從歷史上看,二者都存在一些弊端,但如果基於現實的考慮還是可以有所偏重和取捨的;不能否認的是當今中國的社會分裂是不健全的自由主義和不完善的國家主義相結合產生的怪胎,有學者稱之為“權利資本化”;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左右之爭是虛設的,主張既要限制政府的胡作非為,又要利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增加民眾的福利(這實際上取消了“藏富於民”與“藏富於國”的爭議)。但從改革突破口角度出發,我們必須思考首先要做的工作,自由主義思想良性應用的前提是健全的法制、配套的文化根基和良好的外部環境;國家主義積極效果的生產之基礎是智慧和正義政府的建設,顯然前者達標的難度遠大於後者,而且後者的實現可以依靠少數人的努力,那麼從可行性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國未來的政策取嚮應該更傾向於國家主義。
政府首先要創造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使企業家得以生存、發展、壯大,社會財富得以積累,政府財政得以充盈。這就是各國政府永遠是為富人服務的本質所在。

藏富於民
藏富於民是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貧富分化現象極為嚴重,城鄉資源配置不平衡引發的社會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飽受詬病,國民收入未能與GDP保持同步增長更是令居民生活幸福感減弱,再加上內需嚴重不足,經濟轉型升級困難,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國已初見端倪。“利可均布,民可家足”,保障收入公平分配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關鍵。只有真正藏富於民,消除兩級分化,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形成“橄欖形”的社會結構,讓社會大眾真正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才能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藏富於民是激發民間創業熱情的“發動機”。為緩解高校就業壓力,國家出台了扶持應屆畢業生創業的諸多優惠政策,但居高不下的物價成本和萎靡不振的市場需求卻令很多人喪失了創業致富的激情、動力。日本在二戰後依靠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效擴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以消費拉動市場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拉動內需。2011年,我國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了“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只有以藏富於民拉動內需,才能迎來民間創業致富的新高潮。
藏富於民是使國民永葆愛國熱忱的“保證書”。管子云:“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明朝末年,統治階級窮凶奢極欲而大片地區卻餓殍遍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終致社稷傾覆。這個教訓告誡後代執政者“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話的正確性。政府只有藏富於民,保證人民生活水平隨著GDP的增長而穩步提升,才能保持安定和諧的大好局面,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
30年過去,中國人民生活有了顯著提高,但在國力強勢增長的背景下,中國表現出來的還是“國富而民不富”。或者說,是少數人先富起來了,而大多數人還遠未實現共富的理想。從國家到地方,連年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形成了較大的反差。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翻了5.7倍,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農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同期,中國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而城鎮居民特別是農民,這兩個群體的增長速度要慢很多。

藏富於民
根據中央財經大學民間金融課題組2006年初對27個省市借貸利率的調查,全國民間借貸利率平均為16.4%,其中借方以企業為多,這說明他們的資金使用后回報率至少在16.4%以上,遠高於4%左右的國債利率。減稅讓更多的錢留在民間,顯然會創造更多財富。
第二,過去20幾年,特別是1994年後,相當一部分公債被投到各類形象工程,或者是這些債券融資雖然沒有直接投入形象工程,但間接地讓政府一些揮霍性工程的上馬成為可能,造成了大量浪費。比如,2005年國家審計署的審計結果表明,部分城市基礎設施國債項目(包括污水處理)效果差,城建項目中有許多由於規劃不當、管理不善、設備不合格以及工程質量缺陷等原因,存在嚴重的損失浪費問題。這些項目的投資回報是否趕得上4%左右的國債利率,顯然是個大問號。
第三,給政府部門更多的錢花,就必然創造更多的貪污腐敗機會,也必然導致更多的地區間、城鄉間以及社會群體間的機會不平等。特別是在缺乏實質性權力制約、財政預算過程又不透明的情況下,政府開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近日,在新華社上海分社舉辦的“大亞——新華企業發展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吳曉求教授為當前的股改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前景。吳曉求教授稱,國家花大力氣和大代價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是構建和諧社會戰略的體現,通過發展資本市場帶來的投資回報,形成最終的藏富於民。
藏富於民!筆者不能不佩服吳曉求教授的妙筆生花之功。不過,或許是因為自己置身於股市之中,見過股市裡太多的人與事的緣故,以至於不論筆者怎麼看這幅股改的圖畫,但始終都看不出“藏富於民”的美好未來。以至於筆者不能不對吳曉求教授的觀點表示質疑。
應該說通過資本市場的發展給投資者帶來回報,形成最終的藏富於民,這應是股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正如郎咸平所認為的那樣,讓股民盈利這是股市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使命。同時它也確實應該是當前股改所需要達到的目標。並且對於股權分置改革來說,投資者確實也存在著這樣的要求。其實早在若干年前的時候,筆者就提出過國有股減持要讓利於民的觀點。而且在此次股改之初,筆者也還是對股改寄予了厚望,並積極地為股改的進行而搖旗吶喊。然而,伴隨著當前股改的進行,筆者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當前進行的股改與廣大投資者心目中的股改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甚至是南轅北轍。這樣的股改甚至根本就不能體現“國九條”所提出的要“切實保護投資者特別是公眾投資者合法權益”的精神,而要實現吳曉求教授所提出的“藏富於民”的目標,那更是一種空想,一種天方夜譚。
首先,當前的股改採取的是“低對價”的方式,給予流通股股東的補償明顯不足。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之間的不公平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可以這樣認為,在目前非流通股股東權益的增值過程中,通過流通股的高價發行、增發、配股而帶來非流通股的增值超過了目前非流通股所擁有的每股凈資產值的一半以上。因此,給予流通股股東以補償,非流通股股東的送出率應達到50%以上才行,但實際上,在當前的股改中,非流通股股東的送出率只有15%左右,象氯鹼化工非流通股股東的送出率甚至只有1.33%。因此,面對這樣的送出率,流通股股東連自身的利益都沒有得到,又何來的“藏富於民”呢?不僅如此,就是面對流通股股東每10股得到3股這樣的對價率,有關主管部門也不樂意,還要求有關上市公司的大股東要減少對價支出,而更多地採用其他忽悠投資者的方式,比如承諾、權證等等,以至給予流通股股東的補償更加缺少應有的保障。正是由於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不足,這不僅難以消除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之間的不公平,難以使流通股股東得到應有的補償,而且這種不公平的繼續存在還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股市的健康發展構成負面影響,以至股市的投資功能很難得到真正的體現。
其次,在當前的股改中,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東還意圖借股改之名再撈一把好處。這一點最明顯地體現在以股抵債股改公司的股改過程中。不過否認,在大股東確實缺少還款能力、缺少優質資產的情況下,以股抵債確實是解決大股東占款問題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有的上市公司大股東有款不還,有優質資產卻不拿來抵債,相反通過不合理的以股抵債定價方式,來達到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特別是損害投資者利益的目的。如電廣傳媒的以股抵債就是這方面的典型。而在當前股改的背景下,鄭州煤電在股改中推出的回購,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以股抵債,根據該公司的股改方案,鄭州煤電非流通股股東將向流通股東每10股支付3.3股對價;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後,鄭州煤電將通過定向回購控股股東鄭煤集團最高不超過2億股股份,擬一次性解決鄭煤集團的占款金額為4.65億元,然後依法註銷以達到縮股的目的,從而解決大股東長期占款問題。在股改方案里,鄭州煤電模擬計算的回購價格為2.9元/股,回購股數16,000萬股。而實際上,鄭煤集團目前所持股票的每股實際成本僅為0.40元,按此計算,鄭煤集團只有6400萬元的付出就還清了4.65億元的欠款。換句話來說,通過佔用上市公司資金到歸還欠款這個過程,鄭煤集團可得到近4億元實惠。因此,正是面對如此誘人的利益誘惑,一些佔有上市公司資金的大股東們均希望推出以股抵債的股改方式。比如最近就有媒體報道稱,國資委方面就力挺以股抵債的股改方式,並且本年度內預計將有近30家公司會上報“以股抵債”式的股改方案。看來,借股改之機,再來撈取一筆利益,大股東早就形成了共識。而面對這樣的股改,投資者的利益只有受損的份兒,又何來的“藏富於民”呢?
其三,從股改的目的來看,還是為了融資,為了上市公司更好地“圈錢”。中國股市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上市公司圈錢的需要。一直以來融資也是中國股市惟一的功能所在。而目前管理層之所以要花大力氣來股改,這實際上也與股權分置背景下的融資已引起投資者的強烈不滿有關。而從股改中管理層把融資與股改掛鉤的一系列做法來看,融資與再融資不僅是上市公司股改的動力,同樣也是管理層當前股改的目的之一。比如當前管理層要求股改加速,實際上就是為了新老划斷服務的,以便股市早日推出融資與再融資措施。並且,據有關媒體的報道稱,在當前證監會開在醞釀之中的新股發行和再融資新政里,放寬條件是主基調。當然,其目的也是為了能讓更多的公司能夠從股市裡融資。由此可見,股市雖然在進行股改,但管理層為融資服務的宗旨並未發生任何改變,融資仍然還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也正因如此,面對即將到來的上市公司“圈錢熱”,這股改還能“藏富於民”嗎?這投資者又如何能從股市裡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呢?只怕又是一場黃粱美夢吧?
藏富於民正應了依據古話:“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