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
徐中舒
徐中舒,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 192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等著名學者。在此期間,他受到王國維先生的影響,樹立了“新史學”的觀念。以後更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將古文字學與民族學、社會學、古典文獻學和歷史學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把王國維開創的“二重證據法”發展成為“多重證據法”。徐先生先後在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任教授、研究員。應中英庚款與四川大學的協聘,來到四川大學歷史系,除短期在武漢大學、華西協合大學、燕京大學、中央大學兼課外,終身執教於此。
人物關係
徐中舒(1898~1991),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
1991年1月9日徐中舒逝世,享年92歲。
1898年10月15日出生。1914年先生考入安慶第一師範學校。在該校他接觸到桐城派古文,學習興趣很濃。1916年畢業,在該校附小任教。
1918年後又曾在武昌高等師範及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讀書。
1921年經人介紹,到桐城方家任家庭教師。1922年又到上海李家任教,均講授《左傳》。

徐中舒
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後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
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後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
1949年建國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併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1991年1月9日徐中舒逝世,享年92歲。
徐中舒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學是其主攻方向,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顯著貢獻。他在治學方法上,除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外,擴大研究視野,力求掌握全面,盡量利用有關學科的科學知識,聯繫補充,以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獻,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資料,又具有宏觀素養,善於把田野考古、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工藝學諸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反覆論證,力求其是。他強調研究古文字學應和古史研究相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豐碩。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有《木蘭歌再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再論小屯與仰韶》、《〈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陳侯四器考釋》、《金文嘏辭釋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利簋文箋釋》、《周原甲骨初論》等論文,論證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獨到的見解。從40年代開始,還對四川地方史進行研究,撰寫《巴蜀文化初論》、《續論》、《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等文。
專著有《氏編鐘圖釋附考釋》、《史學論著輯存》、《論巴蜀文化》、《左傳選》等;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錄》、《甲骨文字典》等多種工具書。
先秦史是徐先生的主攻方向,撰文達四五十篇之多。早年的重要論著有著名的《耒耜考》,該文將出土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及實物相互對照,作了周密的考證,闡明了古農具耒和耜的形制及其功用。關於耒和耜,雖兩千年來有不少學者作過研究,但他們大多僅僅根據文獻典籍來考察,故而始終眾說紛紜,似是而非。該文的發表,一舉廓清了這學術上的迷霧。文章首先從考釋甲骨文的“藉”字入手,此字字形奇詭,不易認識。以前羅振玉先生曾釋為“掃”字,但驗之卜辭,字形與辭例均不相合。先生該文聯繫與此字形相近的金文,探索其發展變化的蹤跡,發現甲骨文“藉”字是“象人側立推耒,舉足刺地之形”。此字既明,“耒”字之形以及由耒字省變的“力”字、從力的“男”、“協”、“加”等字的字形均隨之而明。一些有關字的本義與引申義也可從而鉤稽出來。如金文中的“麗”字,從兩耒,古時兩耒並耕為耦耕,故而“麗”有匹偶之意,引申之,夫婦二人稱為伉麗。這一系列與耒字相關的字,不僅可以證明藉、耒二字考釋的正確,並可從金文耒字像秉耒之形而知耒的形制是“上端鉤曲,下端分歧”的木製農具。
徐先生對古代生產工具的考察,最終目的是為了揭開古代社會發展的奧秘。他在文中指出:“雖是一兩件農具的演進,有時影響所及,也足以改變社會的經濟狀況,解決歷史上的困難問題。”該文發表后,得到了國內外學者很高的評價,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該文的另一重大收穫,是古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進展。早期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很不完善,很多人輕出臆說,不講究科學的方法,更無周詳的考證,務在釋出別人所不識的新字,而結果往往是一無所獲。而徐先生則是將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充分結合起來進行古史研究,使文字的考釋與古史研究緊密結合,其結果不僅使古史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的考釋上也大有創穫。陳夢家先生就曾對這種方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談到《耒耜考》的時候指出:“用這種方法處理文字是很正確的。”(《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頁。)
為了論證殷商文化絕非受西方外來文化之影響而產生,徐先生髮表了若干論著,其中《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一文,對商及先商農業之悠久歷史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討論,論證了甲骨文的“為”字是“從又(手)牽象”,表示役象助勞之意。並從《禹貢》豫州之得名,進一步證實古代河南產象之說,指出“豫”字乃“象”“邑”二字之合文,“予”字乃“邑”字之訛。聯繫到古時姓名字多從女,表示以“女生為姓”,從而得知舜後為媯姓,乃服象之族;春秋時鄭有□之地,也不外因服象而得名。傳說舜弟象封於有庳,庳、鼻古音相近通假,鼻為象之特徵,有庳蓋附會服象之事而出現。
後世傳說的古史,多荒誕不經。由於象之南遷,到戰國末年,韓非說人們很少看到活象。中原既無象,這就使人們無法理解“象為舜耕”,“商人服象”以及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的傳說,這些傳說經過徐先生的研究,所謂荒誕也就成為信實了。
徐先生在先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論著還有《殷周文化之蠡測》,該文打破一般學者把我國古代王朝視為同一個民族的傳統見解,指出殷周本屬兩個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而有所革新,故而殷周在文字、生活習俗等方面大體相同,而在姓氏、曆法等方面則有異,這體現了民族習慣之間的差異。《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認為太王居岐以後,即以經營南土為其一貫之政策,所謂文王受命,乃是周人國力膨脹已臻極限,舍伐紂而無他途之時的國勢,舊史所言文王積德行義之說實不值一辯。《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根據考古發掘材料,指出黃河流域有大批豎穴和竇窖,其中有的有足窩可以上下,有的有台階可以出入,並用古文字材料與上述情況相印證,說明古時黃河流域以穴居為主,這一地區地面建築的出現,乃是受淮河流域地面建築的影響所致。《井田制度探源》,認為田的初義為田獵,為戰陣,“田之所象,實與田獵之陣營相符”,“井田之形方,實由田獵社會演變而來”;並對周人的“爰田制”作了新的探索和解釋,指出殷周之際,荒土頗多,周人在農業上實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轉徙他處。其後空地漸少,不能供轉徙之用,則須與他人換土易居,這就是爰田制,所謂“爰田”,就是“交換其田”。《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源》,闡明春秋以前牛耕說之不可靠,指出牛耕始於戰國時的三晉,而普遍推廣則始於西漢趙過。《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兩文,從田制入手對周代社會性質作了詳細考察,並將殷周社會進行對比研究,指出兩者性質不同,殷代是奴隸社會,而周代則屬封建社會。這些論文方法新穎,論據充實,創穫頗多,此不能一一詳述。
徐先生執教於四川大學,居蜀以來,又致力於四川地方史的研究。記述著名特產,作《蜀錦》。考證出土文物的特點及其與中原的關係,作《四川彭縣□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於》、《青川木牘簡論》等文。探索四川古時與鄰接地區的相互關係,撰有《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試論岷山莊王與滇王莊?》、《宋代斗夷源於楚國令尹子文說》、《川甘邊區的白馬人為古氐族說》、《〈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古代蜀楚的關係》(與唐嘉弘合作)、《古代都江堰情況探源》等文。晚年出版的《論巴蜀文化》,是他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代表著作,該書涉及廣泛,見解深透,對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磨滅的開拓之功。此外,在研究四川地方史的同時,徐先生還把視野擴展到整個西南地區,《論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一文,對歷來認識模糊的所謂“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釋,指出“洞”乃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公社,從古代一直延續到明清。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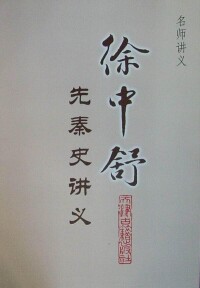
徐中舒講義
《金文嘏辭釋例》是徐先生研究金文的重要論著。該文全面系統地對銅器銘文的祝嘏之辭作了比較歸納研究,充分結合古代典籍,考釋了金文中各種嘏辭的含義,解決了許多前人未曾弄清的問題,並對各種嘏辭的時代進行了探索,許多成果今天看來仍然準確無誤。如指出“萬年無疆”、“萬年眉壽”、“眉壽無疆”等嘏辭主要盛行於西周厲、宣之世;而凡言“無期”者,如“眉壽無期”、“萬年無期”、“壽老無期”、“男女無期”等,均為春秋時成周偏東地區之器,結合《詩·魯頌》“思無期”之語,可知“無期”語春秋時盛行於東方。由此推論,《小雅·南山有台》有“萬壽無期”,《小雅·白駒》有“逸豫無期”,或即東周之作。又如金文時常提到“永命”、“靈命”、“嘉命”,以前多誤解命為性命之命,該文結合古代典籍指出:命並非性命之命,乃天命。這反映了古人以人世興衰繫於天的思想。在時代上,“永命”主要流行於西周,而“靈命”、“嘉命”則是春秋時的常用嘏辭。由於該文考釋精到,論證翔實,因而飲譽學界,成為治金文者的必讀參考資料。徐先生在金文方面的重要論著還有:《□氏編鐘圖釋》,對?氏編鐘銘文中不常見的疑難怪字作了詳細的考釋,釋出了許多前人不曾認得的難字,並考定該編鐘為春秋時晉器。《陳侯四器考釋》,綜合考察戰國時期田齊國君之器,提出了許多新見解。該文在學術界有廣泛影響,郭沫若先生就曾根據該文所取得的成果對其所著《兩周金文辭大系》作過修改。《禹鼎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聯繫大量金文材料,對禹鼎的年代作了全面的考察,將該器年代考定在厲王時期。文中並對金文材料所記載的西周時期周王朝與南方淮夷的戰爭,廣泛結合文獻記載,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指出西周時期,周王朝與淮夷的戰事主要發生在穆、厲、宣三世,使文獻記載與金文材料相吻合,在銅器斷代和西周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徐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除上舉《甲骨文字典》之外,重要的論著還有《甲骨文中所見的儒》,對甲骨文的儒字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該字的多種形體,論證了殷商時期儒為巫師一類人物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周原甲骨初論》,對與殷周史實有關的周原甲骨文作了詳細的考釋,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字體結構和辭彙上的特點,並論證了周原文化的兩個來源以及周文王時期的殷周關係,這些成果都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古代典籍是賴以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寶貴材料,對典籍的整理研究直接關係到古史研究的質量,所以自古即有不少學者致力於此。但只有學臻高深、實事求是的學者,其研究成果方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徐先生的《戰國策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一文,對《戰國策》作了深入的研究。戰國時期的蘇秦和張儀,傳統說法一直認為二人是同時的敵對人物。該文廣泛結合其它有關典籍,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指出《戰國策》中有關蘇秦事迹的記載與史實不符,蘇、張二人並不同時,張儀早於蘇秦。張儀在秦惠王時期(前377—前311年)仕於秦,與之敵對的同時人物是公孫衍和陳軫;而蘇秦乃是齊閔王時期(前300—前284年)的風雲人物,與之同時的人物是田文。蘇秦因替燕國在齊國進行反間活動,被齊國發覺而致死。該文的這些研究成果,竟然為10年後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證實,1974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其有關記載與先生所論基本一致。
徐先生在這方面的成果還有:《豳風說》,該文根據《詩·豳風》所反映的風俗習慣和物候農產,指出《豳風》並非如傳統所說,產生於高寒乾燥的豳地,而應是春秋時期東方魯國之詩。《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一文,指出《左傳》記事雖有誇張失實之處,不必盡信,但其成書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文獻材料,保存了許多古史傳說,仍不失為研究古史的必讀書籍,並將其成書年代考定在公元前375—前351年之間。《九歌九辯考》一文,論證了《九歌》《九辯》並非作於戰國末期,而是西漢人所作。另外,徐先生在這方面還有不少研究成果並未公諸於世,如他在講課中多次談到《尚書·盤庚》應為西周時宋國人所作,不過,文中的記載仍然符合殷代的實際情況,所據材料是可信的。如篇中講到盤庚對殷庶民說,如果我做得不對,我的祖先要懲罰我;但如果你們不聽我的話而帶來了惡果,我的祖先也要懲罰你們,並且還要告訴你們的祖先,你們的祖先也不會來搭救你們。這種禍福由祖先而不由上天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殷人思想,等等。這些古文獻經過了徐先生的深入研究,將會在學術研究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徐先生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在繼承前人治學方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較有特色的科學的治學方法。“古史二重證”的繼承和發展自王國維先生提出“古史二重證”的研究方法以來,傳統的史學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徐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繼承並發展了這種方法,他發表的百數十篇論文,都無一不是運用這種方法的良好範例。如上文提到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等文,都是將出土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充分結合來進行古史研究,其結果不僅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研究上也大有創穫。由於時代的局限,王國維先生的“古史二重證”依據的地下材料主要只是出土的古文字資料,而徐先生除古文字材料而外,還充分吸取了考古學成果。他早年撰寫的《再論小屯與仰韶》,根據當時的考古發掘材料,參以文獻記載,探討了仰韶文化的性質及分佈地域。建國以來,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發展,徐先生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學成果,於1979年寫成《夏史初曙》,放棄了他以前主張仰韶文化為夏文化的觀點,同意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並結合典籍記載,對夏史作了新的探索。此外,如上文提到的《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等文,在古文字材料以外,也充分結合了當時的考古發掘資料。
考古學離不開對古器物的研究,徐先生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論古銅器之鑒別》、《說尊彝》、《殷代銅器足征說兼論〈鄴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國古銅器》、《壽縣出土楚銅器補述》、《關於銅器之藝術》等論著,為我國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上文提及的《四川彭縣?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於》,也都是通過對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與外界聯繫的史實。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對“古史二重證”的發展並不止此,重要的還在於他進一步將對照範圍擴大到邊裔的少數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各個方面。這就是他時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證”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認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從有關殷代的史料去考察,還是不容易弄清楚。如果通過對四方邊裔各種族歷史的考察,再結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國古史關於“五服”、“九服”之制,兩千年來迄無定論。徐先生根據對三國時期夫余族和遼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漢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後北遷的蒲姑之後,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舊制”,“殷商的奴隸制度和契丹的奴隸制頗為相似”。具體說來,契丹人的部族制類似殷“侯”服,乃防守邊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缽”相當於殷之“甸”服,獻納皮革及農產品;遼之“南面官”相當於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遼之“斡魯朵”相當於殷之“衛”服,是擔任保衛工作的近衛軍。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貢》的“五服”和《周禮》的“九服”,則是後世根據殷制改編而成的。這種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個世紀的中國境內的傣族、貴州洞崽苗族中還可以看到(《傣族社會調查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徐先生的“古史三重證”,使中國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考釋古文字是古文字學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確的考釋方法,乃是該項工作的核心。徐先生根據多年來研究古文字的心得體會,逐漸總結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學的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後來寫成《怎樣考釋古文字》一文,系統地向學術界介紹這種方法。文中說:“古人造字,決不是孤立的一個一個地造,每個字的形音義,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因此考釋古文字,一個字講清楚了,還要聯繫一系列相關的字,考察其相互關係。同時還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產、生活情況,根據考古資料、民俗學、社會學及歷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情況,和現在一些文化落後的民族的生活情況,來探索古代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根據這些東西,探索每個字的字源和語源。這樣考釋古文字,才有根據,也才比較正確。”
徐中舒在直接或間接地繼承和借鑒了胡遠浚、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顧頡剛等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學術探索與實踐,不斷加以融通和創新,形成了自己獨到完善的學術思想體系,並對當代學術界產生了頗多積極的影響。
無徵不信、科學批判的思想
乾嘉學派治學講求實事求是,論學立說,注重佐證,反對穿鑿附會。徐不僅重視史料之收集,而且還善於借鑒乾嘉學派科學批判的方法,對各種真偽史料進行科學的爬梳整理和條分縷析,故所作結論多以堅實可靠的史料作為支持,從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讚賞清代乾嘉學派學者在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們“對於澄清漢、唐以來的偽先秦史謬誤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觀研究頗能揭露歷史實際,堪稱獨步千古。可以說,他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批判的科學方法”。
古史多重證法
歷史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涉及的方面至為廣泛。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繼承了王國維首倡的古史二重證據法,並且還在此基礎上將其發展為古史多重證據法。他在古史研究過程中,經常使用相關學科的豐富資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論著本身就是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於近代文化人類學的長足進展,“用邊裔民族的資料闡發古代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同樣成為研究古代歷史的重要途徑”。他說:“我們認為要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歷史實際及其規律,要徹底的平反漢代的先秦偽史,要在世界漢學熱潮中居於領先地位,治史方法應該有所改進。傳統的專治文獻的方法,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必須將寶貴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並和文獻資料結合起來,同時作為‘社會活化石’的現存民族的調查以及民族史志,也應予以重視,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參考資料。”
博涉與專精相結合的治學原則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學者一樣,也並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礎上更求專精。他曾強調做學問“切忌在學習之始就把基礎學習的面鋪得過寬過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謂的博。反造成學習重點不突出,知識不系統,不紮實,精力分散,結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無成,造成時間精力的極大浪費”。綜觀徐中舒的學術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學等學科,這充分體現了他在讀書治學過程中始終將博涉與專精的讀書治學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使二者達到協調與統一。
徐中舒作為一代學術大師,不僅於學術有重大貢獻,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強烈的愛國熱情,自強不息,誨人不倦,提攜後學,誠以待人。其較為突出者,略舉以下數事。
“人之有德惠術知者,恆存乎疾”,早年的艱苦生活造就了先生高尚的品格。先生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深知物力為艱,終身極為節儉,在生活上衣取蔽寒,食取果腹而已。記得我們剛入學時去拜見先生,見先生作為一代知名大學者,竟然居住在總面積不到30平方米的兩間舊房裡,大家都深為他抱不平,而先生卻處之泰然,反而勉勵我們說:“‘士志於道’,搞學術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學術上作出貢獻,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們以後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學業上,千萬不要在生活瑣事上花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後來學校退還給了先生原來的舊居,先生又把最大的一間會客室拿來作為古文字研究室,作為授課、編寫《甲骨文字典》等工作的場所。
徐中舒誨人不倦,為培養後學傾注了大量心血,但卻從不收受學生的任何禮物。大家都深知先生的為人,節假日去看望先生,都從不敢買任何東西。記得一個同學報考先生的研究生,考前的春節,去給先生拜年,同時也向先生請教一些學習上的問題。先生詳細解答了他的問題,並勉勵他認真備考。臨走時他拿出了禮物,先生的態度一下就變了,堅持要他把東西拿走,最後他只得把禮物提走。他回去后惴惴不安了好多天,覺得對他報考研究生肯定會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其實先生待人極為寬厚,也很理解學生的心情,並未因此對他產生什麼成見,後來他通過考試,終以優秀的成績錄取為先生的研究生。
徐中舒本性謙虛樸實,就是對他的學生也一樣。記得畢業后我們在他家編寫《甲骨文字典》,有一次適逢成都古籍書店翻印《說文解欄位注》,來請先生提寫書名,我們也乘機求先生的墨寶以作永久之紀念,先生欣然應允,而在落款的時候竟稱我們為“先生”,我們作為他晚年的學生,實在不敢承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給了後人不朽的學術成果和高尚的人師風範,為後人所景仰。作為一代學術大師,先生德業長存。
《木蘭歌再考》, 《東方雜誌》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第22卷14號。
《<木蘭歌再考>補編》, 《東方雜誌》第23卷11號。
《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 《國學論叢》 (清華國學研究院出版)第1卷1期。
《古詩十九首考》, 《立達》(季刊)第1期。次年又經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6卷65期重載。
《評<中國文學變遷考>》, 《一般》(上海出版)第2卷3期。
《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東方雜誌》第24卷18號。
《王靜安先生傳》, 《東方雜誌》第24卷3號。
《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 《文學周報》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第5卷1、2期合刊。
《追憶王靜安先生》,同上。
《王靜安先生致死之原因》,同上,署名史達。
《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 《歷史研究》本年第5期。
《先秦史講義》;在川大歷史系授課,本年及1963年均編撰有油印本。
《論堯舜禹撣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生和發展》,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1 期。
《巴蜀文化初淪》,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對<金文編》的幾點意見》, 《考古》本年.笫7期。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的問題》, 《考古學報》本年第3期。
《巴蜀文化續論》,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1期。
《四川彭縣檬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 《文物》—本年第6期。
《<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歷史教學》本年第11期。又載所編·《左傳選》,中華 書局1963年出版。
《論自然經濟,階級和等級》,四川大學第4次科學討論會油印本。
《孔子的政治思想》, 《成都晚報》本年1月3日。
《左傳選》,編選一百六十餘篇,寫有後序,註釋標點由羅世烈擔任,中華書局於9月出版。
《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 《歷史研究》本年第1期。
《先秦史專題講義》,四川大學油印,因“文革”影響,未印完。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鋅於》, 《文物》本年第5期.
《甲骨文中所見的儒》,《四川大學學報》(社科版)本年第4期。原文有改竄,后復加修訂。
《古井雜談》, 《井鹽史通訊》 (自貢市鹽業博物館編).本年第1期.又載《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3期,略有修改。
《論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對中國古代村社共同體的初步研究》,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1期。又載雲南《思想戰線》本年第2期.
《西周牆盤銘文箋釋》, 《考古學報》本年第2期.
《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 (筆談摘要), 《文物》本年第6期。
《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四川《社會科學研究》本年3月創刊號。又載《史學史資料》本年第3期。
《對古史分期問題的幾點意見》,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1期。
《殷周史的幾個問題》,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夏史初曙》, 《中國史研究》本年第3期。
《西周史論述》 (上、下),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3期4期連載.又本文補充,見同上刊1980年第1期106頁.
《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堂圖說明》,與伍仕謙合撰, 《中國史研究》本年第4期。
《中國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家屬稱謂》,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1期。 《論<豳風)應為魯詩——兼論<七月>詩中所見的生產關係》,與常正光合撰, 《歷史教學》本年第4期。
《西周利簋銘文箋釋》,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夜郎史跡初探》,與唐嘉弘合撰, 《貴州社會科學》本年7月創刊號。
《<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5輯“四川地方史研究專集”,本年7月出版。
《鋅於與銅鼓》,四川《社會科學研究》本年第5期.又載《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古代銅鼓學會編,文物出版社本年出版。
《川甘邊區白馬人屬古氐族說》,與唐嘉弘合撰,收載《白馬藏人族屬討論集》,四川民族研究所本年編印。
《<西夏史稿>序》, 《光明日報,史學副刊》,本年8月12日.並見吳天墀著《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初版本及1983年增訂本。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序》, 《四川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4期。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一書,先生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第1版,線裝本上、中、下三冊。1981及1982年第 2版第3版,均合訂一冊。
《古代楚蜀的關係》,與唐嘉弘合撰, 《文物》本年第6期。
《周原甲骨初論》,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本年5月出版。
《論殷周的外服制——關於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期的問題》,與唐嘉弘合撰, 《人文雜誌》增刊“先秦史論文集”,本年第5期。
《論巴蜀文化》,系彙集有關巴蜀文化論文六篇成書,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出版。
《經今古文問題綜論》,本年為“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徵稿撰寫,巴蜀書社即將出版。
《數佔法與<周易>的八卦》, 《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本年7月出版。
《怎樣考釋古文字》,香港中文大學編《古文字論集》,本年9月出版。又《先秦史研究動態》1984年第1期(總3期)摘要轉載,四川辭書出版社《辭典研究叢刊》 (6)於1985年5月重載,文物出版社《出土文物研究》於1985年6月重載。
《宋代斗夷源於楚國令尹子文說》,與唐嘉弘合撰,收載《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杜本年6月出版。
《<羌族史稿>序》, 《歷史研究》本年第1期。為冉光榮等著《羌族史稿》作.此書後改名《羌族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河姆渡文化的歷史地位》,與唐嘉弘合撰,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8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2月出版。
《夏商之際夏民族之遷徙》 (講稿),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本年印本。
《徐中舒史學論著輯存》,交由中華書局出版.本書選收論文60篇,約90萬字,先生委託吳天墀編輯,至本年夏間告成。
《古代都江堰情況探原》, 《四川文物》本年第1期。
《怎樣研究古文字》, 《古文字研究》第15輯,中華書局本年出版。
《殷周金文集錄》,由先生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2月出第1版,1986年2月出第2
版。
《青川木牘簡論》,與伍仕謙合撰於本年,中華書局《古文字研究》,即將刊出。
《<兩漢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序》,系多年前為著者黃綬所撰,存有手稿,未刊。
《關於夏商研究—<夏商史論集·序言>》, 《鄭州大學學報》 (社科版)本年第1期。
《關於夏代文字問題》,與唐嘉弘合撰,齊魯書社《夏史論叢》本年第1版。
《<人類學考古學論文集>序》,為著者馮漢輯《人類學考古學論文集》作,文物出版社本年第1版。
《<山海經>和“黃帝”》,與唐嘉弘合撰,載《<山海經)新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本年1月出版。
《漢語大字典》,先生擔任主編,四川及湖北辭書出版社於本年10月出第1版。
《一項開拓性的工作》,載《辭典研究叢刊》 (8),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
《我的學習之路》, 《文史知識》本年第6期。
《甲骨文字典》,先生主編,本年1月交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現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