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人,清代浙東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博學才俊。
乾隆元年(1736)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因不附權貴,於次年辭官歸里,不復出任,專心致力於學術,相繼講學,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曾主講紹興蕺山書院,從者雲集,后又應邀主講廣東端溪書院,對南粵學風影響很大。
在學術上,其推崇黃宗羲,自稱為梨洲私淑弟子,又受萬斯同影響,專研宋和南明史事,留意鄉邦文獻,尤好搜羅古典文獻及金石舊拓,曾編成《天一閣碑目》。
其著作頗豐,撰有《鮚琦亭集》38卷及《外編》50卷,《詩集》10卷,還有《漢書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經書問答》、《句餘土音》等,又七校《水經注》,三箋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續選《甬上耆舊詩》,為我國文化寶庫增添了許多珍貴遺產。
全祖望卒年51歲,葬在六世祖全少微墓之西南。墓呈橫長方形,墓碑上刻“謝山全太史墓”,西北側尚有全氏明代神道石坊一方。
全祖望(1705年1月29日—1755年8月9日),清代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浙東學派重要代表,字紹衣,號謝山,小名補,自署鮚埼亭長,學者稱謝山先生,浙江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洞橋鎮沙港村)人。
全祖望雍正七年(1729年)貢生,乾隆元年(1736年)舉薦博學鴻詞,同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為李紱所重用。次年,因李紱與張廷玉不和,散館后以知縣任用,遂憤而辭官返故里,專心著述,不復出仕。
曾主講於浙江蕺山書院,廣東端溪書院。上承清初黃宗羲經世致用之學,博通經史。在學術上推崇黃宗羲,並受萬斯同的影響,注重史料校訂,精研宋末及南明史事,留心鄉邦文獻,於南明史實廣為搜羅纂述,貢獻甚大。曾續修黃宗羲《宋元學案》,博採諸書加以補輯,成書百卷。又七校《水經注》,三箋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
其著作極為豐富,達35部,400多卷,且大多數學術著作用力極深,是我國文學寶庫中的瑰寶。所著《鮚埼亭集》,收明清之際碑傳極多,極富史料價值。
其主要著作有:《鮚埼亭集》、《困學紀聞三箋》、《七校水經注》、《續甬上耆舊詩》、《經史問答》、《讀易別錄》、《漢書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等,全祖望秉筆直書、文采斐然。他以卓越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繼司馬遷之後最有文採的傳記史家。
其人生雖仕途坎坷,但人品卻冰清玉潔,以耿直清正的品格和汪洋恣肆的才情,構成了德才皆備的人格,成為浙東人民敬仰的先賢。

全祖望畫像
雍正八年(1730),26歲,到乾隆二年(1737)33歲,是全祖望“薄游京洛”,飽嘗人生艱辛時期;
乾隆三年(1738),34歲,到乾隆十二年(1747)43歲,是全祖望“居家十載”,潛心學術研究時期;
乾隆十三年(1748),44歲,到乾隆二十年(1755)51歲,是全祖望“衣食奔走”,二任書院山長時期。

厲樊榭墓碣銘草稿
全祖望生活的時代,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空疏不實的學風,清初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凋零殆盡。鑒於當時學人多從事帖括之業或詞章之學的弊病,他發出“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鮚埼亭集·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的感嘆。
這一時期程朱理學佔據學術主流,但那些自命為朱學的人,議論迂闊陳腐,只知“奉章句傳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於其外”,結果形成“朱學反自此而晦”(《鮚埼亭集外編·橫溪南山書院記》,以下書名省略)的局面。而社會上流行的陸王心學,則往往“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外編·甬上證人書院記》)。全祖望試圖扭轉這種學術風氣,嚴厲批評宋元以來“門戶之病,最足錮人”的弊端(《外編·杜洲六先生書院記》),確立了學貴自得、融會百家的治學宗旨。

全祖望
在他看來,自得之學當是汲取百家之所長,再經過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會,從而獲得屬於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高度評價明代黃潤玉的學術成就,將其與明代大儒陳獻章相提並論。清初黃宗羲曾評價陳獻章的學術“要歸於自得”(《明儒學案·師說》)。在全祖望看來,黃潤玉治學同樣是“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虛剽襲之言”(《外編·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黃潤玉“所以為朱學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外編·橫溪南山書院記》)。全祖望還讚許宋代史蒙卿治學雖以程朱理學為宗主,卻能夠“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為苟同者”(《外編·甬東靜清書院記》)。可見自得之學、融會百家是全祖望治學所追求的一種很高的境界,其中閃耀著不立門戶、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輝,充分表現出對前賢的尊重與繼承。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張的自得之學與兩種虛假的“自得之學”區別開來,並對它們進行了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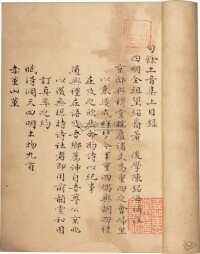
全祖望
其二,以他人之見矜為“自得”。宋代崑山衛湜薈萃百家,纂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是書採擷廣泛,但作者不置一語於其中。對此,衛湜自己坦言:“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全祖望對這種誠實態度倍加讚許,認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獺祭以成書,矜為自得,或墨守一家堅辟之學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編·跋衛櫟齋禮記集說》),給那些以掠人之美為“自得”的無恥之徒敲響了警鐘。
針對以上兩種積弊,全祖望提出“躬行”實踐的主張。他認為既然有蹈空虛說之存在,則“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編·碧止楊文元公書院記》),強調不能僅據其人之言而論其學,應當在實踐中對其學說進行考察。自得之學,必須驗之於躬行,“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與否”(《外編·石坡書院記》)。通過躬行實踐,則狂禪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這種精神,滲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學術實踐之中。
他為黃宗羲輯補《宋元學案》,堪稱是貫徹其學術宗旨的典範。全祖望對《宋元學案》的續修工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在內容上有所增補。《宋元學案》共有91個學案,其中屬於全祖望增補的共計32個,凡33卷,約佔全書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經他增補之後,宋元學術的主流與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學術思想發展的面貌更為全面。
二是對黃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補定”,考訂其中的失誤。全祖望不為黃宗羲的失誤隱諱,明確地指出原書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學案中不存門戶之見,客觀敘述各家各派學術利弊得失,達到了融會百家的目的。
三是完善了學案體例。全祖望將史“表”運用到學案體裁之中,每一學案內先立《學案表》以揭明學術源流,這是一個創舉;同時增訂並精心撰寫《序錄》,概括評價各派學術。他在對待各學派的態度上比黃宗羲更為開放,持論往往較黃宗羲更為博大平恕。經過全祖望續修的《宋元學案》,不僅成為中國學術史著作成熟的標誌,而且反映出融會諸說、不定一尊、注重獨創的治學精神,深為學者所推崇。
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的學術實踐,也是對其學貴自得、融會百家治學思想的最好註解。正因為如此,全祖望對於清代學術風氣的轉變所起的作用至為關鍵,而他的思想認識以及學術見解,對於今天的學者治學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全祖望塑像
但全祖望某些持論也有偏激之處。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譏其對古文"粗識藩籬","敘述不中律度"(譚獻《復堂日記》)等等,其實是忽視內容、過於推敲形式的批評。
全祖望的詩歌多注意評騭人物,表彰忠義,但嫌議論過多,筆較質直。
全祖望著述的整理出版,是全祖望研究的另一項基礎性工作。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庫叢刊本《鮚琦亭集》、《鮚琦亭詩集》,前者收其《文集》內外編88卷及《經史問答》10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為研究全祖望提供了方便。

全祖望塑像
當然這麼大的集子,疏漏也在所難免,辛德勇的《全祖望<經史問答>萬氏刻本綴語——兼談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匯校集注>》(《書品》2004年5、6期)和胡偉的《<鮚琦亭集>校讀札記》(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都對該書的失誤提出批評,胡文校出其標點、文字訛誤61處。
有關全祖望著作的選本和注本,尚有黃雲眉的《鮚琦亭文集選注》(齊魯書社1982年)、詹海雲的《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書局2003年),以及《全祖望校<水經注>稿本合編》(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6年)和《宋元學案》(民國時期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今有1986年中華書局校點本)。
對於全祖望著述成書、流布過程的考辨,最主要、最全面的研究文章是蔣天樞《全謝山先生著述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1、2號,1933年),此文全面考察全祖望所有著作及其流布過程,指出全祖望計有《公車徵士錄》、《讀易別錄》、《困學紀聞三箋》、《句餘土音》、《續甬上耆舊詩集》、《宋元學案》、《漢書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經注》、《經史問答》、《鮚垵亭集》、《鮚埼亭集詩集》、《鮚埼亭集外編》、《甬上望族表》、《孔子弟子姓名表》以及偽書《年華錄》共15種,另外尚有存目之書數種。
此後王永健《評傳》、黃雲眉《鮚埼亭集選注·前言》、謝國楨《清代卓越的史學家全祖望》、子微《全祖望及其著作》(《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五期,中華書局1980年10月第1版)、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五章等文,也對全祖望的著作情況作了介紹和考證。因為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在杭世駿處滯留多年,所以引起一段公案。劉孔伏《<鮚埼亭集>內外編之由來》(《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86年4月)認為,董秉純兩次整理文集,才形成了內外編,指出謝國楨“仿明遺民而分內外集”、黃雲眉“杭世駿懼禍”兩說欠妥。
全祖望曾七校《水經注》。在《胡適全集》中,有許多討論全祖望《水經注》五校本、七校本的文字。但是胡適疑心太重,假設過於大膽,他先是認為全祖望七校本為偽作,貶低全祖望的治學態度和酈學成就,後來發現天津圖書館藏的五校本,又撰文承認了七校本的真實性,引起了一些無謂的考證與討論,謝忠岳的《全祖望·水經注·胡適·天津圖書館》一文對此有具體評說(《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6年5期)。除胡適外,王國維、陳橋驛、吳天任等人也都對全祖望校《水經注》的貢獻有評論。
此外,全祖望還整理完成了黃宗羲的未竟稿《宋元學案》。自乾隆十一年開始,全祖望歷時九載,補寫改訂黃氏原書,又增立學案32個。盧鍾鋒的《論<宋元學案>的編纂、體例特點和歷史地位》(《史學史研究》1986年2期)、陳祖武的《<宋元學案>纂修拾遺》(《中國史研究》1994年4期)、林久貴的《(宋元學案)的作者及成書經過述論》(《黃岡師專學報》1998年8月)、倉修良、呂建楚的《全祖望和<宋元學案>》(《史學月刊》1986年第2期)、陳其泰的《<宋元學案>的編撰與成就》(《史學史研究》1990年3期)、吳光的《<宋元學案>成書經過、編纂人員與版本存佚考》(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1月第1期)及《評傳》等文章,都對全祖望增補《宋元學案》的貢獻作了高度評價。

全祖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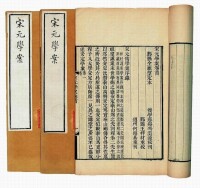
宋元學案
梁啟超在1923年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極力誇獎全祖望的人品與文章,讚賞全祖望為南明忠義之士寫碑傳,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價值,後人研究全祖望,較多引用梁啟超的觀點。張麗珠《全祖望之史學研究及其影響》認為,《鮚琦亭集》揭示了南明鬥爭史的歷史背景,提供了大量志士、隱逸、學者的生平事迹,指出全祖望於明清文獻的貢獻(《越魂史筆》)。呂建楚《全祖望和他的<鮚琦亭集>》論述了全祖望對晚明、清初歷史研究的貢獻表現為:可補《明史》所缺,補舊史之不全,糾舊史所舛,(《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管敏義的《全祖望的學術成就》(《浙東學術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呂建楚的《全祖望和他的<鮚琦亭集>》等文,認為全祖望的學術成就還在於收集鄉邦文獻,《鮚琦亭集》可資地方史志的編纂。
全祖望七校《水經注》,對酈學功勞極大。陳橋驛《全祖望與<水經注>》認為有五點,第一是“合理編排《水經注》所載河流的次序篇目”;第二是開始“區分經注”;第三是“全祖望提出《水經注》在體例上的注中有注,雙行夾寫的見解”;第四是“全祖望提出《水經》成書於三國魏人之手”;第五是“全祖望在其對酈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參考文獻”,嚴謹為學,便利後人(《歷史地理》第十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莫廣銓的《略述全謝山先生之歷史地理學》(《越魂史筆》),從《水經注》校本、 《漢書地理志稽疑》論述全祖望的歷史地理學,指出全祖望校刊《水經注》、考證秦三十六郡的成就。顧志華《試論全祖望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成就》認為,全祖望首倡從《永樂大典》中輯佚,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編《天一閣碑目》,輯《續甬上耆舊詩》,保存了重要的歷史文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曾貽芬《全祖望的史學與“七校”、“三箋”》認為,全祖望七校《水經注》時,提出不改原文的普遍原則,有改動亦慎重,考辨翔實,反映出全祖望史家校書的特點(《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宋元學案
金偉《<鮚埼亭集>的學術價值》指出,全祖望搜集史料時,注意博採、慎擇、精考,對歷史編纂學的意義極大(《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劉玉才《全祖望學術史觀探微》(《越魂史筆》)、鄭吉雄《論全祖望“去短集長”的治學聲法》(《史心文韻》)等文,考察了全祖望的“去短集長”的治學方法和學術史思想,肯定全祖望重視會通、反對墨守一家的做法。
呂芹的《試論全祖望的註釋學特點》(《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總結了全祖望的註釋學特點:
一是註明詞義時,擴大註釋範圍,或注其演變,或注其同類;
二是不通篇註釋字音、字義、詞義,將註釋重點放在對古籍自身內容的註釋上;
三是將自己的歷史注張及思想寓於所註釋歷史事件中。
詹海雲的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第六章和吳贊的《全祖望圖書編撰學術思想研究》(《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4期)則認為,全祖望將目錄學、學術史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方法運用到《宋元學案》、《水經注》編撰工作之中,注重輯佚、辨偽的方法主要體現在箋注《困學紀聞》中。
全祖望於經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他的《經史問答》。論述及此者極少,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謂《經史問答》的寫作形式有《黃氏日抄》、《困學紀聞》的影子,與顧炎武、朱彝尊相比,“互有勝場”。而在經學上的輯佚,顯示了兩點意義:“他是我國學術史上很‘早知道《永樂大典》對輯佚學有很大的幫助的先知。全氏所輯之書,可作為研究浙東區域經學史、王安石新學史或明代經學史之助力。”
關於全祖望的理學思想,詹海雲在《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中認為,在本體的看法上,全祖望同意黃宗羲“本體未嘗離物以為體”以及羅豫章“吾道當無疑於物”的觀點;在理氣問題上,全祖望的看法近於朱學,認為“理先於氣”;在知行問題上,全祖望認為知在行先,但須躬行與實際效果之表現來檢驗“知”是否為正確的認識;在朱陸異同問題上,全祖望主張會同,因為朱陸本身論學並沒有截然立異處。
詹海雲《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指出,全祖望的書院辦學目標是“自拔於時風眾勢之中”,也即“明經”,書院教育的內容是“行修”。因為書院實際上由朝廷控制,而八股時文與“明經行修”也不類,全祖望提出要學習應付公職需要的各種文體。全祖望對教育管理有一套自己的見解,費海璣的《全祖望及其教育思想》(《東方雜誌》復刊1卷6期,1967年12月)、杜成憲的《全祖望書院教育思想述評》(《嶽麓書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紀念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楊布生的《全祖望教育活動評述》(《寧波師院學報》1991年2月)等文,對此有所評述。
研究全祖望的史學思想的論文相對較多,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甚至針鋒相對,也足見謝山史學思想的多面性。
方祖猷《試論全祖望的史學思想》(《浙江學刊》1984年第1期)指出,全祖望雖然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反對農民起義,但還是有民本主義和人民性思想,這也是浙東史學的重要內容。方祖猷還認為謝山繼承了“勢”的歷史觀,認為這是一種與天命歷史觀和英雄史觀相對立的進步歷史觀;全祖望口中的“天命”,其實是人生觀。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認為全祖望的“天命觀”都有“勢”的影子。呂建楚《略論全祖望》(《歷史教學問題》1985年第6期)指出,全祖望是個宿命論者,認為擁護清朝是一種進步。方同義指出,全祖望具有不以成敗論人的歷史眼光(《浙東學術精神研究》第十三章《“博採慎取”、“史以紀實”——全祖望的史學精神》,寧波出版社2006年9年第1版)。
全祖望有極強的經世致用思想,趙宗正的《萬斯同、全祖望的經世史學思想》(陳鼓應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第五十章,齊魯書社1989年7月第1版)、袁元龍的《漫議實學,兼論全祖望在清實學上的貢獻與地位》、李志軍的《全祖望實學思想的特徵及其影響》(二文皆見於《史心文韻》)等文,對此都有詳細論述。張麗珠的《全祖望之史學研究及其影響》指出,全祖望的史學是道德教化下的史學,他是以史教忠、崇尚氣節、以文明道,所以汲汲從事於表,彰忠義的史學工作,也使得他的史學特色表現為富於史識、謹於史法、長於史論、善於史裁(《越魂史筆》)。文暢平《全祖望史學思想初探》(《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汪建豐、陳欣《全祖望史學思想探析》(《浙江學刊》2005年第2期)、潘起造《全祖望的經世史學》(《越魂史筆》),都持相似觀點。
在經史關係上,呂建楚《全祖望學術特點淺論》認為,全祖望有以經史以根,史學為輔的思想。杜維運《全祖望之史學》(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清代史學與史家》1984年8月初版)認為,全祖望的史學淵源為理學,他“講宋明理學而無門戶之見,實已達於一精湛境界”,所以文章富於感情,醉心正義,拳拳於故國喬木之思,此“由內而外之學也”。
“去短集長”既是全祖望的史學方法,也是其史學思想。呂建楚《全祖望學術特點淺論》認為全祖望反對門戶之見,注重獨創精神。鄭吉雄《論全祖望“去短集長”的治學方法》(《史心文韻》)從治學方法考察全祖望的史學思想,調和前人解釋全祖望思想軒格之處,正因為包容會通,所以寫學術史時,不主一家,客觀實錄,而且在政治上也會包容異代,“故國不可遽剪”,解決了全祖望既承認於清朝,又大量寫南明志士的思想矛盾。
全祖望的所作南明人物傳,表彰氣節,極具感染力。在內憂外患的民國時期,民族意識勃發,學者往往以全祖望相激勵,鼓舞民族意識,也是學術受環境影響的表現,周黎庵著文,就直稱全祖望為民族史家,陳垣選擇《鮚埼亭集》作史源學教材時,也是為了“正人心,端士習”。新中國成立后,全祖望的民族思想研究得到深入展開。
研究全祖望史學或者文學的文章,都會涉及其民族思想,部分學者認為全祖望並非“素負民族氣節”。梁啟超就認為全祖望對清朝並沒有什麼憤恨。高國抗、侯若霞的《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異議》(《光明日報》1983年1月26日第3版),文章認為《鮚琦亭集》雖然表彰氣節,有進步的教育作用,但這並不能說明全祖望就素負民族氣節,聯繫全祖望生平,指出全祖望的政治立場上並不反清,反而有歌頌清朝的文字。《鮚埼亭集》的主旨在於表彰忠孝,是合乎清廷的政策,認為全祖望並非素負民族氣節。
呂建楚認為全祖望的文章有激勵人的客觀效果,卻並無故國之思,而且思想上帶有嚴重的宿命論成份,所以明亡清興是必然的,還認為全祖望順清、擁清倒具有一定的進步性。聯繫全祖望僕僕於科舉,還有表彰清朝官員的碑傳,更能說明他並非“素負民族氣節”。全祖望之所以著力於碑傳寫作,主要是想起到激奮名教的作用(《略論全祖望》,《歷史教學問題》1985年第6期)。
陳永明《全祖望及其南明人物傳》(《論浙東學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則認為,全祖望的政治身份是“清人”,因仰慕先賢而寫下了大量的南明人物傳,但其著眼點不再是政治上認同明朝,也沒有繼承他們的反清觀念,而是從道德上、傳統的儒家立場上來表彰氣節,以正人心,否則就與他的“清人”身份衝突。文中提到中國傳統並非單純以種族為考慮標準,更重要是的以文化為標準。只可惜作者點到為止,並沒有入深探討。
楊啟樵認為不適合把全祖望的“褒獎氣節”擴大到民族主義,也不能說全祖望拳拳於故國之思。指出全祖望作碑傳,旨在紀實存真,反清復明的種姓觀念並不濃厚。比如全祖望在大力表彰姚啟聖計擊台灣鄭氏,指責崇禎“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文章還指出全祖望也有熱衷功名的一面(《全謝山史學的精髓》,《論浙東學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陳、楊兩篇文章都側重挖掘全祖望史學的實錄精神,所論比較客觀。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第六章論理學時,從全祖望對宋元之際許衡和劉因兩人的評論入手,指出全祖望對於仕不仕二姓,從理學角度看,在是不是能行道上,而不是民族大義的問題。是反對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的一個佐證。
光明日報《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異議》、一文影響較大,引起了幾篇反駁文章,堅持謝國楨等人所說的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的觀點。方祖猷從全祖望家世考證入手,認為他是有亡明之痛的,那些感情充沛的碑傳文,正是他內心的寫照。在清廷文字獄的高壓下,只得打著“忠”的旗號,以避開迫害。與呂建楚針鋒相對的是,認為全祖望不是完全的“天命論”者,承認清朝入主,並不說明不負民族氣節(《全祖望的民族思想辨》,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4年3期)。徐光仁的《論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社會科學研究》1986第4期)一文,也對《異議》的觀點加以反駁。文章從全祖望的生平與著作中,發掘全祖望的亡明之痛,強調了全祖望的民族氣節,認為《異議》一文所說全祖望激勵士氣的客觀效果與全祖望的主觀民族思想分開是不適當的。楊緒敏、曹威《試論全祖望表彰明季忠烈的動機及策略》(《揚州大學學報》2005年7月)認為,全祖望在《鮚琦亭集》中順應了清初統治者借宣揚忠孝節義以籠絡人心的需要,地借為《明史》增補史實,對明末忠烈之士的事迹作了詳細的描述,熱情謳歌了抗清志士的高風亮節,其中既有其堅持民族氣節的因素,也與其史家強烈的責任心相關。

萬斯同塑像
首先,清代阮元說全祖望“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兼備,可研究表明,於全祖望考據、辭章已有發掘,但是論述經學、理學者極少,詹海雲的博士論文雖有涉及,可真正論述謝山經學、理學者唯第六章之第一、二兩節。而全祖望見重於世人的《經史問答》,並沒有什麼研究。因此,對全祖望經學、理學方面的探討,應該得到加強。
其次,全祖望自言私淑黃宗羲。章學誠《浙東學術》排定譜系時,以全祖望為清代浙東學派第三代。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置全祖望於萬斯同之後,強調’了浙東學派的繼承關係。謝國楨《黃宗羲學譜》也設一章,將全祖望放在私淑黃宗羲的位置。陳訓慈《全謝山文獻學》(《史心文韻》)也著眼浙東學術的繼承,承認了章學誠對浙東學術譜系的描述。後來的學者,大多著眼於浙東學術史上的全祖望。張麗珠《全祖望之史學研究及其影響》就認為全祖望的地方志創作與理論影響了章學誠。《獨立於時風眾勢外的全祖望史學精神》(《史心文韻》)強調了全祖望的浙東史學精神。絕大多數的文章著眼這種歷時的縱向承繼關係,而極少有文章專就全祖望與當世學人共時的橫向交互影響進行討論。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將全祖望系在李紱之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將全祖望的史學與李紱的理學淵源聯繫起來,指出全祖望學術思想形成受學術環境影響。杜維運《全祖望之史學》直接指出全祖望史學的理學根源。李向軍《全祖望治史論述》則從全祖望生平論述其史學思想的形成。詹海雲博士論文《全祖望學術思想研究》承錢著思路,指出全祖望還受到浙西學術的影響,這尤其值得稱讚。這些論文試圖擴大全祖望所受歷時縱向影響的範圍。
這一方面的研究,其實還可以深入細緻地考察。詹海雲的博士論文第二章曾廣泛地考察全祖望與京城、揚州、杭州、寧波學術圈的交互影響,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也就是說,全祖望與時人在學術上共時橫向的交互影響的研究仍待深入,視界還應當更加拓寬。全祖望文學的橫向交互影響,似乎前人也沒有涉足,特別是與揚州文學圈的唱和,有極大的研究空間。

全祖望墓
浙江鄞縣(今寧波)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被李紱所重用,因李紱與張廷玉不和,散館后以知縣任用,遂憤而辭官不復出。後任蕺山、端溪等書院講席,其學術為士林所推重。尤於史學、文獻學多有建樹。黃宗羲《宋元學案》未完成而卒,他博採諸書加以補輯,成書百卷。又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所聞》。研治宋末及南明史事,留心鄉邦文獻。所著《鮚埼亭集》,收明清之際碑傳極多,富有史料價值。又答弟子董秉純、張丙、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為《經史問答》10卷。
一生大部分時間用於文獻的收集及整理,是這一時期文獻學代表人物。世代有藏書。先世“阿育山房”藏書甚富,大半抄自城西豐坊“萬卷樓”,然過後皆為其子孫盡以遺書為故紙,論斤兩出售。他又重為搜羅,少年時,曾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趙氏“小山堂”等藏書樓,遇見稀有之本即借抄,所藏先後達5萬餘卷,貯於“雙韭山房”和“叢書樓”中。“雙韭山房”在鄞縣大雷群山中,因山溪多產野韭菜,故名。
編撰有《雙韭山房藏書目》。對地方文獻收藏頗為勤奮,自稱“四明志乘,以吾家為最備”。所作藏書記聞頗多,如《天一閣藏書記》、《小山堂祁氏遺書記》、《二老閣藏書記》、《小山堂藏書記》、《曠亭記》、《胡梅磵藏書窖記》、《雙韭山房藏書記》等,是研究藏書文化史的珍貴史料,對研究古代私人藏書有較高價值。晚年窮困,萬餘卷典籍盡歸盧址“抱經樓”。著《七校〈水經注〉》、《續甬上耆舊詩》、《困學紀聞三箋》、《公車徵士小錄》、《經史答問》、《漢書地理志稽疑》、《句余士音》、《鮚埼亭集》等30餘種。
李元度:“負氣忤俗”,“其學淵博無涯”。
胡適:絕頂聰明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朱熹,另一個就是全祖望。
梁啟超:若問我對古今人文集最喜愛讀某家,我必舉《鮚埼亭集》為第一部。

全祖望故居

全祖望故居
2014年上半年實施了第三期保護維修工程,新增了“村情村史陳列室”和“全祖望紀念堂”。向遊客展示了全祖望的生平事迹與沙港村的悠久歷史。現全祖望故居成為了沙港村的小型博物館。
全祖望墓,清代建築,原位於寧波南郊王家橋苗圃南端,(今為恆春街南側,市府三招後面),坐東朝西,前為廟前河,北與西塘河相接,南與南塘河相連。
《顧炎武治學》,作者:全祖望
凡先生之游(1),以(2)二馬三騾載(3)書自隨。所至厄塞(4),即呼老兵退卒詢(5)其曲折(6);或(7)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8)坊肆中發(9)書而對勘之。或(10))徑行(11)平原大野,無足(12)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註疏(13);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14)書而熟(15)復之。(選自《亭林先生神道表》)
(1)凡先生之游:凡是先生出外遊歷。先生,指顧炎武。
(2)以:用
(3)載:馱,運載
(4)厄塞:險要的關口。
(5)詢:詢問
(6)曲折:詳細情況。
(7)或:有時。
(8)即:靠近,引申為走向。坊肆:街市中的客店。對勘:核對校正。
(9)發:打開
(10)或:有時
(11)徑行:直接行走。
(12)無足:沒有值得。足:足以,值得
(13)諸經註疏:各種儒家經典著作及註釋疏證。
(14)發:打開
(15)熟:仔細認真。
凡是顧炎武出外遊歷,都用二匹馬三頭騾子馱著書跟隨自己。到了險要的關口,就叫退休的差役和老兵詢問這裡的詳細情況;有時與平時聽說的不一樣,就到店鋪中打開書,核對校正它。有時直接走在平原曠野,沒有值得什麼留意的,就在馬背上默默地記誦各種經典的註解疏證;有時有所遺忘,就到店鋪中打開書,仔細認真地反覆看它。
第一類詳細考論全祖望的一生,以年譜、評傳為兩大宗;
第二類考證全祖望在某一時期的某件事,以單篇論文為主。
蔣天樞《全謝山先生年譜》4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屬於第一類,蔣《譜》訂正全祖望弟子董秉純《全謝山先生世譜》和《全謝山先生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四輯題作《清全謝山先生祖望年譜》,作者題為清代史夢蛟,誤。上海古籍出版社《全祖望集匯校集注》載有此兩文)的缺失和疏漏,系年抄錄全祖望及友朋相關詩文來印證其生平出處。更主要的是將全祖望一生分為四個時期,“於先生思想變遷,甚為清晰”(太玄先生言,見其《讀全祖望先生年譜》,《燕京大學圖書館報》第62期)。王永健《全祖望評傳》也承襲了四期分法。
唯第二期比蔣《譜》提前兩年,以全祖望26歲進京為界,更為允當。《評傳》還詳細羅列全祖望的家世與交遊,以較多的篇幅介紹了全祖望的師友,如方苞、李紱、厲鶚等人,指出這兩方面對全祖望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評傳》是目前最為全面翔實的研究全祖望生平的著作。另外尚有一些文章比較簡練地概述了全祖望的一生,與劉師培《全祖望傳》相近,如《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中的《全祖望傳》、《清儒學案》及唐鑒《清學案小識》中的《謝山學案》部分、周黎庵《清代民族史家全謝山》(《犬風》第54期1939年)、劉季高《全祖望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續編三,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又見劉氏著《斗室文史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楊啟樵《全謝山其人其事》(《明清史抉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顧志華《全祖望傳》(張舜徽主編,《中國古代學者百人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袁元龍《明清浙東學術四大家之一—全祖望》、周時奮《浙東學術的最後一塊豐碑》、俞信芳《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全謝山先生誕辰三百周年紀念》(三篇皆見於《越魂史筆》)等。
另一類文章則專門考訂全祖望生平疑案,形同筆記談助。清人徐時棟《煙嶼樓集》卷16《記杭堇浦》(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542冊)記載杭世駿晚年與全祖望交惡一事,全祖望歿后,他扣壓全祖望文集,又竊全祖望文章六七篇為己有,編入《道古堂集》,徐時棟譏之為“賣死友”。這一記載引起極多的爭議。孟森《鮚埼亭集公案》(連載於《青鶴》雜誌第5卷第14、15、16期,1937年)認為此文大致可信,唯所謂交惡之情形,過於誇張,而杭世駿也未有竊全祖望文章如此下流。謝國楨《清代卓越的史學家全祖望》(《清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0年)也認為確有“交惡”其事,但無“竊文”之舉。黃雲眉、陳平原以及《評傳》則認為,正因為杭世駿的扣壓,才使文集逃過文字獄(黃雲眉《鮚埼亭集選注·前言》,《鮚埼亭集選注》,齊魯書社1982年;陳平原《超越“江南之文”》,《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三聯書店2004年)。
楊啟樵重新細讀董秉純文字,認為杭世駿也是耿介之士,並無扣壓全祖望文集之意,所謂“久索不還”,不過是想留文集在手邊校改,後來清代刊刻出版的文集底本,正有杭世駿校改的墨跡。兩人游粵時亦無交惡之可能,早年也沒有“交惡”之遠因。對引起全祖望弟子“大驚怪”的杭世駿《鮚埼亭集集序》,楊啟樵提出與蔣天樞不同的見解,認為此序不為全祖望諱,也是全祖望為他人寫傳狀、序言的實事求是作風(《全謝山與杭堇浦的轇轕》,《明清史抉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蔣天樞《全謝山先生著述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1、2號,1933年,《<煙嶼樓文集·記杭堇浦>辨誣》,《史心文韻》),我們認為這種見解比較平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