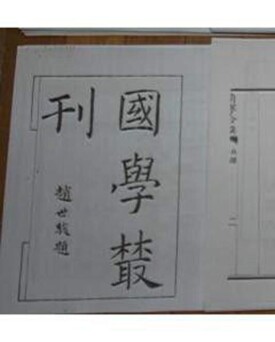國學叢刊
國學叢刊
現代學術史上,取名《國學叢刊》的刊物有四個。它們分別是:羅振玉、王國維1911年在上海創辦的《國學叢刊》,王、羅分別寫有“序”。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1923年3月在南京創辦的《國學叢刊》。主要負責人是陳中凡、顧實。顧實為創刊號作《發刊辭》。齊魯大學國學系1929年創辦的《國學叢刊》。“國學書院第一院”1941年3月在北平編輯的《國學叢刊》,《發刊辭》為周肇祥所撰,發行人為潘壽岑。
南京東南大學的《國學叢刊》。《國學叢刊》的創辦主要得力於陳中凡、顧實兩人。
陳中凡1911年底畢業於南京兩江師範學堂,191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1917年夏畢業后,入文科研究所作研究員(實際上是研究生)。據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所示,陳中凡選修的研究員(生)五門科目和導師分別是:邏輯學史(章士釗)、近世心理學史(陳大齊)、儒家玄學(陳漢章)、二程學說(馬敘倫)、心理學(身心之關係)(韓述組)。他同時任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員。1919年3月20,北京大學《國故》月刊創辦。設有總編輯劉師培、黃侃,特別編輯陳漢章、馬敘倫、康寶忠、吳梅(瞿安)、黃節、屠孝塞、林損、陳中凡。另有編輯十人。《國故》月刊和《新青年》、《新潮》形成對立之勢。而他自己所著的《諸子通誼》就是在該刊第1至第5期連載的。劉師培為“揚州學派”的最後一位學者,劉氏家學相傳,四代治經學,特別是以治《左傳》著名。陳中凡為蘇北鹽城人,這時在北京大學有機會得劉師培親教。此時劉師培因肺病加劇,陳中凡為他“借款”,“以救目前眉急”。此事使劉師培“感謝之至”。劉師培於1919年11月不治而死。在劉師培“疾終京寓”時,承陳中凡“照料一切”。劉師培死後,其妻子何震精神失常,陳中凡又“鼎立維持,俾死者得正首邱,生者得歸故里”⑩。對此劉氏宗親,特別感動。
1921年7月,陳中凡回母校(原兩江師範學堂經南京高師,已經改為東南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東南大學的《國學叢刊》看成是北京大學《國故》月刊的繼續。只是沒有像在北京大學那樣《國故》與《新潮》的對立。《國學叢刊》同時也有別於東南大學《學衡》與新文化、新文學的對立。《國學叢刊》上所登劉師培的遺稿,是劉師培的小叔劉富曾讓師培族親後人“將叢殘稿本寄呈”陳中凡的。
據《國學叢刊編輯略例》所示,本刊為“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同人組織刊行,以“整理國學,增進文化”為宗旨。體例分為插圖、通論、專著、詩文、雜俎、通訊,計劃每年出四期(季刊)。後來體例有所變化,分為插圖、通論、專著、書評、文錄、詩錄、詞錄、通訊。組稿編輯在南京的東南大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售。據第1卷第1期的“國學研究會記事”所示,本會的發起是在1922年暑假以後,由國文系的同學發起,本系教授樂為指導,遂出通告,不二日有一百人簽名。1922年10月13日召開成立大會,並確立了“指導員職員錄”和具體的工作機構。
國學研究會的成員有多人同時也是史地研究會或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的成員。國學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有講習會、討論會和編輯叢刊叢書。其中講習會在1922年10月一1923年1月共舉行十次:10月20日吳瞿安講《詞與曲之區別》、10月27日顧鐵生講《治小學之目的與其方法》、11月3日梁任公講《屈原之研究》、11月9日陳仲英講《近代詩學之趨勢》、11月17日江亢虎講《歐洲戰爭與中國文化》、11月24日陳斟玄講《秦漢間之儒術與儒教》、12月1日陳佩忍講《論詩人應具有之本領》、12月7日柳翼謀講《漢學與宋學》、12月24日江亢虎講《中國古哲學家之社會思想》、1923年1月9日梁任公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此系列演講,加上蔣維喬的一講@,由國學研究會編輯整理為《國學研究會演講錄》第1集,和江亢虎的《社會問題講演錄》一併列為“東南大學叢書”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據《國學研究會記事》所示,研究會各部在指導員的具體指導下,分別舉行了討論會:詩文學部11月15日、12月14日,經學部11月25日,諸子學部12月2日,小學部12月5日,史學部12月9日。同時又開了佛學課和歌曲班。其中佛學課由江蘇省教育廳長蔣維喬(竹庄)每周日上午來會講佛學二小時,並編印《佛學入門》一書。歌曲班由吳瞿安每周講兩次。另外國學研究會還有計劃地翻印、編印古書和遺稿(主要是劉師培的)。
首先從時間和實際的學術工作成績看,南京高師一東南大學的國學研究會所辦的《國學叢刊》只有三年多的時間(1923年3月至1926年8月)和三卷共九期的成績,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和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的工作相比,成績是弱了一些。尤其是大學本科學生的研究工作,無法和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的研究生的工作相比。他們之間的差距是看得見的。《國學叢刊》上的外稿主要是劉師培的遺著,其餘大都是東南大學師生的文章,寫文章的教師主要是集中在國文系的陳中凡、顧實、吳梅。由於陳中凡、吳梅都有來自北京大學的特殊身份和顧實留學日本的學術背景,使得國學研究會及《國學叢刊》較少“學衡派”的保守傾向,也沒有與北京大學的對立情緒。如果說他們也有保守成分存在的話,那最明顯的就是刊物堅持刊登的舊體詩詞。
九期《國學叢刊》的主要作者如教師輩的有顧實(鐵生、惕生、惕森)、陳中凡(鍾凡、斟玄)、劉師培(申叔遺稿)、陳延傑(仲英)、吳梅(瞿安)、陳去病(佩忍)、易培基(寅村)、胡光煒(小石)、章炳麟(太炎)、錢基博(子泉)、孫德謙(益庵)、李笠(雁晴)、蔣維喬(竹庄)等,其他都是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史地學會、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的成員(學生)的文章。其中舊體詩詞是刊物的一項重要內容。南京高師一東南大學的畢業生,暨國學研究會、史地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的成員,有幾位後來到清華學校研究院作研究生,繼續學習。如王庸、楊筠如、王鏡第、劉紀澤。浦江清、趙萬里則到清華學校任職。教師中的陳中凡、吳梅、陳去病,學生中的錢墊新、范希曾、姜子潤、陳訓慈、徐景銓、劉文翮、趙祥瑗、繆鳳林、景昌極、陸維釗、王玉章、陳旦、鄭鶴聲、胡士瑩、王煥鑣等同時在《文哲學報》、《國學叢刊》上登文章。同時,刊物還引起了日本學者的注意,神田鬯盒、大村歸堂(西崖)的文章和與顧實、陳中凡的通信在刊物上發表。為《國學叢刊》寫文章的作者還有陳衍、李瑞清(遺稿)、李詳、聶鴻仁、商承祚、王曾稼、陶鴻慶、冉崇烈、胡樸安、葉俊、李育、李傲、李冰若、余永梁、張世祿、蒙文通、唐圭璋、嚴惠文、黎群鐸、陳兆馨、張右源、樊德蔭、陳登元、江聖壤、杭海槎、吳法鼎、王錫睿、王熾昌、徐天璋、唐大圓、段天炯、田世昌、胡俊、姚鷦雛(錫鈞)、薄成名等。
顧實和他的同人把“國學”視為國家和民族的形象化體現,是對“宗國”和“聖學”的“知”和“思”。同時在學術研究中將學問本身與國家觀念相連,並且從“國學”中想象和構築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的主體。顧實在《發刊辭》中強調,編輯出版《國學叢刊》是為了表達一種愛國之心和好學之心。他說,“強鄰當前而知宗國,童昏塞路而思聖學”。“見兔顧犬,亡羊補牢”。現實的狀況是“外學內充,大有喧賓奪主之概”。“海宇之內,血氣心知之倫,咸莫不囂然曰‘國學…。與世界大的發展趨勢相銜接,“百學熾昌,是日自由”,“天下文明,是日平等”。海禁既開,異學爭鳴,截長補短,獲益宏多。《國學叢刊》就是本著這種基本精神。六藝皆重,統名日國學,綱舉目張。廣求知識於世界,一戒“止爭形式,不問思想”。二戒“高談義理,力追八家,字尚未識,便詡發明”。三戒“根柢淺薄,輒言溝通”。四戒“倡廢漢字,甘作虎悵”,“一切古書,拉雜摧燒”。他要求同人“掃千年科舉之積毒,作一時救世之良藥”。“不隨波而逐流,庶幾學融中外,集五洲之聖賢於一堂。識窮古今,會億祀之通於俄頃”。
顧實在這裡把國學的種類定為:小學類、經學類、史學類、諸子類、佛典類、詩文類。
刊物自1923年3月至1926年8月,共出版三卷九期。原定為季刊,年出四期,后因陳中凡於1924年11月應廣東大學校長鄒魯之邀,離開東南大學到新成立的廣東大學任文科學長,而難以繼續。
據第2卷第3、4期的“本刊特別啟事”所說:自第3捲起,改為不定期,約年出一期,仍有商務印書館印行。據第2卷第2期的“啟事”所示,第1卷4期和第2卷1期的編輯分別是陳中凡、顧實、吳梅、陳去病、陳中凡。即輪流編輯。自第2卷第2期開始在指導員陳中凡的具體指導下,由“國學研究會”的會員自己編輯。其中第2卷第2期註明具體編輯為田世昌。在第2卷第4期的《本刊兩卷總目並敘旨》說,自第2卷第1期以後,改由本會自辦,請陳中凡為指導員。
陳中凡、顧實是刊物的主持人。他們的思想決定了刊物方向,但同時也表現出相對的自由。反對新文學的江遠楷在《文學之研究與近世新舊文學之爭》一文,提出:“文學之新舊,即文學價值之多寡,新舊文學之爭,實文學價值之爭,亦藝術高下之爭也。”他說:“近年來文化運動之現象,作者深為痛心者也。苟能以藝術觀摩文學,則古文學之真者,美者,善者,亦因其新而愛之不忍釋手。今13作品之粗俗者,無聊者,亦以其舊而擯之不使入目。故近世新舊文學之爭,實不知文學為何物者。文學之藝術觀,當視此爭為無聊。徒增研究文學之障礙耳。”可以說,江遠楷個人反對新文學的言論並不能代表《國學叢刊》的立場。1923年12月,《國學叢刊》第1卷第4期,刊出顧實執筆的半文半白的《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1924年3月15、18日,《北京大學日刊》第1420、1422號作為“專件”分兩期連載。南北影響頓時連接。來自北京《晨報副鐫》的主要是批評。結果是“東南大學國學院”也沒能建立起來。據《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所言,“國文學系學程修畢之後,特設國學院以資深造,為國立東南大學專攻高深學問之一部”。顧實強調,因海禁開放,從知有天下到知有國家,從中西對舉之名詞而有國家觀念。於是中國的許多東西冠以國字,學者問也就有了國學問題。西風重古希臘、羅馬學術,而我愛國之士以本國學術精神為重,整理國學,即是研究世界文明源頭之一的學問。這也是晚清以來,面對西學而興的國學的主要原因,是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強化的結果。顧實認為治學功效,在於聯心積智。舊分心理為智情意三部,不如分主觀客觀兩面為簡要。“其民族心理而主觀客觀俱強也,其學術必昌”。“故本學院整理國學,根據心理,假定為兩觀三支如左。客觀:以科學理董國故——科學部;以國故理董國故——典籍部。主觀(客觀化之主觀)——詩文部。”(沈按:原文為豎排,“如左”即“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