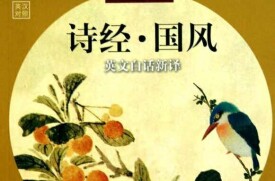鄭風
秦代民歌
《鄭風》為《詩經》國風中的內容,十五國風之一。為先秦時代鄭地民間民歌。鄭,古國名,姬姓。
詩經·國風·鄭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
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
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
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於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袒裼暴虎,
獻於公所。將叔勿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
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衤去。無我惡兮,不{宀疌}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宀疌}好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
報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萚兮萚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雲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雲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誑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洧之外,洵訁於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訁於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鄭風”共有二十一首詩。
| 緇衣 | 將仲子 | 叔于田 | 大叔于田 | 清人 | 羔裘 | 遵大路 |
| 女曰雞鳴 | 有女同車 | 山有扶蘇 | 萚兮 | 狡童 | 褰裳 | 豐 |
| 東門之墠 | 風雨 | 子衿 | 揚之水 | 出其東門 | 野有蔓草 | 溱洧 |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八○六)封其弟友於鄭。鄭地,即今河南的鄭州一帶。友,就是鄭桓公,當犬戎攻破西周王朝時,他與周幽王同時被殺。其子鄭武公與平王東迂,并吞了虢國與檜國的領土,沿襲舊號,命名新都為新鄭(今河南省新鄭市)。春秋時代鄭國的統治區大致包括今河南的中部和河南省鄰省的一些地方部分地方。“鄭風”就是這個區域的詩。
鄭國與東周王畿接壤,地處中原,文化較發達,春秋之際,人民創造了一種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調,激越活潑,抒情細膩,較之遲緩凝重的“雅樂”,無疑是一個進步。所以當時的名人季札聽了也不禁要脫口贊道:“美哉,其細也甚!”孔子責備“鄭聲淫”,要“放鄭聲”,就是害怕鄭國這一“激越活潑”的新聲,會取代周王朝的正樂。
“鄭風”中絕大部分是情詩,這雖同鄭國有溱水、洧水便於男女遊覽聚會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同鄭國的風俗習慣密不可分。從《溱洧》一詩看,鄭國的上巳節,實際就是一個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節日。正因為鄭國保留著男女自由交往的某些古代遺風,所以也就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如鄭厲公四年(前六九七),鄭國大臣祭仲的女兒雍姬問她的媽媽:“父親與丈夫哪個親近些?”她的媽媽答道:“父親只能有一個罷了,而丈夫卻個個男人都可做。”(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傳·桓公十五年》)一個世家命婦居然用這種褻瀆禮教的話來教育自己的女兒,鄭國一般人民的男女觀念,那就更可想而知了。懂得了這點,再讀鄭風中那些大膽的情詩,也就好理解了。
當然,從鄭國人民歌唱的本身說,恐怕反映自己勞苦和怨憤的詩歌也決不會少的。何況鄭國當“虎牢”天險,是兵家必爭之地,古人曾指出“春秋戰爭之多者,無如鄭”,但是,頻繁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卻在“鄭風”中看不到。這可能是編選者排斥的結果。
在《詩經·國風》當中,衛國的詩歌作品保存最多,《邶風》、《鄘風》、《衛風》共存詩三十九首。但是,若按十五國風的分類來計,《鄭風》是其中存詩最多的一類,共有作品二十一首。衛國為殷商舊地,衛詩的繁榮是無疑是接受殷商文化浸淫的結果,那麼鄭詩的興盛是否具有相同的原因呢?答案應當是肯定的。我們知道,從地理位置上講,鄭國處於殷商文化的中心區域,其深受殷商文化之浸淫自不待言。因此,鄭衛兩地的風俗民情也表現了許多相同的特點。《史記·貨殖列傳》雲“鄭、衛俗與趙相類”,而其記趙、中山之俗時云:“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漢書·地理志》記二國風俗時則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在春秋戰國時代,“鄭衛之音”是新興音樂的代稱。《禮記·樂記》魏文侯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由“鄭衛之音”這一名稱,我們可以推知鄭音與衛音賴以產生的共同的文化土壤,以及由此而呈現出來的基本相同的文化屬性。
另一方面,當“鄭衛之音”被作為新興音樂的代稱在春秋以後得到普遍地使用時,孔子卻是用“鄭聲”一名來指代當時的新興音樂的。他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i]他又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ii]其後,“鄭聲”之名與“鄭衛之音”等名稱并行於世。《漢書·禮樂志》云:“(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從這裡可以看出,與“鄭衛之音”相同,“鄭聲”也是被作為新聲的代稱使用的。“鄭聲”何以能夠獨自成為新興音樂的代稱?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這與鄭國商人的活躍、商業經濟的繁盛以及由此而帶來的都市文化的發達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春秋時代,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興盛,從開國之初就建立了經商傳統的齊國自不待言,晉楚等國之間的商業往來亦相當頻繁。但是,在所有諸侯國中,商人在鄭國所擁有的社會地位卻是其它國家無法相比的。這在《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對韓宣子的一段話中得到了相當突出地反映:“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鄭公室與商人盟誓以相保,鄭國商人地位與勢力之強由此可見。《左傳》所記三起有關商人的事件皆出自鄭國,而鄭商人弦高以鄭君的名義與秦軍交涉而使其退兵一事,更集中地反映了鄭國商人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鄭國的商人“出自周”,而這些“出自周”的商人的祖先,卻是在西周初年被遷至成周的殷商遺民。《尚書·酒誥》有云:“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由此可知,“藝黍稷”與“牽牛車、遠服賈”是周人克商后殷商遺民被特許從事的社會活動。在喪失土地的情況下,經商成為殷商遺民最主要的謀生手段,因而也使“商人”成為經商者的代名詞。[iii]失去土地與政治權利的商人雖然地位低下,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依然能夠承襲殷商文化重聲的傳統,保持其文化屬性上的相對獨立。這應是在商人擁有特殊地位的鄭國其聲樂文化相對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由於文化的傳承性所發生的影響之外,鄭國聲樂文化的發達與鄭國商業的繁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知道,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本身即是衡量文化是否繁榮的一個標誌,一個國家的經濟中心往往同時也是文化的中心。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文化的繁榮往往最直接地通過人們對聲色犬馬等物質享受的喜好與追求中表現出來,新聲靡樂的興盛往往是一個城市或地區經濟走向繁榮時最直觀的表現形態。南北朝時的金陵、隋唐時的揚州都提供了這方面的典範。因此,當鄭國的商人與政治家結盟而獲得政治上的保障時,鄭國的商業經濟走向繁榮當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實。作為自由貿易的條件與結果,各種類型的“市”(“肆”)也為人們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機會與場所。出現於《鄭風》中的“東門”,即市民及手工業作坊集聚的東郭的正門[iv]。商業貿易的發達與鄭地故有的濃郁的商文化色彩,共同促進了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鄭地的新興音樂因此成為諸侯國中最為發達的一支。“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其俗淫”,聲樂文化的發達不但為《鄭風》作品的大量採集提供了條件,也成為“鄭聲”之所以能夠指代“新聲靡樂”的重要原因。
“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不但是鄭聲繁盛的原因,同時也造就了《鄭風》作品內容的基本風格。《鄭風》中的二十一首作品,除《緇衣》、《清人》、《羔裘》等數詩之外,絕大部分為男女之間的情思歌唱。作為文學的永恆主題,“愛情”本身不會標示其所處的時代,這是我們很難依據情歌的內容為其斷代的主要原因。然而,對於本文的考證而言,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是,《詩序》“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詩方式,在進行政治的說教時也保存了這些作品被采編的時代。因此,依重《毛詩》首序,搜集各種材料以證成其說是本文給《國風》作品進行斷代的基本思路。
在考訂《鄭風》作品的時代之前,有必要對春秋前期鄭國的歷史稍做概括的敘述。西周末年,鄭桓公寄孥於虢、檜,鄭武公終取之,國於鄭。前742年,鄭武公卒,其子庄公繼位,鄭莊公繼武公為平王卿士,專王政。周桓王繼位后,周、鄭交惡。魯桓公十一年(前701年)五月,鄭莊公卒。鄭世子忽繼位,是為昭公。同年九月,宋人誘執祭仲,使之立厲公,鄭昭公忽出奔衛。魯桓公十五年,鄭昭公復入於鄭,鄭厲公出奔蔡,后居於櫟。魯桓公十六年,高渠彌殺鄭昭公而立公子亹。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齊人殺子亹於首止,鄭祭仲逆鄭子儀於陳而立之。魯庄公十四年(前680年),鄭厲公自櫟入,鄭公子五爭之亂乃定。后八年(前672年),厲公卒,其子文公繼位。鄭文公繼位時,齊桓霸業已成。此後,晉楚代興,鄭國周旋奔走於諸大國之間,尚能苟存,入戰國后,終滅於韓。
《鄭風》中的作品,根據《詩序》,除《緇衣》產生於東周初年鄭武公時代之外,大多出現於鄭莊公至鄭文公約一百年間,尤以眾公子爭位的二十年間產生最多。茲依時代先後,述其可考者如下。
《叔于田》、《大叔于田》當作於鄭莊公克段於鄢之前。《叔于田》云:“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以側面烘托的方式讚美“叔”的豪邁出眾。《大叔于田》云:“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以直賦的方式鋪敘田獵場面,為正面實寫。此二詩互為表裡,因同一母題而成詩,詩歌主人公“叔”應為同一人。據《左傳·隱公三年》記載,鄭莊公母弟名叔段,后因封邑於京,又稱“京城大叔”。故說詩者多以此二詩中之“叔”為鄭叔段,而持異說者以為叔段叛亂鄭國,不應有此讚美之辭。然《春秋·隱公元年》雲“鄭伯克段於鄢。”《左傳》釋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楊伯峻注云:“此若書段出奔共,則有專罪叔段之嫌;其實庄公亦有罪,若言出奔,則難於下筆,故云‘難之也’。”魯史尚不專罪於叔段,況叔段本為有勇有才之人,在其叛鄭之先,庄公因母親之故,對之尊寵有加,鄭人作詩美之亦屬自然。《大叔于田》“襢裼暴虎,獻於公所”既表現了叔之勇武,亦道明了“叔”與鄭公之親近關係。古說以‘叔’為叔段,良有以也。《詩序》云:“《叔于田》,刺庄公也。”“《大叔于田》,刺庄公也。”據《左傳》,叔段之叛亂實因庄公誘導所致,序詩之人以美叔段之詩為“刺庄公”,與《春秋》同旨。
《將仲子》。其詩有云:“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毛詩序》云:“《將仲子》,刺庄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毛傳》云:“仲子,祭仲也。”以詩中“仲子”為鄭莊公謀臣祭仲,其說殊不可通。詩乃一女子婉拒戀人之辭,然首序之言仍有可取之處。從詩歌的語法特點來看,《將仲子》頗與出現於西周後期至春秋前期的詩歌相類。如此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小雅·綿蠻》則雲“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此詩云“仲可懷也”“亦可畏也”,《豳風·東山》則有“不可畏也,伊可懷也”。而詩中“將仲子兮,無逾我里”之“將”,《毛傳》:“將,請也。”為表示願望之義的語詞。在《詩經》中,“將”字作此用者有《小雅·正月》“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衛風·氓》“將子無怒”、《鄭風·大叔于田》“將叔無狃”等。除此之外,此詩次於“美武公”之《緇衣》后,在“刺庄公”之《叔于田》、《大叔于田》之前,《詩序》以為“刺庄公”,其時代可取。
據《詩序》,《鄭風》中與鄭忽相關的作品有以下五首:《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萚兮》、《狡童》、《揚之水》。其中前四首序雲“刺忽也”,后一首序雲“閔無臣也”。由鄭忽辭齊婚而祭仲勸言“君多內寵,子無大援”,以及鄭忽即位為祭仲所逐、復入為高渠彌所殺等事,知“閔無臣”亦就鄭忽而言,《毛詩》續序釋首序云:“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其說不誤。由詩歌本身而言,《有女同車》之“洵美且□”式,亦見於《叔于田》,“美孟姜”,見於《鄘風·桑中》;《山有扶蘇》之“山有□□,隰有□□”為西周末、春秋初詩歌套語,“子都”之名,則見於《左傳·隱公十一年》,即鄭大夫公孫閼。楊伯峻云:“竊疑公孫閼即《詩·鄭風·山有扶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之子都,其人貌美,得庄公寵幸。”《詩》中“子都”不必即是《左傳》之“子都”,子都貌美,取其字以為美男之代名詞亦無不可。《萚兮》之“叔兮伯兮”亦見於《邶風·旄丘》。《狡童》之“維子之故”亦見於《唐風·羔裘》。《揚之水》之“終鮮兄弟”與《王風·葛藟》“終遠兄弟”相近,又《王風》、《鄭風》各有一篇《揚之水》,均作於周平王後期。通過上述語言句式的橫向比較可知,上述諸詩與可被考訂為春秋前期的詩歌語言表現了相同或相近的特點。《詩序》以為“刺忽”,今依其說將諸詩的產生時代確定在鄭庄、厲之世。
另外,《褰裳》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豈無□□”式,見於《衛風·伯兮》、《鄭風·叔于田》、《唐風·杕杜》、《唐風·羔裘》。而“狂童”之稱,亦與出現於《山有扶蘇》、《狡童》二詩中的“狡童”、“狂且”相類。另外,在《詩經》中,《褰裳》與《狡童》諸詩次第排列。其詩之出現當與《狡童》諸詩相近,亦在鄭莊公、鄭厲公時代。
除了這組“刺忽”之作外,《鄭風》中還有一組“刺亂”、“閔亂”之作,它們是:《豐》、《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其中首序直言“刺亂”的有《豐》、《東門之墠》、《溱洧》,言“閔亂”的有《出其東門》,首序未及“亂世”而續序言之者有《風雨》、《子衿》。鄭之亂世,指自鄭莊公卒到鄭厲公定位至約二十多年,即《出其東門序》所云“公子五爭,兵革不息”之世。這一組詩歌內容本身與時政沒有直接的關聯,大多抒發的是相愛、相思的喜悅與怨艾之情。無論是內容還是風格,都與“刺忽”諸詩非常相近,表現了相當濃厚的民俗色彩。再從詩歌的語言句式來看,《豐》雲“子之丰兮”,《齊風·還》雲“子之還兮”、“子之茂兮”,《陳風·宛丘》雲“子之盪兮”;又“叔兮伯兮”,亦見於《萚兮》與《邶風·旄丘》。《東門之墠》之“豈不爾思”,亦見於《衛風·竹竿》、《王風·大車》、《檜風·羔裘》,其“東門”之地與“茹藘”之物又與《出其東門》同;《風雨》之“既見君子”,多見於西周末東周初年詩歌,“雲胡□□”與“云何□□”句式相同,而“云何□□”式習見於西周末春秋初年詩歌。《子衿》之“悠悠我思”,亦見於《邶風·終風》、《雄雉》等,與“挑兮達兮”句式相同的“□兮□兮”式,則有《邶風·旄丘》“瑣兮尾兮”、《衛風·淇奧》“寬兮綽兮”、《齊風·甫田》“婉兮孌兮”、《小雅·巷伯》“萋兮斐兮”;《野有蔓草》之“清揚婉兮”,又見於《齊風·猗嗟》。《溱洧》之“洵□且□”式,亦見於《叔于田》、《有女同車》、《邶風·靜女》等。另外,《溱洧》之士與女秉“蕑”而會,《毛傳》云:“蕑,蘭也。”《御覽》卷三十引《韓詩》云:“蕑,蘭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執蘭而祓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由詩觀之,就士、女而言,秉蕑除了“祓除不祥”之外,還有另一種象徵意義。《史記·鄭世家》載鄭文公二十四年燕姞夢天與之蘭而文公幸之、生子名蘭事可為其證。燕姞之夢蘭,或因其時歌謠所云“士與女”秉蘭而會有所感念,故言之以喻文公。綜上數端,這一組“刺亂”、“閔亂”之作,其產生時代當不出鄭厲、文之世。
《清人》當作於鄭文公世。《毛詩序》云:“《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御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春秋·閔公二年》云:“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云:“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清,鄭邑名,高克及其所率師疑皆清邑之人,故《詩》云云。”詩“清人在彭”《毛傳》云:“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水經·潧水注》云:“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徑清陽亭南,東流即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故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有清陽亭。’是也。”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云:“彭者,河上地名。《左·哀二十五年傳》:‘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封賜彭封彌子。’彌子瑕食采於彭,為彭封人。蓋衛邑而與鄭連境,故克帥眾在此防狄渡河。”由詩中“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等句的描寫,可知此詩之作在其軍未潰之前。后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故鄭人賦之以刺文公等人。詩之作當在鄭文公十三年(前660年)前後。
《羔裘》當作於鄭五子之亂的時代至文公世之間。其詩云: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捨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詩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從詩的內容來看,這是一首讚頌之詩,但是對於讚美的對象,從《詩序》開始即無確指,至明代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始以鄭文公大夫叔詹當之,其後多有從者。如魏源《詩古微》證成其說云:“文公之時,三良為政,所謂‘三英粲兮’也。文公背齊從楚,則孔叔諫之,文公不禮重耳,則詹叔諫之,所謂‘邦之司直’也。又幾被讒殺於齊,見烹於晉,又謂‘捨命不渝’也。”但是,從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v]開始,金文研究的深入使“捨命”一詞得到了重新解釋,他根據《克鼎》、《毛公鼎》的銘文提出“捨命與旉命同意”的說法。林義光《詩經通解》進一步申述說:“舍字在金文多釋為賜予,捨命即錫命,亦即敷命之謂也。《易·姤卦·象傳》云:‘有隕自天,志,不,捨命也。’不為發聲語助,捨命亦即賜命,故為有隕自天之象。此詩捨命之解亦當從鼎文與《易傳》。”據此,則“捨命不渝”與叔詹幾烹於晉一事無涉。季旭升《〈詩經〉“彼其之子”古義新證》一文對此詩的題旨做了全新的解釋,他說:
本詩的“彼其之子”不太像鄭人讚美本朝賢人的口吻,倒是有點像稱頌和鄭人隔得比較遠的人。因為,如果鄭人要讚美自己朝廷的賢人,似乎應該用“烝我髦士”、“勉勉我王”等這種“我”字句式而不應該用比較疏遠的“彼”字句式。因此我們認為:本詩的“彼其之子”應該解釋為“那(其、己、紀)氏之子”,全詩是鄭人感嘆當朝(依鄭箋,是指鄭莊公時)沒有忠正之臣,所以詩人歌詠一位氏的賢臣,以譏刺當朝。[vi]
季氏的解釋的確更符合詩義,也與《詩序》的內容相吻合,但是他根據鄭箋將詩繫於鄭莊公朝未免有些牽強。鄭箋云:“鄭自庄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從鄭國的史事來看,鄭莊公卒后,執政大臣祭仲逐昭公而立厲公,致使公子五爭,內亂不止達二十多年。鄭文公繼位后,又有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退之不以道”,有《清人》之刺。《詩序》所謂“刺朝”,鄭箋所謂“自庄公”,皆就此而言。結合鄭國史事,此詩之作,應不出鄭五子之亂至鄭文公世。
而從詩歌的語言來看,見於此詩的“洵□且□”式、“邦之□□”式等,為春秋前期詩歌慣用之語。再從《詩經》的編次來看,《羔裘》次於《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等“刺忽”之作前,其產生時代當相去不遠。而由《清人》刺鄭文公,知《羔裘》諸詩編入詩文本的時代,應與《清人》同時。

鄭風
根據以上的考訂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鄭風》作品的最後完成期應在鄭文公時代。而從上文的考證我們也能發現《鄭風》作品在編排次序上表現出來的一個特點,這就是凡涉及鄭國公卿大夫的作品,都排列在以男女情愛為內容的民俗色彩濃厚的歌謠之前。其中《羔裘》雖然歌頌的是身著諸侯之服的“彼其之子”,但“彼其之子”畢竟不是鄭國公族,故次於刺文公的《清人》之後,諸民俗歌謠之前。《鄭風》的這種編排次序,相當明顯地體現了周禮“尊尊”的倫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