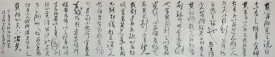朋黨論
北宋歐陽修創作政論文
《朋黨論》是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的作品。這是歐陽修在慶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駁斥保守派的攻擊,辨朋黨之誣。文章實踐了歐陽修“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全文通篇對比,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很有特色。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1.惟:只。幸:希望。
2.大凡:大體上。道:一定的政治主張或思想體系。
3.黨引:勾結。
4.賊害:殘害。
5.守:信奉;名節:名譽氣節。
6.之:指代上文的“道義”、“忠信”、“名節”。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規範進行自我修養。濟:取得成功。
7.退:排除,排斥。
8.共(gōng)工驩兜(huándōu)等四人:指共工、兜、鯀(gǔn)、三苗,即後文被舜放逐的“四凶”。
9.八元:傳說中上古高辛氏的八個才子。八愷:傳說中上古高陽氏的八個才子。
10.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傳說他們都是舜時的賢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樂,稷掌管農業,契掌管教育。《史記·五帝本紀》載:“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
11.更(gēng)相:互相。
12.書:《尚書》,也稱《書經》。
13.惟:語氣詞,這裡表判斷語氣。
14.周:指周武王,周朝開國君主。
15.用:因此。
16.後漢獻帝:東漢最後一個皇帝劉協。逮捕,囚禁“黨人”應是桓帝、靈帝時的宦官所為。
18.目:作動詞用,看作。
19.黃巾賊:此指張角領導的黃巾軍。“賊”是對農民起義的誣稱。
20.解:解除,赦免。
22.昭宗:唐朝將要滅亡時的一個皇帝。殺名士投之黃河本發生於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後一個皇帝。
23.“此輩清流”兩句:這是權臣朱溫的謀士李振向朱溫提出的建議。朱溫在白馬驛(今河南洛陽附近)殺大臣裴樞等七人,並將他們的屍體投入黃河。清流:指品行高潔的人。濁流:指品格卑污的人。
24.誚(qiào):責備。
25.厭:通“饜”,滿足。
26.跡:事迹。
27.鑒:動詞,照,引申為借鑒。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麼“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鑒了。
慶曆三年(1043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後黨議不斷發生,宋仁宗在寶元元年(1038年)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夥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貶,歐陽修在朝廷上爭論力救。只有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認為范仲淹當貶。歐陽修寫給高若訥一封信,指責高若訥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之心。高若訥將此信轉交當局,結果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力救范仲淹而被貶,當時便有一些大臣將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視為朋黨。後來仁宗時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就在慶曆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
歐陽修幼年喪父,家境貧寒,苦讀而中進士,后歷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朝廷要職,因彈劾政敵夏竦、呂夷簡等人,曾遭遇政敵的朋友圈子的惡意攻擊,被政敵指責為在朝廷拉幫結派搞朋黨,因而也曾屢次被罷職貶官,可謂仕途多舛。歐陽修故而憤筆寫就這篇雄文,算是對政敵的一種理論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塊壘。
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迴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闢,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直接提出觀點,認為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
第二段:先說有兩種“朋黨”,即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麼呢?”說明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鍊自身,那麼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為國效力,那麼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這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
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麼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鑒。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並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借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