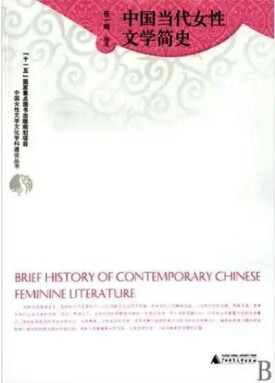女性文學
以女性為經驗主體的文學流派
徠女性文學是誕生於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具有現代人文精神內涵,以女性為經驗主體、思維主體、審美主體和言說主體的文學。
女性文學的發展
女性文學雖然也稱為女性解放文學、女性主義文學,但根據鄭英子(韓國文學批評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學和女性主義文學都只是女性文學領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學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質或由女性執筆寫作的文學。
雖然西方正式開始關於女性文學的爭議具有很長的時間差,但都是指從英國作家維尼吉亞▪沃爾夫(英)的《自己的房間》(1929)和西蒙▪波伏娃(法)的《第二性》(1949)的出版為源頭。此後女性文學的爭議經過對瑪麗·埃爾曼(Mary Ellmann) ,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等人的女性形象批評后,從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1970)開始具有理論和批評的力量,後期通過受到構造主義(特別是雅各·拉岡的理論)和解體主義(deconstruction)影響的法國理論家的“女性寫作(海倫 西蘇(Helen Cixous) )”理論獲得了更大的動力。
伊萊恩·肖沃爾特 (Elaine Showalter)綜合這樣女性文學的爭議將女性文學分為三個階段:①較長時期模仿統治傳統的流行模式,使其藝術標準及關於社會作用的觀點內在化階段(Feminine);②反對這些標準和價值,倡導少數派的權利和價值,包括自治權的要求(Feminist);③從自我發現到賦予女性經歷以特性的階段(female)。
在這一界說之下,女性文學的視野是開放的、發展的系統,而不是封閉靜止的,應該是女作家基於性別主體意識、性別視角表現的關注女性命運、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學,或者是基於超性別意識(隱含性別主體意識)、超性別視角(隱含性別視角)表現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內的、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文本。女性文學仍是一個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題。
女性文學充分表達獨特的女性魅力和奇特理念,完善人性本身精華,展現各階段女性充當的角色,挖掘出靈魂最深處的獨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那些吶喊、那些彷徨、那些輕浮、那些堅強,體會著女性獨有的信仰理念。
女性書寫已成為社會文明的一個文化符號
我們已經開始從文學中分出性別,並定義出“女性文學”這樣的概念,開始看出文學性別的差異對文學與人生的影響。“差異”的概念來自於被認知物與記憶的對照,這種對照其實是對舊有的遺留的文學常識的反思。可以這樣說,中國當代文學的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這種差異的推進和認知中不斷向前的。
中國百年文學中,大量女作家的湧現和大量婦女問題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學關注,大量兩性關係的鄉村化都市化和慾望化的多重敘述和多元描寫,女性從肉體哲學到靈魂鞭笞,從“拷紅”到“審男”乃至於阿Q與吳媽的原初慾念都一一在這種差異中顯示著文學的詩學表達,顯示著兩性文學關係中的深度差異,正在成為文學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但是,從女性的詞根出發,對之的文學定義其實是大有問題的,貌似尊重而將事關女性性別的文學,從創作到實踐都與男性特別區分開來,謀求差異求得平衡以顯示公允。看出差異是一種進步,而差異本身則是一種歧視。因之女性文學的定義也就問題叢生—這是長期以來學界的一個錯誤—是指作者性別,不涉其餘?是指文學題材、女性意識?還是兩者兼而有之?文學史中並不鮮見這樣的現象:一是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毫無二致,二是男性作家照樣可以寫出女性意味或女權主義的作品,如郁達夫、葉靈鳳等;女性作家也不乏寫出陽剛粗獷毫無女性意識的作品,如草明、劉真等革命作家。
(故“女性文學”更為準確的定義應是“女性書寫”,這是社會開放和文學進步予女性的文學尊重,也是現代社會文明通過文學表述,窺視兩性差異以走向和諧的理性補充。而把女性問題囿於女性作家性別視野之內,這恐怕不是女權主義的旨意。)
問題不在於由誰來書寫,在男權時代,女性寫作被當作反抗男權的證明,而在女權時代呢?作者的性別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主張男女平等而又性別文明尚在消長的現代社會,女性書寫才彰顯出它獨特的意義。也就是說,女性書寫本身已然超越自身而成為一面旗幟,一面爭取獨立平等的旗幟,一個表明社會性別文明程度的文化符號。
法國革命喚醒了女性的覺悟,提出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問題。19世紀末,美國英國發生了爭取婦女參政的運動,第一個目標就是爭取選舉權,然後是爭取在教育、文化和工作上的平等。到上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一直在蓬勃發展。
徠1987年12月30日西班牙《終極日報》載文《世界女權運動》:“教育界已不再是男人的勢力範圍,進入大學的男女同學之間的比例逐漸趨於平衡,婦女已認識到受教育是尋求職業的必由之路。20年前主張性解放的婦女,現在發現自己成了男人滿足慾望的工具。因此,她們甚至組織起來反對選美,認為這是對婦女的侮辱。在一系列問題上,需要做出明確判斷。全世界的婦女都知道,她們要走的路還很長,然而目標是不會改變的,這就是男女平等。”
這種描述的基本軌跡至少表明了如下傾向,女權運動在多年挫折和反覆之後,從開始時注重對自身以外的條件進取轉向女性自身,包括對社會生活、家庭角色的體驗,轉向內心生活需要。這種轉向,啟示我們對以往女權運動做歷史檢討和清理。女權運動,究其實是爭取在社會生活同時在心理需求上與男性取均衡平等的權利。這種爭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男性被當作“物種之范”的質疑與反抗。男子在所有神話里被看作具有規範性,而女性則是這一規範的變異和離差。男子是主體,女子是他體。男性對女性的所有作為,其動機都在“收回”,而女性作為肋骨,所有的被動都在於“回歸”。這就是男權理論的最古老註腳和男女關係的哲學解釋。依照這種認知,假如把女性比做左撇子,則女性是生活在為右撇子創造的世界里,在這個世界中男性代表著規範性。這種觀念所產生的心理效果,在人類社會許多文化行為中可以找到例證。
在英語里“男人”這個詞可以作為人類總稱,日文中“男人”的語意為“主人”。中文古代漢語中沒有“她”這個字,女性在世界範圍內的語言領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著,這種語言現象尤為深刻地證明男性文化對人類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一種集體無意識接受了這種侵略和滲透。這種深層意識在男人那裡也處於自覺的超穩定狀態。歷史這樣安排了男人在一切方面的優勢。可是,稍有古代歷史文化常識的人都清楚:所謂男性範本其實是漫長男權社會的結晶,並非有充分的生物學根據。而男性範本的神話,在不同文化時期里,也是處於變動狀態的。
這種歷史變動在文學中以拋物線式軌跡展示著它魅人的況味。
人類是在女性腹腔中發源的,太古初民對女性的神聖崇拜,編織母權中心的漫長歲月。中國最早的神話《山海經》獰厲地記載著中國第一個女神西王母的威儀,這是初民宇宙觀中眾神之首的偉大形象。原始時代的西王母是母氏社會的女神,她從原始神話的半人半獸,至魏晉鋪張成為群仙之首,至此完成了最後的演化,此後再無發展。這至少可說明母權歲月的遙遠追憶,浸潤了漫長的歷史年代,在被父權制代替之後,文學對之依然記憶猶新,但在日漸強大的男權面前,它漸趨黯然,滲入了當代人的思想。
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變動徹底抹去了人們對母權歲月的最後記憶,女性政治經濟地位的沉落在神話的演化中表現得十分徹底。漫長的母權歲月消彌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來,男權優勢一直在左右著歷史的發展,女性由神聖轉為邪惡,作為這發展的反面,在神話中被改寫,在現實中被反轉。希臘神話“潘多拉盒子”,夏娃成為萬惡之源。這些以男權中心為依託的神話或教義,無非都是在強調現實中的男性秩序。男性為中心的神話,它在現代文明社會已銷聲匿跡,但作為一種非意識思想意識,它時時在支配著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為,成為知和行的無形準則。女性們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這種非意識思想在日常生活與精神領域中的危險呢?它微妙的生活狀態與形式表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深刻的理性批判呢?
女性的自我覺醒首先在文學中得到張揚。女性的壓抑首先是人性的壓抑,即性和情慾的壓抑。五四新文學營造了一個個性解放的語境,尤其著名且實績豐厚的堪稱“創造社”的作家們,以兩性關係為切口,注重表現人的情慾和天性,釋放本我,解放情感、情慾的人性革命,是創造社熱衷的話題。據茅盾於1935年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寫的《導言》中說,1921年5—7月三個月間,刊載於各類雜誌的新小說有115篇,其中愛情小說有70篇,農村生活只有8篇,城市生活的3篇,家庭生活9篇,學校生活5篇,社會生活的計20篇,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實在乃是描寫了男女關係”。所以“竟可說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佔了全數百分之九十八了”。這種傾向,在新時期以降的小說創作里又重演了一遍,而這一次的演出竟然是陰盛陽衰的。
女性寫作在80年代勢頭初涌,90年代勢如決堤,21世紀則勢成泛濫。在兩性問題的文學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遠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家。挑逗成為所謂文學的手段和目的,這些出位和離文學甚遠的物事姑且不論,但接續五四新文學的個性解放和張揚自我的文學傳統,且有革命性顛覆的,正是由女性書寫來完成。
在當代文學中,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最早觸摸到女性愛而不得所愛,卻又不能忘其所愛的悲劇,質疑兩性關係中的非愛情因素的合理性,以文學方式探索釋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的當下實踐。
這在文革剛剛結束的1979年,無疑是石破天驚的,也是切中中國式婚姻命脈之作。女主人公鍾雨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她的所愛,只能把對他的愛投注在他的贈物——契訶夫小說選集中去,把現世的苦戀寄寓天國與來生。張潔技巧地表達了中國女性埋藏得很久的生命慾望,而又把這種慾望置於自由的逃避之下。責任、道義、剋制等人類美德,似乎瞬間化作來自遠古荒原的巨垣,橫卧在兩顆吸引得很苦又分離得很累的靈魂之間,異化為一種偽飾的崇高。她把女性生命的焦慮,化作一種崇高,她叛逆了個性慾望而服從某種道義。張潔把主人公的悲劇,置於殘酷的對話系統中去演繹,而把自己間離出來。
張潔斷然和清醒理性地編織這個故事,並以第一人稱的敘述,令人物痴迷沉溺其中難以自拔卻依然期待無望,作品的間離狀態,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辯難的複雜情狀客觀化,完成了對一種普遍真相的返照。張潔因此也就實現了不僅僅站在狹隘的女性立場,而是在人的制高點上俯視兩性關係中東方文化氛圍中的種種詰難。
女性書寫是都市時尚和消費的表徵
下面要說到的是另一種女性書寫,映川的小說,她在追求純粹之愛的同時,塑造著男性,而這種塑造是在面對差異,反覆離合中實現的。這同時也代表了21世紀中國社會女性主義進化的人性成就,她們已經遠遠地走出了張潔的時代牢籠,已經不是被動地被選擇,而是主動地進取地選擇著,選擇就是自由。
映川在長篇小說《女的江湖》中,塑造了一個不僅知道自己愛什麼、怎樣愛,同時具有主體性衝擊的“我要”的女性。她在情感、人性的不斷逃離與回歸中,實現了自我與對方的互救、鋪陳了相互的差異。她在極度自由的情愛空間里遊走,卻又本能地逃避著自由的侵擾。在經歷過三個不同的男人之後,她終於還是選擇了其中的顧角。她給顧角寫了最後的信,她無奈著同時又熱望著,這是一種純粹對庸常的投降,也是對男性的挑戰與和解。這是退守的進攻,是明智的舉意。既是女性最終的現實姿態,也是生活本身為女性準備著的理性姿態。
映川自然未及杜拉斯的冷峻,也沒有張潔撕心裂肺的凄楚悱惻,她只是有所選擇十分明智地消費著、時尚著愛情。而她對愛情的陰謀對生活庸常的穿透,有著一種東方式的現代狡黠。
在這篇文章里,文學女性有著多重的況味。從西王母起始而至榮燈,期間橫亘著女性從神到人,從人的解放和人的張揚到人的心靈自由的模糊身影。從中可讀出時代的女性進步同時面臨更具精神性的危機。女性書寫在這種危機中也就有了別樣的價值。特別是在現代都市化過程中,女性及女性書寫是都市時尚和消費的一個表徵。都市化其實亦是女性化。比如深圳,就其消費、時尚和生活質量而言,它是一個女性的城市。
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的女性文學是中國20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她和“五四”新文學同時誕生並共同經歷了近百年的歷史滄桑,湧現出五、六代女作家和豐富的創作實績。
如果說現代性是新文學有別於傳統文學的特質,那麼女性文學是不是現代性的新文學,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迴避得太久。而回答這個問題,實在是我國女性文學研究的起點。自從女性文學這個命名出現以來至今仍然自說自話的女性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也必須從界定和梳理女性文學的現代性入手。
伊麗莎白·詹威在《美國當代文學·婦女文學》中指出:由於女性文學來自被抹煞的人類“另一半”的生活經歷,需要“用一種不同度數的鏡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們”。
〔1〕也就是說,這個“鏡片”的“度數”要和女性文學的實際相符相配,就必須從女性文學的誕生說起。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的語言中,人類(humanbeing)、人(human )、歷史(history)等詞語都不包括女人,她們在人和歷史的範疇中是不在場的缺席者。文藝復興、啟蒙理性的人文主義思想是抽象的人,如果具體化一些則僅指男人。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只是男權宣言,發現了這一點的阿倫普·德·朱戈在法國大革命兩年後的1791年發表了《女性與女性市民的人權宣言》,她後來因此而被送上了斷頭台。拿破崙法典則明文規定:“未成年者、已婚婦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沒有行使法律的權利。”美國婦女在解放黑奴的運動中才意識到自己和黑人一樣處於無權地位,所以積極投入奴隸解放運動,並引爆了19世紀20—40年代的女權運動,於1848年發表了類似法國女權宣言的《女性獨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她們把“人”這個詞改寫為“@①”。
〔2〕由此可見,女性的覺醒始於認識到“人”這個抽象概念掩蓋下人和人事實上的不平等,始於女人追求和探尋自己作為人的價值的全面實現。到20世紀60年代即美國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被譽為美國現代女權運動之母的貝蒂·傅瑞丹在她的《女性迷思》和《第二階段》里對此有詳細記述和反思。“女性迷思”(Feminine Mystique)是她在1963 年對當時一種關於女性的錯誤思潮的命名,指僅以“性”和生物上的母職來定義女性。
〔3 〕她把美國兩次女權運動中女人走出家門爭取與男人同等的工作權利的鬥爭稱為“激昂之旅”,目的是“尋求新的認同”,是“強烈拒斥對女人所作的定義和認定。她們努力想證實:‘女人也是人’”。這些都說明西方女權運動的思想動力也是從人的發現覺醒到女性的發現覺醒,說明女性的發現和覺醒是人文價值理想的深化和具體化,這也就是我在這裡命名的女性人文主義思想。
世界範圍的女性文學只能出現在現代工業革命和民主主義革命及宗教改革之後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轉型期間,出現在現代人文思想深入人心的現代性進程之中。這在各國的具體時間不盡相同,但大體上是在19—20世紀才彙集成世界性的文學潮流,尤其是在本世紀後半期西方婦女爭取人的權利的女權運動推動下,女性文學遍及全世界發達與不發達地區。法國17、18世紀雖然被稱為“女性的時代”,但20世紀前女作家少得可憐。即使在文藝復興的搖籃義大利、希臘,大批女作家的出現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
〔4〕就此而言,19—20 世紀也可以說是女性文學的世紀,是女性文學在世界範圍的絢麗日出。
在中國,女性文學的誕生與世界各國同中有異。我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的前言中,具體分析了本世紀初西學東漸、興辦女學、大學開女禁、招收女留學生等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及“五四”思想啟蒙的精神成果(人的發現、覺醒女性的發現、覺醒與女性文學誕生的內在聯繫),分析了“五四”前後出現的我國第一批既受過傳統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的現代知識女性。沒有這樣的現代知識女性便沒有我國的女性文學。我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女性文學“與人性、個性同命運”,“同真正意義上的歷史進步同命運”。到現代可以補充的是,女性與女性文學,和人性的完善、個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進步、和平、發展這些人類共同珍惜的價值觀念同命運,和女性人文主義價值的全面實現同命運。
不同的是,西方各國從人的發現到女性的發現一般相距200—300年,而我國則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由一些思想先驅在人的解放這個命題中同時提出來的:
在占人類半數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確的認識,尚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參與文化的事業以前,人類無論怎樣的進化,總是偏枯的人類。
〔5〕(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我國人的解放與女性的解放在同一個時間平面上同時提出,固然縮短了西方婦女那樣漫長的醞釀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覺醒后的路格外曲折漫長,使她們常常要承受夢醒后無路可走的悲哀。早期女作家廬隱、石評梅、馮沅君的作品里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迷惘、徘徊、悲涼之氣,便源於這種女性解放的理想與封建古國沉悶落後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魯迅作為反封建思想鬥士也是婦女解放的堅定的倡導者,但他很快就清醒地覺察到了女性解放前程的曖昧不明,提出了“娜拉走後怎麼樣”的問題並且不得不讓勇敢的子君孤獨悲涼地死去。
我國女性文學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正是因為女性對自己作為人的價值理想的群體性覺醒,出現在第一批現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中,儘管這種覺醒難免帶有初醒者的朦朧迷惘和不成熟。有論者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是歐洲中心論,因而“五四”女性對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價值認同也在此列。這是無視本國本民族社會現實的歷史發展外因論。誠如嚴家炎先生所指出的,“把科學理性、工業化、現代化當作歐洲國家壟斷的專利,才是真正的歐洲中心論。”
〔6〕女性文學19—20世紀在世界範圍內興起,充分說明了“認為人和人的價值具有首要的意義”
〔7 〕這一現代人文思潮對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吸引力。這是超越民族、地區和時間的屬於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對於深受階級的與性別的雙重壓抑之苦的中國女人更具有吸引力、親和力和認同感。娜拉的“首先我是一個人,和你一樣的一個人”雖然是從一位歐洲白人婦女的嘴裡說出來的,也表達了中國女性求解放的心聲,因為在尚未取得人的獨立自由這一根本點上,全世界婦女的處境和嚮往追求是相同的。
以上對我國女性文學誕生的敘述和分析,可以確定女性文學這一概念內涵的歷史性和現代性。也就是說,它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現代人文價值內涵的女性的新文學。伊麗莎白·詹威所說的閱讀分析女性文學所需要的“不同度數的鏡片”,具體地說就是現代的具體的作為人的女人和作為女人的人。前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人”,後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有她與生俱來的自然性別的人”。這也就把忽視自然性別的“男女都一樣”和強調性別差異的“男女不一樣”在女性人文主義這一價值目標下統一起來,就是“五四”思想者所提出的“為人和為女的雙重自覺”。
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化大力氣建立起來的社會性別(gender)與自然性別(sex)這兩個概念,是根據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基本理論“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變為女人的”發展而來,對於解構父權制的性別統治性別歧視使女人認識到自己“他者”的和“次性”的位置具有一種革命的洞察力,但女人在意識到這一切的同時也就要求改變要求超越,朝著做一個完整的健全的女人這一目標改變自己超越自己,這種堅忍不拔愈挫愈奮的探尋是我國20世紀女性文學的思想動力。“社會性別”和“自然性別”這兩個概念以及我國女性文學研究所常用的“女性意識”、“性別意識”、“性別立場”都不足以完整地把握女性文學這一性質。因此,“作為人”與“作為女人”這兩個介詞結構短語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女人的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把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在現代人文理想的目標下統一起來。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總是習慣於從字面上把女性文學理解為一種按性別分類的性別文學,就像青年文學按年齡分類,西部文學按地域分類,女性文學不過是特別標出作家性別的一種性別方言罷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學就不僅失去了它起碼的理論意義,而且可能起到強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為女人者感覺到某種看不見也說不出的以寬容面目出現的性別歧視。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女作家拒絕認同女性文學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獨立意識強,對兩性不平等有深刻體驗的女作家越是拒絕把自己歸入女性文學名下。
女性文學既是性別文學又不是性別文學這一悖論,可以用現代語言學符號學理論來說明。概念符號與所指稱的對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語言相對於它所指稱的對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種暫時的、有待於發現的東西。沒有任何一個符號可以完善的窮盡它所指稱的對象的全部涵義。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學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著悖論的有待於發現、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國《女性獨立宣言》把“人”這個詞改為“@①”,中國女學生把講義上的“他”改為“@②”,美國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創造了一個herstory,便是女性在人的範疇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號學上的體現。
索緒爾認為語言中的意思只是一個差異問題,每一個符號的意思只是因為它不是其他符號的意思。如果我們要相對穩定地和準確地界定一個符號的意思,便應該把與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從該符號不是什麼入手。
前述關於性別文學的悖論,意思是女性文學雖然以“女性”這樣的性別概念為標誌但並非凡是女作家寫的就是女性文學。作家的自然性別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學的現代性這一特質在時間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婦女古典詩詞,包括以秋瑾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後表現了鮮明的婦女解放要求的作品,應歷史地看作是我國女性文學的萌芽或前驅。女性文學的現代性內涵應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及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討論這一概念時,一般認為應該是體現了女性意識的作品,伊麗莎白·詹威認為要看她對自己所寫的生活內容的體驗、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鑒於女性意識、性別意識這些概念含義的模糊性,我認為應在前面冠以“現代”二字加以限制。這就把那些雖為現當代女作家所寫卻體現了傳統的男性中心意識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學也不是一個題材概念。人類生活是由男女兩性共同參加和共同維繫的,儘管歷史對男/女、社會/家庭的角色位置進行了等級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領域都難以截然劃分為純然男性或純然女性的題材,任何女人的問題都和男人有關,反過來說也一樣。題材決定論的實質是題材等級論,即等級制的公眾/個人、集體/私人等二元對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領地而後者則似乎註定屬於女性。廬隱、蕭紅等均因此而受到過非議。2004年以前這種以題材等級論鄙薄女性文學的現象明顯升溫,出現了種種以“小”和“私”為中心詞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說”、“女性小品”等)。事實上題材本身無所謂價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於寫什麼而在於怎樣寫和寫得怎麼樣?女性寫作和男性寫作在這方面的區別不在題材而在女性,一般來說習慣於以內視角和個人記憶、個人生存體驗來處理各種生活範圍的題材。
我們下面討論中國女性文學,在現代性進程中事實上出現了哪些形態類別。女性文學和我國20世紀歷史息息相關,不可能擺脫種種歷史合力的牽制而只能在歷史給定的不盡相同的條件下做出不盡相同的選擇,從而呈現出現代性進程的豐富性。誠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言,“語言並非是一個規定明確、界限清楚,包含著表現者和被表現者對稱單位的結構。它現在看來更像是一個無限展開的蛛網,網上的成分不斷交換和循環,沒有一個成分受到絕對的限定,每一種東西都受到其他各種東西的牽制和影響。”〔10〕
在這個“無限展開的蛛網”上有的成分發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復現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現、發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發生了變異成為不是它原來的東西。“女性”、“婦女”、“女性主義”便是女性文學發展進程這張蛛網上三個重要的“網結”。在我國女性文學之現代性進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學、婦女文學、女性主義文學這三種形態。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學及女性文學批評的核心概念,它和“婦女”這個概念是同義的可以互換的嗎?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在我們這裡基本上是作為同義詞來使用的。女性與婦女這兩個概念的混淆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反映了女性文學批評對女性文學現代性的漠視與無視。
據美國后結構主義學者白露考證,我國直至清末還沒有“女性”這一概念。中國社會佔主導地位的話語不存在一個超越社會人倫關係的女性概念,凡指稱女人的詞語都是指在具體的家庭人倫關係中的女人,如次於兒子的女兒、次於丈夫的妻子、次於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據自己在親屬關係中規定的角色規範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會認可的角色規範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會認可的角色位置。“女性”這個詞與“他、她、tā@③”這些人稱代詞出現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白話文學的主題之一,是一個超越了親屬人倫範疇超越於傳統父權制意識形態對女人社會角色定位的一個革命性反叛性符號,〔11〕也是一個有待發展和完成的概念。從20、30年代的一些論文和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這一有別於恪守三綱五常的傳統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為了與舊式的傳統女人相區別,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個“新”字,“新女性”便成為“現代女性”的同義詞。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詞的負面含義如被動、柔弱、智力與生理上的低能等,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曖昧性不穩定性而在運用過程中被男性偏見所填加進去的意思。
白露還考察了“婦女”(Woman)這個概念內涵的變化。在傳統話語中,泛指女人時有女子、婦人、婦,也有婦女這個詞,都是指的傳統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婦女這個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被填加進去的意思。她指出早期共產黨人將歐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中的Woman譯作婦女,強調社會生產與婦女的關係,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的翻譯奠定了“婦女”一詞的政治意義,30年代農村根據地,蘇維埃政權以至毛澤東時代國家、婦聯等政治機構繼續沿用的“婦女”一詞也主要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12〕
“婦女能頂半邊天”便是從生產勞動和政治功能的意義上使用的。
可見“女性”“婦女”這兩個詞儘管都指稱了“女人”這一性別,但二者的內涵並不一樣也不在一個話語體系之中,前者以區別於舊式女人的主體性為本質內涵,而後者則是一個被國家權力話語政治化了的意識形態話語。在日本,婦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沒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現代社會中已經獲得了某種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義而言,我們今天在使用這兩個詞的時候也應有這樣的大體上的區別。
“女性”、“婦女”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恰恰與“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學的歷史嬗變形成同構的關係,也就是說,上述兩個概念的不同內涵恰恰對應了相應的兩種不同的女性文學類型的基本內涵。我國女性文學與女性這個詞同時出現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20年代後期與婦女概念內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時,出現了女性文學的分化,逐漸形成了恰與婦女概念的新內涵相對應的婦女文學,並在40年代出現了女性文學與婦女文學在不同的話語空間的並存現象。新中國成立后,解放區工農兵文學被規定為新中國文藝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學與“五四”人的文學同時被阻遏,婦女文學以順應時代潮流和主導意識形態的方式與工農兵文學一起得到了長足發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極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隨著“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復甦,女性與女性文學再次出現,成為當代文學中一支既有別於男性文學又有別於婦女文學的現代性的女性文學。而婦女文學則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學的發展中,大約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現了女性主義文學這一新類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學也在繼續發展。
就這三種女性文學類型的關係而言,婦女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都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話語環境下由女性文學衍生出來的兩個分支。應該承認即使是婦女文學,在其發生之初,也還是基於女人爭取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和價值的實現的現代性進程的產物,但二者的思想資源不同。婦女文學的思想資源來自社會主義的婦女觀,主張婦女應投身於社會革命、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洪流之中,在社會/階級/集團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著眼於社會底層婦女,主張知識女性要向工農兵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故其主人公多為各種社會/階級/集團鬥爭中的女英雄。至於這種“社會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婦女和在何種程度上解放婦女,那是另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婦女學理論問題,本文暫不展開論述。女性主義文學的思想資源顯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陸續譯介過來的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但就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來看,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亞·伍爾芙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階段》這些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女性人文主義思想,而對西方激進的和學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嬪主義”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上的性別對抗路線則採取了謹慎的既有所認同也有所保留的態度,王安憶、鐵凝的一些小說則對這些理論進行了嚴肅的藝術探索,從而使自己與西方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拉開了距離。〔14〕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女性主義文學從自在到自覺,對中國婦女尤其是中國知識女性、職業女性的精神成長和主體性建構進行了默默的和艱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張潔、張辛欣、殘雪、陸憶敏、薩瑪(崔衛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張燁、張真、葉夢、斯好,90年代鐵凝、蔣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陳染、林白。這裡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這兩個類別中同時進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現代文學中在女性文學與婦女文學這兩種文學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樣。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於她們的自覺選擇而後者則是無奈的在時代紛紜複雜的歷史潮流里跌著跟斗,而一些眾所周知的女性文學文本還受到過多次批判。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輕得多的蔣子丹、徐坤們不再是別無選擇而是在一定限度內贏得了自主選擇的權利。
有論者批評20世紀女性文學研究對女性文學和婦女文學這兩種文本存在著嚴重的偏斜和理論上的誤植,並認為這樣的批評拉大了這兩種文本的距離。〔15〕此言恐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偏離了這兩種文本的實際。由女性文學而出現了與主導意識形態同構的婦女文學,這本身就說明了二者的差異,加之政治作為一種強大的權力話語的控制和干預,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婦女文學走向了政治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女性這一概念的現代性內涵,導致了女性、婦女在生活中和文學中的雙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時也失落了自己作為精神上獨立自主的人的價值。新時期女性文學的新生,其內在的思想底蘊不能不是對政治化的婦女文學的反思。這不是哪一個女作家個人的問題,這兩種文本的差異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觀意志所能夠消泯的。論者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沖》,50年代菡子、茹志鵑、劉真等對戰爭題材的書寫歸之為“政治文本”,意思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直接講述”。蕭紅的《呼蘭河傳》,張潔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於是什麼樣的政治則語焉不詳,更不提即使是這些對當時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直接講述”的作品(且不論這樣的概括對於這些作品而言是不準確的),也有不少為當時的政治所不容,劉真的《英雄的樂章》、《春大姐》,茹志鵑的《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宗璞的《紅豆》等都受到過左傾政治的批判,至於楊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壓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變化,更是政治對婦女文學的強力扭曲和規範。在這裡,女作家和女性文學批評者的價值立場並不是無關緊要的:是從婦女作為人的價值立場出發還是從泛泛而論的曖昧不明的政治立場出發?論者將廬隱、冰心、凌叔華、蘇青、張愛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張潔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等歸之為“性別文本”即“渲染性別意識、批判父權話語的文學書寫”。這“性別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別”(sex)還是“社會性別”(gender)?而“性別意識”包不包括女人作為人的意識?而“渲染性別意識、批判父權意識”這樣的界定,即使僅指上述的女性主義文學,也基本上不符合這些作品的思想和價值取向。徐坤的《女媧》、《出走》、《廚房》,蔣子丹的《桑煙為誰升起》、《絕響》、《等待黃昏》、《貞操遊戲》、《從此以後》,鐵凝的《玫瑰門》、《對面》、《麥秸垛》、《棉花垛》、《孕婦和牛》,陳染的《破開》、《無處告別》、《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個人的戰爭》及近作《說吧,房間》、方方的《暗示》,薩瑪的《父親》、王小妮的《應該做一個製作者》、張燁的《鬼男》等女性主義文學名篇都是從人性和人的價值的高度探尋女人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們鮮明的作為人的性別意識無論是體現在對父權制男性中心意識的批判還是體現在對女人自身身體的認識對母性和愛的新的認同以及人性的審視,都立足於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長與解放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價值立場,這也正是女性文學能夠超越時代,超越性別,超越時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長久的歷史和美學價值的原因。
女性概念的質的規定性是女人作為人的主體性,而女性文學概念的質的規定性是女人作為創作主體言說主體在文學中對自己作為人的主體位置的探尋。這是20世紀文學史上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女性這一概念的現代性集中體現在女人基於人的覺醒而改變、超越封建的傳統文化對自己的這種強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現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為人的主體性要求。表現在女人由依附性到獨立性這一精神的艱難蛻變。
女性和女性文學的主體性問題,是女性文學批評中一個複雜的和棘手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不應迴避的問題。女性主體性的思想資源是女性人文主義,“女人也是人”便是她的思想起點。女性主體性探尋和建構的全部困難全部複雜性和難以言說都凝聚在這個類似同義反覆的判斷句裡面了。沒有誰能說清楚作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麼?覺醒的意識到了自己人之為人的女性可以說出我不是什麼(不是男人的奴隸、附庸、玩偶……)卻難以從正面說出自己究竟是什麼。
這或許就是解構主義的女性主義何以把女性文學批評的實踐限制在“完全否定的”“解構一切事物,拒絕建構任何事物”的範疇之內,就是克里斯多娃說女性主義“同已經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協,我們可以說‘這個不是’和‘那個也不是’”〔16〕的初衷。這種主張發揮了女性這一概念內涵的革命性、反叛性,當它面對父權統治和男性中心的非人道性和偏執性時,其思想的鋒芒是銳利的。然而遺憾的是它把這種革命性、反叛性推向了極端,推向了對女性的主體性要求和在女性文學中所已經體現出來的積極的探尋和建構的消解。它過分誇大了父權制以來男/女兩項壓迫/被壓迫的對立地位,誇大了話語中的男性偏見色彩、把女性改變自己的命運爭取人的權利和價值的天然合理的鬥爭引向了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成為沒有自己堅實的理論立足點的實踐。在思維方式上,也違背了後現代主義對“虛假的普遍主義”的反思,把女人和男人都看作是無差異的統一的“類”,以一概而論的思維方式看待無比豐富複雜的千差萬別的作為個人的女人和男人。“由於它否認存在著一個認識論上有意義和具體的主體,它使女性主義不可能具有自己的批評。”〔17〕
好在女性文學尤其是我國的女性文學並不是按照這種理論寫出來的。從“五四”女作家對人生的意義和“何處是歸程”的探尋開始直到80、90年代的女性詩歌、女性散文和女性小說,女性自我認識自我價值的探尋,如思想的活水流貫其中。這便是日漸清晰的“女性:人——女人——個人”。也就是說,我國女性對自己作為人的主體性探尋,大體上經歷了“人(和男人一樣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樣的)——個人(以獨立的提升了的具體的千差萬別的個人將做人與做女人統一起來)這樣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這也恰恰是我國女性文學的一條基本的貫穿性的內在理路。
非常耐人尋味的是,西方女性主義運動大體上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由強調男女平等到強調男女的不同和對立,直到90年代對學院派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全體女人”這一概念的解構,出現了“我獨特我完整我是我自己”的個人化趨向,出現了以個人的自由自主為底線的多種形態的做人與做女人的統一。不言而喻這裡每一個階段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與我國沒有自己的理論形態的女性文學又是不一樣的。
何以會這樣?按照後現代主義對主體性的理解,主體性這個概念正如和社會現象緊密相關的話語一樣,不可能是一個內在統一的整體,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穩定的封閉的概念。重要的是在什麼樣的主客觀因素下出現了什麼樣的主體性內涵
女性文學從古至今地一步步走來,一直不曾停下腳步。隨著“女性世紀”的到來,女性文學以其獨特魅力,鋪天蓋地的走到大眾面前,以一種勢不可當氣勢,傲然屹立在文學論壇之中。翻讀大大小小的報刊和雜誌,你不難發現當今的女作家群是那麼的壯觀。先鋒作家、美女作家的美名不斷的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一時之間,文壇晃動的凈是女性面孔,女性文學更是風光無限。
女性文學在走向女性本體和主體方面,在女性自我生命體驗和女性本體慾望表達等方面,表現得比過去更為內在、明顯和豁達;在藝術表現上,注重了把“我”推向前台,文章日益變得個體化,時常從兒女情、家務事等庸常生活支點切入社會。這本是女性文學的一大進步,但隨著社會變革速度的加快,一些女作家開始偏離傳統軌道,轉型為“小女人”或“私人化”、“隱私化”寫作,她們關注的世界只有身體和性,只有愛情和自我。在這些女作家眼裡,女性主義是女性寫作的惟一選擇,女性意識覆蓋了人生的全部。《上海寶貝》、《糖》等美女作家的作品給人一種脂粉的甜膩味和生活腐爛的氣息。而到了九丹的《烏鴉》,更是把床笫之歡寫得恣意汪洋。難怪有人謔稱她們是“身體派作家”。年輕作家這樣寫倒也罷了,可如今,一些傳統作家如張抗抗、池莉、鐵凝也步其後塵。鐵凝的《大浴女》、池莉的《水與火的纏綿》、張抗抗的《作女》,光書名就令人想入非非了。翻開張抗抗的新作《作女》,其目錄就不由人臉紅耳熱: “ ‘作’戰的人生有聲有色;男人和女人一塊‘作’才好;現在不‘作’更待何時;‘作’的慾望從哪裡來……“這究竟是閱讀提示,還是故意誘導讀者?讓人不明白的是:難道非得靠性描寫和帶有煽情的書名,才能取悅讀者的眼球嗎?這種自我作踐“女性文學”的行為,怎能贏得讀者的尊重呢?
“女性擅寫性靈文字。一情一景一細一節,都能化出萬千情思滿腹感慨。”這是女作家素素評價台灣散文家張曉風時說的一句話。在人心浮躁、文壇充滿功利主義的時下,不知道到哪裡去閱讀這麼美妙的文字了。性文學的泛濫不僅辱沒了女性作家的名聲,更敗壞了讀者的胃口———這是出版商的錯,還是女性作家自身行為所致?
文學評論家白燁指出:當今女性作家在相當多的作品中以一種從心靈到肉體都採取叛逆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叛逆精神,也是女性解放自己的一個必然過程。張抗抗也在《作女》的後記中稱“是為‘她世紀’留存的一部‘作女’檔案”。問題是,如果用過激的言語、身體和性來表述這種叛逆精神,恐怕並非上策。道理明擺著,女性文學不是性文學。如果女性文學類同於地攤作品的話,那真的離退幕不遠了。
女性文學不是性文學!在為女性作家喝彩的同時,更應該斷喝一聲,以免女性文學淪落到性文學的尷尬境地。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女性文學將會以其獨特魅力,展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