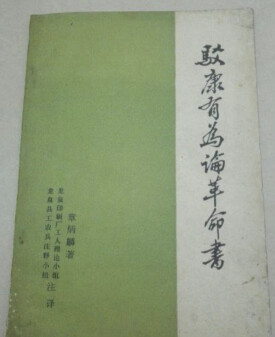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清末章太炎著。
曾參予百日維新後來成為改良派領袖的康有為在海外發表了《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止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闡述了他反對革命排滿、主張立憲保皇的立場。康有為寫這封信,是因為南北美洲華僑中的保皇會會員曾對康談到他們嚮往革命。他們認為,保皇會一向忠心保皇,但清王朝卻緝捕保皇會員,對其或殺或監,既然這樣,不如“以鐵血行之,仿效華盛頓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國民。”於是康有為寫了這封複信加以反對。他在複信中說,要把慈禧、榮祿之流與光緒皇帝區別開來,慈禧等人雖然昏暴,欺國虐民,但光緒卻是個聖明皇帝。他並且說,后黨秉政的局勢不久就會改變。康有為在這封信中以庸俗進化論為依據,博引旁征、洋洋萬言地論述了他的保皇理論。
他強烈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作法,並羅列了中國不能進行革命的四個理由:一曰革命殘酷,二曰國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國干涉,四曰皇帝聖仁。他又攻擊革命派的反滿口號是無的放矢,“大怪不可解”,因為他覺得滿漢早已平等。因此他作出結論說:立憲容易,革命困難,立憲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憲,而不可革命。由於康有為在海內外名氣很大,他的這些保皇言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他的門生信徒又把這些言論編印成冊,廣為散發。這封信在思想輿論戰線上嚴重混淆了人們的視聽,阻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為了駁斥康有為的謬論,澄清人們的思想,同時宣傳革命主張,章太炎在光緒二十九年上半年寫了一封致康有為的公開信,即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這封公開信寫好之後,章太炎曾請人帶到香港轉交康有為,結果未能帶到。六月,《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與鄒容的《革命軍》“同時刊行,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當時上海倡議革命的進步報紙《蘇報》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的評介文章,為之聲揚。
《蘇報》原是一家很平庸的小報,創辦於光緒二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該報的所有權被湖南舉人陳范購買后,面貌略有起色。但陳範本是一名變法改良派,他利用報紙來宣傳變法,雖然刊登了一些政論性文章,但社會影響並不大。直到南洋公學大風潮發生,《蘇報》開闢“學界風潮”欄目,及時反映學潮,以此為契機,《蘇報》才柳暗花明,逐漸成為愛國學社的喉舌,並組織起了一支以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章士釗等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為核心的作者和編輯隊伍。於是報紙顯得銳氣英發,為全國學界所注目,儼然成為號召學潮的旗手。從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903年)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后,《蘇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在國內眾多的報刊中獨樹一職,首先吹響了革命排滿的號角。這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蘇報》排滿革命的議論,如同潮水般宣洩而出,其中反響最為強烈的,莫過於關於鄒容所著《革命軍》的評價和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摘錄。
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蘇報》即刊出書介一則,向讀者推薦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說:“康有為最近《政見書》力主立憲,議論荒謬。餘杭章炳麟移書駁之,持矛刺盾,義正詞嚴。凡我漢種,允置家置一編,以作警鐘棒喝。”六月二十九日,《蘇報》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標題,摘錄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文中點名直斥當朝光緒皇帝為“載湉小丑,不辨菽麥。”這八個字石破天驚,中外震動。清政府氣急敗壞,惱羞成怒,欲把章太炎、鄒容等人置之死地而後快。五月二十五日兩江總督魏光燾即向清廷報告:“有《蘇報》刊布謬說,而鄒容所作《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為之序,尤肆無忌憚”,經外交部呈慈禧太后閱覽,命魏光燾立即嚴密查辦,逮捕人犯。
自文網苛密的乾隆朝以後,文字獄案寥若晨星。道光、咸豐、同治各朝均無文字獄記載,《蘇報》案可說是有清一代文字獄的最後一幕。在案發之前,慈禧太后還夢想著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獄案的處理方法,計劃著迅速撲殺革命火種,“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檻京師”,而後凌遲處死,殺一儆百。但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清廷的意料。由於西方各國領事館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煩。
由於《蘇報》報館設在英租界內,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須事先徵得外國領事的同意。因此當逮捕《蘇報》館主、主筆及章太炎、鄒容的諭旨下達江蘇督撫之時,他們不得不與上海的外國領事團交涉,請求籤發拘票捕人,但各國領事為了維護租界治權,堅持不允。後來經過雙方談判,此案定為“租界之案”,清政府無權將有關案犯解出租界獨立審判,只能由設在租界的“會審公廨”來審理此案。清政府委託洋人律師指控《蘇報》“污衊今上,挑詆政府”,指控章太炎、鄒容“大逆不道,謀為不軌。”
十月十五日,該案移至“額外公堂”,由上海縣會同會審委員、英陪審官審訊。這期間清政府一面聘請洋律師作為訴訟一方與章、鄒等人打官司,一面又與外國領事團暗中交涉“移送人犯”,但未能成功。“額外公堂”開審后,上海縣企圖不顧英國防審官的反對,獨立作出判決,將章、鄒二人俱科以永遠監禁之罪。一時之間社會輿論嘩然。上海的外國領事團亦不承認該判決,並且照會上海縣,要求再審一次,否則將該二犯釋放。清廷不敢違拗洋人旨意,只好委曲求全地下令上海縣按照洋人意思從寬辦結。這樣在經過清政府與外國領事團長達半年的“討價還價”之後,“額外公堂”於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作出最後判決: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二年,罰作苦工,從上年到案三日起算,限滿釋放,驅逐出境。這樣,沸沸揚揚、枝節橫生的《蘇報》案才告終結。
在這起清末最大的文字獄中,清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威風掃地,終未能實現自己企圖將章、鄒迅速斬決的如意算盤,而革命黨的聲勢和影響在這次審判后卻越來越大。可見血腥的文字獄伴同專制的清朝一起在走向它們的末日,民主的曙光已經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
《蘇報案》判決之後,章太炎和鄒容被正式監禁,身陷囹圄。但二人仍然胸懷鬥志,心憂天下。但鄒容終因不堪獄中折磨,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二月病逝獄中。鄒容死後,租界迫於輿論壓力,章太炎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五月,章太炎三年監禁期滿,出獄當晚即乘坐一艘日本郵船,東渡日本。五年之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一篇膾炙人口、傳頌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這篇氣勢磅礴、筆鋒犀利的長文中,章太炎站在鮮明的民主主義立場上,逐條駁斥了康有為的改良謬說。章太炎首先列舉了滿清王朝壓迫漢族的歷史,指出從清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屢興不廢的文字獄,直到清末戊戌政變,殘殺維新黨人,這一系列壓迫漢人的罪行都表明滿為主,漢為奴,並不存在什麼康有為所說的“滿漢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駁斥了康有為稱頌光緒“聖仁英武”的觀點。他說,“載湉小丑,不辨菽麥”,因為害怕慈禧太后廢置自己,才鋌而走險,贊助變法。即使光緒在西太后死後,做起名副其實的皇帝,到那時他也必定是個殘殺維新黨人的獨裁暴君。
此外,章太炎還痛斥了光緒皇帝享有“天命”的無稽之談,他嚴正指出:“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才之難易”。同時,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又正面回答了革命必須流血的問題。他批駁了康有為等保皇黨人所謂的立憲可以避免流血,通過“清”來實現的天真夢想,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立憲”更要流血。最後,章太炎針對康有為信中所謂中國國情特殊,“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能革命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他義正辭嚴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清末一篇歌頌反滿革命的奇文。章太炎在這篇文章中,旁徵博引、觀點鮮明地進行論述,因而整篇文章顯得條理縝密,內容豐富。同時,這篇文章又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裡行間注入了自己充沛的感情。總之,《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以前革命思想發展的理論總結,同時它又吹響了鼓舞革命志士繼續前進的號角,對以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論影響作用。
長素足下: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謂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萬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為是耶?
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為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群獸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賤儒元惡為之則已矣;尊稱聖人,自謂教主,而猶為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盅惑者,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為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
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異同,惟計情偽得失以立說。
雖然,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為上系淳維,出自禹后。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通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華夏,永滯不毛,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耶?智果自別為輔氏,管氏變族為陰家,名號不同,譜牒自異。況於戕虐祖國,職為寇讎,而猶傅以兄弟急難之義,示以周親肺腑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為甚!
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借言天然,則褅袷海藻,享祧猿蜼,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為是聒聒者耶?
長素又曰:“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駱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不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著土傅籍,同為編氓,未嘗自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別;歐、美近制,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為主人,而使彼妥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為歸化漢人乎?其為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髮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已而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人為漢種,乃適使漢人為滿種也。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為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餚滿、漢以同薰蕕於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大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
長素二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始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荊、揚二域,《禹貢》既列於九州,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閡,淪為要荒。而文化語言,無大殊絕,《世本》譜系,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
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為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強迫以成之耶?將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國,被發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為此也,強迫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師摧陷洪氏,復從髡薙。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顛,形狀噩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為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為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素亦何以駁之乎?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而反譏有齒者為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耶?
種種繆戾,由其高官厚祿之性,素已養成,由是引犬羊為同種,奉豭尾為鴻寶。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為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並其所謂復九世之讎,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之事,與白起坑趙,項羽阬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阬之者,出於白、項二人之指靡,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慾盡漢種而屠戮之,其非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圖籍,操政柄者,豈猶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為輿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剚刃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為瘖聾,甘與同壤,受其豢養,供其驅使,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為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也!
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以為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為政?若夫政治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製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決,納丁於地,永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蕞爾彈丸,未參內政。且福康安一破台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爵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曾氏在日,猶必諂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夫大君無為,而百度自治,為首領者,亦以眾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為奴隸,而彼為主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閹宦仆豎,而賜爵儀同者,彼固仰承風旨雲爾,曷能獨行其意哉!
一條鞭法,名為永不加賦,而耗羨平余,猶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無惡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既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悅之。
玄燁、弘曆,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己居堯、舜、湯、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黃廷桂書》則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賦芋,朝三暮四,眾狙皆怒,朝四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況於廷杖雖除,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赭貫木,以挫辱之。
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為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為漢臣,安得不雲爾乎?”
夫長素所以不認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為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為罪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則吾向者為《正仇滿論》既駁之矣。
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丑,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間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於盤盂,勒於鐘鼎,其述則公,而其心則只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長素所謂拿破崙第三新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
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御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
籍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群相讙譊,朋疑眾難,雜沓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勝是也!
共、歡四子,於堯皆葭荸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為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為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為實事,以此誑耀天下,獨不讀劉知幾《載文》之篇乎?謂魏、晉以後,詔敕皆責成群下,藻飾既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
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為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滿、漢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於一皇,為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尚在,而滿洲大長得以兼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既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並不認為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為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
誠如是,則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於種類,而於情偽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為吾漢族籌之可乎?長素以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旍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后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者。長素亦知其無可倖免,於是遷就其說以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蓺,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闊普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長素雖與載湉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挃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載湉亟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為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諑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廢於瀛台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讒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毒、不韋而踣覆之,今載湉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猶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軛,尚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後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太史公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庸有幾乎!
事既無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驗已眾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弒,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為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台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之載湉,何幸有長素以代為王莽也。必若圖錄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緯書尚繁,《中庸》一篇,固為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或篤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湉為滿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則建夷之運,終於光緒,奴兒哈赤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
要之,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賴者為多。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其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雖然,載湉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最絀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崙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崙之微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崙者?而長素徒以阿坤鴉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絕特之彥,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破崙者乎?
長素以為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為反唇相稽,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饑濟困為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以賑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為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為其所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己為主體,而西人為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經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為尤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長素以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為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嘗通情於大將軍,欲為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則從之為多數,而不從為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
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直人心奮厲時難。
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睹精色,哀哀漢種,系此剎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夭閼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為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略得數道,為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為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為乎!
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為英人蠶食,此長素所引為成鑒者。然使莫卧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蠶食耶?當莫卧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為蒙古所有,與為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為蒙古時代,後者為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並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無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綿延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蓺,遠過中國,歷舉書籍見聞以為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見於印度,而不見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為無常,不可執著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勢無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慨然於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為波斯屬州,今觀內典,徒舉比鄰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己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欲自強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蓺,而惟視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賢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於腥羶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蓍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漢人,判渙無群,人自為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抑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為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為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為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蓺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為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為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為,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並擁護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強,為難能可貴矣。次即束身自好,優遊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蓺、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耍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廩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傾覆,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剚刃以死者,不可勝計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為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為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城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為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搢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為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為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為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鋤,良種不滋,敗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以上錄舊著《正仇滿論》。)
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偽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識不逮耶?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為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尚在,未盡澌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瞑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疇昔之易,於是宣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耄,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複,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抑吾有為長素憂者,向日革命之議,嘩傳於人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文、林奎尚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尚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尚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為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直二缶鐘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為之辨也。
若長素能躍然只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壘耆碩之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為素王玄聖。后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於星霧,長素之書,尊藏於石室;長素之述,葆覆於金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抑亦可以尉薦矣。借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槁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為天下笑者,何如哉!
書此,敬問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海上文學百家文庫——章太炎 劉師培卷》,172——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