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契約的結果 展開
契約
概念
契約,最初是指雙方或多方共同協議訂立的有關買賣、抵押、租賃等關係的文書,可以理解為“守信用”。形式有精神契約和文字合同契約,對象多樣,可以是:生意夥伴、摯友、愛人、國家、世界、全人類,以及對自己的契約等,可以用“文字合同”來約定,可以用“語言”來約定,還可以是“無言”的契約。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契約是指“依照法律訂立的正式的證明。出賣。抵押。租賃等關係的文書”。1932年美國律師學會在《合同法重述》中所下的定義是:契約是“一個諾言或一系列諾言,法律對違反這種諾言給予救濟,或者在某種情況下,認為履行這種諾言乃是一種義務”。
從法理上看,契約是指個人可以通過自由訂立協定而為自己創設權利。義務和社會地位的一種社會協議形式。契約的觀念早在古羅馬時期就已經產生,羅馬法最早概括和反映了契約自由的原則。
例如:房屋買賣合同,以書面文字的形式來約束雙方,應盡的議務和責任。契約等同於合同。
1. 契約關係的雙方是平等的,對整個business的順利進行負有共同責任,沒有哪一方可以只享有權利而不承擔義務。
2. 契約關係經常是相互的,權利和義務之間往往是互相捆綁在一起的;
3. 執行契約的義務在我,而核查契約的權力在人;
4. 我的義務保障的是你的利益,而你的義務保障的是我的利益
5. 契約根據性質不同可以分為:
家庭契約,是基於血緣關係之間的一種治家格言,家訓,家禮等,通常也稱精神契約。
財產契約,是基於增加財富為目的達成的財產約定,比如:存單、股票、房產等。
射幸契約,是為了達到財產順利傳承而訂立的以生命為標的的合約,比如:生命信託,人壽保險等。
1. 雙方或多方共同協議訂立的有關買賣、抵押、租賃等關係的文書、條款。
《魏書·鹿悆傳》:“契約既固,未旬,綜 果降。”唐白居易《與執恭詔》:“欲求契約,固合允從。”
2. 特指由雙方依法訂立有關買賣、抵押、借貸、租賃、委託、承攬等事項的文書。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九:“武寧 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於馬商陳貴,契約具在。”茅盾《右第二章》四:“舊職工應得的退職金,公司因為困難而犧牲,不能按照原定契約付給了。”
所謂“契約原件”是指實用的契約原物。保存至今的契約原件以西漢中期的為最早。從那時至民國的兩千年間,這類契約原件雖不是時時有,處處有,但每個大的朝代或長的歷史階段,還是有一些的。不過元代以前的很少,明清和民國的較多。這些契約原件是中國古代契約資料的最寶貴的部分。今按照時先後,結合出土地點,依次簡要介紹如下:
現存的漢代契約原件是在居延發現的,是居延漢簡中的一部分。因之我之為“居延漢代契約”。
居延在今內蒙古自治區西部額濟納旗,西漢時屬於張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轄區,東漢曾置張掖居延屬國。這裡在兩漢時,一直是重要駐軍區,近60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這裡採集或發掘到漢簡約有3萬餘支。已公之於世的,是1930年由西北科學考察團掘得的一批,約有一萬餘支。勞干先生將這批漢簡進行分類、考釋,編成《居延漢簡考釋》一書,於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再版。1962年,又在台灣出修訂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彙輯這批漢簡的圖片,一律按原簡號順序,製成圖版,並全部釋文,編成《居延漢簡甲乙編》,於198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批漢簡有年號的,“起自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迄於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簡中有十餘件契約。有年號的只有三件。最早的一件為《西漢本始元年(前73年)居延陳長子賣官絝券》,最晚的一件為《西漢建昭二年(前37年)居延歐賣裘券》。其他無年號的,有賣衣物、布匹契約,有賣田地契約,還有一些廩給憑證。這批契約的數量雖不多,但卻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批契約原件,距今已有兩千多年了。有了這批契約,我們才得知漢代契約的原貌,才有可能利用這秕契約對照文獻資料,進行有關的研究。

新疆魏唐契約
吐魯番地區在漢代為車師前部地。這裡的高昌城為漢、魏,晉幾個朝代的戊己校尉駐地。公元327年,涼州統治者張氏在此置高昌郡,治高昌城。其後西涼,北涼因之。公元460 年,柔然滅沮渠氏的北涼殘餘政權,立闞伯周為“高昌王”。此後,張、馬、麴諸氏相繼在此稱王,史稱“高呂國”,都以高昌為都城。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滅高弓國,以其地為
西州,高昌城又為西州都督府駐地;9世紀中葉以後,這裡又是“西州回鶻” (即“高昌回鶻”)的王城。由此看來,在千餘年間,高呂城一直是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文化遺存很多。近數10年來,這裡屢有古文書出土。1959—1975年間,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高昌古城遺址附近的阿斯塔那與哈拉和卓兩村附近清理晉——唐墓葬近400座,發現了大批古文書,這就是為中外學者矚目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現由唐長孺教授主持整理,已出版至第八冊。其中有近200件契約,種類豐富,有賣葡萄園、田地、房舍,奴婢、牲畜契約,有租田地、菜園、果樹、葡萄園契約(包括習書),有借錢物契約,有雇傭契約,還有遺囑文書等。少數尚完整,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殘損,有的只剩幾個宇。
龜茲在今庫車縣東。漢代為龜茲國,屬西域都護。唐為安西都護府和龜茲都督府駐地。於闐在今和田縣南,漢代為於闐國,亦屬西域都護。唐為於闐鎮和毗沙都督府駐地。在這兩個地區發現的古文書中,也有一些契約,時間約在唐天寶至貞元(約744—790年)之間,多為借貸契約,亦有雇傭契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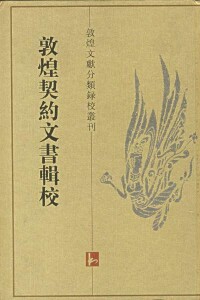
敦煌契約文書輯校
石室藏書中有一部分為契約,我稱之為敦煌契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於1960年編成《敦煌資料》第一輯,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就有這部分契約,共120餘件,分為買賣、典租、雇傭、借貸和其他契約、文書五個部分。買賣契約有田地、宅舍,車牛,奴婢等契約。在這批契約中,有書年號的.有用干支紀年的。敦煌地區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曾為吐蕃所佔,至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又歸於唐朝。敦煌契約中用干支紀年的部分,大約是吐蕃佔領時期的遺物。最早的一件有年號的契約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僧光鏡賒買車釧契》最晚的一件為《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韓願定賣妮子契》.敦煌契約中還有部分契約式樣,即所謂“書儀”,是為人們書寫契約提供格式的.其中有“分家文書”、“放良文書”、“放妻文書”、“遺囑”等式樣。
徽州治今安徽歙縣。隋唐時,已為一方重鎮,名歙州。北宋改稱徽州,元代升為徽州路,社會經濟較發展,經商者很多。至明清時,出現了不少商人地主。解放初期,這一地區有許多舊契約流向社會,最多的一批有一萬餘件,其中南宋和元代的也相當多。由於當時的人對此種文物不甚重視,沒有及時收購,致使此批契約長期在社會上輾轉流傳,可能後來流入北京,分藏於北京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圖書館等處,徽州契約中的宋元契約大約尚有100件左右。現在屈指可數的約60來件。其他均為明清和民國契約。南宋和元代契約原件在他處尚無發現,所以徽州的宋元契約就成為契約中的珍品。徽州最早的一件契約為《南宋嘉定八年 (1215年)徽州吳拱賣山地契》,最晚的一件為《元至t-十七年 (1367年)徽州吳鳳郎賣山地契》o其中還有兩件契約很值得玩味,一為《宋龍鳳五年(1 359年)徽州謝志高賣山地契》,一為宋龍鳳十年(1364年)徽州謝公亮退地契》。“宋”是元末農民起義軍紅巾軍首領韓林兒的國號,“龍鳳”是他的年號。起義軍首領之一朱元璋奉韓林兒為主,用“龍鳳”年號。他的部將胡大海於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三年,1357年)攻佔徽州部分地區,因之出現了用“龍鳳”年號的契約。此外,還有一些“稅給”,是由稅務部、門給予納契稅戶的收據.明清時期,名曰“契尾”,都要粘連在契約之後.徽州稅給也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契尾原件。
明清和民國契約原件在中國各地都有一些。現在大多數省級以上的圖書館、博物館、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及有文科的高等院校圖書館等,或多或少都有收藏。收有千件以上契約的單位不在少數,有數十件,數百件的很多。近10年來,各縣檔案館(局)、博物館、文物管理所等,對殘存於民間的契約原件也注意收集。所收契約,明代中期以前的很少,清代前中期的也不多,道光以後至民國時期的最多.這些契約有用白紙寫的,有蓋官印的紅契,也有無官印的白契。還有部分官印契約,有的粘連契尾。

河北唐縣
宋元時期,今寧夏、甘肅、新疆等地的西夏人,畏兀兒人和吐蕃人留下了一些契約。有用漢文寫的,亦有用民族文字寫的。有用中原王朝的年號紀年的:有用民族政權的年號紀年的,如西夏人用“天慶”年號;吐蕃人則用生屬紀年.有買賣田園,房屋、牲畜契約,也有典當契約。中國前輩學者如黃文弼。馮家異諸先生,生前做了不少這一方面的工作。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國立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於2001年3月出版了由唐立、楊有賡、武內房司主編的《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彙編(1736-1950)第一卷史料編》一書。全書用銅版紙印製,精裝,大16開305頁,裝幀十分精美。書中將契約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並列印刷,每件之首撰有簡約說明文字,便於讀者對比理解。這可以說是一部非常珍貴的中國苗族舊時契約文獻的彙編。
書中所收苗契,主要是貴州省錦屏縣文斗寨和平鰲寨苗族先人們所留下的林業契約。中國貴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楊有賡先生,年輕時即進行民族學研究的田野調查工作,1960年代,他在貴州苗寨收集了200多份清代苗族的林契,進入80年代以後,楊先生先後有研究苗族契約的論文問世,引起日本學者的注意,日本學習院大學的武內房司先生,連續三次赴錦屏考察,他們一起在苗寨又收集到苗族同胞珍藏了幾代人的600多份林契。這兩次的收集成果,組成了現在這本彙編。這些契約絕大多數是楊先生為出此書從當地苗族群眾中借出來的,由於得到日方資助,所以該書在日本出版。
這些苗契使用漢字寫成,最早的一件訂立於乾隆元年(1736年),最晚的一件訂於民國39年(1950年)。所有契約按性質分為如下幾類,每類都按年代順序排列:A、山林賣契283件;B、含租佃關係的山林賣契277件;C、山林租佃契約或合同87件;D、田契55件;E、分山、分林、分銀合同90件;F、雜契(包括荒山、菜園、池塘、屋坪、墓地之賣契及鄉規民約、調解合同等)45件;G、民國賣契20件。
經過認真收集和精心整理的這些契約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文獻學意義。
中國是有著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文明古國,隨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私人土地的買賣、典當、租佃、招佃以及銀錢借貸等,形成了大量的契約文獻,這些文獻既真實直接地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同時本身也作為制約人們交易行為的特殊手段直接參與到經濟生活中去,併發揮作用。這些東西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史學家們的重視,上個世紀90年代,各地契約文書的整理出版即成風氣,徽州文書以其數量和規模最為有名。1993年以後相繼有《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等史料問世。這些資料都成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文獻,但這些契約主要都是反映漢族的情況。近年台灣學界也注意到契約文書研究的重要性,興起編輯出版之風。為了研究漢族和當地土著民族的關係,他們已將大量平埔族的古文書整理刊印出來,比如台灣中央研究院1993年出版的《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上下冊)等。而我們大陸學者利用少數民族契約文書研究當地社會歷史的發展還十分不夠,苗契一書的出版,填補了這方面史料的空白和遺缺,為中國契約文化的研究充實了重要內容。
中國現存的大量契約文書,一般都產生在歷史上文化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而且多為較先進的漢民族所簽訂。少數民族由於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大多生活在偏僻山區,那裡幾乎與外界隔離,文化落後,經濟發展遲緩,他們留下的契約文書十分罕見。過去很多學者在研究中,注意和強調了漢族移民在開發西南地區中發揮的作用,而很少有人能站在當地少數民族的立場來說明他們在相對封閉環境中的生存狀況及與外界的聯繫,他們社會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以及他們在這種變化中扮演的角色。除去一些觀念認識上的問題外,文字資料的缺乏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批苗契對於研究西南土著民族的社會,有著重要的價值。這批契約文書雖然是使用漢文簽訂的,卻都是在苗族內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實反映苗族群眾的經濟活動和各種行為方式,為研究人員提供了說明問題的依據。
可以對清朝及民國年間貴州錦屏地區苗族的經濟生活有新的認識
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基本是以農立國,重農輕商,土地是人們追求的主要財富,所留契約大都是反映土地買賣、租佃關係的,而有關山林的契約卻極少。這一是由於生長於崇山峻岭之中的林木,由於交通等關係,很難成為商品流通;再者人們如需用木材,都以砍伐自然林為主,很少有人工營造樹林,大家並不簽約,即有簽約,林子砍完,成了荒山禿嶺,契約也就沒用了。林木生長周期長達數十年,不像農田一年一收,這種周期的差異,當然要影響到人們的經營和生活方式。林木生長時間這麼長,使人們很難以種植林木為生,中國歷史上開荒砍伐山林之情況極為普遍,而較難見到規模性的人工造林,更難見林業上的租佃關係。貴州清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苗族同胞,靠山吃山,他們一方面要以自然的山林為生,一方面又為了維持、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經營栽培著林木,並由此形成一系列的買賣租佃關係,自然而然的防止著破壞性的開採,形成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這種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比只是單純的政府行為要更有生命力。這些契約對研究清代以至民國期間苗族人民的特殊經濟生活,對研究中國林業發展史都有重要意義,正好為我們從民族的、經濟的、林業的多個方面提供了一批寶貴的原始資料。
契約文獻可以算少數民族古籍的一種。中國一些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一些使用漢字,無論何種文字簽訂的契約,都反映了當時當地特定民族的政治、經濟、歷史狀況,有著重要的文獻學意義。現在這些東西已越來越少,一方面由於歷史變遷,自然損毀,另外解放后,歷經土改、文革,這些契約大都作為封建遺物被付之一炬,所存日見稀少。就筆者所知,還有其他一些民族有零星分散的契約檔案存在,如維吾爾族、藏族等,都應儘快整理出版,作為重要資料保存,以利研究工作的開展。
在銅器銘文和摩崖、碑刻中:有不少契約資料,有的很珍貴。此外,還有一些“買地券”。這三種資料的總量雖不算多,但由於直接來源或脫胎於契約原件,所以其史料價值很高.有些還可補現存契約原件的不足。
在青銅器中,只有西周的青銅器上有契約資料,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沒有這種資料。
西周時期實行土地國有制,土地不許買賣。《詩·小雅·北 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禮記·王制》曰;“田裡不鬻。”這些記載都證明了上述情 況是事實.土地既為國家所有,不許買賣,就是尚未變為商品,因之也就沒有土地買賣契約。其他動產多已成為商品,重要商品在買賣時,已使用契約,而且有專任官吏“質人”負責管理、監督此事.當時的買賣契約叫做“質劑”。《周禮·地官·質人》曰:“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奴婢)、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邦玄註:“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這種買賣契約亦叫做“小約劑”。因廣泛用於民間,所以稱為“萬民約”。
西周中後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田裡不鬻”的原則雖未變化.但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在貴族之間已發生了土地的抵押、典當,贈送,賠償等關係,並出現了相應的契約,與上述民用質劑相應,叫做“大約劑”。因只行用於貴族封君之間,所涉及的是封國、采邑疆土之事,所以稱為“邦國約”。這種契約也是先寫在竹簡木牘上.再折券為二,雙方各執其一。然後再鑄於鼎彝上,《周禮·秋官·司約》曰:“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鄭玄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唐人賈公彥曰:“使人畏敬,不敢違之。”載有這種資料的銘文不是照錄契約原文,主要是記載此事的經過。中間或詳或略地述及立約之事,如周恭王三年(前916年)的衛盉,五年的五祀衛 鼎,九年的九年衛鼎,恭王時的格伯◆,孝王二年(前883年)的口鼎,厲王二十五年(前833年)的◆從盨,厲王時的矢人盤等。都是如此.對契約內容記述較詳的,有立契時間、締約雙方名字、標的、契價和交割、見證人等內容,與“萬民約”基本相同。在日後土地國有制破壞,土地私有制產生髮展,土地買賣關係發展的情況下,此“邦國約”之名不復存在,使用於土地轉讓關係之中的契約也是“萬民約”。青銅器上的契約資料的發現,為研究先秦契約和土地制度等提供了寶貴資料。
摩崖碑記中的契約資料以漢代的為最早,也以這時的為最珍貴.因為此時的契約原件保存下來的實在太少,文獻中的有關記載也不多,能有摩崖碑記為之補充,確是難得之事。
摩崖以西漢地節二年(前68年)的《揚◆買山刻石》為最早,稍晚的是東漢建初元年(76年)《大吉買山地記》。這是兩則記事刻石,也像是簡化了的契約錄文。
碑記中最寶貴的是1973年發現於河南偃師縣緱氏公社鄭瑤大隊南村的漢碑《東漢建初二年(77年)侍廷里父老◆約束石券》,這是里民為輪流擔任里父老時得使用集體所購田地而立的合同。參與合同的里民二十五人都在券上署,唐碑中最寶貴的是《唐大中五年(851)勅內庄宅使牒》,刻在玄秘塔碑碑陰(今在西安碑林),文字基本完好。唐朝實行均田制,規定田地不許買賣。《唐律疏議》卷12《戶婚上·諸賣口分田》曰:“《禮》云:‘田裡不鬻’。受之於公,不得私自鬻賣。”《唐律》又規定,如有特殊情況需要賣時,要“投狀申牒”,即由業主赴官報告,由官府發給一準許出賣此產業的文牒,才可出賣。《通典·食貨·田制》下: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令:“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這種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關田地買賣的文牒原件已經無存,其本來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們得知當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還具體載錄業主、擬賣產業的坐落、四至、價錢等等,契約的大部分內容已經具備。金代《金大安元年(1209年)真清觀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 “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八寸八分”,兩截書寫.上截是牒文,下截載“本觀置買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懷州馬愈賣地契》,兩件的文字都基本完好,真是雙璧生輝。明清時期照錄契約原文的碑記很多,亦有重要史料價值,反映城市經濟生活的尤為可貴。
買地券又叫做“墓箉”,“地券”,是漢代出現的。絕大部分為鉛制,形如漢簡,少數為玉、磚制,字是刻畫上的.魏晉以後,紙契廣泛使用,買地券的質料、形式也有變化,短而廣的磚券、瓦券、石券、木券漸多。買地券的使用,反映了土地私有制在發展。買地券上所寫購買的土地都是死者所用之墓地,有大有小。買地券是墓主對墓地擁有所有權的法律文書。買地券的形制,文字都比較簡單,易於造偽,自古以來贗品很多。現存傳世的幾件西漢時期的買地券都是贗品。估計西漢時期大約尚無買地券。東漢時期的買地契,今能見到的約有20來件,半數以上疑為贗品。在買地券辨偽方面,方詩銘等先生做了有益的工作.東漢時期的買地券剛剛產生,其文字與人間實用的契約基本相同,史料價值很高。魏晉以後的買地券逐漸迷信化,史料價值也降低了。
中國的古文獻浩若煙海,其中與契約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內容極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約問題,必須充分利用文獻資料。這裡想談如下四個問題.
上述現存的契約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約資料,都未接觸到原始社會的契約問題.因為這些資料所反映的都是後代的契約.在原始社會末期,由於交換關係產生並發展,萌芽狀態的契約也已產生。中原地區當時的人類使用什麼樣的契約,目前還無具體資料可供論證。考古工作中雖發現了一些畫在陶器上的符號,但表示何種意向,無從考查.再從文獻記載來看,許慎《說文解字·后敘》曰:“古者庖犧氏……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此八卦、結繩是否已用於契約關係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說過: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社會發展很不平衡.近千年來,許多少數民族經歷或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這些民族使用契約的情況在漢族文獻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曰:兩廣“瑤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元代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說:雲南“土人(傣族)締約,取一木杖,或方或圓,中分為二,各刻畫二三符記於上,每方各執一片.負債人償還債務后,則將債權人手中所執之半片收回。”清代袁枚《子不語》曰:海南島“黎民買賣田土,無文契票約;但用竹籤一片,售價若干,用刀划數目於簽上對劈為二,買者賣者各執其半以為信.日久轉賣,則取原主之半簽合而驗之。”上述三個民族當時都處在原始社會末期,所用契約雖有一些差別,但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都無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籤木片為信物.這種契約形式叫做判書。《周禮·秋官·朝土》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來,判書可能是原始社會末期比較普遍採用的契約形式。漢族祖先在原始社會末期可能也是用這種契約。西周至兩漢時期的契約之所以也為判書制度,淵源於此。
西周至兩漢時期,已用文字書寫契約。這時契約的形式雖仍為判書制度,但比原始社會的判書有很大的進步。此時契約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為三種:即《周禮·天官·小宰》所說:“聽稱責以傅別”, “聽賣買以質劑”, “聽取予以書契”。這就是說,借貸契約用傅別,買賣契約用質劑,授予收受契約用書契。關於傅別的形式,鄭玄曰:“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劉熙曰:“別,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關於質劑的形式,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關於書契的形式,鄭玄曰:“書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劉熙曰:“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清代孫治讓對這三種判書做過這樣的比較說明:“蓋質劑,傅別、書契,同為券書.特質劑,手書一札,前後文同,而中別之,使各執其半札.傅別則為手書大字,中字而別其札,使各執其半字。書契則書兩札,使各執其一札。傅別札、字半別;質劑,則唯札半別,而字全具,不半別;書契,則書兩札,札亦不半別也。”這三種形式的判書在今存漢簡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晉以後,紙契的使用日廣,判書也起了變化。傅別,質劑之制逐漸不用,合同形式在產生髮展.合同形式脫胎於書契,又吸收傅別之長,發展而來.其形式是“書兩札”,將兩札並起。合寫一個大“同”字,後來合併大寫“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兩半字,為合券的驗證。這是最早的◆縫製度。後來,在買賣關係中廣泛使用單契,由賣主—方出具。
官府為了保障人們合法的權利,消除財產等糾紛,維持社會秩序,很重視契約的內容書寫和形式製作。《周禮·地官·司市》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明公書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憑契照。”凡人論訴田業,只憑契照。”這些記載都說明了契約的財產證明作用。官府為了使契約更好地起到這種作用,曾設法使契約規範化,因之契約的內容和形式時有改進。但使契約形式發生重大變化的,不是契約內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歷代稅契政策的作用。如“紅契”的出現就是如此。
有的學者認為,紅契“就是皇權所訂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國有制”的證明,這是一種誤解。其實,紅契之所以“紅”是由於蓋了硃色官印。蓋此官印與土地所有權沒有關係,更不是土地國有制的證明。如上所述,而是稅契的作用。《隋書·食貨志》曰:“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這是中國古代稅契制度的開始。“文券”就是在締約雙方繳納契稅時,官府加蓋官印的契約,後代叫做紅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儀曰:“紅契,買到者則其無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南宋李心傳曰:買賣田宅,“人多憚費,隱不告官:謂之白契。”可見契約的這一大變化是由稅契制產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約上加蓋官印,主要是為了保證契稅的徵收。
契約大約在宋元時期,又發生過第二次大的變化,就是契尾的產生。所以這樣,是由於紅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員侵吞契稅,因之另創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納契稅的收據,元代叫做“稅給”,一契尾分大尾與坐尾兩聯,大尾為收據,坐尾為存根,以備查究.此法實行后,對防止官吏貪污契稅起了一定的作用。從此後,官府規定,凡投稅者,“止鈐契紙,不連用契尾者”。違法。是紅契之後又多了一張契尾,一份合法的契約必須一契一尾。
在先秦的文獻中不見有契約錄文。兩漢的文獻有敘事摘引契約文字的情況,但比較簡單。如西漢初年,陸賈與五個兒子相約曰:“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月而更。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西漢後期,沛郡有一豪富在病危時為遺令曰“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男,年五十以付之。”還有西漢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寫的一篇遊戲文字《僮約》。這些資料雖不是契約的錄文,但都接近於當時的契約原件,很有參考價值。文獻中載有完整的契約錄文是宋朝以後的事。要有兩種情況:一為契約式樣,一為契約原文。
契約式樣大約開始流傳於唐代後期。上述敦煌契約中有契約式樣多種就是證明。北宋太平興國八年,國家制定典賣契約式樣,作為“標準契約”,由地方官府刊印,叫做“官板契紙’或“印紙”。民間締約時,要向官府購買印紙,填寫后,再投稅印契。此種印紙制產生,對契約的規範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文獻中載錄契約式樣之事大增。代的《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明代的《尺牘雙魚》(熊寅幾撰)和《萬寶全書》(清人毛煥文增補本)等,都載有各種契約,為民間書寫契約提供了方便,也為我們研究當時的契約形式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
文獻載錄契約原文,主要見於“家譜”之記述族產、墓地部分中。但今天所見的家譜以清代修的為最多,明代的很少,元以前的已不易見到。因之其中所載契約也較晚.福建晉江縣陳埭丁氏的家譜修於清道光時,中錄元代契約資料八件,這確是一批難得的資料。八件資料分為三組,第一組為至元二年 (1336年)買花園房地用的“問帳”、“公據”、“官契”和“稅給”,共四張。二組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賣花園山地用的“問帳”、 “公據”和“官契”,共三張,缺稅給。三組只有一張,為至正二十七年賣荔枝園及山地的“官契”。大多數家譜中所載契約都很晚,屬於明後期的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