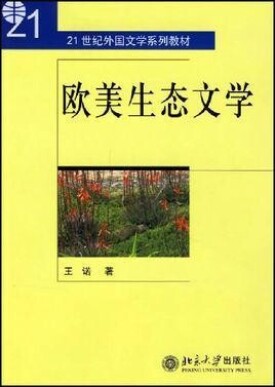生態文學
生態文學
我國生態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王諾先生給生態文學下的定義是:“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係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簡明的定義是:生態文學是一種反映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的文學。
在我國,生態文學沒有明確分類,單有些較模糊的界定。比如水文學,森林文學等等都屬於生態文學。
“生態文學”的關鍵是“生態”。這個限定詞的主要含義並不僅僅是指描寫生態或描寫自然,不是這麼簡單;而是指這類文學是“生態的”——具備生態思想和生態視角的。在對數千年生態思想和數十年生態文學進行全面考察之後,可以得出這樣一種判斷:生態思想的核心是生態系統觀、整體觀和聯繫觀,生態思想以生態系統的平衡、穩定和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和終極標準,而不是以人類或任何一個物種、任何一個局部的利益為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據此我們可以得出生態文學最基本的特質——
生態文學是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文學,而不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以人類的利益為價值判斷之終極尺度的文學。生態文學以生態整體主義或生態整體觀作為指導考察自然與人的關係,它對人類所有與自然有關的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判斷標準是:是否有利於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即生態系統和諧、穩定和持續地自然存在。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並不意味著生態文學蔑視人類或者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災難的惡果和生態危機的現實使生態文學家認識到,只有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根本前提和最高價值,人類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態危機,而凡是有利於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的,最終也一定有利於人類的長遠利益或根本利益。
傳統的描寫自然的文學大都把人以外的自然物僅僅當作工具、途徑、手段、符號、對應物等等,來抒發、表現、比喻、對應、暗示、象徵人的內心世界和人格特徵。“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里的花和鳥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可以用作工具表達詩人的情感。這種寫法是人類中心主義在文學里的一種典型表現。生態文學家非常反對人類純功利地、純工具化地對待自然。生態文學的核心特徵決定了它必須將所有以工具化的態度和工具化的方法對待自然的文學排除在外。這一核心特徵使我們能夠在生態文學作品與非生態的描寫自然的作品之間劃出了一條清晰的界限。
“環境文學”一術語的最大問題在於隱藏在它下面的思想。它的邏輯起點不是生態整體主義、而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觀。著名的生態文學研究者格羅特費爾蒂教授說得好,“‘環境’是一個人類中心的和二元論的術語。它意味著我們人類在中心,周圍由所有非人的物質環繞,那就是環境。與之相對,‘生態’則意味著相互依存的共同體、整體化的系統和系統內各部分之間的密切聯繫。”因此,如果將生態整體主義而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作為生態文學的思想基礎,就不應當使用“環境文學”這個透露出人的自大和驕妄的術語。同理,也應當以“生態保護”取代“環境保護”。生態思想要求人類對一系列舊有概念、話語進行調整。
生態文學是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的關係的文學。生態責任是生態文學的突出特點。生態文學對自然與人的關係的考察和表現主要包括:自然對人的影響(物質的和精神的兩個方面)、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整體以及自然萬物與人類的關係,人對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奪和摧殘,人對自然的保護和對生態平衡的恢復與重建,人對自然的讚美和審美,人類重返和重建與自然的和諧等。在表現自然與人的關係時,生態文學特別重視人對自然的責任與義務,急切地呼籲保護自然萬物和維護生態平衡,熱情地讚美為生態整體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犧牲。生態文學把人類對自然的責任作為文本的主要倫理取向。
生態文學是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的文學。文明批判是許多生態文學作品的突出特點。生態文學表現的是自然與人的關係,而落點卻在人類的思想、文化、經濟、科技、生活方式、社會發展模式上。生態文學家要探索的核心問題是:人類的文明和發展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犯了什麼大錯,才導致如此之嚴重、危及整個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態危機?人類到底應當怎樣對待自然?人類究竟應當做些什麼、改變些什麼,才能有效地緩解直至最終消除生態危機,才能保證生態的持續存在和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的持續生存?生態文學研究者喬納森·萊文說得好:“我們的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獨一無二的方式。不研究這些,我們便無法深刻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只能表達一些膚淺的憂慮。……因此,我們必須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決定著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生存於自然環境里的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並將這種分析與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
探尋和揭示造成生態災難的社會根源,使得生態文學具有了顯著的文明批判的特點。許多作家對人類中心主義、二元論、征服和統治自然觀、慾望動力觀、發展至上論、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思想觀念,對破壞生態平衡的自然改造、竭澤而漁地榨取自然資源的經濟發展、違反自然規律和干擾自然進程的科技創造、嚴重污染自然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研製和使用等許許多多的思想、文化、社會現象提出了嚴厲的批判。正因為這一特徵,在判斷具體作品是否屬於生態文學時,可以不把直接描寫自然作為必要條件。一部完全沒有直接描寫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堪稱生態文學作品。
許多生態文學作品表達了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想,預測了人類的未來。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是許多生態文學作品的突出特點。生態文學家或嚮往神話時代初民們的生存狀態,或羨慕印第安人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或身體力行地隱居於自然山水之中。回歸自然是生態文學永恆的主題和夢想。生態文學家清楚地知道,人類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可能返回與中世紀甚至原始時代同樣的生存狀態中,但他們還是要執著地寫出他們的理想,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激發人們不懈地探索在當今的發展階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與自然和諧相處。生態文學家還創作出大量預測和想象未來生態災難和人類毀滅的反烏托邦作品。這些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向人類發出警告:人類正在向他的大限步步逼近,如果繼續現今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生態系統的末日就為期不遠了。
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思想和生態視角為特點的文學,在藝術上它與其他種類文學一樣,並無特別之處。它僅僅是文學的一部分,也並不奢望取代以人為本的文學。但是,日趨嚴峻的生態危機使它具有越來越重大的價值。生態文學研究專家、哈佛大學教授布伊爾說得好,生態文學是“為處於危險的世界寫作”的。生態文學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裡的必然反映,是作家對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運的深深憂慮在創作中的必然表現。文學家強烈的自然責任感和社會使命感,推動著生態文學興起、發展並走向繁榮。
1949年初,徐遲翻譯的《瓦爾登湖》出版,梭羅的生態思想植入中國文壇的土壤。這是關乎中國生態文學影響源的重要事件。上世紀70年代,世界生態文學里程碑一般的傑作《寂靜的春天》中譯本問世,震撼了並一直震撼著一些中國作家的心。80年代,羅馬俱樂部的思想被譯介引入,為剛剛興起的我國生態文學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資源。21世紀初,歐美生態文學、生態哲學的成就被系統介紹進來,為我國生態文學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參照。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生態文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感悟自然、展現危機和反思根源幾個方面。但中國生態文學遠未成熟,甚至,在生態問題日益引起各界的重視下,文學對生態還顯得較為冷漠。
感悟自然與生態整體觀的缺失
中國感悟自然類作家多具有濃郁的詩人氣質,對大自然十分敏感,用心地聆聽和觀察自然萬物。幾年前英年早逝的葦岸是這類作家的代表。在《大地上的事情》里,螞蟻、麻雀、胡蜂、蜘蛛、啄木鳥、甲蟲,江河湖海,白樺、栗樹、麥子,還有季節輪換、氣候變化、日出日落,是真正的主角;作者自己則只是“觀察者”,主角的每一點細微變化都吸引著他的眼,牽動著他的心。感悟者既“感”且“悟”,在用心靈與自然溝通交流的過程中,他對自然與人的關係產生了頓悟:“人類與地球的關係,很像人與他的生命的關係。”“那個一把火燒掉蜂巢的人,你為什麼要搗毀一個無辜的家庭?”難道就為了顯示“你是男人”?在《動物園》里,周曉楓悟出:人類的審美是畸形的甚至是殘酷的;人類沒有理由自高自大,因為“我們猜測不出鳥的確切身份,也難以了解它見識廣博的心胸;無論多麼渴望,我們不能和它們一同比翼——鳥提醒著人類的不自由,正如伊甸園的蛇提醒著先祖的無知。”這些作家的自然描寫優美而細膩,風格與浪漫主義的自然書寫十分相近。同樣類似於浪漫主義作品的還有對田園生活的懷念,以懷舊和感傷質疑工業化、城市化甚至整個現代文明。在充分評價這些作品之成就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其中對自然的讚美性描繪、對田園生活不再的懷舊性感傷,主要根源於作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他們不是為了自然而讚美自然,他們並非真正為自然界的傷痛而哭泣。他們的立足點仍然是人。因此,他們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思想思索和生態文學描寫。生態文學與傳統的描寫自然的文學有本質的不同。僅僅描繪自然和感悟自然,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生態文學。如果仍然以人為中心、以“我”(作家)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僅僅當作工具、途徑、手段、符號、對應物,來抒發、表現、比喻、對應、暗示、象徵人的內心世界和人格特徵,進行文學領域裡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對象化,那就更加談不上生態文學了。生態文學是具備生態意識的文學,它的創作者能夠從生態整體觀和聯繫觀出發,懷著強烈的生態責任感為生態整體立言,並全面深入地探討和表現自然與人的關係:自然對人的影響(物質的和精神的兩個方面),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萬物與人類的相互依存關係,人對自然的適度利用與超越生態承載力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奪和摧殘之區分,人對自然的保護和對生態平衡的恢復與重建,人類重返和重建與自然的和諧等。
展現危機與文化批判的不足
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和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發生、發展和繁榮的巨大動力。面對嚴峻的生態現實,不少作家憤然舉筆,真實記錄觸目驚心的生態慘狀,為中華民族生存環境的岌岌可危而憂患,大聲疾呼保護環境。鄭義的《中國之毀滅》、馬軍的《中國水危機》、劉貴賢的《中國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機》、沙青的《北京水危機》和《北京失去平衡》、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鷹的《生命之水》和徐剛的《拯救大地》《穿越風沙線——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長江傳》《我將飄逝》等多部作品可視為代表。這些作家把不為眾人所知的事實寫出來,告訴我們正面臨著怎樣可怕的生態危機,其勇氣和責任心絕對令人敬佩。然而對千瘡百孔的自然、對生態平衡的恢復與重建來說,僅僅有憂患、呼籲和真相披露,還遠遠不夠。生態文學研究者喬納森·萊文說得好:“我們的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獨一無二的方式。不研究這些,我們便無法深刻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只能表達一些膚淺的憂慮。”探討導致生態災難的社會原因,分析所有決定著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生存於自然環境里的行為的思想文化因素,歷史地揭示文化如何影響地球生態,進而在文化重審的過程中進行文化重構和文化變革,應當成為生態文學的主要目的。探尋和揭示造成生態災難的社會根源,使得生態文學具有了顯著的文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特點。事實上,一部作品如果在這個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即使沒有描寫任何具體的自然景物,也堪稱生態文學的優秀之作。
反思根源是未來發展的主要任務
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進行生態哲學角度的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是中國生態文學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未來發展的主要任務。1999年10月在海南召開的有許多作家參加的南山會議,是我國作家進行生態危機社會根源反思的標誌性事件。在那次會議上,作家們對唯科技主義、唯發展主義等思想根源提出了質疑與批判。在《生命·生態·生活》《保護動物,我們能做什麼?》和《荒野之鼬與荒野之憂》等作品里,郭耕的生態意識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質疑被奉若神明的傳統的發展觀、進步觀,批判人類中心主義;他以生態整體主義眼光看待世界,指出人和其他生物一樣是食物鏈的一環,對於生態系統來說,任何一環都是重要的。詹克明的《世上本無害蟲》從生態整體論出發,指出一切生物相互依存,本無有害無害的區別;恰恰是人出於短淺的功利主義對它們進行選擇、區分,有用則培養,無用則蔑視、遺棄,最終將給生態系統帶來災難。“人類把許多昆蟲稱之為‘害蟲’,倘由所有動物‘全民公決’,也許它們會一致決定,地球階段的‘害蟲’就是人類自己!”韓少功雖然不是生態文學家,但他的《遙遠的自然》卻是真正具有生態意識的佳作。作品揭示出文明人並非真正熱愛自然、理解自然,並非真想投奔自然,他們不過是想在大自然中尋找“個異”、“尋找永恆”、“尋找殘酷”,甚至“尋找共和的理想”。從《拯救大地》下卷和《我將飄逝》(2004)的後半部分,可以看出徐剛的自然觀有了根本轉變。他基本拋棄了自然為人所用的觀念,轉而主張“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美能使人愉悅的這一屬性的層面,否則人的自私的本性就會把自然美當作可以佔有的奢侈,可以獲利的商品。人要不失時機地把倫理擴展到大地之上的萬物,人的最可貴的道德應是對人之外的萬類萬物的憐愛及呵護。”他開始反思文明對人的異化:“科學是有效的卻不是無限的……”我們熱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作家投身到生態文學創作中來。客觀地說,中國的生態文學還沒有形成熱潮,甚至連流派都還算不上。相當多的作家每天都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但在創作上表現的卻是對生態的無動於衷。這與當代歐美作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僅以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前蘇聯作家為例。前蘇聯作家強烈的自然責任感和生態使命感不僅表現在他們的作品里,還突出表現在他們的行動上。拉斯普京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家,但在80年代卻放下手中的筆,因為他再也不能容忍造紙廠對貝加爾湖的污染。他四處奔走呼號,一次次上書前蘇共中央,直至找到當時的一個領導人,慷慨陳詞,堅決要求關閉造紙廠,保護有著“西伯利亞之海”美譽的貝加爾湖。還是在80年代,前蘇聯發生了一場有關“北水南調工程”的大討論,“主調派”大多為水利專家,而“反調派”竟然有許多是作家。在1985年12月召開的第六次作協大會上,作家們對這一工程討論得極其熱烈,幾乎把文學會議開成了生態討論會。作家們的普遍、強烈、持久的反對終於獲得了成功——1986年8月20日,前蘇共中央和前蘇聯部長會議做出聯合決議:為防止可能發生的對生態環境的災難性影響,決定取消“北水南調工程”。一個國家的作家懷著保護生態的強烈使命感,普遍參與一項重大的環保行動,這是歐美文學史上罕見的文學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連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短缺匱乏的時代,發生在人們的許多最基本的生活欲求得不到充分滿足的國度,尤其令人感動,也尤其引人深思。眼前的民族問題和個人生活問題並沒有使這些蘇聯作家喪失全球性思維和全人類立場,他們是真正的世界級作家,他們真正做到了走向世界、融入自然。作家首先是一個人、一個公民,不能喪失人類良知和社會使命感;同理,作家首先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的兒女,不能喪失生態良知和自然使命感。在愈演愈烈的生態災難危及整個自然、整個人類之存在的時期,文學家怎麼能夠不直面如此嚴重並還在不斷惡化的生態現實?怎麼能夠不反思人類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從哪裡開始走錯了路?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全人類的危機;緩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類的合作與共同努力。因此,中國的生態文學家還需進一步拓寬視野,努力以感人、獨特的藝術形式探討具有普適性的生態思想問題,進行思想文化批判,如人類中心主義批判、二元論批判、征服和統治自然觀批判、慾望動力論批判、唯發展主義批判、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批判、科技決定論和科學樂觀主義批判等,並在批判的基礎上弘揚新的生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如生態整體主義、萬物平等觀、生態倫理思想、生態正義思想、新的生態的發展觀、簡單生活觀或生態生活觀、生態責任觀等。生態文學的前途無量,因為推動它走向繁榮和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動力——生態危機不僅沒有減弱,而且還在增強。事實上,儘管中國的生態文學還沒有走向繁榮,但已經受到世界的關注。例如,美國著名生態文學研究者帕特里克·P·墨菲教授主編的《自然的文學:國際性的資料彙編》(1998),就介紹了中國作家對世界生態文學的貢獻。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斷言:只要這個星球的生態危機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和消除,只要人類仍然面臨生態災難的威脅和滅絕性危險,生態文學就一定會繁榮並持續繁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