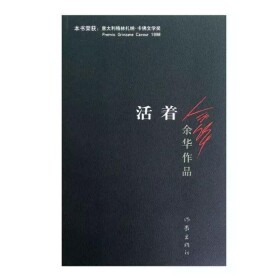先鋒派小說
源於80年代中期的新潮小說
先鋒小說重視“文體的自覺”(即小說的虛構性)和小說敘述方法的意義和變化,帶有很強的實驗性,因此,又稱“實驗小說”。
“先鋒小說”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先鋒小說”是指具有先鋒精神的小說創作,即“先鋒文學”中的小說創作。所謂“先鋒精神”,意味著以前衛的姿態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與之相關的藝術的可能性,以不避極端的態度對文學的舊有狀態形成強烈的衝擊。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先鋒精神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詩歌與小說領域裡的探索,即“白洋淀詩派”的詩歌和趙振開(北島)的小說《波動》等。在這之後,具有先鋒精神的創作還有以北島、舒婷為代表朦朧詩,以王蒙為代表的意識流小說和以宗璞、劉索拉為代表的荒誕小說,以及以高行健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戲劇等。
狹義的“先鋒小說”則專指在80年代中期出現的以形式探索為主要特徵的小說創作潮流。其主要作家有最初的馬原、莫言、殘雪、蘇童、洪峰,和稍後出現的格非、孫甘露、余華、葉兆言、扎西達娃、北村、呂新,也可以包括再晚一些出現的更年輕的邱華棟、朱文、韓東、東西、刁斗、何頓等被稱作“晚生代”的作家。但“晚生代”與“先鋒小說”的關係,有些類似於“新生代”與“朦朧詩”的關係,其反叛的先鋒精神又促使他們的許多創作特徵偏離於“先鋒小說”,是否應歸於“先鋒小說”還有待於對具體創作發展情況的觀察。
“先鋒小說”的興起大致可能性分為兩個階段。
以馬原、莫言、殘雪的創作為代表,並同時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生存探索三個層面上進行。馬原是敘事革命的代表,著名的“元敘事”手法和“馬原的敘事圈套”是其標誌。莫言是語言實驗的先鋒,以個人化的感覺方式有意地對現代漢語進行了“扭曲”,“我爺爺”、“我奶奶”成了打有莫言印記的專利產品;殘雪則是率先在生存探索方面有所突破的前驅,“人間地獄”般的生活場景和內心世界是她個性化的獨特創造。
以格非、孫甘露、余華的創作為代表,他們也是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生存探索三個層面上同時展開,並都有新的突破,甚至把這種藝術探索的力度推到了極致。格非在馬原的基礎上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敘事迷宮”,孫甘露則在莫言的基礎上把小說語言變成了“夢與詩”的結晶體,余華則在殘雪的基礎上大開殺戒,充分展示了人性中原有的暴力和血腥。
“先鋒小說”,特指狹義的“先鋒小說”。
80年代現代派文學的產生、發展及影響:
隨著1978年對西方現代派文學較大規模的介紹、評價和研究,理論界掀起了一場關於現代派文學的論爭。進而,討論進入到中國是否需要現代派文學的階段,一批作家如王蒙、劉心武、李陀、馮驥才等人,從自身的創作實踐中提出了對傳統文學觀念的質疑與引進現代派文學技巧和手法的倡導。隨著高行健《現代派小說技巧初探》一書的出版,以及馮驥才、王蒙等人關於中國需要現代派的通信,構成了這場討論的高潮。而圍繞“朦朧詩”“三個崛起”的討論,則把討論引向對新時期文學中現代主義傾向的評價階段。之後,理論界的介入和創作的探索同步進行,構成了新時期文壇上的繁榮景觀。
新時期現代派文學的產生有其必然性。
首先,“十年動亂”所導致的普遍精神危機,人們在撫摸傷痕、反思痛苦的同時作出了“我不相信”的結論。正是在主體確立的尋找與情感抒發需求的過程中,他們所表現出的迷惘與對世界的不信任感,對非理性世界的否定態度,在思想上表現出了現代主義傾向。同時,由於精神危機而導致的信仰喪失、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態度,使人們面對變化萬端的大千世界而無所適從、不知所措,再加上現代文明快速演進過程中價值體系轉換的不完善、不徹底,又使自我的確立成為難以實現的虛妄舉動,因而自我往往處於“邊緣人”、“零餘者”的角色位置上,在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上表現出現代主義特點。
其二,新時期的文化背景為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空間。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給中國社會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文學作品自然莊嚴地接受了從現代主義視角來表現生活的使命,所以“社會要‘現代化’,文學何妨出現‘現代派’”口號的提出,也成為時代某種需要的回聲。另一方面,“創作自由”口號的提出,在思想界、理論界和文藝界創造和建構了平等、自由和寬鬆的思考、創作環境。對更加豐富、複雜地了解生活、在心理要求直至審美傾向不斷向認識的深處、廣度挺進的需要變化,都使敏感的作家們在創作的同時,感覺到了僅用傳統現實主義一副筆墨的局限與束縛,便自然而然地把思維重心移向了創新與突破。
其三,改革與開放的社會文化環境,打開了封閉多樣的國門,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奇葩一下子展現在中國人的面前,西方文化思想和藝術作品在哲學思想和藝術創作上,給中國人打開了另一扇窗戶。這既成為中國當代作家藉以觀照自己所處環境與反思中國社會以及表現矛盾心靈的參照體系,也成為直接用以表現自己內心世界與生命過程的重要藝術模本。既在心理上產生與現代主義所表現的某些主題的認同;也通過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來表現立體的、多層面、超時空、快節奏的心靈世界,以彌補或反叛傳統現實主義,並保持與世界文學同步,因而在形式上表現出了現代主義的反傳統追求。
現代派文學在80年代的發生、發展,大致可分為二個時期。
第一階段大致在1979年前後,它以“朦朧詩”的崛起、王蒙、宗璞等人的小說以及高行健等人的話劇作品的出現為標誌。這一階段的主要創作特徵表現為反抗既有的意識形態規範,在主題上與傷痕、反思文學同步,表現出啟蒙主義理性和憂患的社會責任感。同時,他們對傳統文藝觀念、文藝模式進行反撥,創作手法上主要以吸收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技法為主,通過移植、模仿來開拓新的文學創作途徑與新美學範疇。這是新時期現代派文學的萌動期與初創期。
第二個階段是在1985年前後,這時出現的新生代部分詩人、“現代主義詩歌群體大展”、劉索拉、殘雪甚至部分尋根小說,以及《魔方》、《野人》等戲劇作品,都表明8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文學進入到了形成和繁榮期。無論在創作姿態或手法技巧上都表現出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個性化風格。
現代派文學在以後便不斷發展而成為80年代先鋒派文學的重要內容。新時期現代派文學的崛起,開拓了中國先鋒派小說走向新生的廣闊道路。
當然,就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先鋒精神而言,它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詩歌與小說領域的探索,但是直到80年代中葉文學中激進的實驗才形成了強大的陣容和聲勢。
所謂先鋒精神,至少表現在兩個層面上,即表現為思想上的異質性,對既成的權力敘事和主題話語的某種叛逆;表現為藝術上的前衛性,對已有文體規範和表達模式的破壞性和變異性。
作為朦朧詩前身的白洋淀詩派,不但標誌著中國當代啟蒙主義文學思想的誕生,同時也可以視為是整個先鋒文學思潮的真正發端。在這之後的朦朧詩、意識流小說、尋根文學都顯現了先鋒文學的發展。這個發展過程,明顯地呈現出從啟蒙主義到現代主義的發展。
具體的說,在先鋒小說真正引起文壇關注前,大致有這樣一些鋪墊為它的出現做了文學的準備: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文學有了第一次較為自覺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始作俑者就是朦朧詩的崛起;但對先鋒小說直接產生影響的哈王蒙、宗璞等人的意識流小說。很大程度上給了先鋒小說作家以藝術上的自信和借鑒的勇氣。
如果說王蒙等人的小說所呈現的新的美學因素還沒有在中國文學中造成革命性的影響的話,那麼,文化尋根小說在文壇上的崛起則實實在在在中國文學一個根本性的觸動。於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學參照下進行民族文化和歷史反思的文學尋根運動誕生了,它結束了文學單一的寫實時代,揚棄了小說創作上所謂主題性、情節性、典型性的規範,在小說的敘事方式和語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貴的突破。它不僅為先鋒小說掃清了部分藝術障礙,先期完成了一部分藝術實驗,同時也以文本的生澀培養了一部分讀者的閱讀心理,使他們不至於在以後面對先鋒小說的晦澀時而顯得驚慌失措。
這是比尋根小說稍晚露面的新小說,以劉索拉、徐星、王朔等為代表。他們表現出對現實生活和生活觀念的背叛,沒有尋根作家的文化批判的神聖感和莊嚴感,也沒有尋根作家文化建構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相反,他們有的是對神聖、信仰、崇高的褻瀆熱情,是衝決既有生活的準則和規範,以遊戲的態度對待人生,他們是一幫生活的玩主,粉碎了曾經建立的完整的生活形象。實際上他們在尋根小說的文化批判之後又完成了對生存觀念的批判。
在此基礎上,先鋒小說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浪潮。
先鋒小說,則是中國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產生的文學現象,它的創作者主要是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群具有較高學歷和文學修養的年輕作家,他們受到西方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等眾多不同作家的作品的影響,不滿於中國文學長期以來的固定模式和陳舊技巧,試圖通過小說形式的探索和實驗來革命中國小說的面貌,從而實現他們走向世界的文學抱負。
80年代中期,文學對文體的重視和強調,是從文學主題、題材、主流話語表達的內容範疇限定中逐漸解脫出來的。先鋒小說家們的出現,使小說寫作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形式美學狀態,文學話語大大突破了傳統文學語言的敘述和描寫功能,並創造了新的情感表現和隱喻象徵功能,給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觀念以衝擊。
當代小說真正地具有現代品格——那種真正與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觀念進行徹底決裂的小說,是被成為先鋒派作家的馬原、洪峰、格非等人的創作。在“文化尋根”和“現代派”小說的基點上,先鋒派小說獲取了自身發展的支柱,在這個框架下獲得了自己的主體性、自主性,從而使中國當代小說最終從政治、社會學、歷史學以及文化學的種種制約中獨立出來。以馬原為代表的先鋒小說家所進行的形式革命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他們向傳統的審美經驗和文學觀念進行了強有力的挑戰,意味著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歷史性轉折的最後完成。
先鋒派小說的第一個高潮
1985年前後,馬原、莫言、殘雪等人的崛起,是先鋒小說歷史上的大事,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看成是先鋒小說的真正開端。
這一開端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生存狀態三個層面上同時進行。
先鋒派小說常常被人稱為“形式主義”小說、“結構主義小說”,這說明他們的小說對表現技巧和形式的注重和追求。他們所強調的不是“寫什麼”,而是“怎麼寫”,盡一切可能去顛覆人們已經習慣和熟悉的閱讀經驗和欣賞觀念,儘可能破壞傳統的藝術秩序,從而使讀者和作品之間呈現出疏離化、陌生化,造成了人們普遍“看不懂”的現象。而在“看不懂”的表象背後,現代主義文學恰恰是在揭示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它刻意創造的形式外觀是在對讀者宣布或傳遞某種世界觀,當讀者在這些作品面前感到艱澀、冰冷和無從理解時,恰恰表達了對現實的態度——拒絕和超越。也就是說,他們用自己的藝術變形使人們對自己所熟悉的世界感到陌生,對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感到茫然失措。
而先鋒派對傳統的反叛,表面上似乎是指向技巧、形式、規範、秩序的層面,但它最終的結果和真實的目標卻歸於哲學、情感和歷史。形式和技巧只是一個中介,被用來充當一道感覺的藩籬,把人與現實疏離開來,造成人們對人生、世界的陌生化。所以文體上的晦澀、隔膜、冷漠、實際上也就是對生活、對周圍人的類似的感覺
馬原是敘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並因之被某些批評家稱為“形式主義者”。在他的創作的頂峰期,他寫了許多被當時讓人耳目一新的小說,如《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虛構》、《塗滿古怪圖案的牆壁》等作品。這些小說中,元敘事手法的使用,在打破小說的“似真幻覺”之後,又進一步混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作者及其朋友的名字直接出現在小說中,並讓多部小說互相指涉,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效果;設置許多有頭無尾的故事並對之進行片段連綴式的情節結構方式似乎暗示了經驗的片段性與現實的不可知性,產生了似真似幻的敘述效果……馬原的這些敘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馬原的敘事圈套”(吳亮《馬原的敘述圈套》,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3期),並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們所熟悉的現實主義手法所造成真實幻覺,成為以後的作家的模仿對象和小說實驗的起點。
與馬原相比,莫言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小說《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系列等小說形成了個人化的神話世界與語象世界,他的貢獻就在於使先鋒小說帶有了奇異的感覺,他擅長把兒童性感覺鑲嵌在小說中,尤其在敘述進入驚心動魄的時刻,這種感覺越為引人注目。他的感覺方式的獨特性,對現代漢語進行了引人注目的扭曲與違反,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個人文體。這種文體富於主觀性和感覺性,在一定意義上是把詩語引入小說的一種嘗試。這在他的《築路》、《白狗鞦韆架》、《球狀閃電》等小說中表現尤為明顯。
殘雪引人關注的是她的的心理小說,同樣是以感覺取勝,殘雪的感覺則充滿了對女性的歇斯底里的尖刻,她的小說具有一種夢幻般的結構,敘事混亂而毫無邏輯可言。無論是人物、故事,還是場景、對話,都變化無常、閃爍不定。殘雪小說文本構成的方式實際上就是一個個噩夢的自然主義的呈現。她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說則以一種醜惡意向的堆積凸現外在世界對人的壓迫,以及人自身的醜陋與無望,把一種個人化的感覺上升到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寓言的層次。
莫言和殘雪是在尋找表達自己的感覺方式的時候顯示出其在形式方面的先鋒性的,這一點與馬原不同,但他們確實基本涵概了以後的先鋒小說的基本方面的萌芽。
先鋒派小說的第二個高潮
1987—1990年,是先鋒小說創作的第二個高潮。主要代表作家有格非、孫甘露、蘇童、余華、洪峰、北村等人。他們是比馬原更年輕的一批作家,又被稱為“馬原后”作家、“后新潮”作家。
第二代作家仍然具有各自的藝術個性,但或許更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在小說的觀念上,他們在馬原的“新潮”前輩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小說作為敘事文本的本體性,進一步否定了功利主義文學的傳統。他們憑藉人多力量大的優勢,幾乎對小說理論的一切層面都進行了全面徹底堅決而極端的清算、消解和顛覆。
與此同時,他們也以自己的創作彼此從不同的層面互補性地豐富、充實和建構了先鋒小說的美學準則。他們的最大成就還是體現在小說形式層面上的小說語言、小說故事敘述和小說文本結構等幾個方面。
格非的小說也致力於敘事迷宮的構建,但他的方式與馬原不同。馬原是用一些並置的故事塊搭成一些近於“八陣圖”的小說,在每個路口上他又加上一些讓人誤入歧途的指標;格非則主要以人物內在意識的無序性構築出一團線圈式的迷宮——其中有纏繞、有衝撞、也有意識的彌散與短路。如在《褐色鳥群》中,“我”與女人“棋”的三次相遇,表現得如夢似真,似乎有幾個不同的“棋”存在於一個共時的世界中,但在小說進行的歷時層面,每一個“棋”都對前面一個“棋”起著解構的作用。這標誌著格非對現實的懷疑。所以他著重寫人與物的背離,在一個錯位式的的情景中,人物彷彿已變成了若有若無的鬼魂,身歷的事件比傳聞還要飄渺,人就是處在這樣的從未證實而又永遠也走不出“相似”的陷阱的一種假設的狀態中。
先鋒作家都很重視小說的語言,但在小說的語言實驗上走得最極端的是孫甘露的《信使之函》、《訪問夢境》、《請女人猜謎》、《我是少年酒罈子》等作品。孫甘露的這些小說徹底斬斷了小說與現實的關係,而專註於幻象與幻境的虛構,但這些幻象與幻境又都知識一些無關緊要的瑣屑線索,無法構成一個條理貫通的虛構世界。他著力使小說語言詩化的詩性探索,詞語被斬斷能指與所指的關係,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來。如《信使之函》中,“信是焦慮時鐘的一根指針”、“信是耳語城低垂的眼帘”、“信是錨地不明的孤獨航行”等等幾十個詩意的夢囈式的對“信”的述說,在每一句述說下載錄一段信使所送的信中的段落,這些段落同樣華美、富於詩意而又沒有任何現實或者象徵的寓意。孫甘露的小說語言實驗,其實最接近於超現實主義的詩歌和繪畫,他的小說是這些語言的與視覺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曖昧的夢與詩。這比莫言著力於表現自己的主觀世界的語言探索更進了一步:在莫言那裡的語言仍然是有著主體的、現實的、與人文的意義,孫甘露則抽空了這些意義而只剩下純凈的言辭。
而余華則發展了殘雪對人的存在的探索,小說以一種冷靜的筆調描寫死亡、血腥與暴力,並在此基礎上揭示人性的殘酷與存在的荒謬。
需要指出的是,這代作家的創作有從形式向歷史轉化的趨勢。他們之間形式探索的程度不同,蛻變和退化也難以避免。特別是到八十年代末期,這種分化就更加明顯,除了孫甘露等少數作家堅持新潮陣地之外,大部分都已經收斂了他們的實驗鋒芒。1989年前後與“新寫實小說”的聯合就是這種撤退的突出表現。蘇童、余華、北村等作家都已經開始熱衷故事性文本的創作。
隨著新潮小說第二代的蛻化,人們紛紛預言了新潮小說的滅亡。確實各種小說的可能性都被實驗過了,各種實驗都到達了極限,當然根本的原因是新潮小說自身失去了繼續探索的動力和目標。
到九十年代以後,先鋒小說又一次復興。這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
一是八十年代的先鋒作家在銷聲匿跡一段時間後於九十年代夾帶著他們的長篇創作重新殺入文壇。可以說這是九十年代長篇小說風起雲湧,也是中國當代文學上個世紀最動人的文學景觀。蘇童、余華、格非、孫甘露等幾乎每一位新潮作家都在短短的幾年內出版了他們的長篇,這些作品無論從思想蘊涵還是從藝術形式來看,確實代表了這批作家創作的最高水平。這是八十年代先鋒作家走向真正成熟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