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諫官的結果 展開
- 諫官
- 諫議大夫
諫官
諫官
徠中國古代官職之一,是對君主的過失直言規勸並使其改正的官吏。
諫官的設置比監官早。春秋初年齊桓公設大諫,為諫官設置之始。晉國的中大夫、趙國的左右司過、楚國的左徒,都屬於諫官性質。秦漢時有諫官之設,但是沒有專門的諫官機構。漢代置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諫大夫、中散大夫、議郎等官職,都屬光祿勛,掌議論,侍從皇帝,顧問應付。東漢侍中、中常侍成為正式官稱,屬少府。隋朝改侍中為納言,武則天時增置左、右拾遺與左右補闕。宋改補闕為司諫,改拾遺為正言,並置諫院,作左右諫議大夫為長官,司諫、正言為其所屬。遼以後,諫官名存實亡,或名實俱亡。
中國古代諫官制度研究。
“諫官”又稱“諫臣”,指諫君過失之臣、勸諫天子過失之官。《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有“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的名論;《白虎通·諫諍》論及朝廷職官時說,“設輔弼,置諫官”,諫官被看作是與丞相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諫”字包含多重意蘊,而要義在“直言以勸正”。《說文》曰:“諫,證也。從言柬聲。”《廣雅·釋詁一》曰:“諫,正也。”《字彙》曰:“諫,直言以悟人也。”綜上所述,“諫”的基本內涵是,以正直之言啟侮別人。諫官之“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給各類人提意見,而是針對君主,“諫朝政之得失”。“廷諍”(在朝廷當面向君主直言)與“上封事”(書面向君主提意見)是諫官將批評上達君主的兩種形式。
白居易說:“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啟我之路久矣。”(P1371)中國的諫官制度源遠流長,自周代設“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諫官設置,雖然其名稱有異,作用各別,但諫議制卻一以貫之。究其原由,則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屬性所使然。大略言之,人類社會所出現的政體(政權構成形式)有三種類型——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氏族民主制,但自從跨入文明門檻以後,則只有不發達的貴族制和發達的君主制兩種政體。由戰國發起端,秦漢定型的專制主義君主集權政體在中國延續達兩千多年之久。這種專制政體的最顯著特點是,將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權集於帝王一身。在這種體制之下,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衡,其“一動之幾”不僅可以給任何人以生殺予奪,而且會導致國家大政方針的傾斜。為了彌補這種由帝王獨斷所可能造成的對王朝根本利益的損害,列朝都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諫官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那些敢於“犯顏直諫”的諫官和善於納諫的帝王,都是這一機制的產物;而一切阿諛逢迎之徒和不納良諫的帝王,則破壞那種彌補機制,加劇專制體制的危機。
諫官制度固然是為專制君主的長治久安效力的制度,但由諫官和帝王演出的“進諫”與“納諫”(或“巨諫”)的種種活劇,卻蘊藏著豐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給後人以啟迪。
(一)先秦諫官的設立
諫官的設立始於周代,盛行於秦漢至唐宋時期。但相傳於舜帝時,已有“納言”一職。《尚書·孔氏傳》說:“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這種納言之官,是諫官的初始。納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呂氏春秋·自知》記載,商湯王時已有“司過之士”,皇帝有過錯,可以由“司過之士”提出或者糾正。司過之士已近似於諫官。
周文王時,周王室內設有“保氏”一職。“保氏”,可算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諫官。《周禮·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諫王惡”。據《周禮註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王有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也就是說,“保氏”的職責是司掌規諫王的過錯。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過保氏一職。王安石《諫官》:“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
春秋戰國時,直接以“諫”命官,稱為諫官。齊桓公設“大諫”之職,其他各國均有類似的設置。齊國中央官制的主體是在相的下面,設置五個行政部門,即所謂“五官制度”。齊國的五個主要部門是:
附圖{圖}可以看出,諫官處在相當顯著的位置,他是齊國中央相府的五個職掌之一。《呂氏春秋·勿躬篇》載:管仲對齊桓公說:“早入宴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請置以為大諫。”其他國家如趙、魏、韓三國相府直屬官有左右“司過”,掌諫議。諫官處在君王身邊,專司其過,找君王的缺點毛病。
(二)秦漢諫官制度
秦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各項制度有較大的變革,但諫官不能不設。秦初置諫議大夫,其諫官制度對後世影響至深,諫議之職直沿至宋元時期。
《通典》卷二十一說:“諫議大夫,秦置,掌論議。”秦置諫官,真正的名稱是“諫大夫”,隸屬郎中令,無定員,多至數十人,職掌議論。郎中令是諸郎官的總頭領,而郎是侍從官的統稱,郎官的主要職責是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郎中令下屬有諫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諫大夫專掌備顧問應對,司諫議之職。
漢武帝時沿襲秦制,仍設“諫大夫”,東漢光武帝時增“議”字,始稱“諫議大夫”,置三十人。漢時,諫議大夫是光祿勛的專職諫官,其職責是“直言極諫”,匡正君非,諫諍得失。漢文帝屬善納諫言之君,曾下詔,察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凡任諫職者,須進行“直言”之士的對策,測試成績優秀,則可任職。漢時的著名諫官有劉輔、王褒、貢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勝、嚴助等人。這些諫官均敢直言,頗有政聲。
秦漢除諫議大夫為專職諫官外,光祿大夫、議郎、博士等均有諫議之責,其他中央官員若加有侍中、散騎、中常侍等官銜,亦可在皇帝身邊起到諫議的作用。 (四)宋及宋以後諫官制度
宋代也重視諫官,曾專門從“三省”中的門下省分出一個諫院與三省并行,以左右諫議大夫為長官,加上門下省的“給事中”,合稱為“給諫”。另外,改唐時“補闕”為“司諫”,改“拾遺”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設“司諫”,表示專司諫諍之職;“正言”,表示向皇帝說正確的話,糾正皇帝的錯誤言論。正所謂“正言之為官,以諫救遺失”。司諫、正言都是很重要的專職諫官。王安石《上田正言書》謂正言者“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症,蹇蹇一心,如對策時”(28)。
宋專置諫院,並置諫官六人,以“司諫”、“正言”充任;另有許多以他官兼領者,謂之“知諫院”、“同知諫院”,帶有加官性質,但也是很重要的諫官。司馬光在遷起居舍人時,就是同知諫院,並有《諫院題名記》一篇。宋代諫官職權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對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說:“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
他官兼領諫官,是宋代諫官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病,諫官的性質發生了一些變化。唐宋以前,言官與察官是分立的。諫官司言,御史司察;諫官掌規諫諷諭,獻可替否,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監督政府,糾察皇帝,御史監督官吏,糾彈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諫官也不得糾彈。宋代初期,御史和諫官也分別職司,並不兼領職務,后諫院獨立,權力擴大,並且規定諫官由皇帝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諫官雖然可以諫諍皇帝,但也有糾繩宰相之責。據宋史載: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諫官皆得諫正。宋神宗以後,諫職更加擴大,以兩省給諫權,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給右諫議大夫權。宋神宗初年,規定他官可以兼領其諫官職務,並以知雜侍的御史鄧綰為中丞,除諫議大夫。唐代重諫官,輕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諫官兼權,諫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職權,這樣對皇帝的箴規闕失、規諫就削弱了。
另外,諫官與宰相,諫院與政府的矛盾也日趨激烈。在漢代,諫官禹光祿勛隸屬於宰相,諫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唐代,諫官屬門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屬,總之是專門向皇帝諫諍過失的。唐制,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后,通常沒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後,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討論,這時旁人不得參加,而門下省的諫官們獨在例外,他們可以隨從宰相列席參加,而且規定要有諫官列席。宰相有時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可以由這些“言者無罪”的諫官來講。諫官講得對固然好,講得不對,也無妨大體,因為諫官的職責就是開口講話,這樣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衝突,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政治上的藝術,即君權、相權之間相互調節。這一關係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又諫諍皇帝。但諫官職權擴大,御史兼領諫職以後,就形成了諫院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諫官往往不是糾繩天子,而是糾繩宰相。
當然這種制度也有積極的一面,如司馬光在同知諫院時,以諫官之職,進行揭露姦邪佞妄,嚴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時,以諫官名義“三彈張堯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樣,諫官的主要任務應是諫諍皇帝,監察政府有御史台。諫官對政府官員有監察權以後,就形成了台官、諫官共同糾察政府官員,宰相再也不好借諫官之口向皇帝發表意見,諫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諫官、台官也漸漸不分,稱呼也逐漸合流為“台諫”。王安石新政的失敗,就與諫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關係。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廢除諫院,正式以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分隸於門下、中書二省,專供諫職,不得越職言事。諫議大夫趙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
宋代著名諫官也很多,如司馬光、歐陽修、范仲淹、王禹chēng@②、蘇轍等。宋代的諫官也敢諫、善諫,諫疏有時多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如神宗時,張舜民做諫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時任伯雨做諫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范仲淹曾有《靈烏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其諫官生涯的真實寫照。
元代廢門下省,諫議、司諫、正言也隨之俱廢,因而未設專職諫官。但御史卻承宋制,得兼諫職。

監察御史袁可立(1562—1633)
清代言諫之官的建置大體如明代,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兩班人馬。康熙初年,撤銷巡按御史,雍正開始又將給事中划隸都察院。凡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給事中、監察御史,都許風聞言事。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風俗善惡,皆能以耳目官的資格,盡量陳奏。故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上諭:“凡事關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應興應革,切實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條陳奏,直言無隱。”形式如此,事實上清代諫官等於虛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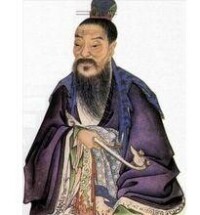
諫官
(一)諫官言者無罪
諫官,是專司諫諍之職的,國家設立諫官的目的,就是讓他講話,所以諫官是言者無罪的,講錯了也不要緊,所謂諫言不咎,諫官不罪。
這裡有兩件事實很能說明問題。一件是:唐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月,白居易初授拾遺時,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依照慣例,在四月舉行的“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的科舉考試中,皇甫shí@③在對策中,抨擊時政,語言激切。牛僧儒、李宗閔也力詆宦官和權貴。當時的考官是吏部侍郎楊玉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他們主持正義,不僅錄取了這三個人,而且還使他們名列前茅。這就激怒了宦官和舊官僚李吉甫。據《資治通鑒》說:“李吉甫惡其直言,泣訴於上。”宦官和舊官僚一齊合力攻擊這次考試。於是憲宗命裴jì@④、白居易等六人複查。複查結果,同意楊玉陵、韋貫之的“策為上策”。可是宦官集團不肯罷休,繼續“泣訴,請罪於上”,結果唐憲宗聽信讒佞之言,黑白顛倒,罷黜楊玉陵、韋貫之,對參加複查工作的裴jì@④罷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其他參加複查工作的人也都受了處分,而白居易也參加“考復”工作,而且慷慨陳詞為楊玉陵、韋貫之、裴jì@④等人辯護,卻未受處分。裴jì@④出翰林院時,白居易遂上《論制科人狀》說:“臣伏以裴jì@④、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用這些人“則必君子之道長”,退這些人,“則必小人之道行。”“臣職為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辜負聖恩,實亦不負神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P1230)這是多麼激烈的言詞!也足見白居易忠於諫官之職守,以致唐憲宗不能容忍。但由於白居易是諫官,而諫官是“言者無罪”的,“不宜阻居易言”,所以唐憲宗只能怒而哀嘆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撥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1560)只能“難奈”而已,不能治罪。但是白居易為太子左贊善大夫時,即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被盜殺,白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恥”。由於他已不是諫官了,唐憲宗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P1560),而貶其為江州司馬。二是:范仲淹在不任諫官而拜禮部員外郎以後,奸相呂夷簡就曾威脅他說:“汝即非諫職,不得妄議軍國大政”。但范仲淹面對奸相,無所畏懼,繼續向仁宗皇帝諫諍,最後被仁宗皇帝以“越職言事”,罷知饒州。
白居易和范仲淹的經歷充分說明,諫官的職責就是直言以諫。既然是直言以諫,就不能因直言而罪之。相反,如果不任諫職,話說錯了或不合朕意,就隨時都有被殺頭、貶官的危險。諫官諫諍,然後皇帝善擇,“言之當者,朕有厚賞,言之不當,朕不加罪”。王安石在論《諫官》一文中說:諫官其所以極言以諫,就在於他是諫官,即“蓋已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P379)因此,言者無罪,也就成為諫官的“特權”。(二)官卑秩微,任選青年
諫官不罪或者言者無罪,這只是一種禮法制度,實際上只是皇帝的一種道德規範。不遵循禮法,就會落得一個誅殺諫臣的罪名,有了這個罪名就是一個昏君。所以,遵守制度的皇帝是不能隨意誅殺諫臣的。但要每一個封建皇帝都不去誅殺、貶謫那些“逆鱗”的人又談何容易?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因此在選用諫官時,往往需要選用那些敢說直話不怕殺頭的年輕人,同時官卑秩微。
所謂“官卑”,是指官位不高;“秩微”,是說待遇不厚。諫官,跟隨皇帝左右,地位相當重要,白居易謂之“位當星象”。但官階甚卑,其秩甚微。諫議大夫作為諫官之長,也沒有超過四品官的。其它諸如拾遺、補闕、司諫、正言,均沒有超過七品的。唐代對諫官是很重視的,但諫議大夫為正五品,而左右拾遺和左右補闕僅為八品之官位,這在九品官位制度中幾乎是最末的。
為什麼諫官的地位相當重要,而官位卻很低呢?關於這一點,王安石曾為之大鳴不平。他在《諫官》一文中說:“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然而,“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P379)因此,王安石提出要為諫官正名。其實王安石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諫官其所以責之三公,命之以士,其秩甚微,官職甚卑,就在於官位低下,說話就沒有什麼顧慮,不會珍惜官位而不敢直言,說錯了大不了不幹這個差事。但官位一高就不行,為了保其官位,免丟烏紗帽,該說的可能也不說了,該諫的一看皇帝的眼色也不敢諫了。白居易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對於“其秩甚卑”很能想得通。他在《初授拾遺獻書》中指出:諫官“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P1228)這就充分說明了諫官職位不高的原因。
諫官除位卑秩微以外,在選人上一般選年輕人擔任。漢時的終軍十八歲任諫大夫,劉向二十歲任諫大夫。唐宋時期的諫官,大多是在初進士后,就委以諫官之職,年齡都是在二十幾歲左右。如陳子昂二十四歲遷右拾遺,元稹二十七歲為左拾遺。諫官選拔年輕人擔任,這一方面同位卑有聯繫,進士以後,首先從小官做起,被皇帝認為是正直敢言,然後再予以升遷。這裡有意思的是古代帝王有時也將能正直敢言作為任官的標準,漢唐舉士都設“能言極諫”科,就是例證。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輕人不那麼世故,“後生可畏”,初生之犢不怕虎。年輕人火氣大,敢想、敢說,臨事不怕冒風險,這些也正是作為諫官之職所必需的。在敢諫上,年輕人實屬可愛。
(三)諫言不露
諫官之所設,在於糾正皇帝的缺失,諫官的使命就是挑皇帝的錯誤和毛病,向皇帝進忠告。皇帝設諫官,當然也就有希望他們挑自己錯的一面,否則,諫官恐怕也就難以存在。但封建時代的皇帝絕沒有讓人當眾批評的勇氣,也沒有將缺點錯誤公開的膽魄和胸懷,因而就出現了一項制度,這就是“諫言不露”、“諫書人莫窺”。諫官言事要“密陳其奏”。白居易《初授拾遺獻書》中說,諫官言事要“密陳所見,潛獻所聞”,“密緘於疏,潛吐血誠”。魏徵就曾為公開在朝廷上“辱”唐太宗,而險遭殺害。
諫言之不露恐怕有兩個原因:
第一,怕影響皇帝的威信。皇帝者,天賜之子,金口玉言,哪會有缺點錯誤?但歷史無情,自然有道,縱然真龍天子,也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不可逆轉歷史的規律,於是乎欲蓋其惡,悄然改正,神不知,鬼不覺,保全了龍顏臉面。但欲蓋彌彰,既然連公開承認缺點錯誤的勇氣都沒有,又何以能真正納其諫言而改正呢?
第二,欲毀滅“罪惡”史。封建皇帝一般都想為自己樹碑立傳,有哪一個君主想將自己的“罪惡”史傳之於後世呢?諫言,自然大多是講皇帝的壞話,如果公開出去,傳之於後世,豈不有損於榮耀?司馬遷著《史記》,只是記載了一點點漢武帝的壞話,結果到後漢的時候,大臣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P23)所以唐代嚴格規定,“領史職者,不宜兼諫議”。但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存在於人民的心目之中。統治者做了壞事,要瞞是瞞不了的,正史不傳,還有野史,“流芳”還是“遺臭”,歷史自有公論。
(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按照禮法,諫官是言者無罪的,但不遵守制度的皇帝卻是大有人在,於是就形成了諫官最重要的職業道德,這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然,這種道德的指導思想又是“忠君”,正所謂“忠臣不避重誅”。
這種職業道德的形成最早當然與遠古時聖賢者的求諫納謗分不開。《孝經·諫諍章》:“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子。”《荀子·臣道》篇曰:“君有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說苑·正諫》:“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這就為直言敢諫,以死而諍奠定了理論基礎。夏桀及商紂時的關龍逄、比干又在行動上開了先河,成為以後諫官及諫臣們學習的榜樣。
同時,從封建統治者來講,也需要這樣“披腹心而效愚忠”的忠良之臣,“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P238)故漢唐選士設“能言極諫”科,選敢於直言者為諫官。古代聖賢更是做出了榜樣,“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從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P385)做諫官的也都以盡忠和諫以死諍為榮。《藝文類聚》載:楚莊王時,三年不聽朝,並對文武百官下命令說:“寡人惡為人臣諫其君”,“有諫即死無赦”。有數百人因進諫而被殺,蘇縱卻不怕死,對楚莊王強諫。他說:“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惜身怕死)不諫,則非忠臣也。”歷史上以死相諫的史例不勝枚舉。范仲淹因諫而三次被貶官,詩友梅堯臣曾寄詩《靈烏賦》,希望他拴緊舌頭,鎖住嘴唇,但范仲淹卻回贈同名的《靈烏賦》,表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三、諫官制度的思想基礎
諫官及諫官制度作為封建國家的政體構成部分之一能夠綿延幾千年,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堯舜禹等古代聖賢的求言納諫作出了榜樣。由於各種輿論影響,古代皇帝不能不以堯、舜、禹的聖明作為皇制的思想目標,這種目標或有真意(如唐太宗),或不得不表面假具(如秦始皇言自己德超三皇、功蓋五帝),但不管怎樣,不能不以堯舜先王為先驅。第二,沿襲諫官例制。歷代帝王無不想留得從言納諫的美名,因而諫官例制不敢輕易取消。第三,諫官對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以及皇權的鞏固,的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歸根結底是同當時的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古代聖賢早知諫的重要並且躬行於實踐,堯舜“設諫鼓、立謗木”,以為“治世之音”就是例證。“諫鼓”之設,“謗木”之置,可以說是古代氏族社會民主監督的一種形式,是實行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當社會進入到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後,君主專製取代了民主,但統治階段為了統治的需要以及古代效法先王的思想,使得諫諍理論得以發展,諫諍現象得以存在和綿延。
春秋戰國時期,言諫之事被提到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上來認識。《新序·雜事》載:晉平公問叔向:“國家之患孰為大?”叔向作為晉國的大夫回答說:“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叔向認為,大臣不極諫,是國家最大的災難。
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古代一些帝王,客觀上也就需要別人的進諫,忠臣的規勸,所謂“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天子之目不能自明”,“木從繩則正,后(君主)從諫則聖”。
另外從思想理論來看,“以多物,務和同”的和諧理論觀念,不能不說是一種影響。《國語·鄭語》中有《史伯論興衰》篇。史伯是周的太史,他認為將許多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而使他們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平衡,這叫做和諧。和諧能使事物豐盛起來,成長起來,而產生出新的東西。如果一定要在相同的東西之上,再添加相同的東西,即加到不可再加的時候,就會被拋棄了。“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鋼四肢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於是乎先王聘後於異性,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P147)這裡講到,先王任用大臣,選取敢提不同意見的諫臣,其目的在於求取“和諧”,協調矛盾。這種“和諧”觀,很有一些辯證的道理。
從這種“和諧”觀念出發,於是為諫為忠。做臣子的不能不忠,而忠的體現是諫,諫和忠形成了辯證的統一。《晏子春秋》中,記載有晏子和齊景公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晏嬰認為,君臣之間的和諧絕不是同一,絕不是唯君是從,而是相反,“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咸”。晏嬰是齊景公的諫臣,“忠”和“諫”在他那裡達到了最完美的統一。由於晏子的才幹和能言善諫,而得齊國三代國君重用,於是大夫梁丘據不解地問:“晏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說:“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P366)這裡的一心,就是“忠”,忠與諫的和諧統一,應該說是構成諫官制度及其得以延伸的重要思想基礎。

諫官
可見,魏徵雖然以敢於“犯顏直諫”而著稱,卻很長時間裡不是宰相或副宰相。“諫議大夫”是諫官,品級只是正四品下;後來升為“尚書左丞”也只是正四品上,只升了半級;這時他都不算“參預朝政”。到貞觀三年(629年),任秘書監(從三品,又升了半級。掌管圖書檔案)才“參預朝政”。直到貞觀十年(635年),為侍中(正二品),才算是真正的宰相。唐太宗雖很看重魏徵,但由於魏徵畢竟是建成的部下,很長時間裡,品級並不高。不過難能可貴的是,他儘管職位不太高,仍然敢於“犯顏直諫”,後來更是積極“參與朝政”,真正盡了宰相的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