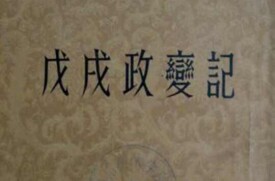戊戌政變記
一部很有特色的紀事本末體史書
梁啟超撰著的《戊戌政變記》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紀事本末體史書,作者將對傳統紀事本末體史書的辯證認識,熔鑄到《戊戌政變記》的撰著中。在編纂思想上,作者確立了具有比較系統和嚴密的指導思想,即確立“史跡集團”,以擴大紀事本末體的記載範圍和強化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確立“以傳記之法,來改造紀事本末之體”,重視偉人在紀事本末中的作用;重視史論,闡明作者對歷史進程的觀點和看法。《戊戌政變記》在編纂方面的實踐,表明它是紀事本末體由傳統型向近代型過渡的代表作。
戊戌政變記是文章專集。晚清梁啟超所撰。作於光緒二十四年。共五篇。
第一篇:《改革實情》
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慘敗,尤其是《馬關條約》的簽訂,給平靜、苟安的中國社會沉重一擊。誠如梁啟超在此篇開頭所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甲午戰敗引起全國極大的震動。人民大眾、士大夫知識分子,以及在朝官員、封疆大吏都捲入為國家、為民族而憂慮、而憤慨、而抗爭的熱潮之中。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全國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社會各階層的愛國人士都用自己所能採取的方式表達愛國的熱忱。然而,既不能再戰、和又受屈辱的形勢已呈現在人們面前,人們十分憤慨,痛定思痛,把譴責的目標集中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受到維新改革的必要。在這種形勢下,康有為發動了公車上書,掀起了維新變法的政治運動。
1895年3月,康有為、梁啟超以舉人的身份到北京參加會試。4月,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全國輿論沸騰,立即掀起反對割地求和的熱潮。由梁啟超等發起,聯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共推康有為起草萬言書,集合了一千多名舉人簽名。5月2日,舉人齊集都察院門前請願上書,向朝廷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要求,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公車上書”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簽訂《馬關條約》,主張遷都與日本再戰,而更重要的是“變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張。清朝本來有嚴禁讀書人干預朝政的制度,公車上書衝破了朝廷的禁令,向專制主義的君主政體勇敢地提出社會制度的改革方案,帶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政治鬥爭的色彩。
“公車上書”之後,資產階級維新派從兩個方面開展活動:一方面是立學會、辦報紙、興學堂,另一方面是上書皇帝,即“上書求變法於上”,“開會振士氣於下”。維新派倡導立學會、辦報紙、興學堂的活動方式是直接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搬來的,是在興民權、開民智的思想指導下,衝破封建朝廷的禁令,爭取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的主要內容。維新派在大力開展立學會、辦報紙的群眾活動的同時,以更多的精力上書皇帝。他們認為“變之自上者順而易”,把變法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以為只要皇帝贊成變法,下一紙詔書,全國實行起來,事情就可以解決。為些,康有為七次上書光緒皇帝,屢次受到封建頑固派的阻撓,第六次上書終於上達,這份上書對光緒帝痛下決心頒布“詔定國是”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對百日維新的新政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的歷次上書終於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贊同,光緒皇帝決定實行變法改革。1898年,維新改革的新政時期開始。
二篇:《廢立始末記》
正當維新運動進入高峰,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也開始行動起來。就在《明定國是》上諭頒布的第四天,慈禧太后逼迫光緒皇帝連發三道上諭,除罷黜翁同和外,還有兩項重要的措施。其一、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謝恩。這道上諭暴露了慈禧太后企圖再度“臨朝訓政”的野心。按成例,凡已歸政的太上皇、皇太後有賞於大臣,應由皇帝代奏謝恩,表示尊崇。現在慈禧太后突然命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顯然是她企圖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皇帝任命維新派為高級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樞密權力中心。其二,任命其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本是朝廷京官,時任兵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在軍機大臣翁同和被罷免之後,西太後有意將軍機大臣的職位授與榮祿。榮祿卻自求北洋大臣職,“意在攬握兵權”。慈禧太后通過榮祿把京畿地區的軍事力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新政時期,慈禧太后和守舊派積極策劃廢光緒皇帝。內務府總管大臣立山等率屬僚數十人一起跪在慈禧太後面前,控告光緒。守舊派又運動手握重兵的榮祿策劃政變。榮祿本人也以密謀政變為己任,曾揚言:“欲廢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聽其顛倒改革,使天下共憤,然後一舉而擒之。”在他離京上任時,曾親自再三懇請慈禧太后訓政,與慈禧太后多次密商,政變的陰謀在守舊派的最上層集團中有所醞釀。待慈禧太後為守舊派抓住軍政實權后,他們便認為穩操勝券,“西后與榮祿等既布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
榮祿這時對守舊諸人求助的答覆是:“如俟其亂鬧數日,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手?”此外,滿洲權貴、內務府諸臣率先奔赴頤和園,跪清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御史楊崇伊擬請太后訓政的奏摺得到榮祿、慶親王奕?諸權貴的贊同。訓政雖未立即實現,但政變的醞釀已接近成熟。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在北京發動政變,當天宣布訓政,由她重新掌握政權。關於這次“訓政”,梁啟超認為,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
在書中,梁啟超說:“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為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為君者何在乎?為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既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為誡者,既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垂簾,皆因嗣君幼沖,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多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率乃易唐為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慈禧“訓政”之後,維新變法遂告失敗。
第三篇:《政變前記》
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其鋒芒所指,直接朝向封建專制制度及其腐朽勢力,因此,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及盤踞要津的官僚必然進行抵制和攻擊。維新派的革新進取精神和驚世駭俗的舉動也為因循守舊的世俗所不容而遭致非議。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更擁戴光緒為首領。於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勢力便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表示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吏部侍郎汪鳴鑾反對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受到光緒幾次召見,為慈禧太后所猜忌,被革職。戶部侍郎長麟反對撤簾歸政的慈禧太后操縱政權,掣肘光緒,也被革職。珍妃的親兄、時任禮部侍郎的志銳在甲午戰爭中支持光緒主戰,彈劾李鴻章妥協避戰、因循玩誤、被慈禧太后貶往新疆烏里雅蘇台。
翁同龢的門生、受到光緒皇帝厚遇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由於力主變法,與康有為在北京發起成立強學會,常集合開明官員、維新人士議論時政,被慈禧太后逼光緒下令將他革職,驅逐回籍。翁門弟子張謇懾於慈禧太后的淫威,引退回籍,轉而經營工商業。百日維新伊始,翁同龢為光緒皇帝起草“明定國是”上諭,為慈禧太后所忌恨,終於於“明定國是”后的第四天被“開除回籍”。至此,光緒的親信大臣基本上被革斥殆盡,慈禧太后逐步地將光緒的羽翼全部剪除。
第四篇:《政變正記》
1898年八、九月間,守舊派企圖政變的跡象逐漸顯露,維新派不能不籌劃對策。康有為想爭取袁世凱。以借用其武力保衛新政。袁世凱為人陰險狡詐。他投機加入強學會,表示擁護維新變法,但他又是榮祿的親信將領之一。在榮祿的北洋三軍里,他統率的乃是清軍中的勁旅。憑靠這支軍隊,袁世凱成為軍隊的實力派。維新派被袁世凱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想依靠他來保護新政。康有為向光緒推薦袁世凱,還寫了一道密折交譚嗣同遞上,請求光緒“結袁以備不測”,意思是要聯絡袁世凱,依靠其武力。以防備事變,指出這是解救當前危局的唯一辦法。
光緒採納康有為的建議,連續兩天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侯補,專辦練兵事宜,並囑袁世凱:“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意為不受榮祿節制。新舊兩派勢力的鬥爭已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在時局緊迫之際,光緒皇帝特地密詔給楊銳,稱:“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願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維新派又聽說頑固派策劃趁十月天津閱兵時發動政變,廢黜光緒,於是決定孤注一擲,讓譚嗣同說服袁世凱,叫袁世凱舉兵勤王,殺榮祿,派兵包圍頤和園。他們把皇上的命運,他們自己的命運、連同整個新政的命運全都寄托在袁世凱身上。但袁世凱陰謀騙過維新派諸人,於9月20日向光緒請訓回到天津后,便向榮祿告密。然而,榮祿尚未來得及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已在北京發動了政變。這就是戊戌政變。
政變后,大部分新政被推翻、廢止,重行禁止士民上書;廢官報局,查封全國報館,嚴拿報館主筆;禁止集合結社;新政所裁減的閑散衙門,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予以恢復,又廢農工商總局;恢復馬步箭弓刀石的武試和八股取士的文試製度,罷經濟特科,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小學堂。大權被慈禧太后所掌握,皇帝徒有虛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
維新派慘遭迫害,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譚嗣同拒絕出走,慷慨就義。御史楊深秀臨危不懼,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追捕維新派的恐怖氣氛里,他抗疏直言,要求慈禧太後撤簾歸政。後來被捕入獄。與譚嗣同一起被殺害。此外,還有劉光第、林旭、楊銳、康廣仁同時遇難,史稱戊戌六君子。
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失敗了。梁啟超在此書第三篇《政變前記》中分析了政變的原因。他認為,“政變之總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太后與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太后與皇上長期格格不入,矛盾甚多,這是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改革受到了頑固派的百般阻撓。新政的改革由於衝擊到一部分守舊人物的既得利益,因此守舊派拚死反對,改革每前進一步都要受到重重阻力。反對新政最力的是樞臣大吏和督撫大員,他們本來是執掌舊政權的權貴,舊制度使他們有權有勢,舊的統治秩序、舊的政策法令是他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變革就會使他們失去一切。因此他們極力反對新政。
百日維新的新政詔書連篇頒發,然而,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只有李端■一人講新政,地方督撫中只有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法比較得力。除此以外,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撫都觀望、延宕、抵制,公開反對,拒不奉詔,形成“明詔但言其始,則彼必不競其終”的局面。維新派企圖通過光緒打擊、抑制守舊官僚的囂張氣焰,扶持推行新政的督撫。然而,守舊大臣既然有握有實權的慈禧作後盾,那麼,嚴懲、嚴斥的詔令又哪能嚇退這些人呢?新舊勢力的鬥爭在進行了幾個回合之後,就進入了決戰階段,戊戌政變便是它的最後結局。
梁啟超在《政變前記》中指出,“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但除舊必有損於一部分官僚的利益,如裁減閑散衙門、裁減冗員的改革,使一批守舊官僚面臨失去權勢的可能,因此引起的震動也非同小可。這項改革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守舊官僚見詔書頒發,與維新派更是勢不兩立。他們採用種種手法破壞這項改革,或者造謠惑眾,或者上書恫嚇。極力阻撓新政。
改革還受到千百年來形成的習慣勢力的阻撓。受舊的習慣勢力約束的人們,他們往往容易受頑固派的驅使和煽動,成為被頑固派所利用的、人數龐大的力量。由此可見,反對維新改革的人群龐雜,勢力相當強大,“而改革黨人慾奮螳臂而與之爭,譬猶孤身之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血刃>也得乎?”維新派勢單力孤,他們沒有軍政實權,沒有廣大人民群眾作後盾,只有一個傀儡皇帝,而這個皇帝連自己的地位也朝夕難保。這就決定了在新舊勢力的交戰中維新派必然失敗。
第五篇:《殉難六烈士傳》
維新變法在戊戌政變后宣告失敗。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訓政”。清政府到處搜捕維新派。有不少官員被革職發配,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梁啟超在此篇中對以上六人表示沉痛的惋惜,對於清政府這種殘害志士的暴行進行了指責:“究之諸人所犯何罪,則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觀者更無論也。”後來這一篇單獨成書,又名《戊戌六君子傳》。
就單行本而言,主要有兩個版本系統,一為九卷本,最早為1899年橫濱清議報社印九卷本,隨後有新民叢報社印九卷本等,1957年香港中華書局重印第16版九卷本。另一為八卷本,根據狹間直樹的研究,最早的八卷本出現在1907年之後,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飲冰室合集》收錄的是這個版本,1953年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戊變法》同樣收錄了八卷本,1954年中華書局又根據《飲冰室合集》本印行了單行本。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清議報》連載本和橫濱清議報社鉛印九卷本,但是為了方便查對,引用的文字一般標出其在中華書局重印本中的位置。關於九卷本和八卷本的差異情況,本文依從劉鳳翰的研究成果,請參閱劉鳳翰《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異》,台北,《幼獅學報》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一書第一次對戊戌維新運動從整體上進行了描述,建立了一個以康有為為領袖和主線的戊戌維新運動宏觀敘述框架。
在近一個世紀戊戌變法史的學術研究中,《戊戌政變記》的總體描述逐漸獲得認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關專著所尊信,並在此基礎上演變出一個戊戌變法史權威敘述體系。20世紀20年代開始陸續面世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和專著,已經普遍採用梁啟超的記載來描述戊戌變法史,比如顏昌嶢的《中國最近百年史》(太平洋書店1928年版),歷史研究社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綱要》(新知書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變記》的體系來描述這段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陸續出版了不少有關維新變法的研究專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略》(聯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濱的《戊戌變法》(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體敘述方面雖然力求精緻嚴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體系。80年代以來有多部相關學術專著問世,其中具代表性的有王栻的《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們對於維新變法運動的具體史實的考訂嚴謹細密,但是在總體敘述體繫上如出一轍,仍然沒有越出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一書的框架。與此同時大量出版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在維新變法史的敘述方面也沿襲了前人的做法。因此,梁啟超對戊戌變法史的敘述體系逐漸權威化,其主要觀點成為史學界長期以來普遍接受的一個基本觀念體系。比如,梁啟超將變法的過程描述為康有為由布衣而卿相的個人發跡史,將清政府陸續推行的新政縮減至康有為主導的“百日維新”(註:“百日維新”這個概念最早見於1903年版的《清議報全編》的《戊戌變法記事本末》,專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間共103天受康有為影響的光緒皇帝推行的新政。),將康有為思想詮釋為戊戌年新政運動的惟一指導思想,將政變的原因約化為主維新的光緒和主守舊的慈禧之間的帝后黨爭。這些觀點在現行的敘述中演變為:康有為是維新運動的主要領袖,康梁譚等人構成的維新派是當時惟一的進步力量,康的思想是變法的主導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動了變法運動的發展,並最終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於1898年推行了短暫的新政。但是由於光緒皇帝沒有權力,又與慈禧太后長期失和,維新派與頑固派的力量相差懸殊,變法被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滿漢頑固派所扼殺。但是在梁啟超的敘述獲得信任的過程中,也有研究者如陳恭祿、陳寅恪(註:陳恭祿:《甲午戰後庚子亂前中國變法運動之研究》,《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1933年11月;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66頁。)等對其整個陳述的可靠性表示懷疑。鄺兆江1984年在其專著中指出康梁的陳述誇大了他們在光緒戊戌年新政中的作用,新政的重要人物是張之洞等人而非通常認為的康梁。(註:LukeS.K.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因而,《戊戌政變記》對戊戌變法史的整體敘述的可靠性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但是到目前為止,參與爭論的各方尚未涉及一個基本的問題,即對戊戌變法史整體敘述框架影響甚深的《戊戌政變記》的敘述結構是如何產生的?戊戌變法史的宏觀框架的一些基本問題往往與梁啟超撰寫《戊戌政變記》的環境有關,理清梁啟超撰寫《戊戌政變記》的過程有助於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這需要對《戊戌政變記》的產生過程進行專門的研究。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只有劉鳳翰的《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異》、吳相湘的《〈戊戌政變記〉考訂》和日本狹間直樹的《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成書考》等少數幾篇(註:劉鳳翰:《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異》,台北,《幼獅學報》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吳相湘:《近代史事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狹間直樹:《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成書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湯志鈞:《人物評價和史料鑒別》,《北方論叢》1982年第1期;戚其章:《〈烈宦寇連才傳〉考疑》,《歷史檔案》1987年第4期;楊天石:《袁世凱〈戊戌紀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張德鈞:《梁啟超紀譚嗣同事失實辨》,《文史》第1輯,新建設出版社1961年版,第81-85頁。),而其中除了狹間教授之外,其他人只是考訂《戊戌政變記》中的片段記載,沒有觸及與戊戌維新史有關的整體敘述框架。而狹間教授儘管初步說明了《戊戌政變記》各個版本出現的時間、機緣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但是仍然有很多疑問有待解決。比如康梁流亡日本初期(1898年10月至1899年5月)為何匆匆發表《戊戌政變記》這樣一本記述當代歷史的著作?《戊戌政變記》是如何描述戊戌變法的來龍去脈的?當時的環境以及他們的思想和活動對這一敘述框架有沒有影響?如果有,又是什麼影響?
有鑒於此,本文重點考察《戊戌政變記》宏觀敘述框架的形成過程,意在引起研究者的興趣,也為進一步研究戊戌變法史提供一點幫助。本文聯繫作者所處環境以及該環境下作者的活動、策略和他所調動的思想資源,力圖揭明:此書與康梁師徒流亡日本初期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關,並且成為他們政治活動的一個內容;書中有關戊戌變法的宏觀陳述框架和關鍵細節實為康梁等人應對當時輿論及具體政治局勢的產物。經過作者梁啟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變記》用以局內人身份說明戊戌政變(新政及其失敗)真相的形式,成為康梁等人爭取外援、反擊輿論、推脫責任、洗刷罪名及宣傳政治主張的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