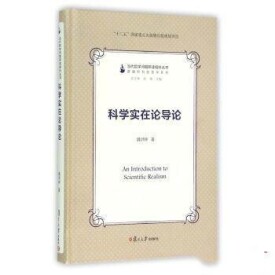科學實在論
科學實在論
科學實在論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一種承認科學理論實體的客觀存在並堅持客觀真理的學派。科學實在論是古典實在論的一種延續和發展,同時又是作為當代科學哲學中邏輯實證主義的對立面而產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塞拉斯,夏佩爾,普特南。
科學實在論者總是在很多問題上產生爭論,他們聲稱反對唯心主義,甚至包括操作主義,此外,他們對邏輯實證主義、波普爾哲學、歷史學派的思想都持批判態度。某種程度上有點偏向實證主義的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同樣反對邏輯實證主義,而可歸到歷史學派的科學實在論者夏佩爾也反對庫恩和費耶阿本德。在科學實在論者內部,同樣也有激烈的爭論。
不論是普特南還是夏佩爾,都要求科學與實在有聯繫,科學與真理有聯繫。在對科學的信仰產生危機和科學自身的可能性受到懷疑的時候,強調這些並非毫無意義,這些畢竟代表了一種探索的方向。

科學實在論
在科學觀方面,科學實在論者一方面反對邏輯實證主義的預設主義和本質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方法、科學推理的規則及科學概念等不是預先假定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另一方面,科學實在論者也反對科恩等人的歷史主義或相對主義的科學觀,認為科學發展並非是突變或新舊範式的更替,科學的發展總是積累式的,並一步步接近真理。
在西方哲學界,科學實在論本身不是一種有重大影響的學派,但在科學自身的可能性及合法性受到懷疑的今天,它所提出的問題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代表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發展的一種趨勢。
幾乎沒有哪本討論物理學哲學的書不討論物理學對象是否實在的問題。
物理學是否提供關於實在的理論?是否在揭示世界的結構及其作用方式?實在論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們的立場又有很大區別。粗分,一些論者是防禦性的,針對反實在論者堅持物理學理論的實在性。另有一些論者持物理主義還原論立場,主張只有物理學對象是實在的,惟有物理學才認識實在,常識所認識的世界不是實在世界。反實在論者的立場同樣是形形色色。粗分,一大批論者從物理學理論的“操作性”出發否認物理學對象的實在性。另一批是所謂“強綱領”的社會建構主義者,主張科學無非是一種意識形態。還原論者可視作實在論中的極端派,社會建構主義可視作反實在論中的極端派。本文不討論這兩類極端的立場。所討論的是物理學理論是否只是操作理論,抑或事關實在。本文中“實在論”和“反實在論”是在這一限定意義上使用的。
有些科學家、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把物理學理論視作約定、建構、操作理論,另一些努力證明物理學對象的實在性。前一個陣營被稱作反科學實在論者,包括勞丹(LarryLaudan)、弗拉森(BasC.vanFraassen)等。庫恩一般也列入這一陣營。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被建構主義者奉為經典,他本人被理所當然地視作反實在論的一個主要代表。這是對庫恩及《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重大誤解。實在論的論證也是多種多樣。這些論證有時各行其是,有時互相合作。這裡不列舉形形色色的論證,主要談一套相互聯繫的論證。
這套論證的主要路線是:從不同角度建立起來的理論能夠互相印證,例如根據某種理論計算出了地球周長,而這種計算的結果可以為其他途徑所驗證。這種情況支持了理論的實在性。如果這些理論的對象不是實在,很難設想它們會碰巧得出同樣的結論。
這個論證對直覺有相當的號召力。但怎樣來把握這種直覺上的號召力呢?也許,可以把這個論證和我們的日常經驗如何印證實在加以比較。在日常生活中,對實在的常見懷疑是幻覺和假象。看著像個鴨梨又怕看花了眼,摸一摸,嘗一嘗,如果不同的感官都告訴那是鴨梨,那它就的確是個鴨梨。幻象和假象恐怕不會同時滿足各個感官的期待。在可類比的意義上,只有實在能使來自不同領域的物理定律互相協調互相依賴。
不過,這個類比會提出更進一步的問題。感官印證實在的力量不是並列的,觸覺更多印證實在。摸著冰涼堅硬,那是個金屬製品,吃起來是木瓜味道,那是木瓜不是鴨梨。這樣類比下來,我們要問,得出同樣結論的不同理論究竟是並列的互相印證呢抑或是某種更基本的理論印證了另一個理論?
除了不同理論之間的互相印證,類似的印證也可以出現在同一個理論內部。一個理論往往能連貫地解釋很多物質變化,而能夠把不同現象進行整合解釋的理論應當是真的,否則很難設想它碰巧適用於多種現象。
在這條論證路線上,預測成為一個關鍵。如果一個或一批由理論推導出來的結論能夠由實測和實驗加以驗證,該理論即是真實的。例如,元素周期表所預言的某些新的元素後來被發現了,這應當說保證了理論的真實性。按常情想,不合乎現實就不可能做出穩定的正確預測。如果一個理論是脫離了實在的主觀建構,系統的成功預測,用普特南的話說,就成了奇迹了。
用正確預測來論證理論實在性現在大概是最被倚重的方法。但反實在論者不為所動。有些論者否認預測在選擇理論時的重要性,他們指出,能提供正確預測的理論有時會被證明為假,如滯止膜理論。這類事實有很重要的意義,但它們是否可以用於反駁實在論則十分可疑。如果你論證有的理論儘管能夠正確預測卻仍然是假的,你似乎已經承認了在別處有判定理論真假的標準。如果沒有任何理論可能為真,單挑出滯止膜理論來說它是假的就沒有意義了。
一般說來,反實在論更多訴諸技術性的分析,實在論者則較多訴諸直覺,他們盡可以在技術性層面上與反實在論爭論,但是最後還是會訴諸直覺。這一點並不奇怪,實在,說來說去首先是一個常識觀念。連貫性、成功預測這些特點是否證實了實在性?按常情想,似乎是這樣。但它們似乎仍然不能算充分的證明。例如,庫恩也注意到科學理論的一個標準是能連貫地解釋很多物質變化,但他不願由此得出實在論結論,只是含含糊糊地說,這種對於概念圖式的信奉是科學中的一種普遍現象,而且看上去是不可缺少的。
看來,物理理論是否在對待實在方面始終存有疑問。這一點不僅可以從有那麼多反實在論者看到,而且,實在論者不斷嘗試通過種種途徑來論證物理學的實在性,似乎也表明這裡的確有疑問。也許,如帕斯卡和迪昂所稱,物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最終也無能證明實在論的信念。

科學實在論
懷疑總是特定的懷疑,對實在的證明總是針對某個特定懷疑的。從而,就能夠接受J.L.奧斯汀的論斷,“實在”不是一種正面屬性,而是一種對否定實在的反駁。“‘但這是真的嗎?這是實在的嗎?’這類懷疑或質問總有一個、必定有一個特定的緣故,”有時會疑問這隻金翅雀是不是真的(real),懷疑這片綠洲是不是錯覺,“……給定語境,有時(通常)明白這個問題提示的是哪類答案:金翅雀也許是個標本,但沒人會設想它是海市蜃樓,一片沙漠綠洲也許是海市蜃樓,但沒人會提議它是個標本。”J.L.奧斯汀,“OtherMinds”,載於《哲學論文集》,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61,第55頁。因此,關於實在性的證明總是有限的證明,總是針對特定懷疑的證明。消除了特定的懷疑,就“證畢”了。如果要求超出特定的懷疑而對實在性提供終極證明,那麼無論是物理學對象的實在性還是任何東西的實在性,都將無能為力。
某一理論所設的對象是否實在,這是科學內部的特定懷疑,是在科學內部得到解答的。某一假說是否真實,如何加以證實,也自有相關科學自己的標準。科學理論所設想的存在物也許不存在,某一假說也許是錯誤的,科學通過自身的發展去處理這些問題。科學理論所設的實體,有時被肯定為真實存在,有時被否定,例如熱素、以太。科學理論所設想的聯繫,有時被證明為錯誤,有時則被肯定為真實。魚鰾與脊椎動物的肺同類,一開始這也許只是“純粹觀念上的聯繫”,但經過物種譜系學的全面發展,經過基因學說的建立,這種同源性得到了充分證明,那不是博物學家編造出來的方便假說,而是自然的真實。夏佩爾曾就構成論的物質觀表達過這層意思。他說,構成論的物質觀並沒有先天的必然性,它可能是錯的,它需要得到證明,問題不在於科學是否是對實在的認識,而在於科學工作中的不同推論如何競爭。夏佩爾:《理由與求知》,褚平、周文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頁。
科學家很少承認自己的全部工作只是操作性的。一個科學理論認定的某種東西可能並不存在,科學得出的任何結論總是可錯的,假說可能被證偽,這些正是科學整體是在探求實在的最好佐證。
但假說是否真能獲得充分的驗證呢?現在是在討論科學內部的特定懷疑,如何消除一種特定懷疑,是在科學內部得到解答的。不過,這裡所涉及的實在問題和平常涉及的實在問題原則上是一樣的。如果一種論證消除了特定的懷疑,其論證就是充分的。能夠更連貫地解釋世界,所預言的事情後來發現果然如此,等等,當然都是判定實在的方法。科學論證實在和平常論證實在的差別只在於,如何判定一個理論是否連貫地解釋了某些特定的物質變化,某個新元素的發現是否確實等等,這些是專家們的事情,是科學內部的事情。
庫恩的範式轉變給人一種印象,覺得那是對實在論的更強烈的挑戰。但即使像庫恩後期那樣,更多強調科學的逐漸演化而非革命性的變革,即使科學是在線性進步,粗糙的實在論也會碰上困難。什麼是線性進步呢?是在不斷接近實在嗎?但若從來不知道實在真正是什麼樣子,怎麼知道自己在接近它?如庫恩本人在其後期反覆強調的,這裡的關鍵是重新澄清一般的實在觀念,而不是在範式轉變和漸進演化之間進行選擇,後者是一個科學史的內部問題,並不涉及一般的實在問題,能認識實在,不斷接近於對實在的認識,還是根本不能認識實在?
說到預測儘管保障了理論的正確性卻並不保障理論的實在性,要討論的是正確和真實這兩個概念的一般同異問題。
上述爭端,以及其他許多爭端,涉及的主要是一般實在概念問題,而不是科學史的專業問題。固然,從科學史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有可能做出別有新意的貢獻,但分清問題的層次,很多爭端會變得比較鮮明可解。
關於實在的爭論,關於真實的爭論,是哲學的首要的、永恆的話題,物理學的實在性爭論是一般的實在問題的一例。例見陳嘉映《真理掌握我們》載於《雲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一期。本文要討論的是:怎麼一來物理學的實在性就成了問題?為什麼古典理論不發生實在的問題?這裡談到對物理學實在性所生的懷疑,是以肯定日常對象的實在性為一般背景的。於是,需要澄清的就是,物理學對象和日常對象有何種不同。問題不是科學怎麼一來就接觸實在了,而是科學怎樣一來就似乎離開了實在。
科學是理論,理論的真實性從來就和日常對象的真實性不同。知道並接受這種區分,所以並不一般地對理論的實在性提出質疑。自古以來人們就從各種角度爭論實在問題,然而,總的說來,希臘人爭論感覺是否實在等等,而理論對象是否實在則不形成一個特殊的問題。古典理論是依賴於經驗的理論,其真實與否可驗之於經驗。當然,經驗、感性是否實在本身也可以成為問題,但那是另一個問題,而不是理論對象是否實在的特殊問題。實際上,哲學-科學本來意在確切認識實在。如果把實在一般地區別於神話、幻覺、主觀感受等等,那麼,哲學-科學正是關於實在的認識的專門發展。
這造成了物理學特有的實在問題。須得警惕,不要把它泛化為一般的實在問題,把假說—預測—驗證—實在當作討論一般實在問題的模式。
然而,科學探索並不滿足於停留在經驗定律上,如柯瓦雷所言:“科學思想總是試圖透過定律到達其背後去找出現象的產生機制”。柯瓦雷:《牛頓研究》,張卜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21頁。機制才是科學所探求的實在。柯瓦雷的這句話本來是要說明,操作態度只是暫時的,科學探求實在,其方式是從定律走到機制,而這就是說,從操作走向真實。
日常世界里有不同種類的存在,同樣,科學對象也以種種不同的方式存在,能量、磁場、夸克的存在方式和電子的存在方式不同。把粒子理解為場,當然不是把它視作某種不實在的東西。場不是空洞的、僅僅具有幾何性質的空間,而是具有物理性質的空間。場就像風一樣實在,只不過在這裡,實在和虛空的截然兩分被取消了,發現質子並不是像米花糖球里的一顆小米花而是更像一個電磁場,這絲毫不減少質子的客觀實在,除非是說,風不像旗子那麼實在。
物理學對機制的描述,包括對微觀物體的描述,依賴於它所特有的一套語言。如在別處陳嘉映:《論近代科學的數學化》載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表明的,這是一套用數學定義的語言,或者乾脆就是數學語言。物理學的實在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數學世界”是否實在的問題。數學世界是不是真實的世界、實在的世界?
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呢?漢語是否真實地描述了世界;可以用漢語真實地描述世界,也可以用漢語歪曲世界。漢語和英語所描述的世界哪個更加真實。會問,漢語的長處何在,漢語的短處何在。一個雙語者在有些場合覺得說甲種語言達意,有時說另一種語言達意。可以像布魯納那樣,把自然語言和數學語言視作“一種特殊意義上的雙語”。
當然,在這裡,必須強調“特殊意義”這一點。語言使用是有規則的,但說話遠遠不止於一種遵守規則的行為。維特根斯坦關於“遵守規則”的研究給語言哲學帶來了很大影響。他本人有一個時期那麼強調語言使用和遵守規則的聯繫,乃至給人要把兩者等同起來的印象。但這不是維特根斯坦關於該問題思考的結論。這裡無法細論,只用一句引文來提醒注意:“在哲學里常常把使用語詞和具有固定規則的遊戲和演算相比較,但不能說使用語言的人一定在作這樣一種遊戲。”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陳嘉映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版,第81節。語詞與語詞之間的聯繫只有一小部分能夠形式邏輯化,它還包含其他多種聯繫,隱喻的聯繫乃至詞源、情感意味、音色、字形之間的聯繫,言說是否通暢入理,所有這些聯繫都在起作用。眼下,把邏輯關係之外的所有這些因素籠統稱之為“感性因素”。而在數學中,只有一樣東西決定符號之間的聯繫是否成立,即數字之間的相互定義。由於數字不再具有感性內容,所以數學表達是充分遵守演算規則的活動。通過努力可以熟練掌握一門外語,最後像母語一樣親熟。也可以通過努力,最後極為熟練地使用數學語言,這意味著,極為純熟地應用一套規則。但數學表達不會成為任何人的母語。
對於英語和漢語,不存在哪種語言描述的世界更加實在的問題。然而,由於數學語言和自然語言是兩個層次上的語言,才出現了哪種語言在描述實在世界的爭論。數學和實在的關係曾一直是雙重的。一方面,理論傾向於區分實在世界和現象世界,理論把握實在,這個實在,強烈地含有“數”的觀念。數遵循著自己的規律循環替代,數世界才是實在,數的運行決定現象世界的展現。另一方面,對自然的純數學處理,曾一直被認作是操作性的。在科學革命時期發生了關鍵的轉折。自然逐漸被理解為用數學語言書寫的。因此,只有數學才能真正把握實在。牛頓曾把萬有引力稱作“數學的力”,那仍然可以被理解為操作性的。但牛頓並沒有放棄萬有引力的“真實的物理的意義”。在《原理》的結尾部分,牛頓反過來直截了當宣稱,reveraexistat,萬有引力實際存在。牛頓仍然在為“數學的”和“物理的”兩者之間的區分苦惱。然而,這裡所發生的並不是牛頓引入了操作定義,彷彿在此外還有對物理世界的真實理解,是對物理世界的基本理解發生了轉變。為方便計而引入操作定義是一回事,由於理解的轉變而不得不重新定義基本概念是另一回事。新物理學家重新定義關於自然的基本概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從數學上處理關於自然的問題。正是牛頓完成了從形而上學到數學物理的關鍵轉變。從今以後,對物理學來說,凡合乎數學描述的,就是實在的,乃至唯有合乎數學描述的,才是實在的。
在伽利略看來,能夠使用數學來描述的兩個直線運動及其合成才是現象背後的真實存在,曲線運動只是現象,乃至只是幻象;就像X光照出來的才是真相,臉蛋兒長得漂亮不漂亮不過是些主觀的感覺。然而,對的感知來說,真實存在的似乎仍是單一的曲線運動,力學分析只是迂迴的假說。早已普遍接受了數學物理的自治,但的自然理解仍然感到“數學的”和“物理的”兩者之間存在區別,這一區別仍隱隱對物理學的實在性提出質問。關於數學世界和日常世界孰真孰幻的爭論錯失了要點。這裡的區別不是真和幻,而是所使用的語言是否可得到直觀的、自然的理解。
在一個平俗的意義上,張三比中國實在:你可以實實在在擁抱張三,但你只能在比喻的意義上擁抱中國。在這個意義上,當然可以說數字所指的東西不像張三所指的東西那麼實在。然而,這裡的差別不是張三和中國是否具有指稱,也不是這兩個詞所指稱的東西哪個更多實在——這種說法不過是把平俗意義上所說的實在轉化成為形而上學的說法,把原本明明白白的話變得無意義或至少意義含混;這裡的差別是具體和抽象的差別,或是在討論哪些概念就理解而言依賴於哪些概念。實數比虛數實在,大概不外乎是說:不掌握實數就無法理解虛數,而不是說,世界上有一些叫作實數的實體卻沒有虛數這種實體。用稱稱出了黃瓜的實實在在的分量,通過計算得到地球的重量,或氫原子的重量,那也同樣是實實在在的分量。
數學通過遠程推理達到某些結論,這本身並無傷於這些結論的實在性。麥克斯韋方程描述的內容無法用自然概念充分翻譯出來,但它仍然是關於實在的方程。世界的一部分真相只能用一種特定的語言表述出來。牛頓的術語並非一般而言更好地揭示了自然的真相,而是適合於讓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自然的某種真相。
不過,數學通過遠程推理達致的結論的確已經遠離了可感可經驗的自然世界。它們由於缺乏自然感而缺乏實在感。但這毋寧是說,隨著理論離開自然世界越來越遠,實在這個概念本身改變了。在數學物理世界里,自然對實在已經沒有多少約束力。這使得在物理學中談論對象的實在性和日常所謂的物體的實在性頗為不同。剛才提到,在日常經驗中,觸覺最能印證實在,而驗證物理學對象是否實在,觸覺很少派上用場。科學理論通常通過觀察來驗證實在,但在很多情況下,所謂觀察也是非常間接的觀察。某個理論是否只是假說抑或它揭示了物質實在的結構,其所依的標準和通常在看得見、摸得著意義上的實實在在有了很大區別。對炮彈確切沿著何種軌跡飛行可以發生種種爭論,但炮彈穿過這片田野的上空卻不會是爭點。然而,如果把電子視作炮彈那樣的實體,電子的很多行為就無法解釋。但這並不意味著電子不具有實在性。不如說,實在這個概念在物理學中發生了變化。玻爾說:“我們依賴於我們的言詞……‘實在性’也是一個詞,一個我們必須學會使用的詞。”轉引自羅傑?牛頓:《何為科學真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頁。在微觀世界里,那裡既沒有經驗也沒有適當的語詞。無法把關於身周物體的實在觀念直接套在物理學對象上。用羅傑。牛頓的話來說:“能滿足我們用日常語言對微觀世界進行實在論描述來代替量子理論並避開‘幽靈般的超距作用’的渴求,看來是無望了。”羅傑。牛頓:《何為科學真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頁。
總體上說,近代科學之所以面對特殊的實在問題,是因為它逐步遠離了的經驗世界。遙遠是由論證的數理力量造成的,數學推理可以一環一環達乎遙遠的結論而不失真,然而,感性卻隨著距離減弱。除了檢查所採用的數理推論的過程是否正確,用實驗結果來驗證推論的結論是否正確,沒有別的辦法確定它所通達的對象是否實在。而如何判斷理論的正當性、判斷其結論是否與實驗結果相吻合,如上所言,是物理學內部的工作。
哲學-科學是關於實在的認識的專門發展。然而,科學在加深對實在的認識的同時改變了一般的實在觀念或真實觀念。就好像現代專業體育的發展改變了體育的觀念,與一般強身健體的原初目的已經相去很遠。關於物理學實在性的爭論,一大半由此而來。
一般認為,換用一個新概念並不會使問題消失,反倒掩蓋了觀念的延續發展,使我們更難看清實質問題所在。物理學的確仍然面對實在問題或曰真實問題。在物理學內部,一個對象或一個理論是否真實始終是可爭論的。在物理學和常識之間,關於誰是實在或誰是首要的實在的爭論也是有意義的,是有重大意義的。
從一開始,哲人就探求實在。他要找到不含雜質的實在。多少世紀以後,通過科學,他終於找到了純粹的實在,它們原來是些遠離實在的公式。這時,他也許幡然醒悟,並沒有不含雜質的終極實在,並沒有不可錯的真理,那個混雜著虛幻和虛偽的世界才是最實在的,必須連同虛幻和虛偽,必須針對虛幻和虛偽,才談得到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