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衛拉特蒙古的結果 展開
- 衛拉特蒙古
- 瓦剌
衛拉特蒙古
衛拉特蒙古
衛拉特(主要內容見瓦剌詞條):元明時期是瓦剌,清朝時期稱衛拉特或厄魯特蒙古,所在主要區域是變遷的。分為四大部:和碩特、綽羅斯(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另有輝特等小部。
瓦剌最早居於葉尼塞河上游,以狩獵為生。13世紀初歸附成吉思汗改畜牧業,至嶺北行省時改營農牧為主漁獵為輔。15世紀中葉形成了強大的衛拉特聯盟,其首領也先汗(1407~1454年)曾取代北元政權而短期統治東西蒙古各部,勢力範圍東起興安嶺,西越阿爾泰山至巴爾喀什湖、蔥嶺,北起安加拉河、貝加爾湖,南抵大漠,成為北元朝滅亡后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最後一股強大勢力。也先被殺后,瓦剌諸部分散於西域。清代時期,有過很大發展,和碩特部4萬人在固始汗率領下到青海於1642年消滅卻圖汗,開始建立和碩特汗國,很快成為青藏高原巨大汗國,臣附於后金和清朝。準噶爾部打敗西域的和碩特部而在1676年實行集權即把衛拉特聯盟變為準噶爾汗國,后被乾隆皇帝打敗。
概念區別:衛拉特與漠西蒙古並不相同,前者是族群類型(可在不同地域演出不同歷史),後者是地域類型,在漠西階段才是漠西蒙古,否則會混淆不同的歷史面貌。
“衛拉特”是蒙語“Oilrad”的漢語音譯,蒙元時期漢語譯為“斡亦剌惕”、“斡亦喇”等,明代漢譯為“瓦剌”,清代漢譯為“衛拉特”、“厄魯特”等。由於在清朝初年時主要分佈在蒙古高原的西部,故又稱為“西蒙古”。
元明時期是瓦剌,清朝時期是厄魯特蒙古,所在主要區域是變遷的。

衛拉特蒙古
我國學術界認為,衛拉特史是元朝蒙古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了解,國際學術界早已矚目於衛拉特,把它視作元朝蒙古的一部分。蘇聯、日本、德國的專家曾先後出版發表探索衛拉特歷史之謎的專著和文章。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學術界對衛拉特史的研究也蓬勃興起。截至1986年,內蒙古、新疆、甘肅、青海、黑龍江、北京等地學者先後發表了300餘篇論文和一批專著,如《論四衛拉特聯盟》《衛拉特歷史文獻》《準噶爾史略》《準噶爾的歷史與文物》以及有關衛拉特的史料摘編等書。
起源
衛拉特蒙古元朝稱為斡亦剌惕,明朝稱作瓦剌,其先世為“斡亦剌惕”。原居住於葉尼塞河上游八河地區。成吉思汗立國時,忽都合別乞領有四千戶。與成吉思汗家族有世婚關係,在蒙古國中一直享有“親視諸王”的特殊地位。14世紀時,以元朝式微,遂乘機擴大勢力,積極參與各派系紛爭。
瓦剌興起
1423年,東部蒙古阿魯台與明廷關係惡化,被明軍擊敗,脫歡乘隙於飲馬河(今克魯倫河)破其眾,俘其大量馬駝牛羊和部眾。飲馬河之捷,使脫歡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得到大大加強,統一瓦剌各部。
1434年,又出兵擊阿魯台於母納山(今內蒙古烏拉山)、殺阿魯台及其子失涅干,盡收其部眾,東西蒙古一時據為所有。脫歡本欲自立為汗,但因他不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遺裔,受到部下的強烈反對。於是擁立元裔脫脫不花為汗,並讓其管轄阿魯台舊有部眾,居住於呼倫貝爾草原一帶;又將己女嫁與脫脫不花為妻,自封太師,居於漠北,直接掌握蒙古的政治、經濟實權。
1439年,脫歡病逝,子也先繼位。也先在位期間,瓦剌進入全盛時期。
瓦剌控制東部蒙古各部,一面又利用軍事征討、封官許願、聯姻結盟等手段,把乞兒吉思、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兀良哈三衛等,分別置於自己統治之下。又結好女真各部,使之為其效力。極盛時勢力東抵朝鮮,西達楚河、塔拉斯河,北括南西伯利亞,南臨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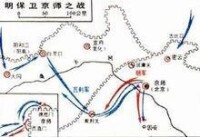
也先攻打明朝
也先與脫脫不花向不相睦。脫脫不花名義上雖然是汗王,但實權卻操在也先手裡,與傀儡無異。也先自恃勢強,垂涎汗位,欲立自己的侄子為“太子”,脫脫不花拒之,雙方關係徹底破裂,兩部爆發激烈戰爭。脫脫不花初與弟阿噶多爾濟聯兵,彼此實力大致相當,難分勝負。后因兄弟內訌,阿噶多爾濟叛投也先。脫脫不花勢單力薄,逃往兀良哈(唐努烏梁海)。脫脫不花死後,也先自稱“天聖大可汗”,建號“添元”,以次子阿失帖木兒為太師。
西蒙古
後來東部蒙古達延汗再興,瓦剌部則移師西北地區,勢力一度擴張至伊犁河流域一帶。為了保證貿易的順利進行,阿失帖木兒還不時遣使向明朝通貢。
也先之後約150年﹐哈剌忽喇興起。哈剌忽喇與馬哈木﹑脫脫不花、也先祖孫一樣﹐亦出身於綽羅斯部。約與其同時﹐還有和碩特部首領拜巴噶斯。二人先後為瓦剌四部盟主。此時瓦剌的分佈地在額爾齊斯河左岸低洼地帶﹐其牧場地可直達伊賽克湖。
清初活動
清代瓦剌分為四大部:綽羅斯(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另有輝特等小部。準噶爾部強勢控制天山南北。明朝崇禎元年(1628),土爾扈特部西遷到伏爾加河沿岸。明朝崇禎九年(1636),和碩特部又在固始汗率領下遷到青海建立和碩特汗國。杜爾伯特部游牧於科布多阿爾泰山一帶。
順治三年(1646),衛拉特蒙古各部首領便派使臣赴北京朝貢,進獻各種物品,表示願與清朝保持良好的政治關係,開展雙方的物質交流。清朝對這些來使熱情接待,賞賜各種物品,表示尊重保持他們原有的政治經濟模式和生活狀況。
順治十年(1653),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之子僧格繼任準噶爾部首領后,不斷派使臣到北京進獻貢物,著力加強與清朝的政治關係和經濟往來。因此,在僧格執政準噶爾部的近二十年中,清、准之間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關係和頻繁的經濟往來,對準噶爾部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康熙十年(1671),噶爾丹繼其兄僧格任準噶爾部首領。時準噶爾部勢力已居衛拉特蒙古諸部之首。噶爾丹上台初年,羽翼未滿,無力與清朝對抗,便繼承其父、兄的政策,繼續保持與清朝良好的政治關係,不斷派使臣到北京朝貢。康熙十一年(1672),派使臣攜帶大批貢品到北京示好,清、准雙方保持著比較好的政治關係,經濟往來也日益有所增多。
1675年噶爾丹打敗和碩特首領,次年集權即把衛拉特聯盟變為準噶爾汗國,1679年,噶爾丹稱“博碩克圖汗”。
噶爾丹執政初年,實施“遠交近攻”策略,不斷對四鄰用兵,擴張地盤。康熙十八年(1679),他先派兵攻佔天山南部的哈密、吐魯番兩地。康熙十九年(1680),噶爾丹趁天山南部的葉爾羌汗國內亂不斷,力量衰落之機,派12萬騎兵從伊犁翻越天山,經阿克蘇、烏什一舉攻入天山南部的喀什噶爾(今喀什)、葉爾羌(今莎車),消滅了延續一個世紀的葉爾羌汗國,使天山以南、昆崙山以北的廣大地區及其生活在這裡的維吾爾等族群眾處於準噶爾的控制之下,不但大大擴張了準噶爾的管轄地域,而且也增強了準噶爾的經濟軍事實力。
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朝為了慶賀平定“三藩之亂”的勝利,顯示自己的武力,特派祁塔特作為使臣,帶領多人和大量財物,到準噶爾的政治中心伊犁進行封賞。噶爾丹對祁塔特一行的到來盛情款待,並回贈了大批財物。次年初,祁塔特返京時,噶爾丹還派專人一路護送。祁塔特的這次出使,更增強了當時清朝與準噶爾之間的良好關係。
隨著統治地域的擴大和軍事實力的增強,噶爾丹妄圖統一全蒙古、重建大蒙古汗國的野心也迅速膨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爾丹率精銳騎兵3萬在擊潰喀爾喀蒙古之後,長驅直入,進兵到離北京僅700里的內蒙古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內),嚴重地威脅到清朝的安全。康熙皇帝親率清朝大軍與準噶爾軍隊決戰。當年陰曆八月二日,雙方在烏蘭布通激戰一整天,清軍先用大炮轟擊準噶爾軍隊的所謂“駝城”,繼而各路軍隊英勇衝殺,攻破敵軍營壘,大敗準噶爾軍隊。噶爾丹率殘軍數千人逃出。此戰使準噶爾軍隊元氣大傷,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清朝北方的軍事威脅。
噶爾丹在烏蘭布通戰敗后,逃往科布多(今蒙古國西部)一帶暫住,經過幾年休整,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集合3萬騎兵進攻喀爾喀蒙古各部。康熙皇帝這次率10萬清軍分路出擊,深入漠北。噶爾丹見清軍人數眾多、勢力強大,在克魯倫河稍一接觸便率眾逃跑。清軍隨後窮追猛打,經3天急行軍,終於在昭莫多地方(今蒙古國烏蘭巴托東南)將準噶爾軍隊阻截包圍,雙方隨即展開激戰。最後,準噶爾軍隊大敗,噶爾丹僅帶幾十名親隨逃脫。此戰幾乎全殲噶爾丹的精銳部隊,從此噶爾丹再無力向清朝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噶爾丹在烏蘭布通之戰和昭莫多之戰中連續失敗后,率殘眾在今蒙古國西部一帶流竄活動,再加上準噶爾政權內部發生政變,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自立為汗,取而代之,後路斷絕,處境日益困難,其部下也紛紛離散。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為了徹底消滅噶爾丹的勢力,第三次親自帶兵出征,指揮前敵諸軍行動。噶爾丹在清朝大軍的圍追堵截下,無處可去,於當年在逃亡中病死。清朝征討噶爾丹的戰爭取得最後勝利。
反擊俄國侵略

準噶爾
康熙末年,清朝與準噶爾為爭奪對我國西北地區的控制權再次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為了配合北部蒙古高原和南部西藏方面清軍的作戰,駐巴里坤的西部清軍也向天山東部兩側的烏魯木齊和吐魯番的準噶爾軍隊發動進攻。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軍隊在散秩大臣阿喇納等人率領下進軍吐魯番,當地準噶爾軍隊或死或降,迅速瓦解。
在準噶爾的發展壯大過程中,不斷與四鄰的一些民族發生衝突,與當時游牧於中亞地區的哈薩克人為了爭奪牧地人畜的衝突更是頻繁。雍正元年(1723)春,哈薩克草原上大雪成災,準噶爾的軍隊向游牧於塔拉斯河谷地的哈薩克人發動大規模突然襲擊,毫無防備的哈薩克人毫無抵抗能力,倉猝間只得丟下牲畜、財物四散奔逃。準噶爾軍隊佔領了原由哈薩克人控制的中亞重要城市塔什干、土爾克斯坦等。通過這次軍事行動,準噶爾的管轄地域不僅進一步擴大到中亞廣大地區,而且迫使哈薩克的一部分部落臣附自己,策妄阿拉布坦也因這次戰爭的勝利而把準噶爾推向了一個新的強盛時期。
額爾德尼昭之戰
從雍正七年(1729)起,清朝與準噶爾之間的武裝衝突再起,互有勝負。雍正十年(1732),準噶爾軍隊主力在噶爾丹策凌親自率領下攻擊喀爾喀蒙古各部,遭遇副將軍策凌所率2萬名清軍的反擊,遂退守額爾德尼昭(亦稱“光顯寺”)地方,依山傍河列陣,以圖阻擊清軍的進攻。策凌率追兵到達此地后,分兵兩路,一支正面攻擊牽制敵軍,一支繞到敵後山頂自上而下攻擊。雙方激戰一整天,準噶爾軍隊在前後夾擊下潰敗。此戰準噶爾軍隊死傷萬餘人,元氣大傷,噶爾丹策凌乘亂逃出,清朝取得對噶爾丹策凌執政準噶爾時期戰爭的決定性勝利。額爾德尼昭之戰後,清、准雙方開始談判,雙方關係進入一個相對友好平靜的時期。
清朝使臣阿克敦伊犁之行
雍正十年(1732)額爾德尼昭之戰後,清朝與準噶爾之間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告一段落,雙方又開始互派使臣,暫時和好。雍正十二年(1734),清朝派內閣學士阿克敦等作為使臣,赴準噶爾的統治中心伊犁,商討劃分雙方牧地。次年,阿克敦與準噶爾使臣那木喀一起返回北京。由於雙方談判未果,乾隆三年(1738),阿克敦作為清朝使臣再次出使伊犁,與準噶爾首領噶爾丹策凌等進行商討,但由於雙方意見不一,仍未達成協議,不得不與準噶爾汗國使臣哈柳一起又返回北京。在談判中,阿克敦堅持以阿爾泰山作為雙方牧界,最後清、准在乾隆四年(1739)達成的協議中基本接受了這個方案。阿克敦在這次清、准談判中來往奔波,努力調解,為雙方良好關係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作了大量工作。
乾隆四年(1739),準噶爾與清朝經過談判劃分牧界后,雙方關係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良好發展時期。噶爾丹策凌經過幾年的努力,很快擺脫額爾德尼昭之戰失敗的陰影,便利用這個時機,率軍分兩路攻打相鄰的哈薩克的中玉茲和小玉茲兩大部落,並取得勝利,進一步擴大了在中亞及哈薩克草原的管轄地域,使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都納入了準噶爾的版圖,也使準噶爾進入了一個新的強盛時期,為後來清朝統一新疆后在我國西北地區疆域的確立打下了基礎。
和碩特崛起
明朝崇禎九年(1636),和碩特部又在固始汗率領下遷到青海,1642年消滅卻圖汗,開始建立和碩特汗國,後來成為青藏高原巨大汗國,從屬於后金和清朝。
準噶爾衰落

達瓦齊像
特蒙古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於乾隆十七年(1752)殺死噶爾丹策凌的長子喇嘛達爾札,奪取汗位,執政準噶爾。準噶爾在近十年的內亂中,力量大為削弱。達瓦齊上台後,殘殺異己,荒淫無度,弄得眾叛親離,民眾怨恨,最後與曾支持他上台的阿睦爾撒納也發生衝突,使阿睦爾撒納在爭權鬥爭失敗后投奔清朝。達瓦齊的倒行逆施,使準噶爾迅速衰落。1753年,杜爾伯特部歸屬清朝。1754年,阿睦爾撒納歸屬清朝。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皇帝聽從阿睦爾撒納等人的建議,發大軍5萬,順利進抵伊犁,在格登山合殲準噶爾軍隊,一舉消滅了準噶爾政權,遂后擒獲準噶爾的最後一位汗達瓦齊,取得統一包括今新疆在內的我國西北廣大地區戰爭的決定性勝利。當年,土爾扈特部遷回新疆,史稱土爾扈特部東歸。
準噶爾政權滅亡后,阿睦爾撒納妄圖作衛拉特蒙古各部的“總台吉”,為清廷拒絕,遂起兵反叛,殺死留駐伊犁的清朝官兵。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朝出兵平叛,阿睦爾撒納不敵四處流竄。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爾撒納經哈薩克草原逃到俄羅斯軍隊控制的地方,旋病死,清朝取得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的完全勝利,從而確立了對天山以北廣大地區的直接治理權。
衛拉特早期稱瓦刺,蒙古帝國或元朝時代,衛拉特人繁衍生息於葉尼塞河上游地區,成吉思汗興起后,成為蒙古帝國的一部分,被劃分為四個萬戶。元朝末年明朝初年,其社會發展迅速,部眾人口猛增至四萬餘戶,領地也大有擴張。除了原來的葉尼塞河上游廣大地區外,已西越阿爾泰山,擴張到額爾齊斯河上游,西南與哈密、別失八里相鄰,東南進入扎布汗河流域與東蒙古(韃靼)相接,北邊與乞兒吉思為鄰。
佛教早在蒙古帝國時期即已在蒙古人中有所傳播。蒙古統治者出於鞏固與穩定政權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1246年,蒙古闊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與西藏薩迦派四祖薩班(1182~1251年)在涼州會晤,藏傳佛教始傳入蒙古,薩班並被蒙古統治者確立為西藏各地僧俗的領袖。闊端也成為最早皈依藏傳佛教的蒙古王室成員。不過,當時藏傳佛教還遠沒有像後來那樣居於獨尊地位。在忽必烈繼位之前,蒙古統治者對宗教採取的是兼容並蓄政策,而居於主導地位的應為來自漢地的禪宗,如“歷事太祖、太宗、憲宗、世祖,為天下禪宗之首”的海雲和尚,在蒙哥(1251~1260年在位)時即受命“掌釋教事”。《佛祖歷代通載·海雲法師傳》還記載了海雲法師為國家祈福事:
乙巳(1245年),奉(元太宗)六皇后旨,於五台為國祈福……丁未(1247年),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海雲)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丙辰(1256年),奉(蒙哥)聖旨,建回於昊天寺。
這些說明,在忽必烈奉佛教之前,海雲法師已在朝廷多有活動,影響不小。
此外,嵩山少林寺禪宗大師福裕亦被邀至“北庭行在”,講經累月。蒙哥汗時期,以福裕為代表的佛教和以李志常為代表的道教互相攻擊,雙方都標榜自己的教義最正確。為了平息這場爭論,蒙哥汗於1256年下令在和林舉行御前辯論,以決勝負。最終,蒙哥汗認為:“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宣布以禪宗為代表的佛教取得勝利。直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后,蒙古統治者的佛教信仰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他先後敕封薩迦派五祖八思巴(1235~1280年)為國師、帝師,統領全國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許多皇室貴族都紛紛皈依帝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舉措將藏傳佛教薩迦派很快推向極致,使其以凌駕於佛教其他各宗派之上的特殊地位而蔓延全國。
1953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庫蘇古爾省阿爾布拉格縣發現《釋迦院碑》(又稱《蒙哥汗碑》)一通。該碑立於元憲宗七年(1257年),以回鶻式蒙古文和漢文鐫刻,系斡亦剌惕“奉佛駙馬八立托”與公主為慶祝憲宗蒙哥五十大壽而勒立的,以示“廣興喜舍之心……重發菩提之意”,旨在酬謝皇恩,祈佛保佑,使“國泰民安,法輪常轉”。該碑的發現,證明早在13世紀中葉,衛拉特中即有佛寺——釋迦院——存在。此外,據載,貴由汗(1246~1247年在位)的皇后海迷失是衛拉特人,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由於當時蒙哥汗推崇的是漢地禪宗,以理度之,當時衛拉特封建主接受的亦當為禪宗。《釋迦院碑》的發現即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同時,我們可以認為該寺“很可能是邀請漢僧主持建造,並由漢僧主持”。不過,在那個時代,佛教在衛拉特中的傳播主要局限在貴族階層,影響不大,普通百姓則大多信仰蒙古族的傳統宗教——薩滿教。故終元一代,衛拉特佛教絕少見於史書的記載。
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在衛拉特中的發展與興盛,最早可追溯到15世紀30年代,與衛拉特統治者脫歡、也先父子的支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明初,衛拉特部開始崛起,當時其首領為猛哥帖木兒。建文四年(1402年)左右,猛哥帖木兒去世,衛拉特被分為三部,由馬哈木、太平和把禿孛羅分別領屬,其中以馬哈木力量最強,曾派使入明朝貢。永樂七年(1409年)五月,明成祖分別封三部首領為順寧王、賢義王和安樂王。永樂十六年(1418年),脫歡繼馬哈木之位襲順寧王爵。這是一個富有政治抱負的蒙古貴族,他在位期間,勵精圖治,經過連年征戰,先後擊滅太平和把禿孛羅所部,統一了衛拉特。接著,與脫脫不花聯合,擊敗東蒙古北元政權中掌實權的和寧王阿魯台,使分裂既久的東西蒙古復歸於統一。脫歡本欲自立為可汗,但迫於當時根深蒂固的正統觀念,只好擁立“黃金氏族”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脫脫不花可汗充當傀儡,而自任太師。在其晚年,加強了對佛教的利用,並有意提高喇嘛在衛拉特社會中的地位,這在明朝史料中有側面反映:
正統二年(1437年)十二月甲子,命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哈馬剌失力為慈善弘化國師,大藏為僧錄司右覺義,答蘭帖木兒等指揮、千戶、鎮撫等官。初,哈馬剌失力自陳屢來朝貢,厚蒙恩齎,乞賜名分,以便往來。行在禮部以聞,故有是命,仍賜哈馬剌失力僧衣一襲,及答蘭帖木兒等冠帶。
正統三年(1438年)正月丙戊,命瓦剌使臣兀思答阿里為都指揮僉事,僧人也克出脫里也為都綱,賜冠帶僧衣等物。
這一記載說明,脫歡不僅信仰佛教,而且還以僧侶為使臣前往明朝,進行外交活動。明英宗對其使臣哈馬剌失力一行來朝一事相當重視,厚加封賞,封哈馬剌失力為“慈善弘化國師”,大藏為“僧錄司右覺義”,並“賜哈馬剌失力僧衣一襲”。這些記錄足以證明當時佛教在衛拉特人中是被抬得相當高的。
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子也先繼位,稱太師淮王,同時也秉承了先父優恤佛教的政策。正統十一年(1446年),他上書明廷,要求提高喇嘛的地位:
瓦剌太師也先所遣朝貢灌頂國師剌麻禪全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並銀印、金襕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畫像、鈴杵、鐃鼓、纓絡、海螺、咒施法食諸品物。事下禮部議。尚書胡瀅等以為稽無舊例,請裁之。上曰:“朕撫御外夷,一惟祖宗成憲是式,今也先妄求,既無舊例,豈可勉徇,其勿予。”
看來,也先之請並不如其父那樣來得順利,被明政府以前無舊例可循而予以拒絕。正統十四年(1449年),也先糾合各部眾,分兵四路進攻明境。明英宗倉促應戰,御駕親征,在土木堡遭到襲擊而被俘。此役使也先的勢力大為擴張。也先借其餘威,遂再於景泰三年(1452年)重提十年前曾被明廷拒絕的要求。史載,是年十一月庚申:
又別為其國師三答失禮、番僧撤灰帖木兒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帳房、金印、銀瓶、供器等項,俱不允。結果仍然未得應允。
為什麼父子之請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結果呢?究其原因,應與此時也先勢力擴張過快,引起明政府的警覺與擔心有關,以此之故,明政府也加強了對蒙古人所信奉的藏傳佛教的戒備,故而對藏傳佛教由支持專為排斥。
景泰四年(1453年),也先襲殺傀儡可汗脫脫不花自立,稱“大元田盛(天聖)可汗”。但命運乖舛,次年便被阿剌知院擊殺。也先之死,導致了衛拉特政權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東西蒙古短暫統一局面的結束,代之而起的是北元王室的重新崛起。成化六年(1470年),巴圖蒙克被立為大汗,稱達延汗。繩其祖武,經南征北戰,不久又重新統一了漠北,衛拉特不得不退回西北一隅,即使如此,還不時受到東蒙古貴族的軍事進攻。為了應對這種被動局面,陷於分裂的衛拉特四部:綽羅斯(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於15世紀後期,經過重新磨合,結成衛拉特聯盟以對抗來自東蒙古的威脅。其中以準噶爾為首,但互不統屬。
衛拉特聯盟時期,喇嘛仍然受到統治者的優遇。在《1640年蒙古衛拉特法典》之前形成的一部法典——學界習稱《衛拉特舊法典》——中有這樣的內容:同僧侶的通姦完全不受處罰,而普通人的通姦,姦夫應交出四歲馬一匹給喇嘛傳令吏。這裡的僧侶、喇嘛,顯然指代的都是黃教傳進以前的各派喇嘛。這也足以說明,也先死後,即15世紀後期到16世紀前半期,藏傳佛教在衛拉特中的傳播還是相當廣泛的。
其後不久,西藏黃教即漸次傳入衛拉特各部,新疆佛教的面貌也隨之大為改觀,邁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吾人固知,衛拉特是游牧民族,而佛教戒殺生、戒爭鬥的教義肯定會與其騎馬射獵、尚勇好武的習俗存在牴牾之處。那麼,衛拉特人又何以不遺餘力地尊崇佛教呢?我認為應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一、蒙元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利用藏傳佛教作為精神統治的武器,故對藏傳佛教極力推崇,甚至將其定為國教。衛拉特上層與元朝皇室,世聯婚姻,有的成為皇室的駙馬,有的受到蒙古皇室的加官封爵,受其影響皈依佛門自屬情理中事;二、衛拉特與沙州、罕東、赤斤三衛蒙古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繫,也先曾“遣人偽授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都督喃哥等為平章等官,又擅置甘肅行省名號,意在邀結夷心”。這三衛蒙古人都是藏傳佛教信徒,其統治者往往以喇嘛為使臣與衛拉特往來,“交往深密”,也促進了衛拉特封建主對佛教的接受。此外,與衛拉特關係密切的哈密及泰寧、朵顏、福余兀良哈三衛也都是藏傳佛教的興盛之地,而且都曾受到衛拉特首領也先的控制,故其佛教對衛拉特產生影響亦當情理中事;三、黃教倡導生死輪迴、善惡相報之說,鼓吹今生尊佛積善,來世可以修成正果,並宣稱蒙古貴族——諾顏就是前生行善而轉生成正主的,與“神”的地位相等。這些說教自然符合蒙古貴族的利益;另一方面,處於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勞苦大眾之所以受貧受欺,同樣也是前世行為之果,因作惡而在今生得到了惡報。此說掩蓋了衛拉特社會階級差別、貧富差別的本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勞動人民忍受、順從,放棄改革現實生活的鬥爭,有利於穩固衛拉特封建主的統治,比蒙古人原來尊奉的薩滿教更符合於統治者的需要,故而得到衛拉特封建主的倡導。
黃教是15世紀初在西藏興起的一個喇嘛教派系。當時,藏傳佛教各派戒律廢弛,僧人追逐世俗權利與財富,引起信譽危機,有鑒於此,宗喀巴倡導宗教改革,主張依據噶當派的教義,要求僧侶嚴守戒律、終身不娶、脫離農事,嚴格寺院組織與管理制度,使世俗貴族不能操縱寺院事務;主張顯密並重,強調顯密兼修及先顯后密的修行次第,故被稱為格魯(善規)派。又因該派僧人戴黃色僧帽,俗稱“黃教”。
16世紀,東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將衛拉特勢力逐出杭愛山之南,又進兵青海,驅逐了衛拉特在那裡的勢力,逼迫衛拉特將其活動中心局促於天山南北一帶。萬曆元年(1573年),黃教首領鎖南嘉措應邀抵達俺答汗在青海的駐地。俺答汗皈依黃教,成了護法王,並授予鎖南嘉措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之號。達賴之名,由此而始。這一事件標誌著蒙古開始接受黃教,在蒙藏佛教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接著,東蒙古其餘各部也相繼改宗。在達賴三世鎖南嘉措的授意下,俺答汗的孫子云丹嘉措成為達賴四世。一位蒙古人坐床拉薩,成為黃教的一代教主,這對蒙古佛教信徒而言,不啻為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而對黃教來說,此舉也必然為爭取更多的信徒開闢了廣闊的道路。於是乎,黃教更如洪水一樣,迅速漫及東西蒙古的所有部落。但由於衛拉特“同西藏沒有直接聯繫,以及跟東蒙古執政者不和”,黃教在衛拉特中的流行要比東蒙古晚了不少。
黃教與衛拉特的最初接觸,庶幾乎可追溯到17世紀初葉,系由東蒙古傳入。佚名氏著托忒文《和鄂爾勒克歷史》對此作了如下敘述:
在喀爾喀烏巴什琿台吉時邀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到蒙古地方,從此蒙古人開始皈依佛教。以後衛拉特人在拜巴噶斯時代請了察罕諾們汗呼圖克圖。呼圖克圖創造了托忒文字,給大家教書,使大家了解佛法的精義。同時傳播醫學和其它學問。這樣,衛拉特人對佛法就更加深信不疑。
上述引文中所說的佛教無疑是指黃教,察罕諾們汗即哲布尊丹巴,系喀爾喀黃教教主的封號,烏巴什琿台吉即碩壘烏巴什琿台吉。碩壘烏巴什琿台吉時,黃教在喀爾喀部已有流布,但當時哲布尊丹巴一世尚未出世,因此引文所說的哲布尊丹巴不可能是哲布尊丹巴一世,而只能是哲布尊丹巴一世的前身,即庫倫掌教大喇嘛扎阿囊昆噶寧波。扎阿囊昆噶寧波原是西藏大喇嘛,四世達賴在位時,曾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計劃在土拉河畔的庫倫設置一名坐床掌教大喇嘛,以弘揚佛法,但未派人前去。後來,拉薩黃教各大喇嘛公推扎阿囊昆噶寧波前去就任此職。他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抵達庫倫(今烏蘭巴托)。臨行,達賴四世賜以“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之號。大喇嘛由西藏而住持蒙古,應以此為鎬矢。扎阿囊昆噶寧波被選為蒙古掌教大喇嘛,宣傳教旨,靈異昭著,受到了喀爾喀人的極度尊信,被尊以大慈諾們罕之號,並上“博碩克圖濟農”號,為轉金輪徹辰濟農汗。崇禎六年(1633年)圓寂於蒙古之庫倫。扎阿囊昆噶寧波圓寂后,“轉生”為哲布尊丹巴一世,駐錫庫倫,仍為掌教之大喇嘛。
通過上文的考證,可以看出,衛拉特人最初皈依黃教,當在扎阿囊昆噶寧波於1614年抵達庫倫后不久。日本學者若鬆寬進一步考證認為,黃教正式傳入衛拉特蒙古之年應是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時當俺答汗皈依黃教之後的第42個年頭,可以信從。
拜巴噶斯“聽取了察罕諾們汗講授的有關情器世間必將毀滅的道理,決心脫離無常之根”,遂發願出家為僧。由於那時拜巴噶斯是四衛拉特的領袖,故其出家念頭受到所有衛拉特王公貴族的反對。眾人問察罕諾們汗:“是一個人當喇嘛福大,還是眾人當喇嘛福大?”呼圖克圖回答:“眾人當喇嘛福大”。於是四衛拉特王公決定每人派一個兒子代替拜巴噶斯當喇嘛。這些王公有:烏巴什汗、杜爾格齊諾顏、楚庫爾、哈喇呼喇、巴圖爾琿台吉、墨爾根岱青、土爾扈特的和鄂爾勒克、羅卜藏、墨爾根托木尼、杜爾伯特的達賴台吉、輝特的蘇勒坦台什等,每人出一個兒子,總共有32個王公的兒子當了喇嘛。同時還從庶民中選了200個男孩子作為上述王公孩子的侍從,也當了喇嘛。這些人被送到安多學習,不久又被送到拉薩求學。拜巴噶斯當時還沒有兒子,便從和碩特巴巴汗諾顏的兒子中認了一個義子,獻出當了喇嘛,這便是後來聲名卓著的咱雅班第達。
衛拉特諸部之皈依黃教,使黃教勢力更為壯大,引起了藏傳佛教其他教派的擔憂與警惕,遂與世俗權力聯合起來試圖予以遏止,其中最突出的例證就是后藏藏巴汗及其聯盟對黃教的反對與抑制。也就在這一時期,衛拉特部的勢力又逐步滲透到青海地區,與黃教有了更密切的接觸。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大力量來自和碩特部的顧實汗。
顧實汗本名圖魯拜琥(tho-rol-pā’i-hu,1582~1655年),是和碩特部著名首領哈尼諾顏洪果爾之子,拜巴噶斯汗之弟,自小即以勇武著稱。據傳,他13歲時曾領兵擊敗了“白頭回回”的4萬士兵,“威名大振,所向無敵”。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喀爾喀與衛拉特之間產生衝突,戰爭一觸即發,為了消弭這場戰爭,他冒生死前往調解,獲得成功,東科爾胡圖克圖與喀爾喀首領們對其活動極為推崇,共贈其“大國師”的稱號。顧實汗實即“國師汗”之音轉。
天啟五年(1625年),顧實汗以熬茶為名,秘密到后藏參加了羅桑卻吉堅贊主持的吉祥法會。羅桑卻吉堅贊賜給他“顧實·徹辰綽爾濟”之號,並說:“是贊助我蘇瑪第·吉爾第教之高徒也。此後,汝之事業將獲昌盛!”顧實汗原駐牧於天山北路,此時已率部到轉牧於天山南路,本有襲據青海之意,此時正好獲黃教首領的邀請,遂乘機於1636年初率部到達青海湖畔,答應保護黃教。這次會見,標誌黃教護法權由東蒙古向西蒙古之轉移。
在此之前,西藏地方首領藏巴汗率六路大軍進入拉薩,黃教慘遭踐踏;而在青海,喀爾喀部首領卻圖汗也嫉視黃教,故而響應藏巴汗的請求,遣其子阿爾斯蘭率兵一萬,侵入衛藏,公開聲稱他們是“黃教的敵人”,以為藏巴汗之奧援。他殺害了西藏的三位大汗,非常“仇視佛教,尤其是破壞格魯派最為激烈”。故黃教上層遂於崇禎八年(1635年)向衛拉特求援。衛拉特的王公貴族立即召集“丘爾干”(蒙古語意為“會議”“會盟”),決定答應黃教首領的請求,“一致表示:拜達賴喇嘛為上師。他們說:‘難道藏族人不都是達賴喇嘛的子民嗎?衛拉特人不必縮手縮腳,要把他們安置到他們願意去的地方。’”衛拉特王公的這一決定,不僅僅是為了護教,同時也是出於自身發展的需要。因為自16世紀末以來,衛拉特周圍處在敵對力量的夾擊之中,東方受喀爾喀蒙古的攻擊,西面與哈薩克族也時常發生衝突,南方與察哈台後王有矛盾,北面又受到沙俄的侵擾與遏制,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加劇了諸部的矛盾。出兵西藏,既可緩解內部的矛盾,擴大自己的勢力、地盤與影響,又可得到西藏黃教勢力的支持。當時,雖為衛拉特盟主,但卻受到準噶爾排擠而早有另尋牧地打算的顧實汗對丘爾乾的決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崇禎九年(1636年)初,衛拉特大軍由顧實汗、巴圖爾琿台吉、墨爾根托木尼、吉魯圖爾台吉四人率領,從烏魯木齊一帶出發,南下遠征青海,翌年擊滅了卻圖汗。卻圖的覆滅,對西藏黃教諸法王來說,暫時避免了一場災難,對衛拉特人來說,使其對青海的佔領成為事實,同時也使其與黃教寺院集團的直接接觸進一步加強,正如義大利著名藏學家杜齊所言:
顧實汗強大的游牧部落緊靠西藏邊境,顧實汗的虔誠與專一信仰使他本人多少享有不無誇張的威望。不但黃教的上層與顧實汗之間的信使往來趨於頻繁,而且黃教的僧侶經常被召集起來為這位蒙古大汗的軍隊舉行宗教儀式,祈求神佑。然而,卻圖汗的滅亡,無論對衛拉特還是對黃教來說,都不是最後的勝利,因為勢力更大的藏巴汗還毫髮未損,不僅未因卻圖汗的滅亡而改變對黃教的政策,而且對黃教的仇視進一步變本加厲。崇禎十一年(1638年),顧實汗以香客的身份從青海來到拉薩,在大昭寺拜會了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決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共同派兵到盛京與清皇太極取得聯繫;二是清除青、康地區敵對勢力;三是共同摧毀藏巴汗地方政權。在顧實汗返回衛拉特部前,達賴與班禪又贈他以“丹增卻吉傑波”(bstan-’dzinchos kyi rgyal po)的稱號,意為“護教法王”。崇禎十四年(1641年),擊殺藏巴汗,其聲望“威鎮后藏、阿里、康區、安多、五色四夷、漢蒙衛拉特。顧實汗讓他的兒子和外甥扶持了佛教,立下了豐功偉績”。
擊滅藏巴汗后,迎五世達賴坐床拉薩,治前藏;上羅桑卻吉堅贊“班禪額爾德尼博格達”的尊號,坐床於扎什倫布寺,建立了班禪活佛系統,治后藏。從此衛拉特之護法王地位得以確立,護法王由和碩特部擔任。
顧實汗出兵西藏,意義重大。戰後,顧實汗沒有離開西藏,也沒有把西藏交給黃教寺院管理,而是在布達拉宮直接通領全藏和青海的行政、軍事,並擁有任命第巴的特權。自此以後,和碩特汗廷與達賴、班禪共同掌握西藏宗教事務,歷四代五汗,計75年(1642~1717年),使黃教在西藏樹立了牢固的統治地位。達賴喇嘛利用既得利益的優勢,搶奪其他教派所屬的封地與寺廟,強迫其他教派改宗黃教,使黃教的勢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為了進一步加強黃教的優勢地位,顧實汗極力促使達賴五世與清政府加強聯繫。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他遣使向清政府奏言:“達賴喇嘛功德甚大,請延至京師,令其諷誦經文,以資福佐。”順治九年(1652年)正月,顧實汗再度“以勸導達賴喇嘛來朝,奉表奏聞”。同年十一月,達賴五世率班禪及顧實汗的代表來到北京,受到順治帝的隆重接待,並齎送金冊、金印,封達賴五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亦喇坦喇達賴喇嘛”,冊文、印文均以滿、蒙、藏、漢四種文字寫成。從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確認了達賴喇嘛在蒙藏地區的宗教領袖地位。
顧實汗的巨大成功,無疑會加速衛拉特社會黃教化的進程,促進衛拉特封建貴族與黃教首領的政治聯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