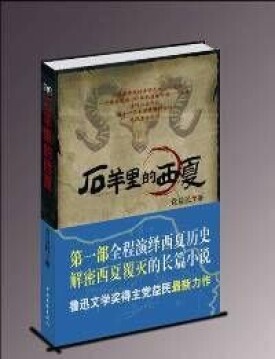石羊里的西夏
2008年黨益民所著書籍
西夏史本身是一部絕學,“遺跡的泯失,史料的闕如”。但作為黨項後裔的黨益民,書寫西夏歷史肯定是一重情結。並且我們也已經厭倦了大唐大漢大明大清的興衰。於是可以跟著黨益民的文字去看一看西夏——一座繁榮了兩百年的帝國,何以如同人間蒸發,是仇恨?是報復?或者也僅僅只是歷史的巧合?
黨益民在寫《石羊里的西夏》時,做了6年的準備工作,手頭常年備著一張西夏地理圖、一張西夏都城圖,一張人物關係圖。作品的初稿在06年初就已完成,然後作者有意無意地將他擱置起來,叫文字冷卻、陌生,這種刻意的冷靜剛巧使作品避開了異族歷史文化書寫時那種神秘傳奇的濫觴。雖然在小說中我們依然可以讀到羌寨、古碉樓,“釋比”老人,但他們只是和情節同構在一起,並不以取悅我們的獵奇心為樂,並且在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並沒有刻意迴避自己民族的劣根性。於是這種自覺本身,就看出寫作者很大的勇氣和獨立了
讀《石羊里的西夏》時,更讓人迷信一點:“作者是被選定的人,至於寫什麼,實在像極了一場召喚。書寫在更大的意義上,就是一種輪迴。血液里的東西肯定是要流的更遠的。”所以石羊也只是一個借口。在這借口之後的歷史,那些隱痛,幾乎結了痂,但是,黨益民生生將它們扒開了,叫一場祭祖本身更顯血腥真實,他從寫西夏滅亡前的20年寫起,試圖找到滅亡前的種種徵兆、歷史在極深處那些似曾相識的密碼,雖然這種尋找在文章最後也變得模稜兩可。正如小說結尾講到的那樣,在異常華麗地重構了西夏王朝的同時,作者也不無唏噓:“不知道自己真的擁有過一部西夏秘史,還是僅僅只是剛才的一個夢。”
於是這樣的結尾,就不光是作者一人的唏噓了。我一口氣讀完小說,被歷史的橋段、陰謀、滑稽、無可奈何喂的飽飽的。但另一方面,也覺得人有些虛脫,類似南柯一夢醒來后的那種虛脫。大夢一場,急管繁弦、鑼鼓錚錚,但是在小說的最後,被當頭棒喝。也許所謂歷史,根本就是空無一物,對整部歷史的重構,無論怎樣險象環生,搞不好也只是子孫的錯覺,關於前人的徹底的對錯和出路,也依然是不存在的。
所以作者這種在結尾彷彿無知無覺的將自己看低,在歷史興衰復滅的真相面前依然束手無策、無限惶惑,這就需要克服內心巨大的虛榮,他還算沒有以文字的方式賣掉自己的民族,雖然這種出賣我們多少都有些司空見慣了。
所以也發現,有時寫作最弔詭而惡毒的地方是:你越去做個全知全覺的人,你越會不知不覺地成為一個可笑的人。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角色接近文字,這絕對是個問題。
也慶幸黨益民帶給我們的不是什麼自戀的全知全覺的東西,他在小說最後抓了一下歷史的那種虛空,並且克制了講述自己祖先時的一種精明,這種含蓄剛巧使作品成功的繞開了一種愚蠢的歷史書寫。“我們很可能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關於歷史的寫作,本身就容易陷入一種民族情緒。這種情緒一方面狹窄,但另一方面,又十分飽滿。兩廂疼痛,壓迫著書寫著滑入一種有效的、狡猾的、精良的通道里,所有關於民族的信念、觀點、甚至偏見都已經歷史性的擺在那裡了。於是不小心就會成為自戀的文明的複製品。
因為不去全知全覺,於是《石羊里的西夏》算是一部非常善良的作品,在善良背後,小心翼翼地隱藏著作者關於西夏王朝所有荒蕪、狂亂、蒼涼、荒唐的畸想。雖然讀過小說,我也依然不清楚這個曾經縱橫馳騁於長江北的鐵蹄,怎麼會陷落在中土田園的夕陽里。但是清楚與否也已意義不大,這又是另一種虛空了,永遠不要指望從歷史本身得到什麼答案。因為不指望得到什麼答案,於是小說里也看不到太多地道德評判,也許在歷史面前,道德本身是毫無用處的吧。所有裹挾在歷史中的謊言和真相,並同全部的生命和人情世故,我們都可以一併的,在合上小說之後,喘一大口氣,就算是將它撕碎洞穿了。畢竟所有地歷史在被人演繹之後肯定失真,我們所有人也只有承認它的失真,才有可能離歷史稍微地近那麼一點點。
瑕疵:小說的開頭,勉強觸及了一下5·12大地震,多少還是暴露了一點寫作者在文化市場面前的不自信和對文化市場本身的不相信。
黨項人原本和羌族同宗,唐代以前一直居住在四川汶川、茂縣一帶。其後的兩宋時期,遷出故地的黨項人勵精圖治,建立起雄踞西北的西夏王朝(1038~1227),先後與兩宋、遼、金等政權鼎足而立。1227年,西夏王朝在蒙古鐵騎的踐踏之下土崩瓦解,人民被屠殺,大量有關資料、文物不知所終。近八百年來,由於史料闕如,這個盛極一時的王朝一直在歷史的風煙中若隱若現,沒有人能夠窺見其廬山真面目。
黨益民,陝西富平人,1963年生,魯迅文學獎得主,訴訟法學研究生,武警交通二總隊副政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先後40餘次進藏,12次立功。出版長篇小說4部,散文集1部,長篇報告文學1部。其中:長篇小說《喧囂荒塬》獲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巴金文學院優秀作品獎;長篇小說《一路格桑花》入選新聞出版總署向全國青少年推薦的“百部優秀圖書”;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獲第十屆全軍文藝新作品一等獎,第四屆報告文學“正泰杯”大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2004—2006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買下這尊石羊時,我絕對沒有想到其中會隱藏著一個天大的秘密。
三天前,我才從汶川地震搶險救援一線回來。那裡的龍門山斷裂帶,是我們黨項人的同宗羌族的聚集地。西夏立國前的唐代,我們的祖先就生活在那裡,西夏滅亡后他們又回到了故地。那裡的汶川、茂縣、理縣、北川、丹巴的羌寨被譽為“雲朵上的村落”,歷經千年滄桑的碉樓被稱為羌族建築的“活化石”。然而,“5.12”大地震卻改變了那裡的一切,奪去了那裡八萬同胞的生命,蘿蔔寨等許多羌寨被夷為平地,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館中的四百多件羌族文物被毀,許多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人也在地震中遇難。所幸的是,那裡最具羌族特色的古碉樓只有三座出現裂縫、樓尖部分垮塌,其他都完好無損。我在桃坪羌寨親眼看見,古碉樓背後著名的“魚脊樑”沒有一絲裂縫。
汶川地震過去整整一個月了,但我還沒有完全從悲傷的情緒中走出來。現在,我正在努力恢復以前的生活狀態。
這天早上,我在元大都跑步時遇到了一個男人。那男人說,他是地鐵十號線工地的民工,地鐵就要通了,他要回老家收麥子了。可是奧運會馬上就要開了,現在安全檢查可嚴了,要是帶著一件寶貝回家,肯定會在火車站被警察逮住,說不定還得坐牢。我聽他說得玄乎,便起了戒心,懷疑他是我們常見的那種騙子。但時間尚早,我用不著急著回家,便問他什麼寶貝。他神秘兮兮地從懷裡掏出一個東西,說是元朝時期的石羊,一個月前在地鐵里施工時挖出來的。地鐵十號線沿元大都遺址繞北三環而行,下個月就要起運通車了;地鐵五號線從元大都遺址穿膛而過,早在去年十月就開通了。男人工服上印著某某集團公司,看上去憨厚老實,不像是騙子。我半信半疑,蹲下來看他手裡的石羊。
石羊憨態可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我驚奇不已。再仔細一看,感覺有些似曾相識,但又一時想不起來在哪兒見過。儘管上面還沾有泥土,但我一眼就認出是塊賀蘭石。難道真是元大都地下的文物?如果真是這樣,怎麼會是一塊賀蘭石呢?難道這石羊跟遙遠的西夏有什麼關係?我對與西夏有關的事情一向很敏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用八百塊錢買下了石羊。心裡想,即便是個假的,擺在屋裡欣賞也很不錯。
我問民工:“你是什麼時候從地鐵里挖出來的?”民工以為我想反悔,下意識地將錢揣進兜里:“一個月前啊,咋啦?”“具體是哪一天?”
民工想了想說:“五月十二號,就是汶川地震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腳下晃了一下,我不知道咋回事,以為是加班施工太累了,閉上眼休息了一下。等我再睜開眼睛,就看見了這玩意兒。後來才知道四川地震了。”
我心裡“咯噔”一下:汶川那邊的羌族聚集地一地震,北京這邊的元大都遺址下面就發現了可能跟黨項羌人有關的石羊,難道真有這麼離奇的事情?
我疑疑惑惑地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把石羊仔細刷洗乾淨。我嗅到了一股腐朽的羊血的味道,驚奇地發現石羊的肚皮下面有一行字,竟然是西夏文。我的心一陣狂跳,急忙拿起電話打給夏教授。接電話的不是教授,而是夏雨。夏雨聽出是我,說你有病呀,這麼早打電話。我說我有急事,找教授。她說我爸遛彎去了。我把石羊的事對她說了,她說你下班后拿來讓老爺子看看不就得了。
我一整天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如果石羊真是西夏時期的物件,那它就跟我太有緣了。小時候常聽老人講,我們的祖先是黨項人。十幾年前,我回陝西老家翻修祖屋,在屋樑上發現了我們的《黨氏族譜》,那上面清清楚楚記載著我們的祖先是在西夏滅亡后遷徙入陝的黨項。祖先們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殺,隱姓埋名,不再使用黨項語言,不再穿黨項服飾,不再留黨項髮式,不敢承認自己是黨項人,久而久之,黨項人就這樣從人間“蒸發”了。很多年後,為了讓後代記住自己是黨項後裔,才開始姓“黨”。從此,我對黨項祖先和他們建立起來的那個神秘的西夏王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西夏王國是一個以黨項為主體,包括漢、吐蕃、回鶻在內的多民族 地方政權。西夏立國一百九十年,帝王更替了十代,疆域廣闊,包括今天的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陝西北部、青海東部和 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點集不逾歲、征戰不虛月”,前期與北宋、遼抗衡,僅與北宋就進行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戰爭,同時又攻滅甘州回鶻、涼州吐蕃;後期與南宋、金成三足鼎立之勢,數十年兵連不解,最後被蒙古人所滅。這麼一個“以武立國”雄霸西北的軍事強國,最後為何會被蒙古人消滅?而且蒙古人為何會對西夏進行慘無人道的屠城,使得黨項人包括他們的歷史、文字幾近滅絕?當年元朝人為宋、遼、金三朝修史,為何唯獨沒有為西夏修史?致使我們今天翻遍了“二十四史”也尋找不到西夏史。儘管黨項人的許多風俗文化在他們的後裔羌族人身上得以傳承,但是作為一個獨特民族,黨項早已從歷史的長河中消失了,連同他們創製的奇特文字。
所以,西夏文在世界上被視為“絕學”、“魔鬼文字”。所有這一切,都給這個消失在絲綢古道上的王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我想撩開這層神秘的面紗。在搜集資料研究這個神秘王國的過程中,我結識了夏教授,並很快與他成了忘年交。夏教授是 B大的研究生導師,在研究西夏歷史和文字方面很有成就,與當代西夏史學家韓蔭晟、李範文、史金波、杜建錄、吳峰雲、吳天墀、韓小忙等人齊名。我曾經陪同夏教授多次去過四川的理縣、茂縣、丹巴美人谷等地考察古老的羌族文化。聽夏雨說,這次汶川地震發生后,夏教授當即捐出二十萬元稿費,指定用於修復被毀壞的羌寨和古碉樓。
夏教授經常推薦一些西夏史學家的書籍給我看,比如,《西夏紀》、《宋西事案》、《西夏戰史》、《西夏簡史》、《西夏文化》、《西夏與周邊民族關係史》、《黨項與西夏資料彙編》等等。其中韓蔭晟老先生編撰的《黨項與西夏資料彙編》這部書就有四卷九冊,而且是豎排版,我都基本讀完了,但我知道這還遠遠不夠。面對神秘的西夏歷史,我感到了自己的淺薄,我無法窮盡這段歷史,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親近它、撫摸它。
許多時候,我對八百年前的西夏所發生的一切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我就曾經生活在那個時代,那些帝王將相,那些血腥的場面彷彿就發生在眼前。其中最吸引我的是西夏的最後一個帝王李。恍惚中,我感覺自己就是那個倒霉的李。我時常有一種強烈的敘述慾望。好像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告訴人們八百年前曾經發生的那一切。我想把我所知道的西夏,那個屬於我自己的西夏寫出來,告訴世人,這是我多年的一個夢想。
晚上,我抱著石羊去找夏教授。教授還沒回來,夏雨一個人在家。她穿著一襲寬鬆的白色棉布睡袍,不知道是剛回家換上的,還是壓根兒一天就沒出門。她喜歡穿棉布衣裳,喜歡光著腳丫在木地板上走來走去,有點波希米亞的味道。她是搞服裝設計的,人很漂亮,在服裝設計圈裡小有名氣,她穿著自己設計的服裝還上過《時尚》雜誌封面呢。
我問她:“教授呢?”
她說:“開會去了,還沒回來呢。”
“你怎麼不出去玩呀,整天貓在家裡,都快變成‘物乾女’了。 ”
“夠前衛的啊,還知道‘物乾女’?什麼‘物乾女’,我都快
變成剩女了。”“聖女好啊,聖女多純潔啊。”“純潔你個頭!”她笑著罵我一句,轉身進了廚房。 “現在,又變成野蠻女友了。”
夏雨給我端來一杯咖啡,味道很純正,我喝了一口說:“條件別太高了,趕緊找個人嫁了得了,免得老讓我惦記。”她笑著說:“惦記什麼呀,我乾脆嫁給你得了。我屬羊,你屬兔,
卦書上說了,屬羊的最適合嫁給屬兔的了,我們就搭夥過吧。”我笑著說:“典型的‘結婚狂’,逮誰想嫁誰。”我們開著玩笑,夏雨打開電視,新聞里說今天的奧運聖火已經傳遞到了貴陽,明天將傳到凱里。我讓夏雨將電視調到新聞頻道,想看看汶川地震的最新情況。白岩松正在神情凝重地直播。夏雨說,今天是地震整一月,新聞頻道一直在直播紀念節目。新聞里說,前幾天因救援災民失事的直升機的殘骸已經找到,五名機組成員和機上的災民全部遇難。特級飛行員、機長岳光華是少有的羌族飛行員,是當年周總理親自選定的第一批少數民族飛行員之一。他的家鄉就在地震重災區汶川與茂縣之間的南興鎮。救援開始后,還有幾個月就要退役的他,每天駕機在家鄉的天空飛來飛去,就在他第六十四次執行救援任務時飛機墜毀了,他將自己的生命永遠地留在了那片生他養他的古老羌地……
正看著電視,教授回來了。我對教授說了早上在元大都遇到的事情,並把石羊拿出來給他看。教授帶我走進書房,擰開工作檯燈,戴上老花鏡仔細端詳石羊。我提醒他說,石羊肚皮上還有西夏文呢。教授用放大鏡一看,驚訝地說:“真是西夏文,而且是難得一見的西夏篆書!”
我問教授:“那上面寫的是什麼意思?”
教授一字一句地念:“白、高、大、夏、國、秘、史。”夏雨覺得驚奇,湊過來問: “‘白高大夏國’是什麼意思?”教授說:“就是西夏的意思。西夏是宋代時我們漢人的叫法,
而黨項人把自己的國家叫‘白高大夏國’。”
我欣喜若狂:“這麼說,真是西夏的物件?”教授點了點頭。“這石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真是可愛!”夏雨說著,突然驚叫一聲:“呀,這石羊的形狀怎麼跟我的玉羊一模一樣!”
夏雨取下自己脖子上的玉羊,比對了一下,除了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他幾乎一模一樣。我和教授也感到很吃驚,仔細比對,真是驚人的相似,難怪我早上一看見石羊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和夏雨問教授這是怎麼回事。教授說,夏雨的玉羊是許多年前一個西夏考古學家朋友送給他的,至於朋友從哪裡得到的,就不得而知了。這事簡直太神奇了!
夏雨好奇地用手去摸石羊睜著的那隻眼睛,那眼睛突然陷了進去,夏雨又是“呀”的一聲驚叫。只聽“嘎嘎”幾聲怪響,石羊的脊背上慢慢裂開了一道縫,轉眼間裂成了兩瓣,像殺開的西瓜一樣攤開在書桌上。我吃驚地發現,石羊肚子里竟然藏著一個羊皮囊。教授用鑷子小心翼翼地剝開羊皮囊,剝了一層又一層,一共剝了三層,裡面露出六冊黃褐色的古書。
夏雨驚訝地說:“太神奇了,有點像指環王!”
教授說:“這是一部《白高大夏國秘史》。”
我激動得雙手直哆嗦:“真沒想到,石羊肚子里藏著一部西夏秘史!”
教授坐在椅子上,顯得很累,好像打開三層羊皮囊耗盡了他的全部力氣。
我問教授:“蒙古人消滅西夏時,不是燒毀了西夏所有的書籍嗎?怎麼突然會在元大都遺址下面發現西夏秘史呢?”
教授沒有馬上回答,仔細翻看著古書,過了一會兒才說:“剛才我懷疑這是《夏國世次》中的一部分,但現在看來不是,這是一部歷史上沒有過任何記載的奇書。”
我說:“我以前聽您說過,《夏國世次》是羅世昌寫的,共有二十卷,在西夏滅亡時被蒙古人燒毀了。可是,這部秘史是誰寫的呢?”
教授說:“書上沒有撰寫者的名字,但是在書頁里有一枚西
夏文印章,上面刻著‘阿默爾’,這個‘阿默爾’很可能就是秘史的撰寫者。這個人歷史上沒有任何記載,他也許是西夏的一個無名史官,也許是一個被罷了官的大臣,也許是一個與宮廷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在野文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個黨項人,因為只有黨項人才稱自己為‘白高大夏國’。我剛才大概看了一下,這部秘史雖然前半部分已經模糊不清,但後半部分卻清晰可辨。這後半部記載的是成吉思汗第一次攻打西夏開始直到西夏滅亡的這段歷史。儘管這段歷史在西夏立國的一百九十年中,只佔有短短二十二年,但它的分量很重。這不僅因為成吉思汗滅絕了西夏,而且西夏的十位帝王中有五位在這短短的二十二年內先後更替……”
“可是,蒙古人怎麼可能將秘史保存在自己的都城裡呢?”
“是呀,我也納悶,這是一個謎。”
“這又是一個謎。”教授說,“也許當初寫此書的人怕招來殺身之禍,才採取這種奇怪的記述方法,因為這畢竟是一部不可示人的秘史。”
我們正說著,夏雨突然驚叫一聲:“看那羊皮!”
我們扭頭一看,剛才剝下來的那堆羊皮在輕輕顫動,像一個受傷的人在那裡痙攣,又像是乾枯的樹葉在烈日下沙沙捲曲,羊皮漸漸變干、變硬,最後“嘎嘣嘣”碎成了粉末。我們都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
教授說:“不好,秘史很有可能也會變成粉末。”
我著急地說:“那怎麼辦?我們趕快跟文物局聯繫,他們有保護經驗。”
教授說:“來不及了!現在是晚上,上哪兒去找人?你趕快打開電腦,我口述,你記錄。我們要搶在秘史消失前把它全部整理出來,然後再交文物局。”
夏雨幫我打開電腦,教授翻開秘史,開始口述。我坐在電腦前“嗒嗒嗒”地敲擊鍵盤,記錄著我們黨項民族最後的那段歷史。恍惚中,我彷彿看見了八百年前的自己,那個叫尕娃的男孩。我也看見了夏雨,那時她不叫夏雨,叫阿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