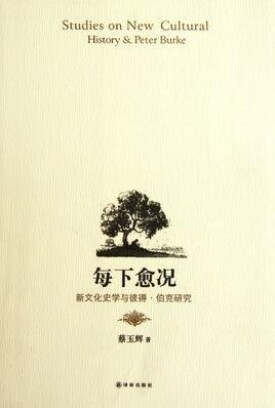新文化史學
新文化史學
近三十年來,西方歷史學界出現了一股新的國際性潮流,由於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將社會和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因而被稱作“新文化史”,又被稱為“社會文化史”。
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史學界的普遍認可。新文化史的內容非常複雜,本身具有多樣性、零散性和非系統性的特徵,但總體而言,它相對於傳統史學和新史學而言,更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對研究對象和讀者都體現出一種更加平等的精神。在方法論上,不再以宏觀的理念為出發點,而是強調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具體事實;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從結構——功能主義的因果的聯繫的分析轉向文化的闡釋;在研究主題上,放棄了或政治或經濟或心態觀念的單一形象,轉而尋求各因素之間的互動過程,從而推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史學著作。
20世紀70年代,國際史學界發生了重大轉折。一方面,新史學運動追求的科學性在計量史學的實踐中發揮到極致,同時自身所無法消弭的弱點也暴露無遺,使歷史學陷入了新的危機,從而呼喚史學的進一步革新。另一方面,對科學和理性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更動搖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傳統學術范型的根基,為學術創新掃除了種種舊的藩籬和障礙。這樣,新文化史學作為史學領域內的新探索之一開始脫穎而出。
(一)科學主義歷史學——計量史學的危機
二戰以後,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運用計算機統計分析材料和重建歷史的計量史學在西方史學界風行一時。眾多歷史問題,諸如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家庭規模大小、貿易數額和經濟發展速度,甚至人們的心態,都可以進行量化的分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學者提出的“系列史”。“系列史”基本方法是選擇某一方面的特徵,在時空的許多點上將此特徵計量化,然後置於長時間序列統計數據中加以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將過去只限於經濟範圍的計量研究擴大到社會、思想和文化史學領域。他們對這種研究方法充滿了自信,認為依據這些涵蓋長時段的系列統計數據,並運用數學方法的處理和計算,便能洞察歷史變遷的長期模式和趨勢。系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肖努指出:“系列數據一旦建立起來,它的證明能力便成倍地增強,因為系列數據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處理,可以取代社會科學中無法進行的實驗,從而有能力揭示長時段中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
如果說系列史“從觀察到概括再到一個科學的規律”的方法仍是舊實證主義的模式,那麼,美國的克萊奧學派則將現代數學模式注入了歷史研究中。在美國的計量史學者看來,世界就是一個嚴格的模型體系,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是相互聯繫的,某一部分的變化將影響到整個體系。他們常常採用集體合作的形式進行研究:在一個負責人的指導下搜集資料,將資料輸入計算機。至於採用何種模型分析資料以及最後由誰執筆,是由不同的人分工完成的。這種研究方式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結果。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羅伯特·福格爾在《鐵路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一書中,利用了反事實計量法。他設計了一個反事實的沒有鐵路的19世紀美國經濟模型,從中發現美國在這個反事實的狀態下發展速度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因為其他的運輸方式將會取代鐵路,從而推翻了鐵路建設是美國19世紀經濟發展首要因素的傳統結論。
計量史學的成就有目共睹,並得到了廣泛承認。它意味著歷史學方法論的進一步精確化,強有力地支持了歷史學作為“證明普遍觀點的一個方法”的信心。大量的計量史作品表明,如果研究對象能夠被清楚地界定,可以進行分類觀察並且其數量達到相當巨大的規模時,計量研究便能有出色的表現。然而,隨著這種研究范型的目標不斷擴大,它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來。首先,它不能抓住人類生活中大部分領域的獨特性。例如,即使在群體構成的社會中,決定和造就生活方式的最終力量依然是眾多的個人。他們的想法和行動幾乎難以通過計量分析的方法來駕馭。其次,還存在著一個與讀者交流的問題。在這類歷史作品中充斥著冷冰冰的公式、圖表和模型。這種做法雖然能夠使歷史對象變得更加精確和有序,但也使其變得枯燥、晦澀,只能為少數人所讀懂。計量史學家不僅難與大眾溝通,甚至也無法和其他歷史學家交流。再次,現代經濟的理論和模型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鴻溝似乎難以彌合,這就帶來了驗證結論的困難,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很多計量經濟史的結論所依據的是永遠不可能得到確證的演繹模式,因此它的某些方法實際上是“反經驗的”和“反實證的”。因此,這種方法遭到了新文化史學的代表之一卡爾洛·金茲伯格的否定。在他看來,定性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如果沒有定性研究的印象主義方法,精確的定量研究也是難以實現的。計算機只能執行命令,不可能思考問題。因此,只有經過一系列特別深入的調查,一個闡述的計劃才可能發展為應用計算機進行統計的工作。
基於對計量史學惟科學論傾向的不滿,歷史學界的有識之士不是退回到傳統的敘事史去,而是另闢蹊徑進行新的探索。新文化史學正是其中的努力之一(另一努力是生態史的興起)。與年鑒學派不同,新文化史學不是源於某個國家或某所大學,而是西方史學界在差不多相近的時間內出現的國際性動向,這表明它不是某個人的突發奇想促成的,而是集體的自覺選擇。羅伯特·達恩頓的看法也許可以代表新文化史學的基本思路。他強烈反對以系列數據的和計量的形式研究心態,甚至也不贊同那樣來研究經濟和社會。他說:“文化客體與經濟史或人口史研究的系列數據不是同質的,因為它們不是歷史學家製造的,而是由記錄它的人製造的。它們傳達出的是意義,應該被閱讀,而不應被計算。”“文化是一個連貫的概念,不是與政治、經濟並列的一個社會實體,因為許多個人之間構成的所有關係,甚至那些我們認為是‘經濟的’或‘社會的’的關係,本質上都是文化的。”
(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挑戰
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核心是從語言的本質和知識的性質入手,對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以科學和理性為根基的西方文明和學術傳統作了批判性的反思。由於這種思考“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關於人類現實的符號學描述模式和說明模式”,因而,它促發各學科的新動向。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以及對各門學科產生的重大影響,其重要意義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公認。
後現代思潮與當代歷史學發展的關係,也是史學理論研究者一直關注的問題,因為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一樣,首先是一門用語言表達的學科,也是現代知識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所謂的“語言學的轉向”中。“語言學的轉向”是指語言學從語音、語法和句法的研究,轉向對語言與其所指對象關係的研究。重要的突破源於費迪南德·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關於“語言學的轉向”、後現代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福柯、德里達、海登·懷特等的思想,前面幾章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論述,這裡恕不贅言。不過,關於後現代主義思潮與新文化史學的關係,還需要強調以下兩點:
首先,後現代主義思潮與新文化史學靈犀相通的一點是,它們都是對戰後西方社會弊端的批判和反思。二戰後物質財富的增加,似乎不僅沒有有效地解決貧富分化、失業等嚴重的舊的社會問題,相反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如生態環境的惡化、東西方冷戰格局中的核武器威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越來越重等等。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要求改革傳統的教育制度,反對專制和暴政,呼籲建立自由和人道的社會。在美國,反戰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也前赴後繼。後現代主義思潮正是與這種動蕩和變革的西方社會背景相契合的激進思想。新文化史學家大都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戰後時期正值他們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生活風格的青少年時代。許多新文化史學家目睹了西方60年代的學生運動,有的甚至親自走上街頭,成為運動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新文化史學家對後現代主義是耳熟能詳的。無論是羅伯特·達恩頓還是彼得·伯克,在他們的作品中都經常提及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如米歇爾·福柯、雅克·德里達等,並對他們的思想作出過認真的思考和批判。
其次,後現代主義主要是形而上的批判,因此通常是非常極端的。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學則是實踐的,後現代主義只是促成新文化史學興起的因素。如果只是簡單地徹底打碎現代的權威和理性,那麼我們就會看到諸如五六十年代的"X一代”,看到在他們當中流行的性解放、吸毒和犯罪這類現象。人們似乎並沒能找到為如何實現更幸福的生活前景而建設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和知識體系的方案。後現代主義思潮並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在面對後現代主義對歷史敘述的可能性和歷史必要性的否定時,新文化史學在實踐中堅決捍衛著自己的陣地,並沒有完全屈服於後現代主義的理念框架,而是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觀點作為出發點之一。顯然,新文化史學並不願意只做一個批判者和破壞者。它從後現代理念中的受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後現代思潮直接影響了新文化史學的研究主題。眾多以“創造”或“塑造”為標題的著作,就是將觀念作為社會和政治的進程來考察的。《東方學》(又譯作《東方主義》,的作者愛德華·薩義德承認,福柯的有關知識霸權的思想對他的寫作有很大啟發。二是間接的影響。“語言學轉向”所揭示的理性和科學的局限性,迫使歷史學家重新審視傳統的史料觀、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等問題。
(三)新文化史學的興起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先問世的新文化史學作品,卻出自一直熱心鼓吹和實踐計量史的學者。1975年,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學者埃馬紐埃爾·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紀法國南部一個村莊中的異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此前不久,他還宣稱惟有計量史學才是真正科學的歷史學,並預言歷史學在80年代將成為計量史學的一統天下,然而,在這本書中,他放棄了數字和圖表模型,轉而對幾百個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狀況以及他們對貧窮、財富、婚姻、愛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描述。他還試圖通過這些描述揭示出這個村子的權力體系、它與外界的交往,以及這種交往對村民生活和觀念的不同影響。這本書的問世立即引起了學界和大眾的廣泛注意,成為20世紀法國最暢銷的歷史著作之一。
一年之後,義大利歷史學家卡爾洛·金茲伯格出版了《乳酪與蛆蟲——16世紀一個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書。金茲伯格出生於1932年,曾任教於波羅涅大學,先後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洛杉磯蓋提中心(The Getty Center)和英國倫敦的沃布格學院等地做過訪問學者。自1988年至今,他加盟世界一流的大學——洛杉磯加州大學,擔任義大利文藝復興研究方向的富蘭克林·D·墨菲講座教授。1998年,他當選為哥倫比亞大學義大利高級研究院的在籍院士。這本《乳酪與蛆蟲——16世紀一個磨坊主的精神世界》試圖為16世紀一個名叫麥諾齊奧的普通磨坊主的怪異看法尋找合理的解釋。麥諾齊奧對世界的形成和現世的生活有著不同於教會正統學說的獨特認識,並且喜愛到處向家人、周圍的鄰居和村裡的人,甚至面對審判他的教會法官宣講自己的觀點。在金茲伯格看來,一方面,麥諾齊奧的生活經驗、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民間文化傳統、宗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環境對他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這個下層人物並不是外界觀念被動的接受者,而是通過自己的頭腦中一個“過濾器”,進行了創造。
在美國,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於1978年面世。薩義德是阿拉伯裔美籍學者,出生於耶路撒冷。雖然在埃及生活過,但他從小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美國讀完學位,1968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文學。薩義德的這本書探討的不只是東方學這樣一個學科在西方發展的歷史、演變、特性和傳播,而且在作者看來,東方學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在本體論、認識論意義上以東西方相區別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它表現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這一區分,並將其作為建構與東方、東方的人民、習俗、心性和命運有關的理論、詩歌小說與社會分析的基礎。在更隱蔽的層次上,東方學還被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方式,通過作出與東方有關的陳述,對有關東方的觀點進行權威性裁斷,對東方進行描述、教授、殖民、統治等方式,來處理東方的一種機制。在這裡,東方學是交織著學科、思維方式和權力的多層次複合體。此外,在英、俄等國也都出現了類似的作品。
乍看這些作品,除了在書名的選擇上,人們已經看不到通常的“歷史”一詞,而是一些非常具有想像性的辭彙之外,它們相互之間並沒有別的明顯聯繫。然而密切關注歷史學前沿發展的學者,已經逐漸認識到創門背後蘊含的力量和價值。
對於這樣一些在不同國家先後出現的史學作品,最先從理論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學者,是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1979年,他在《過去與現在》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敘事史的復興》一文。他雖然沒有用“新文化史學”(而是使用“新的舊敘事史”)這個概念來概括這種以新的文化理念為取向的新史學潮流,但他的具體分析已初步揭示了這一新潮流的特點和意義。斯通的文章指出,新的歷史寫作側重於敘述個人的歷史或某個重大事件的歷史,其目的並不是為了敘述而敘述,而是為了發現歷史進程中文化和社會的內在運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寫作方式的轉變,而且體現了歷史學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全面轉向,即“從圍繞人的環境轉向關注環境中的人,研究的問題從來自於經濟學、人口學轉向來自於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來源從主要接受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的影響轉向主要接受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影響,關注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人,從對歷史變化的分層的、單因果的解釋轉向相互聯繫的、多因果的解釋,在研究方法上則從計量轉向個人例證,組織文章的形式從分析轉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識到這些變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試圖對過去的變化作出連貫的、科學的解釋的結束”。羅格·夏特爾非常簡潔地將這一變化概括為“從社會角度的文化史向文化角度的社會史轉向”。1989年,美國學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為書名主編了一本論文集,收錄了有關政治文化,如無形的政治規則、組織方式、非正式權力體系等研究論文。
正如斯通指出的,在70年代,儘管新文化史學還只是寥寥可指的少數歷史學家的實踐,卻在歷史學界引起了關於歷史研究的性質、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歷史證據的性質以及歷史真理的標準等一系列問題的激烈討論。歷史究竟是靜態的結構,還是變遷的事件?歷史學應該研究獨特的人物,還是應該研究被抽象的群體?歷史學的使命是為人類尋找普遍的規律,還是為了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目的進行釋義?作為史料的歷史文本反映的是客觀事實,還是文本記錄者的主觀印象?隨著討論的深化,90年代后,新文化史學的作品已經數以千計,其中許多不僅得到學界的承認,而且受到大眾的普遍歡迎。諸多世界一流的大學,如劍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都聚集了一批研究者在關注和進行新文化史學的探索,還有許多新文化史學者也在這些大學獲得了重要的教職。這一潮流所倡導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以至於“槍文化”、“暴力文化”等等,一切現象似乎都能與文化聯繫起來。
文化史學的研究主題豐富多彩。相對於學院派的傳統歷史學來說,它開闢了以物質文化(如食物、服裝)、政治文化、身體和性別、記憶、形象和想像為對象的許多新的研究領域。不過,如果從傳統的宏觀分類角度看,新文化史學在研究對象上並沒有重大的突破,我們依然可以將它們歸入政治史、心態史、文化史、婦女史等類別中。但是,新文化史學的貢獻,並不在於平面視野的擴展,而是在事件、人物和觀念的刻畫上向縱深維度的推進。與傳統史學相比,新文化史學在歷史形象的塑造上呈現出了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一)潛在事件同明顯事件的有機融合,而不單是研究表面的事件進程或被降到次要位置中的事件。
在時間和空間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某一事件,通常是歷史學家熱衷研究的對象。在古典歷史學那裡,編年史作品就是以時間為序、以事件為綱的典型體裁。蘭克式歷史學所關注的是將王朝更替、工人運動、社會革命等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客觀地交代清楚。年鑒派學者也描述事件,但他們普遍遵循的是三時段理論,認為由地理、氣候、生物等因素組成的“結構的歷史”是人類歷史的基礎,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等在一段時間內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組成了“情勢的歷史”,而那些令人眼花花繚亂的個別政治經濟事件則是短時段的,猶如歷史浪濤中泛起的泡沫。這樣,事件就是歷史的細枝末節,它對於歷史學的重要性遠不如情勢和結構。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對西班牙王位爭奪、與土耳其的戰鬥、宗教改革等問題,都只有寥寥幾筆的敘述,而對地中海地理環境和當時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描述,卻佔了書中的大量篇幅。這樣,在結構化的歷史學當中,事件雖然沒有消失,但卻只是反映結構的鏡子,居於次要、從屬的地位。
新文化史學再一次將個別事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但它顯然不滿意於簡單地描述某個古典歷史主義所理解的事件過程,而是將事件區別為明顯的與潛在的事件。“明顯的事件”指社會生活中那些容易被人感受到的任何事情,它不僅包括諸如戰爭、經濟危機、政局變動、外交談判等英雄偉人身上發生的事,而且也包括鬥雞、瘟疫這類發生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潛在的事件”指那些不太容易被察覺到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如政治制度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家庭結構以及文化觀念的整體性變化等等,也即年鑒派學者所說的結構和情勢。新文化史學則是以明顯的事件為切入點,力圖揭示出它與哪些潛在事件有關,以及兩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這種影響不僅是明顯事件對潛在事件的改變而且同時也是相反的過程。這樣,在新史學中事件與結構的對立即被消弭,一種新的辯證聯繫得以重新建立起來。
這方面較早的成果是納塔莉·戴維斯出版於1973年的《馬丹·蓋赫返鄉記》。流浪漢馬丹·蓋赫回到法國南部自己的家中時,他發現一個冒名頂替的人已經佔據了他的位置。通過這個故事,作者試圖揭示“當時農民的希望和感情、夫妻之間或者父子之間的關係,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機會”。至於蓋赫的妻子怎麼會承認一個闖入者作為她的丈夫,這必須到16世紀農村社會中的婦女地位上去尋找答案。而羅伯特·達恩頓的著作《貓的大屠殺》描述的18世紀在法國發生大批屠殺野貓的事件,則是印刷工人反抗行東的鬥爭形式之一,因而反映了工匠文化與新興資本主義勢力的對立。
在馬歇爾·薩林斯的《歷史的島嶼》一書中,潛在事件與明顯事件的有機融合表現得更為典型。他以庫克船長1778年到達夏威夷島的事件為例證,來揭示夏威夷的民眾文化結構,說明歷史事件“往往帶有特殊的文化印記,並為該文化所制約”。在夏威夷土著居民的理解中,庫克是他們所崇拜的神——洛諾的下凡,因為在他們看來,庫克具有與洛諾同樣的力量,而庫克到達的那一年在夏威夷的神話中恰好又是洛諾現靈的一年。夏威夷和斐濟的圖騰制度之所以終結,是它們與英國的一系列接觸和衝突給當地文化、結構帶來的結果,也是與其他大陸開展貿易后造成的結果。因此,在多重意義上,當庫克離開時,夏威夷已經不再是庫克剛剛到達時的夏威夷了。
(二)由外圍和核心組成的大規模、系統的研究單位,而不是被清楚界定的空間和時間片斷。
新文化史學的研究單位不是某個清楚界定的實體,而是圍繞研究主體形成的有限但無界的外圍——核心繫統。它包括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就空間維度而言,在15世紀以來興起的民族國家的鼓舞下,民族國家取代王朝成為歷史學的敘述單位,圭齊亞迪尼的《義大利史》、馬考萊的《英國史》等等都是其中經典的作品,至今仍是西方各國普及歷史教育中必有的基本內容。在年鑒學派那裡,以民族國家為主要敘述空間的政治史遭到了批判,他們發展出以超越國界的區域為單位的宏觀研究。例如,在布羅代爾眼中,腓力二世時代的空間不是西班牙、法國或者德意志,而是環地中海的整個地區。在新文化史的著作中,不存在國家和地方的簡單對立,也不存在宮廷與鄉村的勢不兩立。新文化史學家對研究對象的選擇更為自由,研究單位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某個偏僻的小村莊;可以是一片區域,也可以是某個宮廷,或者某個家庭。它們的邊界不像國家或行政單位那樣清晰可辨,有時甚至還是模糊的。但這種空間單位的彈性並不是隨意的,而是以主體的活動範圍為中心。與所述主題直接有關的空間構成了研究的核心;間接相關的空間則構成了研究的外圍。同時,隨著主體的變化,這一空間的範圍和核心――外圍的邊界也在不斷地調整。
傳統歷史學將歷史的進程分割成古代、中世紀、近代、現代等多個時間段,並且為這些時間段的起始點問題而爭論不休。一般而言,不同的史學家和史學流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時段。阿克頓偏愛近代史,而不太願意研究當代史。湯因比這樣的歷史學家喜歡縱橫古今,對人類文化進程宏觀比較。年鑒學派的研究範圍則主要集中在中世紀的歐洲。然而,新文化史學研究和寫作涉及的時段卻不限於某一時期。從古代世界一直到20世紀初,關於各個歷史時段,都有不少優秀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同空間維度上的處理一樣,新文化史學家並不堅持一種僵化的時段劃分,而是關注研究主體具體涉及的時間,所以,他們的著作經常打破慣常的單一的歷史分期方法,揭示出每個敘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獨特的時間系列。眾多不同的時間系列,構成了歷史進程中的多樣性的一個方面。
在史景遷的《天安門》一書里,中國革命沒有被清晰地分為從某年到某年的幾個階段,也沒有以普遍接受的1840年為起點。康有為登上歸國的輪船是敘述的最初場景,隨後以沈從文、魯迅、徐志摩、丁玲等人的活動為線索,時間和空間也依次次變換。與革命直接相關的場景構成了研究單位的核心,無直接關係的內容則被被當作外圍處理。整個敘述中並沒有精確的階段劃分。例如,康有為這樣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生命空間,從中國到海外,從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到喜馬拉雅山腳下的村落,或者為富國強民而奔走呼號,或者與女兒一起散步聊天。書中著力凸顯的是對敘述主體有意義的時空單位。更重要的是,對不同的人而言,時空單位的規模是千差萬別的。亨利·詹姆斯的《小房間里》一書,則完全以主人公—-倫敦一個區電訊局的電報員—-終日呆著的發電報的小房間為敘述空間。
(三)以人為敘述的中心,但不是類型化的群體,而是具有獨特個性的具體的個人;不單敘述某個人,而且揭示他同客觀條件和外界事件的關係。
新文化史學家反對以長時段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史學,認為這種方法的缺點是把歷史研究的真正對象,即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淹沒在靜態的結構性力量中,喪失了活力。他們的著作不再以政治制度、經濟結構這樣的物質化概念作為自己的中心,而是關注具體的人的歷史。卡萊爾所創造的那類歷史形象再一次成為新文化史學的出發點:即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圖表和公式,而是身著黃色外套和馬褲,兩頰紅潤,內心充滿激情,有自己的語言習慣和個性特徵,充滿活力的人的歷史。但是,新文化史學家對人的刻畫,不只是將他們從抽象的物質性結構中解放出來,而且以不同於以往的文學描繪賦予他們新的生命力。與古典著作和人文史學中的“人”相比,新文化史學家所描述的“人”有三個方面的突破。
首先,新文化史學突破了只有某種人擁有歷史,而另外一些人則不可能進入歷史的狹隘的精英觀念,把各色人等都納入了歷史觀察的視野;歷史不再以精英為中心其他人為陪襯,也不只是工人、農民、少數民族等弱勢群體的聲音,任何一個普通的人都可能成為歷史描述的中心。其次,它強調個人的獨特性和主觀能動性。新文化史學家認為,過去所使用的民眾心態、“階級”、“人民”這樣一些集體對象中,所強調的是集體的力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則被抹殺。而在新文化史學家的筆下,人首先不是作為集體的人,也不是富貴者偉大高尚、貧困者卑賤猥瑣這樣類型化、臉譜化的人物形象,而是首先作為他們自己而存在的有血有肉的個人,然後才是與其他人的某種身份認同。再次,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而是有自己的生活背景;個人的自由意志,不僅僅是簡單的利益驅動,而是與心理的、社會的、文化的形態有著相互作用的關係。新文化史學將個人置於他生活的客觀環境中進行考察,不是抽象地談某個人的看法、行動,同時又力圖避免惟意志論或物質、結構決定論,從而揭示出個人與生存環境之間衝突與和諧的複雜關係。磨坊主麥諾齊奧、辦公室的小職員、流浪漢馬丹·蓋赫、“太陽王”路易十四等等,這些新文化史學的人物無不因此呈現出豐滿、深厚的形象。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1936――)的《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一書,在塑造中國革命進程中知識分子的獨特形象上甚為精彩。在史景遷筆下,康有為面對國難家仇,是一個全身心投入尋找救國途徑的人。先是公車上書,為皇帝召見,改革失敗后流亡國外,他仍念念不忘大同社會的理想。但因為他堅持的是君主立憲的政體,遂又有復辟的鬧劇。魯迅也是滿腔義憤的義士,猛烈抨擊當時中國的處境。中國讀者對這類人物非常熟悉。然而,書中同時還貫穿了沈從文、徐志摩這樣的人物。在9歲的沈從文眼裡,辛亥革命只是暴力和流血。徐志摩生性浪漫不羈,無論時局如何變幻,他總是盡情地地享受著愛情和友情。他在動蕩的時局中演繹的不朽愛情故事,與梁啟超的師生之誼,還有他無法抑制的詩情靈性,同樣是對革命時代的一種回應。丁玲則是懷著解放婦女的理想參加革命的,但也曾因現實的殘酷而苦惱、動搖過信念。
《天安門》的作者並不想陷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一般革命敘事模式中。在他看來,結局不是最重要的,一個政權的勝利建立,並不一定意味著革命的終結,應當把革命過程作為真實的圖景呈現出來,因而並不存在簡單的革命者與反革命者的對立陣營。為了理想不惜犧牲生命、上書請願、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向敵人口誅筆伐這樣的行為,當然是革命的一部分;但誰又能否認,顯現出自己生命的本真、敢愛敢恨的人,就不是革命時代的一部分呢?這些知識分子同屬一個群體:他們反對舊制度,懷有富國強民的理想,並為此進行了不懈的追求;他們不是麻木的社會旁觀者和時代環境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積極思考時代變化的人,並以或深刻、或優美的文筆將他們的思考傳達給了大眾。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強調了每個人物獨特的個人背景和經歷,他們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婚姻家庭經歷不盡相同,性格也千差萬別,因此,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在關於進行什麼樣的革命、以何種方式進行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麼等問題上,每個人物有著不盡相同的認識和態度是很正常的。因此,書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是多層次、多側面的,生活在一張複雜的網路之中,不再是抽象的聖人、才子,而是活生生的凡人。在康有為的形象里,有他的家庭背景、教育、婚姻,他和弟弟的手足情深,和女兒的父女深情,以及他對富國與養民的不同論述,還有在《大同書》中對人類美好未來的幻想。作者以這樣一種多層面的圖景讓讀者獲得了對於近代中國革命史的豐富理解。
(四)注重心態、觀念和生活結構的聯繫及觀念、思想傳播和交流的敘述傾向。
新文化史學深入挖掘了人的內心世界。時代的精神風尚,傑出人物的有關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思想,一直是人文主義史學對抗社會科學式歷史學的最後陣地。然而,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是現象決定了觀念,而不是觀念決定了現象,因而在二戰後計量史學風行的西方史學界,傳統的思想史研究進一步受到冷落,喪失了信心。新文化史學研究的思想,不僅包括系統的理論和思想,而且包括感受、情感、體驗以及非系統的散亂的看法。早在20世紀初,荷蘭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加便對中世紀末期的群體情感、氛圍、觀念和思維模式作過描述。新文化史學家的研究興趣,則集中於對任何一個個人的觀念表述和情感心緒。羅伯特·達恩頓在《貓的大屠殺》里指出:“每一個從田野工作回來的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他者就是他者,他們與我們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如果我們想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我們必須從捕捉他們的思想觀念開始。”
在追尋思想觀念的形成時,傳統的思想史只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回溯過去,而沒有將思想者置於其真正歷史背景的語言辭彙中。在觀念的社會史里,概念則被下降為次要的現象,是被社會的、經濟的或政治的結構所決定的。新文化史學不是孤立地看待它們,而是探索個人的心態與其客觀條件和外界事件的合理關係,以“使思想史擺脫對超驗因素的屈從,從中清除所有的超驗自戀症,並使它從尋找業已喪失的起源的惡性循環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除了外在的聯繫,新文化史學也積極認可為語言所表述的思想中個人的理性和創造力。約翰·波科克和昆廷·斯金納的作品里,注意到了各種群體在不同時期的政治對話中使用的語言。這些語言包含、反映和限制了話語參與者的觀念世界。他們不再通過選擇一些個人的思想來重現過去的抽象觀念,而是把思想史看作是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之間的思想交流。儘管話語有許多層次,但這些語言仍能使權威的意圖得到肯定。金茲伯格在《乳酪與蛆蟲》中則明確提出,即使像麥諾齊奧這樣的下層人物,也不是被動地接受精英的和傳統的文化影響,而是用他頭腦中一個“過濾器”以扭曲、修正甚或篡改的方式處理外來的信息,然後才形成自己的看法。
同時,新文化史學還以印刷業、新聞業和書籍業的發展過程為線索,為過去的思想和觀念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建立了另一個鏈條:它們在歷史上是如何傳播和交流的?作為思想的載體,書籍等又是如何改變既有價值觀念的?這樣,書籍史、印刷史也為羅格·夏特爾這樣的新文化史學家所鍾情。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史在這一思路下的獲得新生,因為印刷品和書籍作為一種新式傳媒是各種政治勢力鞏固自身地位最得力的武器之一。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出版於1992年的《塑造路易十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作為新君主的代表,“太陽王”路易十四無論是在世時,還是死後至今的三百多年裡,有關他的相貌、武功偉績的紀錄和描寫,以及他統治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情形的探討,已數不勝數。然而,伯克在路易十四的公眾形象中發現了“榮耀”的觀念;在肖像中,路易十四的形象往往表現得威風凜凜、英姿煥發,特意展現他那熱忱、威嚴和不輕易露出微笑的表情,還有作為權力象徵的高跟鞋、斗篷和披風。在有關他的詩歌里充滿了對他的不朽、明智、公正等讚譽,他的紀念章、銅像、油畫等等種種藝術形式都用來展現這位國王的榮耀。有些藝術史和文學史的研究者曾分別對路易十四在繪畫、雕塑、紀念章、文學作品中呈現出來的形象作過探討,但伯克借用了“媒體”、“宣傳”等概念,使關於路易十四的各種藝術形象得以綜合成一種整體效果。作者把塑造路易十四的整體過程視為一個集體的、系統的工程,一種自我包裝和推銷的活動,著重考察了象徵形式的製造和傳播。作為國王,路易十四不同於一般人之處在於,他的形象塑造得到了特殊的幫助,也就是當時的畫家、雕刻家、版畫家、裁縫師、假髮製造人、舞蹈老師、典禮儀式主持人和建築設計師的幫助,從而主動引導大眾形成有利於增添國王威嚴的認識。
從宏觀層面看,新文化史學並沒有擴展歷史學的研究領域,但它打開了歷史上的某扇門,或者是某個人的行動,或者是某個事件,或者是某種觀念,然後帶領讀者進入個人與集體、客觀環境與自由意志、物質與精神的網路,真正實現了文化與社會的綜合。這正是費弗爾所希望達到但沒有實現的目標:“人不可能被雕刻成一些片段,他是一個整體。我們也不可能分割已經完成的事實——這裡是事件,那裡是信仰。”年鑒學派雖然提出了總體史思想,試圖把“歷史綜合理論”從探討階段推進到具體實踐階段,但他們的途徑是通過集體努力來實現多學科的綜合。因此,儘管他們擴展了僅以政治、軍事外交為對象的歷史研究,但仍然沒有在個人和結構之間建立一種互動的關係。在年鑒學派的實踐中,各個領域並未能能達成系統的綜合,政治史仍是政治史,經濟史仍是經濟史,社會史只是社會史。比如說對於資本主義的研究,就是由幾位學者分別撰寫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然後組成一個整體的資本主義歷史。結果歷史學非但沒有總體化,反而被“碎化”了。新文化史學則呈現了不同的面貌,每一本成功的著作,都以個體的方式實現了歷史的綜合。
下面,我們以卡爾洛·金茲伯格的《乳酪與蛆蟲》為例,一窺新文化史學呈現的歷史綜合形象的魅力。這本書抓住了磨坊主麥諾齊奧與眾不同的世界觀,對一個不可能載入傳統史冊的小人物與他所處時代的關係進行了全面的梳理。麥諾齊奧拒絕將世界的產生歸於神意,不承認世界是上帝創造的,而認為“一切都是混亂”,上帝和天使的創造類同於乳酪腐爛、蛆蟲出現。在他看來,天堂也不是上帝統治、不朽靈魂居住的地方,而是一個吃喝娛樂的宴會;進入天堂不是緣於苦修,而是每日辛勤工作的結果。與此相反,人間的天堂就是那些擁有大量財富、不需要勞動的紳士們的生活;教士如同人間的魔鬼一樣,洗禮和懺悔等聖儀都是人所發明的商品而已,是教士用來剝削和壓迫信徒的工具。他對其他宗教沒有褊狹的態度,認為“上帝將聖靈給予了所有的人,基督徒、異教徒、土耳其人、猶太人,他們都是珍貴的,能以同樣的方式得到拯救”;“由於教會行為不端,奢侈浮華,因此,我嚮往一個新的世界和生活方式”。
不僅如此,麥諾齊奧還非常願意與他人一起分享自己的觀點。他對妻子、鄰居、村裡的其他人以及他所能遇到的一切人談他的想法,甚至站在教庭法官面前,他還想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看法。他還說,如果可能的話,他願意向領主、國王和教皇說出自己的想法,因為他“明白自己想法的來源”。《乳酪與蛆蟲》的作者注意到,麥諾齊奧的言談並不是瘋子的胡言亂語,而是態度嚴肅和認真的。但是,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並不能明白和理解他的想法,親人疏遠了他,周圍的人也都不理睬他,正統的教會更無法容忍他的那些想法,以至視他為危險的異教徒、思想的犯罪者。
那麼,麥諾齊奧的想法究竟來源於何處?是如何形成的?是來自某種神秘的天啟,還是人性的覺悟?麥諾齊奧並沒有明確告訴人們他的想法究竟來源於何處。這本書的魅力就在於作者利用有關材料,大膽地、富有啟發性地探索了這些問題。
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是傳統解釋模式強調的一個重要方面。金茲伯格首先也考察了麥諾齊奧所生活的16世紀下半葉義大利弗瑞烏里地區的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農民和貴族、外來者威尼斯人和當地人之間矛盾複雜,但在麥諾齊奧腦子裡只有一個簡單而清晰的印象:社會由“上等人”和“窮人”組成。他知道自己是窮人中的一分子,領主、國王、貴族等都是上等人。但他認為最主要的壓迫者是教士等級,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屬於教會的某個主教或紅衣主教”。這是對農民社會裡的階級結構進行純粹的兩分法的典型觀點,儘管麥諾齊奧並不能準確地為自身的處境定位。另一方面,麥諾齊奧也意識到了自己的權利,並依據這個權利抨擊了教會和教士的腐敗和專權。這顯然受到了宗教改革時期對權威原則進行衝擊的影響,儘管從他的言談中分析,他所受到的宗教改革的影響微乎其微。顯然,僅僅把握當時的社會現實、傳統思潮這些宏觀的外部因素,並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那麼,只能從主人公自身的活動中去尋找答案了。麥諾齊奧沒有聲稱自己的觀點受到特別的啟示或點撥,因此可以將他與預言家、雲遊四方的教士區別來。對個人而言,書籍通常是獲得信息、形成看法的一個極佳途徑,麥諾齊奧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作者因此根據他的回答整理出了一份他所提及的閱讀過的書目。到這裡,答案似乎已經很清楚了。然而,細心的作者還是發現了某些疑點:一是這些書大多是麥諾齊奧借閱的,而不是他自己購買的,這說明讀書已經成為當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書目不能反映其真實的閱讀傾向,因為它們不是個人有意識的愛好和挑選。二是這個書單並不完全,因而僅通過這些書名,並不能解釋他如何形成了“瘋狂的觀點”。
求解之路似乎又一次走進了死胡同。對他所閱讀的書籍內容進行分析固然很重要,但了解他是如何讀這些書的恐怕更重要。作者敏感地捕捉到麥諾齊奧宣揚自己觀點時帶有的一種自信心,這說明他並非被動地接受他人的觀點。那麼,麥諾齊奧如何閱讀他提到的那些書呢?作者大膽的但卻不是胡亂猜測的設想,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超越時空的思想世界:“關鍵是他已經超越了文本,在自己和書面文字之間無意識地放置了一個屏幕:一個能夠強調某些單詞而忽略其他單詞、脫離一個單詞的背景而將其意思延伸的過濾器。它作用於麥諾齊奧的記憶,扭曲了所讀文本的單詞。這個在他閱讀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屏幕,不斷將我們引向一種非常不同於我們書面表達的文化—建立在口頭傳統上的文化。”因此,歸根到底,“不是書本,而是書面文字與口頭文化的碰撞,在麥諾齊奧的頭腦中形成了一個爆炸式的‘瘋狂觀念’”。就麥諾齊奧的閱讀而言,他頭腦里的“過濾器”遠比他所閱讀的“材料”更重要。
作者隨後在書中將麥諾齊奧的言談與他所提及的書籍當中的對應段落作了逐一對比,具體分析了他的閱讀方式。作者指出,麥諾齊奧的閱讀習慣是片面、武斷的——幾乎只是為了印證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和信念才去閱讀書籍。有時,他改變了文本強調的重點;有時,他將文本中的記述變成了完全相反的故事。14世紀中期由約翰·曼德維爾爵士撰寫的《旅行記》曾對麥諾齊奧產生過直接的影響。即使對於這本書的理解,他也以自身的宗教激進主義為先入之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本的原意。他的宗教激進主義一方面來源於中世紀的宗教寬容,從中汲取了營養;但另一方面則更多地體現了與當時複雜的宗教理論以及受過人文主義訓練的異端的共同之處。
因此,作者分析道,麥諾齊奧的表述,諸如“母親子宮中的孩子”,“上帝是人類的父親,也是權威的形象,是不需要用雙手勞動而把繁重工作交給下人的地主”等等,混合了來自上層和下層的語彙。一方面,麥諾齊奧是普通民眾中的一員,口耳相傳的生活經驗,決定了他的世界觀基本上是物質的—比教會關於創世紀的教義更科學;另一方面,與大多數文盲村民不同,他能夠閱讀,這又使他有可能超越已有的認識。作者強調了宗教改革和印刷術在文化傳播和區別不同階層文化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認為前者使一個簡樸的磨坊主敢於想到要說出他自己關於教會和世界的觀念;後者使他有機會運用詞語來表達頭腦中模糊的未曾說出口的世界景象。最具革命性的因素體現在他對“新世界”的嚮往中。這個“新世界”既不是中世紀原始的以牛奶和蜂蜜為目標的烏托邦主義,也不是沒有社會制度束縛、沒有家庭、沒有財產、完全性自由、不需要工作、共享所有物品的國土,而是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形象。它不是通過上帝在雲端的顯靈,而是通過他這樣的農民的鬥爭來實現。“他以無意識的開放心靈,利用了其他人的思想來建構自己的想法。”
在充分展示了麥諾齊奧獨特的思維和精神世界之後,該書的結尾部分又引入了同時代其他有關磨坊主的教會審判案件,試圖將他與一個更普遍、更廣泛的由小磨坊主構成的文化聯繫起來,並將觸角伸及農民的人文主義文化和16世紀歐洲的主流文化。作者指出,麥諾齊奧的經歷不是惟一的。這位磨坊主被指控為異端,這本身就反映了農民和磨坊主之間長久的敵視立場。在歐洲的前工業社會中,以水或風為動力的磨坊是當地居民社區的中心,儘管是一種最小的中心。磨坊主在大眾心中的形象是“精明、奸詐,註定要受地獄之火的炙烤”。然而,在當時相對封閉和靜止的社會裡,磨坊不僅是一個聚會和社會交往的場所,也是一個思想交換的場所。這種工作環境使磨坊主特別容易接受新思想,也很方便宣傳新思想。磨坊主具有直接依附於當地封建領主的一種特殊社會地位,也會將他們與當地居民生活的社區分離開來。同時,16世紀的教會,無論是耶穌教會還是新教教會,都加強了對邊緣群體如流浪漢和吉普賽人的控制,加緊了對巫師的審判。在精英階層迫害和消滅大眾文化的企圖這一背景下,麥諾齊奧的個案可被視為對他們的企圖作出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