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
清代著名書畫家、篆刻家
趙之謙(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漢族,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初字益甫,號冷君;后改字撝(huī)叔,號悲庵、梅庵、無悶等。清代著名書畫家、篆刻家,與吳昌碩、厲良玉並稱“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與任伯年、吳昌碩並稱“清末三大畫家”。
從青年時代起,就刻苦致力於經學、文字訓詁和金石考據之學,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尤精書畫、篆刻。在繪畫上,他是“海上畫派”的先驅人物,其以書、印入畫所開創的“金石畫風”,對近代寫意花卉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書法上,他是清代碑學理論的最有力實踐者,篆刻成就巨大,對後世影響深遠。近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畫家都從他處受惠良多。著有《六朝別字記》《悲庵居士文存》等,又有篆刻《二金蝶堂印存》。
1884年11月18日去世,享年53歲。

趙之謙像
自幼讀書習字,博聞強識,曾以書畫為生。參加過三次會試,皆未中。四十四歲時任《江西通志》總編,任鄱陽、奉新、南城知縣,卒於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畫風工麗,后取法徐渭、朱耷、揚州八怪諸家,筆墨趨於放縱,揮筆潑墨,筆力雄健,灑脫自如,色彩濃艷,富有新意。其書法初師顏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書,筆致婉轉圓通,人稱“魏底顏面”;篆書在鄧石如的基礎上摻以魏碑筆意,別具一格,亦能以魏碑體勢作行草書。趙之謙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后追皖派,參以詔版、漢鏡文、錢幣文、瓦當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變,意境清新的獨特風貌,並創陽文邊款,其藝術將詩、書、畫印有機結合,在清末藝壇上影響很大。其書畫作品傳世者甚多,後人編輯出版畫冊、畫集多種,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詩》《勇廬閑詰》《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譜》。此外趙之謙撰有《張忠烈公年譜》,以編年的形式敘述明末抗清名將張煌言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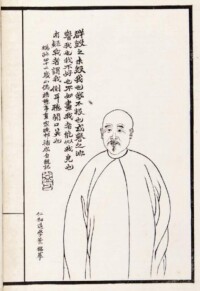
趙之謙半身像
趙之謙在《章安雜說》中記道:“二十歲前,學《家廟碑》,日五百字。”可見其於顏體,用功極勤。然而時世之變,帖學漸衰,碑學方興,歷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為所說的:“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趙之謙處於此時此境,以其性格,絕不甘落人之後,憑其才能,亦必定成為時代的弄潮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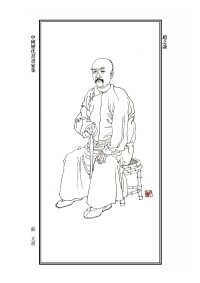
趙之謙畫像
然而,觀趙之謙三十五歲后之書,甚至是四十歲前後書,風格雖初步形成,而乏筆力,其中運筆、轉折、連接,多有勉強之處。正如他在致魏稼孫函中所說的:“弟此時始悟通自家作書大病五字,曰:起訖不幹凈。(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萬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則其中神妙處,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這一“起訖不幹凈”五字病,在行書方面,顯得更為明顯。大約是在四十歲之後才逐漸得以解決。確切說,是在赴江西任前後—四十四歲前後完善定格,五十歲以後最終完成而至“人書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稱:“漢后隋前有此人”,信然!
上溯秦漢,下開風氣,篆隸行融會貫通
趙之謙於篆書,或因其學篆刻,最初源自鄧石如、吳讓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響。當時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趙之謙亦學此而只擅長小篆,大篆作品極少,能見得到的僅一橫額,故不足論。清代善篆書者以鄧石如為第一,這在趙的時代已成定論。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錢坫、孫星衍等篆書高手,皆重玉筋篆,乏變化,不合趙之謙性格,故不為趙所重。鄧之後,張惠言、吳讓之、德林傳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則於此道有專長。趙在五十四歲為弟子錢式臨《嶧山碑》冊時寫道:“嶧山刻石北魏時已佚,今所傳鄭文寶刻本拙惡甚。昔人陋為鈔史記,非過也。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后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觰甫。熙載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錢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鄧法書繹山文,比於文寶鈔史或少勝耳。”這其中出的種種種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則是師法鄧石如。然而,趙之謙與吳讓之的最大區別,便是不墨守成規,師法鄧石如而不死守鄧法,化人為己用。他評鄧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吳讓之天一人九;自己則是天七人三。憑天分則在諸人之上。因此,從心底里,他也不服鄧石如,以為經過努力,除卻“起訖不幹凈”五字病,則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
趙之謙三十四歲臨《嶧山碑》冊及前後篆書作品,結構在鄧石如、胡澍之間,筆力尚乏沉雄。中年為鶴年臨李陽冰《城隍廟碑》等篆隸二體團扇中篆書,將結構美化到了一個極致,在鄧石如、吳讓之、胡澍之外,別出新意。而此新,則主要在於“結構”之美。隸書對於趙之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附帶性的書體。他曾說:“生平因學篆始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正書—北魏書是趙之謙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稱“僅能作正書”,篆隸則是為正書的學習作鋪墊。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實際上趙之謙的篆書已如前述,而隸書亦自成家。

趙之謙書法
趙之謙初學鄧石如,而後上溯漢碑。以趙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於某家某體,甚至某碑,故其師法漢隸,終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見到的約三十五歲前後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為幼堂隸書七言聯》(40歲)、《隸書張衡靈憲四屏》(40歲)、《為煦齋臨對龍山碑四屏》(41歲),則已入漢人之室,而行筆仍有鄧石如遺意。晚年如正書,如篆書,沉穩老辣,古樸茂實。筆法則在篆書與正書之間,中鋒為主,兼用側鋒。行筆則寓圓於方,方圓結合。結體扁方,外緊內松,寬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傾之勢,奇正相生。
趙之謙作品最多、傳世最廣的是行書。三十五歲前作品多行書,皆自顏體,細審之,與何紹基有同出一轍者,溫文爾雅,雄渾而灑脫。三十五歲時,在四月為厚夫作行書七言聯:“參從夢覺痴心好,歷盡艱難樂境多。”還依然顏面,而在一個月之後為子蒓作行書八言聯:“春雲乍陰,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遊仙。”則開始疏遠“顏風”了,在十月作篆書四言聯為魏稼孫補款時,則字形由長方變方扁,雖然點划還未完全脫離“顏風”,而已由量變開始質變。三十六歲之後此種顏體行書便再不復作。三十七歲前後以北碑法試作行書,多牽強之處,其自評之“起訖不幹凈”五字病,在這一時期可以明顯看得出,轉折不自然,筆力亦靡弱。眾所周知,趙之謙北魏風行書是其獨創,前無古人。鄧石如開北魏書風氣,而其行草則不作中鋒行筆,而用卷鋒,裹筆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則未脫唐人風範。唯有趙之謙,始將北魏書筆法直接運用到行書之中。因此,它沒有前人所遺留下的“參照物”,而且由於北魏書獨特的用筆方法:卷鋒加側鋒轉換為中鋒,很難於連貫。對此,趙首先是在“文稿”小行書,或者說小字落款中得以解決。四十歲前後的款書已經自然老到而全然無生硬之處,雖筆力還不夠渾厚,而行筆已無不暢。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行書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於正書、篆書以及隸書,是最後才得以羽化成形的。四十五歲以後,心手雙暢,已能隨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從筆驅毫,揮灑自如。趙之謙曾自稱:“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其實趙之謙晚年作品中行書佔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間以北魏正書論趙之謙,而忽略其它書體,以至於視北魏風行書為“趙之謙北魏書”,而不予以區別。大凡有成之書家,必自正書入,而以行書結。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趙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書法,多掛軸於牆面來欣賞,更是注重行書作品。儘管趙以北碑名世,傳世仍以行書為多。這大概是世人對書家的要求。
一個人的書風,各種書體最終如果能得到統一,則其必具獨到風格。五十歲之後的趙之謙,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種書體均已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趙之謙平生少作草書,從中年草書《為犍汀草書集聖教序聯》觀之,渾厚質樸中見飄逸,亦全出自北魏筆法。

徐君陶繪《趙之謙》
從他的畫中題款,我們可以看到他所取法的畫家有:吳鎮、李鱓、張彥、馬元馭、惲壽平、張敝、王武、蔣廷錫、陳洪綬、寄塵、李方膺、金農、鄒一桂、周之冕、陸治、高鳳翰、邊壽民、王蒙、錢載、王宸、沈襄等等。這其中,提及最多的當是李鱔,其次是惲壽平、徐渭等。

趙之謙畫作
但趙之謙更長於分析綜合,他把惲南田的沒骨畫法與“揚州八怪”的寫意畫法相結合。特別是汲取李復堂(鱔)小寫意的手法,以“南田”設色出之。將清代兩大花鳥畫流派合而為一,創造出新的風格。由於他書法功力深厚,線條把握精到,以這種富有金石氣的筆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橫生。運用各體字體題款,長於詩文韻語,這也是他高出其他清末畫家,成為繪畫巨匠的一個重要因素。他是詩書畫印有機結合的典範。
綜觀趙的傳世畫作,最令人讚歎的就是他的繪畫題材,畫前人所未畫。三十三歲時為避戰亂而客居溫州一帶,在那兒見到了新奇的花卉和海產品,他將所見一一寫入畫中,從而大大開拓了繪畫的題材。他的《異魚圖》、《甌中物產卷》、《甌中草木圖四屏》等等,成了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傑作。
由於他高超的藝術成就,以上海為中心的藝術家們,特別是吳昌碩等新一代受趙之謙影響,逐漸形成了嶄新的流派—海派繪畫。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中這樣寫道:“會稽撝叔趙之謙,以金石書畫之趣作花卉,宏肆古麗,開前海派之先河。”事實上,趙之謙的影響不只限於海上,肖俊賢、陳師曾等北派巨匠們也一樣受過他的影響。

趙之謙篆刻
—趙之謙篆刻
儘管趙之謙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顛峰。其中諸多的歷史經典,影響著後來的吳昌碩、黃牧甫、任頤、趙叔儒、易大廠,直至這一百多年的整個篆刻史。
篆刻
現代意義上的篆刻藝術始於明,盛於清中期,以丁敬、鄧石如為代表,開派立宗,形成兩大體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趙之謙初學篆刻之時,趙次閑、錢松還在世,皖派則有吳讓之。趙之謙家在紹興,離杭州不遠,在當時的交通以及社會環境下,受地域影響,從浙派入手,便成為必然。事實上趙之謙是從學陳曼生開始的。他三十六歲時說:“余少學曼生,久而知其非,則盡棄之。”(《杭四家印譜〈附二陳〉序》)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棄曼生,卻沒棄浙派。在三十四歲與魏稼孫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這期間的作品,大約有近百方傳世。現在能見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二十四歲的兩方:《躬恥》《理得心安》。此時印風明顯是浙派,但很快就發現有鄧石如的皖派風格的出現。二十六歲前後刻的《陶山避客》,款稱:“學完白山人作。此種在近日已如絕響。俗目既托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於時習,不知幾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鄧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則稱“略有秋景陁意”。約同年刻的《以豫白箋》和二十七歲刻的《郭承勛印》又明顯是漢印風。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作品是介於浙派、皖派、漢印之間,搖擺不定的。然而,他不滿足於浙派、皖派和漢印,而是在尋求浙、皖兩派合處的同時,上溯秦漢,進而將觸角伸向漢碑漢鏡等等。其取法之廣,是前無古人的。
辛酉冬,避亂溫州的趙之謙應在福建為官的老友付節子的邀請,航海到了福州。次年三月,魏稼孫來訪,二人一見如故,結為金石交。二人的結交,對於趙之謙篆刻藝術來說,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
魏稼孫雖不刻印,卻對印學有精解,且好集印譜。趙之謙印名在外,魏早為之心儀。相見之初,互贈詩稿,趙為作書畫。之後,一起探討印論,並請趙為其刻印。趙之謙精於篆刻,而不好刻印,“以少有合故”(《何傳洙印》款)。即便遇到魏稼孫這樣的知音,也不輕易奏刀。魏稼孫深知其為人,故以激將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提出為趙集印譜,索趙的舊作,所集不過幾十方,不足以成譜。而且面對舊作,趙之謙自己也不能滿意。為此,趙之謙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批量性的刻印,為自己,為魏稼孫,也為付節子等好友們刻。其次,二人探討印論時,魏稼孫或有意將趙與丁敬、黃易等前輩高手相比,以為趙不及丁黃,這樣激起了趙要與古人爭雄的創作心理。趙在為魏刻《魏錫曾》、《稼孫》對印時,刻款道:“稼孫目予印為在丁、黃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黃之上。”又在《趙之謙印》刻款云:“龍泓無此安詳,完白無此精悍”。又在另一方《趙之謙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更在《松江樹鏞考藏印記》刻款云:“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模印家立一門戶。”本來就不服輸,俯瞰千古的趙之謙創作欲被激發,一發而不收。他在致友人函中說:“弟在三十前後,自覺書畫篆刻尚無是處。壬戌以後一心開闢道路,打開新局。”這種創新慾望,應該說與魏稼孫的促使不無關係,而為趙編印譜是個關鍵性契機。
魏稼孫為趙集《二金蝶堂印譜》是壬戌夏開始的。趙之謙大量創作也是從這時開始的。約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後隨刻隨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譜。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歲)三年中,趙為魏稼孫刻二十多方,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應讀為韻初)刻三十餘方。加上自用印及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餘方,占趙之謙一生刻印的一半多。
大批量的精心創作,直接的原因應該是為了補充《二金蝶堂印譜》,另外一個原因,是篆刻前輩吳讓之的存在和刺激。
與吳讓之交誼
吳讓之(1799~1870年)長趙之謙三十歲,是當時惟一的前輩篆刻巨匠。魏稼孫在決定編《二金蝶堂印譜》之初,便擬請吳作序。癸亥夏秋之際,魏專程到泰州訪吳讓之,出示《二金蝶堂印譜》初稿,吳應請為作序,中云:“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贊一辭耶。”趙之謙得印譜序后,以為吳對自己的評價並不如想象那麼高,僅稱自己“已入完翁室”。這對趙之謙來說恐怕是個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開創新局,超越皖派。
這期間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風格了,而且形式多樣,變化豐富,某些印章反差極大。印風雖然未能統一,卻能反映出趙之謙一心想要開闢道路的追求。
約三十四歲刻的《悲翁》,款雲:“由宋元刻法迫秦漢篆書。”—追求“書從印入,印從書出”,強調刀筆的統一和秀美的結體。三十五歲刻的《會稽趙氏雙勾本印記》,《之謙》連珠印,《二金蝶堂藏書》等等,是其中精品。
約同年刻《魏錫曾印》,款雲:“此最平實家數,有茂字意否?”—追求漢印平實中見朴茂的境界,開趙叔儒、陳巨來為代表的近代海派印風。此類以漢印為藍本的作品是這個時期趙之謙白文印的主要取向。同年的《二金蝶堂》,三十五歲刻的《趙之謙印》,三十六歲刻的《吳潘祖蔭章》等等,皆為此類精品。
約三十六歲刻的《鄭齋所得》,款雲:“略似六國幣。”—取法漢金文,追求線條的爽朗,結構的巧妙,平中寓奇。《靈壽華館》、《鏡山所得金石》等此類名品,開黃牧甫印風。三十五歲刻的《壽如金石佳且好兮》,巧妙構思也是黃牧甫印風的基礎。
三十五歲刻的《積溪胡澍川沙沉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以《萊子侯刻石》為形式,以篆書為形體,追求古拙渾厚,啟吳昌碩印風之萌。《靈壽華館》(款稱法啶君開褒斜道碑)等印是為同類。
三十四歲刻的《錫曾審定》,繼三十一歲刻《丁文蔚》之後,再次嘗試單刀直入,開齊白石之先河。
三十五歲刻的《巨鹿魏氏》,加十字界格,師法秦印,強調刀筆並重,在鄧石如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真正去接近秦印,古典而現代。在此之前的所謂“師法秦漢”,是只師法漢印而已。這種實踐,為吳昌碩及以後的印人提供了新的模式。新發現的《靈壽華館所藏金石記》屬於此類。三十七歲之後直至四十四歲的八年間
雖然也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三十八歲刻的《為五斗米折腰》,約四十一歲刻的《安定佛再世墜落娑婆世界凡夫》,四十三歲刻的《漢學居》,四十四歲刻的《金石錄十卷人家》等等,這是他印風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可惜,八年間所刻也不到七十方。
在十年趕考,四次禮部試均告失敗之後,四十四歲的趙之謙心灰意冷,轉求實務,呈請分發,以國史館謄錄議敘知縣分發江西。為官是他的理想,他決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愛戴的好官。為此,他放棄了自己經營多年的愛好—篆刻。在壬申春(44歲)為潘祖蔭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又為胡澍刻下《人書俱老》之後,南下赴任,從此就“誓不操刀”(趙的江西任上同事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五十四歲為潘祖蔭刻《賜蘭堂》刻款中稱:“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這是趙之謙赴江西之後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後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創作的原動力。觀其一生所刻,皆是為自己及親朋好友所作,絕無泛泛的應酬作品。他曾在杭州(42歲)以字畫為生,晚年也有過應酬,但卻從未以篆刻鬻食,這表明了他不願以篆刻為生的態度。也可知其對篆刻藝術愛好的純粹。
我們不能不為他惋惜,畢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這是趙之謙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
在晚清的藝壇上,出了一個書畫篆刻都使人為之耳目一新的全能大師,那就是眾所周知的趙之謙。在書法上,趙之謙不僅精於隸書、楷書,並且對於篆書和行書也極擅勝場。有意思的是,他在《與夢醒書》中卻對自己的各體書法作出了這樣的自評:“於書僅能作正書,篆則多率,隸則多懈,草本不擅長,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然平生因學篆而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這除了隱約表示了自己於書法擅長篆、隸、楷之外,對於行、草書則有些自謙。但事實又怎樣呢?單就他的行書來看,其實造詣是很高的。從整體著眼,他的行書筆墨腴潤,風致瀟灑,有著強烈個人風格的“創新”一面,又有著符合大眾欣賞習慣的“從俗”一面,可謂推陳出新、雅俗共賞。
現藏日本的《吳鎮詩》一帖,堪稱他的行書代表作之一。作為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行書來說,在創作時既要有跌宕的風致,又要有翩翩的運筆技巧,然後才能得心應手,合情調於紙上。趙之謙在此帖中表現出來的用筆基調,無疑是紮實而又靈動的。說其紮實,無論是點畫波磔,無論是提按頓挫,全都起訖分明,交待得清清楚楚,毫無含糊拖沓的地方,可見書寫之時精神是很貫注的;說其靈動,落筆重時不濁不滯,落筆輕處血脈流貫,遊絲掩映,又頗得得心應手之妙。至於用鋒的偏正藏露,也是隨機應變,交替互出,不主故常的。而在用筆上最有特色的,則更是表現在豐腴而不剩肉、清勁而不露骨上,這是《吳鎮詩》中用筆難能可貴的地方。
再從結字來看,也是很具匠心的。在每一個字中,都有一個精神綰結的中心,然後再由中心舒展四旁,這就是所謂的斂放。如“暮雲多蕭森”句,每一字的精神綰結處,差不多都凝聚在字心的中心偏上部分。當然這是就常規而言的,其中反其道而行之的地方也不少,於此可見其隨機應變之妙了。作品中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如“愛”字的上密下疏,“澹”字的左疏右密,等等,也是較為典型的。因此造成了一種藝術上布白與留黑的強烈對比,茂密和疏朗的強烈對比。在用筆的輕重肥瘦方面,如果是左側不足的便肥重其左側,右側不足的則肥重其右側,其他上下內外等也多參用這一方法,如“風”字誇張其左垂撇,“鉞”字誇張其“金”旁,於此頗見趙之謙的匠心獨運。
在帖學漸衰、碑學興起的時代,趙之謙不但在理論上加以闡發,為北碑盛行推波助瀾,並以創新的北碑書法橫掃了因帖學及館閣體造成的媚弱書風,其功大焉。趙之謙北碑風貌的書法,在其四十歲前後已臻成熟。他取諸碑之長,領悟筆意,尤重精神氣骨。
《近三百年書學》:“學鄧石如篆書的莫友芝最好,趙之謙、吳熙載其次”。
趙之謙的作品非常受收藏家的歡迎,尤其是日本和港台、東南亞地區的收藏家。他的作品傳世不多,又不易臨仿,買家感到放心,因而價格高而穩定。在香港市場,趙之謙的作品價格起點就比較高,1986年剛出售時就達到45000港元,1987年僅一幅扇面就達到4萬港元。1989年僅出售過兩幅作品,一幅是《隸書》四屏,達到20萬港元;另一幅是《歲朝清福》橫披,達到21萬港元。1990年也僅見到兩幅作品出售,一幅是《牡丹書法》扇面,38500港元,另一件是《花卉》四屏,一舉達到352萬港元。這件作品極其精美,四幅畫中分別繪有牡丹、紫藤、桂花、梅花、色彩鮮麗、畫面洋溢著一種喜氣,引起購買者的極大興趣,競爭十分激烈。這件作品創下了清代畫家作品的最高售價記錄。
趙之謙書法竹刻作品十分罕見,圖冊中所示之件系美國亞洲文化學院藝術中心文庫(崇德宣印堂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