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天
流行於川東渠縣等地的漢族習俗
郊天,是漢族信仰習俗。流行於川東渠縣一帶。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日夜,各村農戶皆在村外南野外設置香案,擺上供品,焚香明燭,向上天跪拜叩首,祈求五穀豐收,人丁興旺。祭畢,觀察天象及其及變化,以此預測來年莊稼豐歉。
郊天是在郊外祭拜天帝的簡稱。自階級社會產生以來,古代天子往往自稱受命於天,所以,對天帝的祭禮是’相當隆重的。相傳郊天始於有虞氏時代,夏商兩代均有祭把。西周時對郊天的記述較為具體。《逸周書·作洛》稱:周代在國都外五十里的南部營建郊天祭壇。古代認為天園地方,所以郊天的祭壇為圓形,因此,古文獻中又稱郊天為泰壇、圓丘、圖丘等。《周禮.春官大宗伯》稱,郊天由大宗伯執掌,祭把的方式是“以桎把把吳天上帝”,以煙祭把稱為程。《初學記》卷13稱:“祭天日燎柴。”可見,邦天的祭把除其它物品外,主要是點燃柴堆,直達上天。關於郊天的時間,《左傳·襄公七年》稱:“啟蟄而郊,郊而後耕。”這裡的“郊”,指的就是郊天,郊天在啟蟄(古代節氣名,當時尚未具備二十四節氣)后舉行。漢代以後的郊天祭禮,又大都在冬至時舉行。據《宋史·禮志二》記述:漢代郊天一般在冬至日丑時開始舉行。丑時為深夜,深夜在祭壇上炳柴,帝王率領群臣拜把上帝。漢代以前,三代另有“迎氣”的活動,即認為五天帝掌管春、夏、季夏、秋、冬五個季節。每季節到來之時,在郊外舉行迎接五天帝的祭把,這就是“迎氣”。戰國后迎氣併入郊天祭把,五天帝也作為郊天時的配享。秦時配享四帝,漢高祖增設五天帝,漢後部天配享神位擴大,東漢時所奉天神達1514個之多。同時,隨著中央專制主義的不斷強化,為了“尊把世統、以昭功德”,漢文帝后,歷代開始以帝王祖先神與天帝一起配享。郊天的祭把也是古代帝王家天下的象徵,除了天子,其他任何人不得舉行郊天活動,否則即被指責為“僧越”。歷代帝王即位后,也以祭把天帝說明白已是正統王位的繼承者。因此,郊天的禮儀在古代經久不衰,影響很大,歷代制訂禮儀,均把郊天作為吉禮的第一位,其祭把用品為太牢,等級為大毒巳。

郊天
關於鄭、王兩派的爭論,《禮記·郊特牲》首節孔疏有一個極簡要的概括:“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郊、丘各異。”這裡所引《聖證論》的觀點,即王肅的觀點,(註:《隋書·經籍志一》:“《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三國志·魏書·王朗傳附子王肅傳》:“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書今佚。)而所謂鄭氏,即指鄭玄。因為這裡的概括過於簡略,故需稍加說明。

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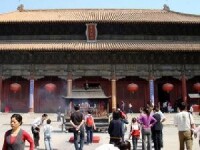
郊天
鄭、王二氏之說對後世影響極大,後世儒者關於郊天禮的爭議,實皆由鄭、王所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鄭、王二氏之說所涉及的問題作一番考察。
鄭玄的“六天說”實出自緯書,其怪妄自不待言。而且這是漢人的宗教神學思想,決非周人的信仰,鄭玄用以說周禮,自屬荒謬,毋庸深辨。後世治鄭學的人,頗有為其“六天說”辯護者,不過是堅持門戶之見。然即使不信“六天說”的學者,亦多采其圜丘祀天之說,如清人秦蕙田雖力駁鄭玄的“六天說”,卻仍以為“冬日至以禋(yīn)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乃虞夏商周四代“天子祀天正祭”。”因此必須首先弄清楚的是,西周時期究竟有沒有所謂圜丘祀天之禮?
“圜丘”一詞,始見於《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鞀,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周禮》中“圜丘”一詞,亦僅此一見,而傳世之其他先秦文獻亦皆未見。且就圜丘之祭禮而言,此處明雲“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所祭不主於某神可知。而鄭注則曰:“天神則主北辰。”此所謂北辰,即緯書所說的“天皇大帝”。(如《太平御覽》卷684《服章部一·總敘冠》引《春秋合誠圖》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這樣,《大司樂》此文,便被解釋成圜丘祀天,亦即祀“天皇大帝”或“昊天上帝”之禮,故鄭玄注《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更明確地說:“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
然上引《大司樂》之文,不僅未明雲於圜丘祀昊天上帝,且《史記·封禪書》所引古《周官》此文,文字亦與之相異,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此處唯雲“祀天於南郊”,不雲“圜丘”。又《大司樂》載祭地之禮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而《封禪書》引古《周官》此文則曰:“夏日至,祭地祇(qí)。”亦無“方丘”之文。相反,秦與西漢時期,倒是有圜丘祭地神的例子,且以為圜丘在“澤中”,而非“地上”。如《封禪書》云:“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二曰地主,……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雲。”是秦始皇時以澤中圜丘為祭“地主”之所。《封禪書》又云:“其明年冬,天子(指漢武帝)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後土,後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後土祠汾陰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孝武本紀》及《漢書·郊祀志上》所記同)是漢武帝時亦以澤中圜丘為祭地神後土之所。到西漢末年王莽時,議祀天地之禮,引《周禮·大司樂》之文,始同於今傳本,而不同於《封禪書》所引古《周官》。《漢書·郊祀志下》云:
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
因此我很懷疑今本《周禮·大司樂》之文中所謂“圜丘”、“方丘”字樣乃西漢後期王莽時所增。其實凡先秦文獻所見祀天正祭之禮,皆曰郊天、郊祀,或徑稱郊,其例俯拾即是,而從不見“圜丘祀天”之說,足見此說非周代祀典之實錄。

郊天
自(秦文公)未作畤(zhì)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雍東有好,皆廢無祠。據《秦本紀》,鄜(fū)畤之作,在秦文公十年(前756),時當東周初年。而未作鄜畤之前,雍旁即“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畤好”,且已“皆廢無祠”,則武、好二畤必為西周時期所建。(註:王學禮在其《隴西秦漢尋蹤——古上畤、下畤的發現》(《社科縱橫》,1994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武、好二畤是“軒轅氏黃帝建的”,蓋據《史記·封禪書》引“或曰”所謂武、好二畤“蓋黃帝時嘗用事”一語所作的推斷,實不可信。)又雍地近岐,而秦被封侯並被賜以岐以西之地,是在秦襄公時,即在周平王初年,則武、好二畤必非秦人所建(註:秦最早所建的是西畤,是在秦襄公封侯之後,這是《史記·封禪書》有明文記載的。),而原為西周時期周王郊天之所。又《說文·邑部》“郊”下曰:“距國百里為郊。”又據《司馬法》說:“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據此說,則郊壇當在國之近郊。而雍地之武、好二畤距宗周鎬京,皆遠在百里以外,(註:宗周鎬京在今西安市西南。吳陽武畤,據王學禮《隴西秦漢尋蹤——古上畤、下畤的發現》一文考證,在今甘肅華亭縣,距宗周將近1000公里。又漢有好畤縣,因古有好畤而得名,屬右扶風(見《漢書·地理志上》),在今陝西乾縣(參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圖15-16,中華地圖學出版社1957年版),距宗周將近250公里。)則武、好二畤不在周都之郊明矣。其實一直到秦和西漢時期,行郊禮也不一定在國郊。如秦都咸陽而郊雍之四畤,漢都長安而郊雍之五峙,又郊甘泉太一(皆見《封禪書》),都不在國郊。行郊禮而必於國郊,是到西漢末年才定的制度。由上可見,“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而不可望文生義以為說。
西周行郊天禮是否築壇?這也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漢以後有築壇之例,如文獻所見最早有漢文帝於渭陽築五帝壇,後來武帝於長安東南郊築太一壇(皆見《封禪書》)。周秦時期是否有壇,因史無明文,已不可確考。即如雍地周之武、好二畤,秦之四畤,其形制如何,今皆不可得知。《史記·秦本紀》“(秦襄公)祠上帝西畤”下“索隱”曰:“祠白帝……謂為壇以祭天也。”是乃唐人之說,不可據信。至於禮書所記及經師之說,則自來不一。如《禮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是以為有壇。《郊特牲》則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禮記·禮器》亦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是又以為無壇。又《周禮·大司樂》之“圜丘”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鄭注無說。賈疏曰:“按《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是以圜丘為自然之高丘,而非人功所為。又《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下孔《疏》云:“《爾雅》曰‘非人為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然此疏又引王肅云:“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雲‘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是王肅亦主有壇,且以為圜丘就是泰壇,乃人功所為。後世學者多主有壇說,所爭議者,在於圜丘是否人為之壇,或圜丘是否即泰壇。(註:參見秦蕙田《五禮通考》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黃以周《禮書通故》卷12《郊禮通故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在這個問題的爭議中,鄭玄的圜丘與泰壇分異說實本於其“六天說”,(註:鄭玄說泰壇,僅一見。《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鄭註釋之曰:“封土為祭處也。”是以為泰壇乃人工所築之壇。據孔疏,《祭法》此文是“論祭感生帝於南郊”,是即鄭玄所謂郊祭“五帝”之禮,而非祭至上帝“昊天上帝”,祭“昊天上帝”則當於圜丘。)自不可信。而王肅的郊丘合一、郊必築壇以象圜丘之說,亦屬臆鑿。且如前所考,西周本無所謂“圜丘祀天”之禮,則有關圜丘與泰壇關係之論,自屬無謂之爭。
其實關於西周行郊天禮的處所問題,所能知道的只是,周人郊天,必在地勢較高處而已。正如《封禪書》述雍畤引“或曰”所云:“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yù),故立z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雲。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漢書·郊祀志上》同這種因高而郊的禮儀,大概與傳說天帝喜游於高山、高原之處有關。如《山海經》中談到“帝”的地方很多,僅見於《西山經》之《西次三山》、《中山經》之《中次七山》和《中次十一山》的,就有十六處之多。這些“帝”常來常往的地方,都是在高山、高原之處。如《西次三山》所記為崑崙丘附近,大約當今青海高原,因為地勢崇高,所以叫做“帝之下都”。帝既喜游於高地處,因此人們即於高地處祭之,如此而已。
西周的郊天禮,就是祭天的最高祀典,此外再無所謂圜丘祀天之禮。“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西周郊天不一定在國郊,更不一定在南郊,也不一定築壇,只是擇地勢較高處祭之而已。
[1]、秦蕙田,五禮通考:卷5[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王肅,孔子家語:卷7[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唐蘭,尊銘文解釋[J].文物.1976,(1):60-63
[5]、竺可楨,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N].人民日報,1951-02-25
[6]、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M].上海:上海書店,1988
[7]、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