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
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鹽長木橋(今富亭鄉)上水村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狀元朱昌頤族孫。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及中央大學(1949年後更名南京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前著名的史學家。他較早地倡導開設中國史學原理及史學理論等課程,並講授“中國史學概論”,在中國史學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4年7月因肺氣腫病發,逝於重慶。
人物關係
宣統元年(1909年)歸國后,與魯迅同受聘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翌年改就嘉興府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后公舉為海鹽縣首任民事長,積極推行剪辮放足、破除迷信、禁止鴉片、興辦學校等新政。旋改到省教育廳任事。

朱希祖一家
1918年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教授中國文學史。不久兼任史學系主任,寫成《中國史學通論》一書及許多史論。其間積極參與推行白話文。
1921年,為北大接收歷史博物館殘存內閣大庫檔案1502麻袋,於研究所國學門設明清檔案整理會,擬定整理辦法,領導史學系學生整理研究。
1923年夏,應陝西督軍劉鎮華之請,入關中講學,摹拓漢唐石刻。
1926年夏,改任清華、輔仁兩大學教授。
1928年重返北大,任史學系主任,併發起成立中國史學會。
1930年入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
1932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長,先後撰寫《南明之國本與政權》、《南明廣州殉國諸王考》、《中國最初經營台灣考》、《屈大均傳》、《明廣東東林黨傳》等數十篇論文,成為研究南明史的權威。
1934年受聘為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同年任古物保管委員會主任。教學之餘,與其子朱偰對南京古迹實地調查,寫出《六朝陵墓調查報告》等專著,為研究南京歷史文化奠定了基石。
1935年、1936年任高等考試典試委員。
1938年隨校西遷,在四川7年中,先後撰成《偽楚錄輯補》、《偽齊錄校補》等書,以隱刺偽滿和汪偽政權。
1940年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不久即辭國史館職;3月,由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改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后兼任考試院公職候選人檢核委員會主任。
1944年7月因肺氣腫病發,逝於重慶。友好門生曾編印《文史雜誌》專號,介紹其生平。
朱希祖,字逷先。先世系出吳郡,后一遷歙縣,再遷婺源。清光緒九年(1879年),他生於尚胥里上水村。1905年,考取官費,赴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史學。與魯迅等同受業於章太炎之門。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演講三民主義,朱希祖經常前往聽講,於是欲用明季歷史,闡揚民族大義。
1909年,學成回國,擔任嘉興第二中學教員,並宣揚革命學說。辛亥革命時,他被推為海鹽縣知事,鄉里安堵。
1913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國語讀音統一會,朱希祖奉派出席。會議代表們審核音素、采定字母時眾說紛紜,久爭不決。朱希祖獨主張采古文纂籀經省之形為字母;既采其形,復符本音;凡聲母四十二,韻母十二,介母三,名為“注音字母”。代表們對此決議通過,因此,朱希祖之名動京師,國立北京大學馬上聘為預科教員,併兼清史館編纂。后因清史館總纂趙爾巽贊成袁世凱帝制,背叛民國,朱希祖遂憤而辭職。不久改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及史學系主任,講授中國史學概要、斷代史及文學史。
1919年,朱希祖在新文化運動中,也提倡白話文學,並鼓吹民主與科學等革命思潮。他以為歷史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必須用科學方法從事研究。研究歷史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科學。考證史事須以原始史料與實物為依據,決不可輕信坊間輾轉複製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時,把課程分為六系:(一)史學的基本科學,(二)史學的輔助科學,(三)史學史及史學原理等,(四)中外通史及斷代史,(五)專門史,(六)第一、第二外國語都是必修科。這種制度施行后,國內公私大學歷史系,一致採用。從此以後,中國史學乃得躋於科學之林,而史學名家培養漸多。
1922年5月,朱希祖主持明清檔案整理會,開設陳列室,供學者研究。他指導北大史學系同學整理,辦法是分為三步:首就檔案的形式分類,區分年代;次則編號摘由;再次者則研究、考證,並分類統計。以整理就緒者,送入陳列室,供人參觀,並在《北大日刊》公布其事由。他編有《內閣檔案各衙門交收天啟崇禎事迹清單》。朱希祖整理檔案的辦法為後來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軍機處、內務府、清史館及刑部等檔案所採用。
1926年,朱希祖應聘為台灣清華大學及北京私立輔仁大學教授。
1928年,他仍回北大為史學系主任,兼清華大學等教授,並於是年秋髮起中國史學會於北平。
1930年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次年,日本軍人發動瀋陽事變,東北淪陷,朱希祖深痛國難嚴重,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發揚民族精神。
1932年,台灣中山大學校長鄒魯電聘朱希祖為文史研究所主任。
1934年春應聘為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兼古物委員會委員。講學之餘,赴南京郊外作古迹調查,撰寫調查報告書,又撰《偽齊錄輯補》、《偽楚錄輯補》及《楊么事迹考》,寓古為今用之義。
1937年,全國抗戰開始,南京中央大學奉命西遷。是年11月,朱希祖隨校到了四川重慶。會教育部擬頒布大學課程標準,徵求意見,朱希祖以為歷史學系課程,當以學習理論為主;就學理言,則目的有二:一為發現歷史真相,除普通史和社會、政治、經濟為必修課外,須以考古、地史、人類、人種、言語等學為必修課,而以各種國別史為選修課,更輔以社會史、經濟史、專門史等科目;二為發現歷史真理。除普通史如社會史、經濟史、哲學史、美術史、宗教史等為選修課外,還要以人文地理學、人類學等輔之。
抗日戰爭既起,朱希祖嘗論“藉歷史以說明國家之綿延,鼓勵民族之復興”,主張政府當開館修史。
1940年2月國民政府接受朱希祖關於籌辦檔案管理總庫和國史館的提議,於重慶歌樂山設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並聘請朱希祖為總幹事。3月,又簡任他為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於是,朱希祖辭去中大歷史系主任之職,並遷居歌樂山向家灣。后又因多病,遂辭史館職務,專任考試院務。並從事著作,晝夜無間,而病勢日劇。
1944年7月5日卒,年僅66歲。
朱希祖自主持北大史學系以來,即以新史學相倡導,於南朝梁氏及南明歷史,改力最久而精深。他嘗遊歷陝西、晉北、金陵、廣州以及名山大川,訪求遺文舊事,並旁通目錄、版本、校讎金石、考古等學。曾擬編刊史學叢考,公開發表。“九·一八”事變后,嘗恨民族敗類在東北、華北、南京組織偽政權,又憤於日寇沿襲金人封建張邦昌、劉豫故技,因而勾稽兩宋史料,撰《偽楚錄輯補》六卷、《偽齊錄校補》四卷、《偽齊國志長編》十六卷,揭發敵人奸謀,揭漢奸穢跡,以昭告國人,以明學以致用之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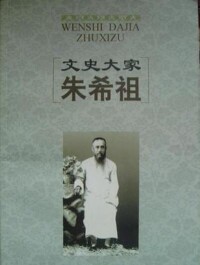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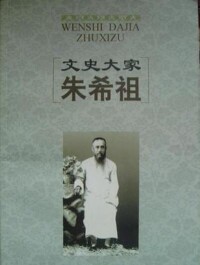
朱希祖
朱希祖開始藏書大致始於日本求學時代,到北京執教后,更是南北奔走,東西驅馳,節衣縮食,以求善本。他的酈亭藏書在學界,享有盛名。倫哲如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朱希祖》中雲:“書坊誰不頌朱胡(因當時朱希祖留有大鬍子),軼簡孤編出毀余。勿吝千金名馬至,從知求士例求書。”詩注云:“海鹽朱逖先希祖,購書力最豪,當意者不吝值,嘗歲晚攜巨金周曆書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現。又嘗願以值付書店,俟取償於書。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圖書館以至私家,無能與君爭者。”這樣幾十年積累下來,酈亭藏書全盛時達二十五萬冊,百餘萬卷,其中不乏善本,如《山書》、《鴨江行部志》、宋版《周禮》、明鈔宋本《水經注》等,均為海內孤本。其中明鈔宋本《水經注》曾被王國維譽為《水經注》諸版本中第一,章太炎、王國維二先生先後為此書作跋,許壽裳、汪東二先生為此書題籤,後來胡適之先生也為此書寫了考證文章。也正因此書,朱希祖替自己的藏書室取名“酈亭”,並請章太炎書匾。酈亭藏書以南明史料和地方志為主,以史書、文集、奏議、乃至古本、稿本為主要收藏目標。
朱希祖喜收集古籍,於明清珍刻、宋季野史、南明史籍、地方志乘、抄本秘籍,無不蒐求。最初藏書是為研究晚明史收集資料,所收稗官野史資料甚富,繆荃孫所藏野史多被他收藏,尤以明代史料為多,其它稿本、抄本為數不少,因有明抄本酈道元的《水經注》,版本極珍,遂命其藏書樓為“酈亭”,章太炎為其題寫“酈亭書室”,藏書多達25萬冊,其中有明清珍刻、宋季野史、南明野史、南明野史、地方志乘等,嘗得明影抄本《水經注》,海內孤本康熙《海鹽縣誌》等珍貴善本。據《酈亭藏書目錄》統計,約有4000餘種,分經、史、子、集和海鹽地方史志五個部分,史部書籍最多,約2000餘種,並多有藏書題跋,有“讀書藏書家”之稱。解放后,其子朱楔將部分南明史書籍及部分宋刻本出售給北京圖書館,其他大部分則捐給了南京圖書館。藏書印有“酈亭”、“朱希祖印”、“逖先讀過”等。
他撰《汲冢書考》五卷、《戰國史年表》八卷。這兩部書實是治史的典型。他搜集古籍,尤貴地方志書,所收兩廣方誌頗多,所載南明史料尤為可貴。朱希祖以金石考古為歷史研究的輔助材料,考釋《竹書紀年》,親歷南京南朝陵墓,更喜搜集古文物,有商父乙鬲、五代錢幣、雕印佛經,四川、湖北出土的宋代鐵錢、元明清三代銀幣,高麗、安南等銅幣。
張元濟長朱希祖12歲,當朱希祖14歲時,張元濟已經進士及第;當1896年朱希祖考中秀才時,張元濟已經是名動京師、變法圖強的“新黨”。但這種年齡以及身份地位上的差別,並不妨礙他們日後成為學術上的摯友。這除了他們學術興趣相近之外,還與他們是世交有關。
張、朱兩家均為浙西望族、海鹽世家,兩家為數百年之世交。張元濟先祖張惟赤(螺浮)先生,拓展先世大白居為涉園,為自己讀書、藏書之處。涉園不僅是海鹽,而且是江南的名園,四方名士來園借書、校勘、遊園,往返唱和,張氏後人張鶴徴(雲汀)先生輯四方名士唱和為《涉園題詠》,錄有桐城張英、長洲韓菼、華亭王鴻結、濟南王士禎、德清徐倬,及同縣彭孫遹、彭孫貽、朱炎等人的詩作,這朱炎就是朱希祖的族祖,號笠亭先生,有《陶說》、《明人詩抄正、續集》、《笠亭詩集》、《詩學逮津》、《金粟逸人逸事》等書行世。
數百年來,張、朱兩家一直有交往,且多次聯姻。朱希祖的夫人張維女士就是張元濟的本家堂妹。
朱希祖師承章太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費生赴日留學,后肄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那時章太炎正東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與黃侃、錢夏、周樹人、馬裕藻、許壽裳等,共同受業於章氏,聽他講說文、音韻諸學。太炎先生自撰年譜,其宣統二年條云:“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對朱氏的史學素養給予稱讚。袁世凱想稱帝,章太炎力詆之,遭袁氏軟禁,章氏以絕食相抗。朱希祖奔走營護,對章氏可謂是情誼篤深。朱希祖治史,主張“以搜集材料、考訂事實為基礎,以探索歷史哲學、指揮人事為歸宿”,認為這是“史學主體之大用也”(註: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民國初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朱希祖任史學系主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是國內成立最早的史學專業。它為史學的發展、史學成為近代化意義的科學作出了可貴的貢獻。沈兼士在《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之趨勢》中說:“民初蔡元培長北大,初設史學系,大家都不大重視,凡學生考不上文學系的才入史學系,但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學獨立的基礎”(註:《經世日報·讀書周刊》1946年8月14日)。顧頡剛也盛讚北京大學史學系的成績,說:“國立北京大學的歷史學系比較辦得理想……北京大學一向就保持著文、史、哲三門學科特別有成績的優良傳統”(註:《顧頡剛論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家》,《文化先鋒》第6卷16期,1947年)。
朱希祖任系主任時,十分自覺地推進史學的科學化,注重將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引入史學研究。羅香林在《朱逖先先生行述》中說:“北京大學史學系,首以科學方法為治史階梯,謂歷史為社會科學之一,欲治史學,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而於史實考證,則首重原始資料與實物證據”(註:《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合刊,1945年)。為了貫徹這一思想,朱希祖在史學系把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人種學、政治學、憲法、經濟學之類視為史學的基本學科,並規定為史學系的必修課。史學史及史學原理等課也被定為必修課。這類課程有:中國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歐美史學史等。由於對原始史料的重視,他支持北京大學設立研究所國學門,建立考古學研究室,積極參與保護和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工作。可以看出,由於他在北京大學的地位,朱希祖在本世紀初在建立科學的新史學方面,還是有相當的影響的。
在北大史學系,他能夠廣攬人才,耆儒新進,皆所延聘。各種學術觀點,不分派系,兼容並收,有蔡孑民先生之風度。傅振倫回憶說,當時“通儒如陳伯弢漢章、葉浩吾瀚、陳援庵、馬書平、鄧文如之誠諸師,碩學如李大釗、陳翰笙、李璜、王桐齡、孔繁燏、李季谷諸先生,咸來講學,一時稱盛”(註:《先師朱逖先先生行誼》,《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為了推進新史學的建設,朱希祖特別重視史學理論。他聘用李大釗、何炳松同時開史學理論課程,李大釗講史學思想史和唯物史觀研究,何炳松依據美國魯濱孫的《新史學》,講授歷史研究法、歷史教學法等。何氏1923年翻譯《新史學》,朱希祖為之作《序》:“我國史學界總應該虛懷善納,無論哪一國的史學學說,都應當介紹進來。何先生譯了這部書,為我國史學界的首倡者。我很望留學各國回來的學者,多譯這種書,指導我國史學界”。朱氏這種提倡各種理論并行,大膽引進和吸收西方史學理論的做法,對我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三十年代,史學理論著作大量湧現,著者很多出自北京大學,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他還建議學校當局,就文理科高材生各考選一人,派送德國。文科留學生專攻史學方法、史學史等科目。姚從吾,即是應選而赴德國留學的。姚氏曾留德十一年(1923-1934),是著名的蒙古史、元史專家。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他也造詣很深。1940年代,曾在西南聯大開設中國史學史。當代著名史學史專家楊翼驤先生就曾親受他的指導(註:寧泊:《史學史研究的今與昔——訪楊翼驤先生》,《史學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朱希祖本人那時講授中國史學概論。從內容看,他講授的實際上帶有中國史學史的性質,雖然他未採用“中國史學史”的名稱。他的講義1943年在重慶由獨立出版社出版,取名《中國史學通論》。受朱氏影響最深的是傅振倫。傅振倫早就撰有中國史學史方面的論文多篇,著有《史通之研究》、《劉知幾年譜》等。從1929年至1937年,他在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史學系教授中國史學通論。抗戰以後入蜀,1942年在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係為學生講授史學通論。1944年,他把講義整理成書,由史學書局印行,本想取名《史學通論》,為了與老師朱希祖的書相區別,改名《中國史學概要》。此書分為十篇,分別為:史之解誼、史官建置、史學起源、史書名目、史學流別、史體得失、史學名著舉要(上、下)、史學上兩大思想家、史籍之整理,並有附錄“編輯史籍書目提要之商榷”一文。雖寥寥八萬言,但對中國史學的許多方面,都有簡要的論列,是較早的關於中國史學史方面的專著。1947年,顧頡剛在回答蔣星煜的採訪時,談到當代史學史專家的成就,就提到了傅振倫並刻意說明“朱希祖之弟子傅振倫”(註:《顧頡剛論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家》)。傅氏本人也承認他在史學史方面取得成就,與朱氏的教導和鼓勵有關,他曾說:“余每有專著,輒就正於先師”,“及閱《史通之研究》,推為研究劉知幾學說之津梁,論《劉知幾年譜》,曰搜集資料甚備。……《中國史學概要》,則謂能廣師說,而備述各方面”(註:傅振論:《先師朱逖先先生行誼》,《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朱希祖南下廣州去中山大學工作,任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前身是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兼文學院史學系教授。他為學生講授元、明史,並開“史通研究”,“對於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和所舉的史實,每每有所駁正,引證贍博,聽之入神”(註:王興瑞:《朱先生與台灣中山大學》,《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那時的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是朱謙之。朱謙之開設西洋史學理論,也很受學生歡迎,史學系同學稱他們為“二朱”。朱傑勤是那時中山大學的學生。後來朱傑勤先生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也成為專家,恐怕與朱希祖早年的影響不無關係。

朱希祖
1937年8月,朱希祖隨中央大學西遷入蜀。雖感懷國難,但教學不歇。時教育部擬頒布大學課程標準,徵求意見。作為資深的史學家,朱希祖提出將中國史學史定為大學史學系必修課之一。這對中國史學史的建設是有重要意義的。1944年,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出版,即被教育部定為大學教材。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至此可以說初步建立起來了。(金氏著作,數次引用朱氏《中國史學通論》的觀點。兩書僅差一年出版,而金氏的書39年即已寫成。金氏在寫作時,大概參考了朱氏的講義稿,因那時他們都在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授。金氏畢業於北大,受黃侃影響至深,而黃侃與朱氏又曾同受業於章太炎,故金氏與朱氏也有一種師承關係,閱其講義或聽其講課都是可能的。)
作為章太炎的學生,朱氏既能夠繼承章氏治史精華,又能對西洋史學理論寬容地吸收;既重視歷史史實的考據,又強調歷史哲學的重要,並認識到史學以指揮人事為歸宿。這在新史學的建設中,就方法論而言,代表了一種正確的治學方向。中國史學的歷史非常悠久,古代的著名史學家及史學評論家在他們的著作中,談到了許多史學史的內容,但史學史在本世紀以前卻未形成專門學科。把它作為獨立的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進行建設是梁啟超在1926-1927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提出的。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幟,對傳統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積極引進西洋史學理論來改造傳統史學。隨著社會的發展,他的史學思想有所變化,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對傳統史學的態度由原來的“葬魯疏闊”的否定轉向逐步地肯定。他提出研究中國史學史,就是這種轉變的一種表現。1922年發表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其中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具有中國史學史的雛形。可見,中國史學史的產生與中西史學的交匯、中國新史學建設的需要有很大關係。朱希祖在史界革命的重鎮北京大學史學系任系主任,為史界革命的開展,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重視中國史學研究,應該說是這些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朱希祖在中國史學史方面的成就集中體現在他的《中國史學通論》里。該著本是1919年夏在北京大學史學係為學生講授本國史學概論的講義。原為三篇:一中國史學之起源;二中國史學之派別;三歷史哲學。以後在其它大學講授此講義時,刪除了第三篇。1942年,朱氏應女婿羅香林之請,決定出版該講義,附錄論文兩篇:“太史公解”和“漢十二世著紀考”。
該著對中國史學史的貢獻,應該給予積極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國史學史方面最早的講義。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在大學講堂里系統講授這類內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時寫出這個講義,與那時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改革有很大關係,是建設新史學的需要,上文已談到,此不贅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響很大,民族主義情感熾烈,國學根基雄厚,對弘揚民族文化極有熱情。所以講本國史學概論自然是他樂而為之的事情。這部講義,比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過去之中國史學界”還早二三年。可見,朱氏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總結的意識在史學界是比較早的。這點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其次,該著雖是講義之作,卻是作者潛心研究的心得,與陳陳相因之作有別。作者在自序中對一些不良學風提出批評,說:“近世治史學有不免鈔胥陋習者,或從中國名著顛倒抄襲,或從外國人著作中片段抄譯,乾沒其名,據為己有”,而對自己的講義則頗為自信,認為講義之作,雖“不足以言著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習”(註:《中國史學通論·序》)。
第三,這部著作在內容上確有許多精到的見解。
《中國史學通論》第一篇論中國史學的起源,包括七個部分:一、史學之本誼,二、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三、再論書記官之史,四、未有文字以前之記載,五、再論追記偽托之史,六、論歷史之萌芽(上),七、論歷史之萌芽(下)。關於史之本義,朱氏引許慎、江永、吳大澄、章太炎諸說,並作了進一步解釋,說:史從又持中,又為右手,中為冊字,而非“中正”之中。“史,記事者也”,所謂“記事者”,就是後世之書記官,而不是歷史官,歷史官是以後引申出來的。王國維作《釋史》篇,認為“中”為盛算之器。朱氏認為這是周制,初造字時,並無盛算之器,所以,他不採王說。
他認為,歷史之法,必為治歷明時者所創。他引《漢書·百官志》,說太史令的職掌是負責“天時星曆”,制定和頒布曆法。西周以前,沒有編年之史,西周以後,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於太史。因為太史有時間觀念,能夠發現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寫作歷史,不過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專職。漢之太史,到後漢時還專掌星曆,奏時節禁,記瑞歷災異。著作歷史,反而在蘭台東觀。蘭台東觀,本是藏書之所,所以到東漢時,並沒有歷史官專職。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晉元康初,改隸秘書,專掌史任。南朝梁、陳時,又設置史學士,至此,才出現專職的歷史官。由此,他斷言:“西周以前,無成家之歷史,魏晉以前,無歷史之專官”。至於《史通·史官篇》說的“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朱氏認為,這是把書記官誤以為歷史官了。《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曆紀成敗存亡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為柱下史,或云為守藏室史。柱下為藏書之地,老子實猶今圖書館長或圖書館書記耳,未嘗作歷史官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0頁)。總之,他斤斤致辨於書記官與歷史官之區別,破除了千餘年來歷史官起於黃帝之舊說,不失為一種新見解。
在論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記載時,他說,此等記載,不出追記,便出偽托,且偽托之書,多為神話,不足以當信史。
關於中國史學的起源,朱希祖以德國人郎伯雷希脫(Lamprecht)的理論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典籍給予揭示。郎伯雷希脫說:“歷史之發端,有兩元之傾向,皆由個人之記憶,而對於祖先尤為關切。兩元者何?即所謂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取自然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譜學,取理想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英雄詩”(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8頁)。朱氏贊同這一理論,認為中國史學的產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繫世辨昭穆之譜牒,及春秋以前頌美祖先之詩,皆我國歷史之萌芽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9頁)。談及史學的發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論:“譜學進而為年代紀(吾國稱為編年史),英雄詩進而為紀傳”(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1頁)。從原則上講,朱氏認為這一理論是正確的,但具體到中國史學上,又不完全是這樣。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是“詩最先,紀傳次之,譜系又次之,年代紀最後”(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1頁)。對此,他進行了詳細的考辨,頗有古文家的治學風格。關於這幾種史體出現的時間及其相互關係,還可以進一步考辨,但朱氏這種試圖發現中國史學產生的規律性的研究旨趣,還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還對史學和史料進行了自覺的區分,如他說:“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譜牒政令之屬,可稱史材,未成歷史,斷非魯春秋等所可比擬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18頁)。“春秋以前,年代不明。雖歷人亦多爭執異同,此譜系之所以不能稱為歷史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20頁)。史學要有明確的時間、空間要素,沒有這些要素,史學不足以成立。如《尚書·堯典》篇,所載史實前後延續一百五十年,“實為本紀之權輿”,但與司馬遷的本紀相比較,《堯典》的不足在於年代不明。《尚書·皋陶謨》,純為記敘之體,“實為列傳之權輿”,但與《史記》中的列傳相比,《皋陶謨》不書皋陶為何地人,這是史學上空間的觀念尚未發達的緣故。《堯典》、《皋陶謨》繼英雄詩而起,是史學還處於幼稚時期的作品,而司馬遷的《史記》,則是在年代記(即編年體)發生之後,史學已達進步之時的作品。朱氏通過史學要素的有無顯晦,說明史學的萌芽、產生,較為清晰地展示了史學進步的脈絡。
《中國史學通論》的第二部分是“中國史學之派別”。朱氏認為,史學有兩大派別,一是記述主義,一是推理主義。上文提到史學的發端,有兩元傾向,即自然主義和理想主義。這兩主義都包含於記述主義史學當中,但隨著理想主義的漸次進步,即產生推理主義,於是出現記述主義與推理主義兩派史學的並立。孔子修《春秋》后,出現《春秋》三傳。記述主義表現為《左氏春秋傳》,推理主義則為《公羊春秋傳》、《穀梁春秋傳》。記述與推理兩主義,其發展之難易,各不相同。中國記述主義,得以長足發展,而推理主義,自漢以後,漸次衰微。推理主義的發展,除憑藉記述主義的發展外,還必須有哲學、社會學為基礎,“於物心兩界及宇宙全體,透澈悖悟”。而我國既無系統之哲學,又無求實證之社會學,所以推理主義不能發達。
朱氏所論的記述主義和推理主義,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講的歷史編纂學和歷史哲學。也就是說,中國史學,在歷史編纂學方面發達,而在歷史哲學方面發展不足。這正與歐洲人對中國史學的評價相似。事實上,中國的史學思想、歷史哲學也是相當豐富、相當發達的,不過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點,精湛深邃的史學思想往往被更為發達的歷史編纂學所掩蓋。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沒有進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結論,與歐洲人一樣,都是較為膚淺的。
由於他認為中國推理主義史學不發達,故他於推理主義史學,略去不談,只論述了記述主義史學。他把中國史書分為七類:編年史、國別史、傳記、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紀事本末等,並對各類史書的源流、得失等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中國史書類別繁多,各代目錄學分類標準不同,所分類別也有很大差異。如《隋書·經籍志》將史書分為十三類,而《四庫全書總目》分為十五類,且各目不完全相同。朱氏的分類雖不很嚴謹,各類之間不少可以相容,但也畢竟把多數史書作了歸類,並對它們的特點予以比較正確的分析。他還糾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觀點。如劉知幾對司馬遷立《秦本紀》、《項羽本紀》提出批評:“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朱氏評論說:“子玄以成敗論人,實非公論”(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4頁)。劉知幾批評司馬遷列傳雜亂,說:“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著,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朱氏說:“子玄以為傳以記人,志以記事,自是唐代俗見,昧於傳記之原。不悟子長列傳,原有以人為綱以事為統兩類,以事為統,後世謂之叢傳,又稱匯傳,蓋書志之記事,重在政治,匯傳之記事,重在社會,例如平準書與貨殖傳,皆記財貨之事,而其注意實有不同者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5頁)。對劉知幾輕視史表、重正統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評。朱希祖對《史通》的評論,得到以後許多史學史研究者的認同,羅香林評論說:“此書駁正《史通》數十條,均為精深之論”(註:《中國史學通論·序》)。這個評論並非溢美之詞,是能夠成立的。
關於中國史書體裁的變化,朱氏這樣論述道:“此六類之史,皆由簡單而趨於複雜,又由混合而趨於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時間分)、國語(以地方分)、紀傳(如禹本紀、伯夷叔齊傳,皆先《史記》,以人分)、書(如《洪範》、《呂刑》亦開《史記》八書之體,以事分),而後有《史記》、《漢書》,此由簡單而趨於複雜者也。先有《史記》《漢書》之書志匯傳,而後有各種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趨於分析者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35-36頁)。這個認識符合中國史學發展的實際,也揭示了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史學由簡單而複雜,標誌著史學的進步:“《史記》以前,史之各體,固已有之。司馬遷特混合各體以為一書耳。此史學進步之徵也”(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1頁)。由混合而趨於分析,這看似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但卻是更高層次的回歸,是螺旋式的發展。此外,他還論述了現當代史的重要性,說:“史學要義,以最近者宜最詳,良以當代各事,皆由最近歷史遞嬗而來,其關係尤為密切,吾國史家,頗明斯義”(註:《中國史學通論》第77頁)。他以《史記》、《漢書》及歷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風尚為例,進一步說明重視現當代史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綜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從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國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概貌。雖然還很簡略,但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
《中國史學通論》就內容看,屬於史學史的範疇,主要從史官、史書體裁的變化兩個方面闡述了史學的成立和發展。但朱氏是把它當作史學概論來看的,“史學史”的概念在他那裡(至少在這本書里)並不像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當中那麼自覺和明確。1940年代,在討論大學史學系教學大綱時,他主張設立中國史學史,同時又認為“史學史、史籍舉要,亦當用其一種,不必重設”(註:羅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雜誌》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說明中國史學史在他心目中,與史籍舉要還沒有本質的區別。可見,對於如何建設這門學科,他的認識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朱希祖對中國史學研究的貢獻,我們要給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們也要認識到。
關於中國史學理論者
《中國史學通論》,重慶獨立出版社,1943年
《史館論議》(未刊)
關於史跡者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年
《汲冢書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關於史料輯錄者
《偽楚錄輯補及偽齊錄校補》,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
《孫吳佚史輯校》(未刊)
關於史學考證者
史籍、氏族、地理、金石、雜考等論文八十篇,多未發表。
關於版本目錄論文八種
《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年
其他如《酈亭藏書目錄》、《酈亭藏書題跋記》、《中興館閣書目·續目》(輯佚)、《新梁書藝文志》等,多未發表。
關於戰國史論文十五篇
未發表。
關於蕭梁歷史者七十篇二十四篇
未發表。
關於唐代歷史者十篇
未發表。
關於宋代歷史者
專著三種,僅《楊幺事迹考》於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關於明代歷史者七十篇
多未發表。
關於近百年歷史者九種
未發表。
關於中國文學史者十二種
多未發表。
關於小說經解者二種(自印一種)
詩文四十四篇
多未發表。
日記、隨筆三種
未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