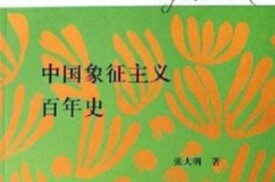中國象徵主義百年史
中國象徵主義百年史
《中國象徵主義百年史》史料豐富,全面、系統、準確。悉數囊括百年珍籍秘刊之史料精華。既無天馬行空的臆斷,也不搬運未經消化的外來教義。文風樸素、學風淳厚。《中國象徵主義百年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科研基金重點項目並獲老年科研基金出版補貼。
序 一
序 二
寫在前面
序 引
一“五四”時期(1915—1923)全方位引進初嘗異域果汁
象徵主義及其作家作品最初引進
表象主義是以暗示為根本的文藝
“靈的覺醒”——新浪漫主義文藝的核心
風格流派多樣化是文學發展的歷史趨勢
初次翻譯象徵派詩歌
評《青鳥》在中國的演出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
中國文壇第一篇專門介紹波德萊爾的文章
全面介紹“法國近代第一個詩人”魏爾蘭、“惡魔詩人”波德萊爾
首次全譯“象徵主義憲章”詩
安德列耶夫、豪普特曼
專文介紹魏爾蘭 田漢譯《秋歌》
中國人編寫的第一部《法國文學史》中的象徵主義
二 一九二五年前後(1924—1927)創作實踐 別開生面
由象徵派作家引出法國象徵主義文學歷史
張聞天譯波德萊爾研究的重要論文
《小說月報》號外《法國文學研究號》中的象徵主義論
徐志摩禮讚波德萊爾的《腐屍》
《近代文藝思潮》論象徵主義和頹廢派
李思純譯波德萊爾《腐屍》、魏爾蘭《獄中》和《秋歌》
李金髮著《微雨》出版,這是中國新文學歷史上第一部由中國詩人
創作的象徵主義詩集
戲劇家說象徵主義
魯迅論勃洛克長詩《十二個》
《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聖母像前》、《死前》、《旅心》、《野草》、《天堂與五月》、《骷髏上的薔薇》:中國詩人的象徵主義詩集集中出版,並有初步評論
三 左翼文學時期(1928—1929)象徵主義和左翼文學并行不悖
托洛茨基論勃洛克
馮乃超詩集《紅紗燈》出版
本間久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中的象徵主義
瓦萊里和保爾·莫朗
全面評說“詩怪”李金髮
梁宗岱的瓦萊里評傳
眾說紛紜話《青鳥》
陳勺水譯《萬物感應》 日本象徵主義消長圖
“雨巷詩人”第一部詩集問世
登上法國現代文壇鳥瞰象徵主義詩人
流亡到莫斯科的革命者的言論
李金髮詩風的追隨者
又一部文學史泛論象徵主義
美國人論象徵主義
徐志摩論波德萊爾的散文詩
四 一九三零年時期(1930—1931)創作面臨過渡升華理論著述逐步深入
波德萊爾散文詩譯本首次出版,並全面論述
又一部法國文學史
魏爾蘭:朋友的論述
西洋文學整體觀中的象徵主義
中國象徵派詩歌創作軌跡
梁宗岱《論詩》
不多見的安德列耶夫專論
兩部歐洲近代文藝思潮比較論
五 《現代》雜誌時期(1932—1933)《現代》雜誌創刊象徵派融入現代派
雜譯波德萊爾、葉芝、勒維爾第、果爾蒙
戴望舒詩論十七條:放棄詩歌音樂性追求,強調情緒的表現
論魏爾蘭
“靈魂的飢荒無法滿足”
象徵主義是一種情調的藝術
戰後法國文藝思潮及新興英美詩派
藝術社會學批評家論維爾哈倫
卞譯《應和》
論李金髮序《望舒草》
現代派詩的宣言
論波德萊爾和象徵主義
六 一九三五年前後(1934—1937)新詩創作豐收季節理論建設密集問世
一個象徵主義詩人的心路歷程
諸候譯《交響共感》
領會象徵派精髓梁譯《契合》
評王獨清
象徵主義否定論
象徵派與純詩
李金髮答問
波德萊爾《巴黎的煩惱》中譯本出版
經典論文:《論“現代派”詩》
穆木天講法國文學史中的象徵主義
從政治層面和思想意識層面解釋象徵主義穆譯《交響》
朱自清論中國象徵派詩人
象徵主義是個人靈感的記錄表
歲末年初:詩集密集出版
蘇佩維埃爾
梁宗岱的《詩與真二集》
馮至與里爾克
靈魂在象徵主義作品里跑馬
《望舒詩稿》
曹葆華編譯的《現代詩論》
瓦萊里的文論絮語
七 戰爭時期(1937—1949)戰爭年代象徵不興
全方位介紹象徵主義:波德萊爾等人的藝術觀
戴望舒是象徵派詩人
戈蒂耶為《惡之花》寫的長序
象徵主義表明文學的墮落
《惡之花》是法國頭等好詩
又一組望舒詩論
瓦萊里文學語錄
瓦萊里紀念專號
《中法文學》月刊出紀念瓦萊里專號
在文學史的流變中看象徵主義
在戰爭的中國再譯波德萊爾的詩歌是不合時宜的
戴望舒用翻譯出版《惡之華掇英》的實際行動回答:要辯證地對待波德萊爾留下的遺產戴譯《應和》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象徵主義觀
八“十七年”(1950—1966)視為逆流遭受厄運
詩歌中的逆流
《譯文》的紀念
《夜讀偶記》一反“五四”觀點引人深思
九 改革開放時期(1978—2000)思想解放敢於拿來
重新啟蒙
依然是否定
書話點睛
一流專家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
在新起點上認識象徵主義
中國學者新編《法國文學史》中的波德萊爾
蘇聯學者論中國象徵派
第一部研究中國象徵派詩歌的專著
多種選本問世
融會貫通的《惡之花》專論
旅美華人論中國象徵派詩歌
清點李金髮象徵派詩創作
錢春綺譯《惡之花》
中國象徵派詩歌史
第一部漢譯《魏爾侖詩選》
新穎獨到的波德萊爾論陳敬容譯《通感》
對中國象徵派詩歌的恰當解說
首部,也是唯一一部中國學者編譯的《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
戈蒂耶《回憶波德萊爾》
外國文學流派研究資料叢書《象徵主義·意象派》
馬拉梅、蘭波散文詩集首次單獨出版
人文版全譯本《惡之花 巴黎的憂鬱》錢譯《感應》
《惡之花》全譯插圖本出版郭譯《應和》
第一部李金髮傳出版
《中華文學通史》論李金髮、戴望舒
蘇聯學者論蘇聯象徵主義
年輕學者的世紀總結
寫完綴語
本書引用報刊及書籍主要目錄
李金髮(1900.11.21—1976.12.25)原名李淑良,筆名金髮,廣東梅州市梅縣區人。據他在《我名字的來源》一文中說‘1922年在法國患病,老是夢見一位白衣金髮的女神領他遨遊太空,他覺得自己沒有病死,於是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李金髮。早年就讀於香港聖約瑟中學,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學留法預備班。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就讀於第戎美術專門學校和巴黎帝國美術學校,在法國象徵派詩歌特別是波德萊爾《惡之花》的影響下,開始創作格調怪異的詩歌,在中國新詩壇引起一陣騷動,被稱之為“詩怪”,成為我國第一個象徵主義詩人。1925年初,他應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邀請,回國執教,同年加入文學研究會,並為《小說月報》、《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學秘書。1928年任杭州國立藝術院雕塑系主任。創辦《美育》雜誌;后赴廣州塑像,並在廣州美術學院工作,1936年任該校校長。40年代後期,幾次出任外交官員,遠在國外,后移居美國紐約,直至去世。
李金髮詩歌深受波德萊爾的影響。在法國留學期間,弱國子民在異族裡所受到的歧視、戀愛的無望、祖國的憂患,都使他心理籠罩在一片灰濛濛的煙霧之中。於是,以表現死亡、丑等為擅長的詩人彼德萊爾的詩歌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1921年,在飽嘗了白眼之辱的環境里,李金髮課餘就在書籍里尋找安慰,“鮑特萊爾的《惡之花》,他亦手不釋卷”了,遂成了一個“唯丑的少年”,謳歌唯丑的人生:“我撫慰我的心靈安坐在油膩的草地上,/靜聽黑夜之哀吟,與戰慄之微星,/張其淡白之倦眼,/細數人類之疲乏,與牢之不可破之傲氣。”(《微雨·希望與憐憫》)1923年春,他在德國編好第一本詩集《微雨》。在創作《微雨》集期間,李金髮讀魏爾侖、波德萊爾、薩曼、雷尼耶等的詩最多。同時,他還讀福爾·瓦雷里以及耶麥等人的詩。當時周作人、宗白華等人讀了《微雨》后,稱讚李金髮為“東方的鮑特萊”,鍾敬文認為李金髮是魏爾侖的徒弟。在柏木不滿三個月的時間裡,李金髮又創作了第二本詩集《食客與凶年》。這時他一方面由於潛心研究叔本華的哲學,愈加深了其悲觀思想,另一方面,閱讀了歌德等人的作品,詩風有所變化,較少神秘色彩。又過六個月,李金髮又寫出了第三本詩集《為幸福而歌》,從這本詩集的題記、譯詩所涉及的範圍來看,有德國的歌德、海涅,法國的雨果、夏多布里昂等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金髮的三本詩集的傾向日趨明晰:在象徵的整體特徵下,滲透了浪漫的感傷主義。儘管李金髮所吸取的影響比較雜,但是,他的詩作中最突出是對死亡、醜惡的抒寫以及始終籠罩著的絕望、鬱悶、悲哀的煙霧。李金髮有兩句歷來為人們指責的詩句:“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在李金髮看來,“死亡”是人最終的歸宿,它並不可怕,“死!如同睛春般美麗,季候之來般忠實,/若你設法逃脫,/啊,無須恐怖痛哭,/他終究溫愛我們。”(《死》)可怕的倒是現實生存。德格格爾認為,死亡能夠“使自己從普通人當中解放出來”,能夠使人一次性擺脫焦慮和沉淪的煩惱。現世生活帶給人無休止的壓抑、焦慮、厭惡,使人產生了濃重的渺小感、孤獨感、軟弱感、恐懼感,造成了普遍的“神經症人格”。怎樣消除這些基本因素呢?李金髮認為只有死亡。這裡,我們找到了詩人歌頌死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在於對醜惡社會現實的徹底絕望,或者是以死來完成對生存的最有力的詛咒。李金髮對法國象徵意義詩歌的借鑒,不是技巧上的,而是骨子裡的。這表現在他的詩與波德萊爾們的詩,有著同構的關係。李金髮詩歌中,有的提示了生命的虛無(如《希望的憐憫》),有的提示了靈魂的漂泊無依(《里昂車中》),有的詩歌頌死亡,以死來完成對生存的最有力的詛咒(《生活》),有的提示了上帝死掉後人的靈魂的不勝重負(《不幸》)。李金髮詩歌與波德萊爾的詩歌,在表現死亡主題時所使用權的意象有許多相異處,但是,李氏詩與波氏詩的相似處,是主要的。在詩的主題與抒寫對象上,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突出了三大主題:死、夢幻、愛情。李金髮的三本詩集也是如此的。傳統的中國詩歌,是少有“丑怪美”的審美心理的。我們民族肯定“生”的價值,且具有“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樂感文化特點,弱化和麻痹了知識分子對苦感、愁感、丑感、惡感的感受。在藝術表現層次上,鑄造了他們不敘苦、不言貧、羞於言苦、恥於言貧的心理。魏晉時“人的自覺”思潮對這種價值觀有所衝擊,但畢竟未能成為支配中國人靈魂的主要力量。對人生、生命、生活的強烈欲求和信念,突出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進而在否定的形式中達到對個體生存價值觀的肯定,這是近代人或者現代人的現代意識,在悲劇性的微笑中發掘“丑”之美,意義在於正視了生活落差、人生落差、命運落差在心靈上引起的酸辛。要寫出“丑怪美”的作品,必須具備三個層次:⑴生活上的“丑況”;⑵心理上的“丑感”;⑶詩人的表現意象。“丑況”在主體心理上轉化成強烈的“丑感”,但形成藝術表現的意象還需要特定的文化心理。李金髮在巴黎形成的“厭世、遠人”,“頹廢而神奇”的思想,主要並非來自民族和傳統,而是在異域受《惡之花》潛移默化的結果。例如,李金髮與波德萊爾對“死”之讚美,對“生”之厭膩,都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染上了“世紀病”,心上開出了一朵又一朵病態的“惡”之花,其主題,乃至抒寫對象都極為相象。他們對死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愛好。夢幻和愛情,又是象徵派逃避“生”之痛苦的避風港。現世生活使人有無邊的煩惱,死神又無處不在地向人微笑。固然,死是對生的煩惱的解脫,除了死亡之外,在象徵派詩人的眼中,還有夢幻和愛情。李金髮有不少詩作都寫自己對愛情至死不渝的追求,如他的《假如我死了》。這首詩假設自己死了,其幽靈夜間走近愛人的身邊,給其親吻和撫愛,並表明自己的愛情將“統治”所愛人的整個青春與生命。幻想的世界有兩種:一為天堂,一為夢境。《為幸福而歌·樂土之人們》屬前者,《微雨·寒夜之幻覺》為後者。
象徵詩派:以李金髮為代表的象徵詩派出現於20年代中期,後期創作社的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也是象徵主義詩歌的重要作者。象徵派詩人多受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影響,其作品的特點是注重自我心靈的藝術表現,強調詩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謂“觀念聯絡的奇特”。①運用一種象徵性的形象和意象來表現自己微妙複雜的內心世界,傳達對外部世界敏銳的感覺和印象。②運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現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藝術形象的暗示來表達感覺和情調。④追求詩歌語言的省略和跳躍。李金髮於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是中國早期象徵詩派的代表作,為中國新詩藝術的發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象徵派詩歌後來趨向成熟,取得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評價
被譽為中國象徵主義“第一詩人”(1)和“中國雕塑界之泰斗”(2)的李金髮無論在20世紀新詩史上或是雕塑史上都是一個繞不過的話題。歷來對李氏的研究多各執一端。研究詩人的李金髮和研究雕塑家的李金髮在兩個互不關聯的領域裡平行展開。於是,活生生一個李金髮被一分為二,見其詩人一面者因其20年代那批怪模怪樣的詩作而稱之為“詩怪”;(3)見其雕塑家一面者,則因其學成回國后在中國白紙一張的雕塑界拓荒創業而稱之為“泰斗”。然而“詩怪”與“泰斗”判若兩人,兩種身份各行其是。一個完整的包含多個側面的自相矛盾的李金髮似乎沒有真正進入研究者的視域之中,一些重要現象也因此而被遮蔽。比如:在20世紀的中國,涉足兩個以上藝術門類的文學藝術家比比皆是,在不同的領域,他們以不同的角色身份拓展著自己的空間。多數情況下,藝術家所兼具的兩種藝術身份往往互相涵養,精神氣息相通相融,相得益彰。像既是畫家又是文學家的豐子愷、凌叔華、葉淺予等就是這樣。而李金髮的情況卻有些例外。
李氏20年代涉足中國文藝界。當其時無論新詩領域或是雕塑領域都存有大片空白地帶。有所不同的是,新詩背後,站著有幾千年傳統的優秀而強大的古體詩巨人。無時無刻不處在這個“巨人”的陰影之下,新詩人所面臨的不是“創業”的艱難而是“轉型”的焦慮及壓力。不蹈前人舊轍而重創一種新詩的體式,這是20年代新詩人必需面對的最大難題。一切剛剛起步,如何用現代漢語重造一個詩的世界,如何給世間萬物及感受以新的命名,以建立新詩的體式或說一種新詩的傳統?一切尚在摸索之中。李金髮遇上了這樣的歷史時機。作為雕塑家和作為詩人:李金髮一體兩面,為歷史留下兩個絕然不同的形象。寫詩,他宣稱“我的詩是個人靈感的記錄表,是個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15)做雕塑,他則有忡忡疑慮。他一再檢討當年選擇雕塑專業時的“天真無知”(16):“沒有體會到中國現在的社會是什麼社會,藝術是否可以謀生,是否甘心一輩子過窮藝術家的生活?”(17)前者作為一種精神性的表達幾乎是不計功利不顧一切的,後者作為一種生存手段卻不得不與“價錢”、“合約”、“交易”聯繫在一起,在與位尊如宋慶齡、孫科、汪精衛之輩,財大氣粗如歌院老闆之流的扯皮中實現他的雕塑藍圖。寫詩純屬個人事件,做雕塑則是面對公眾的社會行為,尤其是歷史人物塑像,它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總擺脫不了當局者或具體歷史情境的諸多限定。因此,雕塑家的李金髮就沒有詩人李金髮的那份灑脫超然,他不得不在生存的枷鎖中小心翼翼地扮演他該扮演的角色。這種持重、穩妥的姿態在他30年代中期任廣州市立美專校長一職時體現得更加充分。事後有穗美學生回憶道:李出任穗美校長,“完全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沒有展拓藝術教育的崇高理想,充分表現當時腐化的官僚主義壞作風。”(18)此說法可能含有個人偏見,但那幾年穗美沒有明顯發展卻是事實。任何藝術家都在一定的環境中生成、發展、形成自己的面目,那怕是擁有兩種身份的同一藝術家也會在不同境遇、不同心態的制約下呈分裂狀態,其在同一時空中所進行的兩種藝術行為也可能會持明顯相悖的價值理念和審美趣向,李金髮正是如此。他是20世紀中國具體生存環境所塑造的一個藝術家,對他的雙重身份的考察,應是一個有趣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