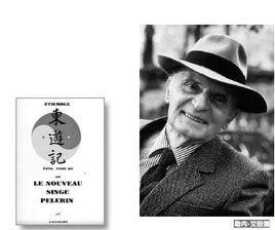艾田蒲
艾田蒲
艾田蒲是法國著名的漢學家,知名作家和當代西方最傑出的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學者,巴黎大學中西比較文學講座的主持人,學貫中西的作家與社會學教授。他研究中國和歐洲關係的兩卷集巨著《中國之歐洲》,精闢地論證了中國文化對自羅馬帝國至法國大革命間歐洲的影響,為西方人重塑了中國形象,著重闡明了人類文明是一個互相依賴、互為補充的有機體。
中學時代就讀於拉瓦勒公學,畢業後於1927年進入設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學(Lycée Louis-le Grand)的高等師範學院預科讀書,自此他開始對中國語言文學感到興趣,開始學習中文,並攻讀法國學者用法文寫成的有關孔子的著作,他迷戀孔子、莊子、老子還有荀子,認為使其受益的中國哲學家,如孔子、莊子,絕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與奧古斯丁、孔德媲美,王充勝過黑格爾。隨後,他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現代東方語言學校和巴黎大學文學院攻讀語言學,獲得在大學授課資格和文學博士學位。
1939—1943年,艾田蒲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法國語言文學教授。1943年曾在美國印第安人納瓦霍族和霍皮族地區和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有一段時間,進行人種學調查,隨後前往埃及亞歷山大大學擔任法語及拉丁語系系主任(任職期間為1944—1948年)。1949—1956年,他在法國蒙彼利埃大學擔任法國語言文學教授。1956年進入巴黎(索邦)大學擔任普通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學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
艾田蒲自1958年起擔任蒙彼利埃大學文學系名譽教授,自1979年起擔任巴黎(索邦)大學文學系名譽教授。1946—1952年為法文《現代》雜誌撰寫小說並擔任文藝評論員。1953—1955年為埃及一家雜誌和法國《證據》雜誌以及法國《新文學》雜誌撰稿並擔任評論員工作。艾田蒲還是威尼斯藝術、文學與科學院院士。他還獲有多種榮譽稱號。艾田蒲為自己取了不同譯音的中國名字,除了常用的艾田蒲外,還有艾瓊伯、安田朴、艾金伯勒等。
艾田蒲的著作數量極多,他既是小說作家,也是隨筆作家,而且一貫向法語讀者著重介紹中國文學、哲學和中國的情況。
自20世紀30年代,艾田蒲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國人譯介茅盾、丁玲、張天翼、施蟄存等人的小說,共同編寫了《公社》雜誌起,艾田蒲對中國文學的興趣與日俱增,他不僅翻譯過丁玲的作品《水》、張天翼的《恨》,還曾比較過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也比較過蘇格拉底與孔子。
他在巴黎大學多年講授中國自羅馬帝國時期到法國大革命時期對歐洲文化藝術的影響。1934年,曾和馬爾羅、瓦揚·古久列等人組織“中國之友協會”(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譯“中國人民友協),先發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發行《中國》(La Chine)。他以敏銳的目光注視中國紅軍的鬥爭事業,同年3月,以讓·魯維爾納的化名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文化生活》,盛讚當時的紅軍,對紅軍表示支持。
1956年,艾田蒲出任巴黎索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院院長,組織了亞非歐研究中心,介紹中國等東方國家文學,推動法國中學設立漢語課,促使法譯中國文學書籍出版。
艾田蒲讚賞魯迅,並引為同道。他熱烈歡呼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提議把中文作為比較文學學者的通用語言。1957年,他率領法、中友協代表團訪華,首次踏上中國本土,和中國文化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之後,他多次訪問中國,並欣然擔任中國學術團體的名譽職務。
20世紀70年代,艾田蒲主持編譯的《認識東方》叢書,主要譯介亞洲地區各國的文學作品,彙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賓、越南、日本、中國等國家的作品。在現有60種出版物中,就有《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老殘遊記》等17種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其中《水滸傳》法文譯本分上、下兩冊,由加利瑪出版社、專門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庫”發行,它是進入西方文學殿堂的第一部中國文學作品,艾田蒲寫序向法國讀者推薦。1976年出版其《我的毛澤東思想40年(1934-1974)》,書中敘述毛澤東時代中國文化的高潮與衰落,表達了他對中國的熱愛和痴迷。
1983年,七星文庫出版了艾田蒲的《金瓶梅》法文全譯本,《金瓶梅》是世界文學中最精彩的小說之一,他從文化角度對中國這部名著做了多方面的考察。
1985年8月24日,在巴黎第11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上,國際比較文學耆宿,法國的艾田蒲教授以《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為題做了他的總結髮言,那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後一次學術講演。他總體評價了這一時期中國比較文學發展態勢,並介紹了《文貝》、《中國比較文學》、《國外文學》以及台灣的《淡江評論》,評價了包括錢鍾書、季羨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還涉及到了梁啟超、王國維、魯迅、茅盾等作家的評述。
艾田蒲對中國的熱情體現在他的漢學研究中,他寫下了文論著作《蘭波的神話》、《世界文學論文集》、《論真正的總體文學》、《比較不是理由》,但寫得更多的則是漢學專著,比如《我們知道中國嗎》、《孔夫子》、《耶穌會士在中國》、《東遊記》(或稱《新孫行者》)等著作。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國比較文化研究會的聘請,擔任該會名譽會長。
最為引起世人矚目並給艾田蒲帶來真正聲譽的,是他研究中國和歐洲關係的兩卷集巨著《中國之歐洲》(L’Europechinoise,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這部800餘頁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學養、宏闊的文化視野,精闢地論證了中國文化對自羅馬帝國至法國大革命間歐洲的影響,為西方人重塑了中國形象。此書原名為《哲學之東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學比較文學教席時,曾多次給西方學生講授過。1988年,由加利瑪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庫”正式出版時,改成現在這個書名,后經中國學者、法國文化藝術勳章獲得者耿升譯介到中國,譯名為《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商務印書館,2000)。
《中國之歐洲》上卷從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一直寫到萊布尼茲同中國哲學以及文化關係的比較分析,寫的是這一歷史時期歐洲到底接受了中國哪些影響。下卷寫歐洲人從對中國的仰慕到排斥的轉變過程,並專門考證了《中國孤兒》的起源、傳播及其文化意義。
根除歐洲中心論的偏見和殖民歷史的後遺症是艾田蒲創作本書的初衷,他在書中貫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文化交流只能在不對等的前提下進行,現實存在的文化之間的差異,包括歷史經驗、政治體制、經濟實力、意識形態、乃至深層次的文化價值觀,恰恰不是文化交流過程需要迴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文化之間相互交流、和平共存的基礎。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求彌合實際上永遠無法彌合的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而是建立起一種共同認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寬容精神,在一種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的過程中,最大程度發揮和挖掘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他看來,文化關係的運動像鐘擺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狀態才能獲得動力。只有在一種競爭性的互相期望中,才能夠結出豐碩的文化成果。相反,真正實現了人們理想中的、沒有現實幹擾的文化關係的狀態,文化交往的內在動力可能也就喪失了,如同一隻靜止的鐘錶,沒有衝突,但也沒有意義。
基於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實的史料介紹了歐洲得益於中國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這部大著中準確地描繪出中國與歐洲的真正面貌,著力探討他所鍾情的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為西方文明的發展究竟起過何種促進作用?產生過何種積極影響?做出過哪些實際貢獻?他描述了絲綢之路對西方藝術的開發作用,考析了中國文化對歐洲藝術的深遠影響,探明了中國哲學對啟蒙運動的啟示。他認為,在中國比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歐洲中心論表現為無視中國文化的創造,曲解其價值而拒絕加以受用。據此,他在該書前言中援引舊作,就誰是印刷術的發明者的問題,開宗明義地向歐洲中心論發難。
在艾田蒲看來,人們過去對文化關係屬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文化關係史的不充分的考察基礎上的。文化關係史的研究,特別是東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世紀以後,當然其中包含了一些學術方面的考慮,如研究視域的空白、史料的豐富程度、學術的積累等等,但這必然造成一個後果,就是把某個特定階段的文化關係的屬性放大,上升成為普遍反映文化關係規律的認識。
艾田蒲的《中國之歐洲》改變了過去那種從孤立的短時段來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慣例,而代之以一種從全局、從長時段來考察的方法,把中國和歐洲文化的關係考察回溯到中國的先秦時代。他在對豐富的考古資料和大量的詞源學分析的基礎上,大膽地推測,實際上歐洲和中國的文化交流在羅馬時代已經非常充分了,中國和歐洲已經相互進入了對方的視野。
艾田蒲在《中國之歐洲》中通過中西文化歷史的考察,著重闡明了人類文明是一個有機體,是一個互相依賴互為補充的整體,他認為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地域的文化,無論是歐洲文化還是中國文化,都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都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應當受到平等的對待,而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獨特的,都為整個人類文化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都應該得到同樣的重視。
在《中國之歐洲》中,艾田蒲頗有深度地描述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這種哲學進程。交流是雙向的、互補的。他在考析了中國哲學對歐洲產生的影響之後,認為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輸入和吸收,往往伴隨著一種明顯的政治意圖,常持一種實用的價值取向。他在這兩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實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學家在分享中國文化時所產生的種種誤讀現象,以及造成這種誤讀的內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書中,艾田蒲表達並提出了另外一個思路,那就是“顯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隱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認為,“顯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種表現出熱潮、有意識地展開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識分子為主導,從學術的角度切入,以觀念的方式展開,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對其他文化的借鑒和進入,但也因此容易產生對他者文化的誤讀,如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中國熱、中國五四時期的西學東漸等。而“隱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對平靜的時期,它往往採用間接的、民間的、物質性的形式,在觀念的層面人們一般不會注意,它呈現的更多是一種緩慢、細微的脈動。例如,在東西文化關係史上漫長的“史前時期”,即兩種文化在意識層面直接接觸的17世紀以前的近兩千年的交流史。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們可以忽略不計,相反,這種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種更深刻、影響更深遠的交流。這種文化交流是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滲透於日常生活當中的,是以體現了另一種文化價值觀念的物質為中介傳遞的,它沒有那種顯性交流中的觀念先導,更容易進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層。
《中國之歐洲》寫了五年,但艾田蒲為此書準備了三十年,這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時,他研究法國象徵派詩人,同時研讀中文,從那以後,他一直沉醉於對漢語的研究,並“記下歐洲受惠於那些‘中國佬’的一切”。他在《論真正的總體文學》一書中也說過:“如果沒有鑽進中國這個圈子,我永遠不會獲得真實、道德和幸福”。他在致中法比較文化研究會的信中說,從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竭力堅持的一條重要生活道路”。這部凝結著艾田蒲畢生的著作表現了他廣闊的學術視野、深厚的學術功力和獨特的批判精神,一經問世,就轟動了西方,得到西方學術界高度的評價,榮膺巴爾桑比較文學基金獎(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為第一部獲此殊榮的比較文化著作,1992年由錢林森和許均翻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漢譯本。
艾田蒲終生不能忘懷的仍是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實體的存在,無論早期翻譯丁玲的《水》和張天翼的《恨》,還是對中華蘇維埃的宣傳;也無論是為中國人爭回了印刷術的發明權,還是晚年真摯地、持久地對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支持;無論是寫作《中國之歐洲》、《孔子》,還是永無懈怠地為陶潛、李白、《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在法國的問世奔波,艾田蒲都以一個世界主義者的形象出現在中國人面前。
艾田蒲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但他不是為記載“文化功勞簿”而寫此書的,如他所說,他的目的是想為學科“注入一點活力”。他的研究是不帶任何偏見的,在破除“歐洲中心論”,讚揚中國文明的時候,他也實事求是地指出歐洲文化如何傳入中國的。因此,他在闡述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的時候,總是把這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放到廣闊的世界文化背景下進行探討。在此基礎上,從世界文化的交流角度來認識人類文化相互影響及其規律。
艾田蒲曾長期在巴黎(索邦)大學主持比較文學講座,並擔任指導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比較文學研究工作的導師,對於向法語讀者介紹中國文學十分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