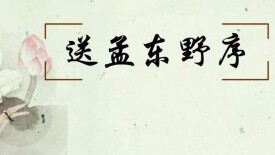送孟東野序
唐代韓愈創作的一篇贈序
《送孟東野序》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為孟郊去江南就任溧陽縣尉而作的一篇贈序。全文主要針對孟郊“善鳴”而終生困頓的遭遇進行論述,作者表面上說這是由天意決定的,實則是一種委婉其辭的含蓄表達,是指斥當時的社會和統治者不重視人才,而不是在宣揚迷信。文章屢用排比句式,抑揚頓挫,波瀾層疊,氣勢奔放;而立論卓異不凡,寓意深刻,是議論文中的佳制。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郁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屍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丑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1.撓:搖動。
2.盪:振動,振蕩。
3.躍:飛濺。激:在此意為阻遏。趨:快走,此指水流迅速。
梗:堵塞。炙:燒。
4.思:思慮。懷:感傷。
5.樂:音樂。郁:鬱結,蓄積。假:藉助。
6.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我國古代製作樂器的八種材料,一般用來指代各種樂器。金,指鍾;石,指磬;絲,指琴、瑟;竹,指簫、笛;匏,指笙、竽;土,指塤;革,指鞀、鼓;木,指祝、敔。
7.時:季節。
8.推奪:推移、交替。
10.夔:舜時樂官。《韶》:相傳為舜時樂曲名,由夔製作。
12.伊尹:商代的賢相,作《伊訓》、《太甲》等文。
14.《詩》:《詩經》。《書》:《尚書》。六藝:指《詩經》、《尚書》、《易》、《禮》、《樂》、《春秋》六經。
15.孔子:儒家創始人,他的弟子將他的言論集為《論語》一書。
16.木鐸:木舌的鈴。
17.莊周:戰國時哲學家,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著《莊子》。荒:廣大,唐:空闊。
20.楊朱:戰國時思想家。墨翟:戰國時人,墨家學派創始人,其言行見《墨子》,管夷吾:春秋時政治家,其言論見《管子》。晏嬰:春秋時齊國大夫,其言行見《晏子春秋》。老聃:即李耳,春秋時人,道家學派創始人,著有《道德經》。韓非:戰國末人,法家著名代表人物,著有《韓非子》。慎到:戰國人,作有《慎子》、已佚。田駢:戰國時人,著有《田子》,已佚。鄒衍:又作騶衍,戰國末人,陰陽家,著有《終始》、《大聖》。屍佼:戰國人,著有《屍子》。孫武:春秋時著名軍事家,著有《孫子》。張儀、蘇秦:戰國時縱橫家,分別著有《張子》、《蘇子》,已佚。
23. 魏、晉氏:魏、晉兩朝。
24. 節:音節、節拍。數:頻繁、細密。弛:鬆懈。肆:放肆。
25.無章:沒有法度,丑:厭惡。形容詞用如動詞。
26.陳子昂等:均為唐代著名文學家。
27.浸淫:滲透,接近。
28.從吾游者:指跟作者學習的人。尤:特出,傑出。
29.奚以:何以。
30.役:股役,此指“供職”。釋然:舒暢、開心。
大概各種東西不能處於平靜就會發出聲音。草木本來是沒有聲響的,風吹動它,它就發出聲響。水本來是沒有聲響的,風激蕩它,它就發出聲響。水浪跳躍,是有東西在阻遏水勢,水流快速,是有東西阻塞了它。水沸騰了,是有東西在燒它。鍾、磐一類樂器本來是沒有聲音的,有人敲擊它就會發出聲響。人在言論上也是這樣,有了不可抑制的感情然後才表達出來,他們歌唱是有了思念的感情,他們痛哭是有所懷念。凡是從口中發出來成為聲音的,大概都是有不平的原因吧!
音樂,是由在心裡鬱結的情感然後向外發泄出來的,它常常借用那些發音最好的東西來發出聲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樂器,是各種器物中發音最好的。自然界對於時令的變化也是這樣,選擇那些發音最好的東西藉以發出聲音。所以用鳥聲表示春天,用雷聲表示夏天,用蟲聲表示秋天,用風聲表示冬天,四季的推移變化,那必定是有不得平靜的原因吧!
對於人來說也是這樣。人的聲音的精華是語言,文辭對於語言來說,又是其中的精華,尤其要選擇善於用文辭發音的人,來借他們發音。在唐堯、虞舜時代,咎陶、夏禹是最善於用文辭發音的,就借他們來發出時代的聲音。夔不能用文辭發音,自己就借著《韶》 樂來發音。夏朝時,太康的五個弟弟用他們的歌來發音。伊尹為商朝發出了聲音,周公為周朝發出了聲音。凡是記載在《詩經》、《尚書》等六經上的文辭,都是文辭中發音發得最好的。周朝衰落時,孔子一班人發出了聲音,他們的聲音宏大而且傳得長遠。《論語》說: “上天要讓孔子成為宣揚教化的人。”難道不是真的嗎?周朝末期,莊周用他廣大無邊的文辭來發出聲音。楚,是一個大國,到了滅亡時屈原用楚辭來發出聲音。臧孫辰、孟軻、荀卿用儒道學說來發出聲音。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屍佼、孫武、張儀、蘇秦一類人,都用他們各自的學說來發出聲音。秦朝興起時,李斯用文辭來發出聲音。漢朝時,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等是最善於用文辭發出聲音的。這以下到魏、晉兩朝,用文辭發出聲音的人都趕不上古代,但也從來沒有中斷過。就其中好的來說,他們用文辭發出的聲音清麗而浮華,節奏頻繁而急促,語言放蕩而哀婉,思想鬆弛而放縱,他們作的文章,雜亂而沒有法度。這大概是上天認為他們德行不好而不肯照顧他們吧!為什麼不讓發音最好的人來發出聲音呢?
唐朝得到天下以後,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都是用他們的才能、用文辭來發出聲音的。那些活在世上晚於他們的人中間,孟郊開始用他的詩來發出聲音。他的詩超過魏晉的作品,其中精妙的已經趕得上古代作品,其它作品也逐漸接近漢朝作品的水平了。同我一起交遊的人中,李翱和張籍是其中突出的。這三個人用文辭發出聲音的確是很好的,但是不知道上天要使他們的聲音和諧,而使他們為國家的興盛發出聲音呢?還是要使他們窮困飢餓、心情悲傷愁苦,讓他們為自己的不幸發出聲音呢?這三個人的命運,就決定於上天了。他們身居高位,有什麼可高興呢,身居下位,又有什麼可悲哀呢!東野這次到江南去任職,好像心裡放不開似的,所以我講了命運由上天決定的道理來安慰他。
孟東野(751-814)名郊,字東野,浙江人氏,韓愈的學生和摯友,唐代著名的詩人。孟郊一生窮困潦倒。早年屢試不中,直到46歲才成進士,仕途更是坎坷,直到50歲才被任命為溧陽縣尉。這篇序文,就是韓愈送他去江南時的勸慰之言。文章暗喻了當政者不能任用人才,埋沒人才的惡劣做法。整篇序是為孟郊的不得志鳴不平,可見韓愈對他的同情和推崇。
文章內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論述“物不平則鳴”的道理。從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動而發出聲音,論及人的言論、歌、哭,都是因為有所不平的緣故。
第二段,列舉自然界多種現象論證“不平則鳴”的觀點。例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樂器,就是最善於發出聲音的東西;而上天則用鳥鳴、雷鳴、蟲鳴、風聲來告訴人一年四季的推移。這就為下文闡述“人也亦然”打下論證的基礎。
第三段,論證人也如此,不平則鳴。文章承接上文,從自然界論及人類社會,從唐虞、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一直談到隋、唐,列舉了眾多的歷史人物的事迹,論證了“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論點。
第四段,從唐朝的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一直說到孟郊、李翱、張籍,認為他們都是善於用詩文來抒發情懷的人。作者發問:孟郊、李翱、張籍三人的優秀詩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們的聲音和諧來歌頌國家的興盛,還是要使他們窮困飢餓、心情憂愁,而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終點明題旨:“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藉以抒發對孟郊懷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運用比興手法,從“物不平則鳴”,寫到“人不平則鳴”。全序僅篇末用少量筆墨直接點到孟郊,其他內容都憑空結撰,出人意外,但又緊緊圍繞孟郊其人其事而設,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並不顯得空疏遊離,體現了布局謀篇上的獨到造詣。曆數各個朝代善鳴者時,句式極錯綜變化之能事,清人劉海峰評為“雄奇創辟,橫絕古今”。
韓愈首先著重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從自然界的草木金石、風雨雷電之類到人類社會中的三皇五帝、至聖先賢,作者一口氣用了三十八個“鳴”字,其中文筆千變萬化,議論恣肆縱橫,恰如清代吳調侯、吳楚材所評,是“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韓愈在此以潑墨之法述古編新、竭力鋪陳的用意就在於要以本文“不平則鳴”的中心論點去對孟郊進行一次思想上、心理上的說服、啟發,因而這其中包含這樣幾層意思:一是不要認為自己不該“鳴”,認為今日之不幸均因“鳴”字而起;二是“鳴”乃天性,想不“鳴”也難做到,不如當個“鳴之善也者”,三是為世所用則“鳴”“國家之盛”,為世所疾則“自鳴其不幸”,兩者無不可。總而言之,韓愈以古今萬物為例,說明的正是一個極普通但卻很重要的道理,即為人不能不“鳴”,為文人更不可不善“鳴”,至於“幸”與“不幸”,在“上”還是在“下”,那就不必強求了。依此看來,韓愈在此文中所闡發的理論基本上還是沒有超出儒家“窮達”之說的範圍。
在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之後,韓愈又從“鳴”的“善”與“不善”入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者涉及三代,論述百家,以“鳴”字為經線,用旁逸側出之筆,突兀崢嶸之法。時抑時揚地表達出自己對歷代名人雅士的評價。韓愈把從唐、虞、夏、商到魏、晉、隋、唐的歷史時期劃為三個階段。認為周以前及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是盛世之言;周衰后的孔子至西漢的司馬遷也是“善嗚者也”,但屬衰世之音;至於魏晉之後則“鳴者不及於古”,純屬亂世之音了。這種厚古薄今的論調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一是出於反對六朝以來駢文占統治地位的反常現象的考慮,再是對於魏晉以降志士仁人愈發地“不得其鳴”之現狀的極大義憤。
由此,韓愈就在末尾一段里以正大的議論,閃爍變化的語言向孟郊表示出了自己的真實看法,即:溫故可以知新,從上古至今眾多人物的遭遇就可以懂得,立身處世的關鍵是毋以勝敗得失論英雄。一個人只要敢“鳴”,只要善“鳴”也就足夠了。至於幸與不幸,遇與不遇,在上位還是處下位等等則一概不足論。更何況賢才不被知遇實為古今通例,本無可悲之處,如此,則“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就可以達到一種不悲而樂且幸,“鳴”之而已矣的最高境界了。
對於“鳴不及於古”,其中“善者”,韓愈以“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衰,其志弘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作出評說。但對於怎樣“鳴”才算是“至善”,韓愈卻一字未提,反以“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作了反問。為什麼三代兩漢各種人物都可以“鳴”而且評之為善,到了魏晉以後卻一落千丈了呢。作者以“天怒其德”作口實,此含糊其辭之法也。其本意顯然是在指出亂世之中大批人才被埋沒、被輕視的事實。由此也就講明了“不及於古”的真正原因,併流露出對歷代當權者壓抑、摧殘人才的強烈的不滿情緒。
全篇緊緊扣住一個“鳴”字進行論述,其中“鳴”字出現三十八次,句法變換二十九回,聲調頓挫之處更是層出不窮。明代茅坤論及此文時說:“以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既指出了連用一字貫穿全文的先例,又給予此文以高度的評價。韓愈在這篇贈序中溯古論今,獨闢蹊徑,反覆以古人之鳴與今人之鳴相比較,於論述之中寄託感慨,在敘說之中有諷刺,達到了奇而不詭,收放自如,波瀾迭起,令人擊節的閱讀效果,體現出變化多端,格調高奇,深刻雄健,氣象萬千的行文風格。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七: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宋·李塗《文章精義》:“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為笱簋’來。”
宋·黃震《黃氏日鈔》:“‘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之所言,又至‘天亡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為文。歷敘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
明·茅坤《唐宋八家文鈔·韓文》:“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肖何追韓信,用十‘亡’字。此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卷七:“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也。”
清·金聖嘆《才子必讀》卷十一:“拉雜散漫,不作起,不作落,不作主,不作賓,只用一‘鳴’字跳躍到底,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以逐鱗逐爪觀之。”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歷敘古來著作,而以孟郊東野之詩繼之。閃鑠變化,詭怪惶惑,其妙處公自言之矣。‘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也。氣盛則宜,後人有如許氣,才許摹仿他四十個‘鳴’字。”卷八:“直是論說古今詩文,寫得如許靈便。通篇數十‘鳴’字,如迴風舞雪。後人仿之,輒纖俗可憎。其靈蠢異也。”
清·林雲銘《韓文起》卷四:“千古文章,雖出於人,卻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作樂,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已者,便是不得其平,為天所假處。篇中從物聲說到人言,從人言說到文辭,從歷代說到唐朝,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把個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落入東野身上,盛稱其詩,與歷代相較一番,知其為天所假,自當聽天所命。”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二:“只說文章如何關係,便有酸氣。旁見側出,突兀崢嶸。‘鳴’字句法雖學《考工》,然波瀾要似《莊子》。”
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七:“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為多。謂凡形之聲音,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
清·過珙《古文評註》卷七:“本篇極拉雜散漫不可捉摸。然大旨謂凡形之於聲音,皆雲於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之別;而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則皆系乎天也。至其用‘鳴’字凡四十,而轉換處二十有九,便有二十九樣頓挫,二十九樣聲調。有起有伏,有抑有揚。總把個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轉到東野,盛稱其詩,愈讀愈可喜。”
清·蔡鑄《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文以‘鳴’字為骨,先以‘不平則鳴’句提綱,通篇言物之鳴及古人之鳴,今人之鳴,總不出‘不平則鳴’之意。文成法立,奇而不詭於正。”
清·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曆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出以離奇倘恍,使讀者呵嘆其言,其實法律謹嚴,無逾此文。通篇表其文辭。未以所性分定,解其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間但賞其連用四十 ‘鳴’字,猶皮相也。”
清·余誠《古文釋義》卷七:“自首至尾,不肯使一直筆,頓挫抑揚,離合緩急,無法不備,而又變化詭譎,不可端倪,那得不橫絕古今。”
清·周鍾岳《韓文故》:“拈一‘鳴’字,將天地萬物古今聖賢盡歸陶鑄,不漏不支,各識其職,是為廣博粹密,與‘四原’並建。”
今·錢基博《韓愈志》第六:“《送孟東野序》、《送廖道士序》、《送高閑上人序》,恁空發論,妙遠不測,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隋煬帝迷樓;而正事正意,止瞥然一見,在空際蕩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此太史公《平準》、《封禪》諸書,《伯夷》、《孟荀》、《屈賈列傳》法也。特其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未極神妙自然之境。”
韓愈(768—825),字退之,孟州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唐代傑出的文學家,與柳宗元創導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復古崇儒,抵排異端,攘斥佛老,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身於官宦家庭,從小受儒學正統思想和文學的熏陶,並且勤學苦讀,有深厚的學識基礎。但三次應考進士皆落第,至第四次才考上,時年二十四歲。又因考博學宏詞科失敗,輾轉奔走。796年(唐德宗貞元十二年)起,先後在宣武節度使董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任觀察推官,其後在國子監任四門博士。803年(貞元十九年),升任監察御使。這一年關中大旱,韓愈向德宗上《論天旱人飢狀》,被貶為陽山縣令。以後又幾次升遷。819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韓愈上《論佛骨表》,反對佞佛,被貶為潮州刺史。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召回長安,任國子祭酒,後轉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後世稱為“韓吏部”。死後謚號“文”,故又稱為“韓文公”。有《韓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