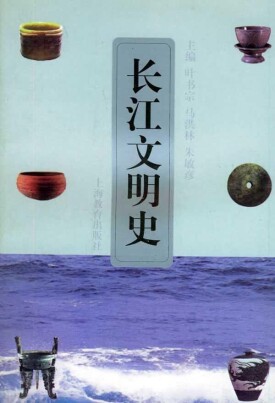長江文化
多維度的文化複合體
長江文化,以長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佔優勢,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基礎的歸趨性文化體系,是長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結的總和和集聚,包括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上海、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等省區,這些地區是長江水系的幹流或支流流經區,在文化體繫上同屬中國南方文化體系。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兩支主體文化。
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中,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無疑是兩支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主體文化。雖然,它們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內涵、形式、作用和歷史發展進程,但卻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在長達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它們既相互衝撞、相互對抗,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補充,是兩支平行發展的、並駕齊驅的文化系統。這種剛柔相濟、陰陽互補的文化聯繫,在血緣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統一體,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基礎,使大一統的中華文化呈現出絢麗多姿的色彩,並給周圍的海外文化以深遠的影響。
長江文化是一種以長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佔優勢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基礎的具有認同性、歸趨性的文化體系,是長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結的總和和集聚。從其生存空間來說,除傳統所謂的長江流域包括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上海七省二市外,還應包括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等省區,這不僅因為這些地區是長江水系的幹流或支流流經區,而且在文化體繫上也同出一轍,同屬中國南方文化的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說,長江文化是一個時空交織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複合體。
所謂文化區,就是指有著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質的地理區域,又稱文化地理區。在同一個文化區中,其居民的語言、宗教信仰、藝術形式、生活習慣、道德觀念及心理、性格、行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帶有濃厚的區域文化特徵。作為文化特質的區域分類,文化區與行政區不屬於同一個概念。行政區是一個行政管理區域單位,而文化區則是不同文化特質的空間載體。前者是人為劃分的,而後者則是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形成的。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運用行政區劃的概念來代替文化區劃,否則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當然,有一些行政區劃由於是按照一定的地理環境劃分的,加之歷朝行政區劃的延續性,久而久之也就具有文化區的性質,如四川省的巴蜀文化就是典型代表。但許多行政區劃在古代與文化區截然有別,如江蘇省雖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但在文化上卻以長江為界,有蘇南、蘇北之別,不能構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區。而蘇南地區與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區由於所處的地理環境相同,在文化上也如出一型,因此在事實上應認為一個區域。又如安徽省也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但在文化上卻可根據淮河、長江水系,將其劃分為淮北、江淮之間和江南三個部分。淮北地處黃河流域,具有濃厚的中原文化色彩;而江南的徽州地區由於接近太湖流域,則應歸入吳越文化的體系,為江南文化之一支—一徽州文化。江淮地區則帶有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過渡的性質,但更多地具有長江文化的因素。
同時,文化區還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隨著長江文化的發展、擴散和融合,一些舊的文化區衰落或消失了,一些新的文化區卻出現了。如在近代,四川文化區、江西文化區等處於衰落或消失之時,上海和嶺南文化區卻迅速崛起。另外,文化區的文化特質也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它不斷地淘汰舊的因素,進行更新改造,自我組織,自我完善,形成和造就與傳統文化區域性質和面貌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區域。因此,我們在研究文化區的分類和特徵的時候,既要考慮傳統的文化區域特徵,又要認真研究和分析新文化區的形成、發展和變化。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認為,在長江文化這個大整體中,可以根據流域內局部的和地區的多樣性將其劃分為相當數量的亞文化區(或稱次文化區):
巴蜀文化區又稱四川文化區,位處我國西南,地跨青藏高原東緣及四川盆地,與陝西、甘肅、青海、西藏、雲南、貴州、湖北、湖南等省區接壤。是一個氣候溫和多雨的地區,十分有利於農業生產,自古以來便有“天府之國”之譽稱。但四川“其地四塞,山川重阻”,以致大詩人李白在所作的著名詩篇《蜀道難》中發出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概嘆。這種地理上的封閉性和其文化特徵上的開放性,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自然也對巴蜀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一方面,這種獨特而優越的地理環境,使它具有特別穩定和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有利於當地文化的獨立發展;另一方面,這種地理環境對文化的發展也有非常不利的地方,由於它地居內陸盆地之中,使該地區的文化很難與周圍文化交流,容易形成一種“盆地型文化”,容納雖多,外射卻少;保守意識容易生根,開放意識難以生長;創業精神強烈,外拓意識薄弱;文而不華,柔而不弱;具體而微,絀於宏觀;善於籌措現實,不善規劃未來;因歷史傳統的羈絆而生渴求新奇感與懷疑拒斥心;深沉有餘而自省不足”。這種現象和困難,是需要四川人民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以開放的姿態進行艱苦的努力奮鬥,加以克服和揚棄。
從巴蜀文化的發展進程來看,巴蜀文化始終是長江文化中的主體文化,在長江文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根據考古資料,四川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便有人類活動。新石器時代月亮灣—一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說明巴蜀文化是一支具有鮮明地域特徵的、獨立發展的區域文化。而從廣漢三星堆—一成都十二橋早期蜀文化遺存的發掘和研究來看,殷商時期的巴蜀文化已與中原地區不相上下了。到春秋戰國時期,巴蜀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度,青銅冶鍊、蠶絲紡織、造船及漆器等手工業並不遜色於同時期的中原地區。秦漢時期,四川地區的經濟已經非常發達,成為統一全國的重要基地。而秦遷民巴蜀及西漢統治者蜀地政治、文化措施的加強,對巴蜀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西漢文翁守蜀立學,更使“蜀學比於齊魯”。在詞賦、黃老、律歷、災祥等巴蜀固有文化的基礎上,出現了象落下閎、司馬相如、揚雄這樣具有重要影響的代表人物。到隋唐五代時期,巴蜀文化的發展再次形成高潮。在繪畫、文學、書法、音樂、舞蹈、科技等方面都產生了具有重要影響的代表人物或流派。兩宋時期,巴蜀文化繼續發展,達到了歷史最高峰,與當時號稱文化極盛的江南地區不分上下,互為伯仲。但自宋以後,巴蜀文化便迅速衰落,至近代幾乎湮沒無聞,令人深思。為此,早在元代,袁桷便感嘆道“蜀由秦帝入中原,至於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滇文化區,又稱雲南文化區,位於我國南部邊疆,西部、南部與東南亞的緬甸、寮國、越南三國交界;東部、北部,鄰廣西、貴州、四川、西藏等省區。地形地貌錯綜複雜,氣候屬亞熱帶-熱帶高原型濕潤季風氣候,各地差異很大。是我國居住民族最多的一省。據統計,全部或部份居住在雲南境內的有二十五個民族。
滇文化的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東方人”和元謀猿人的發現,表明在人類的童年時代,雲南地區就有原始人群活動。而近年來該地區一大批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出土,則有力地推翻了雲南地區在史前時期是“茫荒異域”的傳統偏見。而這一時期生活在洱海區域“稻作民族”,還創造了非常發達的、豐富多彩的稻作文明,以至國外的“照葉樹林文化論”者認為“以刀耕火種為基礎的雜糧栽培(包括陸〈旱〉稻和薯類栽培農耕)最早起源於‘照葉樹林文化帶’的中心——雲南地區”。此後,劍川海門口銅石並用文化遺址的發現,揭開了雲南文化史的新篇章。表明大約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雲南劍門地區已走近文明社會的大門。而晉寧、江川、安寧、楚雄、祥雲、大理、永勝等地相繼發現的大批青銅器,表明雲南古代存在一個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其青銅器的技術水平較之中原和長江流域並不遜色。但由於種種原因,雲南的大部分地區在春秋末期到戰國時期尚處於“編髮左衽,隨畜遷徙”的原始社會。楚頃襄王時的庄入滇,加速了雲南地區文化的發展,成為滇文化的最早淵源。秦漢時期,滇文化在接受漢文化輻射的同時,繼續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到唐宋時期,雲南的“哀牢夷”和“白蠻”等民族在滇文化的基礎上,又大量吸收了先進的漢族文化,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一南詔文化、大理文化。明清時期,雲南在文化方面進一步發展,達到了鼎盛,出現了一些象鄭和這樣聞名全國的人物,並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滇戲、雲南民居等文化叢。
貴州文化區,又稱黔文化區或黔中文化區。它位於祖國西南部,是一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地貌複雜多樣的地區。西部與雲南高原相接,合稱雲貴高原;北面與四川盆地相連;東部與湖南丘陵接壤;南部與廣西盆地為界。其境內的沅江、烏江和赤水河都是長江的重要支流。
貴州在古代被蔑稱為“蠻貊之邦”。但根據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貴州境內早在五六十萬年前就有人類生活。其境內的舊石器時代觀音洞文化與湖北大冶發現的石龍頭文化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貴州境內已有越人先民的分佈,他們主要集中在烏江以南地區。這一地區發現的雙肩石斧和有段石,就充分表明了它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古文化的關係。到春秋戰國時期,在巴蜀、楚、吳越及中原文化的影響下,居於這一地區土著民族和越人一起終於創造出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點的“黔文化”(或稱“黔中文化”),其主體便是今人所說的“濮文化”和“夜郎文化”。此後,由於各族豪強的割據混戰,貴州地區的文化從東漢末年到宋代末年,竟然出現了“千年文化斷層”。這種現象直至明代王陽明貶謫貴州時,才有所改變。王陽明在貴州的講學活動,有力地推動了貴州文化的發展,使貴州文化在文學、藝術和方誌學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至今,貴州地區的蘆笙鼓、玉屏簫笛、茅台酒、蠟染等成為黔文化的主要特色。
兩湖地區的歷史可以推溯到舊石器時代。“鄖縣人”、“長陽人”等的發現,表明早在幾十萬年前這裡就是遠古人類的重要活動地區之一。而我國考古學家在湖北江陵雞公山迄今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在平原上的活動遺址,更被列入1992年度的中國十大考古發現,它為進一步探討長江文化的淵源,提供了科學實物資料。新石器時代,傳說中的三苗主要活動在這一地區。考古發現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和較晚的屈家嶺文化以及更晚的季家湖文化、石家河文化,都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遺存。夏商時期,通過對黃陂盤龍城、石門皂市等一系列與中原二里頭、二里崗、殷墟時代相當,而又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遺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表明這裡也已進入文明時代。春秋戰國之際,兩湖地區的文化達到了鼎盛。是其“最繁榮、最光輝的階段。銅器生產登峰造極的發展,促進了鐵器的改善和推廣。其他各行各業,如絲織、刺繡、髹漆和城市建設等,也欣欣向榮。經濟結構方面,封建領主制的普及與家務奴隸制的延伸并行而不悖。政治體制方面,陸續有所改革、有所創造。
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異常突出,哲學行於前,文學殿於後,這是一個從老子經莊子到屈子,東方的智慧之星一個接一個升起的偉大時代!”,但秦漢以後,這一地區的文化很快衰落,逐漸變成為“碌礙無所輕重於天下”的文化閉塞落後地區。葉適說:“漢之末年,荊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說:“唐開科三百年,長沙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直到宋代,長沙嶽麓書院的創立和湖南道州人周敦頤在廬山蓮花峰下濂溪書堂講學授徒,才為這一地區文化的再次崛起創造了條件。此後,福建崇安人胡安國父子講學南嶽,更是“率開湖湘之學統”,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礎。而四川綿竹人張栻在湖南的講學活動,亦有力地促進了南宋兩湖地區文化的發展。史稱“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但從總的來說,宋代兩湖地區的文化遠遠不及鄰近的四川、江西和兩浙地區。其文化發達的景象僅在長沙及其周圍的少數府州方可見到,絕大多數地區仍是荊榛塞路,教化未開。明清時期,兩湖地區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一躍而成為“湖廣熟,天下足”的富庶之地,其文化自然也相應高速發展,以至在近現代變成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顯赫省份。變化之大著實令人矚目,值得深入探討。
江西文化區,又稱贛文化區,位於長江中下游以南,鄰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其分佈範圍集中在今日江西省境內的鄱陽湖和贛江流域一帶。
江西地區的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1962年和1989年先後在樂平縣涌山岩(洞)和安義縣城郊發現舊石器晚期的打制石器,說明距今四五萬年前贛江流域已有遠古人類活動。而六十年代在萬年仙人洞發現的一處以漁獵和採集經濟為特徵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距今約有8000至1萬年的歷史,對研究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長江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到商周時期,從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遺址,樟樹吳城商代遺址和瑞昌銅嶺商周礦冶遺址等的發掘和研究來看,遠在三千多年以前,贛江—一鄱陽湖流域就已有著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有著與中原殷王朝並存發展的另一個奴隸主政權。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江西被人喻之為“楚頭吳尾”,受到吳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左右夾擊”,東西方的吳越文化和楚文化給予了強烈的影響,使生活於這一地區的干越也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成就。貴溪仙岩崖墓的考古資料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原始青瓷器的成功燒制,紡織印花技術的熟練掌握和斜織機的出現,這些都是江西先民對中華古代文明及長江文化的貢獻。秦漢時期,江西文化較之鄰近的吳楚腹地要落後,自然更比不上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到了六朝時期,隨著江西地區的開發和經濟的騰飛,文化也蒸蒸日上。政治家和軍事家陶倪、大詩人陶淵明、科學家綦母懷文等的出現,表明這一時期的江西文化已達到一定的高度。隋唐時期,是江西文化大發展的時期。以科舉考試為例,江西中舉入仕者頗多。據《江西通志·選舉表》統計,唐代江西共有進士65名。其中以袁州(今宜春)籍的人數最多,共27名;其次是德興、南昌、余干、高安等地人;故唐人杜佑說袁州“藝文儒術為盛”。有鑒於此,唐代文學家王勃在《滕王閣序》中讚美說:“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五代十國時期,江西為文化繁盛之地。經濟發達,佛教盛行,教育昌盛,人才薈萃。宋明時期,是江西文化的鼎盛期。俊彥輩出,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科技、藝術、哲學諸領域均有一批獨領風騷的卓著人物,對中華古代文明和長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相繼產生了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李覯、朱熹、樂史、劉恕、徐夢莘、洪适、馬端臨、陸九淵、文天祥、吳澄、虞集、揭斯、宋應星、湯顯祖這樣傑出的人物,形成了江西文化中的“儒雅風格”。但自近代以來,隨著江西經濟地位的衰退和海派文化、湖湘文化的崛起,其文化地位也一落千丈,不可與往日繁榮景象同語了。
吳越文化區又稱江浙文化區,以太湖流域為中心,其範圍大致包括今日的蘇南、皖南和浙江省。東臨大海,西臨彭蠡與兩湖文化區、江西文化區接壤,北與江淮文化區隔長江相望,南鄰閩台文化區。
從考古資料來看,吳越文化的淵源可以推溯到舊石器文化時期。1985年春吳縣三山島發現的一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是長江下游首次發現的舊石器地點,為研究吳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吳越文化區內相繼產生了河姆渡、馬家浜和南京北陰陽營三支自成系統的原始文化,其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充分表明長江下游的吳越地區也是中華古代文明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時期,吳越地區的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率先進入文明時代,“從而翻開了中國東方文明的歷史”。並在宗教、禮制和工藝等方面,對中原地區的商周文化發生過深刻的影響。
進入夏商時代,作為良渚文化後繼者的馬橋文化最終與湖熟文化融為一統,使整個吳越文化區的文化面貌趨於一致。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文化隨著吳、越兩國的強大,相繼稱霸於中原,遂著稱於世。青銅冶鍊、造船、航海、紡織、稻作農業、漁業等物質文化,都在當時居先進行列。
秦漢時期,吳越文化先後融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之中,其特徵逐漸開始淡漠。當然,其成就也與春秋戰國時期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現象直至東漢末年才有所改變,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三說:“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浜、滇雲之壤,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
魏晉南北朝時期,吳越地區在北方動亂不定之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故文化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並成為南朝的文化重心,其水平已達到或超過了同時期的中原文化。
隋唐時期,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和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吳越文化的地位也日顯重要,到唐中葉以後已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文化區。錢穆先生說:“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支撐點偏倚在南方(長江流域)。此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關捩
五代、兩宋時期,吳越文化得到了全面的發展。葉適說:“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而北宋,更有“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及“兩浙之富,國用所恃”之說。
元明清時期,是吳越文化的鼎盛期,其水平在全國首屈一指,時有“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之稱。
近代中國文化仍以吳越文化為最盛。梁啟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分佈》中說:“浙江與江南——江蘇、安徽同為近代文化中心點。”“實近代人文淵藪,無論何派之學術藝術,殆皆以茲域為光焰發射之中樞焉。”
江淮文化區又稱兩淮文化區,以巢湖為中心,其範圍大致包括今天長江以北的江蘇、安徽兩省境地。北與黃河文化的齊魯文化區、中原文化區接壤,南與兩湖文化區、吳越文化區隔長江相望。她處在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交流的過渡地帶,是連接中國南北文化的走廊與橋樑。
江淮地區有著悠久的歷史文明和豐富的文化遺存。江蘇泗洪下草灣猿人化石和安徽和縣龍潭洞猿人化石、巢縣猿人化石等的發現,表明早在更新世晚期,江淮地區就有了古人類的活動。新石器時代,這裡又出現了獨具地域特色的潛山薛家崗文化和蘇北青蓮崗文化。蘇秉琦先生在1977年10月14日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說:“淮河流域在中國考古學中確實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這個地區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地之一”。
夏商時期,居住在這一區域的先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徐淮夷文化”,並在西周達到了頂峰,曾給南方的楚文化、吳越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但其文化強烈受到黃河文化的影響,帶有濃厚的中原文化色彩。進入春秋戰國時期以後,隨著楚文化的東漸和吳越文化的北上西傳,江淮地區的徐淮夷文化迅速改弦易轍,向楚文化、吳越文化靠攏,出現了文化大融合,其文化風貌已趨於一致。如春秋中期或晚期的徐國銅器,“大都製作精良,銘文字體秀麗,紋飾細緻優美,為長江流域的風格,與北方的庄穆雄渾不同”。到戰國末年,淮水南岸的壽春曾一度成為楚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江淮地區的徐淮夷文化也溶入楚文化之中了。
秦漢時期,江淮地區是全國文化發達區域之一。特別是淮南王劉安都壽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書立說,對本地文化的發展予以深遠的影響,其文化總體水平當在同時期的吳越文化之上。魏晉時期,由於江淮間大批豪族士人大規模南遷和曹魏的移民,使這一地區的文化迅速衰落,僅靠政治力量維持著畸形的文化繁榮。到南北朝時期,“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自然文化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一落千丈。隋唐時期,江淮地區的經濟和文化迅速得到恢復,時有“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天下以江淮為國命”等說,當然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其總體水平已遠遠落後於同時期的吳越地區,更無法與黃河流域的關中文化、中原文化相比了。此後,江淮文化雖然在五代、兩宋及明清時期有所發展,但已瞠乎吳越文化之後。其內部的揚州等地區,也在明清時期溶入吳越文化區之中。
閩文化區又稱為福建文化區,東與台灣文化區隔海相望,北、西、南分別與吳越文化區、贛文化區、嶺南文化區相接壤。
我們將閩文化區列為長江文化區亞文化區,理由有二:一從地理上說,長江支流延伸到福建省境內;二從文化內涵來看,閩文化與吳越文化、兩湖文化、贛文化、巴蜀文化等基本相同,同屬中國南方文化體系。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福建地區早在1萬年以前就有古人類活動。到新石器時代,距今約4000年的曇石山文化在某些文化因素和特徵上已比較接近於鄰近地區的良渚文化。閩西、閩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面貌,也與武夷山西麓江西地區有較多的共同因素。
西周時期,福建地區已進入青銅時代,其文化受到吳越文化、楚文化等的滲透和影響。西周以後,作為福建土著文化的閩文化在吳越文化的強烈影響下,最終溶二為一,形成了閩江下游的閩越文化。秦漢以後,福建文化與長江流域其它亞文化一起歸入漢文化圈。
三國時期,佔據江東的孫吳政權在福建境內首置封建郡縣,標誌著長江文化在福建主導地位的確立。兩晉南朝時期及唐朝末年,由於大批中原及江淮地區的士大夫避難來到福建,使福建文化有了顯著的發展。顧頡剛先生在《論閩中文化》時說:“唐末黃巢之亂,區域極大,西至陝西,東至山東,南至廣東,中間江浙湖湘河南都經他的蹂躪。福建偏處一方,未遭擾及,當時湖南、江西、浙江的故家世族搬去的很多,所以能彀成就一種文化。但那時土著仍舊沒有開化,到近代原來搬去的家故世族反給土著同化了”。兩宋時期,福建地區的文化水平已處於全國先進行列。“此時期的福建文化一改舊貌,迅速發展,甚至在某些領域(如理學)曾一主潮流,成為全國中心”。據統計,《宋史·文苑傳》所載宋代90名著名文人中,福建有8位,居全國第6位;《全宋詞》輯錄的千餘位詞人中,北宋福建詞人有14名,佔全國第6位;到南宋則有63名,躍居全國第3位。《宋史》“道學傳”、“儒林傳”共載人物89人,福建佔有17人,居全國首位。與此同時,福建地區還成為長江文化與域外文化交流與融會的前沿地帶。宋元以後,福建文化一直在長江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並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如閩學、閩劇、閩菜、閩語等。
桂文化區,又稱廣西文化區,地處我國南部邊疆,南臨北部灣。西南與越南交界,東、北、西三面與廣東、湖南、貴州、雲南等省接壤。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長江支流延伸到廣西境內,並通過靈渠進一步溝通了與廣西地區的聯繫。它雖在地理上也屬嶺南地區,但其文化發展上有著自身的特色,因此應該單獨劃為一區。
“柳江人”、“麒麟山人”化石的發現,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廣西境內就已經有遠古人類活動。到新石器時代,從該一時期遺址中出土的有肩石斧、有段石、石鉞、幾何印紋陶等文化遺物及花山崖畫的內容來看,該地區的主體文化無疑為長江文化。春秋戰國時期,生活於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越人駕駛著“雙身船”,大批移徙到廣西東部,這就是文獻所載的“駱越”和“西甌”人。他們在這裡創造出了名揚四海的銅鼓文化,並成為今日壯侗語族諸民族的先民。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長江文化是以一個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為主體,包含滇文化、黔文化、贛文化、閩文化、淮南文化等亞文化層次而構成的龐大文化體系,這些不同的文化共同體在相同的文化規則下聚合成一個共同的文化體——長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