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
春秋時期著名思想家
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孫、孔子之子孔鯉的兒子。大約生於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歲。
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生卒年則不詳。按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文宗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受儒教祭祀。
大事件
-公元前483
出生
公元前483年出生於魯國
-春秋時期
提出的“誠”,是思孟學派思想的重要內容
春秋時期,子思提出的“誠”和與此緊密相連的五行說,是思孟學派思想的重要內容。

-春秋時期
中和之道
春秋時期,子思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春秋時期
提出“修道之謂教”
春秋時期,提出“修道之謂教”。
-春秋時期
至誠之道
春秋時期,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春秋時期
合外內之道
春秋時期,子思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春秋時期
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
春秋時期,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
-公元前402
去世
公元前402年去世,享年82歲。

子思
八儒中韓非子將子張列為首位。陶淵明將貧民子思,列為首位,顏氏指孔子死後尊顏回的留在曲阜之徒,也是《論語》的編纂者。可見出走的子張的與原憲的教育方法,知名度超過了老師孔子。所以老儒家只能算是第三位從《韓非》與《莊子天下殘文》,我們足以了解到,戰國末年,子張,子思雖然學術影響巨大,但是已經處於少數派地位。《天下殘文》歌頌其他六儒,按詩書禮樂春秋易,六藝順序對六儒家,進行了褒揚,單獨對子張,子思進行嘲諷。可知一,原來分裂出去的五儒,已經在戰國末年趨於統一,而且承認了魯國的曾子學派的正統地位。論功行賞,不再固執的予以對抗。可知二,唯獨子張之儒,子思之儒抗拒到底,成為亂臣賊子,道家不恥。這與《論語》《漢書藝文志》的出版記錄吻合,又說明漢獨尊曾子后,卻並未不發行仲梁子,樂正子,等反對過曾子的學派著作。可知並未履行當初諾言,故《史記》高度表彰季布之諾,一諾千金,暗譏當時之儒食言
康有為的考證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從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於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說孔子68歲時子思出生,而這時孔子剛剛由季康子派人帶厚禮從衛國請回魯國欲招其做官。孔子雖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為與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馳,所以拒絕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業上,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作《易傳》,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從時間上來說,子思兒時的啟蒙教育完全有受之於孔子的可能。其次,孔子本人確實也很重視對後代的培養和教育。他曾教導其子伯魚,讓他認真學習詩、禮,並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告誡他。孔子對於孫子子思也同樣寄予厚望。《聖門十六子書》中記載:孔子晚年閑居,有一次喟然嘆息,子思問他是不是擔心子孫不學無術辱沒家門。孔子很驚訝,問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說:“父親劈了柴而兒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繼承父業,所以從現在開始就十分努力地學習絲毫不敢鬆懈。”孔子聽后欣慰地說:“我不用再擔心了。”
《孔叢子》一書中也有與之意思相近的記載。情況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學說。後來,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隨曾子學習受益匪淺。所以《聖門十六子書》中說:“子思從曾子學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書,以昭來世。”從曾子那裡,子思也繼續學習孔子思想的真傳,闡發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書,被收在了《禮記》里。另外,《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但《聖門十六子書》一書出於清代,此前無類似故事流傳,《孔叢子》一書雖可以為參考,但其成書年代自古便多有質疑,最早也僅能推至秦末漢初,故兩者所載之事,不可輕易當做事實。
然而,關於《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是戰國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種觀點認為作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為《中庸》出於子思之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注家也多遵從此說。如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唐代的陸德明、孔穎達也同意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為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該書大體上還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為從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的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民權和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而《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依據《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話語,不應該出現在戰國時期。《中庸》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認為這應當言於秦亡之後。
實際上,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著錄有《中庸說》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類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也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於《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只有《中庸說》著錄其中,所以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有《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說”《中庸》的著作。這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至於其中“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句,按李學勤先生的觀點解釋,孔子生於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現實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應解釋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語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所以不能因這段話而懷疑《中庸》的成書年代。
不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說法還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什麼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等書中找出了這個學說的痕迹,由此可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經被編輯成《子思子》一書。這個記載是否可信,學者們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荊門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簡,這不僅可以使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證明了《中庸》一書確實為子思的作品。該墓出土的竹簡已經編成《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成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於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之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篇也頗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中庸》一書的確出於子思之手。
在對待傳統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樣很重視禮,也身體力行遵守禮。子思得知父親的前妻去世后,就在孔氏之廟痛哭,他的門人對他說:“庶民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恍然大悟,連連承認是自己的過錯,“遂哭於他室”。子思與其他許多著名儒者一樣也嚮往國家的德治教化,並且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與孔子不同,為了施展抱負,孔子曾仕魯參政,但卻以去魯告終。孔子周遊列國,企圖遊說諸侯,但處處碰壁,甚至在各國受困。子思則不然,魯穆公請他做國相,子思則以推行自己的學說為重婉言謝絕。
子思作為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對後世產生的較大影響,主要還在於他的思想方面,特別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一書中,然而它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於舜時就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後來,子思作《中庸》一書,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了系統闡述。該書全篇以“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係,把“中庸”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到了世界觀的高度。
子思認為: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泄出來的時候,心是平靜的,無所偏倚,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發泄了出來能合乎節度,沒有過與不及,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廣之,那麼天地之間一切都會各安其所,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顏回做人能夠擇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個大智的人,善於徵求別人的意見而且對那些很淺近的話也喜歡加以仔細的審度。把別人錯的和惡的意見隱藏起來,把別人對的和善的意見宣揚出來,並且把眾論中過與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於民眾,這或許就是舜之所以成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聰明的人過於明白,以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樣去行;有才智的人做過分了,而沒有才智的人卻又做不到。這就像人沒有不飲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麼,應該怎麼做呢?首先,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凡是別人加之於自己身上而自己不願意做的,也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其次,君子應在所處的地位去做它應該做的事,而不應去做本分以外的事。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患難的地位,就做患難地位所應該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無論處在什麼地位都是自得的。
處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處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對別人無所要求,自然沒有什麼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歸咎他人。所以君子安於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來的驅使,小人卻要冒險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詩經》上說:“穿著彩色的綢衣,外面加上單層的罩衫。”為的是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了。所以君子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會漸漸彰露出來。小人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鮮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漸漸地暗淡了。

子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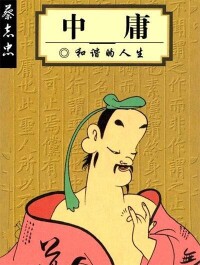
《中庸》
《孔子世家》又說,子思曾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為《禮記》所收,流傳於世。《孔叢子》記有子思固於宋的細節及子思與魯穆公的問答,都不一定可信。《中庸》,司馬遷稱其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說“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淺,”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都是秦漢人的口氣,當非出於戰國時人之手。《中庸》作者認為,人的貧富窮通、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有天命來決定。人的本性能對天命作出正確的反應,表現為行為的準則,這就是道。道是不可須臾離的,如能修養得好,可以與天地相參。他在書中舉出幾個標準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結,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家廟饗之,子孫保之。”這是說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時也離不開“文武之德”,離不開“文王之德之純”。《中庸》作者特別說到孔子,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濤。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孔子雖沒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萬物。這可見《中庸》作者對於存養之功的極力推崇,而對孔子的推崇達到神化的程度。這也反映當時以《中庸》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標舉的心情。孔子有這樣大的成就,而這種成就卻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中庸》作者認為,“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認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問題在於能不能“盡性”。他極力宣揚“盡性”的重大意義,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依這個觀點來說,孔子之為至聖,正是因為他“能盡其性”。 《中庸》的作者又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不遠人”,即所謂“率性之謂道”,道並不需他求。如果要“為”道,如務為高遠之類,反而離道遠了。在這裡,《中庸》沒有明文說性善,實際是說性善。這是《中庸》的理論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論點。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論的創始人,是孟子性善論的先行者。《中庸》的作者強調素其位而行。他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激幸。”這就是說,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作好自己分內的一切活動,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別人。這是順從天命而率性,盡性的為法,也是作者企圖用以消解矛盾的辦法。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與聞。《中庸》則以言性與天命為重要的內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中庸》則說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對於孔子的繼承來說,《中庸》是對於儒學的唯心主義的放大,其間還塗抹了濃厚的神秘色彩。漢代已有《中庸》的單行本及其解說問世。《漢書·藝文志》著錄《中庸說》二篇。南北朝時有宋戴顒《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見於《隋書·經籍志》。以上這些書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書》取士。自此以後,《四書》之流傳日廣,成為學子必讀之書,而朱注成為人感性的著作。
《子思》書自秦代以來已亡失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見於《闕里志》、《韓非子》、《馬總意林》、《說苑》、《文選注》、《中論》、《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馮雲■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記問》、《雜訓》、《居衛》;第二卷《巡狩》、《公儀》、《抗志》;第三卷《補遺》;第四卷《附錄》;第五卷《祠墓古迹》;第六卷《世職》。這樣,經過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統的。
《子思》為子思及其門徒所作。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戰國初期思想家,魯國人。相傳子思曾受業於孔子弟子曾子。他一度遷居衛國,又至宋國,晚年才返回魯國。子思發揮了孔子“中庸”思想並使之系統化,成為自己學說的核心。他宣傳儒家“誠”的道德觀念,並視之為世界的本原。后孟子受業於他的門人,全盤接受並進一步發揮了他的學說,從而建立了思孟學派。他一生除授徒外,致力於著述。《漢書·藝文志》中即著錄其著述23篇,相傳《禮記》中之《喪記》、《坊記》也出自他手。南宋咸淳三年(1267)被封為“沂國公”;元至順二年(1331)被封為“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1530)被封為“述聖”。
孔子死後,儒家分裂為八派。據韓非說,他們是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宋太平御覽古本之韓非與今本異處與史記把荀卿作公孫卿同)、樂正氏為首的八派。①其中孟氏即孟子,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樂正氏即孟子的弟子樂正子。如此說來,子思、孟氏與樂正氏三派儒者當是一派,即思孟學派。這一學派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與孟子合在一起來評論,已經把子思與孟子作為一個學派來對待。荀子離孟子的時代那麼近,他的話當是可以相信的。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也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②與荀子之說是一致的。當然在歷史上,孟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子思。
子思(約公元前492-前431年)姓孔名伋,他是孔子的孫子,一般認為他是曾子的弟子,也有人說子思出於子游氏之儒。《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
子思提出的“誠”和與此緊密相連的五行說,是思孟學派思想的重要內容。“誠”是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也是道德準則。子思說,“誠者天之道”,③即“誠”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還認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說,“誠”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還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說,“誠”是產生萬物的本源。如果沒有“誠”,也就沒有萬物。也就是說,主觀上“誠”是第一性的,而客觀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誠”這種主觀精神來說明世界的產生和發展的學說,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
子思的思想具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神秘性。《中庸》二十四章說:“至誠如神”。達到“誠”便具有無比神奇的威力。甚至還認為,只要“至誠”,就可以預卜凶吉。國家將要興旺,就一定有禎祥的預兆。而國家將滅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現。可見“誠”與天、鬼神是一脈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認為,達到“誠”的途徑,是要“盡其性”,進而“盡人之性”,再進到“盡物之性”,這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矣”。①這一過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這種思想對漢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較大的影響。
子思提出的“誠”,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殷代滅亡之後,為了說明周為什麼能夠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來修補天命思想;春秋後期,天命思想搖搖欲墜,孔子提出“仁”這種道德規範,企圖用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仁”本身雖然沒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誠”的提出,則是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並把上帝泛神化。這種思想是將孔子倫理思想擴大化,從而成為更廣泛、更唯心主義化,以至趨向宗教性的思想。這是思孟學派對儒家思想的重大發展,從而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學的基礎。
子思的“誠”與五行說有密切的關係。鄭玄注《中庸》一章“天命之謂性”時,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即是說,“天命之謂性”,包含了五行的內容。章太炎的《章氏叢書·子思孟軻五行說》,認為這是子思的思想。這兒需要說明的是,《中庸》里的“誠”就是“信”。子思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①由此可見,“誠”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則信”的土居中央。可見“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誠”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誠”來代替“信”更說明問題,更易使人理解。子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樣,但其中五行說的內容確是存在的。
五行說指仁、義、禮、智、聖。2005年即有魏啟鵬先生《簡帛文獻〈五行〉箋證》,與鄒衍的陰陽五行有別。
《子思》是極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經典,雖出自子思及其門徒之手,但後人對它有所增損,有所潤色。它與孔子的哲學思想體系一脈相承:孔子哲學的出發點,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於天道的本體論環節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現為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表現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由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誠”的理論,由“誠”的理論到合外內之道,由合外內之道到復歸於中和之道的“天地參”,這就是子思用以闡述和發展孔子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子思》的思想,我們可以分以下幾點具體闡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子思所謂的天命,實質上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天道與其必然表現的統一。這是一個純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體性來說,是老子所謂不可再加規定的“一”,而子思則聯繫它的主宰天地萬物的表現作用,而導入一個對它的普遍界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現作用,這種表現作用作為規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動之,而表現之,這就是道。在這裡,道與天道有相對的區別,後者指天道的主體——物質本體與其表現作用之為規律的統一,前者指天道作為這個統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現作用(規律)之為性而動,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動之道。天道循性而動的活動之道,同時也是人、物的活動之道,人、物循性而動,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動。
天道作為“一”,不能不表現自己,由此散發而為多種規定,二者的統一便是一個性與其活動之道的統一體。天道的多種規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這個命題,從本體論上闡明了性道一體的普遍性。而這個性道一體的普遍性,內部也有其不同邏輯層次上的區別與聯繫。
對孔子說,禮作為人行大法,雖然是仁本身的具體大全,但它與行仁的具體情節相聯繫,便以“克己復禮”為尺度而轉化為一個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門最高之道,它制約人行而指向人對人人關係、人物關係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確認識和處理。但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為人性的必然表現。子思從人性上闡發了這種必然表現的心理實質,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層次上歸結為一個中和之道。
子思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謂教”。這裡所謂“教”,就是實現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徑。他認為,把禮法的規範系統化為一種制度系統,作為一種社會倫理制度,加以社會權威化,而成為一種人人必須遵守而不能有所違犯的普遍社會制約性,這就是人類最主要的“修道”。在此基礎上隨之而來的派生“修道”環節便是:第一,設立社會機制從政治上集中體現社會倫理制度;第二,輔之以各種形式的體現人的社會遺傳的教育制度。
所有這些以禮法的規範系統的制度化、社會權威化為基礎的“修道”環節的總和,其作用是對社會成員進行禮義上的社會制約和教化,這就是“修道之謂教”的教。人只有在這種社會制約和教化中,才能通過實踐逐漸克服其情發而不中節的非和,達到情發而中節的達道一和,亦即達到中與和的對立統一。這是一個人在其社會屬性中承受其社會制約和教化的過程,它對儒家哲學,同時也是一個“致和格物”、修身正心的過程,是一個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的自我完善過程。
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如果人心全為其明德之性作為人性亦即真實無妄的所充溢,人性或理性通往真理的思維規律便能所向無礙、暢通無阻地起作用,這便是一個至誠的實在性。達到這一點,人心便完全成了一個理性以感性為中介而與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它能洞察人倫之道和一切事物的規律。這便是無須’修身正心”的“有為”而能無為無不為的一個實在性,這樣的人便是孔子所說的“不斷而得,從容中道”的天生聖人。子思認為,聖人之心,至誠如一,具有由誠而明,亦即由性而明的全德。
子思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合外內之道,是一個人性的理性規律與客觀存在規律的主客統一性,二者在其統一性中是一個見之於人性的道,所以人據此因時而發之,便無不中道而理當。天道是一個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體,它的整個屬人環節,也必須是這樣一個主客統一體。這種觀點的展開,必然是一種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物質論和萬物有靈論。
子思的思想有形而上學的若干特色,但也有辯證的思維。
中和之道從反對矛盾轉化的立場出發,重視對立間的相互依存,重視(並極端誇大)同一性在矛盾發展中的作用。它所推崇的中,即是哲學上所說的同一性,是辯證法的一個片段。明末哲學家方以智用“交”這個概念表述對立面的同一性,他認為“兩間無不交,無不二而一”,“交者,合二而一”(《東西均·三征》)。方以智說:“子思辟天荒以千古相傳不可言之中,恐墮滉洋,忽創‘喜怒哀樂之未發’一語當之,而又創出中和之節,則明示未發之中即和合於己發之中矣”。(同上)。“合二為一”與中和之道思想的聯繫是十分清楚的。
駁斥中國人缺少思辨精神的觀點
不少人認為中國人是缺少思辨精神的。而我們從《子思》中可以駁斥這個觀點。可惜的是,《子思》在秦代遭到了被禁毀的厄運,使之面目全非,我們只能從零星的著錄中尋求它的光芒。秦王朝統一六國,實行專制統治。為鞏固政治專制,秦始皇採取臣下建議,進行“焚書坑儒”。下令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子思》作為儒家經典,其被焚命運在所難免。在我國現代的“五四”時期,中國的建設者們高揚“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儒家學說再一次被打倒推翻。它的不分青紅皂白再次被扼殺的命運是我們現代人的悲哀。以《子思》為例,書中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與思想依然值得我們借鑒、學習。我們從總體上來把握《子思》,以為它的“天人合一”思想既有科學的光輝,也有民主的光芒。
“天人合一”是儒學的大一統,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原理,掌握了天人合一,也就掌握了《子思》的基本精神,也就掌握了中國儒學的精神。
“天人合一”是天道與人道的合一。天道作為人世間的公理,它是由人去把握支配的。人可以並且應該在客觀規律面前充分發揮主動性,做世界的主人。而“天人合一”從美學意義上講,它追求的是一種和諧美。只有人與人和諧、人與物和諧,才能達到乾坤運轉的整體和諧。反之,則是混沌無序,則是人妖顛倒,則是紛爭、動蕩,一團亂麻。社會不進步,人類不得安寧,失去安定和團結,也就失去了發展的機運。除了倒退,別無其他了,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平民百姓所最不願看到的。
《子思》極力強調主觀努力的意義,它的名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就是儒學傳統中大量保福避禍方案的哲學概括。我們應當承認,儒、道、法各家的發展觀,對於辯證法各有所見,亦各有所未見。對中庸之道的阻止轉化、固循守回、反對變革的傾向加以否定是完全必要的,這種否定不應當妨礙我們肯定其對矛盾同一性的正確認識,正如肯定法家對矛盾鬥爭性的犀利洞察不應當妨礙否定其抹煞矛盾同一性的觀點一樣。
中庸之道反對“過”與“不及”,主張“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在哲學上,還具有從量去找出與確定矛盾的質的規定性的意義,這個思想也符合辯證思維。
要追求并力爭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關鍵還是在人,在人心,在人性。於是這又回到了仁與義、人的本性抑或說人的道德修養上來了。因此,以仁為本,從善如流,德行統一,允執其中,仍然是我們不可悖離的宗旨。應該說,這些就是《子思》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公元前484年)
〇子思約生於此時
子思,名伋,魯國人。孔子之孫。
【文獻】《禮記·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註:小功,五服之一,其服輕於大功而重於緦麻。位,指哭位,哭位是根據與死者的親疏遠近關係排列的),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禮記·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記·檀弓下》:“子思之母喪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子之廟?’子思曰:‘吾過矣!過矣!’遂哭於他室。”
【考辨】子思生卒,《世家》未有明確說明,只說“年六十二”,而這“年六十二”也是大有疑問。子思的父親孔鯉生於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共活了五十歲,若以二十歲成婚計算,從成婚到卒尚有三十年,子思生於這三十年的那一年,無法確定。又根據《孟子》、《漢書·藝文志》,子思曾為魯穆公師。有人說“年六十二”是困於宋作《中庸》時的年齡,又說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作《中庸》時六十二不可信,因《世家》下面還說“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這裡的四十七、四十五、四十六都是指實際年齡,為什麼偏偏對子思例外呢?明顯說不通。所以合理的解釋是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誤。但子思即使活了八十二歲,他也是在孔鯉晚年甚至卒年才出生的。因為既然為魯穆公師,就不可能在魯穆公一即位時就去世,而應該有一個過程,由此推算,子思出生時孔鯉已屆暮年。
古人結婚較早,孔子十九歲成婚,二十歲即生孔鯉,而孔鯉為何這麼晚才生子思呢?錢穆說:“《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則知其有兄矣。伯魚早卒,而子思有兄,則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又,《檀弓》有“子思之母死於衛”,門人曰“庶氏之母死。”錢穆說:“謂庶氏之母者,謂子思非嫡出,故子思之母乃庶氏之母耳。”(《子思生卒考》,《系年》第173~175頁)錢氏之意似說子思之母非孔鯉正妻,故出生較晚。按,子思生年已不可確考,大致在孔鯉暮年。古人晚年得子,也為常見。錢穆所舉理由皆顯勉強,不如付之闕如。
周貞定王二年、魯哀公二十八年甲戌(公元前467年)
〇子思年十六,相傳此時作《中庸》
《中庸》,子思作,后收入《禮記》,儒家經典之一。從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部分(朱熹《四書集注》為準)主要為記言體,討論中庸;第二十章以下則為議論體,提出作為世界本源的“誠”,認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可能原為子思的兩部作品,后被編在一起。
【文獻】《史記·孔子世家》:“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叢子·居衛第七》:“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考辨】《史記》說“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未說明具體時間,《孔叢子》則說“年十六”。《孔叢子》雖有後人篡改的痕迹,但並非全偽,“記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屬於采輯舊材料或據舊材料加工而成。”(黃懷信《〈孔叢子〉的時代與作者》,《西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其說或有據,暫列於此。但《孔叢子》說“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則有誤。子思“困於宋”時所作應為《中庸》,而“《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則是指《子思子》。據學者考證,《中庸》為《子思子》的首篇,而古書有舉首篇代替全書之例,故用來作為全書的稱謂,稱“《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古籍中常有以《中庸》代稱《子思子》之例,如李翱《復性書》:“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說之《中庸傳》:“是書本四十七篇。”鄭樵《六經奧論》也說:“《中庸》四十七篇。”武內義雄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子》二十三篇,每篇分上下二篇,另加一篇序錄,即成《中庸》四十七篇(《子思子考》,載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冊第121~123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版)。所以《中庸》四十七篇和“《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均是《子思子》的代稱。《子思子》應為子思弟子或後學所編,不可能是子思十六歲時所作,子思“困於宋”時所作應為《子思子》的首篇《中庸》。另據學者考證,今本《中庸》實包括兩篇,其中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子曰”的部分即是原始的《中庸》,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以下議論體的部分應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誠明》,兩篇分別是子思早期和晚期的作品(梁濤《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台大歷史學報》2000年第二十五卷)。則子思十六歲時所作,應為今本《中庸》的上半部分。
周孝王五年、魯悼公二十一年乙巳(公元前436年)
〇子思約四十八歲,居衛
子思約四十八歲時,居於衛國,與衛君多有問答。他說衛國的政治是“無非”,但他的“無非”並不是說衛國的政治已完美無缺,沒有可批評的,而是指衛君聞過則怒,喜歡阿諛之言,結果使沒有敢於提出批評。
【文獻】《孟子·離婁下》:“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孔叢子·抗志》:“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孔叢子·抗志》:“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憂。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說苑·立節》:“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考辨】子思居衛,史書多有記載。《孔叢子·抗志》說:“子思居衛,魯穆公卒。”但魯穆公元年,子思已六十八歲(詳見“周威烈王6年公元前402年子思約卒於此時”條),魯穆公共在位三十三年(《史記·魯周公世家》),若子思得見穆公卒,則年齡已在百歲以上,故穆公當為悼公之誤。《魯周公世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據錢穆考訂,魯穆公元年為周威列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魯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頁)前推二十一年。
周威烈王十一年、魯穆公元年丙寅(公元前415年)
〇魯穆公禮事子思
子思晚年,居住於魯國。魯穆公經常派人問候,惟恐不能留住他。子思雖受到禮遇,卻常常直言不諱,認為能經常批評君主錯誤的,才能算作忠臣。
【文獻】郭店竹簡《魯穆公見子思》:“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鄉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孟子·公孫丑下》:“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萬章下》:“(孟子)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后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后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萬章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告子下》:“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者則亡,削何可得與?’”又見《鹽鐵論·相刺》,《說苑·雜言》。《韓非子·難三》:“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左米右間]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以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又見《論衡·非韓》。《禮記·檀弓下》:“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孔叢子·公儀》:“穆公問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叢子·抗志》:“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考辨】魯穆公元年,《六國年表》列於周威列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魯周公世家》則列於十七年,但據錢穆考證,《年表》、《世家》有誤,實際應為周威列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魯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頁)子思已六十八歲。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魯穆公十四年己卯(公元前402年)
〇子思約卒於此時
子思(約公元前483~前402),戰國初魯人,姓孔,名伋。孔子嫡孫。相傳受業於曾子。曾為魯穆公師。其思想以“誠”為核心,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人通過修養達到“至誠”境界,便可與天地鬼神相通。提出“仁義禮智聖”“五行”(帛書《五行》),對以後“五常”的形成產生影響。又說“中庸”也是其主要思想。其學說經孟子發揮,形成思孟學派。後代封建統治者尊為“述聖”。《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現存《禮記》中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等四篇是他的著作。馬王堆帛書及荊門郭店楚簡《五行》是從地下重新發現的子思學派的作品。
【文獻】“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禮家:“《中庸說》二篇。”《孔叢子·居衛》:“(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按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隋書·音樂志》引沈約之言:“《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考辨】《世家》說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詳上文)。子思生於公元前483年,故列於此。
一、孟子與子思的義利之辨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不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起初,孟軻拜孔為師,曾經請教治理百姓什麼是當務之急。孔說:“叫他們先得到利益。”孟軻問道:“賢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談仁義就夠了,何必要說利益?”孔說:“仁義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則下無法安分;上不義,則下也爾虞我詐,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經》中說:‘利,就是義的完美體現。’又說:‘用利益安頓人民,以弘揚道德。’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臣司馬光曰:孔、孟子的話,都是一個道理。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對魏惠王直接宣揚仁義,閉口不談利,是因為談話的對象不同的緣故。
二、子思見衛侯
二十五年(甲辰,公元前377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孔,字子思,向衛國國君提起苟變說:“他的才能可統領五百輛車。”衛侯說:“我知道他是個將才,然而苟變做官吏的時候,有次徵稅吃了老百姓兩個雞蛋,所以我不用他。”孔說:“聖人選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幾尺朽爛處,高明的工匠是不會扔掉它的。現在國君您處在戰國紛爭之世,正要收羅鋒爪利牙的人才,卻因為兩個雞蛋而捨棄了一員可守一城的大將,這事可不能讓鄰國知道啊!”衛侯一再拜謝說:“我接受你的指教。”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衛侯提出了一項不正確的計劃,而大臣們卻附和如出一口。孔說:“我看衛國,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呀!”公丘懿子問道:“為什麼竟會這樣?”孔說:“君主自以為是,大家便不提出自己的意見。即使事情處理對了沒有聽取眾議,也是排斥了眾人的意見,更何況現在眾人都附和錯誤見解而助長邪惡之風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樂於讓別人讚揚,是無比的昏暗;不判斷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諛奉承,是無比的諂媚。君主昏暗而臣下諂媚,這樣居於百姓之上,老百姓是不會同意的。長期這樣不改,國家就不象國家了。”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孔對衛侯說:“你的國家將要一天不如一天了。”衛侯問:“為什麼?”回答說:“事出有因。國君你說話自以為是,卿大夫等官員沒有人敢改正你的錯誤;於是他們也說話自以為是,士人百姓也不敢改正其誤。君臣都自以為賢能,下屬又同聲稱賢,稱讚賢能則和順而有福,指出錯誤則忤逆而有禍,這樣,怎麼會有好的結果!《詩經》說:‘都稱道自己是聖賢,烏鴉雌雄誰能辨?’不也像你們這些君臣嗎?”
三、子思見子貢
子思問什麼是恥辱。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領取俸祿,卻不能有所見樹。國家政治黑暗,做官領取俸祿,卻不能獨善其身,就是恥辱。
子思說:“好勝、自我誇耀、怨恨、貪慾都沒有顯現出來,可以算是做到了仁了嗎?”孔子說:“可以說是難能可貴了,是否算是做到仁,那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逝世以後,原憲就跑到低洼積水、野草叢生的地方隱居起來。子貢做了衛國的國相,出門車馬接連不斷,排開叢生的野草,來到偏遠簡陋破敗的小屋,前去看望原憲。原憲整理好破舊的衣帽,會見子貢。子貢見狀替他感到羞恥,說:“難道你很困窘嗎?”原憲回答說:“我聽說,沒有財產的叫做貧窮,學習了道理而不能施行的叫做困窘。像我,貧窮,不是困窘啊。”子貢感到很慚愧,不高興地離去了,一輩子都為這次說錯了話感到羞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