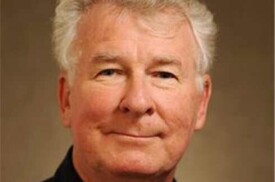安樂哲
安樂哲
安樂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國際知名漢學大師,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尼山聖源書院顧問,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會長、國際儒聯副主席。
安樂哲1966年就讀於加州雷德蘭斯大學,后赴香港中文大學,師從新亞書院的唐君毅先生、崇基學院的勞思光先生。他先後在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等學校分別取得中文碩士、中國哲學碩士,中文博士、中國哲學博士學位。
他是中西比較哲學界的領軍人物,更因翻譯了《論語》《孫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經》等書而蜚聲海內外。主編《東西方哲學》、《國際中國書評》,著有《孔子哲學思微》、《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國:探求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敘述》、《主術: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國民主之希望》 。
安樂哲先生曾接受過劉殿爵先生的指導,精通文言文,是當代傑出古典學家之一。2013年,榮獲第六屆世界儒學大會頒發“孔子文化獎” ;2016年,榮獲第二屆“會林文化獎” 。

安樂哲
自1978年開始在夏威夷大學任教,曾任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台灣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劍橋大學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余東旋傑出客座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第五屆湯用彤學術講座教授和第四屆蔡元培學術講座教授。
安樂哲教授的學術研究範圍主要是中西比較哲學,學術貢獻主要包括中國哲學經典的翻譯和中西比較哲學研究兩大部分。其翻譯的中國哲學經典《論語》《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淮南子》《道德經》《中庸》等,不僅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思想幾百年的誤會,清除了西方學界對“中國沒有哲學”的成見,也開闢了中西哲學和文化深層對話的新路子,使中國經典的深刻內涵越來越為西方人所理解,所接受。
他關於中西比較哲學的系列著作包括:《孔子哲學思微》、《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國:探求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敘述》、《主術: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
1947年,安樂哲出生在加拿大多倫多市。1966年,安樂哲離開多倫多來到加州Redlands大學文理學院讀書。一天,他在經過校園時看到了一則廣告,廣告的大概內容是,主辦方要選派一名學生到香港去學習。於是安樂哲按照對方的要求提出了申請並順利通過。

安樂哲教授
第二年,搭乘“總統號”輪船,安樂哲離開了香港。此後,他輾轉於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台灣大學、倫敦大學、劍橋大學等學府求學,先後受業於張佛泉、陳鼓應、方東美、劉殿爵、葛瑞漢等著名學者。
1978年,安樂哲完成了在倫敦大學的學業,在導師劉殿爵教授的推薦下,來到了夏威夷群島。
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的工作崗位上,安樂哲一干幾十年,期間與郝大維、羅思文等人合作,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引起廣泛關注的學術著作,翻譯了《道德經》《論語》《中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淮南子》等中國哲學經典。在他與一些教授的提議下,夏威夷大學創辦起了中國研究中心。在他主導下,2014年東西方中心與夏威夷大學成立了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夏威夷成為了溝通中西哲學的重要基地,安樂哲本人及其學術思想也被越來越多地中國學人所熟悉。

09年6月與許嘉璐參加尼山聖源書院奠基儀式
《儒學角色倫理學》
辨異觀同論中西——安樂哲教授訪談錄(胡治洪 丁四新)
2006年2—7月,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安樂哲(Roger T. Ames)以富布賴特(Fulbright)學者身份,到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講學。此間,我們與安教授進行了多次訪談,就中西哲學和文化問題向他請教。訪談主要涉及了超越觀、宗教性、系統哲學、過程哲學、儒道思想、經典翻譯、西方漢學、家庭倫理等方面。現將部分訪談內容整理髮表,以饗同好。
胡:安教授,我們國內哲學界對您還是很熟悉的,我在好幾年前讀過您的《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我們也知道您主要研究先秦和秦漢哲學和中西哲學比較。我們想趁您在國內講學的機會,對您作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安:看來這是中國學者的一個優良傳統。日本學者就不是這樣。我很多學術界的朋友花一輩子工夫研究日本哲學,可是日本學者卻認為他們自己的哲學是別人沒有辦法了解的,他們將此稱為yamato,意思是非常複雜、非常深刻的一種東西,別人不可能理解。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對我說,他覺得自己講日本哲學有進步,沒想到日本學者卻說他全講錯了。中國學者則希望我們基於自己的立場去了解中國哲學,從另外的角度去看中國哲學,希望我們“不在廬山中”。
丁:這其實是很有創發性的一種方式。不同哲學和文化傳統的對視,可以激發出新的思想,例如杜維明先生就從西方宗教傳統中激發出了對儒學宗教性問題的研究,他要建立這種對話,就必然關注儒學的超越性問題。
安:我在這方面與維明有點不一樣。如果將超越與內在作為一對類似“陰陽”的相關性(correlative)範疇,當然與中國傳統有關。可是transcendence與immanence是以西方傳統二元論為基礎的,如果將其“中國化”,表述為“內在的超越”或“超越的內在”,這就不是原來意義上的transcendence和immanence。這是中國人的一種說法,而不是西方人的說法。我與維明的差異就在這裡。
西方的transcendence的基本意義就是形上實在論(metaphysical realism),就是柏拉圖主義(Platonism)。柏拉圖是二元論思想家,他要將真實的世界與我們參與其中的現存世界截然劃分開來。中國沒有這種觀念,中國哲學家關注我們參與其中的現存世界。如果泛泛地說“超越”,例如尼采式的“超越”,他的意思是“超越你自己”;通過學習和教育,一個人就“超越”了他原來的境況,這顯然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所謂“超越”相關,比如從“小人”轉化為“大人”就是“超越”。但是嚴格哲學意義上(strict philosophical meaning)的“超越”,指的是一種完整的、不變的、永恆的、時空之外的原則,這種“超越”與中國傳統思想沒有關係。
胡:您在《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中就談到過這個問題。從西方的角度來說是這樣的,他們覺得超越的世界、神的世界是不可能內在於人的世界的。但是,儒家的一些大師大德,他們往往就在自己的內心體貼出本性,那個本性就具有神性,與道、誠、仁等超越的本體是合為一體的。
安:正因為他們是一體,而不是兩體,所以就沒有transcendence。Transcendence一定要依靠一個外在的、獨立性的存在。而“天人合一”之類的觀念,就排除了天人為二。
丁:那麼您認為牟宗三等現代新儒家所說的“超越而內在”是合適的嗎?
安:如果我將朱熹的“理”作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把一個中國的觀念變成西方的觀念,我當然可以這樣做。只是這樣一來,這個觀念就與朱熹沒有什麼關係了。如果將“超越”、“內在”作為中文的範疇,當然也是合適的,只是與新儒家所借用的西方思想原來的意義沒有什麼關係了。現代新儒家將“超越”、“內在”的概念“中國化”了,變成了陰陽、體用之類的範疇。但是,在原來的意義上,“超越”、“內在”一定是二元論的概念。在西方傳統的宗教觀中,個人是絕對不可能與上帝合一的,上帝與我是絕對分開的。如果將上帝看成是與我相關的,我需要依靠上帝,上帝也需要依靠我,這就不再是我們西方的宗教。在西方,上帝是完整的,他不需要任何個人的幫助。
胡:現代新儒家也承認兩種不同的超越觀,西方是外在超越,儒家是內在超越,可不可以認為二者都能夠成立?
安:“內在超越”與“超越”的原來涵義還是不一樣。或許可以用“超絕”特指西方的柏拉圖式的transcendence。“超絕”有斷開、獨立的意義,而“超越”就具有連續性。用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來分別表示西方的和儒家的超越觀。
丁:但“超絕”這個概念表示斷絕,如果上帝與人類斷絕開來,那麼上帝怎樣給人類發布命令,人類又怎樣聽從上帝的命令呢?
安: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問題。關於共相(universal)與殊相(particular)的關係問題,是從柏拉圖以來的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上帝是超越的(transcendence),他與我們還有什麼關係?這是歷來哲學家們無法解決的問題。亞里士多德的form(形式)與matter(質料)如何聯繫,也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西方傳統中有很多矛盾。比如宗教徒說“上帝是我天上的父”(my Father in Heaven),這表示他與上帝有某種關係,上帝是他的父親,他是上帝的兒子。但這與傳統宗教觀是有矛盾的。按照傳統的說法,上帝是一個完美的、完整的、獨立的存在,人類既不可能對他有任何增益,也無法對他加以分解。這樣一來,人類與上帝會有什麼關係?你可以崇拜他,愛他,可是最終對他沒有什麼影響,根本無法改變他。因此,懷特海(Whitehead)指出,如果上帝是完美的,那麼我們人類的創造性(creativity)毫無用武之地,我們只是nothing(無)。所以懷特海在他是哲學體系中,要將創生力(creativity)作為比上帝更基本的哲學範疇。
胡:上帝也並非一開始就是完美無缺的,其實,從猶太教到基督教也有很大的轉化,到耶穌降生之後,博愛就被突出來了。但在《舊約》中,上帝也有許多非理性的東西,甚至是很殘忍的。
安:是這樣。《舊約》是希伯來、猶太的。《新約》則與“希臘化”有關,包含希臘人的世界觀和他們的想法。《舊約》沒有希臘的影響,所以較為傳統。我在劍橋大學念書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可愛的老人參加我們的會議。他寫了《劍橋猶太教史》(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他一直想把《新約》譯成《舊約》,恢復《聖經》原來的面貌,使《舊約》再生。如果把《聖經》放在希伯來的架構中,它確實是另外一種狀態。
胡:那麼您是否認為在基本觀念上,中西之間存在著不可通約性?
安:中西之間最基本的不同在於,西方人是真理的追尋者(Truth seekers),他們永遠要追求超越性的真理,諸如God,Platonic Form,或Universals。而中國人從《大學》開始就把修身(self-cultivation)當作人的主要責任,要創造自己(self-creativity),把自己修養成為君子、聖人;因此,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一種方法來創造自己,這是dao/way-makers,也就是要追求“道”。西方哲學以知識論和形而上學(knowledge and metaphysics)為主,而中國哲學則以倫理和實踐(ethics and practice)為主。這樣看來,中國傳統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有密切關係,因為實用主義也反對形而上學和知識論,而認為理論與行動是合一的,意見只不過是一種習慣(habits),是行為的習慣。
胡:說到底,您還是把宗教和上帝作為西方哲學的發生點,而中國沒有這些東西,所以是世俗的。
安:我將要發表一個演講,題目是《儒家思想的宗教性》(Confucianism and A-theistic Religiousness),我認為,儒家思想是以人為中心的宗教。中國人具有宗教感,但卻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超越的上帝為中心,是另外一種宗教。對於中國宗教的認識要非常仔細。一方面,西方人已將中國傳統思想基督化(Christianized)了,如他們將中國的“天”作為西方的“上帝”,本著西方的宗教概念來理解中國哲學。另一方面,中國人往往把宗教與迷信混同起來,在言行拒絕接受宗教。如果輕率地判斷中國人有或無宗教,那都是不對的。實際上,是“禮”,而不是“天”才是中國宗教性的核心。
“禮”是一個涵義很廣的概念,以ceremony或ritual翻譯它,都不足以表達它的內涵。Ritual通常表示一個空洞的、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的行為,大致相當於“虛偽”的意思。而ceremony,如果你說it’s only a ceremony,這就和ritual的意思差不多了。然而“禮”當然不是虛偽的,它影響深遠,含義豐富,難以翻譯。
胡:這樣看來,以ritual或ceremony對譯“禮”都不恰當,然而許多英文論著卻正是這樣翻譯的,這豈不會引起一般西方人的誤解?
安:正是這樣。比如說羅蒂(Richard Rorty),他最懷疑的就是“禮”,因為他通過英文ritual來理解“禮”,而ritual是缺乏誠信的。一般西方人也這樣理解。道家批評儒家,也是指責“禮”的虛偽性。其實,“禮”是具有豐富內涵的,如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必須“仁”,才能有“禮”。
丁:西方作者翻譯“仁”這個概念時,有的譯作benevolence,如葛瑞漢(A. C. Graham,。安插話:他是仿照劉殿爵的);有的譯作humanity,如陳榮捷和杜維明。怎麼區別這兩種譯法?
安:Humanity是一個普適概念(universal),與羅馬的humanitas相關,意指唯一的、普遍的、本質性的對象。可是在《論語》中,“仁”雖然是一個核心概念(key concept),但由於它對於學生們來說是陌生的,所以學生們六次向孔子請教“仁”的含義,孔子給出了六種不同的解答。可見,如果將“仁”視為一個普適性(universal)概念的話,就會破壞它的個別性。因此我不使用humanity這一譯法。而benevolence也不能準確地表達“仁”的涵義。Benevolence只是表達一種狹窄心理態度的簡單辭彙,而“仁”的意義卻很廣大。我在翻譯《論語》時,將“仁”譯作authoritativeness,authoritative具有“禮貌”、“創作”、“權威”等含義,是一個很好的詞語。我現在正在寫的《中國哲學資料書》(Source book)里,則將“仁”譯作consummate person/conduct。
丁:我發現您在翻譯“儒”這個字的時候,經常使用拼音Ru,而不像通常那樣使用Confucian或Confucianism,這是基於什麼考慮呢?
安:這是為了表示“儒”這個概念在孔子以前就已出現。如果將“儒”譯作Confucianism,這有點像將泰利斯作為蘇格拉底學派的成員。泰利斯早於蘇格拉底幾百年,怎麼能將他歸入蘇格拉底學派呢?“儒”在商、周時代就已出現了,其職責是王室的顧問,若將後來誕生的孔子作為其名,是有點荒誕的。
胡:以上您比較多地談到中西宗教、哲學和文化的差異,您認為這兩大文化之間有沒有共同點呢?
安:也有共同的地方。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從超絕性(transcendentalism)開始,而20世紀西方哲學所批評的正是超絕性。因此,如果談詮釋學(Hermeneutics)、新實用主義(Neopragmatism)、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等等,他們都有一個同樣的目標,就是把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唯心主義(Ide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總之是把系統哲學(systematic philosophy)作為批判對象。因為系統哲學必然依賴某種唯一性,而這種唯一性是超絕的(transcendental)。在這一點上,現代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是可以相通的。
丁:但是中國哲學也有系統觀,如陰陽五行觀。
安:中國哲學的系統觀是開放的(disclosure),不是封閉的,如《易經》中的“易”觀念,那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而超絕性(transcendental)是斷裂的、封閉的,同上帝一樣,所以詹姆斯(William James)把它作為“封閉的宇宙”(the block universe)。西方哲學現在也要往過程式思維(process thinking)的方向轉變,而中國哲學自古就是過程式思維。
丁:中國哲學是有機的,相互聯繫的,過程的,創造性的。
安: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係,據我的了解,在20世紀初,中國重視的是康德哲學,哲學家們希望將中國哲學康德化。五四前夕,杜威(John Dewey)到了中國,並且在中國住了26個月,但他對中國哲學實際上沒有什麼影響,因為那時中國的哲學家們都崇拜德國哲學,以德國哲學作為標準。20世紀整個西方哲學從康德、黑格爾轉到維特根斯坦,再到現象學,中國哲學也遵循了這樣一個進程。西方到了海德格爾,就與中國傳統思想有了比較密切的關係,而康德與中國思想的關係是很疏遠的。康德的思想原質是universals,這是系統哲學的一個範式(model)。而海德格爾卻反對本體論(ontology),要把超絕性的觀念排除掉,所以他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存在著共鳴。但海德格爾主要是一個critic(批評者),而不是一個積極的建構者,他的最大貢獻是critique。而美國實用主義則除了critique之外,還有自己的思想建構。因此,我認為下一步將是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哲學發生相互影響。20世紀初,中國哲學通過以西方哲學為標準的轉化而謀求其自身的“合法性”。到了21世紀,西方哲學本身正在發生革命。我們很難說,中國傳統思想是否將會成為西方哲學——諸如美國實用主義、懷特海過程哲學等等的標準或來源。
胡:看來您對中國哲學未來意義的期望度還是很高的。
安:是這樣。我認為中國哲學的內涵非常豐富。問題是現在的中國學生們對他們自己的傳統不夠尊敬,認為那是保守的,陳舊的,似乎是一份過了夜的午餐。
胡:現在這種情況正在逐漸扭轉,不僅有很多學者在研究傳統文化,而且民間出現了許多書院一類的講學機構,推行少兒讀經,還有一些人士主張恢復“漢服”。
安:我見到牟宗三、方東美等學者的時候,他們就都穿長袍,很舒適,也美觀。
胡:還有一些學者,而且都是中青年學者,力主重建“儒教”。他們認為,中國人的心靈缺乏歸屬感,就是因為沒有一種形而上的約束。他們似乎在往外在超越的路子上走。
安:我昨天給學生們講到達爾文的進化論,一位學生表示不同意這種論說,他不接受人是從猴子進化而來的這種觀點,而相信人是上帝創造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轉向了基督教(胡、丁: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得很快)。一方面,我們意識到超絕性不適合中國哲學;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許多年輕人卻在接受不適合自己傳統的超絕性。
胡: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除了先秦兩漢之外,還有沒有拓展?
安:最近幾年我在夏威夷大學開了宋明理學的課程。西方對宋明理學的解釋,同對先秦儒學的解釋一樣,都存在誤解。他們都用形上實在論(metaphysical realism)來了解中國哲學。他們將朱熹形而上學化。實際上,朱熹的目標(project)也是修身,也是內聖外王,他也在尋求“道”,即一種成聖的方法,而不是要做一個系統性的哲學家,不是要建立一個形而上學(metaphysics)。
對現代新儒家,我關注得不夠。我認為,現代新儒家作為一個學派,他們之間缺乏關聯,如梁漱溟、馮友蘭、徐復觀等人之間沒有什麼思想聯繫;錢穆、徐復觀等人與西方哲學基本上沒有關係,而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卻與康德、黑格爾以及懷特海有很深的關係。他們的差別很大。我想他們的共同點只是在於解救中國文化傳統。
丁:就先秦儒學來說,據我了解,不少西方學者對於孟子和荀子也很感興趣,這是什麼原因?
安:這是由於一些人基於“四端”學說而將孟子理解為民主主義思想家,他們認為孟子的“性善說”為人的天生平等(equality)設立了一個基礎。我不同意對孟子的這種理解,而仍將孟子看作一個過程性思想家。孟子的“四端”並不是一種內在的、不變的本質,它是一個人出生時與生俱來的條件,可以說是一種本性(human nature),或者說是“命”,但這在孟子那裡不是主要的;孟子是以修身獲得的“第二性”(second nature)為主的,這就是《郭店楚簡》所謂的“性自命出”。
關於荀子,一些西方學者則將他作為一個知性的、系統性的、理性的哲學家(rationalist),類似於西方哲學家。荀子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性的思想家,他將墨子的思想儒家化,將兵法思想儒家化,他熟悉百家思想,加以選擇、分疏,他導致了先秦儒學與漢代儒學的轉變。董仲舒很讚賞荀子,認為荀子是非常重要的。而孟子直到宋明時期才上升為一個繼承道統的思想家。
關於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這兩種“性”是不一樣的。荀子的“性”是instincts(本能),所以他說人起初只是動物。實際上,孟子也說人與動物的差別“幾希”。因此,在根本上,他們對人性的觀點又是相同的。但是荀子很聰明,他總是要突出自己的獨特點,所以他批評孟子的“性善論”。他還批評思孟的“五行”說。
關於思孟“五行”與出土簡帛《五行》篇的關係,我個人很有興趣,近期將會寫一篇論文。我已經將《五行》篇譯成英文,但至今還沒有寫出研究論著。我每年在夏威夷大學都要開一門課,專門討論最近出土的材料,並且將其中的一些譯成英文。
丁:現在已有好幾部著作專門研究《五行》,如龐朴、魏啟鵬、池田知久等。不過池田將帛書《五行》定為漢代初年的著作,這個觀點已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郭店楚簡出土后,池田還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其基本觀點仍然是正確的,只需作一些局部的修改。
安:我與池田的看法總是恰恰相反,他說對,我一定說不對;他說不對,我一定說對。
我對《中庸》有一個看法。《中庸》最重要的範疇有五個:天、命、性、心、情。這些範疇在第一章中都提出來了。據此,我認為,《中庸》第一章是子思所作,提出所有重要範疇。以後各章引用孔子、文武之道、《詩經》等等,都是為了闡明第一章的涵義。《中庸》思想的內在一致性就是“人能配天”,突出人與天的共同創造性(co-creativity)。我認為《中庸》可能是中國最了不起的一部著作。朱熹說得很清楚,學者應該先讀《大學》,以便把握修身的基礎;其次要讀《論語》,理解修身所需要的範疇,如仁、義、禮等等;再次要讀《孟子》,它將這些範疇進一步擴大;最終要達到宗教性境界,就需讀《中庸》。《中庸》全篇有一種節奏,開始時很舒緩,而到末章則如同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要用頌歌的形式,通過引用《詩經》來表達深刻的思想。
胡:朱子在《四書集注》中表達過這種看法,指出了從入門的平易到體道的精微這樣一個漸進的過程。
安:我們翻譯的《論語》和《中庸》都是漢英對照本。我把“中庸”譯成focusing the familiar。focusing意為“集中”;familiar是“日常”的意思,並且與“家庭”(family)是同一個詞根,我要突出“中庸”與家庭的關係。
胡:您在中國經典翻譯方面有不少獨特理解,在美國應該可以成為一家之言了,或許還可以成為一個學派。美國做先秦兩漢研究的不少,但您與他們並不一樣,您有自己的看法。
安:我有一些學生,現在已經成為教師,我對他們確實有影響;不過他們也同我辯論。我們的看法與漢學家們的看法不一樣,他們不是哲學家,不支持我們的看法。記得在1972年,有位學者名叫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他寫了一部書,題為《即凡而聖》(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講述孔子之道。70年代是漢學家的時代,人們批評他,說他的書有問題,因為他的中文不好。可是我的老師是劉殿爵,所以誰也不敢這樣批評我,因為他們知道我能讀中文古籍。但是我們是哲學家,不要把自己混同於漢學家,因為我們承認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是哲學。如果談到文字、版本等問題,應該承認漢學家們具有權威,但是一談到形上實在論(metaphysical realism)或超越(transcendence)等等問題,他們就完全不知所云,他們根本不知道柏拉圖與懷特海有什麼區別。其實,漢學家們在字詞的翻譯上也有不少問題,例如他們將“天”譯作大寫的Heaven,這往往引起西方讀者的誤解;又如將“義”譯作righteousness,那是《聖經》中的用語,其本義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動”(obey the will of God),常人一輩子也不會用這個詞。所以,我將“義”譯作appropriateness,也就是“適宜”的意思,“義者宜也”。漢學家們往往以西方思想文化的框架去解讀中國經典,而我則要按照中國思想文化本有的框架來了解中國哲學。有的漢學家批評我顛覆漢學傳統,是激進的(radical)。但我按照中國文化本身來了解中國哲學,這恰恰是保守的。西方漢學家把中國文化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種文化中,這才是激進的。我所有的著作都已譯成中文,中國學者對我的著作當然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是認同的;而我與那些漢學家卻總是存在衝突,或者可以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在研究什麼,不知道比較哲學研究的重要性。
胡:您對《緇衣》與子思的關係怎麼看?
安:既然《禮記》與子思具有密切關係,那麼《緇衣》當然也與子思有關。竹簡本《緇衣》與《禮記·緇衣》我都讀過,文字有些差別。李學勤、龐朴等學者認為竹簡本《緇衣》就是亡佚了的《子思子》的一篇文章的抄本,將它定位為孔孟之間的一個銜接點。
胡:竹簡本《緇衣》與《禮記·緇衣》存在一些重要的差異。竹簡本《緇衣》有兩個本子,一是郭店簡本,另一是上博簡本,這兩個本子雖然比較接近,但也有差異;而兩個竹簡本都與《禮記》本差別較大。其差別一是各章排列有變化,二是有些章的文句有增刪。這些差別是否蘊涵著某種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史的意義,很值得探討。
丁:您有一篇文章經彭國翔翻譯后發表在《中國哲學史》上,談到莊子的生死觀,並涉及莊子哲學的一些基本觀念,還引入了西方生死觀的哲學背景。您如何看待儒道兩家的生死觀?
安:莊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生死問題,他與先秦其他思想家的看法不一樣。儒家雖然也承認人是動物,但又認為人有文化,所以會從動物轉變成另外一種高層次的生物。但莊子認為人與萬物相比,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不過是一個過程而已,人們經過這個過程而“物化”,這有什麼值得可惜的?我們每一秒鐘都經歷一次生死,每一秒種都是死亡之後的一個新生;既然我們經歷了無數次死亡而仍然活得很好,我們為什麼要厭惡將來的死亡呢?這是一種自然化的思想。
丁:莊子的生死觀是對以往那種悅生惡死的生死觀的顛覆,他還嘲弄了那種自以為了不起的人類中心論。
胡:莊子與老子的思想實際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道德經》和《莊子》是兩種風格。
安:是這樣。把它們作為一個學派是司馬談的觀點,這有點勉強。它們有關係,但卻不是相同的。
丁:老、庄的基本出發點和目標是什麼?
安:《道德經》關注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所以老子強調無為、無欲、無知。但無為、無欲、無知根本不是有些人理解的no action、no desires、no knowledge;無為(noncoercive action)是最好的關切,無知(unprincipled knowing)是沒有偏見的了解,無欲(objectless desire)是不要佔有外物。
現在西方已經有兩百多個《道德經》的譯本,最流行的版本可能是我的老師劉殿爵(D. C. Lau)的譯本,已經銷售近兩百萬冊。另一個流行版本是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的譯本,他將《道德經》譯成The Way and its Power。可是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他把“道”上帝化了,超絕化了。但“道”並不是獨立於世的,不象上帝那樣用他的權力來創造世界。
胡:談到翻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一些英文經典作品,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或湖畔詩人的詩,那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讀得如醉如痴,但是我們讀起譯作來就感到很平淡,即使這些譯作是出自第一流翻譯家的手筆。同樣,中國的經典譯成英文,西方讀者能不能夠體味其中的神韻呢?
安:我正在編寫《中國哲學資料書》(Source book),在這部書的《前言》中談到了這個問題。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是美國一位著名的現代詩人,他曾說,把一件作品譯成另外一種語言,就失去了這件作品的詩意(what is lost is the poetry)。將莎士比亞、華茲華斯的作品譯成中文,原作的詩意就喪失了,就沒有那種味道了。但是,我在這篇《前言》中也指出,把一件作品譯成另外一種語言,也可以發現“詩”(what is found is also the poetry)。通過翻譯,一件作品被擴展了。《道德經》如果只有中文版,它就只有中文的涵義。如果將它國際化,它就成為一件意義更大的作品。雖然外國的《道德經》不再是中國的《道德經》,但它也有自己的身份和意義。
翻譯對文化的交流和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曾把唐詩譯成英文,他的譯作既脫離了西方詩歌的傳統風格,又打破了唐詩原有的格律,成為一種自由體詩。龐德所譯的中國詩歌對20世紀西方詩歌的影響非常大,西方詩歌受龐德譯詩的影響而形成了一種新面貌,但這種面貌並不同於中國詩歌原來的風格,而是龐德基於中國詩歌的新創。近來,中國詩人又反過來模仿西方自由體詩進行創作,這就形成了一個循環(circle)。所以,將一件作品譯成另外一種語言,一方面令人擔心,會不會成為第三種語言?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它發展起來。一方面它可能缺損了某些部分,另一方面卻可能增加了某些部分。
胡:您說得對。翻譯確實是一種非常必要的文化交流手段。翻譯雖然可能使作品失去一些內容,但創生的內容或許更多。
安:還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翻譯的重要。20世紀20—30年代,英國有一個非常偉大的團體,稱作Bloomsbury Circle,其成員包括艾略特(T. S. Eliot)、奧斯汀(Jane Austin)、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等,他們都是偉大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家。而阿瑟·韋利就因為將唐詩和日本古劇譯成英文,就被接納為這個團體的一員。這是由於他將一個新世界介紹到英國去了,所以大家都尊敬他,因為他對中國和東方有所了解。
丁:您也研究過《淮南子》,請談談您的觀點。
安:《淮南子》是很有意思的一部著作,但陳榮捷的《中國哲學資料書》(The 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卻忽略了它。陳很重視先秦,因為先秦的思想比較純粹,儒家就是儒家,道家就是道家,而《淮南子》的特點就是雜,就是和而不同。一方面可以說《淮南子》是道家著作,但同時它也調和了其他許多思想,構成一個新的體系,這體現了漢人的思考方式。漢朝在中國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但受到的重視很不夠,人們通常認為什麼都是先秦的好。
《淮南子》是很難懂的一部書,把它譯成英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獲得博士學位后,每年夏季都還到香港去,跟著劉殿爵老師一起繼續《淮南子》的翻譯。現在我們已經出版了兩部書,一部是我的研究著作,另一部是《原道訓》的漢英對譯。
丁:能不能請您談談西方的家庭倫理?
安: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杜威要把民主制度與民主意見分開,二者往往是有衝突的。制度是保守性的,與傳統有關;而意見卻是活生生的。杜威認為,意見就是個人把自己整個地給予社會,社會則回報這個人所需要的材料和條件,使之完成自己。民主意見實際上就是個人與社會的一種合同。現在有很多人在談論中國的民主化,其中有些人主張回到孟子,以“四端”平等思想作為建立民主的基礎。我個人認為,“禮”就相當於杜威所說的那種合同。從《中庸》可見,“禮”是從家庭發生的。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恰恰也是:一個人要把自己整個地給予家庭,而家庭則給予這個人所需的材料和條件使之完成自己。所以,談到中國的民主主義,一定離不開家庭。西方傳統與此不同。柏拉圖斷定家庭關係一定會導致偏袒,亞里士多德說家庭不好,認為家庭是不平等的。可以說,西方傳統哲學家都不關注家庭的重要性。現在,與美國民主主義構成最大衝突的正是個人主義,是自私,是普遍的利己主義,是非社會性和非家庭性。所以,我們要問:理想的民主能否離開家庭?西方人想不到這一層,誰都不願把家庭制度與民主制度聯繫在一起。現在西方的家庭普遍不穩定。以我的家族來說,我有六個兄妹,大哥離婚了,有一個孩子;二哥離婚了,有兩個孩子;我是老三,有家庭,也有兩個孩子;老四離過婚,有一個孩子,現在又有了新太太;老五是妹妹,沒有結婚,但與一個人同居;最小的也離婚了。只有我的家庭是穩定的。
胡:您為什麼會比較特殊?
安:我認為結婚是一輩子的事,而不是一種短期的合同。並且我的夫人也非常好。
胡:這可能是關鍵所在,您的夫人是東方人(按:安夫人是日裔加拿大人),東方人是重視家庭的。
安:可能是這樣。我們在夏威夷受到的東方影響特別濃厚。
丁:不過近年來的調查表明,北京市民有半數是離過婚的。
安:這可能是轉折時期的一種行為表現,比如年輕人要表現自己很自由。
丁:你們兄妹之間怎樣交往呢?你們在交往時考慮道德倫理規範一類問題嗎?
安:我們兄妹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大家互相關心,特別是我的妹妹,她是我們的核心,她把我們弟兄們看作小孩子,是她非常重要的事情。
丁:你們兄妹的配偶在這個家族中處於什麼地位?
安:這與家族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個人交往的事。比如我妹妹的男朋友,我們兄弟都很喜歡他,如果我妹妹離開他,我們還會接受他。老四的新夫人也是這樣。大家也都喜歡我的太太,我妹妹同她的關係特別好。我妹妹從高中十二年級開始就隨我們生活,跟我們一起到溫哥華,到英國,我們到什麼地方,她就要到什麼地方。現在我研究中國哲學,我妹妹就學中文,將來也想來中國。還有我哥哥正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
不過我們的家族關係在西方比較特別。總的來說,西方的家庭制度很薄弱,家庭與個人是相衝突的。西方的個人主義有很長的歷史,從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開始;然後是奧古斯丁(Augustine),他認為一個人如果缺乏自我和自由意志,就不能承擔道德責任;再到約翰·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也都是主張社會和經濟的個人自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容格(Carl Jung)還從心理學方面加強個人的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所以個人主義在西方是一種歷史悠久而且根深蒂固的觀念。我認為這種觀念與民主主義是相衝突的。以美國來說,一方面存在許多機會,另一方面也存在非常大的問題。美國監獄中的囚犯是夏威夷人口的兩倍,已經超過兩百萬。如果我到紐約去,我夫人一定要囑咐我給她打電話報平安,但到中國來,她很放心,這是一個安全的國家。
胡:那麼我們衷心祝願安教授在武漢大學和其他高等學府的講學成功,生活愉快!
《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