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前沿文庫
小說前沿文庫
《小說前沿文庫》是2010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亞伯拉罕·螻冢。
《小說前沿文庫》是亞伯拉罕·螻冢主編,由新世界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的一套先鋒實驗小說叢書,2010年出版第一輯,十本。2011年出版第二輯10本。這是繼長江文藝跨世紀文叢之後又一次對漢語先鋒和實驗小說的拔梳,整理。該文庫集“先鋒、實驗、異端、集成”式的史詩作品於一體,網路本土新新寫作勢力,被坊間稱之為“中國小說的頭腦風暴”。編撰主旨旗幟鮮明地指出,小說創作主體之知識譜系和學問功底已經不同於前三代作者。
現代漢語小說創作自近三十多年以來,惜其有所斬獲,也憐其多受歐美和拉美地域文學所惑,從方法論和更本質的角度看,有所建樹者寥寥無幾,其中原因,最明顯的莫過於乃這一代作者的知識譜系不完備甚或不學無術所致。這幾代人的創作敵不過白話文最初三十年的努力。
本文庫所汲各種形體的小說文本是中國小說土本重建自信的呈現,創作者除了他是一個小說創作者而外,還有一些更加顯耀的背景身份,他們是哲學研究者,是人類學和民族志工作者,是語言學者,是詩人,是物理科班出身的,是文史資料專業收集者,是國學研究者,等等,這些構成他們寫作小說時最堅實的一部分,那種純粹的依靠講故事想獲得小說成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換而言之,整個時代的閱讀水準在發生改變。相應的,創作者對自身的要求也在一再的發生改變。總而言之,這套書的創作者和前一代人的區別在於,創作主體的身份和知識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所以,他們創作的文本也已經與前輩所走過的路表現出了巨大差異,也已經不是先鋒和實驗可以攬廓的了,他們都是異端,是對現有文學價值觀的反撥與顛覆,更是一種大小說觀念的集成。這種集成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創作者自身修為的創備,二是對過往一切集體智慧的繼承與反思。他們當中不乏嘔心瀝血者,有的文本創作時間跨越二十多年。在紙質傳播變得更加奢侈的今天,印刷出版純文學作品尤其顯得杌隉,然吾道不孤,叢書之旨在於集中釐清中國小說重建道路的岔路口在何處,而可以稱之為有所成就的又在何處,其勞自為,其功自顯。
《小說前沿文庫》第1輯(2010年已出版)
□侯 磊《還陽》14萬字 □姚 偉《尼祿王》 15萬字
□張紹民《村莊疾病史》 28萬字 □向祚鐵《武皇的汗血寶馬》 8萬字
□楊 典《鬼斧集》 28萬字 □霍香結《地方性知識》36萬字
《小說前沿文庫》第2輯(2011年 即將出版)
□惡鳥《馬口鐵注》 16萬字 □張松《景盂遙詳細自傳Ⅰ》11萬字
□徐淳剛《樹葉全集》12萬字 □譚毅、一行《戲劇三種》21萬字
□餘地《謀殺》 38萬字 □朱琺《安南故事集》 35萬字
□陳博智《雙橙記》 13萬字 □劉恪《城邦語系》 50萬字
《現代派文學辭典》

小說前沿文庫
這部辭典對於動詞“寫作”的反省在現代漢語當中是獨絕的,它是當代文學集成意義上的初始,不是一般意義的寫作可以賅括得了的。處幽之時,我們在一起談論的話題其豐富性、深刻性已遠遠超越了這部詞典所涵蓋的內容,謂之給“當代作家們上的課”,而輻射枝大多有所本,這個“本”可以說很多都曾出自過這裡,這是輻射源。討論的背後盤旋著一頭幽靈:關於一部自動打字機器輸出結果的問題。這部機器裝載了普遍文字系統——巴別塔之後的任何一種文字,這種隱喻仍然適用於有史以來具有獨立書寫能力和文字體系的部落、民族、國家。它輸出了所有的可能性。換而言之,迄今為止和未來無限時空(一種非此即彼的世俗線性時間觀)的書寫能力和結果都在此列,而且完備。在這部偉大的機器當中,唯一的終端功能就是檢索。這種端倪在現今的寫作當中已現端倪,包括一個寫作者的輸入法,思維路徑,他的凡是關於他的可能性。而作為個體的寫作則遂然顯得無限狹小,不管你是類的,還是無限集成的;你寫得多也好,寫的少也好,在所有輸出結果和可能性中,只有所佔比例之輕重的問題,只有廢話和不那麼廢話而已。這很容易拿光譜、色譜來打比方;某光帶或色帶就是作者或類作者群的棲息的居所。很顯然亂碼則變成一種更為高級的,僭越文、史、哲、宗、藝的存在,無法完全釋讀的譜系帶,它可使用於未來,也可適用於外星文明。我們低估的是亂碼留下的玄機。這種自動輸出機器首先對寫作主體——即作者頭一次構成無邊的威脅,和猥褻。也就是寫作本身被顛覆。寫的意義和作者的意義被顛覆。在這種勞作當中,沒有署名的必要,更沒有知識產權。也許你會問,那麼,心靈(和靈魂)怎麼辦?如果,你所有的東西是依靠了文字的,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存在被提問的前提。它給予的絕望是無邊的。人類的書寫活動正因這逐漸來臨的幽靈而遞減。因此,無限進行的打包壓縮-類,複製-克隆,下載-有用性,獲得正統性,自動打字機器輸出的結果,或許本身並不需要輸出,而只是像雲端計算一樣存在於某個地方,它構成了全部文明史的資料母性-父性。當代的寫作之意義正在於指出這種處境。所以,賈勤更願意選擇這種方式:“說”,而不是“寫”。指向人類歷史的書寫之謎——述而不作。他憂游於這個幽靈的周圍或內部。而已經寫下的——或許是因為不曾放棄《說文》、《四庫提要》以及“百科全書”耀示的宇宙體系和那種最終的也是持久的原始閱讀衝動,是作者在這種廣袤無限的絕望中僅留的一絲情願。而凡想要進入的也須自己找門。
2010年夏至后三日 雲室
《長歌》:最後的詩意鄉村
侯磊

小說前沿文庫
自打那匹布飛上天空以後,有一些布匹上的花紋就印在了天上,幾個月內不消失。當時人們打聽河灣村時,外村人就指著天上那片花紋說:看那,正對著那片花紋的下面,就是河灣村。那段時間,河灣村因此很有名。
由此可見,《長歌》的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首詩,《長歌》是偽裝成長篇小說的一部鄉村史詩。
《長歌》用詩意的語言,描繪了一個名為河灣村的村莊離的人、事、物,和他們的生存狀態。小說的主人公是張福滿一家人,圍繞這一家人發生了許多事情,其中有河灣村中的春種秋收,張福滿和她的妻子張劉氏養育兒女,張福滿的兩個兒子張文、張武成家立業,村中船工趙老大、趙水父子在河上擺渡架橋,卻沒有一件事情作為主線來貫穿,而是像電影一樣,當鏡頭對準哪一場戲時,那一場的畫面就浮現在讀者眼前了。而整部小說就像一條緩緩流動的河,作者帶著讀者坐在河畔,作者說:你們看,這是荷葉,這是柳條,這是花瓣,這是擺渡的小船,這些都漂浮在水面上,他們都往前漂去,一會兒就看不見了,永遠的看不見了。
《長歌》充滿了魔幻描寫,這是作者自己筆下的鄉村,他的鄉村就是如此美麗,如此充滿幻想,然而,這一切都是暫時的。人是會死去的,詩意鄉村的生活模式是會告一段落的。隨著小說的發展,漸漸成了一部河灣村“村人遠去”的經過,先是張武的妻子二丫死了,三叔和三嬸的兒子小三死了,二丫的父親王老頭出走了,張武出走了,船工趙老大在救人之後也死了,再後來就是所有的人都老了,直到張福滿的妻子張劉氏吃多了桑葉,自己做成了一隻繭,準備成為一個新的人。
在小說最後,張劉氏像蠶一樣做了繭是一個非常好的隱喻。它預示著詩意的鄉村不會終結,而是在一段詩意結束以後,還會有新的一段詩意產生,而新的一段詩意是否和原來的一樣,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而這一切,都是作者為最後詩意的鄉村,唱了一曲長歌。
夢亦非《碧城書》 14萬字
鬼師家族的史詩——簡評夢亦非《碧城書》
姚偉/文
按照眾多作家和文學研究者的說法,八十年代至今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作家,是拉丁美洲的兩位文學大師: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簡稱“二斯”。讀罷夢亦非的《碧城書》,讓我由衷感嘆這個判斷的高明。夢亦非是二斯的好學生,他就像自己筆下的鬼師一樣,繼承了師父傳下的所有魔法,並且在自己的書寫中交替使用,從而出色地完成了這部鬼神的史詩。作者的技法更近馬爾克斯,主題則是圍繞博爾赫斯的遺產展開:鏡子,迷宮,時間和命運,如此等等。當然,在結尾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也受到了“火神”赫拉克利特的啟發:“所有的火是同一個火,就像所有的人是同一個人,他有不同名字、身體、性別,所有人是同一個人的不同存在,於是所有的火是同一個火的夢,以及想象。”這種詩與思交融的段落,為作品增色不少。
小說的故事很簡單,大部分段落是不可複述的,而可以複述與無法複述,正是故事會寫法與優秀文學作品的重要區別之一。農民起義軍首領潘新簡與官軍爭奪都江城,目的不過是在鬼師大院里修建世上最出色的迷宮。相信讀到這裡,多數讀者都會和我一樣驚呼:多麼典型的博爾赫斯式主題!果然,在作品行將結束的部分,作者揭開了迷宮的部分謎底,而謎底本身又會盤旋成一個迷宮,“按照潘新簡的說法,每個人都是一個迷宮。因為人總是在追求意義,但意義卻在不斷地改變,一個人自身的不斷改變與他所追求的意義之間的關係也在不斷改變,這即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迷宮。但我想得更深一層:也許人可以了解其他事物,但卻不可能徹底了解自己,對自己來說,自我即是一個迷宮。每一個人即是由無窮無盡的迷宮組成,玄之又玄”。
這樣的段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博氏那些著名的篇目:《關於猶大的三種說法》《小徑分岔的花園》《兩位國王和兩個迷宮》《死於自己迷宮的阿本哈坎-艾爾-波哈里》。在博氏筆下,最大的迷宮只有一個,那就是時間,我們無法經歷的歷史時間,生前和死後的時間,這些事物像漆黑的布幕一般,為夢亦非筆下的鬼神提供了藏身之所。
與考場作文的寫法相反,這部魔幻之作的開頭平淡無奇,甚至略顯沉悶。倘若讀者到此止步,他們或許會以為又是一部郭四娘《幻城》那樣矯情又淺薄的作品。不過讀者若能耐心讀完開頭,會發現後面很不少奇特的部分等著自己,作為對閱讀耐心的回報。都江人的門板上不停地長木耳,木耳堆成的垃圾嚴重擾亂了人們的生活秩序,最後都江知府被迫下令,將木耳鑄成一個大大的圓球,讓全城男人將它推入江中。沒想到木耳球將江水截斷,後來鬼師請來螞蟻才將它毀,卻又釀成了一場水患;“我看到一條閃電宛如靈蛇般從窗子中擊進來擊向我的面目,我大驚失色,感覺自己就要死了。誰知道我的思慮尚未結束,床頭的那面鏡子嘩地響起來,它吸引住了雷,雷竟轉彎擊在了鏡子上,擊得鏡子粉碎,碎片飛濺到數尺遠的地上,壁上只留著一個空空的木鏡框,在輕輕地晃蕩……當我抹著滿臉的冷汗從床上坐起來時,對鏡子無限感激而又無限恐懼。感激的是如果不是因為它我已被雷擊中,恐懼的是,如果不是鏡子掛在我的床頭,我的影子便不會暴露在鏡子中,從而招來了雷。那雷一定是將鏡中的人當作了我,認為那就是我的魂魄,從而放過了肉體的我。”
我相信,這樣的情節如果布滿所有段落,《碧城書》一定會像《百年孤獨》一樣享譽全世界。“都江城人認為鏡子與交媾是神聖的,因為它們讓人口增殖。”小說里這樣寫道。博爾赫斯則在《虛構集》里說,“鏡子和父親身份是可憎的,因為它使宇宙倍增和擴散。”《碧城書》是《百年孤獨》鏡像嗎,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我只知道,在這個什麼極度物化,什麼都不再敬畏,也因而變得極端無恥的時代,品讀一部專寫鬼神的著作,對所有人都是一種警醒。因為很多時候,對鬼神的敬畏是個人或民族重新尋回尊嚴的開端。
人與,把肉體燃燒成哲學童話
李 霞
人,除了肉體和靈魂還有什麼呢。醒著的人,除了行動著的人和思想著的人,還有什麼人呢。
人是肉身化的理性,有思考的生物——這個稱號使他區別於其它生物,成為萬物之靈長。
人類在童年時期,靠行動活著,不行動就會被其他動物吃掉;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主要靠思想活著,不思想就會被其他人吃掉。人吃人,比動物吃人更殘酷更可怕。
絕大多數人都在思想生活和工作。思想是如何思想的,思想應該怎樣思想,——對思想的思想,古今中外有幾人呢。
青年詩人人與,在寫詩的同時也開始踐約他非凡的諾言“我要去耕耘人類。使人類成為一個全稱。”《智慧國:雙岸黃源如是說》,人與寫了10年,已完成20多萬字。它是小說,又像散文,甚至像隨筆,但又都不像,它應該是一部聖經體哲學童話。
雙岸黃源,是書名中的一部分,也是書中的主人公。主人公活動極少,故事沒有,主要是思想,他幾乎就是為靈魂而活著:
雙岸黃源踏上了尋找心靈的道路。在耕耘人類之前,他在耕種自己的內心;在耕耘全人類之前,他要耕耘自己全部的心靈之地。
高山,會是雙岸黃源一生中惟一的出路,心靈指向了這條道路,這是靈魂的選擇,它是對的。靈魂從遠方而來,它有許多未知的秘密,已逝了多少時光它才來到,它從光中而來。
“學習光”,在“光”中得到我們的心靈,迎來我們的靈魂。
雙岸黃源其實就是詩人人與靈魂的化身。
人與,本名向軍,七十年代生於河南信陽。在鄭州上了大學,2003年前後北漂到北京,在一個私人文化公司作編輯謀生。想抽出3年時間,全力做些與登山有關的事情,願能登一次珠穆朗瑪峰。2000、2001、2005,分別主編了3期《審視》民間詩刊。寫了大量詩作,與《智慧國:雙岸黃源如是說》相類似的作品還有《虛象的世界》《時間記史》《論自然生態與人生生態之說》。將來的寫作,人與已列出了計劃,不僅有《靈魂的歷程》《母性聖簡》,還有《國家》《民族》《體育》等20餘種。一些大學者也不敢如此寫作。
人與的寫作,不僅超越了同代也超越時代也超越了國界,的確是在“耕耘人類”。有誰在想“護航那極易出病症的整個人類走向未來”呢。
美麗的母親,注視著面前的自然之子,看著他閃爍清澈之光的眸子,問道:“你長大了為什麼事物工作呢?”
母親想知道雙岸黃源的心愿,赤子的童心。
年幼的雙岸黃源朗聲回答:“我要去耕耘人類的清晨。使人類成為一個全稱。”
——01 冰雪的課堂
他們不知思想性的價值,思想有一條道路可走,陽光從天空而來,思想藉助思想的手段,不是暴力的手段,才能保留最初形成的思想價值的核。而沒有流失、變質。思想惟一可行的道路,陽光從天空上而來,陽光不從暴力內而來。
不要信任心,要信任指向未來的心與良協;不要信任有素養人的言行,要信任更多更為廣大的人群坐下談判、妥協與讓步所形成的法典;不要信任國家和民族,要信任人類;不要信任人類,要信任生靈與自然……
——01 冰雪的課堂
減少人口對大自然的壓力,從而有了大自然給予人以靈性的機會。今天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緊張,很快反映出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人與自然的緊張再次迫使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更難以消解的生存與反生存的血性緊張。
——02 人口
世界性的組織,是人類在這一關鍵時刻選擇了思想性的價值,選擇了思想性的道路。人類的未來,此時選擇了坐下來,坐在桌邊;選擇了談判、妥協,達到雙贏、多贏、協和共贏的結果,對更多他人、它物的尊重與敬畏;選擇了交流;選擇了價值;選擇文化的法典,並以此作為遵循的秩序。
——07 世界性組織
一個連自己都難養活的中國青年詩人,竟去思考“世界性組織”這樣的“地球事”,這事本身就讓人感到“地震”。
人與的思考,使“杞人憂天”這個古代典故終於有了現代版。
人與思考的價值是無價的。誰能說清靈魂被驚醒后的情景?!
人與的詩人哲學家或詩人思想家之路才剛剛啟步。
2006年2月15日在揚子鱷論壇見一貼,是署名“葉樹”的《為中國思想界寫份悼詞》,意思是說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已失去了獨立思考性與批判精神,成了權勢與金錢的奴隸,思想界已死了。如果葉樹看了人與的作品,他會改變自己的說法的。儘管人與的《智慧國:雙岸黃源如是說》還沒有完稿,儘管人與現在的影響力還微乎其微。
《還陽》
命運的純粹鬧劇或絕對嚴肅

小說前沿文庫
《還陽》在形式上有其獨到和創新之處,小說一共八章,每一章節的開篇都在寫畢玉凈身,每一章都讓我們親眼目睹一個人命運轉變的過程。而且,每一章前面類似楔子的這這部分都寫得極其莊重、嚴肅、乾淨利落,和下面“長死賴活”的鬧劇形成鮮明的藝術對比,當我們沉浸於鬧劇或厭倦於鬧劇其實是中了作者的圈套!小說第八章開篇部分的結尾這樣寫道:“隨著畢玉向內務府會計司正式的報名註冊以後,京城中那片古老的宮殿在向他招手,他的太監生涯就這樣開始了。”但是,這時的畢玉已經因走投無路而跟著湯若望逃出了宮,也就是說,他的太監生涯其實已經結束了。開始和結束就這樣處在同一個時空中。小說大結局處,意大里亞人湯若望對手下說:“先不忙,先好好的看著他。回到意大里亞再說吧。”畢玉的太監生涯結束了,而又一輪劫難正在未知之中黑暗之中等待著他,小說至此戛然而止。
《還陽》的京味特色十分濃郁,幽默搞笑的對白,相聲、戲曲的巧妙運用,作家還運用了大量的宮廷野史,醫藥、戲曲、製造、膳食等描寫引人入勝,尤其是對京城街巷生活的描摹筆調蘸滿同情,宮內宮外形成強烈的反差卻又不著痕迹,向我們展示了細膩、廣闊的人世生活。
“還陽”通常的意思是說人死之後從陰間返還陽間,而小說中的“還陽”指的是未盡之男根的死灰復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說處處都點明畢玉燎原的渴望,但他似乎一直被心中的魔鬼、被可怖的繩索所牽絆,臨到最後也未能如願以償。人的命運要麼絕對嚴肅要麼純粹是個鬧劇;“還陽”其實是一個“城堡”般的隱喻,它隱喻的是什麼?我不告訴你。
《尼祿王》
“海灘”之書
——評姚偉《尼祿王》
林國榮

小說前沿文庫
在某種意義上塔西佗乃是此一時期羅馬精神即將實施重大轉變的集中代表;他既不同情舊秩序,也不同情新秩序,相反,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羅馬精英階層在希臘文明的殘酷洗禮之下,開始整體性地有意識遺忘並放棄往日里以政治才華著稱於世的古老民族,將這個民族歷經數百年之久積累起來的龐大政治經驗視為無足輕重的過眼雲煙,並轉而提出異常嚴厲的要求,要求人類從無聊的政治黨爭中走出來,注視發生在人類靈魂內部的劇烈鬥爭。此一潮流之轉變蘊含著難以盡數的力量,要等到一千五百年之後才有人斗膽說出“愛國家勝於愛靈魂”這樣的話,真正的逆轉則還要再等三個世紀。
只有理解到以上所述,才能為理解尼祿搭建一座平台。在將現實的政治鬥爭轉化為靈魂以及激情的內部鬥爭方面,尼祿完全稱得上是埋葬在死狗之地下面的傑出人物。像當年的西皮奧那樣,尼祿再次表明偉人之軀往往並非葬身聖山之丘,而是尋常可見的瓦礫堆下。為了活在這個世上,“只需要小小的一點藝術”,這是尼祿最忠實的自我刻畫,也是古典文明在從小城邦的殘酷鉗制和暴政的自然循環中終於擺脫出來之後,發出的第一聲喟嘆和達到頂峰的標誌。對於羅馬宮廷來說,尼祿是個殘忍且嗜血之人,對於共和派,他是生死仇敵和叛徒,對於帝國的精英階層,他情感上的狂熱則證明了他是非理性的黑暗之王;羅馬平民時而崇拜他,時而欲殺之而後快,他的藝術才華將領袖與群眾之間歷來的危險、善變而複雜的微妙關係演繹到了無以復加的精微之境。蘭克曾慨嘆馬基雅維利筆下的博爾吉亞“原來罪惡也有藝術的典範”,但就罪惡本身而言,博爾吉亞應當以尼祿為師,尼祿為藝術而藝術,博爾吉亞則並未超出純粹手段的範圍。一種被尼祿奉為神聖的意志貫穿在罪惡當中,使尼祿將罪惡推向了絕對之境,並致使尼祿在臨死之時因為“既找不到敵人,也找不到敵人”而感到恐懼;然而,我們應當原諒尼祿,即便耶穌也一度因為承受不起神聖意志的重壓而感受到基於“人性”的哀傷、懷疑和動搖。
然而,何謂“人性”?人性不過是17世紀宗教戰爭結束之後,歐洲精英階層以“理性”之名對人類生活中的常態元素所作的抽離和匯總,這一抽離和匯總正式穩固並紮根在18世紀以來的經濟學體系當中,以和平、統一性、秩序和可解釋性為基礎和訴求。此種模式將理性態度、確定性、安全以及幸福相繼歸入人類生活的上層領域,將歷史中斷裂的、絕對的以及虛無的力量和元素歸入下層領域,這一領域中生活著無產階級或者賤民階層,情感當中的深層之物和一切因喪失統一性而無法解釋之物都淪為非理性的過時和原始之物,作為人類文明史的“史前史”而被驅趕到歷史解釋範圍之外的虛無之地和流放之地。對此,以學術機構的“假定知識”之權威為支撐的史學教授和文學教授們只需說一聲“斯人已逝”,便可避免承認“權威即知識”這一所有學術作品的效力和權力保證的絕對虛無的前提。
《村莊疾病史》 28萬字
閱讀張紹民先鋒長篇小說《村莊疾病史》有感
泥馬度(詩人,小說家,歷史學者,出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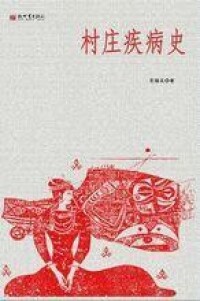
小說前沿文庫
是的村莊里人們生病萬不得已是不去醫院的,活受唄,拖著病體侍弄二畝田地。看似好好的人,一下子就玩了。生就是疾病,生就是苦苦支撐,而不言語。
詩人張紹民用一雙冷眼,揭去表面村莊而抖露出它的真相。高度概括出來的這兩字,又有種種有同的名字。像一頂頂帽子找到各自的主人和故事。一本疾病花名冊組成一部有血肉有肉有淚的小說。
村莊為什麼生病?病因、病理是什麼?小說中都一針見血地扎了下去。
女人是村莊的靈魂。小說中有幾個女性可謂是典型病人。村莊最美而健康的姑娘是湯酥紅。她的笑聲那麼美,彷彿一顆顆種子發出芽來了。萬物見到她都開心。鳥兒落在她肩上。美成一首大地的詩了,美成大地的愛情了。但她要癱瘓!她是活活被村莊的暴力強姦致殘的,在羞辱、愛情破產中死去。死去的人,變成了鬼相反比活人要有了力量。壞人去刨墳時感到“死人顯聖”。在村莊美就是一場災難。美與詩歌慘滅於村莊里代表支書那一種力量的胯下。
《武皇的汗血寶馬》 8萬字
劉麗朵:幫老向澄清一下,同時俺是這件事情始末的見證者之一。胡續冬回國那年,正是俺跟Q老爺如火如荼的階段,軍功和馬爾克斯和一副卡羅牌成為俺們談亂愛的道具啊。這件事可以看到向祚鐵同學的基本風格:機智,又老實。向同學畢業於清華物理系,他的智商絕對令他有不老實的資本,但他又是絕對的老實,怎麼老實呢?他曾經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寫了小說當中的50個字。------------------------------
向祚鐵聲明書
關於“馬爾克斯序言”一事的正式說明
在我的短篇小說集《武皇的汗血寶馬》正式出版之際,關於幾年前的那個“馬爾克斯序言”,網路上出現了一些說法。藉此機會,我就這一序言作一正式的說明:
這一序言確實為我本人杜撰,但就我個人主觀意願而言,只希望在朋友圈子裡和胡續冬先生開一玩笑,並無其他功利想法。
幾年前朋友胡續冬(有時也署名胡旭東、旭東)先生赴拉美講學,在其即將回國時,我杜撰了他大膽拜訪馬爾克斯並機智地為我的自印小說集《軍功》(即本次出版的《武皇的汗血寶馬》之前身)求得一序言。杜撰這一序言的目的,是為了在朋友圈子裡和胡續冬開個玩笑,讓他從拉美回國時產生一種驚愕感、魔幻感。而他回國后也確實莫名了幾天,並很快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我也有被虛構的一天》,以其胡氏幽默的筆調,將此事在2005年初的《新京報》上作了說明。
《軍功》這本自印小說集印數不多,我也只在朋友圈子裡發放。每有朋友來問及此事時,我都實言相告。其間,分別有台灣和成都的出版機構,因為看中了這篇序言,想出版《軍功》,我對他們都實言相告,也就失去了這兩次可能的出版機會。
此次蒙新世界出版社“小說前沿文庫”之青目,能得以正式出版,我高興之餘,也將序言一事實言相告。此次出版的小說集《武皇的汗血寶馬》里並沒有收錄那篇杜撰的“馬爾克斯序言”。
我本人沒想到的是,朋友圈子外的某些讀者朋友,也看到了這本《軍功》及其序言。這一序言給某些讀者帶來了一些疑問和困擾,對此,我感到抱歉。
向祚鐵 2010-10-17
-------------------------------------
我也有被虛構的一天
胡續冬
還在我回國之前,就不斷收到國內一些記者的來信,央我為他們的報紙“再度採訪”世界頂級大師加西亞-馬爾克斯。我堅信這些記者一定是喝多了或者是被版面逼瘋了,因為我那時作為一個身在巴西的無名之卒,怎麼可能見到一個秘密穿梭於墨西哥城、洛杉磯和馬德里之間的哥倫比亞重病老人?而且還是“再度採訪”?我乾脆沒有理會這些在我看來神智錯亂的央求。沒想到,回國之後,我又數次在飯局上聽到有人提起我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之間的某種關聯,看大家說起此事的那種毋需說明前後語境的自然而然的神情,仿似我和馬爾克斯之間真的有什麼事情而且已經成了朋友圈裡的一個眾所周知的典故了。
我越是犯暈,朋友們就越是以為我在賣關子、裝糊塗。我終於忍不住揪住了一個敘事能力高超的哥們讓他幫我解開這團無辜的迷霧,這哥們撂給我了一位向姓青年少數民族摯友去年出的一本自印的小說集,叫我自己回去看。
該向姓土家族摯友是一直為我所激賞的短篇小說高手高手高高手,生於湘西,為人猥瑣而詭秘,為文則高妙而奇譎,後來雖投身商海、銜拜某總,但本著“漢土一家親”、關注土家族精神文明建設的原則,我還是一直鼓勵他在商務洗浴、泡腳之餘繼續從事小說寫作,看到他將自己十年來的文字以《軍功》的書名結集付梓,雖然裝幀略顯猥褻,但我仍感到由衷的欣慰,仿似看到了……
《鬼斧集》 28萬字
楊典的“癖性寫作”
向祚鐵

小說前沿文庫
但是,讀完《鬼斧集》后,不難看出,上述看法是不成立的。在看似蕪雜的背後,整個集子其實有著統一的文學內核,我想稱之為狷介士人的“癖性寫作”。
在這裡,我想指出兩個細節。其一,在前面的幾篇作品中,常有某年月日寫於廣州某閣樓、北京半壁街斗室等落款;後面的好幾篇作品,在作品主標題下面,總有一行核心內容說明式的文字,如:殺王記(丑王蚩尤的百科全書生涯及其毀滅)、菊瓣兒(某中世紀劊子手秘密日記)等。對於楊典來說,斗室、閣樓、百科全書生涯、秘密日記等有著特別趣味的字眼,似乎已內化為其重要的寫作動力。其二,在《今天》雜誌上,我看到過楊典回憶他舅舅的一篇作品,風格比較“賢良方正”,此次,在《鬼斧集》里沒有收錄,這可以看出,《鬼斧集》的編選,有著內在統一的美學標準。
在楊典這裡,癖性寫作是一種修辭性的寫作策略呢?還是一種內在的本能性選擇?從《鬼斧集》里的作品尤其是“我的少年簡史”這部自傳性作品中,大體可以看到,“我”生來就有血熱的異常之處(生理上的根)。童年趕上了文革的后四年,而生長地重慶又是文革武鬥最為火爆的城市(本人也在重慶呆過,重慶有股狠勁,它的犬牙畢露至今讓我震驚);文革這個“時”和重慶這個“空”,兩者結合發生了特異的化學作用,可能將某種文化心理上的根植入到了“我”的體內。而進入青春期的“我”,則和單身離異的父親來到海量文化的北京,一個沉溺於音樂藝術的單身父親,無疑會更進一步促進“我”的放任無羈,再加上中國古典文化的深沉誘惑,“我”的狷介癖性的形成也就不足為奇了。
《地方性知識》36萬字
湯錯在哪裡?
書評人:戴濰娜
在牛津上學的時候導師叫Elizabeth Frazer,她有一個乖張的怪癖,從來不屑於閱讀1930年以後的文本,她總是說現代語言是對不住人類曾擁有過的高潔歷史的。在閱讀這部《地方性知識》時,我不止一次地惡作劇地想象把這本書捧到古怪的老教授面前,唬她說是19世紀的古本,然後在逃過她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后大大竊以為樂得意上一宿。《地方性知識》是一部高貴的,潔身自好的文本,絕無這個庸碌時代那些可以嘲笑的印跡。那些文字散發出的溫度、氣息、容量更像馬可波羅時代充滿好奇和勇敢的探險家拾得的一部優雅札記,處處流溢出無限迷人的縱深的空間。可我們要是用“懷舊氣質”來理解這部“人類學小說”的開山之作就大為幼稚了。整個閱讀過程像一場奇妙的盜墓,若能抵住開始的異界氣息,就能順著作者安置的各類秘道,看到真正吸引人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驚艷與奇迹。這並不是一部普通的湯錯地方志,也不是一本所謂的札記,而竟然是一部“小說”,用作者的話說“是在探賾虛構的底限”,而人類學方誌的體例和小說的內核又讓文本屬性難辨雌雄,“波粒二象性”實為很確鑿的隱喻。我們隱隱約約看到,作者扛起了大旗,向“認識貧困”的現代小說發起了一場政變。這就是我認為這是一本充滿“冒犯”的書了的緣故――作者顯然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博通天文、地理、植物學、動物學、歷史、民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文本當中,作者對超文本和文體泛化進行了實驗。這樣挑戰體例睥睨同行的功力到底怎麼可能被一個現代人獲得?這是我逐漸迷陷進湯錯以後心頭盤旋的一個越來越迫切的疑竇。我不禁抄錄那些文字,想象著一個年輕的修行聖行的乾淨的人,白衫白袍、長發逸動,他把真理像春天採擷來的葉子一樣,一葉一葉地賞玩排列,所有的塵俗舊律――它們都瞬間成了活物,讓1540年的玫瑰變成復活了的語言種子。
書的後記里作者提到了“對枯燥的關愛”,我是不分青紅皂白抄起來先讀後記的人,讀到了這句話,我基本上是帶著敬畏的心理翻看了第一章的,因為害怕這是部太過嚴肅的著作,我對地方志又從來沒有充沛的腎上腺素。可那汪洋般的詩性空間很快淹沒了渺小的個體,令人無法拒。我越來越感覺到,這或許並不是先前我想象中納悶嚴肅的一部書,作者時刻在挑追你的智力和理解力;這卻是一部叫人不得不嚴肅對待的作品。
繼續讀下去,讀到卷二的“語言”部分,“對於語言學者而言,這樣一種方言的存在就好比植物學家或昆蟲學家發現了自然界的一個新物種。”我開始對那些又臟又粗又俗又野卻異常生鮮活潑的語言混身來勁,這才覺得世上根本沒有所謂的“枯燥”的選材,瞧這些八輩子聽不著的新方話,湯錯語,曉錦話,真真是咕碌碌噴噴香的一鍋粥啊!更厲害的是那些髒話,作者稱它們是“眾多文字公民當中的一員。”第一次讀到這樣精細地解釋一門方言里每一個髒話的文章,讀得簡直大快人心。那些直接用方言寫成的段落讀得人心肺酣暢,那是沒有被閹割過的語言,跳動著最原始的生命力,通天接地氣。
行進到卷三風俗研究時,已經進入了狼吞虎咽的小說式的閱讀,作者顯然已經主宰了閱讀者的閱讀趣味。“冥都銀行”、“倒路鬼”、“虹”、“朝門”,這些風俗故事個個引人入勝,一方面讀者可以搬去飯桌上叫賣自己的博學,另一方面無疑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閱讀。而每個人心底被遺忘的對“村莊”的嚮往之情被日漸擦亮,這種種植在集體記憶里的原始的嚮往到卷四愈加彰顯。而讀者的閱讀與文本寫作的關係也變成樹纏藤,藤纏樹。“世界上如果有一本書能夠像藤蔓一樣繁複而又有極負責任的規律,那一定是一本美妙的著作……藤是一種即繁複又有理由簡潔的文本。”極繁複,又極簡潔,這大概是霍香結文字的魔性,可以讓他講敘的任何事物熠熠生輝,關於蜜蜂的那些章節極其惹人愛憐,而《地方性知識》並非僅有這些細緻深刻的觀察記錄,她凝結了作者多年來的思考和積累,處處可見先知般的箴言和詩人即時逮到的那些個閃爍的靈感。這些靈感和沉思,它們是那麼的通透和深遠,令每一個有幸第一次就讀到它們全部的人們深感幸福。
當眼睛一路漂流到卷五往後,等待的就是都是驚艷與撼動心魄。我個人非常熱愛“族譜上的河”裡面“公羊傳”的故事。全卷讀罷又將這一則抽出來反覆摩挲了好幾遍。整個故事溢滿了清澈又詭艷的詩性和巫道,叫人慾罷不能,一遍遍急切的回想。充滿著巨大的缺口,這個故事值得終身懷念。
書的後半部分,文本和作者徹底融為一體,也到了真正考驗讀者智力和分辨力的時刻,那種高階智力的互動交流感時時存在,眼花繚亂之際也正是明凈的神性現身的時刻。而在其中,每一個文本的參與者會獲得一版自己的完整,像一個高智群體里的說謊者遊戲。那作者心目中原初的意圖又為何樣呢,也許回過頭再讀一讀那些個“齉天”,你會會心一笑。語言都跑到哪裡去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湯錯又在哪裡?作者笑而不答,他只是野心勃勃當了一回言語世界的“朕”,像書的最後一句:
“你們都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