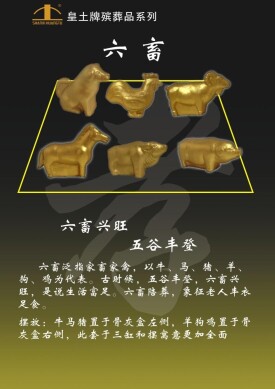六畜
漢語詞語典故
六畜,泛指家畜。《周禮·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預注曰:“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南宋王應麟編寫的《三字經》中也有:“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百家姓》《千字文》同為舊時童蒙必讀識字課本,因此“六畜”一詞可謂婦孺皆知。

牛羊

六畜---狗
六畜中的馬牛羊為食草動物。馬是古代戰爭和交通的重要工具,又是肉食品重要來源之一;屬於戰略物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歷來為人們所高度重視。秦朝頒布《廄苑律》“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枷)”,意思是盜馬的人處死,盜牛的人判枷刑,牛在牛耕時代擔負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是人們生產勞動中不可或缺的好幫手,理應受到尊重;羊性格溫順,在古代象徵著吉祥如意,人們在祭祀祖先的時候,羊又是第一祭品,羊更有“跪乳之恩”而受人尊敬。雞犬豬為雜食動物。在人們的現象中,豬往往和懶惰、愚笨聯繫在一起,除了吃和睡,似乎整天無所事事,僅有“庖廚之用”。其實豬是人類非常重要肉食品來源,其嗅覺靈敏,一些地方安保上已開發利用;雞在農業時代的家庭經濟中,起到拾遺的作用,雄雞能司晨報曉,各有其重要性;狗是人類馴化飼養的最早家畜之一。狗能幫助古人狩獵,是看家護院的好幫手。狗(犬)忠於職守,是其優點。其缺點是有點招惹是非,給人有點壞印象,如成語中有:狼心狗肺,狗急跳牆,狗仗人勢……等貶義詞。
六畜取長補短,為我們大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它們全都選入十二生肖中,其他六位是鼠、虎、兔、龍、蛇和猴,後者有的虛無縹緲,有的是動物世界里的精英,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也有的與人相安無事,更有的卻危害四方。實事求是地評價,還是六畜好,世世代代與人和平相處,已是人們生產生活的好伴侶。
動物的種類成千上萬,惟有六畜和人的關係最為密切,它們的品種優化,有的一專多能,這都是人類的傑作;人類的社會進步,又離不開六畜的無私奉獻,相輔相成,都在爭取達到更新,更高的境界。
六畜在傳統文化中一般泛指家畜,除了馬、牛、羊、豬、狗、雞六種家畜外,還包括駱駝、驢、鴨、鵝等家畜家禽。馬、牛、羊多見於青銅時代文化遺址,與游牧生活方式有關;豬、狗、雞常見於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與定居農業生產方式相關。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漸齊備,表明東方定居農業文化與西來游牧文化的混合。馬是游牧文化的標誌,從青銅時代開始成為顯貴的家畜;豬是東亞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農業文化的象徵。六畜概念始見於春秋戰國時代文獻,豬和馬的相對重要性意味著定居農業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長。六畜在傳統中有豐富的文化內含。“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是人們最美好的願望之一。
《周禮·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鄭玄注曰:“六畜,六性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後來牲畜或畜牲聯用,泛指家畜。《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預注曰:“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宋王應麟《三字經》:“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從此六畜家喻戶曉。
關於六畜起源動物考古學家和農史學者進行了初步研究。周本雄研究了一些重要遺址的動物骨骼認為磁山文化時代己馴化了狗、豬、雞;仰韶文化遺址出土有牛骨、羊骨、馬骨,馬、牛、羊在龍山文化時代出現的家畜,馬可能還要更晚一些。陳文華系統收集了考古文物中六畜資料認為豬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佔有最重要的地位,為六畜之首;商周時期畜牧業特別發達,馬已成為六畜之首。《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業歷史卷》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將野豬馴化為家豬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養雞的國家;犬又名狗是中國最早馴養的家畜;馬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役畜之一,被奉為六畜之首,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馬的國家之一;牛是中國最早馴養的動物之一,包括黃牛、水牛、氂牛三大類;羊也是中國最早馴化的動物之一,包括綿羊和山羊,中國是家羊起源地之一。這代表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農史學界對六畜起源的基本看法:豬、狗、雞是中國最早馴化的,馬、牛、羊也不是外來的。
進入二十一世紀袁靖系統考察了新石器時代中國人獲取動物資源的手段和方式。他們重點研究了豬和馬的馴化或來源問題:豬是東亞新石器時代最主要的家畜,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本土馴化的;確鑿無疑的家馬見於青銅時代,很可能是外來的。
六畜的起源或分佈並不局限於中國,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動物考古學、馴化地理學、動物遺傳學、民族動物學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進展。DNA研究揭示了動物馴化的複雜性,中國學者亦加入了這股研究潮流。張亞平等對狗、豬、驢等進行了分子遺傳學研究,認為豬、狗是東亞本土馴化的,驢肯定來自中亞、西亞或埃及。
每一種動物的馴化過程都很複雜,具體的時間和地點還難已確定。大體而言犬和豬的馴化在東亞和西亞均可追溯到近萬年,牛和羊西亞早於東亞,雞則東亞更早,馬的最早馴化地是中亞。
古文獻中有關六畜傳說不少,現摘錄幾則如下:
《周易·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
清代呂撫輯、蔡東藩補輯《歷代興衰演義》(二十四史通俗演義)記:“卻說太昊伏羲氏,成紀人也。……身長一丈六尺,首若蛇形。生有聖德,人民感戴,推之為君。……帝居位,上合天心,下合人望。共工、柏皇、朱襄、昊英等諸文武大臣,各秉賢能,分理宇內,而政大治,教民作網罟,捕魚蝦,以瞻民用。又教民養馬、牛、羊、雞、犬、豕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為犧牲……”
地方和民間也有不少六畜馴化傳說:
如甘肅省隴東南地區的禮縣一帶(據一九九九年版《禮縣誌》記載,禮縣在夏朝後商、周時名西犬丘),有本歷代謄抄保存下來的《太上慈悲香山寶卷》(以下簡稱《寶卷》),記載有“太白金星渡雞”等六畜馴化傳說:“由雷公、華胥、伏羲和女媧做出了這一開天闢地的第一次人類的和諧,後來就有了他們的後代妙庄王家族,《寶卷》說,牛郎原名大椿,他因渡牛有功,被妙庄王外孫女看中,婚配與他。神話中的牛魔王大仙也就是牛王神。在西犬丘國興盛時期把野牛渡化為家牛的人,所以稱他為牛王神,牛王爺。在媳婦溝有媳婦崖景觀,上原有仙女石像,現已被人盜走。在媳婦溝口,梁坪村頭,那棵傳說中為大椿和仙女做媒的大槐樹還在,這棵槐樹直徑3米左右。玉連渡馬,太白金星渡雞,二郎神楊傑渡狗,竹林渡豬等。……”
在甘肅天水西山坪大地灣一期文化中,發現距今8000年左右的家雞遺存,養雞在我國已經有8000年的歷史。依《寶卷》說,早在伏羲女媧時代,居住在秦嶺太白山一帶的太白族人,救助了人文先祖伏羲、女媧及其族人,後來伏羲“教民養六畜以充庖廚,備為犧牲”,而在這個過程中,太白族人在將雞馴化為家畜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來經過歷代傳頌,太白族人便被神化為“太白金星”的形象。
家馬(Equus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佈於歐亞草原的西端。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文化遺址中大量馬骨的出土顯示了從野馬到家馬的馴化過程。騎馬和馬車技術可能源於西亞的騎驢和牛車製作技術。波台(Botai)位於哈薩克草原北部,是一處特殊的銅石並用時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遺址,出土動物骨骼三十餘萬塊,其中99.9%是馬骨。安東尼等研究表明,這些馬主要是用於食用、祭祀(隨葬)和騎乘,至少部分是家馬。列文認為乘騎必然會導致馬脊椎特別是第13-15腰椎變形。她檢測了波台遺址出土的41個樣本,卻沒有發現相應的變化;由此推斷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獵採集者,以狩獵野馬為主,也許兼營小規模的農業。
在東亞多處經科學發掘的遺址中有馬齒或馬骨出土,是否為家馬存在爭議,確鑿無疑的家馬和馬車見於商代。中原地區土地肥沃,人口密集,也適合養馬,但更適合養豬、牛、雞、鴨等經濟效益高,成本低的家畜。因此沒有選擇養馬之路,而是採用從西方或北方購買方式成本更低,因此中原文化遺址中多見馬具而少見馬骨。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古代遺址很少發現馬骨,但出土了不少馬具,表明歷史上騎兵在各個國家曾起過重要作用。
許多研究表明,中國古代馬的母系遺傳呈現高度多樣性,既有本地馴化,也有外來基因交流。我國養馬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有馬骨。但也有不同觀點。關於中國家馬何時何地起源有幾種不同看法:一是認為馬、馬車等從遙遠的西方傳入;二是認為至遲在新石器時代(公元前9000-6000年),中國人已馴服馬和養馬;三是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末的龍山文化中出現了已家畜化的馬"或"在中國養馬、馴馬和用馬的歷史,至遲可以追溯到龍山文化時期"。
馬的馴化確實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CarlesVila等對來自10個不同時代和地方的191匹馬的mtDNA進行了研究,展示了豐富的遺傳多樣性,支持家馬是多地區或多次馴化的假說。但是Y染色體非編碼區14.3kb序列分析沒有發現任何多態位點,這可能是由於僅有極少數的雄性種馬參與繁育有關。普氏野馬(EquusPrzewalskii)與家馬染色體數目不同。儘管家馬的野先祖先有豐富的遺傳多樣性,分子遺傳學研究亦將普氏野馬排除在家馬的祖先之外。
內蒙古赤峰地區大山前和井溝子遺址青銅時代9匹家馬mtDNA與東亞、中亞、近東、歐洲等地家馬的mtDNA序列進行系統發育網路分析顯示9匹古馬並沒有聚集在一個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佈傾向的現代家馬聚簇中,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家馬起源的複雜性。
此外家驢亦來自中亞或西亞,其源頭在非洲。通過對12個品種126頭本土驢的mtDNA分析表明中國家驢可分成兩系,稱之為Somali系和Nubian系,均來自非洲。
馬車(Chariot)此處特指青銅時代流行於歐亞大陸的一種有輻兩輪輕快馬拉車,主要用於戰爭、狩獵、禮儀和比賽,也普遍用來陪葬。這類馬車在西亞(主要是安納托利亞和兩河流域)、中亞(主要是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和東亞(主要是商、周文化遺址)中均有出土,不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許多細節相同,充分表明它們有共同的起源,但也不排除存在獨立發明的可能。
安東尼等主張馬車起源於歐亞草原西端,主要根據是辛塔什塔-彼德羅夫卡(Sintashta-petrovka)墓葬中出土的14輛車,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100-1700年。李特爾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統地研究了車輛的起源和傳播,指出無輻車和有輻車均起源於西亞,然後分別傳入歐洲、非洲和亞洲的中亞、南亞和東亞。針對辛塔什塔-彼德羅夫卡出土的馬車李特爾等指出它們過於原始和簡陋,還不是真正的馬拉戰車。另外高加索地區出土了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紀的青銅馬車模型,支持馬車近東起源說。
從目前出土的早期馬車來看,東亞安陽馬車可能是最先進的:輪徑最大,軌距最寬,車廂最大,時代較晚。林已奈夫、夏含夷等明確主張東亞的馬車來源於西亞或中亞草原。最近王海成對馬車進行了細緻的系統考察,指出東亞不具備獨立發明馬車的基本條件,但也存在不同觀點。
牛羊是遊動的財富,是游牧民的衣食之源;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縱橫歐亞大陸的可能。牛、馬、羊是草原游牧業的基礎,與豬、狗、雞不同,牛馬羊均可擠奶,而奶或奶製品使游牧生活成為可能。游牧民族橫跨歐亞大草原具有軍事上的優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馬。“胡兒十歲能騎馬”,湯因比認為游牧民就是一種半人半馬怪。馬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或游牧民族的標誌。
一種觀點認為水牛可能起源於南亞,而黃牛很可能來自西亞,但也有爭議。從河姆渡到興隆溝,東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多為水牛骨骼,不止一種,是家養還是野生存在爭議;家養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紀從南亞引進的,中國南方的水牛犁耕技術很可能是受北方黃牛耕作技術影響所致。黃牛與綿羊、山羊生態習性相近,是新石器時代西亞、中亞的主要家畜,在東亞飼養量較少。到了青銅時代,黃牛在東亞大量出現,據今約4000年的甘肅大何庄遺址、秦魏家遺址齊家文化層中出土的黃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黃牛與山羊一樣經歷了大致相同的馴化和傳播過程。
黃牛亦可分為兩個亞種,Bostaurus很可能起源於西亞,Bosindicus起源於南亞。mtDNA研究表明東亞黃牛與歐洲、非洲黃牛非常接近,但與印度黃牛差別較大。更具體的研究顯示日本、韓國黃牛均屬於BosTaurus,可能來自西亞;而20%蒙古黃牛受到了印度黃牛的影響,可能發生在蒙古帝國時期;還發現了不見於西亞、非洲和歐洲黃牛的T4,可能來自Bosprimigenius。中國黃牛包括上述兩個亞種,南部以印度黃牛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類似於蒙古黃牛,包括T2、T3、T4。
另一項與游牧生活方式有關的技術是擠奶(Milking)。西亞和中亞農民新石器時代就已開始擠奶,東亞農民至今仍不習慣擠奶,這有生物學和文化上的原因。動物乳中含有豐富的(約5%)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賴於乳糖酶(Lastase)的參與。成人乳糖酶缺乏現象在東亞和東南亞高達85-100%,而北歐不到10%,其他地區介於兩者之間。就中國而言,成年人(14—66歲)中漢族92.3%、蒙古族87.9%、哈薩克族76.4%缺乏乳糖酶。人類遺傳學研究表明乳糖酶的產生與乳糖酶基因(Lastasegene)有關,是基因點突變(Pointmutations)和重組(Recombination)的結果。人類以牛奶為食可以有選擇性地引起人與牛的基因改變,稱之為基因文化共同進化。有圖像證據表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西亞已經開始擠奶。擠奶或奶業(dairying)是謝拉特提出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的重要內容,亦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關鍵。東亞擠奶活動的出現與羊、牛、馬的出現大體同步。哈薩克、蒙古、漢族中成年人體內產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與印歐人的親緣關係或接觸與交流程度相應減少。東亞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對農業的依賴較為迫切。另一方面東亞農民並不喜歡畜奶和奶製品,容易鄙視或不重視畜牧業的發展。在歐洲種植業和畜牧業的結合異常緊密,在東亞卻出現了明顯的分野。乳糖酶的有無不僅是中國與歐洲飲食方式差異的原因之一,而且影響了歐亞大陸歷史的進程。
山羊和綿羊骨骼經常同時出現在西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位於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的扎格羅斯(Zagros)山脈及其附近地區可能是山羊和綿羊的最早馴化地。最近對扎格羅斯山脈南端的甘茲·達列赫(GanjDareh)和阿里·庫什(Ali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進行了重新研究,進一步確證西亞大約在一萬年前已經放養山羊了。
東亞養羊與西亞相比稍晚出現。數百處經科學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大約有五十處出土過羊骨或陶羊頭。早前新石器時代遺存中都沒有羊的骨骸。西安半坡的“綿羊”標本很少,不能確定是家羊;河姆渡出土的陶羊頭可能表現羚羊,蘇門羚(Capricornis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遺址出土的61種動物中唯一的羊亞科動物。青銅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綿羊骨骼確定是家羊。這說明羊在東亞新石器時代混合農業經濟中所佔比重不大。進入青銅時代后,從新疆到中原羊的數量明顯增多。在齊家文化和殷墟遺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銅時代人們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顯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養羊為業;周代中原養羊亦蔚然成風。《詩·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山羊和綿羊的馴化不僅是考古學亦是分子遺傳學研究的難題。山羊和綿羊是不同的物種,在馴化的初期就表現出明顯的多樣性,都是由至少兩個亞種分別馴化而來。歐洲,非洲,南亞和中亞的綿羊和山羊可能來源於西亞。根據mtNDA山羊可分為四系,A系很可能源於西亞,B系源於巴基斯坦;A、B兩系佔主流;C、D兩系罕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寮國山羊都表現出了豐富的遺傳多樣性。通過對13個品種183隻山羊完整mtDNAD-loop研究表明中國山羊亦可分為四系,A系佔主流,B系次之,C、D兩系僅見於西藏。有人在B系中發現了一個東亞特色的分支,並由此推斷中國西南地區亦可能是B系山羊的起源地之一。韓國養羊已有2000餘年的歷史,山羊具有相對單純的遺傳特性,均屬於A系。
現在世界上的綿羊品種多達1400餘個,Y染色體研究表明至少可分為兩個不同的亞種。mtDNA研究發現西亞綿羊可分為三個亞種,其具體馴化過程比以前想象的還要複雜。這三個亞種的綿羊在中國均有分佈,通過對東亞13個地區19個品種449隻“本土”綿羊的mtDNA研究沒有發現獨特的遺傳標誌,支持東亞綿羊像歐洲綿羊一樣來自中亞或西亞。東北亞地區是東胡或東夷故地,“無羊少馬”。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養羊業一直不發達。沒有發現東亞綿羊與歐洲綿羊有明顯不同,西亞及其附近地區如巴基斯坦被公認為山羊或綿羊的原始馴化地或次級馴化中心。也有人在中國綿羊中發現了新的母系基因,並提出中國綿羊起源的新看法。二里頭遺址綿羊骨骼mtDNA分析表明與小尾寒羊、湖羊、蒙古羊、同羊相同,均屬於A系;盤羊、羱羊並不是中國藏系綿羊和蒙古系綿羊的祖先。分子遺傳學亦不支持東亞特別是中原、東北亞作為山羊或綿羊的起源地。但也仍存在爭議。
新石器時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銅時代羊毛日顯重要。進入青銅時代之後,西亞一些遺址中的紡輪逐漸增多,剝皮工具卻有所減少;山羊和綿羊的比例亦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意味著羊毛逐漸成了重要紡織或編織原料。大約公元前1000年西亞發明了鐵制羊毛剪,加速了對羊毛的開發利用。巴比倫帝國羊毛、穀物、油並立為三大物產;古希臘亦以綿羊、油橄欖、小麥為主要產品。羊是財富的象徵,羊毛被稱之為軟黃金;金羊毛故事廣為流傳。東亞較早利用羊毛製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銅時代毛製品,與中亞毛紡織傳統一脈相承,特別是其中的斜紋織物(Twill)至今在歐洲流行。中國以絲綢和布衣著稱,羊毛衫、毛褲到二十世紀才普及。
養豬是東亞定居農業生活的傳統,無“豕”不成“家”。南起甑皮岩北到興隆窪,西自仰韶東到龍山,東亞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遺址中幾乎均有豬骨出土。用豬或豬下頜骨陪葬不僅具有宗教意義,亦是財富和政治權威的象徵,說明豬在東亞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均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豬骨和玉器一樣是東亞新石器時代最寶貴的陪葬物品,紅山文化玉豬龍和凌家灘文化玉豬合二為一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這種格局到青銅時代才改變:青銅禮器和馬分別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豬的地位。
野豬(Susscrofa)與粟一樣廣泛分佈於歐亞大陸及其附近島嶼,遺傳學研究表明歐洲和東亞家豬有明顯的不同,分別起源於西亞和東亞,歐洲和南亞亦可能是家豬的起源地之一。西亞是公認的家豬起源地。東亞家豬源於東亞野豬,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還難以確定。通過來自中國、東南亞、印度的567隻家豬和155隻野豬的mtDNA研究表明東亞家豬和野家可追溯到同一世系D,其中包含多個支系D2、D3、D4、D1b和D1a2;根據系統發育地理圖可推斷湄公河流域是馴化中心,然後分別向西北和東北方向分佈。
桂林甑皮岩遺址出土的豬骨骼有爭議。李有恆等認為不太可能是狩獵的結果。野豬也是可以牧養的,甑皮岩的豬可能是馴化初期的豬。興隆窪人豬合葬意味深長,野豬特徵明顯,可能也是正在馴化中的動物。新石器時代人類陪葬或祭祀一般用家畜,絕少用野獸。跨湖橋遺址出土動物骨骼部分被確認為是家豬,也是中國最早的家豬實例之一。大約八千年前磁山文化遺址出土的豬骨可以確定是家豬。日本和朝鮮半島亦有野豬分佈,與家豬親緣關係密切。考古發現和歷史記載均表明東亞諸民族具有養豬的傳統。
狗被認為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是人類天生的朋友。家狗源於野狼已經得到公認,但馴化的時間和地點仍在爭論推測中。Savolainen和張衛平等通過對世界範圍內654隻家狗的mtDNA研究發現其中95%可歸為三群,而東亞狗表現出更大的遺傳多樣性;由此推斷家狗源於大約15000年的東亞。作為旁證有人發現新大陸和澳洲的狗源於東亞或舊大陸。另外一群科學家用類似的方法發現犬與東南歐狼有親緣關係,並且推斷至少歐洲犬起源於歐洲狼;有12000-17000年的化石作為證明,支持犬狗的多地區獨立起源說。通過來自歐洲、西南亞、西伯利亞、東亞、非洲和美洲的10隻公狗Y染色體研究表明世界上的犬源於至少五個不同的狼群。狗有豐富的遺傳多樣性,分佈異常廣泛,還可以和狼回交,不大可能起源於一時一地。青銅時代以來歐亞大陸中、西部的犬跟隨印歐人進入了東亞,因此現代東亞犬或狗表現出更豐富的遺傳多樣性。
河北省徐水縣南庄頭、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鄭裴李崗、舞陽賈湖,浙江省餘姚河姆渡,陝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過狗的骨骼或陶狗。舞陽賈湖已有龜、犬陪葬,大汶口、龍山文化中犬與龜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太平洋沿岸地區流行龜祭和犬祭風俗。
在東西方文化或游牧與農耕民族文化中犬或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義。語言學研究亦可得出類似的結論,犬是印歐語和阿爾泰語中對狗的稱呼。農耕與游牧民族對狗或犬的態度明顯不同:直到現代狗仍然是部分日本、韓國和中國人的肉食來源之一,這在游牧民族或印歐人看來無異於吃人肉。
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養雞的國家。江西萬年仙人洞和陝西半坡遺址中發現了原雞的遺骨,說明原雞在長江和黃河流域都有分佈。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鄭裴李崗、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等有雞骨出土,可能是家雞,是目前世界最早記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常有雞骨或陶雞出土,雞可能是唯一家禽。甲骨文有雞字,為“鳥”旁加“奚”的形聲字;殷墟發現有作為犧牲的雞骨架,雞為六畜之一。
家雞(Gallusdomesticus)源於紅原雞(Gallusgullus)。紅原雞分佈於中國、印度、緬甸、菲律賓等國家。達爾文提出家雞是由紅原雞馴化而來,這已被線粒體DNA研究證實。一般認為西亞或西方家雞源於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2500-2100B.C.)。印度和中國不約而同地馴養雞是可能的。
2004年多國科學家公布了紅原雞基因組圖譜:雞的基因組規模相對較小,相當於人類的1/3;基因總數卻相近,為2-2.3萬個,有60%的基因相同。將紅原雞與肉雞、蛋雞和中國烏雞的基因組對比發現家雞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嚴重地近親繁殖,有較大的遺傳多樣性。
豬、狗、雞和人一樣是雜食動物,特別容易和人類建立親密關係。它們的馴化與人類的自我馴化大體同步,也就是說人類在馴化它們的過程中完成了自我馴化。有了這些畜禽人類才逐漸放棄狩獵採集,進入生產經濟時代。雞為“五德之禽”。《韓詩外傳》雲雞頭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敵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類,是仁德;守夜報曉,是信德。東亞民間將雞視為吉祥物,可以避邪除害。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雞犬之聲相聞”,沒有雞狗難成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雞、狗和人的關係異常密切。孟子的治國方略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雞豕狗彘”或“雞狗豬彘”與東亞定居農業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人類在馴養動物的同時也促進人類自身發展。人類與家養動物可以說是一種共生關係:人類在幫助動物生存的同時充分利用動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假如沒有家養動物,人類將長期處於史前或原始狀態。家養動物史實質上是人類文化史的縮影之一,中國家養動物的起源和發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文化的進程。六畜自古以來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人們希望年年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六畜已溶入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如中國傳統十二生肖中包含六畜。古人甚至把六畜定為過年的日期。如正月初一是雞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豬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馬日;初七是人日。六畜在中國傳統中已凝固成文化符號之一,深入人心。
東亞新石器時代,隨著農業和畜牧業的產生和發展,人類逐步進入了定居農業文化時代。畜牧業中的六畜逐步齊備和發展起來,特別是六畜中的豬、狗、羊、雞等率先發展起來,加上農業的發展,使人類逐步擺脫遊獵狀態實現定居,過上比較安定生活。新石器時代許多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豬、狗、羊、雞等遺存。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標誌著東亞新石器文化的頂峰。正是六畜中的豬、狗、羊、雞等養殖率先發展起來,讓人們過上了安逸生活。如傳說中美好的堯舜時期。豬可以說是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家畜,不僅是重要的肉食來源,在精神生活中亦佔有重要地位。如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有玉豬龍;凌家灘文化遺址出土有大型玉豬等。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漸齊備的時代,六畜開始得到了全面發展。六畜的功用也開始多樣化,從提供肉食來源,到成為人類勞作,運輸、戰爭等的幫手。特別是是六畜中的馬和牛,經過人們的馴化,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馬逐步發展成為戰爭、交通等的重要工具,受到高度重視。如周朝專門為馬設官職,配人員,負責馬的放牧、飼養、調教、乘御、保健、繁殖,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馬政制度。牛逐步發展成為運輸和農耕等的重要幫手。如《周易·繫辭下》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禮記·曲禮下》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又《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隨著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東亞社會複雜化;加上農業和六畜的持續發展,中國出現相對統一的中央王朝。黃帝金戈鐵馬,蚩尤銅頭鐵額,兩軍交戰,血流漂杵。炎黃之戰,干戈碎玉帛,象徵玉帛古國進入王國乃至帝國時代。商周時代牛、羊、馬常用用於祭祀活動。《禮記·王制》雲“大夫無故不殺羊”。
六畜在傳統文化中已深入生活方方面面。六畜冠名于姓氏、山河、人物等;歷代以六畜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更是浩若煙海。如歷代中文姓名中有六畜:牛、馬、羊,豬、雞、狗的數不勝數。姓氏大多形成於春秋戰國以後,《百家姓》中有馬、牛、羊,還有司馬,巫馬、羊舌、公羊等複姓。山河、人物、文學作品中以六畜冠名的更是不勝枚舉。
六畜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因其功用不同,重要性也隨著變化。如豬在新石器時代非常重要且神聖。夏、商、周青銅時代因勞作,戰爭需要,馬、牛顯得更重要。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進入帝國時代,隨著牛耕的發展,牛顯得更重要。漢民族圖騰龍最初包含豬形象,新石器時代沒有比豬更重要的家畜。中國西南僳僳、哈尼、珞巴等曾以豬為圖騰。葉舒憲認為豬崇拜可能是母神信仰的產物,紅山文化豬是家神即主管大自然的母神化身。
六畜隨著時代發展內含豐富多彩。商代早期偃師商城遺址祭祀區豬仍然是數量最多的犧牲,總共超過300頭;這是新石器時代用豬祭祀的延續。《豳風》為《詩經》十五國風之一,“豳”意為豬山。甲骨文、金文中有豕、彘等字。《辭源》中有“豕”部“家”、“豪”“奎”“象”等;“該”、“孩”、“駭”、“咳”等以“亥”為聲部。《莊子·大宗師》中狶韋氏是開闢大神。《山海經》中黃帝之孫顓頊之父韓流嘴巴象豬,腳似豬蹄。《山海經》:“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馬、牛、羊、雞、狗等記載則更多。
在不同時期,六畜發揮作用不同,崇尚也不同。戰國時期秦國變法以耕、戰為國策,尚武好戰文化佔上風,霸道盛行而王道衰微,崇尚馬。秦漢時代牛耕普及,農業生產上牛作用大,在戰場上馬作用大;崇尚牛、馬。春秋時晉大夫先轂號“彘子”,劉邦大將陳豨,漢武帝劉徹本名劉彘,左將軍荀彘;漢代以後名字中就很難見到豬的蹤影了。
《符子》曰:“朔人有獻燕昭王大豕者,車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今仗君之靈而化,始得為魯津之伯也。”唐朝豬龍已成貶稱,玄宗說安祿山“此豬龍,無能為”。宋代豬崇拜猶存。陳師道《后村談叢》雲宮中養豬厭勝避邪:“御廚不登彘肉。太祖嘗畜兩彘,謂之神豬。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妖術雲。”豬肉價格波動記載。如《東坡詩話》云:“黃州好豬肉,價賤等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水,小著火,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周密《癸辛雜識》云:“至元癸已十二月內,村落後間忽偽傳官司不許養豬,於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同地區,條件不同,飼養的家畜也不同。如游牧民常飼養馬和牛、羊、駱駝等;農耕地區常飼養豬、牛、雞、鴨等。吳承恩《西遊記》中“天蓬元帥”變“豬八戒”反映豬從神聖到世俗的過程。
馬是游牧民族的象徵,無“馬”不成族。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牛、羊、馬等在東亞,西北(河湟地區)、北方(蒙古草原)、東北(西遼河流域)得到快速發展,游牧民族逐步發展壯大。黃帝傳說與游牧有關。《列仙傳》和《古今醫統》雲黃帝時代馬師皇擅長醫馬,被認為是十大名醫之一。南北各地有馬神廟,大都祭祀馬師皇。游牧民族養馬的盛況從“白登之圍”可略見一斑。中原養馬與游牧文化傳播有關。
《竹書紀年》云:“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都於商邱。”《世本·作篇》亦云:“相土作乘馬,遷都於商邱。”殷墟車馬坑和人馬合葬墓的發現表明馬在商代非常重要。商代中期以後逐步演變為主要用牛、羊和馬進行祭祀。祭祀用動物的多樣化與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進程密切相關。《史記·殷本紀》云:“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太公六韜》亦云:“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千金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良馬來自西方,是商、周公認的珍寶,在周滅商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
周代養馬業已有較大發展。相傳西周已有《司馬法》管理養馬用馬事宜。《周禮·小司徒》鄭玄註:“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周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各國競相養馬,紛紛突破“邦國六閑四種”的規矩,變成千乘或萬乘之國。楚威王時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秦惠王時戰車萬乘,天下之雄國。秦國祖先非子養馬出身,又位於適合養馬的西北地區,戰車與騎兵遂成優勢,嬴政憑此統一中原建立秦帝國。
穆天子西遊,造父駕車,八駿奔騰。先秦時代有相馬出名的伯樂,《相馬經》已失傳,《齊民要術》可能保留了部分精華:“馬頭為王欲得方,耳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肋為城廓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馬八尺以上為龍。龍馬或天馬信仰源於先秦,盛行於漢唐。《周禮·夏官·庾人》:“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來,六尺以上為馬。”《華陽國志·蜀志》云:“(會無)縣有天馬祠,初民家馬牧山下,或產神駒,雲天馬子也。”漢武帝想藉助天馬升天。天馬來自中亞大宛,又以汗血馬著稱。《史記·樂書》載漢武帝時《天馬歌》列為郊祀之歌:“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馬踏飛燕是漢代藝術傑作,表現了天馬行空的境界。《後漢書·馬援傳》伏波將軍馬援是傑出的養馬家:“夫行天莫為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宋書·符瑞志》:“龍馬,仁馬也,河水之精。”河出馬書,洛出龜圖,河書洛圖是河洛文化的象徵。天龍地馬,龍馬並稱;真龍天子必有駿馬相隨。唐代是游牧與農耕文化交相輝映的朝代。昭陵六駿是唐太祖李世民的愛馬,都來是塞外。玄奘過龜茲見一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恢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白馬馱經廣為流傳,洛陽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根據地。《司牧安驥集》是中國現存最古的獸醫專著,《元亨療馬集》集中獸醫之大成,均以馬、牛為主要醫治對象,亦從側面表明馬曾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家畜。
時代不同、發揮不同,重要性不同。何為六畜之首曾出現過有趣的爭鳴。一些人認為馬為六畜之首理所當然,而另外有人認為六畜之首是豬。中國是第一養豬大國,豬肉一直是主要肉食來源。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是中國的經濟重心和政治文化中心,土地肥沃,人口密集,也適合養馬,但更適合養豬、雞、鴨、牛等經濟效益高,成本低的家畜,因此沒有選擇養馬之路,而是採用從西方或北方購買方式以降低成本,是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的,是明智之舉。如果也象北方和西部一樣片面發展養馬,不可能發展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和政治文化中心。
人類社會的發展,反過來影響家畜的發展。以飼養馬牛羊為主的游牧文化和以飼養豬、牛、雞、鴨為主的定居農業文化,各有其優勢。只有充分發揮優勢,同時不斷學習人類先進文化經驗,才能更好促進國家發展,促進文化發展。《荀子·王制》:“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是中國人的美好願望之一,亦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中國傳統文化內含豐富,涉及面非常廣泛,需要不斷加以研究,才能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