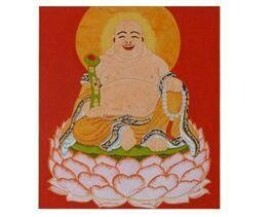九僧
九僧
九僧,中國宋代初期詩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宇昭、懷古、惠崇等九人的並稱。當時西昆體盛行,九僧不滿西昆體的浮艷詩風崇奉晚唐賈島、姚合一派,互相唱和,作品多寫隱逸閑趣及林下生活,風格清奇雅靜。其中惠崇不但能詩,畫亦有名,世稱“惠崇小景”。原有《九僧詩集》,久已不傳。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九僧選句圖》一卷。所作見《宋高僧詩選》及《瀛奎律髓》。
宋初詩壇,先後風靡著三個詩歌流派,即“元白體”、“晚唐體”、“西昆體”,這是文學史家的共識。宋末元初人方回編《瀛奎律髓》,其卷四七收“宋初九僧”之一文兆《宿西山精舍》請,評曰:“有宋國初,未遠唐也。凡此九人詩,皆學賈島、周賀,清苦工密。所謂景聯,人人著意,但不及賈之高、周之富耳。”(見《瀛奎律髓匯評》。以下凡引《律髓》詩評,俱見此書,不另注出。)明都穆《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曰:“宋初譚用之、胡宿、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絕尚多唐調。”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亦持此說。清《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批點《律髓》,不同意方回所謂“九僧”學賈島、周賀的說法,以為“‘九僧’詩源出中唐,乃‘十子’之餘響”。然其在《四庫全書總目·南陽集提要》中又似乎糾正了自己的觀點,同意方回的論斷:“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chàn@①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迫真。”“九僧”詩源出何人,姑且不論,事實上也不可能指定其宗主;但上述論者有一點是共同的,也是正確的,那就是“九僧詩”乃“唐韻”,具體地說是“晚唐體”。
關於“宋初九僧”,從數十年來眾多的文學史著作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們的名字,學術界也極少討論。直到近年出版的幾種文學史(如程千帆等主編的《兩宋文學史》、章培恆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才有所論列,但限於體制和篇幅,又都很簡略。“九僧”作為宋初“晚唐體”的代表作家群,不少人當時有詩集傳世,又編有詩歌總集,且有“句圖”之類,影響不小。尚不止此。宋末江湖詩派的“永嘉四靈”,遠繼“九僧”衣體,在兩宋文學史上首尾呼應,頗為奇特。因此,對“宋初九僧”及其詩歌創作,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現擬從基本史料入手,進行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九僧”何許人也?司馬光《溫公續詩話》曰:“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司馬光舉出了每人的籍貫,知有三位(希晝、惟鳳、懷古)是西蜀人,其餘六位,簡長是北方人(沃州為今河北趙縣),文兆是今福建(“南越”指閩)人,另四位則占籍今江、浙、皖,而“江南”(或作“江東”)、“淮南”地域甚廣,除“淮南”蓋指壽州(今安徽壽縣,詳后)外,“江南”(江南路,又分東、西二路)究指何地,尚不得而知。只有保暹,在元人吳師道《敬鄉錄》卷一四中有小傳,但也極簡單:“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今屬浙江)人,普惠院僧。喜為詩,有《處囊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據《宋詩紀事》卷九一引王隨《惟鳳詩序》,知惟鳳曾獲贈“持正大師”之號。由此可見,“九僧”各自南北東西,並不同貫,這個詩僧群體是“五湖四海”,沒有地域性。
九僧生卒年,已無法確考,只能從他們的交遊及唱和中,知與林逋、魏野、釋智圓等同時,主要活動於太宗至真宗朝,蓋出生於趙宋開國(公元960年)前後。宋祁嘗作《過惠崇舊居》詩,在“雖昧平生契,懷賢要可傷”句下自注道:“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宋景文集》卷一○。“二紀”據《佚存叢書》影殘宋本、四庫本作“二年”,按詩意當誤。)惠崇或謂淮南人,或謂楚人。所謂“淮南”、“楚”,當指壽春,《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引《楊文公談苑》“僧善書”條稱“壽春惠崇善王書”可證。壽春宋代為壽州屬縣。《瀛奎律髓》卷三載《過惠崇舊居》,方回考證道:“元注云:‘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景文年四十四,初得郡壽陽,惠崇舊居院在境內。選此一詩,以見惠崇之死,宋公年二十也。”今按宋祁知壽州在慶曆六年(1046),見《宋景文集》卷三七《謝表》題下原注,時年四十九歲,並非“初得郡”,方氏所考不確。以“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推算,惠崇應死於天聖元年(1023)。但詩人所謂“二紀”,是否即為二十四年確數,尚不得而知,故天聖元年未必即可斷為惠崇卒年,不過這已是“九僧”中卒年唯一可考的了。
“九僧”平生雲遊各地,蓋皆不長期住持一寺。從他們的詩作和別人的贈答中,知他們不僅籍貫相去遼遠,而且活動地域相當廣。希晝有《過巴峽》詩,說明他曾出入川蜀。保暹是金華人,作用《金陵懷古》、《途次望太行山》、《登蕪城古台》、《巴江秋夕》等詩,足跡竟北至太行,西過劍門。文兆也有《巴峽聞猿》。簡長是今河北人,而作有《晚次江陵》,則又到過今湖北。如此等等。釋智圓有《送惟鳳師歸四明》詩,雖是贈惟鳳一人,很能說明這群僧人的活動規律。他寫道:未識鳳師面,早熟鳳師名。毓靈本岷峨,弱冠游神京。出處忌非類,交結皆名卿。高談駭眾聽,雅唱歸群英。曩歲來浙陽,相逢水心亭(樂天水心亭,今水心寺是也)。
翌日倏分攜,南北各如萍。我尋住孤山,師亦往東明。人間一為別,天上七周星。江湖既相望,煦沫安足評。今年春之暮,草堂花飄零。睡起乍憑欄,竹外聞人聲。忽報鳳師至,屣履出相迎。借問胡為來,告我以其誠。度支司外計(轉輸方度支也),夕拜臨茲城(太守王給事也)。二賢俱我舊,故得尋其盟。夏來西湖西,為鄰樂幽貞。朝登隱君堂(林公逋也),暮即中庸扃(予之自號也)。倏忽時節移,秋風拂檐楹。趨裝俄告別,鄞江指歸程。(《閑居編》卷三八)惟鳳本來是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人,二十歲左右到京城開封,“交結皆名卿”,其後又到浙江一帶,因度支方某、給事中王某改官杭州,他也隨著到杭,從“春之暮”住到“秋鳳拂檐楹”才離去。現存“九僧”詩,有不少是贈答各級官僚的,可以看出他們這個群體的共同特點,即游無定處,“交結名卿”,以詩干謁官吏。
“九僧”既然各自東西南北,是怎樣聯繫在一起並成為一個詩歌流派的?或者說,“九僧”其名從何而得?這問題既複雜,也很簡單。簡單地說,那就是因為有《九僧詩集》。
《九僧詩集》乃纂輯前述九位詩僧的詩歌總集。歐陽修《六一詩話》曰:“國朝浮圖以詩鳴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歐陽修所謂“其集已亡”並不確,稍後司馬光曰:“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捨得之。……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溫公續詩話》)南宋間,《九僧詩集》流傳稍廣,目錄學家晁公武、陳振孫皆嘗著錄。《郡齋讀書志》卷二○記載道:《九僧詩集》一卷。右皇朝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陳充為序。凡一百十篇。……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詩可稱者甚多。《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曰:
《九僧詩》一卷,……凡一百七首。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對姚合“射鵰手”。九人惟惠崇有別集。歐公《詩話》乃雲其集已亡,惟記惠崇一人,今不復知有“九僧”者,未知何也。此外《宋史》卷二○九《藝文志八》也著錄“陳充《九僧詩集》一卷”。
景德元年為公元1004年,據前所考,其時惠崇尚在世,其他八僧,蓋亦無恙。按陳充(944-1013),字若虛,自號中庸子,益州成都(今四川成都)人。雍熙間進士甲科,累官至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出權西京留守御史台,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性曠達,有集二十卷。《宋史》卷四四一有傳。陳充蓋與“九僧”有密切交往,今只存其鄉人惟鳳《寄昭文館陳學士》詩,所謂“陳學士”即陳充。詩曰:“秋深荒外客,獨上望京台。遠信未封去,新鴻又見來。地寒邊樹短,天靜瘴雲開。無限心相向,南宮卧錦才。”他的另一鄉人希晝有《寄壽春使君陳學士》,“陳學士”疑亦是陳充。
晁、陳二氏所錄之本,都有陳充序,說明編者相同,但后本比前者少詩三首,不知何故。而南宋間周huī@②所見,似別是一本。《清波雜誌》卷一一曰:
huī@③昔傳《九僧詩》,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並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為節本。按《宋史·真宗紀二》,景德五年(1008)正月戊辰改元為大中祥符元年。所謂有“景德五年”張亢所作序引,蓋作於開年之初。張亢(994-1056),字公壽,臨濮(今山東鄄城西南)人。天禧三年進士,累遷徐州總管,韓琦《安陽集》卷四七有墓誌銘,《宋史》卷三二四有傳。陳充編集五年之後,張亢何以另作序引,所序之集與陳充本有何
上述《九僧詩集》已有兩本,而都只能是“九僧”詩的選本,因編集時“九僧”猶健在。“九僧”身後,蓋多有個人詩集傳世,並不如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說只惠崇一人有別集。前引《敬鄉錄》,保暹有《處囊訣》一卷,其書內容不詳,而《宋史》卷二○八《藝文志七》著錄有《僧保暹集》二卷。保暹猶有《天目集》盛行,釋智圓《贈詩僧保暹師》道:“……卓爾保暹師,生於宋天下。內明卜商道,外減騷人價。鑿彼淳粹源,清辭競流瀉。放意尚幽遠,立言忌妖蟲。旨哉《天目集》,四海爭傳寫。”(《閑居編》卷三九)至於惠崇集,南宋初人朱弁在其所著《風月堂詩話》中寫道:“宋子京(祁)以書托梵才大師編集其詩,則當有可傳者,而人或未之見,恐雖編集而未大行於世耳。”梵才編集,當在宋祁知壽州期間或稍後,時惠崇示寂已二十餘年。陳氏《解題》卷二○著錄“《惠崇詩》十卷”,然《宋志》又著錄“《僧惠崇詩》三卷”,不詳何本為梵才所編。其他人雖不見於著錄,恐也未必無集,《宋詩紀事》引簡長詩張景序、惟鳳詩王隨序,或有單行本。《通志》卷七○《藝文略八》著錄“《九僧選句圖》一卷”,當是摘錄“九僧”詩佳句,久佚,大約是從各集摘編。
南宋末年,杭州著名書商陳起編行《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其中“前集”即《九僧詩集》。清初,毛氏《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著錄“《九僧集》一本,影宋板精抄”。毛yǐ@④《九僧詩跋》稱該本“較之晁、陳二氏,皆多得詩二十餘首”(所得一百三十四首)。毛氏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毛氏影宋本收詩之所以比晁、陳所錄二本為多,蓋出於《增廣聖宋高僧詩選》,而並非由宋代單刻本摹寫。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二○《禪林類》曰: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宗之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清以降藏書家如黃丕烈、丁丙、繆荃孫、李盛鐸、傅增湘等人所藏《九僧詩集》,皆從毛氏本輾轉傳錄。
以上所考,是《九僧詩》的編集及流傳。我們可以回到最初的話題,即將籍貫差異很大的九位僧人聯繫在一起而稱“九僧”,是因為陳充所編的《九僧詩集》。上已言及,宋代猶有所謂《九僧選句圖》,不詳何人所編。在文學史上,以詩歌總集相號召而成為流派的,例子很多。又據唐、宋人習慣,作“句圖”以為法門,也是為了標榜宗派。九人都是和尚,不僅同時,而且關係密切,相互酬唱——但這些也許並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詩歌創作有著共同的風格,確乎是當時一個有影響的流派。
“九僧”之所以得名,《九僧詩集》之所以流傳,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們的創作本身。“九僧”的詩歌創作成就,歐陽修曾給予很高評價,他在題作《九僧詩》的雜記中寫道:
近世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司馬光的評價似乎稍低,《溫公續詩話》,謂《九僧詩》中,“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然而後來黃庭堅又推尊“九僧”,《後山詩話》曰:“黃魯直謂白樂天雲‘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不如杜子美雲‘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雲‘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雲中下蔡邑,林際“九僧”中,尤以希晝、惠崇成就為大。《臨漢隱居詩話》曰:“(歐舊)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玉壺清話》卷五載張師正嘗口佔二詩送別文瑩,中有“淮甸詩豪宋惠崇”之句。又《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六引《楊文公談苑·近世釋子詩》亦曰:“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晝為傑出”(下舉二人佳句,此略)。
關於“九僧”的詩歌創作,有這樣一個故事。《六一詩話》載:“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晁公武對許洞的做法頗不以為然,《郡齋讀書志》卷二○著錄《九僧詩集》時,寫道:“許洞之約,雖足以困諸僧,然論詩者政不當爾。蓋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楚辭》亦寓意於飈鳳雲霓。……若使諸公與許洞分題,亦須閣筆,矧其下者哉。”清初賀裳著《載酒園詩話》,在“詩魔”一節中更為“九僧”大抱不平:“余意除卻十四字(按指許洞所禁之十四字),縱復成詩,亦不能佳,猶皰人去五味,樂人去絲竹也。直用此策困之耳,狙獪伎倆,何關風雅!按‘九僧’皆宗賈島、姚合,賈詩非借景不妍;要不特賈,即謝tiǎo@⑤、王維,不免受困。”
我國古典詩歌,有《詩經》賦、比、興的傳統,《楚辭》則多以香草美人寄託懷抱。許洞所禁十四字,全是自然景觀或動植物名,作詩起興抒情、借物寓懷時難免用之,禁用固然有些絕對;但許洞也正是抓住了“九僧”詩工於寫景的共同特徵,這特徵又正是陳充將“九僧”聯繫在一起,或者說是“九僧”之所以成為一個詩派的主要內在因素。方回評文兆《宿西山精舍》詩時說:“所謂景朕,人人著意。”在評惟鳳《與行肇師宿廬山棲賢寺》詩時又說:“所選每首必有一聯工,又多在景聯,晚唐之定例也。盛唐則不然,大手筆又皆不然。”方氏的意思是說,注重景聯,是“九僧”從晚唐小家繼承來的共性。《瀛奎律髓》卷四七載希晝《書惠崇師房》詩,許印芳評曰:“‘九僧’者……,其詩專工寫景,又專工磨鍊中四句,於起結不大留意,純是晚唐習徑。”我們今天已無法看到“九僧”詩的全貌,但除《九僧詩集》外,尚能讀到大量摘句,而所摘“佳句”幾乎都是景聯。前已言及,《楊文公談苑》曾記載惠崇、希晝的佳句,見《宋朝事實類苑》引;《談苑》又載有惠崇的自撰《句圖》一百聯,見《青箱雜記》卷九引。宋代大作家如歐陽修等,都曾撮舉過“九僧”的名句。《詩藪》外編卷五根據《瀛奎律髓》所選“九僧”詩,較全面地摘錄了“九僧”的佳句。限於篇幅,我們這裡不能抄錄各家摘句,讀者不難找到這些材料。方回評懷古《寺居寄簡長》詩時說:“人見‘九僧’詩或易之,不知其幾鍛煉、幾敲推乃成,一句一聯不可忽也。”前引陳充序所謂“琢玉工”,蓋正是指他們嘔心瀝血、不遺餘力的錘鍊工夫。平心而論,
“九僧”的佳句特別是景聯確乎來之匪易,可說是一生心血的結晶。他們對景物描摹的孜孜追求雖有偏頗,但其作品不失為詩歌百花園中的叢叢奇葩,不必因許洞設禁事而否定。
“九僧”著力寫景,是由他們客觀生活條件和藝術趣味決定的。他們是僧人,儘管喜與公卿官僚往來,但終究是站在社會政治大潮之外,接觸最多的乃是山水風光,大自然有他們取之不盡的詩材,而將其錘鍊成詩句,則是他們的創造功夫。正如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所說:“沙門稱詩者,率工今體,大概不外江山、月露、草木、蟲鳥及禪偈語錄字句而已。宋‘九僧’詩最知名,伎倆亦不過此。當時有立禁體困之者,諸僧遂擱筆不成一字。”事實確乎如此,其長在此,短也在此。許印芳評希晝《書惠崇師房》,以為紀昀稱“九僧”詩少變化“切中其病”,“讀其詩者,鍊句之工猶可取法;至其先煉腹聯,后裝頭尾之惡習,不可效尤也。”
“九僧”著力寫景,也是他們習佛的結果。我們不知道“九僧”屬於佛教的何宗何派,但從他們詩篇中那含蓄空靈、清幽淡遠的意境,處處體現出詩人靜謐的觀照,不難領會其中濃濃的禪意。他們很可能都屬禪宗。長於寫景和苦吟琢句,正是晚唐以來禪詩的傳統。
如果再從專工寫景深入一步探討,便不難發現“九僧”詩的第二個共同點,那就是詩歌題材都較狹窄,思想內容也較貧弱。工於寫景,並不影響詩人取材的廣泛多樣和內涵的豐富深刻;但遍讀現存“九僧”詩,除了題詠風景名勝,便是贈人,而贈人也多連帶寫景,這類詩佔了絕大多數。《宋詩紀事》卷九一引張景《簡長詩序》曰:“上人之詩,始發於寂寞,漸近於沖和,盡出於清奇,卒歸於雅靜。”又引王隨《惟鳳詩序》曰:“持正大師一章一聯,皆出乎清新,發乎俊逸,賦象可以披圖畫,騰英可以潤金石。”張、王的視角,也在清奇、雅靜及一章一聯的清新俊美。《湘山野錄》卷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亭,探鬮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繞池徑,馳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試請口舉。”崇曰:“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馳心於杳冥以搜之”,方得一首半聯,純乎晚唐苦吟派習氣,而脫離生活,有句無篇,乃必然之勢。不妨再舉希晝《寄壽春使君陳學士》為例:
三處波濤郡,連年輟謝公。春齋山藥遍,夜舶海書通。樓潤星河露,川寒鼓角風。誰當刊惠政,一一古賢同。寄贈一地方長官,著力於中間兩“景聯”,春齋夜舶,山藥河露,幾乎搜盡了景物,但到“惠政”,卻只是輕輕帶過,顯得空泛。在“九僧”的題詠詩中,偶爾也可見到一些稍有社會內容的作品,如希晝《草》(或題懷古):
漠漠更離離,閑吟笑復悲。六朝爭戰處,千載寂寥時。陣闊圍空壘,叢疏露斷碑。不堪殘照外,牧笛隔煙炊。雖然調子過於悲涼,在詠史懷古中,倒也寄寓了興亡之嘆。就是這類詩,在“九僧”中也極為難得。釋智圓《贈詩僧保暹師》,評其所作《天目集》道:“……旨哉《天目集》,四海爭傳寫。上以裨王化,下以正人倫。驅邪俾歸正,驅澆使還淳。天未喪斯文,清風千古振。”
清人余蕭客《校影宋本九僧詩跋》又曰:“‘九僧’詩人有唐中葉錢、劉、韋、柳之室,而浸淫輞川、襄陽之間,其視白蓮、杼山,有過無不及。”見仁見智,或失準確。許印芳評希晝《書惠崇師房》時,從寫景的藝術方法,認定九僧“純是晚唐習徑,而根柢淺薄,門戶狹小,未能追逐溫、李、馬、杜諸家,只近姚合一派,卻無瑣碎之習,故不失雅則。虛谷(方回)謂學賈、周固非,曉嵐(紀昀)謂是‘十子’餘響,亦過情之舉。……此等詩病皆起於晚唐小家,而‘九僧’承之。”如果再加上“九僧”詩的取材及思想內容狹窄和貧乏,我們認為許印芳的意見是比較準確的。“九僧”的詩作,與晚唐小家極為相近,因此以他們為代表的詩歌流派,只能是“晚唐體”。唯其如此,故九僧詩不免存在“晚唐體”的共同缺陷,正如《筱園詩話》卷一所評:“九僧、四靈,以長沙(賈島)、武功(姚合)為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當然,對於詩僧,我們不必苛求,但從“詩人”或文學史的角度審視,這又不能不極大地限制了他們的成就,而決定了“九僧”不可能成為詩歌大家。
“九僧”的功夫在寫景,而且是在極狹窄的題材中覓句,缺少變化,像是小擺設,難免大同小異。於是化用前人成句,或在“景”上故做些小小曲折,意重境fù@⑥,成為“九僧”詩的第三個共同點。
《湘山野錄》卷中載:“宋九釋詩惟惠崇詩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傳誦都下,籍籍喧著。余緇遂寂寥無聞,因忌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又《溫公續詩話》:“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進士潘閬嘗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邪?’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毋詣沙門島邪?’”這兩則故事,當時是有名的藝林笑談。按“河分”兩句,見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河分”句用司空曙語,“春入”句出劉長卿詩。《瀛奎律髓》方回評,以為“三、四雖取前人二句合成此聯,為人所詆,然善詩者能合二人之句為一聯,亦可也,但不可全盜二句一聯者耳”。《帶經堂詩話》卷二○《禪林類》曰:“大抵‘九僧’詩規模大曆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平心而論,變化前人成句入詩,未嘗不可,在古人詩集中並不鮮見,文兆的嘲諷,恐更多的是出於私怨。問題不僅僅只這聯詩,而是在其他“佳句”中,我們也時時可以看到古人名句的影子。如前述《詩藪》所舉惠崇佳句,有“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一聯,我們便不難想到王維《使至塞上》詩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以上三點,構成了“九僧”詩的共同特色,也是他們能成為一個較有影響的詩歌流派的基本條件。
“九僧”詩在北宋得到歐陽修等大家的讚揚,以及總集《九僧詩集》在兩宋的傳播,為“九僧”詩風賦予了文學史意義,對宋代詩歌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九僧”是宋初人,他們學詩、讀詩,固然多是晚唐人集,所作詩為“晚唐體”,乃自然之勢。事實上,宋初無論元白體、晚唐體,以及稍後楊億、劉筠的“西昆體”,都是遵循中、晚唐的路子,“宋詩”自己的面貌,這時還沒有形成。所以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一再說,“景德、祥符間詩人有晚唐之風”,“宋詩之有唐味者,皆在真廟以前三朝”(卷一○評曹汝弼詩)。有宋開國七八十年間,這是詩壇的總體風貌。
如果我們再分析一下這三種詩體的作者成份,不難發現,“白體”作者一般是中上層官僚文人,可以王禹@⑦為代表,他們積極參預政治,在平易的詩風中,賦予較廣闊的社會內容,頗能繼承反映現實生活的中唐新樂府精神,甚至不自覺地與杜甫的詩心相通。因此王禹@⑦說:“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喜而作詩聊以自賀》,《小畜集》卷九)然而“白體”詩的流弊也是很明顯的,陳詞濫調,一覽無遺,讀者厭之。《六一詩話》引梅堯臣的話,批評此類詩道:“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曰:‘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雲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雲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為笑也。”“晚唐體”則一般為中下層文人乃至隱逸、處士、釋子作詩的共同門徑,這類詩人數量相當大,寇準早年在巴東時的作品,宋初著名的隱逸詩人林逋、魏野的作品,都是“晚唐體”。所以“九僧”的出現並受到重視,不是偶然的,它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代表了一大群詩人。他們以清苦工密的吟唱,對抗“元白體”末流的平庸淺俗,在當時無疑有一定的革新意義。“西昆體”作者多是台閣文人,學問淵博,官位清華,因而講究文章的“富貴氣”,鄙薄杜甫為“村夫子”。他們以綺麗的詩風,不僅企圖繼續矯正“白體”的淺俗,同時也意在對抗“晚唐體”的山林蔬sǔn@⑧氣。總之,宋初三種詩體或詩歌流派的遞相出現,分別代表了不同階層的審美趣味,既各有其產生的客觀社會原因,又各有其存在及發展的理由。
到仁宗朝,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等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詩歌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白體”、“晚唐體”、“昆體”都相繼退出了詩壇,能代表有宋一代面貌的“宋詩”誕生了。但是宋代詩歌的發展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路,所謂退出詩壇,其實並未絕跡,在有著強大勢力和巨大影響力的詩派(比如“江西詩派”)之外,入晚唐門徑的也不乏其人。
到南宋後期,在詩人們一片“學唐”的口號聲中,一反“江西體”,詩壇再次發生了重大變化,“晚唐體”居然成了主流。“永嘉四靈”之一的趙師秀嘗選編賈島、姚合詩為《二妙集》,又選錢起等七十六家詩為《眾妙集》。在“江湖詩派”中起關鍵作用、專為江湖詩人刊集的陳起,則編行《聖宋高僧詩選》,全部收入《九僧詩》。江湖詩人李@⑨又編行《唐僧弘秀集》十卷,序稱“詩教湮微,取以為淄流砥柱”。他們如此熱衷於晚唐詩及晚唐、宋初僧詩,是有目的的。儘管他們口頭上不提以晚唐或《九僧詩集》為準的,沒有、也不會公然打出“九僧”的旗號,但實際上是以晚唐、“九僧”詩作為效法的楷模。也就是說,他們所學的“唐體”,其實是晚唐體,是晚唐詩風中追求清境的一派,或者是宋初的所謂“晚唐餘韻”。正如方回在《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集》卷三二)中所指出的:“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為‘九僧’舊體唐詩。”
晚唐以降,儒、釋、道“三教”日益融合,詩僧也日益也俗化,他們詩歌創作的審美趣味,彷彿是披袈裟的士大夫。南宋後期,朝廷政治腐敗,國勢衰微,仕途險惡,不少文人感到沒有出路,於是行吟江湖,以佳篇名句博求達官的清賞,形成所謂“江湖詩派”。在創作上,“江湖派”詩人不滿“江西體”,於是sù@⑩流而上,與宋初“九僧”發生共鳴。因此可以說,包括“四靈”在內的“江湖詩人”的生活方式與藝術情趣,彷彿是不披袈裟的雲遊僧。這就是他們與兩三百年前的“九僧”乃至晚唐詩僧“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深層原因。許印芳在評《瀛奎律髓》所收希晝《書惠崇師房》時,以為“此等詩病皆起於晚唐小家,而‘九僧’承之,‘四靈’又承之”。又馮班評論道:“自希晝至懷古,所謂‘九僧’也,亦勝‘四靈’。‘西昆’之流弊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粗勁反之,流弊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唐詩,一洗黃、陳之惡氣味、獰面目。”因此宋末詩人學晚唐、“九僧”,有革除“江西詩派”流弊的客觀功效,其積極意義不可抹殺,不能簡單地斥為復古或倒退。
“四靈”及“江湖詩派”的出現,有其複雜的社會原因,詩歌史上也有他們的地位。但企圖在“詩教湮微”之時,用“晚唐體”或“九僧詩”作詩壇“砥柱”,以矯“江西”之失,則是不甚高明靈便的藥方,所以他們的實際成就不僅遠不及“江西詩派”的代表作家,而且也不及“九僧”,最多只能與“九僧”並駕。上引馮班評論希晝《書惠崇師房》詩,曾繼續寫道:“然(四靈詩)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庭堅)、陳(師道)有力也。”
有宋三百年間,詩歌創作的道路,像是繞了一個大大的圓圈,最後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雖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複,具有某種革新意義,但也表明詩人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接著是趙宋亡國,文運與國運俱敝。到明代,詩人們在“詩必盛唐”的口號下紛爭不已,其成就則連晚唐名家也難以企及,我國古典詩學的鼎盛時期,實際上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了。
“九僧詩”或者“晚唐體”,既是唐音餘響,也是輝煌的唐詩時代的迴光返照。
字型檔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戈下加戈右加刂
@②原字火右加軍繁體
@③原字火右加軍
@④原字戶下加衣
@⑤原字月右加兆
@⑥原字衤右加復
@⑦原字亻右加爪頭下加冉
@⑧原字竹頭下加旬
@⑨原字龍下加異去巳
@⑩原字氵右加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