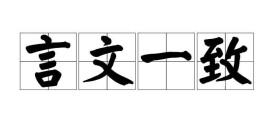言文一致
詞語
指日語使口語和書面語一致的文體,亦指日本近現代為此目的的運動。“言文一致”最初是於幕府末期由受西歐影響的洋學者們提出的。之後福澤諭吉採用寫文章讀給他人聽而修改的寫作方法,於明治時期形成風氣。
目錄
(Genbun Itchi)
1883年“加註假名”會成立,極力主張言文一致。
1899年正岡子規等的《杜鵑》派採用言文一致體。
1900年上田萬年等的《言語雜誌》採用口語體書寫報道,帝國教育會也開始設立“言文一致會”。
1904年第一次國定尋常小學讀本中大幅度增加口語體課文。
明治末年至大正期間,白樺派的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等完成了口語體。在小學,蘆田惠之助提出了“自己作文,自己選題”的主張。報紙社論於1900年前後開始採用“である”調的口語體。於大正末年,小說、教科書、報紙等皆採用了口語體,進入昭和時代后,論文、學術專著也改為口語體,但公用文、法令、昭書等仍保持著文語體(候文和漢文)。但戰後1946年,文語體被徹底取消,完全採用了口語體。言文一致的運動為日本的近現代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言文一致的歷史回顧
論及日本的語言規劃政策及其對我國語言規劃的啟示,首先會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日本的言文一致。日本方面的研究有山本正秀氏的《近代文體發生的史學研究》以及《言文一致的歷史論考》、李妍素氏的《“國語”思想——近代日本的語言認識》、駒迤武氏的《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安田敏郎氏的《帝國日本的語言編製》、酒井植樹氏的《胎死腹中的日本語·日本人——“日本”的歷史—地政學配置》、長志珠繪氏的《近代日本與國語民族主義》、小森陽一氏的《日本近代國語批判》等。
在先行研究中,日本言文一致的歷史背景、發生階段、形式有如下解釋:按照“近代文學史”上的一般說法,現在人們日常所使用的“言文一致體”是由坪內逍遙提倡、在二葉亭四迷的《浮雲》及國木田獨步的《武藏野》中首先嘗試,然後再經過後來的“小說家”不懈努力才得以確立的。
小森陽一(2003)認為這種一般說法排除了《日本帝國憲法》發布前那段把鉛字媒體絕對局限於消費層面的速記講談及速記相聲的歷史。
“速記法”指1884年開始的一種表音符號體系,它是將聲音翻譯成文字的中間媒介性質的符號體系,它在鉛字印刷市場上取得了商業成功,使得“言文一致”成為可能。三游亭圓朝的相聲《怪談牡丹燈籠》就是被田鎖綱紀的弟子若林甘藏、井升造用“速記法”作了記錄后拿去出版,並一舉成為暢銷書的。正是速記法的這種成功事例令“言文一致”的幻想毫無節制地膨脹了起來。(小森陽一,2003:110)
1883年(明治16年)7月12日至16日,日本改進黨在《郵政通報新聞》上刊登了一系列報道,被認為是最早實際應用“速記法”的文章。矢野龍溪在《經國美談》的序篇《文體論》中強調指出“維將漢文、和文、直譯歐文、俗語俚語四體並用,以此獨創一新文體者,始為良文作者”,主張創新文體。
在民族意識高漲的社會背景下,將“文言一致”上升到創造“國語”和“國文學”的高度。“近代日本語言政策的實質性起點,可以說是在甲午戰爭高潮中,(社會上)設定了具備形成國民、教化國民功能和排除異質語言、變種語言這一企圖的‘國語’概念、並為其普及而追求語言的簡單化之時。”(安田敏朗,2003:135)
從形式來看,日本的文體是“將漢文、和文、直譯歐文、俗語俚語”“四體並用,以此獨創”的新文體(安田敏朗,2003:135)。
“《浮雲》的文體之所以事後被作為‘近代文言一致體’或者‘近代口語’的起源得到‘發現’”只是因為“通過西歐翻譯文體而解體漢文翻譯文體,這與當時日本國內由於甲午戰爭獲勝而圖謀‘脫亞入歐’的現狀奇妙地結合在了一起。山本正秀認為言文一致體濫觴於前島密等人的?ござる體?,繼而小報所使用的?ござ(り)います、ます、であります調?,二葉亭四迷《浮雲》的?だ體?、山田美妙的?です體?等接踵而至。文末語出現了複數性。而這種複數性后被尾崎紅葉在《多情多恨》中確立的?である體?所統一,至此“言文一致”體“宣告誕生”(小森陽一,2003:189)。
對文字、書寫語言的問題給予劃時代洞察的是德里達所著的《文法學》(1967年)。德里達把語音中心主義視為柏拉圖以來的西洋形而上學問題。明治時期的文言一致,幕府末年漢字廢止案以後的運動是在西洋的影響之下發生的。18世紀的國學中已經有了語音中心主義。那是由通曉梵文的學者們掀起的,當與西洋形而上學沒有關係(柄谷行人,2003)。
由此得出一點語音中心主義不局限於西洋問題,聲音中心主義與現代的民族國家問題有著必然的關係。
在西歐,最早用俗語寫作並對此賦予理論上之意義的是但丁。其後,在法國、英國、西班牙等地也發生了這種嘗試。現代民族國家的母體形成與基於各自的俗語而創出書寫語言的過程相併行。但丁《神曲》,笛卡爾、路德《聖經》,塞萬提斯等所書的語言分別成就了各國的國語。
但丁所說的俗語是針對作為規範的拉丁語而言的。拉丁語是所謂“世界帝國”的語言。帝國如羅馬、中國那樣的多民族國家,其特徵是使用像拉丁語或漢語那樣的標準語。在東亞有中華帝國存在,日本屬於漢字文化圈。漢字在各國被以不同的發音所閱讀,書面語與聲音沒有直接關係。德里達闡明用俗語來書寫包含了對拉丁語=羅馬教會=帝國支配之政治性的抵抗。語音中心主義里有著政治的動機,與城邦=國家的出現密切相關。
德里達在索緒爾把文字從語言中排除出去這一做法中發現了語音中心主義。索緒爾針對語言和文字的關係:語言與文字,兩者有相互連帶的關係,只有口語才是語言學的對象。進入時間中的語言學之分類,正因為語言被書寫下來了,故其分類才成為可能。
“強大的民族將自己的特殊語言強加於人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政治的支配是不夠的,首先需要確立文明的優越地位。文字語言通過學校、教會、政府即涉及公私兩端的生活全體來強行推行其支配。”(柄谷行人,2003) 文字語言及其所承載的文明到處存在著,口語則不斷地受到它的影響。在18世紀日本國學家的聲音中心主義里包含著抵抗中國“文化”支配的政治性鬥爭。
日本文字:古代日語,把漢語吸收到書寫語言中,漢字同時以日語的意義=聲音被“訓”讀。這種“漢字假名混交”的書寫語言已經出現在8世紀的《古事記》里。與國學家們的意見相反,《古事記》中的文章並不是當時俗語的記錄摹寫,而是根據以前試圖作為正史用漢文寫作的《日本書記》翻譯成俗語的。那時用做表音的漢字不久被簡化成“假名”開始使用。漢文都是被作為“真名”而存在的。日本的書寫語言基本上還是漢字和假名兼用。
在《源氏物語》中,紫式部極有意識地排斥漢語。本居宣長在紫式部拒絕使用漢文的行動中發現了她對“漢意”的批判。《源氏物語》中,作者要用語彙貧乏的大和語言來表達來自漢語的意義。由此,大和語言作為書面語言得到了規範化。
批判“漢字假名混交”語體的國家語音中心主義里,存在著把感情心緒的東西置於知識道德之上的一種浪漫派式的美學思考。與西洋并行的所謂“現代”性的思考。國學派的語言學到明治時期以後遭到了排斥。
日本的現代語言學開始於對19世紀西洋歷史語言學的導入,是把西洋的語法機械地適用於粘著語日語的結果。並且,這種語言學一方面是自然科學化的,一方面又是國家主義的。
言文一致是某種“文”的創立。這個“文”對內在的觀念來說不過是一種透明的手段,在此意義上,這也是文字、書面語的消失。這個“文”的創立是內在主體的創生,同時也是客觀對象的創出,由此產生了自我表現及寫實等。
言文一致不是由國家或國家意識形態理論家,而主要是由小說家來實現的。“言文一致”基本上可以說是在任何國家都會發生的。中國的“言文一致”與其說是在西洋的壓力下,不如說是在日本的侵略下發生的。
“言文一致”是明治20年前後現代諸種制度的確立在語言層面的反映。言文一致既不是言從於文,也不是文從於言,而是新的言=文之創造。言文一致與憲法制度一樣是現代化的努力。
“言文一致”運動一般認為開始於幕府末期前島密提出《漢字御廢止之義》的進言。一般認為言文一致是為建立現代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事項。在明治10年代後期成為重大問題被提上日程。“日語假名學會”(1883年7月)、“羅馬字學會”(1885年1月)的結成是在鹿鳴館時代。這時出現的“戲劇改良”、“詩歌改良”、“小說改良”,在廣義上都包含在“言文一致”運動中。另外,前島密的進言明確標示了言文一致運動其根本在於文字改革和文字的否定。
二、日本近現代文學的吸收與發展
文學方面,隨著這股“洋風東漸”,西方文學思潮大量湧入日本。寫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相繼統領明治文藝領地。大政時代的“私小說”的異軍突起,不能不說是日本文壇對“既西方的、又日本的”、“和洋結合”的文學形式的一種探索。如果說谷崎潤一郎的《源氏物語》的現代版是那種純粹的日本式古典美的回歸,那麼“新感覺派”的川端康成則是日本文化與西洋文化完美結合的傑出代表。西方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甚至異化,塗抹了日本的色彩,為日本所用。日本引種西方文化,並使之隨日本的水土而發生了變異,從而日本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補給。
日本文學不是封閉型發展,而是開放型發展,古代之與中國、近代以來之與西方的文學,是相互交流,彼此影響,成為其文學發展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比較研究也在其中。
近現代以來,日本文學,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儘管存在歷史、地域的距離,然而引進西方的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等形態,都是在與日本古代的寫實的“真實”、浪漫的“物哀”、象徵的“空寂”與“閑寂”等觀念形態的接合點上釀造出來的。這是日本近代文學接受西方種種文學思潮而又實現“日本化”的根本原因。日本近現代文學,是在回應西方現代性挑戰過程中,以西方文學為參照、典範而建立起來的。自啟蒙文學開始,經過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到白樺派理想主義、無產階級文學及新感覺派,留下了一串追尋西方文學的腳印,人本主義、自由主義精神不斷加強,現代意識日益鮮明。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文學的現代化處於滯后的狀態。江戶時代的文學觀念和價值觀念仍占文壇的主導地位。由武士運作和町人運作兩大類文學佔據著文壇的中心位置。前者是以儒教理念為基礎的上流文學,比如漢詩文、和歌、雅文調紀行文,主要強調道德教化的功能,以功利和實用為目的。後者是以戲作為主的庶民文學,比如人情本、滑稽本、讀本、狂歌等,不強調教化作用,而以娛樂為目的。儘管兩者的文學價值觀的出發點不同,但是其立足點都是不承認文學本身的獨立價值,實際上都是輕視文學,將文學視為“無用之業”。 《浮雲》問世后,雖然得到一部分有識之士的好評,但總的說來,人們卻未能真正認識到這部作品的時代意義。二葉亭四迷極端不滿日本文學界到處充斥著以遊戲態度寫作的現狀,曾感嘆:“文學不是大丈夫的終身事業!”
近代文學的先驅者們首先努力擺脫江戶時代遺留的舊文學觀念。比如坪內逍遙首先明確小說是一種藝術形態,有其獨立的價值,從而確立小說在藝術上的地位。同時強調小說只受藝術規律的制約,而不從屬於其他目的。而且,他將小說作為第一文藝,批判了江戶時代勸善懲惡的舊文學觀。森鷗外引進西方文藝理論和美學批評,其“大至藝術全境,小至詩文一體”,整理當時混亂的文學理念,確立新的文學批評原理和審美基準。
文學觀念的更新是不會停止的。隨著時代和科學的不斷進步,文學觀念是在不斷更新的。
30年代開始,伊藤整、堀辰雄引進普魯斯特“內心獨白”和喬伊斯的“意識流”手法,而且將這種手法作為小說的新概念,定位在一種文學的主義上,並將其稱為“新心理主義”。也就是說,文學與心理學、精神病理學發生交叉的關係,促使傳統的以寫實為基礎的文學原理髮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阿部知二在《主知文學論》中進一步主張:文學要繁榮,必須重視科學的知性要素,有意識地採用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精神科學等)的方法,與我們的文明現象、時代精神相結合。所以他強調:以知性處理感情,在具體運作上儘力避免使用情緒的、感情的語言,而要有意識地將語言與知性直接結合,即將科學的方法運用到文學理論和實踐上。
三、現代語境下的文學思考
隨著高科技時代的到來,文學與科學的交叉發展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比如同為醫學博士出身的加藤周一和加賀乙彥分別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文藝評論家加藤周一運用醫學和生物學的“雜交優生”和“進化論”等理論,反對純化日本文化,不管是全盤日本化還是全盤西方化,他既承認“西方文化已經深入滋養日本文化的根干”,同時又肯定日本文化是在“土著文化深層積澱而形成的”(加藤周一,1984:28-29)。
從而提出了“日本文化的雜種性”論點,並運用在文學批評上,強調了日本文學的土著世界觀與外來文學思想上的對應與融合,創造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質的文學。小說家加賀乙彥大膽地將醫學、精神醫學、病態心理學引進文學創作中來。他的《佛蘭德的冬天》、《不復返的夏天》、《宣判》等小說,在文學結構里,存在兩個不同思維結構——醫學的具象思維結構與文學的抽象思維結構的對立與對應,作家在這兩者中找到了平衡,進而切斷醫學與文學的二律背反,在醫學中的文學機制上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完全將醫學變形為文學。
文學評論家秋山駿則以“病患者的光學”的觀點來評論風見治的《鼻子的周圍》,該小說描寫一個病癒后的麻風病患者在鼻子上仍留下病跡,不能在社會上過正常生活,最後造了一個新鼻子才免遭社會摒棄。作家通過“病患者的光學”(視線)來折射日常生活的孤獨感和空虛感。秋山駿估計,出現這種文學現象也許是由於艾滋病新病菌的出現,“病患者的光學”發生作用,產生新的主人公,文學也會發生變化,面臨自我面貌大改觀的局面。
在20世紀後半葉,知識經濟的出現,“邊緣學科”的交叉發展更趨強化。文學與其他學科,包括一些與思維空間相距甚遠的自然科學的相互交流、滲透和影響,不斷地更新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也必將不斷地更新文學觀念。特別是作為文學結構主體的語言學,在上世紀前半葉發生了“語言學轉向”的重大學術事件,使整個文化發展進入文本、語言、敘事、結構、張力、語言批判層面。到了上世紀後半葉,人文理論與社會理論又出現語言轉向後的“新轉向”——由語言轉向歷史意識、文化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研究、社會關係分析、知識權力考察等,進入一個所謂的人文科學的“大理論”之中。同時,帶來文化哲學詩學的轉型(王岳川,1998:4)。這一現象也出現在文學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中,文學擺脫狹隘的傳統界定,與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發生更深刻的聯繫。文學上的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的出現,也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語言學轉向”帶來文學觀念的再一次更新。
日本女權主義者、女性文學批評家水田宗子的專著《女性的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的歷程》(2000),就從多學科和相關邊緣學科的視角出發,以“性差”作為切入點,論述了“性差”的文化與瘋狂、婚外戀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表現和與傳統的戀愛、婚姻和家庭觀的關係、女性超越社會的性別角色與自我表現的聯繫、在性的意義上女性對生育希求與嫌惡的二律背反、女性的人體美與男性的性愛的正常與反常、女性表現深層的沉默等廣泛的問題,並以此透視女性自我的精神世界,深入地挖掘女性的性與愛的深層心理諸相,以及形成“性差”結構的各種因素,包括民族、階級、宗教、民俗、意識、制度諸綜合因素。在這個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分析了“性差”概念的形成原因和“性差”文化結構的特徵。而作者的“性差”概念,不僅是指男女的性別差異,而且是包含更為深刻而廣泛的文化內涵,即包含男女性格特徵和性機能差異的客觀存在。恐怕可以說,這是以一種新的文學觀念進行文學批評的嘗試吧。
20世紀日本文學的歷史經驗證明,日本文學走向現代,儘管存在一定的歷史距離,但與過去的傳統文學和審美理念之間沒有明顯的裂痕,而是一脈相承的。作為西方傳來的各種主義形態,從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到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無一不是在與傳統的觀念形態的寫實的“真實”、浪漫的“物哀”、象徵的“空寂”和“閑寂”文學理念和審美理念的接合點上釀造出來的。可以借用三島由紀夫的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生於日本的藝術家,被迫對日本文化不斷進行批判,從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清理出真正屬於自己風土和本能的東西,只有在這方面取得切實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得出日本言文一致的過程與近現代文學轉型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對日本近現代文學的轉型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它不僅提升了日本民族的總體文化素質,增強了國家社會的凝聚力,而且開闊了日本人的視野。擴大了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吸納能力。與此同時,由於具有日本民族特質的新文學的產生,反過來又進一步豐富了日本文化,增加了日本文化的厚重感,增強了日本文化的張力。
本項目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中心“中國外語教育基金”課題資助,並得到王克非教授指導,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考文獻
[1] 小森陽一。日本近代國語批評[M].陳多友,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 安田敏朗.?脫?日本語?への視座?[M].三元社,2003.
[3]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M].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4]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の雜種性[A].加藤周一著作集(7)[M].平凡社,1984.
[5] 王岳川。語言學轉向之後[N].中華讀書報,1998-04-01.
[6] 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的歷程[M].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雷曉敏,廣東海洋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日本近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