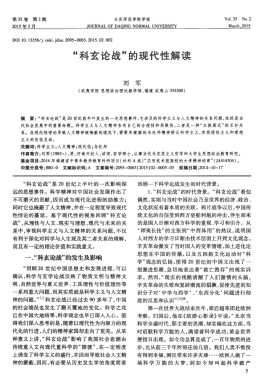科玄論戰
科玄論戰
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又稱“人生觀論戰”。這場論戰雖然已過去90年,但論戰涉及的問題至今仍未徹底澄清。而較之“科玄論戰”所發生的20世紀初,在科學技術迅疾發展的21世紀,今日對科學與人文價值的認識在新的時代問題域中更具現實意義。
科玄論戰自1923年2月開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結束,歷時將近兩年之久;此後仍然斷斷續續,但已不是那麼集中。整個論戰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論戰的緣起與爆發:從1923年2月張君勱發表“人生觀”講演,到同年張發表長文反擊丁文江的駁斥。論戰的展開與深入:從1923年5月梁啟超作《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到同年吳稚暉發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其間科學派、玄學派雙方人物紛紛登場,論戰愈演愈烈。論戰的轉折與結局:從1923年11月陳獨秀為論戰文集《科學與人生觀》作序、鄧中夏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歲末,其間“科-玄”論戰發展為科學派、玄學派和唯物史觀派三大派的思想論爭。
張君勱開宗明義指出,科學與人生觀是根本不同的:“科學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則,而此原理原則,皆有證據”;然而“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他接著將科學與人生觀加以比較,列舉了以下五點區別:
第一,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
第二,科學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
第三,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
第四,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之單一性。
張君勱總結道:“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這一切,都是與科學的特點截然不同的。
關於這種人生觀問題,張君勱列舉了以下九個方面:我與我之親族之關係,我與我之異姓之關係,我與我之財產之關係,我對於社會制度之激漸態度,我在內之心靈與在外之物質之關係,我與我所屬之全體之關係,我與他我總體之關係,我對於世界之希望,我對於世界背後有無造物主之信仰。“凡此九項皆以我為中心,或關於我以外之物,或關於我以外之人,東西萬國,上下古今,無一定之解決者,則以此類問題,皆關於人生,而人生為活的,故不如死物質之易以一例相繩也。”
接下來又專門提出四大方面“有關人生觀之問題”,其中第一點是關於“精神與物質”。他認為,科學是關乎物質的,而人生觀是關乎精神的。他對中、西文明進行了對比,認為中國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質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為物質文明。”而西洋的“物質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觀到底不足以解決人生觀問題,所以導致了“一戰”的災難;唯有中國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觀才能解決人生問題。我們不難看出,張君勱之用心所在,實乃中西文明的比較。他對西方現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評態度的,而對中國傳統文明則是頌揚有加的。但他立論的根據則是“人生觀”與“科學”的區分,其結論是:“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蓋人生觀,既無客觀標準,故惟有返求之於己。”
張君勱“人生觀”演講發表以後,“吾友丁在君,地質學家也,夙以擁護科學為職志者也,讀我文後,勃然大怒,曰,誠如君言,科學而不能支配人生,則科學復有何用?吾兩人口舌往複,歷二時許,繼則以批評之文萬餘字發表於《努力周報》。”這就是丁文江作於4月12日、發表在北京《努力周報》第48、49期的長文《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
丁文江把張君勱的人生觀哲學斥為“玄學”,稱張君勱“玄學鬼附身”,並從以下八個方面駁斥了張君勱的“人生觀”哲學:
(1)“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丁文江首先把張君勱的理路歸結為“人生觀‘天下古今最不統一’,所以科學方法不能適用”,然後據此加以駁斥:“人生觀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何況現在‘無是非真偽之標準’,安見得就是無是非真偽之可求?”“要求是非真偽,除去科學方法,還有什麼方法?”
(2)“科學的智識論”作為一個馬赫主義者,丁文江在此處闡述的是一種“經驗實在論”立場,包括這幾層意思:一是經驗原則:科學知識起於感知。“覺官感觸是我們曉得物質的根本”;“無論思想多麼複雜,總不外乎覺官的感觸。”二是邏輯原則:另外一些知識起於據經驗而進行的邏輯推論。他以“自覺”(自我意識)為例,“旁人有沒有自覺呢?我不能直接感觸他有,並且不能直接證明他有,我只能推論他有。”三是唯心原則:物質存在最終起於經驗-邏輯。“我們所曉得的物質,本不過是心理上的覺官感觸,由知覺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論。科學所研究的不外乎這種概念同推論。”丁文江的立論,是基於兩條“原則”的:其一,“凡常人心理的內容,其性質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聯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個人覺官感觸的經驗(經驗原則——引者注),第二是他腦經思想力的強弱(邏輯原則——引者注)。”其二,“天才豪傑同常人的分別,是快慢的火車,不是人力車同飛機。因為我們能承認他們是天才,是豪傑,正是因為他們的知覺概念推論的方法完全與我們相同。”這兩條原則其實是一條,即經驗主義的心理聯想主義的原則。
(3)“張君勱的人生觀與科學”丁文江從五個方面指出:張君勱的“人生觀”“決逃不出科學的範圍”。其中有幾個論點很值得注意:其一,“凡不可以用論理學批評研究的,不是真知識。”其二,“科學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現象,若是你所說的現象是真的,決逃不出科學的範圍。”其三,“科學未嘗不注重個性直覺,但是科學所承認的個性直覺,是‘根據於經驗的暗示,從活經驗里湧出來的’。”
(4)“科學與玄學戰爭的歷史”丁文江簡述了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和獨立出來的歷史,宣判了哲學的死刑。
(5)“中外合璧式的玄學及其流毒”丁文江指出:“張君勱的人生觀,一部分是從玄學大家柏格森化出來的”;“西洋的玄學鬼到了中國,又聯合了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高談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靈,一齊鑽進了張君勱的‘我’裡面。”
(6)“對於科學的誤解”丁文江在這裡列舉出人們對科學的三種誤解:“向外”的(務外逐物),“物質的”,“機械的”。他申辯道:第一,“科學的材料是所有人類心理的內容”;“張君勱說科學是‘向外’的,如何能講得通?”第二,科學不僅是“物質的”;科學對人心大有裨益:“科學不但無所謂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第三,科學不是“機械的”;“瞭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得透徹”。
(7)“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丁文江不承認“歐洲文化破產”之說,認為:“我所不得不說的是歐洲文化縱然是破產(目前並無此事),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因為破產的大原因是國際戰爭”;“對於戰爭最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然是不科學的”;“歐美的工業雖然是利用科學的發明,他們的政治社會卻絕對的缺乏科學精神。”
(8)“中國的‘精神文明’”丁文江不同意張君勱所採取的“西方為物質文明,中國為精神文明”這種當時比較流行的說法,指出:“至於東西洋的文化,也決不是所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這樣籠統的名詞所能概括的。”
最後,丁文江引用了胡適的一句話來作“結論”:“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
(1)關於“物質科學精神科學之分類”張君勱認為:“精神科學,依嚴格之科學定義,已不能認為科學。”
(2)關於“科學發達之歷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質”張君勱也像丁文江一樣,針鋒相對地通過敘述科學的歷史來證明其觀點:科學的“自然公例”也並不是“萬能”的;“關於純粹之思想”的“純正心理學”更無“公例”可求。
(3)關於“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之異同”張君勱以物理學和心理學為物質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典型加以比較,指出兩者之間有本質區別。這是張君勱的人生觀哲學的基本理據:“第一,凡在空間之物理易於試驗,而生物學之為生活力(Vital force)所支配者,不易試驗,至於心理學則更難。第二,凡在空間之物質,前後現象易於確指,故其求因果也易;生物界前後現象雖分明,而細胞之所以成為全體,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學則頃刻萬變,更無固定狀態可求。第三,三坐標或四坐標,驗諸一質點之微而准者,可推及於日月星辰,此尤為生理學心理學所不能適用之原則。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頓,曰原子,曰質量,曰能力:此數者得之抽象(Abstraction)而絕不為物體之具體的實在(Concrete Reality)所擾。至於生物學,有所謂種別,有所謂個性;而心理學為尤甚。因而生物心理兩界日為個性之差異所擾,而不易得其純一現象(Uniformity)。”“物理現象惟有此四大原則,故日趨於正確;生物心理現象惟無此四原則,故不能日就於正確。”
(4)關於“人生觀”張君勱歸納了丁文江的質問的幾個要點,答覆如下:“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內容不同,絕對可以分別;即以科學分類,久為學者所公認一端,可以證之”;“人與動植物同是活的,然動植物學之研究之對象為動植物,精神科學之所研究者為人類心理與心理所生之結果,故不得相提並論”;“凡為科學方法所支配者,必其為固定之狀態。純粹心理,頃刻萬變,故非科學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觀超於科學以上,不能對抗,故分家之語,不能成立。”
(5)關於“君子之襲取”這裡是針對丁文江譏諷玄學家之所以厭倦科學而取玄學,“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張君勱反唇相譏,指出丁文江“抄襲”皮耳生。
(6)關於“所謂科學的知識論”張君勱在這裡是要反駁丁文江的“科學的知識論”之說:首先,如果所謂“科學的知識論”是指科學家的知識觀,“則古今科學家中有關於知識論之主張者,不止赫氏、達氏、詹氏、杜氏、馬氏數人”,還有許多其知識觀絕不相同的科學家,那麼,究竟哪一家的才算是“科學的”?進一步講,“知識論者,哲學範圍內事也,與科學無涉者也。”科學是知識,但並不是“形而上”的“知識論”;只有哲學的知識論,而無所謂“科學的知識論”。
(7)關於“科學以外之知識(一名科學之限界)”張君勱在這裡劃定“科學之界限”,以求“科學以外之知識”;限定認識論的“真”,確立價值論的“真”。他引證英國生物學家托摩生的話,以說明在科學認識之外還有三種“真”以及求“真”的途徑:哲學(形而上學),宗教(道德),美術(藝術)。
(8)關於“玄學在歐洲是否‘沒有地方混飯吃’”張君勱在這裡列舉若干事實,稱歐洲最近二三十年的思潮可以叫做“新玄學時代”。
(9)關於“我對於科學教育與玄學教育之態度”張君勱對科學教育的流弊進行了批判,但也並不完全贊同社會改造派之教育,而是指出兩者各有偏頗:“吾以為教育有五方面:曰形上、曰藝術、曰意志、曰理智、曰體質。科學教育偏於理智與體質,而忽略其他三者。社會改造派之教育,偏於意志與犧牲精神。”他認為,在現有科學教育基礎上還應該加上“玄學教育”,包括三條:形而上學(超官覺超自然的條目),藝術,自由意志。
(10)關於“我對於物質文明之態度”張君勱進一步申訴了他關於西方為物質文明、中國為精神文明的觀點,對“物質文明”的西方列強那種科技立國、工商立國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惡果進行了批判,告誡國人不要重蹈覆轍,而應“別尋途徑”。
(11)關於“我對心性之學與考據之學之態度”張君勱對傳統的“漢學”(考據之學)、“宋學”(心性之學)的優劣得失進行了比較:他認為中國的漢學與宋學之爭,同歐洲的經驗派/唯物派與理性派/唯心派之爭,是“人類思想上兩大潮流之表現,吾確信此兩潮流之對抗,出於心同理同之原則”,因而是可比較的。他以列表的方法,對中西兩大派思想潮流進行比較,並得出結論說:“關於自然界之研究與文字之考證,當然以漢學家或歐洲惟物派之言為長”;“其關於人生之解釋與內心之修養,當然以惟心派之言為長。”
(12)關於“私人批評之答覆”他再次申明其思想上的“立腳點”:“(一)知識以覺攝與概念相合而成。(二)經驗界之知識為因果的,人生之進化為自由的。(三)超於科學之上,應以形上學統其成。(四)心性之發展,為形上的真理之啟示,故當提倡新宋學。”
就在丁、張激戰的時候,思想界的一員宿將梁啟超出場了。5月5日,他寫了一篇《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暫時局外中立人梁啟超宣言》。這篇“宣言”有兩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其一,“這個問題(即“人生觀”問題)是宇宙間最大的問題。”其二,“這種論戰是我國未曾有過的論戰”;“替我們學界開一新紀元”。這充分表現出梁啟超的敏銳。
科學派繼丁文江之後第一個出場的,則是大名鼎鼎的胡適。5月11日,胡適在上海寫成《孫行者與張君勱》,發表於《努力周報》。他把張君勱比做孫悟空,而把“賽先生(科學)和羅輯先生(邏輯)”比做如來佛;認為玄學縱有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掌心。
胡適此文開其端,科學派對玄學派展開了凌厲的攻勢。其中,科學派主將丁文江的《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是最值得注意的。此文從八個方面反駁張君勱的批評:(1)批評了張君勱的“反進化論”的“現在主義”。(2)反駁了張君勱的“人生觀”定義:如果“人生觀是我對於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觀察、主張、要求、希望。範圍既然這樣廣,豈不是凡有科學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觀裡面?因為那一樣科學不是我對於物同人的一種觀察,一種主張?”(3)指責張君勱對科學有兩大誤解:“君勱對於科學最大的誤解是以為‘嚴正的科學’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變,‘科學的’就是‘有定論’的”;“君勱對於科學第二種誤解是把科學的分類當做科學的鴻溝。”(4)為其“存疑學者的態度”申辯:“無論遇見甚麼論斷,甚麼主義,第一句話是:‘拿證據來!’”(5)繼續宣講其“科學的知識論”,其要點有三:其一,“這種知識論是根據於可以用科學方法試驗的覺官感觸”;其二,“以感覺為知識的原子,有許多心理學的證據”;其三,“我們現在是就知識論知識,沒有把情感計算在內”。(6)說明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是沒有根本區別的,因為它們的“材料”(對象)同為心理“現象”,它們的方法同為經驗“歸納”。(7)批駁張君勱所說“科學以外之知識”,指出:“他把美術宗教當做知識,不但學科學的人不承認,恐怕學美術的信宗教的人也未必承認的。”(8)丁文江第一次明確給“人生觀”下了一個定義:“一人的人生觀是他的知識情感,同他對於知識情感的態度。”“知識情感”這個短語很令人費解,從他的上下文來看,他認為“情感是知識的原動,知識是情感的嚮導”,則所謂“知識情感”似乎指在知識規束下的情感衝動。
後來丁文江又於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發表於《努力周報》。此文除附了一個長長的書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指出:“他說玄學就是本體論,張君勱所講的人生觀與玄學無關,我卻不能承認。”“宰平先生要我給玄學下一個定義。我就斗膽地說:‘廣義的玄學是從不可證明的假設所推論出來的規律’。”
除胡適、丁文江外,這一階段科學派中其他人物的觀點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觀的科學或科學的人生觀》提出:“人生觀成不成科學是一事,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又是一事”;“人生觀的科學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學的人生觀卻是可能的事。”其一,科學可以“間接”“改變”人生觀;其二,科學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觀。
章演存發表於《努力周報》的《張君勱主張的人生觀對科學的五個異點》,是直接針對張君勱“人生觀”演講中所列的人生觀與科學的五點區別而發的:(1)一方面,“不能說科學純為客觀的”;不過,客觀的“原則還是存在”。另一方面,“人生觀里最不容易統一的,就是一種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沒有情感一樣的地步,原則也一定還是存在。莊子說,‘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這就是去求人生原則的方法。”(2)認為張君勱所謂“直覺”也還是“意見”,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學的“論理”。(3)指出:“張君沒有告訴我們人生觀是全體的——不能分割的理由。”(4)指出張君勱的一種“自相矛盾”:他所舉古今中外偉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觀及其表現都是有動機和理由的,“動機和理由就是因,他們的人生觀就是果。”(5)指出張君勱的“人生觀”“是從張君‘皆以我為中心’一句話產出來的”;“張君要是換句話說,‘凡此九項,皆以“真”為中心’,這個是非立即就解決了。”
朱經農《讀張君勱論人生觀與科學的兩篇文章后所發生的疑問》,從八個方面對張君勱提出質疑:(一)既然人生觀為文化轉移之樞紐,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標準,也即人生觀之“是非標準”;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捨,即“方法”;由人生觀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則有其“果”。(二)張君勱既說人生觀無絕對之是非標準,又說人類目的避惡向善,此善與惡,正是“是非標準”。(三)指出了張君勱的一個嚴重混亂,就是把“無公例可求”的“人生觀”歸入哲學,又把哲學歸入了所謂“精神科學”範疇,而又承認精神科學是有公例可求的。(四)對張君勱關於“物質”與“精神”的對立、“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劃分提出質疑。(五)批駁張君勱關於科學的“金科玉律”、“一成不變”的說法,捍衛丁文江關於科學“日進無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六)質疑張君勱的“純粹心理”概念,並指出他以“頃刻萬變”來證明其不為科學所支配的謬誤。(七)揭露張君勱的矛盾:既雲“人生之所謂善者皆精神之表現……其所謂惡者皆物質之接觸”;又雲“所謂物質者,凡我以外皆屬之”(包括父母、妻子、國家、社會等等)。可是人誰不接觸父母妻子,這豈非說人人皆必陷於惡?(八)指出了張君勱的另外一個問題,即把中國文明歸結為“精神文明”,而把歐洲文明歸結為“物質文明”;進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質文明的制約、尤其是受物質自然環境的影響的。
《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共收入唐鉞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心理現象與因果律》開宗明義:“我這篇文章的主意,在說明一切心理現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他強調:“因果律是從經驗得來的。”第二篇文章《“玄學與科學”論爭的所給的暗示》,與梁啟超那篇《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性質相當。第三篇文章《一個痴人的說夢——情感真是超科學的嗎?》 是針對梁啟超《人生觀與科學》中的論點而發的,認為,梁文以為情感如“愛”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實上愛與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第四篇文章《科學的範圍》是針對林宰平對丁文江的質疑,解釋說,“我的淺見,以為天地間所有現象,都是科學的材料。天地間有人,我們就有人類學、人種學、人類心理學等。天地間有魚,我們就有魚學。天地間有藝術,我們就可以有藝術學。天地間有宗教,我們就可以有宗教學。說藝術宗教的科學的研究是科學,不是說藝術宗教就是科學,同說魚的科學研究是科學,不是說魚就是科學一樣。”最後一篇文章《讀了〈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後》是針對范壽康的駁議而發的抗辯,堅持“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全部”。
心理學家陸志韋的《“死狗”的心理學》發表於《時事新報·學燈》,指責丁、張兩家都在大談心理學,卻都不懂心理學。
王星拱作了一篇題為《科學與人生觀》的文章,與後來出版的論戰文集同名,發表於《努力周報》。與丁文江一樣,王星拱也是個馬赫主義者。王文貫徹了他的“科學”立場:“依科學去解釋生命問題,應該叫做‘人生之科學觀’”,即對人生的科學認識;“依科學態度而整理思想,構造意見,以至於身體力行,可以叫做‘科學的人生觀’”,即建立在科學認識基礎之上的人生態度。結論:“科學是憑藉因果和齊一兩個原理而構造起來的;人生問題無論為生命之觀念、或生活之態度,都不能逃出這兩個原理的金剛圈,所以科學可以解決人生問題。”
《科學與人生觀》書中收入了一篇署名為“穆”的文章《旁觀者言》,文中標舉“科學家的人生觀”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尊重事實”;二是“對於事實之平等觀”;三是“條理密察”。
吳稚暉以嘻笑怒罵的文筆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學》,發表在《晨報副刊》。認為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學和物質文明。另外,在“附註”中,他對中國的“國故”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里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吳稚暉同時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長文,題為《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洋洋6萬餘言,全面闡述了自己的主張。自稱:“吳稚暉拚命做這文章,鼓吹物質。”在他看來,人生不外乎三件事:“清風明月的吃飯人生觀,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觀,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要把這三件事辦好,都需要科學與物質文明。他在文中表明了七個“堅信”:“我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惡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知識之能力,可使善亦進惡亦進”;“我信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之疑難,亦愈易解決”;“我通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表達了堅定的科學主義立場。
面對科學派的攻勢,玄學派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發起反擊。其間尤可注意的是,張君勱又在中國大學發表了一次演講《科學之評價》。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個方面的問題:形上、審美、意志、理智、身體。除身體外,前四者是心靈的問題,分為兩個層次:形上、形下。形下又分兩個方面:情意(審美、意志)、理智。科學主義注重於身體和理智,忽視了形上和情意。
此時,那位“暫時局外中立人”梁啟超也披掛上陣來,並成為玄學派的另外一員大將。他於5月23日作《人生觀與科學——對於張丁論戰的批評》,發表於《時事新報·學燈》。這篇文章要義有五:(1)對“人生”、“人生觀”的界說:“人類從心界物界兩方面調和結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們懸一種理想來完成這種生活,叫做‘人生觀’。”(2)對“理智”與“情感”的分辨:“人類生活,固然離不了理智;但不能說理智包括盡人類生活的全內容。此外還有極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是生活的原動力,就是‘情感’。”(3)肯定科學的作用:既然人生觀如張君勱所言的基於“觀察”,“觀察離得了科學程序嗎?”即便人生觀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要與理智相輔的。”(4)對科玄雙方都提出了批評:“在君過信科學萬能,正和君勱之輕蔑科學同一錯誤”,因為“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5)最終卻落腳到對情感與自由意志的歌頌。“生活的原動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現出來的方向很多。內中最少有兩件的的確確帶有神秘性的,就是‘愛’和‘美’。”“一部人類活歷史,卻什有九從這種神密中創造出來。”“‘科學帝國’的版圖和威權無論擴大到什麼程度,這位‘愛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遠保持他們那種‘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的身份。”
林宰平的《讀丁在君先生的〈玄學與科學〉》發表於《時事新報·學燈》,全文共八個部分:(1)抨擊了科學主義的酷似宗教的“排他”傾向、企圖“統一一切”的“野心”、“帶有殺伐之音”的霸道。(2)對“科學”和“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嚴格的區分,指出對藝術與人生固然可以使用科學的方法,但本身仍不是科學。(3)對丁文江的邏輯觀念提出批評。(4)從“心和物”的關係問題出發,對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論”、“唯覺主義”的經驗論原則進行了批判,說明科學主義以為根本的“經驗”原來是“靠不住”的東西。(5)對丁文江所確立的用來審查概念、推論的“兩條原則”、“三條方法”加以評說,批判丁文江的經驗原則。(6)捍衛張君勱關於“純粹心理現象”的觀點,認為它不僅在作為自然規律或“天然律”的“因果律”之外,而且在作為思維規律的“思想律”之外。(7)具體談了他對“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的看法:一方面,他贊成“科學有益於人生觀”;另一方面,他卻反對“人生為科學所支配”的觀點。(8)最後,林宰平表示:“科學我是相信的”;但是“別像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
甘蟄仙《人生觀與知識論》雖然力圖公允,其實應該屬於玄學派的。他談了六個方面的問題:“(1)人生之目的——良知之完成。”“我們為什麼活著?就是為完成我們做小孩時的一片赤心——生來的良心——而活著。”“(2)人生之途徑——到良知完成之路”在於“於可能的範圍內,妥為設法,使吾良知美滿實現。”“(3)人生之修養——致良知之工夫,不可不做;我知我行之真自由,不可不保持。”“(4)道德的自由之所從出——本體論中的自由論。其引伸之義,在肯定良心的自由,道德的自由。”“(5)由知識論略釋先哲學說——以知識論為從事研究或解決人生問題者所宜知故。”“(6)由人生觀略釋先哲之人格態度——以人格態度為從事建設新人生觀者所宜知故。”
針對唐鉞《一個痴人的說夢》,屠孝實發表了《玄學果為痴人說夢耶?》。在他看來,科學派中兩位大將,吳稚暉“僅謂玄學之提倡,無益於今日之中國”,“對於玄學之本身,未嘗有否認之意”;唯有丁文江“則直斥玄學為鬼物”,“然細讀丁君前後諸文,對於本體論之研究,亦未嘗否認之,且自稱為存疑的唯心論者。”由此確立其文的主旨:玄學決不可無。
菊農的《人格與教育》,發表於《晨報副刊》。此文立場是與張君勱一致的。他把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文明概括為兩大基本精神:個人主義,機械主義。此文的哲學觀可以說是一種“生命意志論”,認為宇宙的本體即“變”、“生活的創新”,而“自由意志便是中心的創造力”;“人生的目的便是完成他自己的人格以貢獻於大的全體;換言之,便是實現小己的人格以求超人格的實現。”
王平陵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的《“科哲之戰”的尾聲》,篇幅雖小,卻極有分量。此文將“科玄之爭”稱為“科哲之戰”,即科學與哲學的關係問題,是很有見地的。圍繞這個問題,他著重談了兩點:1.科學(實則科學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哲學)企圖排斥哲學是辦不到的。2.科學與哲學是一種對立互補的關係。
論戰進行到此時,這場論戰的兩本文集幾乎同時推出了:一本是汪孟鄒編輯、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另一本是郭夢良編輯、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的《人生觀之論戰》。兩書均於1923年12月出版發行,所收文章差別不大:《科學與人生觀》收文29篇,另有陳獨秀、胡適兩篇序;《人生觀之論戰》收文30篇,另有張君勱序。但兩書的思想傾向性卻是截然對立的:《科學與人生觀》代表了科學派的立場,突出體現在陳、胡二序上;《人生觀之論戰》代表了玄學派的立場,不僅體現在張君勱的序上,而且尤其突出體現在編排上:該書三編,甲篇收玄學派的文章,乙篇收科學派的文章,附錄則收其它文章。
論戰文集《人生觀之論戰》是代表玄學派的主張的,張君勱所作的序是對其關於“人生觀”觀點的更進一步闡述。他說明心理學、社會學和唯物史觀作為“科學”是不可能的,而尤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科學的社會主義”不以為然,認為其“公例”無定準,絕非科學。在他看來,“第一,科學上之因果律,限於物質,而不及於精神。第二,各分科之學之上,應以形上學統其成。第三,人類活動之根源之自由意志問題,非在形上學中,不能了解。”
論戰的另一種文集《科學與人生觀》則是代表科學派的主張的,而且,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另一個重要派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正式加入到論戰中來了。這個標誌就是陳獨秀為《科學與人生觀》作的序,以及書中收入的胡適《答陳獨秀先生》與陳獨秀《答適之》之間所展開的辯論。所以,文集的出版不是論戰的結束,而是論戰的深化。此所謂“深化”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理解:科學精神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與此同時科學主義傾向與唯物史觀相結合,更加勢不可當。
11月13日,陳獨秀應邀為即將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作了一篇序(以下簡稱“陳序”)。應邀作序的還有胡適,其序(以下簡稱“胡序”)作於11月29日;並附《答陳獨秀先生》。陳獨秀又於12月9日作《答適之》。兩篇答文一併收入《科學與人生觀》書中。這“兩序兩答”,是在陳、胡之間展開的關於科玄問題的對話。
陳序表明,他是同時要對玄學派、科學派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這就為科玄論戰當中唯物史觀派的立場定下了基調。他批評了玄學派的三個人物:批評張君勱舉出的“九項人生觀”;批評梁啟超的“情感超科學”的“怪論”;批評范壽康所謂人生觀的“先天的形式”。然後又批評科學派代表丁文江的所謂“存疑的唯心論”,認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張君勱走的是一條道路”;“其實我們對於未發見的物質固然可以存疑,而對於超物質而獨立存在並且可以支配物質的什麼心(心即是物之一種表現),什麼靈魂與上帝,我們已無疑可存了。”最後表明:“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由此,“唯物史觀派”旗幟鮮明地加入到科玄論戰之中。
胡序所涉及的問題更廣泛一些,著重正式提出了他的“科學的人生觀”或者“新人生觀的輪廓”,此即著名的“胡適十誡”:
(1)根據於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窮之大。
(3)根據於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著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據於生物的科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5)根據於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只有程度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
(6)根據於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也演進的原因。
(7)根據於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象都是有因的。
(8)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方法尋求出來的。
(9)根據於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物質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靜的,是動的。
(10)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凈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適的《答陳獨秀先生》與陳獨秀的《答適之》是科玄論戰中科學派與唯物史觀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鋒。胡文是對上述陳序的批駁,他區分了自己的“唯物的人生觀”與陳序的“唯物的歷史觀”:“(1)獨秀說的是一種‘歷史觀’,而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人生觀是一個人對於宇宙萬物和人類的見解;歷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見解,是一個人對於歷史的見解。歷史觀只是人生觀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觀是用物質的觀念來解釋宇宙萬物及心理現象。唯物的歷史觀是用‘客觀的物質原因’來說明歷史。(狹義的唯物史觀則用經濟的原因來說明歷史。)”“我們雖然極端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陳獨秀的答覆是:“‘唯物的歷史觀’是我們的根本思想,名為歷史觀,其實不限於歷史,並應用於人生觀及社會觀”;“唯物史觀所謂客觀的物質原因,是指物質的本因而言,由物而發生之心的現象,當然不包括在內”,但是“唯物史觀的哲學者也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
馬克思主義者最早正式對科玄論戰雙方作出批評的,是兩篇幾乎同時出現的文章,即上面談到的陳獨秀的《科學與人生觀·序》和鄧中夏的《中國現在的思想界》。
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於1923年11月24日發表在《中國青年》第6期上。此文雖然不長,其價值卻不容忽視。第一,他對中國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了一種異常清晰的勾畫,這種勾畫直到今天仍舊適用。第二,他運用唯物史觀的原理來對此格局進行了分析,尤其強調了論戰的階級鬥爭性質。第三,他談到了唯物史觀派與科學方法派之間的異同,強調了兩者的一致:“唯物史觀派,他們亦根據科學,亦應用科學方法,與上一派原無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們相信物質變動(老實說,經濟變動)則人類思想都要跟著變動,這是他們比上一派尤為有識尤為徹底的所在。”次年1月26日,鄧中夏又在《中國青年》第15期上發表了一篇《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提出:“我們應結成聯合戰線,向反動的思想勢力……向哲學中之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傅侗等包括在內)梁漱溟;……分頭迎擊,一致進攻。”
緊接著鄧中夏的,就是瞿秋白分別批判科、玄兩派的兩篇文章:《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駁張君勱》,《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駁胡適之》。《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作於1923年11月24日,發表於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此文針對玄學派的“自由意志”論,而集中討論自由與必然的關係問題。全文分五部分:(1)確認自然現象及社會現象的因果性。(2)區分“自由”與“意志”:意志是不自由的;自由在於探索並利用必然規律。“‘自由’不在於想象里能離自然律而獨立,卻在於能探悉這些公律;因為只有探悉公律之後,方才能利用這些公律,加以有規畫的行動,而達某種目的。因此所謂‘意志自由’,當解作:‘確知事實而能處置自如之自由’;若是否認因果律,就算自由,那真是盲目的真理了!人的意志愈根據於事實,則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據於事實,則愈不自由。”(3)談歷史的必然與有意識的行動:“那‘附條件的必然’是主觀的行動,‘障礙力的必然’是主觀的受動。至於‘因果的必然’才是客觀的解釋。”“歷史是人做的;當然,人的意向不能不是歷史發展的一因素。可是,人所做成的歷史偏偏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正因為其中亦有個‘必然’在。既有這一‘必然’,便有這‘必然 ’的果——人的某種意向。此種意向再回過去做社會發展因素。”(4)理想與社會的有定論:由意志而產生社會理想,但理想最終是社會歷史之必然性的產物,這就是歷史唯物論的決定論。(5)談社會與個性。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來說明個人意志。《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發表於1924年8月1日《新青年》季刊第3期。這篇文章是批判科學派、尤其是胡適的實驗主義的,其目的在於要說明:實驗主義不是真正徹底的科學,只是一種唯心論的改良派哲學;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徹底的“科學”、因而才是一種“革命哲學”。
1924年5月25日,陳獨秀又作了一篇《答張君勱及梁任公》,發表於8月1日《新青年》季刊第3期。這篇文章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以下幾點:(1)對於張君勱列舉的九項“人生觀”問題的駁難:“彙集各種事實而推求其由來,而為之說明,此非科學之方法而何?此方法倘有應用於說明及推求社會現象所由來之可能,則社會現象亦必為因果律所支配,尚何待贅言?社會科學亦得成為科學,又何待贅言?”(2)關於張君勱對於“事實”與“思想”之關係的觀點的辯論:“第一先有了物質的世界這個事實,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這個事實,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對象這個事實,然後思想才會發生,思想明明是這事實底兒孫,如何倒果為因,說思想是事實之母?”(3)關於梁啟超對馬克思主義的“兩個誤會”:一個是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機械的人生觀”;另外一個誤會是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宿命論”。
1924年7月29日,蕭楚女(署名“蕭初遇”)作了一篇《國民黨與最近國內思想界》,發表於8月出版的《新建設》第2卷第2期。此文全面評述了當時的思想界,其中談及“東方文化派”或“精神文明派”之反對科學、反對物質文明、反對工業,乃是出於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厭惡;卻是一種幼稚的、落後的觀念。
1924年還有一些關於科玄論戰的文章發表,例如謝國馨的《評吳稚暉的人生觀》,陳大齊的《略評人生觀和科學論爭——兼論道德判斷的普效性》,張顏海的《人生觀論戰余評》,等等。這些可以說是科玄論戰的“尾聲”了,並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進展;問題的解決只得俟諸將來了——可是這個“將來”至今似乎尚未來臨。
“科玄論戰”對中國唯物史觀派文化哲學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在“科玄論戰”中,唯物史觀派對形形色色的唯心論、二元論和不可知論的批判,宣傳了唯物史觀,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科學地解決人生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思想武器。人生觀論戰之後,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其二,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在論戰中對科學與玄學關係問題的解答,也明顯地表現出科學主義傾向。他們對科學主義思潮的支持、對唯物史觀的科學化的理解、對形而上學的拒斥,構成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無法剔除的解釋學背景。科學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影響,主要積澱和濃縮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之中。這主要表現在有關價值論的問題長期處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視野之外,“實踐”範疇始終未能溢出認識論、知識論的範圍,對辯證法的唯科學主義理解,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長期存在以自然主義和發生學的態度糾纏在作為物質總體的自然界的“先在性”問題等等。正是這種哲學詮釋的科學主義化,從而使得作為科學指導的理論長期落在實踐的後面。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隨著人們對馬克思哲學再認識的逐步深入,教科書體系所代表的科學主義解釋傳統受到了質疑和挑戰,從而導致對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的重新發現和創造性解釋,彌合了事實與價值、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兩分的鴻溝,以便應對世界範圍內的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對峙與互動,推進了唯物史觀派文化哲學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