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
美國公理會在華傳教士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年-1861年),新教美國公理會在華傳教士。美國馬薩諸塞州人。
1825年畢業於阿默斯特學院。1829年得安多弗神學院學位。1830年來廣州,從馬禮遜學習漢語。1834年與郭士立共同組織益智會,任中文秘書。1836年參與創辦馬禮遜教育會,並任該會通訊秘書。1838年開設博濟醫院。1839年任林則徐的譯員,曾到虎門參觀焚毀鴉片。1841年獲紐約大學神學博士學位。1844年任美國公使顧盛的譯員和秘書,參加訂立《望廈條約》。1847年出席在上海召開的《新約》翻譯代表委員會會議。1850年譯完后,繼而進行《舊約》翻譯,次年 2月譯就。1854年任美國公使麥蓮的譯員。1857~1859年擔任亞洲文會首任會長。
他曾創辦並主編《澳門月報》,刊載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和文化等資料。他主張用武力強迫清政府訂立不平等條約以打開中國門戶,從而使得當時民智未開的中國人可以接受正確的思想觀念;認為傳教士應不受清政府嚴厲的法律約束而深入內地活動。晚年主要從事《新舊約全書》新譯工作。1861年在上海去世。

脾治文
1812年,裨治文皈依我主;第二年加入了本地的公理教會,按受波特牧師(Rev. E. Porter)的指導。不久之後,裨治文開始對傳教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這種想要將福音帶到異教土地上的渴望使他下定決心放棄早年從事的農業生產,轉而投入傳教事業的準備工作中。裨治文在自己的家鄉按受基礎教育,在阿默斯特學院接受高等教育(1826年畢業);在安多福(Andover)神學院學習神學。
1830年2月19日到達中國,作為美國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裨治文受到了當時中國境內唯一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歡迎。裨治文不但自始至終致力於傳教事業,同時還積極投入所有為改善教友境況而實行的公益計劃。
1834年11月益智會成立后,他和郭實臘一同被任命為中文秘書;作為馬禮遜教育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他從1836年1月協會成立之初就擔任通訊秘書一職。
1838年2月中華醫學傳道會在廣州成工之時,他又被選為副會長。
1839年中英產生政治衝突繼而導致戰爭爆發后,裨治文移居澳門,之前一直居住在廣州的外國人商館中。
1841年7月14日,紐約大學授予裨治文神學博士學位。
1842年7月1日裨治文前往香港,9月接替德姆(Dem)先生成為馬禮遜教育協會主席。
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在香港召開了傳教士大會,討論《聖經》新譯本事宣,裨治文出席了每一場會議,他和憐為仁(Dean)一起受命在8月25日的會上就“Baptizo”一詞的中文譯名發表了意見,但在9月1日會上的報告中,他們表示將不再建議用任何譯名來表達該詞。
1844年2月,由顧盛(caleb cushing)擔任專使的公使團建期后,裨治文和伯駕博士被一同任命為使團秘書及隨團牧師。
1845年6月28日,裨治文在香港的殖民教堂同伊來扎·簡·吉列(Eliza Jane Gillet)女士結婚,7月3日返回廣州。9月裨治文夫婦二人去了一次香港,作為《新約》翻譯代表委員會的廣州委員,裨治文於1847年6月23日到達上海參加該委員會的會議。
從1847年7月1日會議開始到1850年夏天 《新約》翻譯工作完成,裨治文一直堅持出席委員會會議,接著他又被選為《舊約》翻譯代表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於1850年8月1 日成立,次年2月12日解散,之後,裨治文依舊留在上海從事《聖經》的翻譯工作,直至1852年2月3日他因健康原因同夫人一起乘坐“阿德來德號”(Adelaide)起程前往紐約為止。裨治文夫婦於6月16日抵達紐約; 10 月12日登上“野鴿號”(wild Pigegn)經合恩角和舊金山返回中國,1853年4月1日通廣州,5月3日抵上海。
1854年5月,裨治文以翻譯員的身份同遠征隊一起乘坐美國輪船前往正爆發起義的南京,繼而前往蕪湖。
1856 年他匆匆遊覽了福州,同年11月與夫人一起前往寧波旅行,裨治文還積極推動了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支會的成立,從該會成立之初的1857年他就被選為會長,並擔任這一職務直至1859年。從美國回來后,他把主要的一部分時間用於同克陛存牧師合作重新翻譯《聖經》,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天。
1861年11月2日,裨治文在自己的家中去世,他被埋葬在上海的墓地中,傳教士同人們為他樹立了一塊大理石碑以示紀念。
裨治文來華之初,在其頭腦中,中國人只是一個“簡單、落後和無知的拜偶像的民族”。但自從踏上中國的土地后,他所面對的異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使他的世界觀得以改變。他開始明白“這是一場對抗無知的現代化戰爭,決勝關鍵不僅是在於獲得屬靈的真理,也在於獲得屬世的知識”。同時他相信“教育是上帝用來提升人類心靈和解救人類脫離懲罰的一種方法”。這些觀念上的改變,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協調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
在裨治文和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實臘的推動與主導下,1834年11月,一個為促進華人認識西方文化的組織“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在廣州正式成立。他們的目標是“希望藉著和平的手段,促使中國不論是在商業、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全方位對外開放”。他們決意“以智慧作為炮火”,讓中國人不僅可以接觸到“現代的發現和發明所產生的最豐富的果實”,還可以認識西方國家的歷史和國情。
中國益智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廣中文書刊,藉此“開啟華人的思想領域”。除裨治文外,郭實臘和馬儒翰等宣教士,都有份參與撰寫文稿的工作。美國商人奧利芬,英國商人麥雅各(James Matheson)和佐威廉(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曾先後出任該會的會長,他們同時也是經濟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益智會已出版了七種刊物,向中國讀者詳細介紹“那在中國以外、正在改變中的世界”。後來,中國益智會亦在新加坡設立堅夏書院,出版中西書刊;同時承辦郭實臘主編的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5年1月,即馬禮遜逝世後半年,裨治文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以及一些在廣州的歐、美商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籌備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草擬章則等事宜,裨治文擔任該臨時委員會的召集人和書記。1836年9月28日,“馬禮遜教育協會”正式成立,裨治文被選為理事會執行秘書。他在成立典禮上致詞時說:為要完成馬禮遜對中國教育事業的未竟之願,該組織要在中國“興辦西式教育事業”,因為當“教育在中國普及化之後,全中國的人民將會受益,而我們的傳教事業最終也會成功”。從中可見該會宗旨之一斑。
1839年11月4日,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府“馬禮遜紀念學校”(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在澳門正式開學。第一期學生共有六人,皆為寄宿生。他們的學費、書費和食宿費等,均由馬禮遜教育協會全額提供。校長為撒母耳·布朗(Samuel Brown),他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且在紐約已有多年執教經驗。他的新婚妻子來華前也是一位教師,她願意與丈夫同心負起領導學校之責。
馬禮遜紀念學校以英語授課的科目有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化學、音樂和初級機械原理等,當然還設有聖經課程。該校學生雖因不習八股文章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但他們畢業后可進入香港的洋行充當買辦或譯員。
1845年9月,馬禮遜教育協會舉行第七屆年會,裨治文被選為會長。翌年,布朗校長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國養病之機,帶同容閎、黃寬和黃勝等三人前往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芒松學校(Monson Academy)進修。其中除黃勝因水土不服,生病輟學回國外,容閎與黃寬兩位均於兩年後從芒松學校畢業。容閎繼續前往耶魯大學深造,而黃寬則前往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黃寬苦讀七年後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在國外獲得醫學博士榮銜的西醫。他先後在香港的倫敦會醫院、廣州的惠愛醫院,以及博濟醫院服務,並於1867年擔任博濟醫院代理院長。容閎畢業回國后致力於推動留美教育,“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學生到美國讀書,以便學成后能改造中國,振興國運”。經過了十七年的努力,滿清政府終於在1871年接納了容閎的建議,派遣120名中國幼童,分二批到美國留學,容閎則被聘為留美學生監督。十九世紀后,容閎更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
1847年6月,由於裨治文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而馬儒翰於鴉片戰爭結束后不久病故,再加上其他理事們皆私務纏身,因此在舉行過第十屆年會後,馬禮遜教育協會便自動解散,而馬禮遜紀念學校也從此停辦。
裨治文攜妻伊莉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移居上海第二年,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每月召集學人聚會交流,並印行學報。不久,該會更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裨治文自任會長。
1850年4月,裨治文與夫人在上海創辦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開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從該校畢業的。1881年,由於美國公理會與美國基督教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之間發生分歧與衝突,裨文女中的部分師生轉到美國聖公會所辦的聖瑪利亞女校(St. Mary Girls’School),而裨文女校則被美國基督教女公會接管。1931年,該校以“裨文女子中學”之名向上海教育局註冊立案;1953年,中國政府予以接管,改名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學”;1966年“文革”開始后,取消女中,再次更名為“上海市第九中學”(今上海市黃浦學校)。
1838年2月,裨治文聯同美國公理會的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Peter Parker),以及宣教士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等人,在廣州發起組織“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該會成立的目的,旨在“呼籲歐美各國差會派遣更多醫生來華,藉行醫和開設醫院推廣福音工作”。當時參加成立典禮的有十多人,裨治文被公推為副主席。該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麥嘉諦(D. B. McCaetee)等在中國教會史和醫學史上重要的醫療宣教士,都曾經是中國醫藥傳道會的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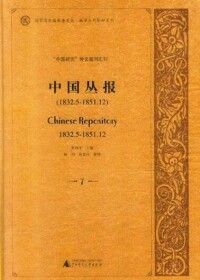
裨治文
《中國叢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等相關知識,也記述宣教士們在東南亞各地如新加坡、馬六甲、檳城、巴達維亞等城市的宣教活動。該雜誌除報導中國語言、文化、歷史、藝術、典制、風俗、宗教,以及迷信等內容外,且屢次刊文針砭時弊,力陳婦女纏足,以及吸食鴉片之危害;以致廢除婦女纏足成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標,並卓有成效。反對鴉片的文章,則前後刊載48篇之多,其中有15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為中國仗義執言,並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
《中國叢報》創刊於廣州,在鴉片戰爭期間曾一度遷至澳門和香港,戰後再遷回廣州。裨治文一直擔任《中國叢報》的主編,直到1847年他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時為止。其後,由宣教士貝雅各(James G. Bridgman)接任,但他只做了約九個月的時間便離職。從1848年10月起,美國宣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接任主編職務,直到1851年12月《中國叢報》停辦為止。《中國叢報》從創刊至停辦前後約20年,合共出版了20大卷。安德森於1851年7月信中說:“我認為《中國叢報》是關於現在進展中的中國宣教事業半世紀來最有價值的資料和意見的寶庫。我切盼我們所有重要的圖書館都擁有整套的本刊”。《中國叢報》不僅激發了西方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的宣教熱忱,更成為當時西方人探索與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後世則成為學者們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華宣教活動的主要資料來源。
廣州履任欽差大臣,頒令外商禁止販賣鴉片。其中林則徐是清廷少數有見識的官員之一,為要了解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歷史和風俗等情況,他特意聘用了四位華人為他翻譯外國書刊,並為他作傳譯,其中一位就是梁發的兒子梁進德。通過閱讀,林則徐始知裨治文,並很想與他結交並使用他。由於梁進德是裨治文的學生,所以林則徐曾派梁進德走訪當時仍在澳門的裨治文,請他前往廣州相敘,以及協助林則徐把一份照會交給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並請義律轉呈英女皇,期盼英女皇禁止種植罌粟,使鴉片商人無法毒害中國人民。裨治文雖然婉拒了林則徐的這項要求,但這份照會的全文則一字不漏地登載於1839年5月的《中國叢報》。裨治文還在報上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我們要告發英國,因她帶頭從事鴉片貿易。這個號稱是開明的、跟從基督的國家,竟給尚陷在黑暗中、信奉異教的中國種植和生產有害的東西,且以此(鴉片貿易)補充她的國庫。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顛倒。我們深信,這個以善行和信仰原則作為基礎的基督教國家,將會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相對地與她當有的責任和榮譽不符的事情——遭受長期的苦楚。(英國政府)在一個異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沒有原則,這隻會使他們(中國人)在反抗基督徒時落入不道德的試探中”。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將查獲英商的鴉片,在虎門銷毀。裨治文是應邀前往現場觀看銷煙的西方人士之一。在林則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摺中,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臣等欽遵諭旨,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在粵銷毀。……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無不肅然懷畏。並有咪唎堅之夷商經(King)與別治文(即裨治文)、弁遜(Benson)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游擊羊英科遷稟,求許入柵瞻視……”。
裨治文也將林則徐在銷煙現場所說的話,登錄在《中國叢報》上,其中有雲: “凡經營正當之貿易與夾帶鴉片之惡行確無牽涉之船隻,應給予特別優待,不受任何連累。凡從事私售鴉片之船隻,必嚴加查究,從重處罰,決不寬容。總而言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者不必掛慮,如常互市,必無阻撓。至於惡者,惟有及早離惡從善,不存痴想”。
此外,裨治文也不時在《中國叢報》上撰文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而在裨治文的巨著《廣東方言撮要》的第六章中,他更將林則徐頒布的禁煙令全文登載出來,可見他對林則徐的禁煙之舉是積極支持的。
1844年7月5日,中美雙方談判,清廷方面的代表為耆英和潘仕成;美方代表是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而裨治文與衛三畏則擔任顧盛的譯員,參與條約的擬定與翻譯工作,結果是“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其中第十七條款規定,基督教可在五個開放口岸設立禮拜堂並傳道。有論者認為該條款得以納入此條約中,與裨治文等人在中國民間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們與滿清官員之間的交情不無關係。由於耆英和潘仕成兩人,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皆為美國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的病人,通過接觸與交往,他們對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因此,當美方爭取在中國的傳教權益時,耆英和潘仕成並沒有提出反對,而且在他們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理由。故有論者認為,這些與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煙,與滿清官員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有間接的關係。
1852年2月3日,裨治文因病無法繼續工作,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乘搭“野鴿號”(Wild Pigeon)輪船離開中國,6月16日抵達紐約。這是他們在華工作三十年中,僅有的一次休假。在美國逗留期間,裨治文無法忘懷在中國的事業。因此,他只在自己的家鄉住了短短四個月的時間,便於同年10月12日離開美國,於翌年的5月3日抵達上海。隨即投入到譯經、寫作、學術及外交等工作。1854年5月,裨治文隨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從上海進入太平天國轄區考察,回上海后發表《調查報告》,否定太平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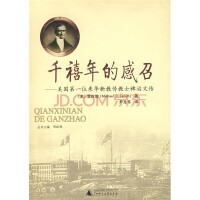
裨治文
1843年8至9月,西方各基督教差會的代表在香港舉行宣教士譯經大會,商討出版一部“不僅為各差會共同認可,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聖經譯本”。裨治文與波乃耶(Dyer Ball)二人,以美國公理會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大會決定對《新遺詔書》再次修訂,並且重新翻譯舊約。裨治文作為廣州/香港傳教區的翻譯委員,被委派加入專責小組,與宣教士憐為仁(William Dean)一起處理某些聖經專有名詞的翻譯。
1851年,裨治文與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宣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合作,翻譯舊約聖經,同時參與《委辦譯本》新約的修訂工作。1859年,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下,修訂后的新約聖經正式出版。1863年,《裨治文/克陛存舊約譯本》以四冊本的方式面世。可惜的是,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沒能看到此譯本的出版,因為他們已分別於1861年和1862年去世。
裨治文在其最後歲月里,還曾致力於將新約的歷史書卷翻譯為官話。可惜,該官話譯本不知何故,未能傳於後世,只能從其他宣教士的書信中,得知裨治文確曾從事這項譯事。1861年12月,在裨治文逝世后不久,美國公理會宣教士白漢理(Henry Blodget)曾寫信給他的差會說: “裨治文博士最近寫信給我,說他有六、七年的時間是常常忙於預備一部《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官話口語譯本。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他所遺留下來的這部分聖經的手稿”。此外,美國宣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其1864年7月30日寫給美國聖經公會的信中,也曾提到裨治文的這部官話譯本,是他與克陛存合作翻譯的。
裨治文不僅是美國第一位來華宣教士,也是第一位漢學家。他具有熱誠的奉獻精神,特別的語言天賦,以及對文化的透視力。他用中、英兩種文字從事著述,向中、西方介紹彼此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從而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
中文
1. 《真假兩歧論》(The Ways of Truth and Falsehood),在兩頁長的前言之後,作者講授並舉例說明了真假這兩種自然結果及其利弊。1837年在新加坡重版; 12頁。作者使用了“樂善者”這一筆名。
2.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5頁,1838年。該書分27個部分全面介紹美國曲情況,內容包括: 總論、國界、早期歷史、獨立、簡史、原住民、人口、自然風光、物產、農業、製造業、商業、政府、未健全的法律、宗教、語目、教育、文學、慈善事業、社會關係、風俗以及國防。1846年該書以《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為名在廣州重版,同樣是27個部分,共75頁,插有摺疊地圖,述及新近發生之事,后經作者大規模修訂后,於1862年以《聯邦志略》為名在上海出二版,城2卷,共107頁,包括3篇序目,凡例以及目錄第1卷包括總論、國界、地理特徵、道路、氣候和土壌、物產、早期歷史、獨立、完法、政府、法律、語目、教育和文學、宗教、遺書、商業、慈善事業和風俗習慣。第2卷則從地理角度簡要介紹了41個州和准州。
3. 《永福之道》(The Way of Eternal Bliss),5頁; 1843年,這是一份簡短的關於如何獲得真福的講道文,同時收錄了一篇與之相關的禱告文,作者署名: 美國人裨治文。
4. 《復活要旨》(Important Facts concerning the Life to come),9頁;香港; 1844年。
這份小冊子的正文內容要由《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31節至最後一節以及一篇簡短的禱告文組成,但序高長達5頁,作者署名“泰西裨治文”。
5. 《靈生詮言》(Disquisition on Spiritual Life),6頁; 1844年,這是關於《約翰福音》第三章第7節的講道文,末尾附一篇簡短的禱告文。作者署名同前書一樣,這份小冊子同上述兩種分別為同一套叢書的第10、 11和12號。
6. 《耶穌獨為救主論》(Jesus the only saviour),6頁。
7. 《新約全書》(New Testament),254頁;上海; 1863年。這是1851年裨治文空與翻譯的委辦本 《新約》的修訂本,由裨治文和克陛存合作完成,書中有一張印有讀者導言的插頁,在此之別,這一版本的各個獨工部分已先後出版,例如1854年出版了《羅馬書》等。
8. 《舊約全書》(old Testament), 1002頁;上海; 1863年。《舊約》這一譯本同樣為裨治文和克陛存的合作座果,裨治文去世后,克陛存繼續這一工作直至將其完成,該書共39章,分為4卷,每一卷都有3頁紙的讀者導言。
9. 《關於中國的書信》(Letters on china),18開本; 124頁;美國波士頓; 1840年。
英文
10.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廣州方言撮要》),8開本; XXXVI十698頁;澳門, 1841年。除了導言之外,全書共分為十七章,內容涉及藝術、科學以及其他各個方面,每頁分為三欄,左邊一欄是一連串的句言和段落,中間是中文譯文,右邊則是用羅馬字標註的中文讀音。書中有許多有價值且有意思的內容,但由於方言本,效用不免打了折扣,該書是作者在益智會的資助下著手撰寫的,這也是該機構贊助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此書詳細描述了中國人在文藝、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況。這部巨著面世當年,美國紐約大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貢獻,特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
11.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20卷;廣州; 1832~1851年。該月刊由裨治文在1832年5月創辦並擔任主編,18望年他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后,由布里奇曼牧師(Rev. J. G. Bridgman)接手編輯直至1848年9月衛三畏博士按管這一工作為止,不過自始至終裨治文部是這份刊物穩定而積極的撰稿人。在第4卷中,有他翻譯的《三字經》、《千字文》、《神重詩》以及《孝經》;第5卷中有《小學》的第一部分,第14卷有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譯文;第19卷則有徐光啟為耶穌會士所作辯護的譯文。
裨治文博士還積極負責地編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該刊發刊詞以及第一卷中孟子的一篇文章皆出自他的筆下,在波士頓出版的美部會會刊《傳教先驅報》上也刊登了大量他的書信。此外中國的報刊也常常能收到他的投稿。
裨治文夫人伊菜扎·簡·吉列是米爾納牧師(Rev. Dr. Milnor)教會的成員。1844年12月14日她和美國聖公會的一批傳教士一起乘坐“霍雷肖號”(Horatio)離開紐約,1845年4月24日抵達香港,6月28日且裨治文博士結婚。裨治文去世后,她於1862年經由英國經回美國。稍待振作,她便返回中國,計劃為促進北京的女子教育事業出些力。裨治文夫人於1864年6月到達北京。
其英文作品:
1.Daughters of China,or 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中國婦女:天朝的家庭生活素描》),1852年,該書在美國出版,扉頁上是裨治文夫人的一位中國學生的肖像。在格拉斯哥重版時未使用此肖像,12開本,189頁。這是作者在1852年短期回國時所寫的。
2.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先驅》),該書介紹裨治文的生平和事業,阿薩 ·D.史密斯(Asa D. smith)為其撰寫序言,8開本;xI十296頁;紐約; 1864年。這是1862-1863年裨治文夫人最近一次回美國時所寫。
1829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啟程來華,途中遇到了亨特,亨特成了他的中文啟蒙老師。這為裨治文的在華活動提供了方便。他到廣州后,一面行醫,一面辦起了英文書刊《中國叢報》,介紹中國的文化典籍和人情世故,還翻譯了一些中國私塾的教科書,這成了美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窗口。1841年,他出版了《中國廣東話註解文選》,長達728頁,用中英文兩種文字相互註解,簡明易懂,對溝通中英語言文字有開拓之功。1842年,在裨治文的努力下,成立了美國東方協會,以研究東方為宗旨。後來,英國皇家亞洲協會中國分會成立,裨治文也參與其中,貢獻尤多。鴉片戰爭時期,裨治文是美國人來中國探險的重要人物,他出版的《廣州市及其商業介紹》,是美國人關於廣州情況的最早著作之一。
1861年9月,裨治文罹患痢疾,以致10月舉行的皇家亞洲學會會議,他都不能出席。延至11月2日,終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終年60歲。自其神學畢業應召來華,歷時30年之久。他的突然離世,令人深感震驚。其摯友衛三畏從澳門寫信給伊莉莎說:“當我細讀你寄來的幾封信,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數天對他的情況所作的描述時,那有關過去的種種回憶,都湧現在我的腦海中。裨治文與你,每一天都在我的心裡。他是我親愛的朋友——為他的存在,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夠永遠與他在一起享受上帝。……他那不屈不撓的堅忍和那恆久不變的愛心,時常鞭策著我,要我以他作為學習的榜樣”。裨冶文逝世后,伊莉莎返回美國一段時間。1864年,伊莉莎在北京燈市口創辦了貝滿女校,以紀念亡夫裨治文。
裨治文是一位富有遠見的宣教士,他不僅有奉獻的精神和事奉的熱誠,更知道語言和文化對宣教工作之重要。他經常找機會與在租界內工作的中國人聊天,藉此操練中文會話。有時甚至冒著被捕的危險,向他們傳講福音。經過一年多時間,裨治文的中文有了顯著的進步。除語言學習外,他還注重對中國文化、宗教及習俗之研究,為的是“將人的思想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后10:5)。
斯人去矣,但裨治文在世時為中國社會和人民所作出的貢獻,為後人所記念。他不僅把基督福音之光帶到中國,也以真理和科學啟迪了中國社會。他一生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不愧為溝通中西方文化的“搭橋人”(Bridge-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