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陵
向世陵
向世陵,1955年生,四川仁壽人,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儒家哲學和儒釋道關係研究。中國哲學史學會《中國哲學史》雜誌副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執行編委、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北京市哲學學會理事
A 法學士(1982): 西南師範大學政治系(哲學專業)
B 哲學碩士 (1987):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
C哲學碩士 (1993):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
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 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6.12
中國學術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 2004.12
寫給大眾的中國哲學(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0
《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中國哲學的“問題”光明日報 2003.1
“性與天道”問題與宋明理學分系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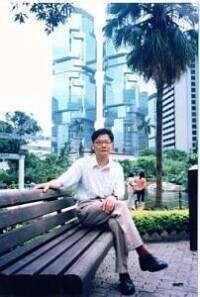
向世陵
中國文化氛圍中的人權考量 中山大學學報 2005.1
儒佛之際與宋初性無善惡說 東嶽論叢 2005.1
“生之謂性”與二程的“復性”之路 中州學刊 2005.1
張載“合兩”成性義釋 哲學研究 2005.2
程學傳承與道南學派 社會科學戰線 2005.2
石峻先生《略論中國人性學說之演變》研究 中國哲學史 2007.1
中國人民大學向世陵教授訪談錄
採訪時間:2011年5月29日
採訪地點:山東大學哲社學院中國哲學教研室
採訪者:趙炎峰 崔朝輔 訪談整理(中國哲學2008級博士研究生)
向世陵教授簡介:向世陵,四川仁壽人,1955年生,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教學培訓部主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中國哲學史》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北京市哲學學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執行編委。主要從事中國儒家哲學和儒釋道關係研究。主要專著有《儒家的天論》、《中華哲學精蘊》、《〈訄書〉選注》、《善惡之上--胡宏·性學·理學》、《中國哲學範疇叢書·變》、《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中國學術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寫給大眾的中國哲學》(主編)等,另有合撰著作多部。主編《中國哲學智慧》、《智慧的故事》等系列教材,承擔等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
向世陵教授是國內知名中國哲學研究專家。5月28日,向教授受邀來我院主持2011屆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畢業論文答辯工作。向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淵博的學識、儒雅的風度給全體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答辯工作結束后,向教授不辭工作和旅途的勞苦,於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採訪,通過自身經歷向我們介紹了如何進行哲學的學習和研究,並對中國哲學的一些前沿問題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現將對向教授的訪談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一、興趣是學習和科研的嚮導
我與哲學的聯繫起於文革時期。1973年,我在工廠當工人,正值“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的高潮。毛澤東主席提倡讀四本書,都是中國哲學方面的。其中包括楊榮國先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先生的《論孔丘》、馮天瑜先生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我接觸到這四本書以後,慢慢對中國哲學產生興趣。後來調到地委當通訊員,接觸到為幹部印刷的《中國哲學史》和《歐洲哲學史》。恢復高考后,我於78年考入西南師大政治系哲學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國語言大學,在那裡工作了兩年。84年考取研究生(中國哲學專業)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留校,一直工作到現在。我最早讀的哲學書籍就是關於中國哲學,不管是批判也好還是其他的,都使我對中國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就一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喜歡中國文化,對中國哲學有著由衷的愛好和體悟,這對我以後從事的研究工作很有助益,可見興趣對於學習和科研是非常重要的。
二、哲學與生活息息相通
我們這代人的經歷決定了我們的人生體驗比較豐富。我是屬於樂觀派的,比較容易看到生活中積極進步的一面。人生和生活總是有順利的時候,也有不順的時候,就象海上的波浪,有起有浮,這個問題會始終伴隨著我們的一生。面對不順利的事情,我們要學會坦然接受;順利的時候也不要得意忘形、趾高氣揚,時刻保持心態的平和,這對於中國哲學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一方面很多事情要努力去做,另一方面心態也要平和一點,這樣才能夠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現如今社會上存在一些矛盾,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要學會關照生活,關照自我。孟子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前半句做不到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做到後半句,獨善其身。不管什麼時候,自己把自己這一塊兒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分,同時儘力地為社會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培養學生,還是自己讀書、寫文章。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要處變不驚,坦然地接受生活,接受自己。這就是做人和做學問的相通之處。
三,對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與中國哲學未來走向的反思
2000年左右學界開始重新提出“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我在頭兩三年還對這個問題有所關注。2000年下半年我到德國時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德國漢學界的中國哲學研究》,介紹了一些德國及歐洲漢學家對中國哲學的看法。再往後學界熱炒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反而對這個問題失去了興趣。就這麼一個問題,再討論什麼“合法”和“不合法”就沒什麼理論和實際意義了。糾結於這些問題對哲學的發展和前進起不到什麼作用。這與二十世紀初的關於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相比,在理論上沒有什麼前進,只是把同樣的問題重新擺在桌面上。對學術史的回顧、總結是可以的,但它不是一個推動哲學發展的動力。在現今的社會思想文化背景下,再過分地強調這個問題,把它擴大化進行炒作,並沒有太大的價值與意義。我的觀點是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哲學界的一個百年反思,反思當時一些哲學概念的引入,以及中國人用西方哲學範式來整理傳統思想資源,建設中國哲學這樣一個新學科等問題。它的意義就在於此。如果過分將這個問題擴大化,想以此來證明中國文化的偉大,反而是不大恰當。這個問題的意義本來沒有那麼大。後來人大有一個通識課的教材叫《中國哲學智慧》,是由我來主編的,在概論裡面還對西方中心論進行了批評。黑格爾當時對中國哲學的否定,前幾年德里達到中國講學,西方哲學家本身的觀點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黑格爾認為西方哲學是對古希臘以來哲學思辨精神的總結,認為哲學思辨是一個普遍性的標準,拿這個普遍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思想,顯然缺乏應有的主體性,不足以作為哲學思想來討論。不過後來到德里達的時候,問題就發生了變化,隨著中國國際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們開始講哲學的特殊性,已經脫離了西方中心論的束縛。
我認為這個問題只是一個名稱和表示的問題,中西哲學有各自不同的特性,面臨的社會和思想對象和問題也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間也有一些共性。這是一個特殊性和普遍性關係的問題。這兩年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轉換為學界對過去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反思,使得這個問題具有了較深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人們開始考慮如何把哲學向前推進。到現在為止,人們開始承認中國哲學具有自己的特點,西方哲學中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方法也可以為我們所借用,不能完全排斥。西方哲學的一些概念,比如說“本體”、“本原”、“形而上”,中國哲學對這些概念的運用恰不恰當,我去年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哲學的“本體”概念和“本體論”》,專門探討這個問題。中國哲學原來就有“本體”這個詞,它最初是多義的。西方哲學中的“本體”一詞的涵義也是多樣的,不是一個固定和僵化的概念。嚴格來講西方哲學所謂的“本體”有好多種涵義。中國哲學中的“本體”概念也是有一個逐步孕育、發展的過程,涵義是非常廣闊的,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對於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我不贊同那種中國哲學挽救世界的觀點,即所謂以後西方哲學都不行了,挽救世界,要靠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不可否認,儒家哲學也有自身不可逾越的消極作用,如對血緣家族的盲目推尊和尊卑上下的過度強調等。當然我也不贊成一味貶低和排斥中國哲學的做法。文明其實有其內在的共通性,各種文明也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特色,正確的做法還是應該取長補短,相互融合。哲學作為文明世界的精神產物,尤其應該如此。至於以後世界哲學到底呈現出一種什麼狀態,我們很難估量。但是多民族的文化交融、文化創造這個主流不會改變。
四、論易學在宋明理學發展中的地位
我最近幾年主要研究易學與理學方向的問題。易學在宋明理學的發展過程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周易》作為五經之一,是五經中真正能從形上思維層面發揮的經典。《易傳》講“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開始了對天道的探討,兩漢時期,正式以《易》學為核心展開了天道與人道關係的對接,魏晉時期,隨著王弼掃象,《易》學趨於玄化,流於空談;漢唐時期,由於佛教哲學的傳入,儒學不彰,人們忽略了發揮五經中心性哲學的意蘊,這對後世儒家來說轉化為一種刺激和激勵,迫使後來學者注重在心性哲學層面去加以挖掘、開拓,以對抗佛學。其實關於“性與天道”的問題一直是儒家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魏晉時期人們曾對這個問題有所反思,“性與天道”到底是什麼?後來的學者一方面要立足於儒家經典本身,另一方面,需要對經典作出新的詮釋。只有對經典作出新的詮釋,才能回應佛教心性論的挑戰。在這個時候,《周易》正好充當起一種思想資源的作用。因為儒家其他的經典,如《尚書》主要是征伐史實的記載,能夠被理學家所借鑒的只有“人心”、“道心”等部分思想;《詩經》中能被運用的也只有少部分篇章和詩句,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禮記》的作用會大一些,但是也僅僅局限於《樂記》、《大學》、《中庸》等個別篇章;《春秋》在宋初思想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主要作用還在於歷史方面,哲學思辨性不夠。綜合起來,就全書來看,哲學意義最重要的就是《周易》。宋初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有關於《周易》的專著。從宋初三先生經過司馬光到北宋五子都十分重視對《周易》哲理的闡發。北宋五子中周敦頤有《太極圖說》和《通書》,張載有《橫渠易說》和《正蒙》,程頤有《伊川易傳》,邵雍關於象數學的專著和貢獻就更多了。易學作為一種思想資源,作為一種思辨的智慧結晶,集中體現了儒家哲學精神,對理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往後到胡瑗、胡宏,到東南三賢、朱熹、呂祖謙、張栻,都對《周易》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理學的產生與儒家對易學資源的再造是一個同一的過程。在對易學哲學的再造過程中,儒家學者結合佛老的思想,建立起理學的思想體系。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就是以《周易》的話為結尾的。
五、回到經典本身,探尋問題根源
搞學問,首先還是要多讀書,多思考。要多讀一些經典原著。雖然說像《尚書》、《春秋》等書籍中哲學思辨的東西並不是很多,但是當你去用心研讀的時候,就會發現許多值得我們共同思考的問題。經典是一個思想資源,可以不斷地被我們詮釋、再造。舉一個很簡單而又尖銳的例子,我們經常講孟子的“性善論”。孟子認為“惻隱之心”是不證自明的,從“惻隱之心”中能推導出人性本善。他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叫“孺子將入於井”:設想有一個孩子快要掉進井裡的時候,旁邊的你總是會一把拉住不讓他掉進去。孟子認為這個舉動第一不是想藉此討好孩子的父母,第二不是要在鄉鄰朋友中博取好的名聲,第三也不是討厭那孩子驚恐的哭叫聲,它就是出自人的本能。在“性善論”的最初階段,孟子這個思想講的非常好。可是如果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問題的所在:當你讀過《禮記》、《尚書》之後,你會發現還有另外的問題:現實社會的複雜性。如果承認人人皆有惻隱之心,承認性善論,那麼現實社會中的“惡”從何來?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後來南北朝和隋唐的思想家們提出來:當你用“惻隱之心”把孩子救出來之後,就會問“這是誰家的孩子?”如果有人告訴你這個孩子的父母就是你的殺父仇人,你還會不會去救他?你會不會產生為了報仇而不去救人的想法?《尚書》、《禮記》中有關於報仇、復仇的明文記載:“父母之仇,不與同生;兄弟之仇,不與聚國;朋友之仇,不與聚鄉。”在現實社會中間,面對一些現實的社會問題,只靠最初的“善”的“閃念”的效力是不夠的。面對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主張“性善論”會面臨很多問題。所以後來張載、朱熹才會提出“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分,為的就是解決孟子“性善論”在面對複雜社會現實問題時的尷尬與困境:人一方面具有先天稟賦的“善”的根源,另一方面也受後天“氣”的稟賦不同的影響,呈現出“惡”的傾向。作為一個現實的人生,由於每個人所稟賦的後天氣質不同,因此呈現出的善惡傾向也是相差不等的。人們重在通過後天的自覺,排除氣秉的各種污染,通過一番艱苦努力,才可能走向“善”。在這個過程中,在先天“天命之善”的基礎上,主體自身的修養和自覺的作用即後天的作用更加明顯。所以當你讀到更多的經典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問題的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問題。如果你沒有讀過《尚書》,你會認為周公是一個仁德的聖人。可是當你去看《尚書》原典的時候,裡面記載更多的是關於周公南征北戰的記載,他主要在征伐諸侯、賓士叛亂。不解決這樣的問題,他就無法安頓自己的仁德,更不可能將仁德思想推廣開來。歷史的發展就是在這樣尖銳複雜的變革中走過來的。當你讀到更多經典的時候,你會對歷史和思想發展的複雜性有更深切的理解和體會。
在學習和科研過程中要有自覺的問題意識,而問題的發現要通過對經典不斷的研讀和反思中獲得。有了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書,會發現一些新的問題。要解決新的問題,必須又要回到經典本身。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過程。問題意識不是憑空產生的。問題的提出的另一方面來自於對社會現實的反思。要通過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和深入思考,才會發現別人所沒有發現的問題,才能想別人之所不能想,做別人之所未作,提出別人所沒有發現的思想和理論。換言之,多讀書,多思考,在此基礎上,才能有所創新。除此之外,別無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