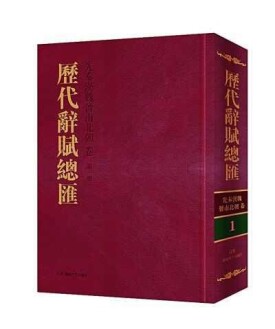歷代辭賦總匯
歷代辭賦總匯
《歷代辭賦總匯》是由湖南文藝出版社歷時20年出版的辭賦大典,總字數達2800多萬字,是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全書共26冊,收錄先秦至清末7391位作者的辭賦30789篇。
《歷代辭賦總匯》是由湖南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辭賦學會第一任會長馬積高主編,項目集聚了國內近60位頂尖賦學專家進行點校。
該書從1994年進入湖南文藝出版社編輯程序,至完成出版,歷時20年。
該書收集廣博,凡題目標明“辭”或“賦”、“騷”者,一併收入;考訂精審,編者糾正了前人編輯中的一些錯誤,對作者的時代與作品的歸屬,做了精細的考量;資料詳備,配有作者小傳及作品校記,以備讀者了解相關知識。
南京大學教授、中國辭賦學會會長許結認為,《歷代辭賦總匯》是古典辭賦的集成,是首次全面而系統地展現“中國賦”的風采,為賦學研究與辭賦愛好者提供了最完整的創作庫存。
全國首家賦社彭城賦社專家普遍認為,《歷代辭賦總匯》是古典文學的集大成者,叢書的出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必將被載入史冊。
馬積高(1925—2001.5),男,湖南衡陽人,原為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賦學專家。
賦在漢代興起以後,歷代都有賦體文學作品的彙集編輯,規模大的,當屬清代康熙年間彙編的《歷代賦匯》和光緒年間初版的《賦海大觀》,前者收入先秦至明代的賦作4161篇,後者則收12265篇。而《歷代辭賦總匯》收集之廣,編輯之精,分類之明,遠遠超越前人,可謂古典文學出版方面空前絕後之舉。
辭賦是繼《詩三百篇》之後首先繁衍起來的一種文學體裁。它古老而又典雅,最具有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對我國文學的發展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一,中國古代文學中許多傳統的題材、主題是在賦中首先出現或加以開拓的,如山水、行旅、田園隱居、遊記、宮怨、宮殿室宇、亭台樓閣等,無不是率先在辭賦中發展起來然後再蔓延到其他文學種類去的。此外,如田獵、歌舞、詠物等,雖或始於《詩經》、《楚辭》,然加以開拓使之成為普遍注意的題材的也是由於漢以後的賦。
第二,最初對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文物制度、生活習俗作綜合性的藝術概括,最初對當代重大的政治事變作出較全面的綜合性描述的也是賦。如揚雄《蜀都賦》、班固《兩都賦》、李諧《述身賦》、庾信《哀江南賦》等都是這種宏偉的結構。
第三,具有悠久歷史的我國古代的諷諭文學和通俗文學也是最初出現於辭賦之中。從宋玉的《風賦》到阮籍《獼猴賦》、孔稚珪《北山移文》,至唐賦而發展到高峰,其流至清代而不絕,構成我國諷諭文學的優秀傳統。俗賦從王褒《僮約》始,到曹植《蝙蝠賦》,到南朝宋袁淑的一些俳諧文,到唐代的敦煌俗賦,構成通俗賦的一脈,其流及於清代蒲松齡的某些賦。這種俗賦是唐以來大量湧現的說唱文學的源頭,因為變文、話本等那種韻散結合的形式就是從賦的問答體蛻變而來的。而說唱文學對中國戲曲和小說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俗賦可以說是中國俗文學之祖。
第四,文學藝術的描寫(包括對客觀事物和作者主觀感情的描寫),由簡單到複雜,由概括到細膩,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屈宋賦,到漢賦,到魏晉南北朝賦,其中描寫的細膩精確和手法的變化多樣,是駕於同時期的詩文之上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當時的辭賦哺育了同時代和唐代的詩人。
第五,辭賦對中國文學的語言也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國的語言大體上有一個由單音詞為主到逐漸增加雙音詞的過程。屈宋賦在這一演進過程中也是一個飛躍。漢以後的賦中更是大量增加,特別是許多雙聲疊韻形容詞的首先出現多在賦中,然後才擴展到詩文。
此外,如在造語上注意煉動詞和注意排偶等,也始於賦或首先在賦中得到發展。我國的一種特殊文體——駢文就是在辭賦的母體中孕育發展起來的。於此,可見辭賦對我國文學發展的影響至深且遠。賦之所以在許多方面帶有開創性,這是由於它是繼《詩三百》之後率先產生的一種文學體裁,是兩漢乃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作家精力之所萃,它自不能不負擔起這一承前啟後的任務。
而且,賦是一種體式多樣化的文體,較之詩文更容易表現作者多方面的才華和修養。因此,能否作賦始終被看成是衡量一個作家的文學才能的一種重要尺度,是他們抒情達志的一種重要方式。他們認為,辭賦創作是一個作家的學識和才情的表現,因此,十分重視。司馬相如以創作了《子虛賦》而深得漢武帝的讚賞,被召至京師;又以創作《天子遊獵賦》而被任為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曹植以年紀輕輕卻能創作《銅雀台賦》而大得曹操賞識,“特見寵愛”,“幾為太子者數矣”(《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左思作《三都賦》,“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文苑傳·左思傳》)北魏時,邢邵、魏收、溫子升並稱為北魏三大家。但“收以溫子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他以能作賦而傲視邢邵與溫子升(《北齊書·魏收傳》)。杜甫向別人誇耀他的文學才能也是說“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韻》),把賦的創作還放在詩之前,可見他對作賦的看重。的確,創作賦,特別創作大賦,要堆砌大量的雙聲疊韻聯綿詞,要使用很多的連邊字,要了解所描寫的事物的有關史實,要熟悉它的有關特點,要“苞舉宇宙,總攬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這就非博學不可。大賦要求“散五彩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西京雜記》卷二),這就非有才情不可。既要博學,又要有才情,必須二者兼備,才能創作辭賦。所以,古代有名的大賦作家,大都是著名的大學者,大史學家,大文學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蔡邕、曹植、庾信等,便是這樣一流人物。辭賦受到人們的重視是理所當然的。故古代作家無不嘔心瀝血、花時費日地去經營大賦。據記載:“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西京雜記》卷二)桓譚說:“余少時見揚子云之麗文,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小事而作小賦,用思太劇,而至感動發病,彌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上甘泉,詔令作賦,為之卒暴,遂團倦小卧,夢五臟出,以手內之。及覺,大少氣,病一歲。”(《新論·祛蔽》)張衡作《二京賦》,“精思附會,十年乃成”(《後漢書·張衡傳》)。左思作《三都賦》,“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晉書·文苑傳·左思傳》)。可見他們對能作賦的鄭重。從《文選》開始,特別是唐宋時期的作家,他們編總集、別集,一般都是首列賦、次列詩文,《盧照鄰集》、《楊炯集》、《李太白全集》、《杜工部全集》、《皮子文藪》、《唐文粹》、《文苑英華》等無不如是。也可見古代作家對賦的重視。
正因古代作家如此重視辭賦,故輯錄者代有其人。早在西漢成帝時,劉向校中秘書,即輯錄屈宋諸人之作及漢人部分擬騷之作,編為《楚辭》16卷,東漢王逸更益以己作《九思》,為《楚辭章句》17卷,凡收作家10人,作品73篇。至於賦,班固《兩都賦序》說:“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劉歆編輯《七略》,其《詩賦略》即著錄西漢一代之賦。班固撰《漢書》,“刪其要”而作《藝文志》,著錄西漢賦作家78家,作品104篇,可惜今存者十不及一。
魏晉南北朝是辭賦輯錄的鼎盛時期,《隋書·經籍志》著錄的“七”和“對問設論”體賦集有:《七集》10卷,謝靈運撰。《七林》10卷,梁12卷,錄1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37卷,錄1卷,亡。《七悟》1卷,顏之推撰。梁有《弔文集》》卷,錄1卷,《弔文集》2卷,亡。《談論集》2卷,劉楷撰。梁有《談論集》3卷,東晉人撰。《客難集》20卷,亡。
著錄的賦集有:
《賦集》92卷惠謝靈運撰。梁又有《賦集》50卷,宋新渝侯撰;《賦集》40卷,宋明帝撰;《樂器賦》10卷,《伎藝賦》6卷,亡。《賦集抄》1卷,《賦集》86卷,後魏秘書丞崔浩撰。《續賦集》19卷,殘缺。《歷代賦》10卷,梁武帝撰。《皇德瑞應賦頌》1卷,梁16卷。《五都賦》6卷,並錄。張衡及左思撰。《雜都賦》11卷,梁《雜賦》16卷。又《東都賦》1卷,孔逭作;《二京賦音》2卷,李軌、綦毋邃撰;《齊都賦》2卷並錄,左思撰;《相風賦》7卷,傅玄等撰;《迦維國賦》2卷,晉右軍行參軍虞干紀撰;《遂志賦》10卷,《乘輿赭白馬》2卷,亡。《述征賦》1卷《神雀賦》1卷,後漢傅毅撰。《雜賦注本》3卷,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1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2卷,晁矯注《二京賦》1卷,傅巽注《二京賦》2卷,張載及晉侍中劉逵、晉懷令衛權注左思《三都賦》3卷,綦毋邃注《三都賦》3卷,項氏注《幽通賦》,蕭廣濟注木玄虛《海賦》1卷,徐瑗注《射雉賦》1卷,亡。《獻賦》18卷。《圍碁賦》1卷,梁武帝撰。《觀象賦》1卷。《洛神賦》1卷,孫壑注。《枕賦》1卷,張君祖撰。《二都賦音》1卷,李軌撰。《百賦音》10卷,宋御史褚詮之撰。梁有《賦音》2卷,郭征之撰;《雜賦圖》17卷,亡。
這些著作,新舊《唐書·藝文志》尚有著錄,但宋以後多已亡佚,今已難以復見矣。
唐人專為輯錄整理的賦集今未見,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者,僅有下列幾種:劉楷《設論集》3卷,謝靈運《設論集》5卷,卞氏《七林集》12卷,顏之椎《七悟集》1卷。這些書卷數雖與《隋書·經籍志》不符,而書名皆見《隋志》,蓋承前人之遺。但唐人所輯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皆多收辭賦。雖或系節錄,至今為研究者所資。《文館詞林》收賦亦多,惜今多佚失。然其殘膏剩汁,猶可沾溉後人。
宋代又是辭賦集結的重要時期。輯錄騷賦較多的著作有:《文苑英華》。該書《雜文·騷》收有從梁至唐的擬騷之作5卷,收騷體賦42篇,計有梁元帝《秋風辭》、范縝《擬招隱士》、盧照鄰《五悲文》5首、《釋疾文》3首、《獄中學騷體》、岑參《招北客文》、韓愈《訟風伯》、柳宗元《吊屈原》、《訴螭》、《哀溺》、《憎王孫》、《逐畢方》、《罵屍蟲》、《招海賈》、沈亞之《文祝延》、《為人撰乞巧文》、《湘中怨解》、陸龜蒙《迎潮送潮曲》2首、劉蛻《憫禱詞》、《吊屈原辭》三章、皮日休《祝瘧疫文》、《九諷系述》九首、《反招魂》、《悼賈》等,這是繼《文選》之後收錄擬騷賦較多的著作。其《雜文·問答》收有蕭統《七契》,蕭綱《七勵》,何遜《七召》,盧照鄰《對蜀父老問》,駱賓王《釣磯應詰文》,韓愈《進學解》、《釋言》、柳宗元《晉問》、沈亞之《進學解書對》等9首作品。
《宋史·藝文志》著錄有晁補之輯《續楚辭》20卷,《變離騷》20卷。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續楚辭》20卷,收有“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變離騷》20卷,“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十九十六首”。二書《四庫總目》已不見著錄,不知已佚於何時。朱熹據《續楚辭》與《變離騷》,輯有《楚辭后語》六卷,收有自荀況《成相》至宋呂大臨《擬招》共28位作家的52首作品。可見這又是騷體賦的一次較大的集結。
宋人對賦的輯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據《宋史·藝文志》,宋人輯錄的辭賦總集有:徐鍇《賦類》二百卷,目一卷。《廣類賦》25五卷。《靈仙賦集》2卷。《甲賦》5卷。《賦選》5卷。江文蔚《唐吳英秀賦》72卷。桂香賦集》30卷。楊翱《典麗賦》64卷。《類文賦集》1卷。謝璧《七賦》1卷。許洞徐鉉《雜古文賦》1卷。王咸《典麗賦》93卷。李祺《天聖賦苑》18卷。
此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集部總集類》著錄有《后典麗賦》40卷,云:“金華唐仲友與政編。仲友以辭賦稱於時。此集自唐末及本朝盛時,名公所作皆在焉,止於紹興間。先有王戊集《典麗賦》93卷,故此名《后典麗賦》。王氏集未見。”又著錄有《指南賦箋》55卷,《指南賦經》8卷,云:“皆書坊編集時文,止於紹興以前。”
上述辭賦總集至《四庫全書》均不見著錄,可見亡佚已久。
金元時期收錄騷體賦的著作有兩部:一為蘇天爵《元文類》,該書於第一卷“賦”后列有“騷”一目,收有劉固《白雲辭》二章,袁桶《悠然閣辭》、《垂綸辭》、王士熙《雲山辭》共《首。一為祝堯《古賦辨體》。該書卷九《外錄上·后騷》目下錄有宋玉《招魂》、賈誼《惜誓》、庄忌《哀時命》,淮南小山《招隱士》,揚雄《反騷》,韓愈《訟風伯》、《享羅池》,王安石《寄蔡氏女》,黃庭堅《毀璧》,邢居實《秋風二疊》;於《騷》目下錄有漢武帝《秋風辭》,息夫躬《絕命辭》,陶淵明《歸去來辭》,黃庭堅《濂溪辭》,楊萬里《延陵懷古辭》,皆為擬騷之作,而祝堯將其收入《古賦辨體》,作為古賦的一個支派。
金元時期賦的輯錄,錢太昭《元史·藝文志》著錄有下列數種:郝經《皇朝古賦》1卷。虞廷碩《古賦準繩》1卷。祝堯《古賦辨體》8卷,《外錄》2卷。《元賦青雲梯》1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有:郝經《皇朝古賦》1卷。馮子振《受命寶賦》1卷。虞廷碩《古賦準繩》10卷。佚名氏《古賦青雲梯》3卷。《古題賦》10卷,又《後集》6卷。
這些賦集,《四庫總目》大都不加著錄,今存者唯《古賦辨體》、《青雲梯》二種。
收錄元賦最早的著作為《元文類》。該書卷一“賦”選錄有元賦作家6人的6首賦。收錄金、元賦最多的為《歷代賦匯》,收有金元作家137人,賦338首。
明代收集騷體賦的總集有蔣之翹《續楚辭后語》,附蔣之翹所刊朱熹《楚辭后語》之後,收有明人騷賦如劉基《思歸引》,方孝孺《絕命辭》,王達《琴操》,郭愛《自哀》,李夢陽《省愆》、《吊申徒狄》、《君猶夷》、《騁望》,何景明《蹇賦》、《九詠》、《倚柱操》,徐貞卿《漢反騷》,孫一元《屏之山》,王廷相《吊時賦》、《巫陽辭》,陸深《春山辭》,王世貞《少歌》,盧桶《幽鞠》、《放招》,周九四或《今已矣》,黃道周《乘桴》、《廣引》,蔣之翹《攘詢賦》、《讒賦》、《行路難》、《吊屈原》等,共15位作家的26篇作品。程敏政《明文衡》有“騷”一卷,收有宋濂《思美人》、《孤憤辭》,詹同《題王子充琴邊秋興圖辭》,胡翰《吊董生文》、《憫淑文》,劉基《懷龍門辭》、《九嘆》九首,王禕《招遊子辭》,高啟《吊伍子胥辭》,蘇伯衡《雲林辭》,方希古《吊茂陵辭》,楊士奇《退庵辭》,胡儼《辭劍閣辭》、《冰雪軒辭》,周敘《吊余青陽李同州詞》,劉定之《竹坡辭寄金川蕭樂善》等12位作家的16篇作品。別集有黃道周《黃漳浦集》卷36“騷賦”一卷,收騷6首,凡62章。
明人騷賦之成卷帙者還有:《明史·藝文志》著錄的張燦《擬離騷》20卷(《千頃空書目》作20篇),姜亮夫《紹騷隅錄》著錄的黃禎《擬騷》一卷,姚舜明《補楚辭》一卷,高元之《變離騷》9卷,徐瑤舉《藏騷》1卷,《紹騷隅錄》還著錄有散見於別集的明代騷賦作家的作品共58首,為研究明代騷體賦提供了豐富資料。
收錄明人“問答體”賦最多的為黃宗羲《明文海》。其中有“問答”5卷,收作家28人,作品40首。這些作品有的是無韻的論文,但其中有相當多的問對體賦,當分別觀之。
明代對賦的輯錄也做了許多工作。《明史·藝文志》著錄有:劉世教《賦紀》100卷,俞王言《辭賦標義》18卷,陳山毓《賦略》50卷。而今存明人選編的賦集尚有:袁宏道輯王三餘補精鐫《古今麗賦》10卷。周履靖劉風屠隆輯《賦海補遺》30卷。李鴻輯《賦苑》8卷。施重光輯《賦珍》8卷。俞王言撰《辭賦標義》18卷。陳山毓輯《賦略》34卷,緒言1卷。列傳1卷,外篇20卷。佚名氏輯《類編古代賦》25卷。
而收錄明賦較多的著作有:《明文衡》,有賦一卷,選錄明賦作家15人,賦18首。《賦海補遺》除收錄從漢至宋的賦265首外,還收周履靖賦606首。《明文海》有賦46卷,收明賦作者175人,賦292首。《歷代賦匯》共收明賦作家369人,賦735首。
清代是辭賦輯錄成就最大的時代,可以說是對前代的賦作了全面的輯錄與整理。其代表著作有:(一)陳元龍奉敕編《歷代賦匯》。該書總計收賦(包括逸句)4067首,“正變兼陳,洪纖畢具,信為賦家之大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歷代搜賦較為完備的總集。(二)董誥奉敕撰《全唐文》。書中收唐賦作家544人,賦1622首,除敦煌賦外唐賦基本收全。(三)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書中收有這個時期的賦作家342人,賦1211首。先秦至隋的賦除已有專集者外,大體上可稱完備。(四)鴻寶齋主人編《賦海大觀》。該書《凡例》稱其“得賦二萬餘首”,實際刊入該書的為12000首,錄自先秦至清光緒十四年之前的賦,分32類,子目500餘目,確是歷代輯錄賦最多的總集。但此書主要收清代律賦,於明以前古賦則大體仍《歷代賦匯》之舊,殊少補益。此外,清賦的選本尚多,大都以律賦為主,較有名者有法式善《同館賦抄》、黃爵滋《賦匯海》與《續編》等。其頗具撰述之意者,則有:(一)蘇興編《清代律賦類纂》。此書成於光緒二十六年,主要選錄清翰詹律賦,分類凡七,共選清代律賦作家182人,律賦372首。又以“各家法式,率本先民,稽錄古賦,用殿全篇,俾來者因類以討義,循流而溯源”(《律賦類纂序》),因此又選錄自陶淵明《閑情賦》至明徐渭《梅花賦》等駢賦凡44首,殿卷末以使讀者循流溯源,了解律賦的發展。(二)李元度所編《賦學正鵠》,其類有十,前9類選錄清代“清醒流利,輕靈典切”的律賦129首,“高古”類則錄有自唐宋王景《梅花賦》至漢班固《兩都賦》共18首,以便讀者循流而溯源。清代各種賦選甚夥,據我們所知者即有50餘種,其中有些還是抄本,如林佶輯《集英閣賦選》2卷,清抄本,藏河北大學圖書館;汪憲輯《宋金元明賦選》8卷,清抄本,藏北京圖書館;吳槐輯《賦海類編》20卷,清抄本,原藏上海圖書館,乃“文革”時抄家之物,現已物還原主矣。
收錄清代騷體賦較多的著作為姜亮夫教授著的《紹騷隅錄》。計收有尤侗《西堂雜俎·騷類》的《招魂》、《驅夢》、《招盪子》、《悲秋風》、《反招魂》、《梅花三弄》、《秋風圖辭》、《鼓琴圖辭》、《獨醒圖辭》、《九訟》共10篇,汪琬《堯峰文集抄》之《反招魂辭》,朱筠《笥河文集》之《擬招隱士》,方履箋《萬善花室文稿》之《小山招隱圖賦》,洪亮吉《卷施閣文集》之《七招》,王詒壽《縵雅堂駢文》之《九招》,龔自珍《定庵文集》之《戒將歸文》,凌廷堪《校禮堂文集》之《九慰》等,共計作家8人,作品17首。姜教授在該書《序》中說:“其僅有體貌結構,志卑言淺,或無病而呻者,皆不錄入”,可見該書只選錄清人騷賦的最優秀者。可惜清人騷賦散見於各種別集之中,不見有彙輯為總集者。
我們這次編集《歷代辭賦總匯》,在前人輯錄的基礎上,做了較為廣泛的搜集,所收作品亦有較多的增加。據初步統計,計收有先秦漢魏南北朝隋賦作家412人,辭賦作品1625篇;唐代辭賦作家579人,辭賦作品1711首;宋代辭賦作家347人,辭賦作品1445首;金元辭賦作家248人,辭賦作品761首;明代辭賦作家1019人,辭賦作品5107首;清代辭賦作家4810人,辭賦作品19499首。合計共收辭賦作家7450餘人,辭賦作品29100餘首。這雖是初步統計,但我們認為,這次輯錄進行得是比較廣泛的,除了宋人鄭起潛《聲律衡裁》所載的唐宋人律賦的殘垣斷壁未進行一一比勘輯錄外,對明以前的總集、別集及我們所能找到的部分地方志所載的辭賦作品,作了廣泛的全面的收集,較以前的幾種辭賦總集,如陳元龍《歷代賦匯》、鴻寶齋主人《賦海大觀》,篇幅都有較多的增加,可能還有遺佚,但不會太多了。至於清代辭賦,我們雖收有作家4000餘人,作品近20000首,但清人集部到底有多少,尚無精確統計數字,恐怕還有許多手稿未被發現。故清代可能遺佚較多。但主要是清律賦,且就我們的精力、財力和時間說,可以說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至於更廣泛、更深入的輯錄,就只好以俟來哲了。
前人編輯賦集,一般只收以賦名篇的作品。首先將屈原作品及其擬騷之作另立名目,名之曰“辭”或“騷”。劉向就最先定名為“楚辭”。《文選》於賦外,另立“騷”一目;又立“辭”一目。後人多繼承他們的說法,且相沿襲至今,並有人撰文作著來論述賦、辭、騷之區別。清人程廷祚就著有《騷賦論》加以論證,今人論之者更夥,可以繼續討論。但漢人“辭”、“賦”是不分的,將“辭”或“騷”稱之賦者比比皆是。如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就說屈原“乃作《懷沙》之賦”,班固《漢書·賈誼傳》也說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地理志》又說“楚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其《離騷贊序》亦云“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其《藝文志》更明確稱“屈原賦二十五篇”而歸入《詩賦略》中。自茲厥後以訖於今,稱屈原作品為賦者代不乏人。晉人皇甫謐《三都賦序》說:“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摯虞《文章流別論》亦云:“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故揚子稱賦莫善於《離騷》。”唐李白稱“屈平詞賦懸日月”(《江上吟》)。元祝堯《古賦辨體》首列“楚辭”,並云:“屈子《離騷》,古賦之首也。”清人戴震著有《屈原賦注》,馬其昶著有《屈賦微》,今人姜亮夫先生著有《屈原賦校注》,譚介甫先生著有《屈賦新編》。故本書將“辭”或稱之為“騷”者,作為賦之一體(名曰騷體賦)而收入書中。但不收“哀辭”,一則因為哀辭有具體的哀悼對象,與哀祭文相似,應歸入“哀祭類”;一則歷代哀辭太多,為節省篇幅,故不錄。並將用騷體寫作的“操”或“歌”收入,因這些“操”或“歌”既為騷體,則近於騷體賦,故可歸入賦類。這樣做,我們也並非是始作俑者,朱熹《楚辭后語》即將鄂君《越人歌》、劉邦《大風歌》、劉徹《匏子歌》、《烏孫公主歌》、李白《鳴皋歌》、顧況《日晚歌》、韓愈《琴操》、張載《鞠歌》收入書中。元祝堯《古賦辨體·外錄下》亦收入“操”與“歌”,並雲“操與詩賦同出而異名”,“益歌者,樂家之音節,與詩賦同出而異名爾”。可見這種騷體的“操”和“歌”是可以歸入“騷”的,為見其流別的有分有合,故亦列入。
“七”體創自枚乘。自枚乘作《七發》設英客以七事啟發楚太子之後,仿作者紛起。《藝文類聚》卷57引傅玄《七謨序》云:“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馬因、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等亦引其流而廣之,馬作《七勵》,張造《七辯》。……至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辯》,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此外,其著名者尚有崔瑗《七蘇》、張協《七命》、陸機《七征》、左思《七諷》等,漢魏以下文人幾乎無不作“七”,《隋書·經籍志》著錄有謝靈運《七林》10卷,梁《七林》10卷,又30卷。《文選》專設“七”一目,明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清張火介《古文辨體》亦皆設“七”一目,只是唐宋以後不復見有“七”的總集。“七”的歸類,前人很不一致。有的單設“七”為一體,已如前述。有的則將其歸入《雜文》。首先,《文心雕龍·雜文》就包括“七”,《文苑英華》亦將蕭統《七契》、蕭綱《七勵》、何遜《七召》歸入此類。歐陽詢《藝文類聚》亦將“七”歸入“雜文”。而有人則將其歸入辭賦,如姚鼐《古文辭類纂·辭賦類》就收有枚乘《七發》,張相《古今文綜·辭賦類》就收有李慈銘《七居》。我們認為,“七”實則是賦之一體。第一,它形式上採用客主問答,符合賦之“設客主以首引”;第二,它藝術上採用鋪陳的手法描寫七件事物,符合賦的“極聲貌以窮文”;第三,它“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大多而托諷詠”,符合賦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第四,它行文有韻有散,而以韻文為主,符合賦是“有韻者文也”的要求。故本書將“七”收入書中,既有體裁上的依據,亦有前人的先例,想來也不算是閉門造車吧!
“對問”體(《文選》分為“對問”、“設論”二目)創自屈原《卜居》、《漁父》。自茲而後,繼作者紛起。“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解。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間》,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文心雕龍·雜文》)。此外,著名者尚有曹植《客問》、庾凱《客咨》,韓愈《進學解》,柳宗元《廢起答》、《愚溪對》,宋元以後,作者代有其人,黃宗羲《明文海·對問》即有五卷,收明作家28人,作品40首。這種問答體,有的是設客主就某一問題進行辯駁論難,以申述作者對某一問題的見解或某種現象的意見,其行文純是無韻的散文,如黃宗羲《明文海·問答甲》所收的趙潔《葬書對問》、劉基《賣柑者言》、貝瓊《土偶對》、董軒《補余氏潮汐對》、《名實對》等,這種文章當然只能歸入論說或雜文。有的則是設客難以剖白作者的內心矛盾與不滿情緒,如東方朔《答客難》、韓愈《進學解》之類,實則是抒發作者不得志的牢騷與進行自我寬慰而已,行文雖與散文或駢文相似,但它大體有韻,應屬於有韻之文,與前種問答體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問答體歸屬歷來也眾說紛紜。有的分作“對問”、“設論”二目。如《文選·對問》即錄《宋玉對楚王問》、《設論》收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對》。清張《古文辨體》亦有“對問”、“設論”二目。有的名之曰“設論”或“客難”,如《隋書·經籍志》就著錄有劉楷撰《設論集》二卷,梁有《設論集》三卷,東晉人撰,又有《客難集》二十卷。有的即名之曰“對問”,如《盧照鄰集》就有“對問”一目,錄《對蜀父老問》一首,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亦均設“問對”一體,吳訥說:“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徐師曾說:“按問對體者,文人假設之辭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答、曰諭、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仿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郁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有的將其歸入“雜文”,如《文心雕龍·雜文》就論述了問答體,《文苑英華·雜文》就收有盧照鄰《對蜀父老問》,駱賓王《鈞磯應詰文》,韓愈《進學解》、《釋言》,柳宗元《答問》,沈亞之《進學解對書》。有的則將其歸入“辭賦”,如姚鼐《古文辭類纂·辭賦類》就收有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朔》、《解難》,韓愈《進學解》,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詞賦之屬》亦收有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解難》,班固《答賓戲》,韓愈《進學解》,並於《序例》中說:“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之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詞、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我們認為,這種問答體,它設客主問答,它鋪彩摛文,它體物寫志,它大體有韻,因而更接近於辭賦,故我們將其作為賦體之一收入本書。
還有一種以“文”名篇的作品,雖以“文”名篇,卻又不同於一般的文。其一,它有韻,屬於韻文一類;其二,它的寫作目的在抒情,在諷諭,或純為遊戲文字。這種文字,其歸屬歷來更不一致。有些用滑稽詼諧的筆調寫的遊戲文字,有人就名之曰“俳偕文”,新舊《唐書·藝文志》均著錄有南朝宋袁淑《俳偕文》15卷,這種文章如王褒《僮約》,張敏《頭責子羽文》,袁淑《雞九錫文》、《驢山公九錫文》之類。有些以吊名篇,形似弔祭,有人就歸入弔祭一類。如《文選》就收賈誼《吊屈原文》,陸機《吊魏武帝文》歸入“弔文”一類。《文苑英華》亦將韓愈《吊田橫文》、李華《弔古戰場文》、柳宗元《吊屈原文》歸入“哀祭”一類,姚鼐《古文辭類纂》亦收賈誼《吊屈原賦》、韓愈《吊田橫文》歸入“哀祭”一類。其實,這種弔文雖名之曰吊,實則是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以抒發作者的牢騷與憤懣,與一般的具體弔祭某人的祭文有所不同,不可以收其作為一般哀悼死者的弔祭文等同視之。有些以論說名篇,形似論說文,有人就收其歸“論說”一類。如魯褒《錢神論》,《藝文類聚》卷666引即歸入“論”類,曹植《髑髏說》,吳均《餅說》,《藝文類聚》卷71、卷72引皆歸入“說”類。但這種論說不同於一般的論說文。就內容說,其重點在抒情或諷刺,而不在辨事析理;就形式說,它是韻文而不是無韻的散文;因此與一般的論說文有很大差別。有些以檄移名篇,形似檄移,有人就將其歸入“檄移”一類。如孔稚珪《北山移文》,《文選》就歸入“移”類,吳均《檄江神責周穆王壁》,《藝文類聚》卷84引就歸入“檄”類,其《食移》,《藝文類聚》卷72引就歸入“移”類。其實,這種檄文、移文也不同於一般的檄移。《文心雕龍·檄移》云:“檄者,皎也,宣露於外,皎然明白也。”其作用是“振此威風,暴彼昏亂。”“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而這種檄文、移文,多為俳偕文,多是以檄移的形式,詼諧的筆調,抒寫其對某種現象的嘲諷,或純為遊戲文字,與一般檄移大不相同。有些因採用騷體,內容又極博雜,有人就收其歸入“騷”,歸入“辭”,歸入“雜文”。如晁補之《續楚辭》、朱熹《楚辭后語》就收韓愈《吊田橫文》、柳宗元《招海賈文》、《吊屈原文》、《吊萇弘文》、《吊樂毅文》、《亡巧文》、《憎王孫文》收入書中,而《文苑英華》則將盧照鄰《五悲文》、《釋疾文》、柳宗元《吊屈原文》、《憎王孫文》收入《雜文·騷》。這種歸類有合理的一面,但因其形式既為騷體,歸入騷或辭,我們認為要更妥貼。既為辭或騷,即為賦之一體了。有的則歸入賦類。特別是弔文,與賦更是有難以分割的淵源。《史記》載賈誼為賦以吊屈原,《文選》即標題為《吊屈原文》。祝堯《古賦辨體》蓋本此,故其《外錄下·文》即收有孔稚王圭《北山移文》,李華《弔古戰場文》,韓愈《吊田橫文》,柳宗元《吊屈原文》、《吊萇弘文》、《吊樂毅文》;張相《古今文綜·辭賦類》亦收有李慈銘《答仆消文》;蔣瑞藻《新古文辭類纂稿本》亦收有李慈銘《答仆消文》、《詰司命文》、《瘞狗文》,林抒《釋斑貓文》,李詳《哀輪船文》,劉師培《招蝙蝠文》,祝堯在《古賦辨體·序說》中還特別說明云:“昔賈生投文而後代以為賦,蓋名則文而義則賦也。是以楚辭載韓柳諸文以為楚聲之續,豈非以諸文並古賦之流歟!今故錄歷代文中之有賦義者於此。若夫賦中有文體者,反不若此等之文為可入於賦體雲。”可見此等之文,雖名曰文,而其形式和內容均更接近於賦。故本書將其作為賦之一體,我們稱之為“賦體文”而選入書中,以備一家之言云爾。
本書將作家作品按時代先後次序排列,分為《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唐代卷》、《宋代卷》、《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不似前人賦集如陳元龍《歷代賦匯》、鴻寶齋主人《賦海大觀》之按內容分類編排。也許有人要問:“你們的書只名曰《歷代辭賦總匯》,收入辭(或稱騷),收入賦,是合理的。卻又將‘七’、‘問答’、‘文’收入書中,豈向自亂其體歟?”我們認為,“七”、“問答”、“文”,前代已有人視之為“騷”(或稱“辭”),視之為賦,我們並非始作俑者,這已如前述。其次,這些類型的體裁,自唐以後即無人輯錄。我們將其輯錄起來,編入一書,這就給研究這些文體及其演變發展的歷史軌跡提供了比較完備的資料。這應該也是有益的。
余自1990年受賦學界一些同仁委託,主編是書,訖今已十有餘年矣。自接受委託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有負同仁的殷切期待。於是朝夕孜孜,不避雪案嚴寒,晴窗酷暑,口不絕吟於古籍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書,嘗兀坐終日,思考著資料的輯錄,籌畫著編纂的體例,比勘著文字的異同,盤算著經費的籌措。它幾乎傾注了我晚年的全部心血。我常自思忖,這是我晚年做的一件費力不討好的蠢事。本書曾列入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重點項目,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八五”圖書選題出版計劃》的重點圖書選題。這樣重要的項目,本應由年青力壯、精力充沛而又有雄厚財力依靠的大學者、大專家來承擔。而我只是一介寒儒,學識譾陋,見聞狹窄,風燭余年,精力衰退,欲將事情做好而往往經費捉襟見肘,精力力不從心。孟夫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余於是書亦有是嘆。了解是書編撰的艱辛過程的同志,一定會同情我,理解我,原諒我所作的不足;不了解的同志,一定會批評我的粗疏,責怪我的失職。“知我”、“罪我”,其亦惟在是書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