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證據法
三重證據法
三重證據法是在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史學研究證據法。對於三重證據法,有多種不同的體現。一是黃現璠三重證據法(又稱黃氏三重證據法),即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結合調查資料或材科中的“口述史料”研究歷史學、民族學。二是饒宗頤的三重證據法,即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將考古材料又分為兩部分——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三是葉舒憲的三重證據法,即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再加上文化人類學的資料與方法的運用。
三重證據法是建立在二重證據法基礎上運用三重或多重證據研究歷史的考據方法。在近代之前,傳統史家常常只是運用文獻記載作為唯一的研究歷史的證據材料。近代學者打破傳統,推陳出新了二重證據法。如王國維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陳寅恪說:“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二重證據法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考古學和考據學的重大革新,現代許
黃現璠
黃現璠三重證據法(又稱黃氏三重證據法)是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結合調查資料或材科中的“口述史料”研究歷史學、民族學。三重證據便是:紙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口述史料。
饒宗頤
饒宗頤的三重證據法是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將考古材料又分為兩部分——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三重證據便是有字的考古資料、沒字的考古資料和史書上之材料。李學勤對此‘三重證據法’十分認同。
葉舒憲

葉舒憲
楊向奎先生主張:紙上的文獻材料、地下挖掘出考古材料和民族學的材料皆可作為史料證據。
汪寧生先生認為:文獻、考古發現、民族學資料、考古學的發掘皆可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實證,而語言學的分析可為古史研究(特別是民族歷史及古代習俗的研究)提供有用資料。即民族學(文化人類學)調查來的資料,同樣可供研究古代社會和文化進行類比。從而主張:研究中國史現在已不再限於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而應提倡“三重證據法”(文獻、考古發現和民族學資料),甚至“多重證據法”,即有關學科所能提供一切證據均可利用。
葉舒憲、蕭兵認為:紙上的文獻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及跨文化的民族學與民俗學材料皆可作為證據而運用於歷史研究。毛佩琦先生針對《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一書所撰的書評《歷史研究中的“三重證據法”》中提出的“三重證據法”為:紙上的文獻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社會調查材料。馬彪先生於2006年12月25日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作題為《談談簡牘學研究的三重證據法——以龍崗秦簡與雲夢禁苑為實例》的學術講演中提出的“三重證據法”為:紙上的文獻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實地調查史料。彭裕商先生認為徐中舒先生運用“邊裔的少數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史料研究先秦史,即運用了“三重證據法”。從而主張“徐中舒先生是“古史三重證”的提出者”針對上述觀點,也有學者予以反駁,說道:通過對饒宗頤、楊向奎、徐中舒等學者的論著細讀,發現三位學者的主張及其學術實踐,並未突破王國維的“古史二重證”中“歷史文獻”和“考古史料”的範疇。筆者理解的汪寧生提出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調查來的資料”;毛佩琦先生提出的“社會調查材料”;馬彪提出的“實地調查材料”,包括調查所獲得的文書、實物、口述三方面的資料。這些“調查資料或材科”顯然是獨立於“歷史文獻”和“考古史料”之外的第三重證材料,特別是口述史料。其實,調查資料或材科中的文書也在王氏所列的“紙上之材料”之內。
沒有證據顯示“徐中舒先生是“古史三重證”的提出者,但他是“古史三重證”實際運用的學者之一,現在的研究表明,20世紀上半葉已有部分學者運用“三重證據法”從事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如徐中舒、黃現璠、鄧少琴等學者。
在從事民俗學或民族學的研究過程中,黃現璠逐步認識到學界盛行的二重證據法並不能在史料上充分說明民俗學或民族學研究中遇到的許多新問題,即歷史留下的文獻或近代流行的考古地下遺物挖掘史料依然有限,不足以解決一些新學術研究領域的新問題。於是,黃現璠開始了他的“行萬里路”的田野學術考察,期望於學術實踐中有所突破。從1943年到1979年的36年間,他曾領導組織了大小數十次的田野考察活動,以其中1951年和1956年的兩次調查最為重要。1951年6月,黃現璠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團長費孝通),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收集到大量史料。1956年8月,黃現璠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學術調查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少數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調查,足跡踏遍廣西境內桂西所有少數民族地區,不但收集到大量的調查資料(包括歷史文獻和古代遺物),同時還獲得了豐碩的第一手人物調查採訪口述史料。這些為他在民俗學、民族學或人類學的研究上能突破二重證據法而建立“黃氏三重證據法”創造了重要條件。
晚明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從來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並在一些研究領域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於某個專題或側面,缺乏整體關照或綜合研究。同時,由於歷史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上,或者比較保守,或者比較傳統,不論在宏觀的把握上還是在微觀的深入上都顯得不夠精到。
《晚明社會變遷》這一研究成果的突出特色,就是它開創了晚明歷史研究的全新格局。它的新表現在:
對晚明歷史的宏觀、整體的觀察。研究大體涵蓋了影響晚明社會的主要結構領域。重要的是,研究者把晚明社會看成是一個整體,注重各個發展變素之間的交叉與互動。因為有了整體關照,各個社會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清晰,而對整個社會變遷的分析和認識也就更加令人信服。
把晚明的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進行考察。實際上,可以說在晚明時代世界的一體化進程就已經開始了。研究者把明代中國置於世界大環境中,以對比和發展的觀點考察中國社會發展的程度,突顯了明代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
把明代中國置於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儘管明代中國已經與世界發生了密切的聯繫,其獨特的發展線索仍然是清晰可見的。與以往的一些研究者不同,本課題的研究將中國與外國進行比較,而不將其與外國生硬比附。在考察了諸多社會變遷的因素之後,本課題研究者向我們展示了中國獨特的近代一現代化的歷程。研究者試圖擺脫歐洲中心論,也無意建立中國中心論。這種獨特的視角,在中國史研究中是有創新意義的。
在研究中引進了社會學、人口學、法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傳統的中國史研究在方法上是比較單一的,研究古代社會不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古代的人口不用人口學的方法,是普遍的現象。引進相關學科的方法,不僅使研究者有了新的觀察角度,也使得對於問題的觀察更加深入。社會本身是鮮活的,古代社會也曾經是鮮活的。新研究方法的引進,將使研究者的眼界大開。
本研究的最後附錄了一項社會調查報告,即《貴州安順屯堡社會調查報告》,這是很有新意的。長期以來史學研究對社會調查重視不夠,甚至完全忽略了。這項社會調查報告證明,社會調查這種方法對歷史研究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明代社會史的研究。明代離今天並不遙遠,一些幾百年前的社會痕迹至今仍然殘存於我們的社會中。作者只進行了貴州安順屯堡的社會調查,如果進行更廣泛的社會調查,必將會有更多新鮮的發現。
史學研究需要證據。證據充分,結論才可能穩妥可靠。前人把出色的研究比喻成“老吏斷獄”,因為證據充分、推理嚴密,所得出的結論成為不可推翻的鐵案。學術研究如同斷獄一樣,最忌孤證。傳統的史學研究所引用的證據大都出自傳世文獻。被稱為“新史學開山”的王國維首開風氣之先,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這就是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二重證據法”在方法上與傳統史學對於證據的處理相銜接,即尊重傳統史學,又擺脫了傳統史學的局限,是由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一項重要變革,在史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今天,我們不妨提出“三重證據法”。那第三重證據是什麼?答曰:社會調查。
社會調查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社會學、人口學、人類學、經濟學等等學科中被廣泛運用,但一直很少將其與歷史學相聯繫,或者說一直沒有明確將其作為史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如果把地下出土之古物稱為化石,那麼,現實生活中之古代遺存則是“活化石”,除地上遺存物之外,它們保存在語言、生活習俗、服飾乃至歌舞、戲劇表演之中,大多可以歸為非物質歷史文化遺產。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也是我們得以用之證史的又一重證據。《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的作者們對此的嘗試是有益的。讓我們提倡“三重證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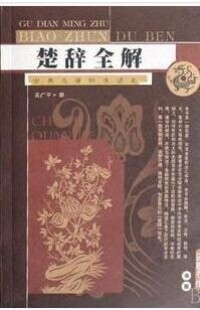
楚辭全解
作者吳廣平先生善於綜合運用“三重證據法”(即“文獻典籍”、“文物考古”、“文化人類學”三個方面的證據)來破解《楚辭》的疑難、死結與公案,《楚辭全解》一書正是“三重證據法”演繹下的楚辭研究的可喜成果。
善於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典籍資料與證據,是《楚辭全解》的第一個重要特點。傳世文獻典籍是我們從事古代文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資料與證據。吳先生在破解《楚辭》疑難時,十分注重運用傳世文獻典籍資料與證據。如《九歌·國殤》“天時墜兮威靈怒”,今人多誤將“威靈怒”釋為“鬼神發怒”或“鬼哭神號”;但《國殤》的主旨是歌頌“鬼雄”,鬼神始終是剛強的,怎麼能說“鬼哭神號”呢?吳先生據《廣雅·釋詁三》“怒,健也”的訓詁材料,將“威靈怒”釋為“神威剛強”,就通達多了。游國恩曾撰寫專文主張宋玉《大言賦》、《小言賦》乃模擬晉人傅咸《小語賦》之作,幾成定論。此書據《永樂大典》卷一二○四三《酒》“賜方朔牛酒”條載西漢東方朔《大言賦》,乃模擬宋玉《大言賦》之作,遂斷定游氏所言乃祖孫顛倒的推論。世傳宋玉《微詠賦》,明代學者楊慎、胡應麟、陳繼儒、張燮均認為系南朝宋代王微《詠賦》之訛,今人多信從此說。此書據唐代陸龜蒙《自遣詩》“宋家微詠有遺音”及其舊注“宋玉有《微詠賦》”,以及明代錢希言《戲瑕》、周嬰《卮林》和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鈔》等書的觀點,乃斷定宋玉確實寫作有《微詠賦》。
陸龜蒙、錢希言、周嬰、俞樾等人關於宋玉作有《微詠賦》的言論,為上世紀以來的楚辭學者所忽視,吳先生髮掘出這些詩人與學者的觀點與材料,毫無疑問十分有利於學術界進一步考辯《微詠賦》的真偽。這些正是作者善於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典籍資料與證據的表現。書中依靠傳世文獻破解屈宋作品疑難的例子很多。如據《山海經》和《本草綱目》破譯《天問》中“鯪魚”的神話原型為穿山甲,據《周禮》和《說文解字》破譯《天問》中雨師“蓱”的神話原型為金龜子,據《廣雅》和《詩經》破譯《天問》中“繁鳥”的神話原型為貓頭鷹,據朱熹《楚辭集注》、戴震《屈原賦注》以及王引之的觀點糾正《九章·懷沙》“亂詞”的錯簡,據清代吳楚《說文染指》和謝彥華《說文閑載》釋《九辯》“塊獨守此無澤”的“無澤”為“蕪澤”。類似例子,書中俯拾即是。
善於充分利用出土文物考古資料與證據,是《楚辭全解》的第二個重要特點。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編撰的講義《古史新證》的“總論”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王國維所謂紙上材料即傳統的文獻材料,地下材料即考古發現的新材料。所謂“二重證據法”就是用考古發現的新史料與傳世的文獻典籍互相釋證。閱讀《楚辭全解》一書,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大量引用出土的甲骨、金石、簡牘文獻和出土的實物圖像來與傳世的文獻典籍互相印證,顯示了作者對考古發掘出土新資料的重視。如解釋《大招》“小腰秀頸”中的“小腰”,作者先引述《墨子》、《荀子》、《管子》、《晏子》、《屍子》、《尹文子》、《淮南子》、《新論》等文獻典籍有關楚靈王好細腰的記載,然後輔以楚墓出土的織錦、刺繡、帛畫和漆畫上所繪男女均一律細腰來互相印證,這樣兩相印證,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傳世文獻所載“楚王好細腰”當確有此種風尚。此外,如據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孫子兵法》佚篇《吳問》的記載釋《離騷》“滋蘭九畹”之“畹”的面積,據湖北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出土的祭祀“雲君”的竹簡來證釋《九歌》中的“雲中君”即雲神,據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排簫實物來描寫《九歌·湘君》中的“參差”(排簫的俗稱)的形制,據山東濟寧縣發現的漢代石抱子俑像來印證《九歌》中“少司命”的神格,據湖北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出土的樂器編鐘和篪來解釋《東君》中描寫到的相關樂器等等,均是善於利用二重證據法的表現。
善於充分利用文化人類學的資料與證據,是《楚辭全解》的第三個重要特點。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葉舒憲先生的專著《詩經的文化闡釋》。葉先生以《人類學“三重證據法”與考據學的更新》一文作為此書的“自序”,正式提出了“三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是指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之外的文化人類學所提供的域外的、原始的、民族的、民俗的資料。許多古典文化的奧秘,我們完全可以“禮失而求諸野”,通過田野採風,運用民俗事象來破解。吳先生在《楚辭全解》一書中引用了大量域外的、原始的、民族的、民俗的資料來破解《楚辭》中的文化秘密,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如引用湖湘民間流傳的“顛倒歌”來解釋《九歌》“二湘”倒反辭的修辭藝術來源與藝術特徵;引用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祭神賽會時男女“拋綵球”和湘西苗族的《領魂辭》來解讀《九歌·禮魂》;引用原始社會奇特的“產翁(couvade)”習俗來破譯《天問》“伯禹腹鯀”的文化秘密;據原始社會以及烏干達前總統阿明和中非已故皇帝博卡薩均信任裝神弄鬼的巫師,嗜食人肉,特別喜歡吸人的骨髓,來解釋《招魂》“以骨為醢”的巫術宗教背景;根據文化人類學提供的聖婚儀式材料,結合《神女賦》的文本實際、《神女賦》與《高唐賦》的內在聯繫、魏晉至隋唐大量詩人詩作的佐證,校勘訂正《神女賦》中夢神女的應當是襄王而非宋玉……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楚辭全解》一書,由於成功運用了三重證據法來破解《楚辭》,書中文獻的、考古的、民俗的材料紛至沓來,相互印證,珠連璧合,顯示了作者深厚的學術底蘊與寬廣的學術視野,從而使得全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這也彰顯了作者守正出新、銳意開拓的學術個性與學術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