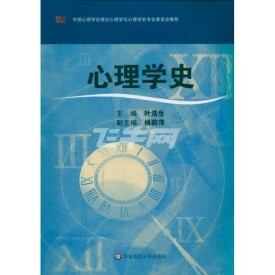心理史學
由弗洛伊德所開創的學科
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又稱“心理歷史學”,西方“新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汲取心理學的某些理論、原則和方法,探究世界歷史進程中人類的各種活動,從“心理”的視角豐富和完善歷史認識的能力,提高歷史研究的科學認識水平。由精神分析學大師弗洛伊德所開創。
心理史學的提出,和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S.弗洛伊德及他的精神分析學說有直接的聯繫。弗氏等認為,運用該學說的無意識理論、釋夢理論、人格學說和性的理論等進行歷史研究,有助於開拓歷史認識的視野。1910年,弗洛伊德撰有《萊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童年的一個記憶》,這是一部體現精神分析理論的歷史人物傳記。一些人認為,這是西方心理學和歷史學的完美結合,是心理史學一次成功的嘗試。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這是在普及精神分析理論,而不是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西方史學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心理史學開始擺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使心理史學開始具有完備的現代史學的意義。1957年,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威廉·蘭格在看到社會史、經濟史、科學史和心態史等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呼籲加強心理史學的研究。新一代的心理史學家強調,心理史學不是在歷史資料裡面發現心理學的概念,而應當從心理分析學的角度來考察這些史料。1958年,美國學者E.H埃里克森的專著《青年路德:一個精神分析和歷史的研究》出版,他在進行心理分析時,高度重視文化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被公認為是心理史學的奠基之作,成為心理史學問世的標誌。他還認為,心理史學的實質,是用精神分析學說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個體和社會群體的活動。這種認識,反映了西方心理史學的主流觀點。60年代以來,心理史學在美國得到迅速發展。1965年,在埃里克森、李夫頓等人的努力下,心理史學方法研究小組成立。1972年,心理史學協會在紐約成立。1973年,《心理史學雜誌》和《心理史學評論》等專業學術刊物創刊。在美國,約有1/3的大學開設心理史學的課程。影響所及,藉助精神分析學說撰寫歷史人物傳記蔚然成風,也成為心理史學研究的主要形式之一。
美國《心理史學評論》(The Psychohistory Review)系其主要的發表重鎮,為目前重要的心理學學術刊物。“心理史學”在華語社會中因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ssac Asimov)的科幻小說,及田中芳樹“銀河英雄傳說”的故事得以普及,但真正認識這門學說的人並不多。
心理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社會群體的心理史,如種族歧視、法西斯主義等;在童年史和家庭史研究中,對人的童年時代和家庭生活進行心理分析。
P.洛溫伯格的《解開往昔之迷》(1985)詳盡探討了“納粹青年追隨者的心理歷史淵源”,認為那一代人在其性格形成的決定性時期的遭遇,特別是童年早期的遭遇,他們在童年時期心理形成和政治社會化方面的共同經歷,導致了他們成年時期性格上所有的畸變。
近年的心理史學研究中,更加重視使用非精神分析方法。一些研究者還強調,對於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個體或群體的心理解釋,只是諸多分析歷史人物中的一種,或者僅是其他解釋的補充,並不是要取代其他的解釋。這些認識,反映了心理史學發展中的一些新的特點和新的趨勢。
弗羅伊德精神分析法
心理史學是運用心理學方法研究歷史上人們心理狀態的一種史學流派。佛羅伊德是西方心理史學的奠基人,他所創立的精神分析法後來成為許多歷史學家進行心理研究的主要依據。佛羅伊德在1912年率先運用精神分析理論寫出了關於達·芬奇的傳記《童年的回憶──達·芬奇》。他在書中指出,達·芬奇的性格非常奇特,他有時溫柔得就像善良的女孩兒,有時又非常狂妄,懷疑一切,蔑視權威。他的繪畫藝術本已達到很高水平,但卻花費大量時間從事與繪畫毫無關係的科學研究活動,如研究鳥類飛行、植物的營養等。佛羅伊德認為這些矛盾反映了達·芬奇的心理變態,心理變態又根源於達·芬奇的童年。達·芬奇生於1452年,是一個公證人和一個農家姑娘的私生子,後來他的父親拋棄了他的母親,和一個出身高貴的姑娘結婚,達·芬奇便同母親一起生活,直到5歲才回到父親身邊。
佛羅伊德認為這5年恰恰是達·芬奇性格和心理形成最重要的時期,由於沒有父親,引起了他個性的嚴重失態,並形成了他女性化的性格和同性戀的傾向。達·芬奇的母親由於失去戀人而加倍愛撫幼兒,她對達·芬奇的不斷親吻刺激了達·芬奇對母親的依戀和性的早熟。佛羅伊德認為蒙娜·麗莎迷人的微笑實際上就是他母親的微笑,反映了他對母親的愛和深深的懷念。這本書被認為是心理史學最早的著作。另外,佛羅伊德還著有《歌德對童年的回憶》、《托馬斯·傑斐遜心理研究》等。在心理史學方面有所成就的還有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學者呂·費弗爾,他提倡歷史學和心理學的結合,並對心理史學進行了理論探討。他在《拿破崙卜書中,曾對拿破崙性格的形成進行過心理分析。他的《拉伯雷的宗教》也是重要的心理分析著作。
美國心理學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心理史學開始在整個西方興起,美國仍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早在1935年,美國史學家威廉·蘭格出版的《帝國主義外交》一書中,就用心理學方法分析了19世紀末英國的對外擴張。1957年,蘭格擔任了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在12月29日的就職演說(《下一個任務》)中,呼籲歷史學家把心理史學方法引人歷史研究領域,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門新的史學。通常人們都把蘭格的講話看作美國心理史學真正形成的標誌。就在蘭格演說后僅僅一年,美國精神分析專家埃里克森就出版了他心理史學的經典性著作:《青年路德·對精神分析與歷史學的研究》。埃里克森的貢獻主要是:第一,強調自我的獨立性,認為自我在為本我服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內容、需要和機能;第二,強調人格的可變性,把人們從生到死的心理狀態分成8個階段,人就是通過解決各個階段的心理危機而向前發展的;第三,在人的內在心理世界和外在社會環境的關係上,注意到了外在環境對心理的影響;第四,從心理學角度闡述了領袖與群眾的關係,認為領袖所以成為領袖,是因為他能克服內心的種種障礙;但領袖又是不能脫離群眾的,群眾的心理往往對領袖的心理產生影響。除此之外,埃里克森還寫了其他許多心理史學方面的著作,如1963年的《兒童期與社會》、1969年的《甘地非暴力主義的起源》等,是公認的西方心理史學的權威。
在蘭格的號召和埃里克森的鼓舞下,美國的新史學在60年代有了迅速發展,一批年輕的學者逐漸成長,他們大都受過歷史專業和心理學專業雙學位的訓練,他們年富力強,成果卓著,比較著名的有洛溫伯格和科胡特等人。美國心理史學還擁有兩個專業刊物《心理史學雜誌》和《新史學評論》。其他刊物如《美國歷史評論》、《現代史雜誌》、《交叉學科歷史雜誌》等還經常舉辦心理史學的專刊。到70年代末,美國已有30多所大學開設心理史學的課程。可見,新史學在美國也是一片興旺景象。當然,新史學在當代並不局限於美國,也波及了西歐所有的國家和加拿大,如德國對路德和希特勒時代的心理研究,在世界上就有一定的影響。
注重探討歷史人物的童年經歷
如美國學者奧托·弗萊茲1972年發表的《俾斯麥心理分析》就頗具代表性。他探討了俾斯麥的童年生活與他的人格形成的關係。俾斯麥從小缺乏母愛,母親對他非常嚴厲和冷淡。上學以後,他又經常受到老師的粗暴對待,所以成年的俾斯麥就形成了一種權力欲,因為他要通過不斷追求權力來補償他童年時未得到滿足的心靈;
廣泛應用精神分析的概念與術語
用精神分析法研究集體心理
法國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在《1789年的大恐慌》中認為1789年穀物的漲價、農村的飢荒、乞丐、暴徒、土匪的騷擾、領主對農民起義的鎮壓、貴族和宮廷的陰謀,這一切使整個法國陷人心理上的大恐慌之中,農民由於恐懼而作出了防禦反應,恐懼消失后又產生了懲罰的願望,從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這場農民革命構成了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認為群眾革命心理的三個方面:恐懼、防禦反應和懲罰願望是解釋法國大革命的關鍵;第四,擴大了史料應用的範圍。除了傳統的文獻著作外,心理史學還運用了其它有助於心理分析的資料:回憶錄、私人信件、日記等。另外,生活習慣和個人痛好也被心理史學所注意。如佛蘭茲就注意到了俾斯麥愛決鬥,愛表現自己等等,通過這些細節來說明俾斯麥的心理狀態。
心理史學的方向是正確的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馬克思主義從不排斥從人類心理的角度去認識和了解歷史,認為經濟因素是影響歷史發展的最終的決定的因素,但人的心理、情感等因素在歷史上也起一定的作用。如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因此,歷史科學是不能忽視人類的心理活動的;二是心理史學為歷史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它擴大了歷史研究的範圍,把不被傳統史學所注意的東西如童年經歷、性格、情感、潛意識等等引人歷史學領域,從而造成了一場革命性的變革。
不能不加分析盲目搬用
應當看到它的缺陷:西方心理史學基本上是建立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基礎之上的,這一理論在醫學和心理學上特別是在治療精神病方面有獨到的價值,但用它來研究整個歷史領域就顯得牽強附會了。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因此脫離了社會關係總的結構,脫離了社會歷史環境,僅僅從人的本能和心理活動去概括解釋歷史,就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從另一個角度看,心理史學在西方的發展也限制了史學家的眼界,許多史學家只盯著人的內心活動,而不顧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存在,這顯然背離了心理史學應有的發展方向;心理史學還導致了不顧事實,隨意解釋歷史的主觀主義傾向。精神分析法強調追溯歷史人物童年的經歷,但這方面的資料又非常缺乏,因此許多毫無真實性的傳說也被心理史學家用來作為精神分析的證據,這樣的歷史是無科學性可言的;歷史研究機械化、簡單化的傾向也很嚴重,許多史學家用一個固定的理論模式生搬硬套歷史,還有的歷史傳記乾脆就是人物的精神病病歷,而不作任何歷史解釋。另外,從心理學領域引人大量的理論術語也給人以故弄玄虛之感。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心理史學要發展,必須打破西方心理史學的唯心主義體系,發展自己的科學的心理史學理論。
影響歷史學方法論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於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義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已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時代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注的是“對於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歷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權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並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於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他的多卷本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蘭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則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對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勁旅。
新康德主義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於“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為了避免歷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於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於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實現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範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於歷史學家,人們習慣於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藉助於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於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
法國年鑒學派
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法國年鑒學派,以其“精神狀態史”的研究範式對心理史學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法國年鑒學派最初同樣是出於對蘭克學派那種只關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戰役史的不滿,主張擴大史學的研究範圍並使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他們認為,這樣即可以在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長時段”、“總體史”的綜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會、經濟、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歷史學”。所謂跨學科研究,就是藉助於經濟學、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計量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從多種視角認識和研究歷史。年鑒學派的先驅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是最早強調心態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學者。費弗爾在對腓力二世時期弗朗什-孔泰省的歷史研究中,就試圖在使用地理學、社會學方法的同時,結合使用心理學的方法,探索該地區的歷史全貌。後來,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了對人類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運用集體心理方法考察了長期支配以往人們的種種觀念,揭示了一定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態。”他的《馬丁·路德:一個命運》一書,探討了十六世紀德國社會的精神風貌和集體心理,開創了法國式的心理史學研究的先河。他運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紀的不信神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該書中強調,“一定時空範圍內人們的思維工具,即長期左右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觀念,揭示了社會的思想文化氛圍和普通民眾的精神狀態。”因此心理史學的研究,“是要揭示歷史上人們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憂慮、愛憎、信念等。為了勾畫這種情感世界,歷史學家必須運用語言學、人類文化學、哲學、肖像學、文學、尤其是社會心理學方法進行綜合研究。”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國心理史學的經典之作。
法國年鑒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鑒學派創立前,就致力於以心理因素說明人的研究。他在《創造奇迹的國王》一書中,以“國王觸摸”的功效———即通過國王觸摸患者治病為事例,運用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的方法,對中世紀王權崇拜的產生、發展和消失,進行了綜合性的考察,從而揭示出那個時代普遍存在的社會心態。他在分析的過程中涉及到人們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機制26二十世紀中外心理史學概述時,提出的國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與德國馬克斯·韋伯在約略同時提出的神聖的克里斯瑪(Charisma)特質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史學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當時法、德兩國的知名學者中已獲得了廣泛的共識。後來,布洛赫在其史學理論的經典之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多次運用了心理史學的方法。他認為,“考證涉及到心理狀況,它是一門微妙的藝術,決沒有訣竅可言,而它又是一門理性的藝術,有條不紊地運用某些基本的思維程序。總之,如果要加定義的話,那它本身就是一種辯證的東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證,也與心理分析相關。因為有關史料真實性的考證,在史料來源及其外在標準無法確定時,“就只有從原物或文獻內在的特性著手,這就又得藉助心理分析”。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布洛赫特彆強調:“史料的取捨取決於心理分析,何為真假錯誤的理由都得經過鑒定”。費弗爾與布洛赫在心理史學方面的嘗試和努力,為法國後來的精神狀態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代著名學者戴維斯即受到他們很重要的影響。她有關法國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與社會研究的一系列論文,即成為心態史研究方面的成功範例。
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思想在進入布羅代爾(1902—1985)時代之後,心態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為布羅代爾“長時段”的“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地理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文化心理結構諸結構中的一個主要構件,這體現出年鑒學派在史學思想與結構體繫上的趨於成熟。布羅代爾在《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中曾說過,是“長時段”理論架起了溝通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橋樑,從而促進了歷史學與各門社會科學全面而系統的交流,各類學術相得益彰。不過,正像布羅代爾“長時段”理論對於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樣,他在對於“長時段”整體結構的認識上,同樣由於過分強調地理環境和生態結構的作用忽略了心理結構的作用。他的《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即體現出這種環境或生態決定論的傾向。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布羅代爾史學路徑不同、曾被布羅代爾批評的另一部分法國歷史學家,則直接繼承了費弗爾集體心理分析的方法,並將其發展為比較純正的精神狀態史研究。如迪比的《戰士與農民》、芒德魯的《近代法國概論:心理歷史學》、菲雷的《18世紀法國的書籍和社會》。他們試圖從各個角度揭示時代的精神狀態。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奧克族村莊蒙泰尤》更具典型意義,他通過具體詳實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史料,準確直觀地勾勒出法國那個特定時代的鄉村生活,使人們看到了當時村民們的精神狀態,從而了解“深處的法蘭西”。這種與社會學方法相結合的心理史學方法,的確有著如他所說的“由地窖進入頂樓”風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緣於此。
如果說法國年鑒學派的心理史學,主要是以史學為主體而藉助於心理學的分析方法的話,那麼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則是以心理學為主體把比較科學意義上的心理分析理論應用於歷史研究的具體實踐。二者的視角不同,學術路數自然相異。後者這種產生於史學外部的心理史學,可能更具典型的現代科學意義。1900年,弗洛伊德《夢的解析》問世,1910年後,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種理論運用於具體歷史人物、歷史現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後發表了《達·芬奇的幼兒期之回憶》(1910年)、《圖騰與禁忌》(1913年)、《群體心理學與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與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於弗洛伊德運用的心理分析比較規範,使得心理學與歷史學自此真正結緣。亦可將其稱為真正意義的“心理史學”,或“歷史心理學”,實際上就是心態史。不過由弗洛伊德開創的這種心理史學,在二次大戰前還未引起史學界足夠的重視。
美國的心理史學
美國的心理史學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並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運動。魯濱遜在其代表作《新史學》一書中,提出用綜合的多種因素的觀點來分析歷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與法國心理史學相對應的學術研究重鎮。這主要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對於法西斯主義那種狂熱行為的關注,由此而加強了對於無意識和非理性行為的研究。如戰時美國戰略情報部門,專門組織精神分析專家撰寫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態:戰時秘密報告》。五六十年代,很多歷史學家開始對於心理史學進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茲利希將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編成《心理分析與歷史學》一書。此外,利夫頓和奧森收編了《心理歷史學的闡釋》。七十年代,美國在這一學術領域先後創辦了專門的學術刊物《心理歷史學雜誌》、《童年歷史·心理歷史學》和《心理史學評論》。連過去比較正統的歷史雜誌《美國歷史評論》,也發表了不少討論心理歷史學的文章。心理史學,成為當時新興的而且是最活躍的學科,被當時的學者稱之為“新心理歷史學”。作為基本形成體系的“新心理歷史學”,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內容,即個人傳記,家庭史,集體心理史,社會與歷史的重大問題。
在個體心理研究方面,具體的心理分析一旦與歷史人物的研究結緣,便會產生以“心理傳記”為形式的心態史著述,類似於弗洛伊德為達·芬奇所作的傳記。自弗洛伊德進行了首例的歷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後,個體心理的分析與研究開始出現在不同的時代和各類人物中。作為心理史學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強調潛意識的作用;由於人的潛意識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論偏重於人的童年,尤其是過分強調生物性的本能衝動和慾望的作用。這樣的理論在心理史學奠基之初,雖具有拓寬歷史研究領域的作用,但對於歷史人物的行為分析還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學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為弗洛伊德的學術後人,他除了重視人的自我發展在童年期之後的持續性外,他還注意到了整個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他先後出版了《年輕的路德·心理分析學與歷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諦·富有戰鬥性的非暴力主義的起源》兩部著作,“從理論和方法上為心理歷史學開闢了新的研究途徑,成為心理傳記分析的典範著作。”
家庭史
作為心理史學的另一個領域———家庭史,它既與歷史人物的個體相聯繫,又與集體心理相溝通。因此它是處在一個相互交叉的中心領域。不過,心理史學最初對它的關注是源於對於歷史人物兒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稱之為“兒童史”。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會史》和勞埃德·德莫斯的《童年歷史》。
集體心理史
集體心理史,是二次大戰後迅速興起的心理史學新領域。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出現,以及世界各地民族運動與政治運動的興起,二戰后心態史的研究便由個體心理研究轉向群體心理。群體狂熱、民族仇恨以及群眾對法西斯專制的支持等問題,都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如美國著名學者H·阿連德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與其他國家的學者如K·洛倫茨的《論侵略》、N·W·阿克曼和M·傑荷達的《反猶太主義和情緒混亂的心理分析學解釋》、E·西梅爾編的《反猶太主義———一種社會病》、M·伏維爾的《意識形態與心態》、《大革命心態》等著作,是這一時期群體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會與歷史重大問題方面,較有影響的成果有諾曼·布朗的《生與死———歷史中的精神分析含義》,斯坦利·埃爾金斯的《黑奴制———一個美國制度與理智中的問題》,諾曼·科恩的《對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紀與宗教改革時期歐洲的革命烏托邦主義及其對現代極權主義運動的影響》。
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心理史學在對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進行了不斷的揚棄之後,又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研究數量之多、範圍之大都超過以往各個時期。其中以托馬斯·A·科胡特的《德國的影像———對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溫伯格《納粹青年追隨者的46二十世紀中外心理史學概述心理歷史淵源》影響較大。科胡特和洛溫伯格都是接受過心理學與史學雙重系統訓練的心理史專家,因此他們的研究已完全擺脫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論去嫁接歷史事實的套路,主要是以歷史事實說明歷史人物的行為,心理分析理論僅僅作為分析歷史事實時的工具。洛溫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學方法的同時,還藉助於社會人口學、社會統計學的方法,並把文學作品作為參考資料,真正實現了多學科方法的綜合。他認為,歷史學分析應當“同社會科學的模型、人文學者的敏感、心理動力的理論及臨床對心理深層的洞察相結合”。這種五類大綜合研究法,與歷史發展合力論在對於歷史本身的認知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頗耐人尋味的。
中國心理史學
中國史學界介紹、接受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學理論家朱謙之,受孔德、杜里舒和蘭伯列希影響,開始注意史學研究中“心理的方法”問題。他在1926年撰寫的《歷史哲學》中,詳細介紹了西方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關於人類社會的進化,“歸宿在‘知識線’的進化上”,而所謂“知識線”的進化,“又由於人類社會之心理的原因”的理論。認為社會愈進步,心理因素的影響就愈大。同時,他對孔德的心理史學理論也十分重視。認為“從孔德以後,歷史才漸漸有科學的根據,才漸漸去注意歷史事實的‘所以然’”。因為孔德明確指出:“歷史現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來是進步,而從它方面看來,社會的進步又是原於人類的心理。”因此,歷史研究除了“研究社會生活的各種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經濟諸問題———以外,還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從人類心理的現象,去找出歷史的程序來。”不過朱謙之認為孔德歷史哲學有一定偏頗。因為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樣幼稚的時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學的方法以解釋歷史現象,結果只能把歷史現象弄變易,而不能完全解釋它。”“對於蘭伯列希的“歷史為社會心理的科學”的口號,他也給以中肯的批評:“蘭伯列希只把歷史看作社會心理的一個連串,而沒有注意到這個連串背後那種逼促人們實現他進步的‘生機力’,所以還算不得盡歷史的意義。”朱謙之是那個時代生機史觀的代表,因而對現代史學的評判,離不開他生機史觀的價值尺度。
同一時期,另一位著名學者何炳松,受美國“新史學”運動發起人魯濱遜的影響,主張歷史研究是多門學科、多種方法的綜合研究。具體來說,就是“必待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經濟學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馳,以解決此問題。”何炳松所提倡的綜合研究法,對於當時的中國史學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他還專門翻譯了魯濱遜的《新史學》、紹特韋爾的《西洋史學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歷史哲學概論》中,除了對當時歷史哲學的主要流派進行了介紹和評價之外,專門對“心理史釋”作出了論證。他認為,“自人類之心理以至時代之思潮,其影響於歷史及文化之形成,自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然以此為社會歷史之動因,則尚嫌不足。”因此他主張將“心理史釋”作為歷史學方法論中不可缺少之一種,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紀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國史學界在心理史學方面,可以說基本上僅限於在理論上對西方史學理論的譯介和初步的探索,還沒有產生出心理史學理論的系統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學理論的譯介來說,也有相當大局限性。比如法國年鑒學派精神史和心態史的理論幾乎沒有問津,對於德國新康德主義的心理史學也注意不夠。只是由於杜里舒曾來華講學,故他的所謂“知識線”理論———即社會心理推動文明進化的理論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才比較大一些。
作為當時講學社的主要發起人和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創者的梁啟超,對於杜里舒的理論,在肯定的同時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確的闡述,特將精神文明的進化確定在兩個方面:一是“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這裡,就心理與文明的關係而言,足以看出梁啟超對於該問題認識的深度。
民國心理學史
20世紀之初,心理學的引進與傳播主要以教會學校的傳教士為主體,最早開設心理學課程的是山東教會學校——登州文會館。隨著西學東漸的風潮日益盛行,清政府實行了“新教育政策”,這導致促使心理學科以制度化的形式在清末師範學校的課程體系中被固定下來。
進入民國后,心理學知識翻譯和傳播主要由留學生承擔,但多數是個人性質的。到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后,在他的支持下,正式的心理學科的發展開始活躍起來。20世紀20年代,國內各高校紛紛設立專業科系,十餘年間,共有21所院校設立了心理學系(組),此外,一些學校的教育系或教研所建立了心理學試驗室,開展學術研究工作。即使沒有設立心理學系或試驗室的院校也大都開設了此類學課。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心理學發展進入了“學科化”時代。一大批學者學成回國后,在我國高校致力於心理學的建設與發展,很多人在各大學和研究所擔任要職,其中唐鉞和汪敬熙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長,艾偉、陸志韋分別擔任中央大學和燕京大學心理系主任,郭任遠在復旦大學創建心理學院並親任院長。北大的心理學發展更是得到校長蔡元培的親自扶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陳大齊於1917年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後來隨著唐鉞、孫國華、劉停放、樊際昌、汪敬熙、陳雪屏等一批著名留學心理學家的加入,專業教師陣容不斷擴大,培養了諸多後備人才。到1924年,郭任遠受聘於復旦大學,著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心理學院,還向外國輸送了一些心理學留學生。
在這批學者的呼籲下,各大學相機成立了心理學系。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師範學校的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科目在清末時節就已經被規定為必修課,由留美心理學家張耀祥來校任教,使心理學在北師大極盛一時,吸引一部分學子轉向心理學學科。中央大學系南京高師和東南大學前身,南高師時期,留美心理學家陳鶴琴和廖世成就為該校心理學日後發展打下較為牢固的基礎。陸志韋作為“中國現代心理奠基人”,致力於本校心理學學科化發展,還為科學心理學在我國的普及和發展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他組織北京五大學(燕京、輔仁、清華、北大、北師大)每月舉行一次心理學界聯誼會,商討發展大計,還主編出版了《中國心理學報》。
南京大學前身南京高師和東南大學,在南高師階段心理學系就得到了相當的發展,東南大學時期該校心理學系更是為全國最先進完備者,中央大學成立后,在艾偉、潘菽、蕭孝嶸為首的留學心理學家的領導下,該校的心理學事業,尤其是教育心理學得到了長足發展。中央大學成為眾多留學心理學者的首選。
除《中國心理學報》外,1921年中華心理學會成立至1949年,留學生心理學者共創辦了《心理》、《心理半年刊》、《測驗》等十餘種專業雜誌。雖然這些雜誌創辦時間長短不一,但從整體上貫穿了民國心理學發展全過程,對完善學科體制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當時的很多心理學者希望用心理學解決中國的社會實際問題。其中,學術中國化的代表是心理學家潘菽,他認為我們不能把德、美等國家的心理學搬來了事,而是研究我們自己要研究的問題,提倡研究中國實際需要的應用心理學。陳鶴琴、艾偉這兩位留美學者也關注到這一點。1934年,艾偉在南京建立第一所學科心理實驗學校——萬青天才試驗學校,抗戰爆發后,他又轉移至大後方,在重慶沙坪壩創辦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學習心理實驗班。
20世紀上半葉,我國出現過一次“教育測驗運動”,規模很大。參與者認為,通過各種測驗,可以解決當時中國教育改革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某些問題。至抗日戰爭前夕,我國出版或修訂合乎標準的智力與人格測驗約20種,教育測驗50多種;廖世成團體智力測驗;陳鶴琴圖形智力測驗,劉湛恩非文字智力測驗;艾偉訂正賓特納智力測驗;陸志韋與吳天民完成比納智力量表的第二次修訂等。
當時,已有學者認識到挖掘整理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重要性。其中張耀祥可謂開此先河者,1940年他發表了中國心理學史的開山之作《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史略》,系統梳理了我國古代心理學思想和現代心理學起源與發展,並對中國心理學發展提出幾項建議。
但是,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期,各高校心理學系的發展出現了滯緩,一些心理學系招生連年空白,心理學系次第取消。由於辦學經費的緊張、不是顯學的心理學使畢業學生不易於解決生活問題,難有生存發展空間。國民政府教育部變更學制,很多院校心理學系被取消。很多學者只能輾轉遷徙,另謀發展。民國時期高校教師流動性很大,有的心理學者在同期身兼數職,生活不能安定。隨著抗日戰爭的日益臨近,國內形勢惡化,中國心理學發展舉步維艱,一些心理學者仍然在報刊發表文章,爭取社會對心理學的了解、重視及支持,同時堅定同行的決心。由於他們的執著,使心理學研究和教育在中國風雨飄搖的環境下得以生存,為以後心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心理學研究和教育才逐漸走上正軌。
梁啟超關於心理學的認知
關於心理史學,梁啟超在其史學名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中,更有相當全面深刻的認識。這在當時的中國史學界實不多見。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學術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學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選取歷史專題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種都與心理相關。第五種“精研一史跡之心的基件”,講要抓住歷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動,以把握歷史的本質;第六種“精研一史跡之物的基件”,講要研究和把握影響心理活動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第七種“量度心物兩方面可能性之極限”,主要講來自心理方面的主觀認識與其客觀外在條件之間的辯證關係。
其次,在歷史研究中他還強調社會心理對於階級、黨派、民族的重要影響。他說: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復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而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生因果關係者,始能成為史跡……所謂大人物者,不問其為善人惡人,其所作事業為功為罪,要之其人總為當時此地一社會———最少該社會中一有力之階級或黨派———中之最能深入社會閫奧而與該社會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應作用,極緊張而迅速。
另外,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還就歷史事實“予以新意義”的問題,專門談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吾人的動作,一部分是有意識的動作,一部分是無意識的動作———心理學上或稱潛意識,或稱下意識……一人如此,一團體一社會的多數活動亦然。”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對史料獲得新的意義。他以義和團運動為個案,運用了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根源,認為主要是民眾長期以來已經完全無意識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積蓄己久的“排外心理”,與當時帝國主義侵略和清政府的賣國以及戊戌變法的失敗諸原因聚合彙集而成。其實,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梁啟超在他對歷史事實的五種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聯絡法”,與同一時期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法國年鑒學派正在醞釀的“長時段”結構理論十分相似。他說:
許多歷史上的事情,順著平看似無意義,亦沒有什麼結果,但是細細的把長時間的歷史通盤聯絡起來,就有意義,有結果了。比如晚明時代,許多士大夫排斥滿清,或死或亡,不與合作,看去似很消極,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滿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這種死亡,豈不是白死亡了嗎,這種不合作,豈不是毫無意義嗎?若把全部歷史綜合來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結果,極明白了;意義價值,亦很顯然。假如沒有晚明那些學者義士仗節不辱,把民族精神喚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產生還是問題呢。
這裡,梁啟超的“長時段”同樣包含著心理結構的傳承、演變過程在其中。從方法論起源的意義上說,梁啟超的原創性與法國年鑒學派相比,應當說是難分伯仲。因為就考察來看,還未見到梁啟超受法國年鑒學派影響的歷史依據。
中國台灣心理學實踐
心理史學理論真正付諸於具體實踐,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台灣學者殷海光是這方面最早的實踐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運用了文化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對傳統社會與近代社會給予了相當深刻的分析。此後,他以同樣的方法對五四以來的思想文化變動,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他開始注意到“歷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對於五四以來的“偶像破壞”與反傳統的文化現象,注重從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層的分析。他認為:“如果一個文化在迎接科學的時際之‘baseline’(基線)是monism(一元論)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傾向意締牢結)的,那末科學一來,就變成‘科學主義’”,講經濟學就講成了各種各樣的經濟主義。這對於中國近代的社會大變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則顯然是長年以來形成的各種各色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動)。而在(人格)方面則為出於ambivalentcharacter(內在衝突的性格)。”另外,殷海光晚年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同步研究,在運用心理史學方法的同時,他還兼采文化人類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方法,對文革的結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評估。而就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來說,1973年台灣學者黃培在《歷史學》一書中,強調了心理學在史學研究上具體應用的問題。
中國內地心理學研究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陸學者開始接受並使用心理史學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澤厚的《孔子再評價》,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結構”問題,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後來他在《哲學答問錄》中特意作出說明,謂其目的在於區別西方“心理———文化結構”的認知模式:“從文化解釋心理,並認為文化無意識地積澱為心理。所以文化結構與心理結構(具體地說,如思維方式、情感狀態、行為模式、審美趣味等等)密切相關”。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綜論》中,開始嘗試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新編》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魯迅那種“嚴冷”與“炙熱”、苦悶與焦慮的矛盾、緊張、複雜、豐富的心理;進而解釋魯迅筆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
1987年,已故歷史學家謝天佑的《專制主義統治與臣民的心理狀態》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關注,被稱之為“觸摸了千百年來的歷史神經”。後來,謝先生將其擴充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書。如果說從李澤厚、王富仁到謝天佑,他們都是以具體的研究作為心理史學方法範例的話,那麼陳旭麓先生則是從純史學理論的角度強調心理史學方法的重要意義。他在1988年說過:“雖然,中國以往的史書,在記述事實和人物中也可以窺見心靈的跳動,但以存在決定意識為旨趣,著眼對歷史人物和歷史活動的心理刻畫,則是史學領域和方法上的開拓,而剖析人物心態又是推動和激發歷史反思的機杼。”
此外,馬敏的《中國近代商人心理結構初探》、樂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說”的心態分析》、己故歷史學家唐文權的《同盟會倡始時期宋教仁心態研究》等論文,都是運用心理史學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力作。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章開沅在《離異與回歸》這部著作中,將文化社會學的分析方法與心理史學的分析方法相結合,提出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離異與回歸”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國近代的一些文化現象,其中包括耐人尋味的“淮橘為枳”現象;並以此為基礎探索了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變遷的特殊軌跡。他還將文化心理結構作為“社會歷史文化土壤學”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從而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關於重建中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研究的端緒。章先生勾勒出這樣一個線索:“在戊戌維新時期,先進人士比較突出地提出國民素質改造問題,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國魂、國民精神的謳歌與論述,則是前者的延續與發展。這是經過艱苦內省以後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調節,即改進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以適應國家近代化的需要。”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心態的專著問世,如周岩的《百年夢幻——近代中國知識分於的心靈歷程》。1990年代初,中國心理史學以及與心理史學相關的研究已經發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規範化的階段。其顯著特徵是專著和論文的內容覆蓋範圍廣、數量多,而且論題所涉及的層面大多具有開創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鄉土意識》、羅宗強先生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樂正的《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朱義祿的《逝去的啟蒙——明清之際啟蒙學者的文化心態》、張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心態錄》和趙伯陶的《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等書相繼問世。其他史學專著中關於個體心理、群體心理和社會心理以及區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論述也不在少數。如李良玉的《動蕩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書,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各類知識分子心態的進行了甄別,朱英的《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一書,對於近代中國商人的心理結構、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唐力行的《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對於中國近世商人群體心態演變與整合作出了精闢的論述;李長莉的《先覺者的悲劇》一書,關於洋務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給以綜合性研究;馬敏的《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迷》一書,關於中國早期工商資本家和新式知識分子過渡型心理特徵進行了詳細而縝密的分析;李文海先生《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一書,對於義和團運動時期的社會心理給以全面的解剖;等等。真可謂見仁見智,新見紛呈。在歷史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中,運用心理史學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數量更為可觀,限於篇幅,不再贅述。“心態”已成為史學研究的常用術語,“心態史”或“心理史學”,也基本上成為一個新興的前景廣闊的研究領域。台灣著名學者張玉法先生所說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歷史”的說法,基本上已成為史學工作者的共識。
心理學的研究方向
自進入又一個世紀以來,從心理史學的研究情況看,己不僅僅是過去那種心理學與歷史學的簡單結合,它正逐步吸收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以及倫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向著以心理與歷史為主、同時綜合多種學科方法的“大綜合”的方向發展。而歷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學理論也已達七、八種之多,如生理心理學、差異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動機心理學、知覺心理學、人格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因此,心理史學已成為多學科研究方法相互滲透與融合的綜合性學科。這種綜合性研究,由於認識途徑、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史學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人們可以藉助於新方法、新途徑的優勢,將分析、研究的觸角深入到過去研究無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歷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現歷史的真實感和歷史人物思想的豐富性。同時,人們也可通過思想與社會之間的中間環節———社會心理,來把握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的內在動因和變化信息。